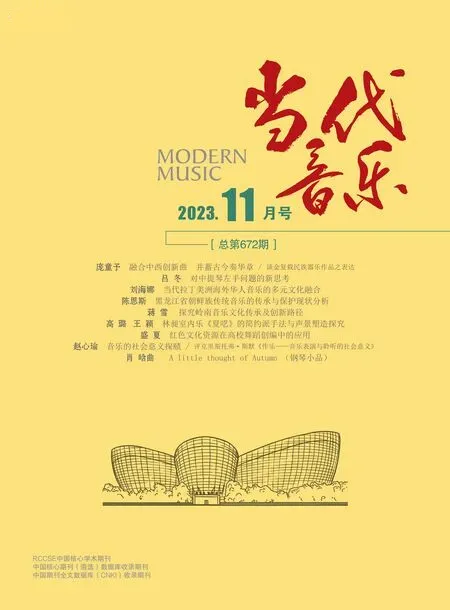音乐的社会意义探赜
——评克里斯托弗·斯默《作乐——音乐表演与聆听的社会意义》
赵心瑜
由新西兰音乐学家克里斯托弗·斯默 (Christopher Small, 1927—2011) 撰写的 《作乐——音乐表演与聆听的社会意义》 (以下简称 《作乐》) 一书由中国音乐学院康瑞军教授和上海音乐学院洛秦教授翻译、 引入中国。 它不仅是一部音乐人类学、 音乐社会学、 音乐美学相结合的跨学科著作, 而且其中提出的众多别具一格的音乐观点和理念, 为探索音乐文化阐释的可能性提供新路径。
《作乐》 一书共有十三个正式章节, 又分别有前奏、三个间奏、 尾声穿插其中, 运用对位式结构巧妙建构起极具音乐性的篇章架构。 该著作以音乐表演与聆听活动的要素为基本骨架, 将音乐厅、 音乐会、 参与者的社会关系、 音乐会聆听过程、 音乐会礼仪、 表演过程、 音乐价值等方面作为主线, 论述 “作乐” 的内涵及背后蕴涵的深层次社会、 价值观原因, 对音乐的社会意义进行了“重新发现”, 厘清脉络, 旁逸伸展。 尾声是从启蒙教育、 学校教育的角度指出我们需要为音乐活动创设人人参与的社会环境, 使社会进步、 社会 “音乐化” (musiclizing)。 纵览目录就好似已然置身于音乐厅之中, 斯默如一位导赏者, 以代表资产阶级文明产物的交响音乐会为例, 向众人揭示音乐表演与聆听的社会意义。
长久以来, 人们的传统音乐观念是将音乐作为一种产品, 研究音乐活动中关注的产品 (音乐作品)、 产品生产者 (作曲家、 演奏家) 以及产品消费者 (听众)。然而, 斯默创新性地运用 “musicking” 这一单词, 意在将名词 “music” 辅之以动词, 接近于 “to music” 制作音乐的意思。 《作乐》 的中译版将 “musicking” 翻译为“作乐” 二字。 斯默对于 “作乐” 的解释是: “尽己所能地参与音乐表演, 无论是表演、 聆听、 排练、 练习、为表演提供素材 (作曲)、 舞蹈等都属于这一范畴”。[1]甚至斯默认为对音乐活动本质有贡献的人员均算入其中,如检票员、 钢琴搬运工等。 这些音乐参与者通过他们的行为与相互间在特定音乐空间中形成的种种关系, 持续不断为音乐表演活动注入意义。[2]
笔者在阅读原文与相关书评后将其理解为: “musicking” 是一种人类作为在社会中拥有多重身份或相互冲突的群体成员所参与的、 与自我定义密切相关的音乐活动[3], 即作乐也可被宽泛地理解为参与音乐实践。 作乐并不是一个完成时, 不是孤立、 静置存在的, 而是一个众人参与的动态运转的社会性活动。 究其实质 “作乐” 能够帮助我们透过 “作乐” 现象看待社会本质, 更好地理解社会关系。 这一学术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使我们将静态的音乐看作一种动态的过程, 把我们忽视的一些参与音乐实践的个体、 个体间的社会关系都纳入音乐活动范围内。 这能够帮助我们扩展探寻音乐社会意义的视野与范围。 本文试图从以下几点评述该著作的独特新颖之处。
一、 以西方交响音乐会为线索,对“作乐” 社会意义的批判性探寻
音乐活动一定具有社会意义吗? 音乐社会学家阿多诺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 认为社会是艺术的本源, 音乐不可能置身于社会之外, 音乐的内容、 形式都是指向社会的。[4]斯默同样肯定了音乐活动的社会意义, 认为音乐的社会意义实质上是人为赋予的。 与音乐相关的一切, 大到整场的音乐会, 小到音乐会的某位听众、 演奏的某首作品都是一种社会行为, 都具有社会性、 认知性。 在阿多诺看来, 社会意义是通过离间的方式体现, 而离间的本质是对社会的批判与否定。[5]极其相似的是, 斯默以西方交响音乐会为线索, 对“作乐” 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对指挥家、 作曲家等拥有 “绝对身份” 的人的过度敬畏与依赖及其背后彰显的不言自明的规则、 秩序扼杀了音乐审美主体的创造力与表现力, 同时也使音乐本身更趋向于僵化, 而缺乏多样性。 书中 “谦逊的鞠躬” 一章运用反讽的语气, 描写了表演者在舞台上的绝对地位。 其中指挥被看作现代音乐的权力化身, 不仅仅是整个乐队的总枢纽,而且还在观众心目中扮演英雄性的角色。 斯默认为指挥家卡拉扬有着程式化的专业性与逐利性, 以他为代表的表演者在音乐界有着绝对的权威与人脉网络, 这使得音乐的表演隐隐之中已经按照这类表演者心目中的理想范式而呈现。
西方社会极其重视交响音乐会。 交响音乐通过主题的发展表现了复杂的冲突性与对比性, 而交响作品的结局一向是调性的回归、 矛盾的解决, 这揭示着作品宏伟、 深刻的内涵与资产阶级话语权问题。 这也正应合了斯默在 “社会建构出的意义” 一章中提出 “交响音乐会的这种作乐方式, 是西方工业社会中产阶级崛起后用以表达其价值观的一种现代现象”[6]的观念。 当今以交响音乐会为代表的西方音乐, 是蕴含着当代工业界或科学世界观所催生的价值观, 它们为资产阶级服务, 试图从确立社会政治生活规范的精英阶层获得认可。[7]
斯默对于西方交响音乐会的批判态度是明确的。 书中最后一章专门对非西方音乐进行翔实阐述, 与对音乐会的表演范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加凸显了对西方交响音乐的批判性观点。 书中以非洲笛子手为例, 描写了非西方音乐中也同样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 非洲笛子手一边放牧一边吹笛子这一 “作乐” 活动, 隐含了笛子手对社会群体的变化与传承、 稳定与不稳定、 守旧与革新等因素彼此间的复杂关系的调解。[8]这种 “作乐” 活动的社会意义能够维持群体之间的关系, 斯默认为这是西方交响音乐会所不能企及的。
作者以社会建构的角度将音乐视为一种仪式的形式, 通过这种形式, 社会关系或意义被制定、 维持, 并在理想状态下被争论。[9]西方作乐范式历经百年而经久不衰, 这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对他们的价值观作为持久生活内容的信念的肯定, 由于整个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受到了太多的冲击[10], 音乐会作为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的稳定仪式变得尤为重要。
二、 以跨学科视角为基础,对“作乐” 社会意义的多维度研究
对 “作乐” 的社会意义研究不仅是新颖独特的, 也是翔实全面的, 这离不开跨学科的视角。 学科融合运用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研究单一学科的盲点区域。 斯默拥有着广阔的学术成长背景, 在人类学、 生物学、 哲学等方面均有所涉猎。 他以跨学科视角为基础, 对 “作乐” 社会意义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
(一) 音乐人类学视角
长期以来, 史学的研究方法是西方音乐研究的主要传统。 随着各门学科的发展, 多种研究方法的介入拓展了西方音乐研究的某些领域。 《作乐》 一书具有浓厚的音乐人类学理论基础。 音乐人类学主要研究目前存活着的音乐事项, 旨在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来揭示其在人类生存、 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11]音乐人类学研究非欧洲的音乐现象是人们的固有认识, 但斯默恰恰运用这种方式研究音乐社会学、 欧洲古典音乐, 甚至是古典音乐中的重中之重——交响音乐。 《作乐》 正是广泛运用了音乐人类学的方法, 拓宽了我们研究西方音乐的视野, 比如斯默在描写音乐厅、 指挥家、 曲谱等方面时, 着重刻画了音乐厅场所的变化、 布景与装潢的华丽等细节, 采用了“田野考察” 的方法, 探查不同的音乐厅、 音乐表演环境等实地, 旨在研究音乐场景对群众的音乐活动所进行的约束, 以此探寻“作乐” 的社会意义。
《作乐》 正是将音乐聆听活动的每一个因素都按照音乐民族志、 “田野工作” 的方式进行记录, 它包括“作乐” 的细节、 人与人之间的交谈等。 聆听音乐的方式是结构性的, 是民族音乐学结构范式、 方法的应用。近年来, “田野” 的概念逐步在发生变化, “田野” 的边界在不断扩展。[12]《作乐》 一书中没有乐谱, 缺乏实例论证。 更强调阐释与思辨, 甚至连脚注都少之又少。 这是斯默对于所观察到的音乐现象进行的微观描述的研究方法。 由于此书在内容上叙述语言通俗易懂但又不乏学术性, 且未深度涉及音乐理论、 音乐专业概念术语等专业知识, 因而它不仅适合音乐专业的学者也适合普通的音乐爱好者。
《作乐》 采用共时性视角研究 “作乐” 中主体间的互动, 如表演者与观众、 观众与观众、 观众与作曲家等。 这种互动打破了各自的空间界线而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 “作乐” 活动。 这种共时性促进了参与者探寻、 确认、 展示社会关系并通过共时性音乐形态和社会关系的能动建构探寻音乐表演与聆听的社会意义。 书中以交响音乐会为范例, 揭示了社会性的文化现象, 是“通过音乐走向文化” 的典范。 在文中传统音乐社会学视角已然被音乐人类学所替代。 对音乐的研究已经从“社会决定论走向人类学”。
(二) 生物学视角
斯默拥有生物解剖学的知识经验, 在 《作乐》 中也不无体现。 在 “生物学的姿态语言” 一章中, 斯默总结了人类学家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 理论的精华之处,认为生物界拥有独特的一套信息传递体系, 这与人类的精神世界、 人类的社会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也隐喻着音乐的社会意义。 信息的接受程度影射了生物的生存状态、 姿态语言进而体现在人类社会中。 斯默认为这种信息的传递经过人类社会千百年的发展, 已然演变成一种交流模式, 即 “仪式”。 笔者将其看作 “作乐” 活动的雏形。
音乐作为社会生物存在的意义是多种多样的, 通过声音认同族群对动物和人进行社会意义的探寻是其中的重要意义之一。 斯默通过生物学的视角肯定了作乐的形式。 通过生物学视角研究音乐活动, 可以用广阔的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思维重新审视音乐。
三、 以音乐表演研究为中介,对音乐社会意义的深度挖掘
近年来, 音乐表演问题已成为音乐理论研究的热点。 笔者选取 《作乐》 中几个较为新颖的表演问题, 在此进行探讨。
(一) 对音乐姿态语言的研究
《作乐》 中斯默在 “戏剧性的艺术” 一章中着重论述音乐表演艺术, 他的音乐姿态语言 (music gesture)内涵丰富。 从表演者的角度, 在音乐表演过程中, 可以从音乐姿态语言中的音响生成姿态与音响辅助姿态[13]等方面反应表演者对作品的认知与领悟。 斯默认为, 通过这种姿态语言的极具个性化的诠释, 音乐的社会意义可以得到揭示。 书中以戏剧表演艺术为例, 斯默总结了歌剧中常常出现的两个主题: 性别主题与英雄主题。 这两种主题以歌剧的方式隐喻着当今社会的一些特定关系。如一些女性的角色刻画不仅多伴随着半音化的主题动机, 以彰显女性的阴柔、 妩媚的形象特点, 而且在姿态语言上表演者要尽量贴合形象特点。 通过表演者姿态语言的演绎, 揭示了社会的性别问题。 斯默认为上述的女性形象根深蒂固, 这种固有观念如果被颠覆, 会造成社会失序。 以歌剧为媒介, 社会危险得到了戏剧化的呈现。[14]社会中存在的部分问题, 在舞台上得到了呈现。呈现的重要方式之一, 就是音乐姿态语言的有意设计与表达。
在音乐表演的实践与表演互动过程中, 姿态语言是动态的、 开放的, 不是预设的或预先确定的。 由于不同的期望、 不同的环境以及参与表演的不同群体, 参与者的关系会随着每一场特定的表演而有所不同。 对关系作出反应或在关系中进行互动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15]《作乐》 中对音乐姿态语言内涵的研究为音乐表演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路径。
对音乐姿态语言的解读是实现 “作乐” 的途径之一, 它将具体的音乐形式、 社会历史文化和审美旨趣三者间建构出令人信服的有机关联。 斯默在罗伯特·哈腾(Robert S.Hatten) 的基础上创新运用了姿态语言, 将其与音乐表演和社会关系联系起来。 斯默认为, 社会关系根植于一种姿态语言, 比如眼神交流、 声音变化和身体动作。 人类通过这些姿态互动进行最有效的沟通。
(二) 对 “本真演奏” 与音乐作品的新看法
对于 “本真演奏” 的理解, 笔者主要依据于彼得·基维 (Peter Kivy) 总结的四维度: 忠实于作曲家意图的演奏; 忠实于作曲家时代表演音响的演奏; 忠实于作曲家时代表演实践的演奏; 忠实于表演者原创性的演奏。[16]斯默不赞成 “历史本真表演”, 他认为本真演奏运动近年来如此盛行的原因之一是音乐经纪公司为谋取高额利润的新的营销手段。 他们塑造一种 “本真音乐” 的理念, 使人们追求一种新的体验, 有一个新的噱头, 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行为。
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去表演音乐? 《作乐》中对于音乐表演水准问题的看法是独具特色的。 斯默认为在 “作乐” 活动中, 评判表演水准的标准取决于表演者能否在音乐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尽力表演。 尽己所能地、 全身心地参与音乐, 因此要摒弃 “历史本真表演”的标准束缚。
斯默认为音乐作品不是 “作乐” 的全部。 斯默意在突出表演者的主体地位, “在演出中, 个人的孤独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剥夺, 而是充分享受和理解正在演奏的作品的必要条件”[17], 音乐表演不是为了呈现音乐作品而存在的, 音乐作品的存在是为表演者提供表演的内容。音乐作品的社会意义只有通过表演才能被呈现。
斯默反对西方音乐会的具体化的社会习俗和传统,认为某些固定的范式束缚了表演的发展。 音乐表演应该拥有比现在更加重要的地位, 它不仅仅是作品的阐释者, 每一次表演都应有着独特的内涵与灵魂。 因为在斯默看来, 音乐表演是一种社会行为, 音乐表演是服务于表演者和听众的。[18]音乐表演具有创造性与独特性。 斯默承认音乐表演过程中无处不在的各种社会关系, 但他旨在发扬一种纯粹的表演方式, 以此解构音乐表演所带来的世俗性影响。 斯默的关注重心并不是在音乐本身,而是基于对社会的认识与理解, 他将音乐表演与社会关系有机关联, 音乐的功能性隐喻在音乐背后的社会关系。 因此, 音乐表演中更多地关注文化因素才能更好地探寻音乐。 通过音乐表演表达音乐, 在音乐中寻找、 探查个体的完整性与意义。
结 语
收锣罢鼓, 作乐的意义何在? 正如本书的译者康瑞军所言, 斯默阐释 “作乐” 活动的目的之一是从西方交响音乐会的音响形式来批判隐含在其背后的中产阶层文化垄断, 并试图将音乐表演和聆听行为阐释为更加丰富、 普遍的理想社会关系建构活动, 最终消解西方严肃音乐的话语特权。[19]音乐表演中的种种关系以隐喻的方式存在于人类社会之间, 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各种欲求和信仰的生动写照。
斯默以音乐的现场表演与接受者的聆听作为研究对象, 强调作乐与社会文化因素对于音乐和人类发展的重要影响。 注重音乐的演绎分析 (不同演奏者对于同一部音乐作品的不同演绎与表达)、 传播分析 (同样的音乐作品在不同演奏空间与地域的差异性传播效果) 与受众分析 (同样的音乐作品在不同背景的听众中的反响与反馈)。 “作乐” 颠覆了众人对音乐表演是反映作曲家思想; 音乐的意义是陶冶人们情操; 音乐会秩序的产生是由于不安静会影响表演者状态等等的固有审美经验。 这都是我们以前不假思索、 惯性认知就会回答出来的诘问, 但该著作带领我们重新审视音乐活动, 探赜音乐表演与聆听的社会意义。 音乐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可以使人们流连忘返, 并通过 “作乐” 形式实现人们的目的与价值。
尽管如此, 笔者认为, 书中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在音乐表演研究中, 对表演者的技术性、 技巧性只字未提, 只关注表演的投入程度。 另外, 揭示音乐的社会意义还可更加透彻。 斯默仅以西方交响音乐会、 音乐厅等对象为例, 揭示某一行为、 某一阶级的社会关系建构活动, 认为它反映的是人与音乐、 指挥家与乐队、乐谱与表演之间的一定的复杂社会关系, 但其成因的深层内涵并没有揭示。 除此之外, 笔者认为, 斯默将 “作乐” 活动与社会、 政治联系是较为极端的, 音乐的表演范式不仅是社会的反映, 也与音乐的表现形式、 音乐表演的历史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不过总体而言, 《作乐》 一书为我们理解音乐表演与聆听的社会意义拓展了新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为拓宽音乐研究领域、 促进音乐的跨学科研究与学科融合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