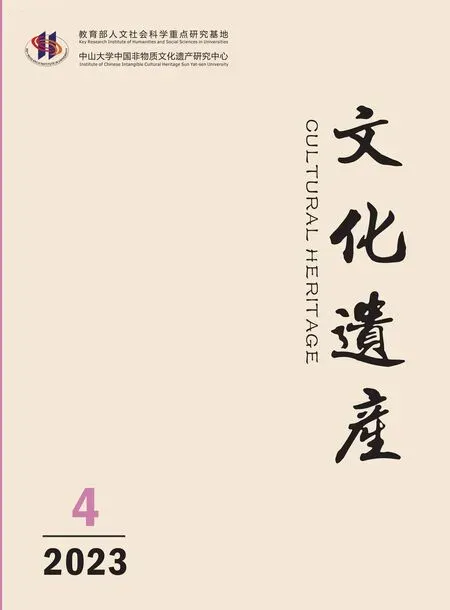董其昌“密码”和顾绣的转向
刘森林
晚明以来纷繁的话语构成了上海顾绣的历史进程,其亦绣亦画的技艺和绣画融合的风格成为有明一代的典范。其中,董其昌的禅悦、画学思想和价值指引对顾绣的影响深远。寻绎董氏影响、引领顾绣演进的“密码”,一为文献,二是传世实物。前者主要蒐集于《容台集》“崇祯三年本”、重梓“崇祯八年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明末《容台集》“二十卷本”。广泛流布的《画禅室随笔》善本有汪汝禄序本、大魁堂本和戏鸿堂本,以上版本虽驳杂,但大体不出崇祯诸文本的范围,(1)谢巍:《中国历代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370页。以上各版本未收董跋《韩希孟绣花卉虫鱼册》(下称《花卉虫鱼》,上海博物馆藏)、《顾韩希孟绣宋元名迹册》(下称《宋元名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后者包括《花卉虫鱼》《宋元名迹》在内,既是流传有序的传世实物,也是1989年上海松江《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上海《董其昌研究文集》和2008年澳门艺术博物馆《南宗北斗——董其昌书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未涉顾绣的渊薮。2006年顾绣入列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后,2007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海上锦绣——顾绣珍品特展》,在成果汇集的《顾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数十篇文章引录了1636年董题《花卉虫鱼》跋,却没有文章对题跋的具体内容进行读解和阐释。此后数百年来,所有关于顾绣的文字均皆无涉此跋的读解,从而形成了董氏引领顾绣这一事实认知的盲点。基于此,本文拟就董其昌与顾族互动、董跋的画学史观、知识谱系以及对顾绣形而上言说的内涵进行解析和论证,期能揭橥顾绣题材变化、援画入绣的萌蘖、勃兴和趣味转向的脉络与关节。
一、董其昌与顾族的互动
织绣助耕是古代自然经济模式的常态,先秦桓公说“一女必有一刀、一椎、一针、一鉥,然后成为女”。(2)管仲:《管子》卷二十四,房玄龄注,《文澜阁四库全书》子部第3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0页。揆诸宋崇宁三年设文绣院,南宋华亭人朱克柔于织机融丹青、以缂仿画,其作《莲塘乳鸭图》雌雄双鸭浮游新荷绿苹间,白鹭、花草色泽雅丽;元人管道昇援画入绣,针黹绵递。明代以降江南刺绣以官营系统为荦荦大端,(3)孙珮:《苏州织造局志》卷3,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4页。民间异彩纷呈,浦江人倪仁吉“染色既工,运针无迹”;(4)王崇柄:《金华献征略》卷1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64页。薛素素“手绣大士,精妙之极”;(5)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4,屠友祥校注,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316页。上海顾绣隆誉海内,“顾太学家,姬侍多工善绣,擘丝细过于发,翎毛字画无不精好,天下称曰‘顾绣’。(6)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21,上海市松江区地方志办公室(内部资料准印证96)1998年,第426页。嘉、万后话本、言情、典故、画谱剞劂兴盛,刊刻的粉本赋能针黹工艺、形式和材料的拔新:松江“组绣之变”绒线和刻丝“用劈线为之,写生如画,间有用孔雀毛为草虫者”,近绣“素绫装池作屏”“堆纱作折枝”;顾绣斗方“作花鸟香囊,作人物,刻画精巧,为他郡所未有”。(7)陈继儒:《崇祯松江府志》卷7,徐乐帅、曹光甫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1页。顾绣“团体型”模式在突破技艺经验传授层面中,跳脱出疏于交流的窠臼,也规避了沉湎于技精于熟的自足。顾名世1568年在尚宝司丞任上谢政后修建露香园,其伯子箕英,号汇海;仲子斗英,号振海。前者讲求生活艺术化,后者工诗擅画,昆仲同莫是龙、董其昌、陈继儒等友善,藉助诗社、文会、雅集、游园、翰墨、鉴藏、品藻、馈赠、赞助等艺术活动,建构了丰姿粲然的文化场景,顾族女眷无时迫的追求、无迭宕之虞的技艺磨砺在品藻吟诵、唱酬交谊的氛围中脱颖而出。
董其昌先后问学莫如忠、陆树声、韩世能诸师长,自称法书于率意中得秀色,山水渊源董、巨、二米,以黄、倪为模范,在16、17世纪画坛行、利两派的先分后融中,高屋建瓴地凝练出禅、画分南北的重大理论建构。平实而论,董并没有对顾绣进行系统的阐述,归纳其话语、题跋、馈赠、画论,其思想境界、价值取向、艺术观念和审美趣味约略体现如下:
(一)绣佛。在由来已久的绣佛艺事中,唐太宗以萧瑀好佛道,“尝赉绣佛像一躯,并绣瑀形状于佛像侧,以为供养”;(8)刘昫:《旧唐书》卷63,《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2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74页。早在诸生时,董与达观法师交往后沉酣内典,参究宗乘,“复得密藏激扬,稍有所契”,(9)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四,叶子卿点校,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17页。嗣后又同憨山、达观、莲池、苍雪禅师相知,额其“画禅室”;1577年丁云鹏为顾氏青莲宇绘制白描《十六应真像》,就在董寓。(10)董其昌:《容台集》别集卷四,邵海清点校,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706页。他在及第前说,“吾邑顾太学家有针圣,绣此‘八骏图’,虽子昂用笔不能辨,亦当代一绝。余每劝太学,令多绣大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因,正如秀铁面说法耳”。(11)董其昌:《容台集》别集卷四,第712页。“每劝”云云说明非仅一次——北京故宫院、上博分藏“皇明顾绣”绣章和每套18页的《十六应真册》,庶可坐实。
(二)题跋。董跋传世实物《弥勒佛像》“于一毫端观宝王刹,向微尘秉转大法轮,董其昌书”,(12)《顾绣弥勒佛像》无款无年月,纵54.5公分,横26.7公分,辽宁省博物馆藏。他也深信凭一己之力,能够推进画之法轮的转动;上述的《八骏图》约题于1588年,以及1634年跋《宋元名迹》、1636年跋《花卉虫鱼》等,表明题跋着力于题材的抉择和丹青趣味的引导。
(三)馈赠。1632年董馈《东山图卷》跋曰:“东山图,有赵伯驹粉本。海上顾氏多绣工成此卷,儿子权持赠肖莪(程绍)大中丞年丈,望为苍生一出。观图中大类宋子京,围红袖,写乌丝,得无耽此乐事,非中丞公忧之素否?”该卷援东晋谢安“东山再起”典,劝程氏为黎民计出仕。将顾绣馈赠友朋表明,董氏已认同顾绣非寻常之作,也洩露了顾绣以粉本为模范的事实。
检视董与顾族的互动,大致裹卷在四种情分中:董从上海占籍至同府的华亭,与顾族同府更为同县,此为同里情;汇海与继儒缔为义兰交,其昌与后者友情长达六十余年,显示故人情者,有董撰《寿顾汇海文学》为证;(13)董其昌:《容台集》诗集卷四,第122页。所谓师生情,指的是寿潜绍董学画——他作为汇海的第五子,视董为师长,而为师的其昌,自然也倾力指点弟子画学中的迷津 ;寿潜师董丹青,是为艺坛的同道,此属艺道情。董氏对顾绣持续的揄扬、鼓励和批评,蕴含着建构绣画融合主线的深邃内涵。
首先,欲摆脱女红故径,唯有问学、向艺、入禅、提升境界,且看董氏画学宏旨与刺绣之间一而二、二而一的逻辑:“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可以学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唯有力行“两万”,气韵遂自生;反之,“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14)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四,第51、66页。寿潜无力山水,未必不是“两万”欠乏的因果。其次,高悬标杆。管道昇书、画、绣兼擅且精,南京博物院藏其绣《观音像》,但见观音大士身披长袍,跣足而立。大风鼓涌鬓发衣角,静穆端庄的大士岿然不动;右手执腕于前胸,左手盘串佛珠好似祈祷状。董题《墨竹图》称管氏所作属“卫夫人后无俦……又似公孙大娘舞剑器,不类闺秀本色,奇矣,奇矣!”(15)董其昌:《容台别集》卷四,《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517页。复跋管绣曰,“余见山庐绣佛图,亦工山水。今复见此佛像及小楷,皆有法度,虽文敏续书数十行,无能远过也。”(16)陈继儒:《崇祯松江府志》卷56,第1108页。董以管氏绝艺为指针,旨在激励顾眷的内生动力。
二、赏鉴家与刺绣
崇古和摹古之风弥漫于明代文坛始终,虽然归有光、徐学谟、程嘉燧和公安派等戒除俗学、力革流弊,然前、后“七子”的影响非一时之深。嘉、万间交错的正统异端、守成创新等矛盾和冲撞,成为文化模式变革的先兆,彼时江南赏鉴家大都奉宋代刻丝和刺绣为圭臬,昆山人张丑说:“姑苏吴氏文顒宋绣暨沈氏子番、朱氏克柔刻丝八帧,其间山水、树石、人物、花鸟种种,精妙罕俦,足称针绝、丝绝。”(17)张丑:《清河书画舫》,《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2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15页。其父以为,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待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谗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生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18)张应文:《清秘藏》,《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7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16页。在今不如古的认知和话语言说中,异军突起的顾绣赢得了士林的交口赞颂,竟陵派代表人物谭元春1619年于南京获赠顾绣佛图,但见画面中17尊佛像,联同水面涟漪、岸边绿植和仙鹤,构成了神境佳景,其《顾绣歌》“有鹤有僮具佛性,托汝针神光明映”的赞美,和美仑美奂的绣艺跃入眼帘。此外,谭另有诗作如《绣关帝君像赞》《颂》等,(19)谭元春:《谭元春集》卷四、卷二十九,陈杏珍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2-133、804页。对顾绣赞誉有加。还有湖州人凌义渠,1634年受谭元春馈赠绣佛后赋歌曰,“大士幻身藏指尖,一丝飄断一丝黏”;(20)凌义渠:《凌忠介公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3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3页。松江人陈子龙1639年应希孟儿子之倩,跋《花卉虫鱼》曰:“宋人有发绣、丝绣,如阿房宫、滕王阁今皆架画,触棱尤易结构。若韩媛花鸟草虫,生气劻动,五色斓发,即薛夜来、苏蕙兰未能妙诣至此,或天孙织锦手出现人间邪?旅仙为上玺龙海先生文孙,诗坛、画苑,最称擅长。其俪韩夫人,不减松雪翁之有管道昇矣……岂灵汉机丝,又不知有蜀江水濯出奇丽也……”(21)陈子龙题跋:《韩希孟绣花卉虫鱼册》,上海博物馆藏。首句从宋人用发、丝绣阿房宫、滕王阁类界画,至明代架画历史的维度展开,界画横平竖直,形质清晰,于刺绣而言易于掌控图式结构。作者以为,三国薛灵芸、十六国前秦的苏惠所作,也不能同韩绣的生气、五色无界至无限真,乃变幻莫测的“妙诣”相颉颃;疑问式天孙织锦的运用,不啻强化了前句。天孙,织女星,题跋借喻韩氏巧于织造的仙女。颈句述寿潜身世,复将韩比附女史管氏。再次,作者称观绣后不作唐代蜀女薛涛的绮丽之想。陈氏之跋援典故、传说、史事、艺坛轶事,信手拈来的叹赏咄咄,在反诘士林今不如古的史观和趣味认知中,试图建构女性工艺知识谱系,以证女学的渊源和韩绣的价值。
相对陈跋古今比照的揄扬,张淑瑛层次细密、逻辑递进的话语既趋于具体化,又在诸要义中揭示了女红形而上的精尽之微:“一之品,二之图,三之法,四之质,五之器,六之供,七之忌,八之候。”一品是“刺绣须蕙心妙质,静女、文姬及风神萧远有林下风气者”,必当具有纯美内心和美好气质,好比娴静之女,抑或文姬般,甚或神韵潇洒逸致、有林下风度之人;二图是“绣佛外,则洛神、龙女、绛树、青琴,他如楚江秋、汉宫春晓、滕王蛱蝶、裴家鹦鹉、并蒂芙蓉、七十紫鸳鸯、碧云、断雁、绮石、红蕉皆其选也”,这是作者胪列的唐宋刺绣题材佳者、范围及边界;三法为“度针欲轻重,如书法之错落;结线欲疏密,如画家之写生,庶非女红。”(22)张淑瑛:《刺绣图》,秦淮寓客《女史》,王金玲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3页。也就是说,运针也好,落针也罢,均应轻重有别,要如书法般错落有致,并内含秩序;在线的分布上,宜疏中含密,密中见疏,好比画家的写生;至于从女红上升到艺术高度或审美的境界,又非擅绣者均能有所成就。无独有偶,数十年前“后七子”领袖王世贞洞悉以往凡织绣艺事汲汲于技巧的窠臼,在刻丝、刺绣的议论中,高扬“画趣”的宏论:
宋刻丝仙山楼阁颇精工,而不甚得画趣,盖宣政间装经像函物也……高皇帝初禁人间,不得蓄技巧,一时妙迹永绝。诸君以为叹?……今人间盛行新刻,或故令揉涴成旧,以索高价,然亦不难办也。(23)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137,《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22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5页。
开篇点题宋刻似函物而未得画趣,回首明初禁绝尚巧,针对新刻仿旧牟利的取向,王不以为然。虽然所论刻丝,但同刺绣主旨大致无二,寥寥数语折射出王氏所论蕴含的文化史意义;“趣味”命题的提出,不仅蕴含着批评意识,而且孕育了概括山水画发展中五次风格的演变,(24)王世贞:《新刻增补艺苑卮言》卷12,《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5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3页。影响了嗣后董其昌南北宗画论的建构。
三、董跋的“密码”
有人说董氏从少量古画中创造出一种绘画学说,堪称绝无仅有,誉为“艺林百世大宗师”。实际上这并不针对创作书画而言的,“而是针对作为批评家的董其昌的恰如其分的表现”。(25)古原宏伸:《晚明的画评》,《朵云》编辑部《董其昌研究文集》,李天译,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842页。可见,从第一代缪氏“人以绣传”到韩氏“绣以人传”的嬗变,暗含着董的“密码”。 且读1636年他为《花卉虫鱼》题的跋语:
韩媛之耦,为旅仙,才士也。山水师予,而人物、花卉尤擅。冰寒之誉,绣采绚丽,良丝点染精工,遂使同济不能望见颜色。始知廓景纯三尺锦,不独江淹梦中割截都尽,又为女郎辈针锋收之。其灵秀之气,信不独于男子。观此册,有过于黄荃父子之写生,望之似书画。当行家迫察之,乃知为女红者,人巧极,天工错。奇矣!奇矣!(26)董其昌题跋:《韩希孟绣花卉虫鱼册》,上海博物馆藏。
读解此题跋,应契合于历史情境,只有理解人物身处历史的现实环境,方有可能理解、认识昔时人、事、艺的脉络和关节。因此,阐释需要回归原典,这是“解码”的前提。首先,“山水师予,而人物、花卉尤擅”句,说寿潜绍董山水,却长于人物、花卉这两类董基本不染的题材,约等于舍难取易。好比今人调侃画家技艺平平,辄聊称为音乐家中画之佳者,而在画家中,又是最擅音乐者,其理一也。
其次,援引南北朝江氏夜梦张景阳、所借锦缎被夺的“江淹梦锦”典,暗喻才思枯滞的“江锦割尽”意,反衬“为女郎辈针锋收”的“绣采绚丽”“点染精工”——俟韩绣甫出,同济颜色遂被遮蔽。
复次,“有过于黄荃父子之写生”句。五代后蜀画家黄荃集诸家之善成一家法,绘异卉珍禽的轻色染成之“写生”,钩勒精致而难见笔迹。后人将其与徐熙并称为“黄家富贵,徐熙野逸”,是为五代、宋初花鸟画的两大流派。黄荃及仲子居寀“钩勒填彩,旨趣浓艳”的画作格调,同宫廷之好尚若合符契,成为翰林图画院取舍图绘的程式;倘将北京故宫院黄筌《写生珍禽图》、台北故宫院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同《宋元名迹》《花卉虫鱼》比较的话,前者源自写生,后者摹于粉本,取法的高低已决定了韩难忘前者项背的端倪。据此可知,董意盖属嘉勉——好比家长给孩子起名国梁,并不代表日后就是经世大材。
再次,“行家”。元初钱选、赵孟頫的“行家(职业画家)画”和“隶(戾、利)家(业余画家)画”的“行利”之辩,是一段著名的对话。前因是苏轼提出“士夫画”后,良作被视为有“逸气”,而钱以为,士夫画就是业余画,如此直白的回应使赵氏难以认肯;赵遂收缩在士夫画的范围内界分“行家画”和“利家画”,从而转移了两人讨论的概念和范围。(27)曹昭:《格古要论》卷上,士夫画,《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177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0页。在苏轼、米芾、赵孟頫盛名下的明代利家画,已迈越了虽擅技巧但少内涵、虽形似而含匠气的行家画;迨至董氏更易士夫画为文人画后,遂在禅悦中将画史凝练为南北两宗。
最后,作为古代社会德、言、容、功之“功”的表徵,女子普遍长于既是生产也是生活内容的女红,所谓“当行家迫察之,乃知为女红者”,是指职业画家细察韩绣后以为女红,系“人巧极,天工错”范畴中的极致,是圜转于“逸”“神”“妙”“能”四大层次中后两者之间的艺术,同文人画的层次和意蕴气息轩轾。董谓黄公望的“骨”、倪瓒的“韵”乃是文人画的核心;而其巨眼中的非女红者,一是林天素,二是王友云:前者秀绝,然如“北宗卧轮偈”,故“吾见其止”;后者澹宕,如“南宗慧能偈”,故“特饶骨韵”,若假以时日,则友云“殆未可量”。董氏此番对闺秀绘事、门派的评议,暗涉希孟未辨逸、神、妙、能的品第之差异,以及利、行两派旨趣的等第之别。
所谓董氏的“密码”,是指长达半个多世纪以来,对顾氏家族暨女眷绣艺虽断断续续、但主旨明确的引领,如引禅入画、援佛入绣、变法创造等。他数十年葛心孤诣地搜藏董源绘画以印证南宗画脉络建构的正确,在酝酿古法“落笔之顷,各有师承”外还须创新,以法书为例,“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学古人应“如禅家悟后拆肉还母,拆骨还父”,惟其方能脱胎换骨,面目非故而“尽变前时面目也”;(28)董其昌:《容台别集》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32册,第449、521-522页。董深刻地认识到,往昔之变已成为当下的传统,在管绣、顾绣、援禅入绣和绣画同理中极力倡扬创新之变,而寻绎董、米、黄、倪一脉乃是认知绣画领异拔新的关节。不妨来看萃集山水、人物、折技、草虫各二幅的《宋元名迹》,其中,第五、八幅是其心旌神会之作——前者《米画山水图》缥缈烟雨、意蕴江南的米氏山水,正是其念兹在兹的“吾家山水”、画艺极境之规模。请读其赞:
南宫颠笔,夜来神针。丝墨盒影,山远云深……(29)董其昌题跋:《顾韩希孟绣宋元名迹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丝墨盒影”的画、绣映现,“夜来神针”是谓溢美;后者桃源、花溪、渔隐的神景仙道不啻萦绕其心旌之梦境。题曰:
何必荧荧,山高水空。心轻似叶,松老成龙。
经纶无尽,草碧花红。一竿在手,万叠清风。(30)董其昌题跋:《顾韩希孟绣宋元名迹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董氏四十多年的漫长仕途,在官位实际任职仅15载,也频遭立储挫折、阉竖横行等厄运,他以趋利避害的敏感和远识的抉择回旋于峰谷浮沉间,在出处、进退、仕隐的心理冲突中,明哲保身的道德价值固然令人怀疑,却也因此得以醉心田园和艺事耕耘。“元四家”之一的王蒙所作的《花溪渔隐图》,表现了平淡天真的意趣,然董氏韵语何以置绣画不顾而言他?挚友的一席话揭开了迷底:
霅有华溪,胜国时人多写华溪渔隐,尽是赵承旨倡之,王叔明是赵家甥,故亦作数幅,今皆为玄宰所藏。玄宰每欲买山霅上,作桃源人,以应画谶。(31)陈继儒:《妮古录》卷三,印晓峰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我们知道,董终其一生于书法、绘画较劲的一、二人中,赵孟頫是绕不开的“靶点”。他自诩是继赵后“要亦三百年来一具眼人也”,从“每欲买山霅上”可证,董对赵孟頫外甥的《花溪渔隐图》烂熟于心并不为过。而韩绣如此,夫复何言?两跋未收入董著未免使人浮想联翩。若对比韩绣、王画,前者了无后者纵逸多姿和苍楚秀润的笔意,庶几不可同语。
回首题跋首句“才士”画人物、花卉但不言山水,暗喻其未得丹青堂奥;二、三句“冰寒之誉”“绣采绚丽”“江淹梦锦”“灵秀之气”褒赞的铺垫,引申的主旨却是相反相成的“女红”。董其昌明确的褒贬 ,提出了韩绣处于女红属性的论断;而黄氏父子写生、“行家迫察 ”等的字里行间,隐现的是路径偏差、流派正歧交错和粉本的杂沓。今人数以百篇引录董跋,并视为对顾绣至高的评价,实属误读和曲解;董氏言说的内涵,指涉利家即文人画,那种自娱复娱人、由景境向趣味的转向和追求,也未尝不是摆脱女红或院体桎梏的方向。事实上,董氏画学中不乏其价值观取向及其阐释,比如在他梳理的两大传统画派中,文人画“自右丞始”,其后董巨李范为嫡子,再后为李王米至元四家“皆其正传”,而马夏李唐刘诸家的大李将军派,“非吾曹当学也”。就是说,董氏崇尚唐代王维创开门径的“一超直入如来地”式的南宗画,而非李思训为祖、“积劫方成菩萨”的北宗画。又说画家“为造物役者”,乃因“刻画细谨”,结果不仅损寿,而且了无生机。眼前富生机者是“寄乐于画”,从元人黄公望肇始;因此,“寄乐于画”,一刹同于永恒;奴役于画,大千等于微尘。前者贵在自然,脱尽窠臼;后者因板刻易落蹊径。在董看来,学习传统的最高境界应是“如大火聚”的涅槃,粉碎虚空,在传统灰烬中形成自成一家的“凤凰”,正如他说的:“若要做个出头人,直须放开此心,令之至虚,若天空,若海阔。又令之极乐,若曾点游春,若茂叔观莲。洒洒落落,一切过去相,见在相,未来相,绝不挂念。到大有入处,便是担当宇宙的人。何论雕虫末技?”(32)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卷三,第61、62、66、100、101页。一言以蔽之,董氏的“密码”中,绘事至高境界应是,“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33)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第66页。绣画亦当如斯!然而,董并未留下有关绣画精确的知识话语——比如心、眼、手同工具、材料的厮磨相印,如何超越绣和画、针和笔、绫绢和纸楮,挥洒点染,以及由一针一线而生发的本体差异。由此也可窥见,大士和山水画,已迈越了张的题材之囿;而“宇宙在乎手”的画之大道,在于个体心灵提升到文化创造的主导高度,也就是董的“天真烂漫”境界——也超越了王世贞“画趣”的藩篱。
四、顾绣的转向
顾族女眷以其不凡的绣秤针管高标于艺林,谭元春《顾绣歌》中“华亭顾妇”“顾姬”乃是顾芝云之妾缪瑞云,程馟《顾绣》一文说他与顾湛(伯露)游毕常熟,分别时“伯露出其太夫人所制绣囊为赠”,此“太夫人”即其生母缪氏。(34)刘森林:《顾绣人物谱系新证》待刊。程述其绣艺云:
……其一面绣绝句,字如粟米,笔法遒劲,即运毫为之,类难如意,而舒展有度,无针线痕,睇视之,莫知其为绣也。(35)程馟:《石交堂集》顾绣,朱子锐:《明清闲情小品赏析·衣食住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62页
无论是人物、战马,还是云旗锦幡等,均皆逼真毕肖,实非绝艺不能为,故程云“盖云间之有绣也,自顾始也”。(36)程馟:《石交堂集》顾绣,朱子锐:《明清闲情小品赏析·衣食住行》,第162页。2007年上海博物馆发表的《竹石花鸟人物图册》,首帧《枯木竹石》左上角墨题“仿倪迂仙墨戏”,丝绣朱文方印“缪氏端云”,第一代顾氏针神始现于世。该册中《昭君出塞》《文姬归汉》《苏李泣别》的人物栩栩有生韵,《松鼠葡萄》《杨柳隼翠》的动植物形象灵动,而针法的平、薄、匀、细,则彰显出卓绝的绣艺和高超的工艺技术。如果说第一代缪绣题材还属于自发性,大士像、墨戏为趣味转捩的话,那么,韩氏则从非确定性中迈向了自觉——以宋元明名迹为底稿,以针代笔,丝线化为丹青,细针密缕,亦绣亦绘,一如《花卉虫鱼》中的苔点、水纹等处的笔绘墨迹。进言之,韩在丹青趣味的基础上转向了亦绣亦画的摸索。寿潜1634年跋《宋元名迹》说从1634年春开始,“搜访宋元名迹”,摹临八种,“盖已穷数年之心力矣”。其昌翁问,技何以至此,寿潜回答:
往往天清日霁,鸟悦花芬,摄取眼前灵活之气,刺入吴绫。师益诧叹,以为非人力也。欣然濡毫,惠题赞语,女红末技,乃辱大匠鸿章。窃为家珍,决不效牟利态,而一行一止,靡不与俱。伏冀名钜,加之鉴赏,赐以品题,庶彩管常新,色丝水播,亦艺苑之嘉闻,匪特余夸耀于举案间而已也……(37)顾寿潜题跋:《顾韩希孟绣宋元名迹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跋语述寒暑风雨四时不事,前揭谭氏说黎明作业最佳的“离朱晨曦,日午则疲”,寿潜则将之提升到仪式层面。“决不效牟利态”与其说表态,毋宁说对顾绣正脉的捍卫、数年摹绣的定位,以及对“惠题赞语”的感恩——作者深知翰墨老人的历史价值和影响力。明乎此,董跋助力顾韩成为顾绣文化遗产的合法承继者中,凝淀的非仅顾绣和法书的价值,更是首屈一指的文化资本和艺术荣耀。而“匪特余夸耀于举案”的表达,既属于“传达自我的印象”(38)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黄爱华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9页。范畴,也寓含着绣画转向的标志。
顾跋点明了寝寐经营的韩绣蕴含的家族名望、文化资本,和维系世家文化品格的精神动力。虽然,寿潜系汇海庶出的五子,其名、字与兄长存异,其妻妾及希孟姓氏未列入《宗谱》;(39)顾心毅:《顾氏重汇宗谱》第四卷,世系考,天佐支,上海图书馆藏,第66页。而《尚宝司丞龙海顾先生行状》非但未列其名,且明确名世“孙男三,长芝云,次芝玉,芝室,俱箕英出”(40)陈继儒:《陈眉公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37页。的“声明”。由此看来,希孟的地位,远非顾湛生母缪瑞云可比,母以子贵的缪氏藉助“三从”之“从子”,俨然成为族、园、绣三维的正脉。对寿潜来说,嫡庶无法选择,唯有发掘顾族的文化遗产,然长嫂缪瑞云的大士佛像、鞍马人物、竹石墨戏已名满天下,除己著《烟波叟诗草》外,唯擅长契合女子情感细腻和托物言志、比兴审美的花卉人物画,或能有效彰显其妻的个性和格调;而通达的津梁,无非祖上余荫和董师的资源。以往学界大都习称韩氏精谙六法,实属附会和想象——《珊瑚网》《式古堂书画汇考》《玉台画史》《国朝画征录》等入列的是宋代女画家韩希孟,(41)吴其贞:《书画记》卷六,邵彦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而非明代针黹圣手韩希孟。董、陈题跋的光辉,“武陵绣史”“韩氏希孟”“韩氏女红”类的钤印,不啻宣示了韩氏对于家族网络中被边缘化的不满,也不复“丹青之在闺秀,多隐而弗彰”(42)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八,引自《中国书画全书》第5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第1163页。的隐秘,以及自娱的叹喟,抑或不再囿于闺阁的觉醒。
结 语
董其昌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悉心引导顾绣从绣画内容、题材、技法和风格的转向,显现了禅悦和南宗画趣味融合的端倪。第一代缪瑞云自女红而大士、人物、竹石,第二代韩希孟自花鸟而山水绣画,见证了织绣文明和女红文化的璀璨辉煌,共为明代刺绣的杰出代表。事实上,韩希孟绣技不及缪氏,翰墨难同倪仁吉颉颃,识见难忘张淑瑛项背,但凭借家族资源、团体型绣工交流的优长和董氏倡扬的创新绣画,展现了刺绣的独特气质和艺术品味。然笔墨缣素和针黹画绣的工具、材料、施艺的偏差和限制,却是横亘在韩氏及后来者的瓶颈——绣画如何呈现天真烂漫、复极精能而臻于宇宙在乎手的宏阔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