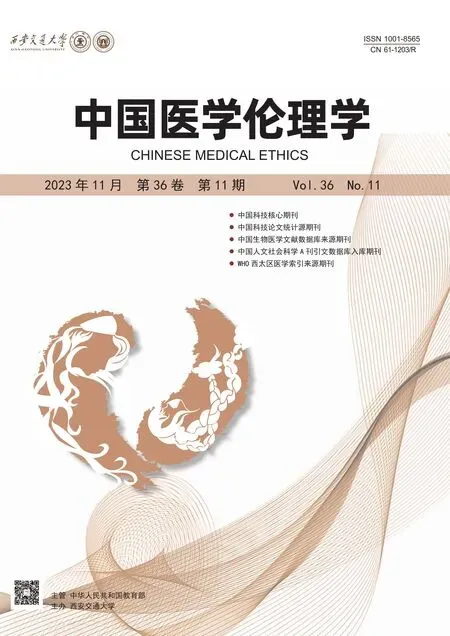癌症隐喻的转化和破除
——癌症患者的自我叙事研究*
曾繁萍
(福建医科大学健康学院,福建 福州 350122)
癌症作为一种令人谈之色变的致命疾病,病因的多样性、治疗的不可预知性,以及在生命边缘摆荡的模糊性等特质,使其饱含着丰富的隐喻[1]。社会群众往往将生活周遭的各种负面或贬义词作为癌症的指涉。既有研究指出人们恐癌的根本原因是来自对“死亡”的畏惧[2]。“死亡”作为癌症的隐喻,已然成为社会普适性的认知,迫使多数社会大众在面对癌症患者时会不由自主产生排斥或歧视等负面反应。是以癌症的隐喻具有转变人们对癌症和癌症患者认知的强悍力量[3],影响着癌症意义的社会建构。此外,癌症的隐喻还存在着动态的流动性特质,会随着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的不同而变化[4]。因此,探析特定社会中癌症隐喻的使用与发展形式,将体现癌症意义的社会建构脉络[5],知晓群众用以理解癌症的方式及其受癌症隐喻的影响程度[6]。
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美国分别出现两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女性癌症幸存者——郭林和苏珊·桑塔格。她们二人有着极为相似的家庭背景和生命历程,并且都在以癌症患者的新身份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发展出能够应对中国和美国癌症患者困境的社会行动。然而,受到社会文化中医疗体系的发展差异所影响,最终她们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郭林创编《抗癌健身法》锻炼,苏珊·桑塔格写出《疾病的隐喻》,以此转化和破除癌症隐喻引发的威胁,重新建构癌症的社会意义。
美国医学伦理学家埃德蒙·佩莱格里诺[7]指出,医学在任何时代都具有文化特征并由此生成对应自身社会需求的医疗体系。循此脉络,对疾病的解释便不能单纯视为一种生物性的病菌侵入身体或者器质性的病变[8],应当将其理解为是结合生理、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并且兼具时间性、地方性和群体性的复合型概念。正如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9]认为人们对疾病的理解和共识更多受所处地域环境的社会文化所熏染,并改变他们对治疗模式的选择。因而尽管郭林和苏珊·桑塔格有着极为相似的生命历程,她们对癌症的认知与治疗的行动亦深受她们所处社会文化医疗体系的影响与作用。诚然,个人生命史的意义与价值绝不仅是呈现出她们的人生轨迹,同时也将烘托出当时社会、文化、疾病与人之间交织缠绕的关系[10]。
据此,本文将基于郭林和苏珊·桑塔格自行书写的日记和个人传记作为叙事分析的主轴。从她们二人的生命历程、患病经历和治疗过程中,论述她们对癌症的认知与治疗抉择的实践模式,从而深入阐释癌症隐喻的滋生何以造就癌症患者的艰难处境,以及她们二人如何展开对应的社会行动,重新建构癌症的社会意义。
1 郭林与苏珊·桑塔格极为相似的生命历程
1.1 残缺的童年时期
郭林,原名林冠明,字妹殊,1909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2岁时父亲战死,她自幼便被祖父带在身边养育。她的家族在村里开设中药店,这使得郭林从小受到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她儿时经常独自登上高山为祖父采集草药,山上宏伟壮丽的自然美景让郭林产生作画的兴趣,埋下未来从事绘画工作的种子。
苏珊·桑塔格,原名苏珊·李·罗森布拉特(Susan Lee Rosenblatt),1933年出生于美国纽约曼哈顿。成长于一个商贾家庭,自幼由保姆带大。4岁时父亲因肺结核去世,12岁随母亲改嫁。在新家庭的生活中,母亲限制她与外人交流,过度保护使苏珊·桑塔格童年时期缺少同伴的陪伴。她将她的童年称之为“漫长的监禁生活”[11]26-28。然而童年的孤独时光却也培养出她对阅读的兴趣,为她日后的写作生涯奠定了基础。
1.2 早熟的青少年时期
郭林和苏珊·桑塔格在求学期间都有着优异的表现。郭林因为成绩优异和热心助人被推派为学生会副主席,又因连续两年夺得广州市万米赛跑女子冠军,被选任为广州市学生联合会副主席。苏珊·桑塔格则是因成绩优异而连跳三级,15岁便从高中毕业,19岁获得芝加哥大学学士学位,随后取得哈佛大学英语及哲学双硕士学位[12]。
在青少年时期,她们二人在性格上都比同龄人更为成熟,于待人处事上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郭林行为举止较为中性,惯用男装扮相在外行走,在性格上也有着不属于同时代女性的胸怀气度与行事作风。苏珊·桑塔格则性格倔强、特立独行,在社会行为上喜欢仗义执言,拒绝被归入任何类型、贴上各种标签。
1.3 以文艺为业的成年时期
成年后,她们的职业都是文艺工作者。郭林自幼就培养起对绘画的热爱,也如愿进入艺术科学习,毕业后任职于北京中国画院,从事绘画艺术工作长达50多年。苏珊·桑塔格由于爱好阅读,幼时便与文字结下不解之缘,日后也成为作家,于1962年出版第一本小说《恩主》。直到临死前,也不忘在病床上继续写作,被誉为“美国最聪明的女人”。
1.4 背离传统的伟大女性
依循前述郭林和苏珊·桑塔格的生命历程得以窥见,虽然她们分别成长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社会文化差异悬殊的国家,但在家庭、求学、婚姻、工作、性格等方面,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从她们成长到成年的过程中,均背离当时社会期待的女性角色,经历到打破传统女性角色时所面临的社会冲突。她们皆不愿违背自我意愿迎合社会的期许,最终也都通过自身的努力建立一定的身份地位,获得社会认可。正是这种独特的生命经历,淬炼出她们坚韧的意志,进而使她们在罹患癌症后,不甘受制于疾病的压迫,跳脱出当时癌症隐喻所营造的社会氛围,起身与社会进行抗争。
2 “自疗”与“治疗”:郭林与苏珊·桑塔格不同的抗癌实践
除了成年后共有的患癌经历之外,在郭林和苏珊·桑塔格成年前也曾深受疾病折磨所苦。郭林在高中时被发现患有肺结核,苏珊·桑塔格在5岁时哮喘发作。两人过往的病史使她们在患癌和治疗的过程中有着比常人更为敏锐的身体经验。正如黛博拉·勒普顿所言“人对疾病和健康状态的理解是动态的,甚至前后不一致,会随着个人经历和周围环境的改变而不同”[13]。从罹患癌症到治疗癌症的过程中,郭林和苏珊·桑塔格的生命历程开始产生差异。
2.1 郭林:身心一体的“自疗”
郭林第一次患癌是在1949年。因为长期血尿导致身体不适而就医,医生在手术过程中发现是子宫颈癌,便径直将她的子宫连同肿瘤全部切除,那年郭林才40岁。手术后她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承担昂贵的放射治疗,便自行返家疗养。第一次患癌使郭林直接体会到死亡的恐惧[14]87。
郭林第二次患癌是在1964年。她又因血尿问题住院。经医生诊断为膀胱癌,需要手术治疗,这让她再度感受到死亡的威胁。郭林在日记中提及,当被推进手术室,等待麻药起作用的这段时间,她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从小她便爱好各种体育运动,但是这些锻炼却未带给她一个健康的身体,反而使她屡次遭受癌症的侵犯。这使郭林开始思索该如何才能永久摆脱癌症的纠缠,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若是这次死了,虽有种种牵挂,什么也管不了了。若是有幸生还,今后要如何活下去?不能总是在手术刀下求生,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摆脱病魔的纠缠,对,必须争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11]58。于是,她回忆起过往和祖父学练养生功法的那段岁月,令她兴起用中国传统健身术来对抗癌症的念头。手术成功后,郭林便开始潜心钻研健身术锻炼,同时也阅读大量医学书籍,包括医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经络学、心理学等[15]30-33,借以了解导致自身患癌的原因和采行健身术锻炼抗癌的可行性。
在将西方医学知识、中国传统医学和健身术锻炼抗癌的思维结合后,郭林认为人之所以罹患癌症是根源于自身免疫力低弱所致,要想对抗癌症的关键在于提高自我抵抗疾病的身体机能[15]。在经过长时间的功理钻研和锻炼实践后,郭林最终创编出一套因应癌症患者需求的健身锻炼法——《抗癌健身法》。
此外,郭林还特别强调心理因素的调适对癌症患者的重要性。幼年起便受到中国传统医学和道家养生文化的熏陶,使她将身心视为一体,认为疾病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影响所致,心理和情绪的变化都会导致疾病,甚至是死亡。因此,郭林认为疾病的治疗不单只是治身,还包括治心,抗癌不只是对抗体内的癌细胞,还在于对抗自己身体内部那些“滋养”癌细胞的心理因素。所以在郭林看来,癌症治疗是一种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自我疗养过程。
2.2 苏珊·桑塔格:身心二分的“治疗”
苏珊·桑塔格第一次患癌是在1975年。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她被查出罹患乳腺癌四期。当时医生告诉苏珊·桑塔格能存活过两年的概率仅有10%,另一位医生则对她说只能存活半年。“他们告诉我,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所以我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和痛苦的手术,还有我所有的思想都将在一两年之内死去的事实。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外还有害怕和恐惧,我吓坏了……”[16]9为了增加自己活下来的希望,苏珊·桑塔格在医生的建议下进行根治性乳房切除手术和淋巴结切除手术。手术后,她在日记中写道:“绝望一定会让你翻身得到解放”[17]89。现实也确实如此,这次的患癌经历使苏珊·桑塔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将这次患癌视为人生中“分水岭一样的经历”[18]202。
苏珊·桑塔格将自身患癌归究于是过去错误的生活方式所致,不断自我谴责。身体上的疼痛和心理上的悲苦,逐渐将她推往崩溃和放弃生命的边缘。直至一天,当苏珊·桑塔格在医院接受治疗时接触到几位受制于癌症隐喻附加的道德批判,而忽视甚至放弃治疗的癌症患者,顿时激起她的恼怒,恼怒她和那些癌症患者们都遗忘了自我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由此燃起她强烈的求生意志,开始大量阅读医学文献和科学杂志,并且不顾众人反对,坚决在巴黎进行一项需要使用大剂量且尚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可药物的极端性化疗方案。当时的苏珊·桑塔格宁可承受化疗对身心带来的毒副作用,也想求取延续生命的一丝机会。经过八个月的治疗后,她体内的癌细胞获得控制,身体状态也逐渐回稳。苏珊·桑塔格用她治癌成功的经历向癌症患者们表明,患癌的责任并不在己,但作为癌症患者是有责任去寻求治疗疾病、延续生命的最佳方案[18]215-217。
苏珊·桑塔格第二次患癌是在1998年。她被诊断出罹患罕见的宫颈癌,医生说她存活率只有5%。但是基于第一次治癌成功的康复经验,苏珊·桑塔格乐观看待这次的病况,“这次,是一种不同的癌症,不过尚在早期阶段”[16]211。苏珊·桑塔格相信,正如她23年前所坚信的:她可以战胜死亡。于是她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并进行漫长的化疗医治[11]315-317。最后化疗虽然成功抑制住癌细胞的生长,但强烈的副作用使苏珊·桑塔格产生严重的神经性病变,而她却不以为然,仍为自己能活下来感到雀跃[11]318。凡是在苏珊·桑塔格住院期间来探望的人,都能见到她在病床上卖力撰书的模样,写作已然成为她验证自我生命延续的一种展现形式。
苏珊·桑塔格第一次患癌时,除了不良的生活方式之外,她也将患癌原因归于是心理问题,认为是她长期重度沮丧、过度压抑情绪所致。但在治疗过程中,她逐渐摒弃了导致疾病生成的心因说,改以医学科学的角度审视疾病,认为癌症是一种身体上的生理疾病,无法依靠心灵救赎或信仰力量来寻求治愈,唯有对病体进行医学科学的治疗。于是在癌症治疗的行动实践上,苏珊·桑塔格将身体和心理进行区分,反对从患者的心理层面来干预癌症治疗的各种另类疗法,认为只有立基在医学科学的治疗手段才具有医治癌症的资格与能力,同时患者还必须主动配合医生的治疗才能够真正获得疾病治愈的机会。
2.3 不同抗癌实践背后的医疗体系与身体经验
在面对重大疾病威胁时,人们的行为离不开自身的观念和生活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对疾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6]。从郭林和苏珊·桑塔格的患癌和治疗行动中,得以知悉她们二人在患癌前虽然有着极为相似的生命历程,但在患癌后受到各自所处社会文化医疗体系影响而对癌症的病因认知与治疗抉择产生分歧。郭林选择通过健身术锻炼来提高身体免疫力进行“自疗”的抗癌手段,根源于中国传统医学和道家养生文化,她认为疾病的出现是身体和心理同时出现问题所致,所以强调治病要同时兼顾身与心的治愈。相反,苏珊·桑塔格则受西方医学的影响,认为罹患癌症是一种生理问题,必须使身体接受“治疗”才能获得治愈。多数西方人在西方社会文化的医疗体系影响下认为身体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它像机器,是物体,是与思想感情相分离的客体[19]。因而在苏珊·桑塔格看来,癌症的出现就像是一台机器中有一个零件出现故障,需要由专业人员(医生)进行维修(治疗)[16]23,身体并不具有自行修复的能力。
除了因为所处社会文化中医学对于疾病与治疗的诠释脉络不同之外,两人之间差异的产生也与她们在患癌和治疗过程中的身体经验有关。对郭林来说,反复患癌带给她的死亡恐惧,使她决心要寻求医学以外的抗癌方式,所以她从西医的治疗转向中国传统医学和道家的健身术锻炼。苏珊·桑塔格则由于第一次患癌的治愈经验,使她对医学科学治疗癌症的各种手段抱有极大的信心,并且抗拒各种另类疗法。故而当她第二次患癌时,即便治疗过程伴随着严重的副作用,她也依然坚持利用医学手段治疗癌症。
3 重构癌症的社会意义:癌症隐喻的转化和破除
死亡作为癌症的隐喻,使人罹患癌症之后,便被迫失去作为一个常态之人的生存权利,在病而未死之际就已经在别人的意识里被宣判为死者[20]。郭林和苏珊·桑塔格都不止一次患癌,在反复患癌和治疗过程中遭遇到的医疗处置和身心经验,是使她们产生转变的重要契机。有研究指出,病痛或者严重疾病会造成人生进程的断裂,对个人的完整性、生命意义和自我认同产生破坏[21-22]。但反观郭林和苏珊·桑塔格的经历,“患癌”反而成了她们建构生命意义和自我认同的重要机遇,除了体现在她们患癌和治疗的过程外,也呈现在她们应对癌症隐喻威胁所开展的社会行动中。
3.1 转化癌症的死亡隐喻,赋予患者生的希望
对于癌症患者来说,癌症不仅会造成难以忍受的疼痛,更被视为是死亡的同义词。以中国为例,“癌症等于死亡”的意象之所以深植人心,是因为当时癌症在医院治疗的费用高昂,癌症患者多数无法接受完整的治疗疗程,再加上受限于医院检测技术和设备条件的不足,许多癌症患者一经确诊即为晚期,导致癌症死亡率极高[23],不少城市的癌症死亡率甚至已经接近或超过国外最高死亡水平的国家[24]。是以在癌症死亡隐喻的作用下,癌症患者在患癌后总是抱持着悲观、绝望和恐惧等负面情绪,有的甚至是放弃治疗,消极等待死亡的到来。
面对癌症等于死亡所造成的影响与威胁,郭林带着她创编的《抗癌健身法》走进社会大众视野,试图以中国传统医学和道家养生文化中的健身锻炼法来唤起癌症患者的自我抗癌意志,帮助他们摆脱癌症死亡隐喻造成的阴霾。
如何消除癌症死亡隐喻引发的社会恐慌?郭林认为关键在于使癌症患者建立起对抗癌症的主动性。对此,她以战争、狼、毒瘤等隐喻,转化癌症的死亡隐喻,重新塑造癌症患者对癌症的认知,打破癌症和死亡之间的连结,赋予癌症新的社会意象。如下列所示:
“要坚持,要有信心地苦练……掌握了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与病魔斗争必将获胜,而永远脱离了病魔就得自由了。”[14]7-8
“癌症好比一只狼。你不斗它,它就要吃掉你,敢于斗争,胜利一定属于强者。”[25]
“不能肯定毒瘤之症是不治之症,真理的认识是永远没有完结的。祖国的医务人员正在不断地研究。听了毛主席的教导,怀着诚恳的为人民服务的红心,已经展开临床的观察,并进行种种研究,来同这恶性肿瘤的病魔作斗争。”[14]87
此外,在郭林转化癌症的死亡隐喻过程中,她将《抗癌健身法》视为能够帮助癌症患者提高自我身体机能、对抗癌症的重要锻炼方式,“下定决心坚持锻炼,把自己的病自己负起责任来,不仅能治病,巩固了健康,也锻炼自己的意志,加强了生命力,亦加强了精神生活的快慰感”[17]59。由此起到转变癌症患者对癌症、治疗和身体认知的作用,改变癌症带给他们的恐惧,赋予癌症患者延续生命的动力,进而强化转化癌症隐喻的作用。
3.2 破除癌症的负面隐喻,回归纯粹病理解释
除了死亡隐喻之外,癌症的各种负面隐喻也无孔不入地渗透在社会各处。苏珊·桑塔格发现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文学著作,疾病总是作为一种不好的、坏的、邪恶的等负面标志的隐喻,“癌症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事实上癌症也的确没有那么多矛盾因素。它就是一种恶的隐喻,不象征任何积极的东西。”[16]28在这些负面隐喻的作用下,癌症的疾病状态受到了遮蔽,夹杂着多重且复杂的意识形态,导致癌症患者被迫陷入社会污名、歧视和道德批判的困境中,无法正视自身仅只是一名癌症患者,阻碍了癌症患者接受治疗机会。“当我患上癌症时,尤使我感到愤怒的,是看到该病的恶名声怎样加剧了癌症患者的痛苦……我的病友们……都一致表露出对自己所患癌症的厌恶,并引以为耻。”[26]95
不同于郭林致力于转化癌症的隐喻,提高癌症患者抗癌的主动性,苏珊·桑塔格则是借助文字的力量,尝试彻底破除潜藏于癌症背后的所有负面隐喻。“癌症就是疾病,疾病就是疾病”,这是苏珊·桑塔格要传达给癌症患者和社会群众的重要信息,同时也是她破除癌症负面隐喻的关键。“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看待疾病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26]5。
苏珊·桑塔格破除癌症负面隐喻的行动意念是不赋予癌症和癌症患者更多的诠释和象征意义,而从本质意义看待和理解他们的存在与价值,让癌症患者们从癌症隐喻中获得解放,同时也向社会群众揭示癌症隐喻如何使癌症患者陷入艰难的处境,“我想为患者和照料他们的人提供一种方法,来消除这些隐喻、这些障碍。我希望劝说那些心怀恐惧的患者去看医生……要正视癌症,就当它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也未必是一纸死亡判决”[26]97-98。
1978年苏珊·桑塔格于《纽约书评》上连载的《疾病的隐喻》一文成为她最有力的战斗武器,据此开展各种社会宣讲行动来阐述她的理念,让大众从思想上转变癌症的社会认知,以此破除癌症的各种负面隐喻,让癌症回归到生物学上纯粹的病理解释。最终逐渐营造出对癌症患者友善的社会环境,使他们愿意走进医院接受治疗。
概而论之,在应对癌症隐喻威胁所开展的行动中,郭林转化癌症隐喻的方式是藉由引入群众熟悉、具体和可触及的生活元素来取代抽象的死亡概念,并经由这些隐喻重新赋予癌症新的意义,以此将癌症具现化为一种可以被击溃的事物,例如可战胜的战争、可被打死的狼、可被剥除的毒瘤等,从中营造出我强、癌弱的社会场景,并且癌症患者能够维系自身的强大并战胜癌症的关键还在于学练《抗癌健身法》来提高身体机能。在此运作下,郭林不仅成功转化癌症的死亡隐喻,同时也在癌症患者的治疗和康复过程中,为她创编的抗癌健身法建立合理性的存在。苏珊·桑塔格采取的行动则与郭林截然不同,她关注的是癌症和癌症患者的社会性生存,强调只有破除社会中有关癌症的各种负面隐喻,并以客观科学的视角来解构癌症作为一种疾病的事实,才能使癌症患者脱离死亡和被社会边缘化的困境。
4 结语
既有研究指出社会文化最根本的价值观和该社会文化中最基本的隐喻结构具有一致性[27],隐喻的本质是人们通过生活中的具体经验对当前事物和现象进行诠释和理解的过程[28]。换言之,隐喻嵌入社会文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对于隐喻的认知以及隐喻可能起到的影响与作用。本文通过阐述郭林和苏珊·桑塔格两位女性癌症幸存者的生命历程和患癌经历,揭示出她们对癌症认知和治疗抉择的分歧是根源于不同社会文化中医疗体系的发展差异所致,致使在癌症治疗中她们感受到不同的身体经验,改变她们日后应对癌症隐喻威胁的社会行动模式。作为疾病叙事的比较研究,本文不仅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文化适应性的研究参照,同时也经由分析郭林和苏珊·桑塔格日记与传记中的个人生命轨迹,得以深入理解当时社会、文化、疾病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连结,体现出生命史研究与叙事研究相结合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