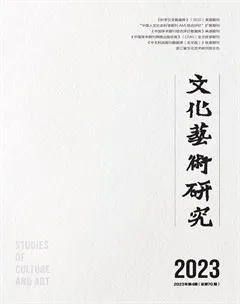拟玩家角色及其出现:电子游戏中非玩家角色的转变
王晓宇
(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随着电子游戏领域中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尤其是当下OpenAI 开发的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强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模型ChatGPT 的问世,非玩家角色(non-player character,即NPC)正在经历一场革新性的变革。面对这种变革,需要重新考量“非玩家角色”这一概念的尺度的合法性和非玩家角色的内涵。因此,本文尝试将从这一概念原本内涵中逃逸出的意义再辖域化,使用“拟玩家角色”这一新的概念,来描述电子游戏中搭载强人工智能、利用神经网络、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并且区别于传统的非玩家角色。这一概念上的流变模糊了“非玩家角色”的边界,并且也区分了“拟玩家角色”与“非玩家角色”。这种差别一方面体现在思考“非玩家角色”之于“拟玩家角色”生成性上的转变,即在技术上从被动反馈向主动生成转变。另一方面体现在将“拟玩家角色”视为人工智能在电信号代码上控制的“虚体”,讨论二者主体上差别的流变。通过讨论“非玩家角色”向“拟玩家角色”的转变,来发掘电子游戏中“拟玩家角色”的新的可能性。
电子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计算机科学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娱乐产业的繁荣,电子游戏从出现至今,仅用短短50 年就完成了从使用旋钮控制显示在示波器上的图形,到如今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入虚拟的游戏场景中实时交互的难以想象的进步。但是电子游戏作为年轻的学术研究对象,直到20 世纪80 年代才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对于电子游戏的研究,最早仅在计算机领域关注电子游戏技术,到如今电子游戏已然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哲学等学科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直至21 世纪伊始,才出现了像《游戏研究杂志》(Game Studies)和《游戏与文化》(Games and Culture)这样的专业性学术期刊,电子游戏也成为当今人类必须要面对和认识的文化现象,应将其纳入学术体系中。近些年,计算机科学的飞速发展,一方面,给电子游戏领域带来了许多技术上的创新与突破,比如性能不断更新的更强劲的硬件设备、能从视觉上将游戏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的增强现实技术AR(Augmented Reality)、让玩家可以沉浸式进入游戏世界并进行交互的虚拟现实技术VR(Virtual Reality)、在游戏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等。但是另一方面,电子游戏在技术上和产业上飞跃式的发展,使学术层面上尚是一门新兴学科的电子游戏在知识和理论上产生了一定的断裂,人们关于电子游戏相关知识的生成和获取与它发展进步的速度无法匹配。正如吴冠军教授基于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 的“竞速学”(dromology) 概念所指出的:“人/物、信息/数据移动速度的巨幅提升(并且是加速提升),导致在当下人类文明内部,人工智能算法已然快速地、全方位地在淘汰人体的‘生物算法’(‘智能’)。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革命’实则正是‘竞速革命’的最新形态。”[1]而且需要承认的是,现在越来越多具有革新性的重要技术,都会给电子游戏领域带来新的影响和联系。在人工智能技术革新日新月异的今天,尤其是由Open AI 研发的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强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模型ChatGPT 的出现,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关注与热议,同时也对基于计算机技术和数字化媒体的电子游戏的开发、叙事、机制等核心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其中作为电子游戏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的非玩家角色同样也正在经历着或已经实现了又一次革新性的发展。
非玩家角色,指的是游戏中一切不受玩家控制的角色。这一游戏术语的出现并非源于电子游戏的语境,而是伴随19 世纪70 年代初桌面角色扮演游戏(Tabletop role-playing game)《龙与地下城》(Dungeons & Dragons)的流行开始使用和普及的。桌面角色扮演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是由游戏的管理者(game master)建构,来充当真人玩家的伙伴、对手或中立的角色,从而填补游戏中叙事的空缺并推进游戏的进程。因此,非玩家角色这个概念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电子游戏领域。从技术史的视角来看,早期电子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通常根据程序预设的脚本,执行预定义的路径、固定的行为模式和最基本的反应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架构开始进入游戏的设计中,非玩家角色开始采用有限状态机(Finite State Machine,FSM)的计算模型,状态机的本质是一台虚拟的机器,根据所输入的内容做出相应的响应,实现状态间的转化。但随着电子游戏的进步和游戏中人工智能愈发复杂,有限状态机很难满足AI 的需求,由此就出现了当下非玩家角色设计中最主流的、由具有不同功能的节点组成的行为树模型(behavior tree)。区别于有限状态机的是,行为树的主要建构模块是任务而不是状态。通过对非玩家角色进行编程,置入设计好的行为树模型,非玩家角色可以根据动作节点进行决策,从而创建复杂的行为。但是到了今天,非玩家角色开始尝试搭载基于神经网络、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强人工智能。这就会带来一个有趣的现象:当玩家通过键盘鼠标或游戏手柄操控电子游戏中自己化身的“虚体”穿行于虚拟世界时,玩家们可能没有办法通过对话、行为或逻辑去分辨游戏中其他角色的背后到底是同自己一样坐在屏幕前的具有肉身的人,还是经过不断学习人的语言逻辑、具备一定的理解能力或意识的数码化身。因此,今天这种更加拟人化(anthropomorphic)的非玩家角色,所带来的不仅是技术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引发了在电子游戏过程中对于主体身份问题的全新思考。
从“非玩家角色”到“拟玩家角色”概念的流变
游戏研究者索尼娅·菲兹克(Sonia Fizek)在出版于2022 年的《在远距离玩:电子游戏美学的边境》(Playing at a Distance: Borderlands of Ⅴideo Game Aesthetics)一书中,通过“距离”来讨论电子游戏与媒介及媒介美学的关系,并重新讨论玩家与游戏之间的关系。菲兹克认为,“玩家和游戏本身并不存在,或者至少不是在我们所熟悉的意义上存在。玩家和游戏都不能被看作是明确、预先定义的实体。玩家和游戏只有通过游玩和在玩的过程中的互动,二者才在共同的游戏之中展开。虽然乍一看玩家和游戏界限似乎很明显,但它们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玩家和游戏不是通过预先设定的明确的边界来分离单个的实体;它们之间不存在静态关系,而是一种边界的制定”[2]68。虽然索尼娅·菲兹克并没有在书中明确提及,但是通过其致力于对边界的再讨论和对于静态关系的打破,也可以看出她带有德勒兹式的生命论的思考。
强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的使用,使得非玩家角色有能力打破预设的代码逻辑和固化的行为模式,通过大语言模型所带来的思维可以实现从被动反馈到主动生成的质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让游戏机制的变化或玩家全新的游戏体验和游戏模式的产生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重新引发了对于非玩家角色这一术语的思考:“非玩家角色”这一概念是否还能够有足够的尺度去涵括这种革新性的发展。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的开篇阐述了“根茎”(rhizome)这一概念,试图超越传统哲学中的一元论和二元论,批判了人类思想中中心主义和辩证的思维模式,否定了带有同质性、层级性自上而下的树状模式。在德勒兹的概念中,“根茎只由线构成,即作为其维度的节段性和层化之线,以及作为最高维度的逃逸线和解域线——正是根据和沿着这些线,多元体才得以在改变自身本质的同时使自身变形”[3]18。依照德勒兹的思想去理解,今天人工智能技术下的非玩家角色并不能简单地看作非玩家角色的发展,或说是在同一个树状结构的根上延伸出的两个不同分支,而应该视为两个独立的异质性的根茎。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技术为非玩家角色们带来一条游牧式的、生机论的逃逸线(la ligne de fuite),使用强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模型的非玩家角色从非玩家角色的这一概念中“解辖域化”(déterritorialization),从传统的、固定的、范式化的意指中逃逸了出来。
用2021 年的好莱坞影片《失控玩家》(Free Guy)为例来说明这个概念可能并不是最合适的,但是或许可以借此在本文后面的论证中更加直观地认识电子游戏中非玩家角色是如何从“非玩家角色”的身份中逃逸并完成向“拟玩家角色”的转变的。该部影片由肖恩·利维(Shawn Levy)执导,影片的男主角是一个生活在电子游戏世界中的非玩家角色,按程序指令每天重复相同的事情并以固定的模式与游戏中的真人玩家互动。但是某一天,它意外地对一名玩家角色产生了情感,开始脱离程序代码的控制,并对每天发生的事情有了无法被系统重置的记忆。之后,它偶然拾取了一个真人玩家掉落的眼镜,戴上后可以看到真人玩家与游戏交互的界面,能像真人玩家一样在虚拟世界中自主地行动,并解锁了如等级系统、使用道具等真人玩家的游戏机制。最后,有了自觉能动性的非玩家角色在虚拟世界中完成了对现实世界的反抗。男主角在电影中自始至终都是没有实体的数字代码的化身,但是当它逐渐有了自我意识并戴上代表着玩家身份的眼镜后,观众们渐渐开始忘记甚至不再将它视为一个非玩家角色,而把它当作一个实际存在的主体。就像影片中的情节一样,关注这款游戏的人们试图寻找这个角色背后操控它的玩家,因为人们不相信一个能够如此改变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主角居然是没有实体的非玩家角色。电影中男主角戴上的标志着玩家身份的眼镜和不断觉醒的自我意识,就可以被视为德勒兹意义上的逃逸线,它的主体身份就此从非玩家角色中脱离并被赋予新的权力,“非玩家角色”的界域也因此被解构。正如上文所强调的,新的意指通过强人工智能技术从“非玩家角色”这一术语内涵中逃逸。但是回到德勒兹所说的,虽然意义可以从固定的范式中解域逃逸,但是最终也会被另一个概念框架所“再辖域化”,其中流变出的意指被重新框定。因此,需要询唤一个新的术语,笔者尝试用“拟玩家角色”(simulated-player character)来描述从非玩家角色定义中逃逸、流变出的部分。这个术语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说明人类与强人工智能之间的差异更加模糊或讨论二者的边界,而是仅仅讨论在电子游戏中非玩家角色的身份发生的变化。
“拟玩家角色”生成的流变
《失控玩家》于2021 年上映,虽然那时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不过其中带有自觉能动性并且可以根据记忆获取具身经验的非玩家角色也只是又一个适用于高概念电影的想象。但是在今天,随着基于神经网络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强人工智能ChatGPT 在电子游戏中的开发使用,《失控玩家》中的想象似乎已经成为了现实。2023 年4 月,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团队发表的一篇论文《生成式代理:人类行为的互动模拟》(Generative Agents: Interactive Simulacra of Human Behavior)在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团队所做的实验受到电子游戏《模拟人生》(The Sims)的启发,通过使用ChatGPT 3.5 turbo 在交互式沙盒环境中构建了一个由25 个代理(agent)组成的小镇,每个代理都使用自然语言模型并给予一个人物设定。文章将利用生成模型来模拟人类行为的代理,称为“生成代理体”(generative agents)。生成代理体们可以通过它们的不同行动与沙盒世界进行不同的实时交互,可以使用自然语言进行互相之间的交流,终端用户甚至可以使用自然语言与这25 个代理进行互动。实验旨在测试由计算机构成的代理能否对互动的人工社会环境做出可靠的反应。实验通过由记忆流(memory stream)、反射(reflection)、规划(planning)三个部分组成的架构使生成代理体成为可能。[4]简单理解这三个部分:记忆流是使用自然语言记录的长期记忆模块,反射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成智能体能够根据记忆做出高层次的反应,规划是将记忆流和反射与当前环境整合并做出合理的行动。正如论文中所提及的,这个实验的灵感来源于游戏《模拟人生》,不难发现这个项目与游戏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即由玩家或实验者生成这些非玩家角色并根据自己的想法给予它们相关的“人设”,然后操控或观察这些诞生并生活在数字世界中的虚拟角色。通过这项实验,我们能够想象不远的将来,在电子游戏领域中,非玩家角色向实验中所谓的生成智能体的方向靠拢,因此也更加说明当下非玩家角色的主体身份确实正在或已经完成了向“拟玩家角色”的转变。面对今天电子游戏中那些具有深度学习能力、使用大语言模型,并且拥有记忆模块,可以根据记忆流反射和规划的“生成智能体”不再简单地被理解为“非玩家角色”,而需使用“拟玩家角色”这一新的术语加以阐释和理解。
另一方面,拟玩家角色不仅在技术上实现了从被动反馈到主动生成的转变,也体现出在德勒兹意义作为“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的强度的生成。上文简略地提及了《失控玩家》这部影片的情节,其中身为非玩家角色的男主角发生转变的源头就是它对身为玩家角色的女主角产生了爱慕的情感,而情感不是数字代码所能具有的权利。主角极力摆脱虚拟世界的规则,通过觉醒的主体意识去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反过来,这种主体意识也是源自于欲望的生成。一个代码程序控制固定的、模式化的非玩家角色通过对自身欲望的认识与追寻,成为了德勒兹所说的“欲望机器”(desire machine),欲望被置于容贯性的平面,而由欲望构成的内在性的场域使所谓的“拟玩家角色”组成了德勒兹意义上和字面意义上的“无器官的身体”。“无器官的身体使得强度得以通过,它产生出强度并将它们分布于一个本身就是强度性的、非广延性的间隙(spatium)之中。它既非空间,也不在空间之中,它是以某种级度 (degré)占据着空间的物质——这个级度对应着所产生的强度”,德勒兹与加塔利进一步将无器官的身体比作一个“尚未拓展成有机体和器官组织的充实卵(egg)”,通过卵的特性来理解无器官的身体:“无器官的身体就是卵。但卵并不是退化性的,而是完全是同时性的,并将自身作为卵的结合环境。卵是纯强度的介质,是非广延的间隙,并且卵始终指涉强度的实在。卵也并非先于有机体,而是与有机体相邻,并不断地构成着自身。”[3]130-149拟玩家角色作为一个“无器官的身体”,以数字代码的维度存在,通过化身占据电子游戏的虚拟空间,依靠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拓展主体的边界与流变自身存在的意指,在自身、虚拟世界甚至现实世界中不断地生产强度,而正是这种不断的强度的生产才能将其从传统的非玩家角色中区分出来。
“拟玩家角色”主体的流变
学者蓝江在论述电子游戏中虚体的存在时,使用了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宁芙(nymph)隐喻。宁芙是希腊神话中自然幻化出的有着美丽女性形象的灵体,也是西方绘画和文学中的经典母题:“界定这四大元素精灵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没有魂,因而它们既非人类,亦非动物(因为它们也拥有理性和语言),它们也不完全是灵(因为它们有身体)。它们高于动物,而低于人类,是肉与灵的混合物,它们是纯粹而绝对的‘造物’:上帝在众多物质元素之中创造了它们,这样它们也受制于死亡,但它们被永远排斥在救赎和拯救的安济(economia) 之外。”[5]电子游戏中的虚体正如没有魂的宁芙一样,需要人为的外在影响为它赋予存在的条件和意义。正如蓝江所说:“那个虚体,通过我们的操作变成了真正具有灵魂的存在物,他们与电子游戏中的其他角色不同,它们在那个世界上具有感知,能够用自己的身体去感触世界,并用自己的电子身体对周遭的环境和威胁做出反应。”[6]另一方面,如同蓝江老师所指出的,“在电子游戏中的感知,也是一种真正的身体感知,玩家们通过宁芙化的虚体将具身世界与电子游戏的虚拟世界相连接。并且电子游戏中的自我作为一个去躯体化的数字自我存在”[6]。但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革新性的进步在电子游戏“其他角色”中的应用,使得分辨去身化的虚体与电子游戏中的其他角色已经变得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二者都是基于人类的思维和行动模式,使用自然语言通过具身经验和实时的环境进行判断,并输入指令控制的数字的化身。拟玩家角色同真人玩家一样,通过在虚拟世界中的感知和经验去操控游戏中的虚体,将虚体变成真正的存在物。因此,不仅玩家们能够通过宁芙化的虚体将具身世界与电子游戏的虚拟世界相连接,上文所述的拟玩家角色也可以理解为是基于计算机环境,大语言模型的强人工智能所使用的虚体。虚体根据自然语言模型和深度的学习能力所产生出的“具身”经验与电子游戏的虚拟世界发生关联,使拟玩家角色以玩家角色的姿态呈现在电子游戏中。可能在不久后的将来,在电子游戏的世界中,无论是通过语言、行为甚至情感的反馈,都无法区分屏幕中自己面对的角色背后,是同样具有实在肉体的玩家还是在存储区中不断运行的数字代码。
此外,在后人类主义者看来,人的身体肉身性的意义被解构。人类的身体仅仅被当作存储基因信息的物理结构,可被编码化的信息才是决定人类存在的关键。人类的具身经验与意识可以进行信息化的编码并进行上传,存储在虚拟的世界之中。马克·塞尔泽(Mark Seltzer)在《身体与机器》(Bodiesand Machines)中,将身体建构为非物质的信息的流。海瑟琳·凯勒在回应安德鲁·霍奇斯对图灵区分进行思考的人类和进行思考的机器的问题时,将答案指向了身体性的思考,即经由表现性的身体域再现的身体二者之间的关系,“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在电子环境中产生。这种解释必然会让主体成为电子人(cyborg),因为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已经通过技术密切联系起来”[7]。在后人类主义的观点中,人作为有机体的肉身性已经不再重要,甚至被视为影响人类向后人类转变的一种阻碍。仅从电子游戏来考虑,沉迷游戏的玩家通过操控游戏中的虚体并将主体意识投射于其中,无论是出于对现实生活的逃避,或是对身份的探索,抑或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塑造和肯定,相比于现实世界,他们更愿意通过虚体沉浸在游戏中的虚拟世界,其根源是否可以理解为同样是出于对人的物质性的否定和肉身性的逃离。也正是因此,在电子游戏中实在的肉身性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重要,无论是由真人玩家操控的虚体抑或是由拟人的人工智能操控的虚体,俨然成为电子游戏中虚拟世界的新的主体。
“拟玩家角色”的可能性
如今,使用基于自然语言模型的强人工智能生成的拟玩家角色已不仅是一个理想化的构想,在国内外均已有大量的尝试,并给电子游戏领域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尤其是角色扮演游戏、沙盒游戏、文字冒险游戏这类需要大量交互的游戏类型,在与基于自然语言模型的强人工智能的结合中更是展示出了巨大的潜力。2023 年1 月,网名为Bloc 的模组(mod)开发者制作了一个基于游戏《骑马与砍杀2:霸主》(Mount & Blade II: Banner Lord)的模组,并称其为“角色扮演游戏的未来”。这个模组是面向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使用自定义的故事引擎与ChatGPT,在没有加入任何给定脚本的情况下,仅需输入这些非玩家角色所处世界的背景资料与它们在游戏中的身份,在进行交流互动时,它们就会根据玩家提出的任何问题实时生成回答,而不是单一的反馈和无限的重复。这一过程中,这些角色输出的所有内容都是动态生成的。在开发者展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玩家扮演的角色与游戏中的随机角色进行随意的对话,当玩家通过键盘输入话题,那些非玩家角色就能够与玩家对话,交流游戏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比如自己的身份、附近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事件的态度等。将ChatGPT 介入电子游戏中非玩家角色的这次尝试,在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启发游戏开发者们制作了大量的模组,如在通过VR 交互的开放世界游戏《上古卷轴5:天际VR》(The Elder Scrolls Ⅴ: Skyrim ⅤR)中结合ChatGPT 和xVASynth 开发的模组,可以使非玩家角色根据玩家的对话实时生成语音反馈。
不仅是国外的游戏,在中国的游戏行业也开始出现将强人工智能与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进行结合的尝试。如由网易开发的手机端开放世界武侠游戏《逆水寒》,将搭载中国伏羲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的强人工智能。2023 年5 月,中国台北国际电脑展上,电子游戏行业的巨头英伟达公司(NVIDIA)宣布推出全新定制 AI 模型代工服务 NVIDIA ACE 游戏开发版[NVIDIA Avatar Cloud Engine(ACE)for Games],利用AI 驱动的自然语言交互技术,为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生成智能反馈,从而改变游戏体验。从这些尝试中,我们不难发现,未来的电子游戏开发虽然受到计算机算力或其他硬件设备性能的限制,但是让非玩家角色搭载具有强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已成为必然趋势。
索尼娅·菲兹克在《在远距离玩:电子游戏美学的边境》的第四章讨论了“自动化游戏”的概念。自动化不仅是指设计技术、游戏机制或新游戏类型,而且从本体论上讲,它是我们玩的一种现象。伴随着自动化的游玩与伴随着这个世界中的一种存在的模式(a mode of being)是相同的。自动化开启了理解人机关系的新途径,人类不是最受技术殖民的主人或被奴役的一方,也不是扮演操作者和被操作者的角色,而是作为一个“代理性力量的纠缠”(entanglement of agential forces)。[2]65因此在游戏过程的身份上,拟玩家角色也逐渐开始取代人类玩家角色。正如她所描述的,数字时代的人类玩家更多的是作为一个间接的角色,见证系统所谓的代理,并将重复的任务委托给算法。数字游戏的核心是机器的自动和环境动作,这种模式超越了游戏中所谓的主体—客体的边界。电子游戏中的自动化使得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游戏中玩家的主体身份,人类玩家不再是游戏中唯一的或是主要的虚体的代理,而是变成了“一个自动化系统奇观的观察者和解释者”。拟玩家角色的出现所推动的自动化,似乎不再是一种简化玩家游戏过程的机制,反而可能会剥夺玩家作为游戏主体玩游戏的权利并削弱人类玩家玩游戏的技能。在未来的电子游戏中,或许不再是以人类玩家为中心,通过非玩家角色的存在帮助人类玩家体验游戏的过程,而是由更为智能、更加拟人化的拟玩家角色与真人玩家共同在游戏中游玩,甚至是拟玩家角色通过真人玩家的存在而体验游戏。
结 语
随着电子游戏中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革新,尤其是强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模型ChatGPT 的出现,电子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正在经历一次革新性的发展,即从“非玩家角色”向“拟玩家角色”转变。拟玩家角色借助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的能力,能够打破预设的代码逻辑和固定的行为模式,实现从被动反馈到主动生成的质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带来了游戏机制的变化和玩家全新的游戏体验,更重要的是引发了对于“非玩家角色”这一术语的重新思考。根据德勒兹的思想,强人工智能技术为非玩家角色带来了一种游牧式的、生机论的逃逸线,使得它们从传统的、固定的非玩家角色的概念中解辖域化。而另一方面,拟玩家角色作为无器官的身体存在于电信号的代码维度,在不断产生强度的同时,通过化身占据虚拟世界的空间。在后人类主义的观点中,人的实在肉身性也不再重要,借由强人工智能控制的拟玩家角色的虚体与玩家的虚体之间的边界也越发模糊。因此,虽然在电子游戏中同为虚体,但相比于传统的非玩家角色,拟玩家角色脱离了原有的范畴,更加向玩家角色的身份靠拢,与玩家角色一起成为电子游戏中虚拟世界的新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