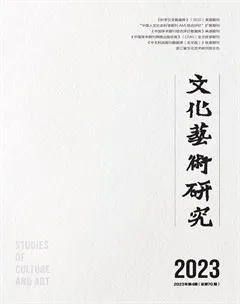军事功能游戏:用户界面的严肃性与娱乐化
李典峰
(北京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 100871)
如果孩子们从一开始做游戏起就能借助于音乐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而这种守法精神又反过来反对不法的娱乐,那么这种守法精神就会处处支配着孩子们的行为,使他们健康成长。一旦国家发生什么变革,他们就会起而恢复固有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1]140
在古希腊文中,“游戏”(παιδιά, paidia)与“儿童”(paides)有着词源上的内在联系。然而,随着识字以及教育(paideia)在古典时代的发展,游戏对儿童而言,具有了除玩耍外更大的文化意义。游戏在文化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渗透到各个方面,从宗教仪式到社交聚会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在贵族的饮酒聚会中,人们会唱歌和弹奏七弦琴,竞赛创作即兴诗句,并进行文字游戏和谜语解答。备受尊崇的音乐家、诗人和哲学家如荷马、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等,将游戏视为一种表达智慧、传递知识的方式。甚至古代的战争也被历史学家们描述为一种受规则约束、近乎仪式的游戏。贵族在童年时期,接受政治和军事领导的培训,参与体育比赛和辩论竞赛等活动。
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如今被认为是体育的运动,以及被认为是艺术的音乐、舞蹈和歌唱,实际上都是扮演着不同功能的游戏(play, paidia)。在《伊利亚特》(第九卷)中,阿喀琉斯的导师菲尼克斯(Pheonix)讲述了自己受委托教导这个男孩成为“言出法随的强者”的故事[2]258-259;而在《奥德赛》(第八卷)中,奥德修斯在旅途中面临致命的危险,法伊亚基人用舞蹈和音乐慰劳他[2]201-204。
柏拉图早期对游戏目的的讨论,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场持续了千年的辩论的起点。这场关于游戏目的的辩论对于严肃游戏研究,特别是教育应用具有直接的影响。当然,在这场游戏目的的辩论中,概念上对游戏的定义的困难与当代对严肃游戏的定义的困难相呼应。此外,在行为主义心理学范式的应用高峰时期,关于研究和衡量游戏的尝试也为这场辩论带来了启示。
与这场辩论平行并交织的,当然还有关于游戏作为软件应用的讨论。这些应用程序,尤其是严肃的、具有功能性质的游戏软件,在功能性软件的发展历史上体现出明显的目的性和环境适应性。此外,当我们回溯现代广泛接受的严肃游戏的定义时,可以发现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游戏如何功能化的历史,以及它们如何成为了承载严肃性的游戏。
考虑到严肃游戏的交叉背景和跨学科性质,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对每个相关学科的丰富而动态的历史都了解透彻。本文拟将当代学者们对严肃游戏的应用与讨论还原到其历史语境中,尝试揭示严肃游戏的隐秘的发展轨迹,弥合哲学讨论与游戏讨论之间的裂隙。
一、模拟的功能:游戏的严肃性表达
通过创建用于模拟这些社会过程的游戏,个人可以再次参与其中,思想和行动可以再次融合。在历史上那些人们参与实现伟大理念模型变革的激动人心时刻所感受到的对生活的热情可以通过严肃游戏中角色模拟的方式重新捕捉到。
——C.阿布特《严肃游戏》[3]
“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这一术语的使用可以追溯到瑞典学者克拉克·阿布特(Clark Abt)1970 年对电子游戏的类型学研究。随着电子游戏在流行文化中的普及,当代“严肃游戏”这一术语主要指数字化形式的游戏。然而,历史上也存在许多非数字化的例子。为便于记录,本文将数字严肃游戏的发展轨迹分成两期,即数字化前和数字化后。数字化前包括上述关于游戏的辩论、重要案例以及与模拟学习相关的领域。数字化后突出历史趋势的延续,使其与当前的严肃游戏研究相融合。
在电子游戏领域,“严肃”一词通常指其在防卫、教育、科学探索、医疗保健、应急管理、城市规划、工程、政治等领域中的应用。这些游戏通过模拟真实的战场场景、空中目标和操作流程,提供与实际环境相似的体验。通过游戏化的方式,操作员可以参与虚拟战斗,并进行目标识别、任务分配、指挥决策等操作。这种训练方法可以提高操作员的应变能力、决策能力和反应速度。后来早期的动作游戏设计的原则和技术主要是来自SAGE 系统①地面防空系统(Semi-Automatic Ground Environment,简称SAGE)是世界第一套防空半自动化指挥系统。它通过现代通信手段将分布在广阔战区内的各作战单元有效地联结在一起,实现了战术信息的快速处理和分发,以及作战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了作战体系的整体效能,使兵力的有限作战能力倍增。这种将各作战要素、资源和武器系统连接在同一整体的功能,是后来大多数民用游戏机开发的早期军用原型机所具备的。的用户界面(user interface,简称UI)中,以提高操作员的训练效果和使用体验。[4]
然而,对于“严肃”一词能否直接修饰游戏,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以游戏目的为基础的游戏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必需品。在其具开创性意义的著作《游戏的人》(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中,约翰·赫伊津哈从与霍尔(Hall)和格鲁斯(Groos)类似的出发点开始,研究动物玩耍的存在给人们带来的意义。对他来说,这证明了游戏先于文化社会存在,并且游戏本身具有文化生成的能力,即“文化形式起初就是以游戏的形式存在的”[5]3。这实际上否定了“严肃游戏”这一命名的合法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继续严肃游戏研究呢?
我们不妨沿着约翰·赫伊津哈对文化中的游戏要素——文化本身展现出的游戏性特质的探索。约翰·赫伊津哈最为人所知的或许是他对“魔圈”(The Magic Circle)的构想。这一构想试图捕捉游戏空间的物理或形而上学的界限:“所有的游戏都在事先划定的游戏场内进行,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理念上的,无论是故意的还是理所当然的。”[5]10在当代数字游戏研究中,这个游戏发生在独立空间的概念常常被应用于数字游戏的虚拟空间。[6]
“魔圈”被广泛应用于后来的游戏研究中,得益于凯蒂·萨伦(Katie Salen)和埃里克·齐默尔曼(Eric Zimmerman)等游戏研究者的普及,但其在严肃游戏中的应用却受到限制。其中一个例子深入讨论了“魔圈”在基于游戏的学习中的必要性,即如何打破这个游戏空间的作用。实际上,“魔圈”这一概念可能存在模糊性。相较于用户界面这一具体的计算机科学术语,它有着更多的人文意涵,同时伴随着语义层面的所指外溢性,特别是随着普遍游戏的兴起,但它对后来的严肃游戏开发具有启迪作用。这就造成了“魔圈”变成某种分辨玩与不玩之间的界限,是“模糊和可渗透的”,直接涉及严肃游戏设计中乐趣和目的的内在紧张关系。
尽管“魔圈”在当前尤为重要,但讨论也受到其他早期有关游戏目的的理论的影响。社会学习理论家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将游戏概念化为愿望实现,即孩子们利用想象力从即时情境的限制中解放自己。此外,维果茨基认为“在游戏中,孩子总是表现出超越他们平时年龄和日常行为的行为;在游戏中,他们就像比自己高一头”[7]。
维果茨基的同时代人让·皮亚杰(Jean Piaget)认为,通过重复,游戏可以巩固现有的技能,并发展出一种掌握感。与其他理论家相反,皮亚杰对游戏的作用几乎没有直接关注。然而,他对认知发展阶段的关注影响了心理学家对游戏阶段进行分类的工作。①参见J.皮亚杰、B.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吴福元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46 页。对于这一理论,美国认识理论学家David Cohen 已有了新的发展。可参见Cohen, D. The Development of Play, Routledge, 2007。此外,儿童在扮演社会角色(如医生或消防员)时所进行的假扮游戏可以被视为其探索文化规范的一种方式。[8]因此,儿童玩特定类型游戏的能力,已经被临床心理领域专家用作评估他们发展的手段。在早期教育游戏理论家的研究之后,人们普遍认为游戏在儿童的认知、情感和社交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进入21 世纪后,不同类型的教育游戏,尤其是那些为年轻学习者设计的游戏激增。其中的许多游戏不是基于计算机的,而是采用了其他传统游戏系统的模型,包括控制台和手持设备。1999 年,跳蛙公司(Leap Frog Enterprises)推出了一款名为LeapPad 的个人电子设备。它将互动书与卡带结合在一起,让孩子们可以玩游戏,并与纸质书互动。这一灵感来源于当时任天堂的Game Boy 等手持游戏机的流行。该公司还在2003 年推出了名为Leapster 的手持游戏系统。该系统是基于卡带的,集成了带有教育内容的街机式游戏。[9]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的严肃游戏理论发展也大多侧重于认知和教育领域的探索,发表于《电化教育研究》上的几篇高引用率论文,如尚俊杰、庄绍勇、蒋宇的《教育游戏面临的三层困难和障碍——再论发展轻游戏的必要性》[10]和鲍雪莹、赵宇翔的《游戏化学习的研究进展及展望》[11]分别涉及教育心理学、游戏化学习,从多个维度展开严肃游戏理论的讨论,并立足于本土的数字化教育和国内学科建设。
而在认知心理学方面,发表于《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电子游戏训练能提高成人的认知控制能力》("Video Game Training Enhances Cognitive Control in Older Adults")[12]已通过定量研究,将严肃游戏的功能性突显,并明确可以作为认知领域的电子处方药部署给有需要的患者。国内的学者也早就开始了相关研究,如丁丽娜、蔡春凤的《自闭症儿童严肃游戏干预研究进展》探讨的是自闭症儿童严肃游戏干预问题[13],李林英、邹昕、王春梅的《严肃游戏: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创新》则重在探讨社会学习、投影身份等心理学理论的应用实践[14]。
关于游戏的严肃性和功能性领域探讨,我们无法忽视的是皮亚斯(Clus Pias)的《电子游戏世界》一书对游戏媒介物质历史的奠基性总结工作。美国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了一种心理测试,即陆军心理测试(Army Mental Tests,简写为AMT)。皮亚斯认为,AMT 是计算机游戏的前身之一,因为它们都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虚拟环境,都需要用户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操作和决策。[4]24-25他还指出,AMT、兵棋(wargames)和严肃游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们都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虚拟环境,都需要玩家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操作和决策。AMT 对用户心理状态的测试和评估研究为后来兵棋训练玩家决策和行动力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模型框架。
由此可见,军事功能游戏更加突出它在服务国防知识传播方面的功能性。“在美军‘像训练一样打仗,像打仗一样训练’的思想指导下,对训练想定、训练环境的建设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使得美军开始开发各种模拟真实战斗的训练游戏。1994 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游戏军事训练机构。”[15]我国早期的兵棋研究者,如杨南征等军事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在21 世纪初就开始了相关方面的工作。[16]
在杨南征的研究中,兵棋作为一种生成死亡知觉的推演工具,是以一系列兼具快速消灭和机动响应为目的开发的人机耦合系统。这便衍生出了两条具有反馈功能的循环回路(loop):军事运筹和数学模拟层面的兰彻斯特方程;多模态反馈具身性(embodiment)的决策系统。
二、武器的界面:数字模拟与打击反馈
兵棋作为早期的严肃游戏,以可交互性的视知觉系统为指挥与控制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博弈研判参考,这替代了一切人类心算速度和知觉可靠性。以下我们将从两个层面来阐述这两种不同的游戏功能。
(一)数字模拟层
在早期运筹学的发展中,兰彻斯特定律是计算军事力量比拼的数学公式,也是军事运筹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性理论概念。兰彻斯特方程是描述两支军队的力量A 和B 的时间依赖性作为时间函数的微分方程,该函数主要描述两军对战过程中战斗部门的火力杀伤和火力存量。1915 年和1916 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M.奥西波夫(M. Osipo)和弗雷德里克·兰彻斯特(Frederick W. Lanchester)分别设计了一系列微分方程来证明对立力量之间的力量关系。其中包括兰彻斯特线性定律(用于古代战斗)和兰彻斯特平方定律(用于使用远程武器,如火器的现代战斗)。
在战斗模拟设计环节,严肃游戏需要优秀的数值策划。为了让影像中的战斗符合某种杀伤拟真状态,早期的兵棋推演作为严肃游戏的主要类型,大都建立在兰彻斯特定律的推演基础上。与其说将兰彻斯特方程应用到实时演算的冲突模型中去,不如说当代市场上的大多数即时战略游戏都是基于兰彻斯特方程书写的兵棋推演模型简化的知觉界面。这些游戏仿真的战斗结果,实际上是以换皮的方式制造出来的,并且事实是,对运动影像设计而言,兰彻斯特方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实用——它适合对非常理想化、单一化的战场情况进行模拟,比如没有第三方火力、友方伤害等,并且排除地形因素等。游戏之所以这么设计,是因为后期模拟出来的效果更为真实直观,既符合影像传递给观众的戏剧真实性,又很大程度上兼顾了某种客观历史的模拟再现。
兰彻斯特方程的前两个方程是线性律,第三个方程是平方律,分别对应了一对一的白刃战、间瞄阵地炮战和现代直瞄远火战。这三个方程是一个渐进推导的过程。第一个方程很简单,但却是战斗量化、模型建立的基础。
在兰彻斯特第一方程这个作为战场上可以持续站场输出火力的“正方形”的基础上,我们明白了站场和输出的关系后,再来探讨间瞄战斗和直瞄战斗,才能有一个最基本的逻辑起点。下面我们主要介绍兰彻斯特第三方程和第一方程的数学表达——这两组方程在描述杀伤效率上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差异,并结合一个历史战例及未来战争运用,以供读者理解兵棋推演作为最早的军事功能游戏,在数字模拟层面如何表达死亡这个严肃又古老的命题。
在古代战争中,一般士兵与士兵之间的战斗都是面对面的白刃战。因为交战行动是暴露的、直接的、一对一的,所以我们假设组成白刃战的许多格斗都是按一种方式进行的。由于兵器杀伤距离的限制(敌我双方要面对面近距离交战),即使在战场上集中比敌军数量更多的士兵,在同一时刻能够发挥出战斗效能的士兵也是一样的(注意这个假设最重要的前提是一对一,所以兰彻斯特第一定律并没有否定古代战争中关于侧翼攻击等战术的作用)。
其中,t示战斗时刻,n(t)、m(t)表示战斗开始后t时刻双方在战斗中剩余的战斗单位数量,α、β分别表示双方在单位时间内杀伤对方战斗单位的比例(战斗系数),整理两式可得:
通过每学期的家长会,向家长介绍学生现阶段的年龄特征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结合教育专家的讲座向家长介绍关注孩子的重要性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指导家长在孩子作业本上要字迹端正地签名做好榜样的示范;引导家长有效关注孩子成长的关键期;关注孩子学习习惯的养成和行为能力的培养。规范的家长签名,不仅能让学生从父母身上真切感受到父母对自己教育的重视,也能给孩子的书写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即时战略游戏中,玩家经常使用的“堵口战术”其实就是对这一方程的直觉性应用,历史上最著名的“堵口战术”就是古代希波战争时期的温泉关战役,电影《斯巴达300 勇士》(2006)非常形象地再现了当年的这一幕。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带领300 名斯巴达人,在温泉关口阻击了波斯“神王”薛西斯和他超过30 万名士兵的强大军队。[17]虽然最终并没有阻止波斯军的进攻,但为整个希波战争的胜利争取了时间。因为温泉关是一个易守难攻的狭窄通道,一边是大海,另一边是陡峭的悬崖。交战双方只能在这个狭窄通道上面对面地进行白刃战,这是兰彻斯特第一线性模型的实战运用。
我们设斯巴达300 勇士的总人数为m,m=300,波斯军队总人数n,n=200000。这里我们以波斯军单兵作战能力为参考量,即设波斯军单兵作战能力为α,α=1。斯巴达是一个以武力为荣的城邦,勇士们从小就接受军事化训练,其个人战斗能力远超过波斯军队,相当于一人可敌十人的作战力量。因此,我们将斯巴达战士的单兵作战能力表示为β,并设定β为10。整场战斗将持续到斯巴达的300 名勇士全部阵亡,即当达到时刻t时,m(t)=0。根据公式:
解得波斯军剩余兵力为n(t)=17000,即损失兵力为3000,斯巴达军损失兵力为300,战损比为10 ∶1,即β∶α。根据实际交战结果波斯军队阵亡2 万人的数据进行修正,以α=1 为基本量,解得β=66.67,即1 个斯巴达勇士的战斗效能约等于67 个波斯士兵的战斗效能,计算结果显示出了两军士兵之间巨大的作战差距。因此,有部分学者对波斯军队阵亡2 万人这个数据提出了疑问,其数据支撑即为兰彻斯特第一线性律。如果算上地形优势,也就是说斯巴达士兵实际上借用了地形优势,事实上造成波斯士兵的排队效应,每一名波斯士兵都无法借助其他十几名战友从正面之外的其他三个方向攻击斯巴达士兵,那么在这一情况下就造成了β 值出乎常理地高,铸成了书写军事神话的某种可能性。
当然,兰彻斯特第一线性律只是一种理想的模型,在运用数学模型来解释作战行动时,必须要建立一种最理想、最基本、最简单的战斗模型,即排除地形、天候、水文、心理士气、战斗态势等因素的作战过程,我们不能苛求这个模型在模拟数据上的精确性,因为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建立了这一模型——将半经验的数学描述方法引入作战模拟研究中,并使之有了严格的理论依据。
从数学模拟层面展开说明第一方程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对比第三方程在数学层面所模拟的高效杀伤能力;另一方面是我们需要借此理解20 世纪以后的战争同古代白刃战之间的区别。在交战双方开始使用直接瞄准火力相互对抗的年代,非常强调火力的集中性,以交叉火力快速消灭已受损的目标,这在策略电子游戏领域有一个说法“血线嘲讽”。因此交战行动在本质上是集体合作的,一方通过火力合作先杀伤敌人来阻止敌人对己方的杀伤。
远距离交战时,任何一方参战单位数量与参战单位战斗效率的平方成正比,这便是被称为兰彻斯特平方定律的第三方程。安装了瞄具的高射速武器在远距离瞄准射击的情况下,可以射击敌方阵线中的任何敌人,也会被敌方阵线中的任何敌人攻击。这时军队消耗的比率与双方的火力数量有关(假设无战斗力差异)。兰彻斯特认为这样的军队实力不只与军队的作战单位数量有关,而是与数量的平方有关。他研究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总结的另一条实战经验:
如果两支数量不等的步兵和炮兵编成的部队在同样大的地区内平行配置,那么,在所有的射击都是以单个人为目标的情况下,命中的弹数同射击的人数成正比。①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1965 年,第1391 页,转引自参考文献[16],第143 页。
也就是说,任何一方的损伤速率都与对方向其开火的战斗单位数量成正比。在双方战斗力可以量化的情况下,强大的一方每增长一点,优势以几何递增。它的方程被表示为:
作为一种军事运筹学中的数学模型,兰彻斯特模型用于优化作战计划和资源分配。这是人类对工业化时代致命武器进行火控描述的第一次尝试,维利里奥在《知觉后勤学》中说:“一种高射炮在遥测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使弹道轨迹与目标飞机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上重合,通过在屏幕上实时立体叠加两个飞行图像来实现致命的结果。因此,在拿破仑战争中,浴血厮杀的演员有节奏地移动,徒手格斗靠肉眼和武器进行,在本世纪初,这种作战方式被暗箱取代,面对面的对抗被即时界面取代,地理距离被实时概念取代。”[18]
兰彻斯特模型与陆军兵棋的数值设计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早期大多数兵棋推演类的严肃游戏,其主要功能就是向官兵再现兰彻斯特方程的实际运用场景,让他们获得直观的体悟。
(二)具身反馈层
兵棋作为军用领域的一种教育工具,促发了商业兵棋数字化和平台应用软件的兴起。20 世纪90年代,大多数玩家都玩过教育电脑游戏,如经典的小霸王学习机等。从那时起,将游戏应用于教育的方式越来越受欢迎,学生也越来越多地在课堂上使用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
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催生了新型的远程在线兵棋。这些数字兵棋通过桌面模拟器和steam 等平台连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玩家。这种现成的机会为培养新的兵棋推演提供了自然的途径和好处。
媒体研究学者杰夫·金(Geoff King)和塔妮娅·格沃斯卡(Tanya Krzywinska)认为,电子游戏有独特的模态(Modal),“电子游戏的模态有自身独有的媒介符号,并能与其他媒体区分开”[19]65-66。以军事模拟射击游戏《全频段战士》(Full Spectrum Warrior)为例,杰夫·金认为,一些后来作为商业发布的内容在游戏内部的肖似符号(icon)上,设计了模糊原有军用模态化(modality)的平视操作台(head-up display,简称HUD),以此来标榜“真实性”或“拟真性”的地位。“特别是它最初是为美国陆军设计的训练助手”[19]69-70,游戏内部叙事是与“前塔利班”及“伊拉克忠诚分子”作战的城市战争,它被明确地定位为现实世界中军事行动的预演。
杰夫·金和格沃斯卡两位学者在分析军事模拟软件及其衍生物电子游戏时,引入了模态这个概念。在这里解释下其来源。模态在科学和技术领域涉及知觉问题时,主要由两种使用语境构成。第一种是刺激模态(stimulus modality,或称为感觉模态),是人体神经网络被刺激后在知觉层面形成的东西。例如,在热或冷刺激受体后,温度模态被记录下来。一些感官模态包括光、声音、温度、味觉、压力和嗅觉,被体外刺激激活的神经细胞受体的类型和位置在感觉编码中起着主要作用。在身体有意识或潜意识层面形成了刺激经验时,身体会自发调度所有的感官模态一起工作,以强化被刺激时产生的感觉。而在人机交互的计算机科学语境中,模态(modality)是指计算机和人之间独立的“感觉输入/反馈输出”通道。如果一个系统只有一个实现的模态,那么它被指定为“单模态”(unimodal)。如果有多个通道,那么它被指定为“多模态”(multimodal)。当多个模态可用于某些任务或辅助任务时,系统被称为具有“重叠模态”。如果一个多模态中有多个模态处于待用状态,则细分成为“重叠模态”与“冗余模态”。多种模式可以结合使用,提供互补的方法。冗余模态一般能更有效地传达信息的不同模式,可定义为两种形式:人机(human-computer)和计算机—人模态(computer-human modality)。电子游戏是典型的调用计算多模态叠加模式进行处理的软件,“感官输出/反馈输入”的交互至少在20 世纪80 年代使用图像显示技术后,包括触觉、视觉、听觉等模态。
一款优秀的功能游戏,可以充分调动用户界面的所有要素进行叙事,要设法融合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模态——身体感知的“刺激模态”和计算机技术的“感官/反馈模态”,而这两种模态叠加形成的任务训练,要求玩家“具身化”(embodiment)地融入交互界面(interface)[20]。如果电影媒介的基本模态分析可以还原为单一“镜头”,那么对于电子游戏产生“具身化”绵延的控制系统循环,我们只能把它还原为一种动态的“身体—意象”(body-image)单位结构[21],可以称之为“肉—帧”(chairframe)。每一帧画面(其实包含声音和震动,这是一种基于感官反馈的媒介系统“框架”)投射到“肉身”的基质上,催动电子竞技运动员做出他相应的操作反馈,而这些熟练精准的反馈又来自他平时训练所打造的“身体图式”(body schema)①"A body image consists of a system of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beliefs pertaining to one's own body. In contrast, a body schema is a system of sensory-motor capacities that function without awareness or the necessity of perceptual monitoring." A. Gregersen and T. Grodal: "Embodiment and Interface",inThe Ⅴideo Game Theory Reader, Routledge, 2008, page 67。。
杰夫·金和格沃斯卡调用了计算机科学的模态理论,解释了电子游戏设计的底层逻辑,但没有解释电子竞技内部为何具有高度沉浸性的叙事机制。用户界面内外的“人体感官/计算机反馈”形成交叉闭环,就像维利里奥的环形“竞速场”(dromo-)[22],人类的知觉在身体内部的竞速场中疯狂追逐更精准、更强烈的刺激,并企图让下一次应对刺激的反馈更精确,知觉最终不再需要将刺激反馈到大脑,并直接在肌肉层面记录所有刺激/反馈在时空中的精准地位。意识在“竞速场”的高速运动中融化,“身体图式”从中解放,这个过程是所有竞技运动员需要通过自身反复训练完成的运动本能,在高强度、高频道的多刺激模态(stimulus multimodality)中,身体形成了不用再通过大脑皮层的逻辑思考支配自己如何选择输入策略,这便是我们所谓的“肌肉记忆”[23]。
这种“身体图式”是通过肌肉记忆形成的叙事,它将世界以“肉—帧”为单位记录在身体中。如果用文字翻译它,我们可以在上古战争的传说中,看到《伊利亚特》中阿基里斯(Achilles)在战场上精确命中赫克托尔(Hector)铠甲的缝隙;在描写现代战争的《红岩》中,看到双枪老太婆精准地射穿敌人的颅骨;亦如在电子竞技中,看到梅原大吾在《街霸》比赛中,使用“肯”点击每一下格挡键,都精确地挡住“春丽”放出的“凤翼扇”。②Chris Baker,Flashback: "Why 2004 'Street Fighter' Match Is Esports' Most Thrilling Moment", Rolling Stone, July 21, 2016。
在以60 帧每秒为刷新率的屏幕面前,身体需要应对的“世界”相对速度实际上变慢了,面对每十分之一秒放出6 幅不同动画图像的动作格斗电子游戏软件,电子竞技运动员需要锻炼自己更精确的反馈能力。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所有在模拟飞行软件上学会战斗机起降的严肃游戏用户。
从物质层面的特点看,高难度的电子竞技要求玩家的身体全方位地适应电子设备的操作界面,玩家“肉体的状态要求一种新的装配逻辑,它既不能彻底接受控制,也不能失去控制,就像《地狱边缘》(Limbo,1984)③1984 年,Bernard Wolfe 创作的科幻小说。中描述的赛博格世界,人在主体认知的边缘徘徊”[24]。新的装配系统需要玩家重新分配自己的感性经验以适应不同游戏情节所带来的知觉场域,而早期的电子游戏玩家由于投入更多的时间参与游戏,也在有意识地逐步提高整个游戏的对抗强度,这种内卷性的竞争,给后加入的玩家带来某种基于学习/训练时长而致的技术壁垒,这是电子竞技的玩家们从二级玩家(遵守游戏规则)转为一级玩家(建立游戏规则)的过程。[25]比较著名的案例是,在网飞(Netflix)关于电子游戏纪录片《高分》(High Score)中,麻省理工学院的1975 年级本科生道格·麦克雷(Doug Macre)与史蒂夫·高尔森(Steve Golson)④道格·麦克雷,通用计算机公司GCC 的奠基人之一。GCC 公司成立于1981 年,由道格·麦克雷、约翰·蒂尔科(John Tylko)、凯文·柯伦(Kevin Curran)共同创立。它最初是一家电子游戏公司,后来改为制造计算机外设。史蒂夫·高尔森和道格·麦克雷一起从麻省理工学院辍学,改进游戏机硬件,并开发了《吃豆人》(Pac-Man)的经典续作《吃豆人小姐》(Ms. Pac-Man)。,为了让玩家持续沉溺于投币游戏机,从硬件上修改游戏,以提升游戏难度,由此催生了比拼通关速度的社区游戏锦标赛。
“肉—帧”通过界面技术相互勾连,这也就是为什么从“魔环”的角度讨论严肃游戏时,我们无法将娱乐与严肃这对二分概念进行严格的区分,就像《安德游戏》中6 岁的天才玩家安德无法区分他是在游戏中拿分还是在执行一场行星级别的屠杀。实际上,用户界面和功能游戏(applied games)是无法进行严格区分的,这与半自动地面防空系统SAGE 作为美国冷战时期早期的一种战术防空系统所使用的火控雷达有关。它本来就是一个基于计算机的系统,用于监控和控制空中目标,并向作战指挥部提供实时的情报和指导。SAGE 系统的用户界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提供了操作员与系统进行交互的手段,使其能够有效地监控和控制空中目标。
在早期的SAGE 系统中,用户界面是基于图形显示终端的。操作员可以通过这些终端查看雷达探测到的目标数据、航空器的位置、飞行路径和速度等信息。他们可以使用键盘和控制杆等输入设备与系统进行交互,例如选择目标、分配任务、发出指令等。这部分通过用户界面发布的任务,后来瑞典游戏哲学家阿布特(Clark C. Abt)在其著作《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中,称之为严肃游戏或功能游戏。这便有了我们之前的关于“serious”与“play”的讨论。如果我们主要是为了描述一种非纯粹以娱乐为目的的软件,它同时具有精密计算的数学模拟层和高度仿真的具身反馈层的话,那么不妨以“功能游戏”为其命名。这包含了一系列汽修工程教学软件、远程医疗执行软件、军事指挥控制软件和大部分在幻想世界进行多人对抗的电子竞技软件。
三、平战转换窗:可高速整合的动员性
具有功能性的图形界面涉及当今网络社会中几乎每个公民生活领域的功能,无论是劳动、教育、交流还是休闲。这是游戏化的开始也是结束,不是因为世界越来越像游戏,而是因为游戏世界本来就是世界的一部分。博格斯特就认为“剥削软件”的游戏化并不影响它的本质属性。①"I've suggested the term 'exploitationware' as a more accurate name for gamification's true purpose, for those of us still interested in truth.Exploitationware captures gamifiers' real intentions: a grifter's game, pursued to capitalize on a cultural moment, through services about which they have questionable expertise, to bring about results meant to last only long enough to pad their bank accounts before the next bullshit trend comes along." Steffen P. Walz and Sebastian Deterding: The Gameful World, MIT Press, 2015, page 69.不论是军用的严肃兵棋还是民用的娱乐竞技软件,图形界面派发的任务目的都是通过反馈回路对用户进行某种“肉—帧”训练,这种训练旨在通过用户/玩家在软件层和硬件层的反复磨合,让玩家达到指定分数。
媒介学者全喜卿在其著作《程序视觉:软件与内存》(Programmed Ⅴisions: Software and Memory)中对派发任务的所谓“友好型”用户界面有过论述,后来被刊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跨学科学术期刊《灰房子》(Grey Room)上:
界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硬件的假想关系:它们不代表晶体管,而是代表台式电脑和回收箱。界面和操作系统产生“用户”——一个人和所有人。没有操作系统,就无法访问硬件;没有操作系统,就没有动作,没有实践,也就没有用户。重要的是,操作系统提供的“选择”限制了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可以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然而,你没有意识到软件的不断限制和质疑(也被称为它的“用户友好性”)……[26]
从全喜卿的这一界面政治学批判可看出,在功能游戏之类的软件设计中,存在着一种“伦理—美学”的政治,它不受主权例外框架内的法律政治辖制,将用户与界面系统的大多数感知区分开。从近半个世纪前图形界面的诞生,到如今对生物感官的反馈回路的模仿及其所带来的知觉混淆,一直是界面设计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在阿甘本的政治哲学著作中,他认为“主权者最初被定位在法律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秩序的门槛上,通过对其例外的确定,积极地描绘了国家的法律内部性。因此,这种关系,或者在更极端的时期,例外状态是任何司法管辖空间的积极定义的关键部分”[27]。用阿甘本的话来说,用户界面的出现构成了一种永久的例外关系,所谓的“用户友好”界面设计,其本来目的是将用户排除在技术政治秩序之外。在界面构成的这种例外关系里,用户永远是被统治的一方。
2013 年出版的《界面效应》(The Interface Effect)是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R. Galloway)“控制寓言”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基于长期的媒介研究,以及对电影和电子游戏的观察,他提出了“界面效应”的概念。[28]也正因此,亚历山大·加洛韦没有提供对界面的正式的定义,也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详尽的分类。他认为,界面不是一个稳定的对象,而是一个多重中介过程。换句话说,界面不仅仅是笔记本电脑LED 或电视屏幕,不只是微软视窗(Windows)操作系统或苹果OS 界面(Mac OS),也不只是当代电子游戏的超媒体平视显示器,它还包含无数平行展开的信息形式(健康水平、地图位置、速度、时间、消息选项等)。亚历山大·加洛韦认为,界面“不是一件物体”,它是“一种效果”,一种调解(mediation)或互动(interaction)的技巧,或者说是一种“阈值”(threshold)。这一概念上的转变与麦克卢汉(McLuhan)等批评家所采取的以对象为中心的方法不同。对麦克卢汉而言,媒体对象是人体的技术延伸。其立场也与基特勒不同。基特勒的观点是,媒体对象有自己的技术逻辑,只是偶尔间接地与人类的感知交叉。亚历山大·加洛韦借鉴了一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包括像马丁·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将技术视为技术、艺术、习惯、精神或生活实践”。从这个角度看,媒体不是“对象或基质”,而是“中介实践”(practice of mediation,或用计算机术语翻译为“调解实践”)。亚历山大·加洛韦的方法将注意力从稳定的界面对象转移到了动态的界面过程上。所以,从他的角度看,计算机不再是标准化和吸收所有其他媒体的媒体机器(包括印刷文本、录音、电影和游戏),而是一个通过界面效应完成不同媒介状态转换的翻译中介。这个中介所需要翻译的内容,完全是由隐蔽在系统背后的设计者所决定。这种“隐蔽自身—瞄准对象—摧毁目标”的行动逻辑也符合基特勒对计算机的判断,即“计算机是一种以消灭另一台硬件为目的的硬件”[29]。
而军事功能游戏的出现,极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些媒介哲学家对计算机功能的预言。通过大量投放军事模拟游戏,美军在冷战期间完成了某种被称为“军队分布式模拟网络”[30]36的部署,这些软件包含并不仅仅应用于训练战斗机飞行员的微软《模拟飞行1.0》(Microsoft Flight Simulator 1.0,1982),以及前文提到的《全频带武士》等。受《反恐精英》在商业电子游戏领域的巨大成功影响,美军随后在2003 年推出了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美国陆军》。这款软件由美国陆军红石兵工厂陆军游戏工作室研发,采取免费下载制,鼓励更多的玩家进入其中。[30]60《美国陆军》取得了巨大成功,达到了20 世纪80 年代末至新千年模拟网络投资的顶峰。军方利用网络化模拟器复盘评估过往战役,并且为未来战役进行训练准备和宣传动员,前者可充分提高年轻军官的战备意识和军事素养,后者可在民众之间树立优秀正面的军事形象。《美国陆军》的成功,让美军看到了将各个系统整合成一个普遍使用的平台的前景。模拟网络之父杰克·A.索普在一篇题为《分布式模拟的前景,永恒世界,指挥和控制》的讲话中,专门谈到了军事功能游戏对未来军事训练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影响。他没有首先提及军方,而是提到了奥森·斯科特·卡德的科幻小说《安德的游戏》。[30]65
小 结
SAGE 也好,《美国陆军》也罢,猎杀模拟或军事功能游戏的设计来源于美军冷战时期对战争的想象,以及对己方军事行动正义性的塑造。索普上校(或称索普博士)以《安德的游戏》为想象力的母本建立起当代军用动员网络,其目的就是将六岁的军事天才在模拟系统中选拔出来。动作游戏、冒险游戏、即时战略游戏,作为玩家的我们在消费它们的同时,是否注意到了它们对我们的改变?
回到文章的开头,在《理想国》被书写的年代,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来说,“什么是正义?”和“人类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这样的重要问题,是和当时苏格拉底所提倡的游戏教育方法联系起来的,游戏和辩证法相似,不是一种提高政治生涯的手段,而是一种揭示真理的方式。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6 卷)①中译本把“问答游戏”翻译为“问答法”,直接剥离了关于游戏的讨论。中,苏格拉底的对话者阿迪曼托斯(Adimantus)说:
你的听众认为,由于他们缺乏问答游戏的经验,他们在每个问题上都被论点引入歧途。当这些碎片在讨论结束时累积起来时,他们最初所说的东西就显得矛盾了。就像业余跳棋玩家最终被专家玩家困住无法移动棋子一样,对话者最终被这种用言语而非计数器玩的跳棋游戏所阻塞,并且他们的嘴巴也被堵住了。但真理并不受那个结果的影响。[1]234
这些以冲突和政治辩论为基础的娱乐游戏,可能导致需要更清晰地阐明娱乐游戏与严肃模拟之间的区别,在建立具有鲜明的正义性区分之前,讨论游戏本身的有趣和无趣反而变成了次要问题。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是,苏格拉底认为孩童会因为游戏传递的理念而对国家产生认同,并因此被感召,从而奋起守卫它。这便是古代先哲们对游戏所蕴含动员能力的指认,而这也是游戏最为严肃的一种功能。
修昔底德陷阱与竞速政治局面的形成,或许是由于某种信息传播的鸿沟,以致信息交流不顺畅,彼此难以形成充分的理解和共识,但被人为设计的界面自身就包含对抗性,这便使矛盾在发展到全民开始调用这些系统时,作为军事娱乐的复合体,它默默地启动了战争机器的齿轮,风险管控已经失效。这就如同阿迪曼托斯对修辞术的滥用,苏格拉底认为这种行为会构成一种零和博弈的“棋盘游戏”,导致僵局并使参与者一无所获。
所以,当一方开始调用这类界面瞄准另一方后,忽视这类界面的存在,并试图继续完成对话已经成为奢谈。对抗也是某种唯一可以继续严肃对话的方式,这时候,作为被瞄准的一方,我们或许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一场已经落后的“竞速游戏”中存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