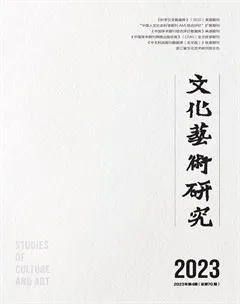游戏中的游戏:电子游戏的双重(或多重)虚构层级①
雷吉娜·塞瓦尔德 文 徐阳日强 译
(伯明翰城市大学 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院,伯明翰市 B5 5JU;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引 言
(电子)游戏之所以不同于现实世界,原因在于我们②本文中的“我们”特指电子游戏玩家。假想式地(make-believe)参与其中。这意味着,在玩游戏时,我们将自身沉浸在一个虚构世界③根据格兰特·塔维诺(Grant Tavinor),叙事型电子游戏被认为是虚构的,并且被定义为这样一种作品:“它的人物、地点、事件、目标以及行动都是虚构而非真实的。一个强有力的假设性观点可能声称电子游戏本质上是虚构的,因为它们必然描绘虚构的人物、地点、物体、事件和动作。”参见Grant Tavinor: "Videogames and fictionalism", The Philosophy of Computer Games, vol.7, Springer, 2012, page 185-199。因此,在(叙事型)电子游戏中创造的世界由于其虚构的状态而与现实不同,但可能会用虚构以外的其他术语来指代,例如罗歇·凯约瓦(Roger Caillois)将其描述为“一种第二现实或……自由的非真实”。参见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University of Ilinois Press, 200l。中并展开行动。我们操控着虚拟的化身,并通过它来使用武器、体验冒险、进行战斗以及与其他玩家互动。在此沉浸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压制“游戏世界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令其不起作用,以便接受来自游戏世界的幻觉。因此,沉浸感对于我们如何理解游戏是十分重要的——它标明了虚假与虚构的差异所在。然而,沉浸并不等同于天真(naïveté),换言之,沉浸并不意味着玩家真的会相信其所在的游戏世界是真实的,或将其与现实世界相混淆。相反,沉浸更多地指向这样一种感受,即接受游戏世界的幻觉、承认它的规则。不仅如此,游戏世界的存在对我们而言,甚至具有着超出于游戏之外的真实性,比如当我们在平台上与其他玩家交流经验或进行讨论时。不过,尽管存在这种沉浸,玩游戏仍是一种从根本上带有反身性的、自觉的、克制的和疏离的模式。
然而,如果这种创造着独立幻觉的游戏世界包含一些戏谑的、不同于我们所进入游戏世界的构成元素,又会发生什么呢?在文章接下来的部分,我将继续探讨“游戏中的游戏”对我们关于游戏世界和各类游戏的一般看法以及对假想的概念具有哪些影响。相对于被包含在其他游戏之中的子游戏(minigames)①“子游戏”的决定性特征是它们必须嵌入另一个游戏中,因此它们不同于像克拉克·阿尔德里奇(Clark Aldrich)所定义的独立迷你游戏。参见Clark Aldrich: The Complete Guide to Simulations & Serious Games: How the Most Ⅴaluable Content Will Be Created in the Age Beyond Gutenberg to Google, Pfeiffer, 2009。,我将包含其他游戏的游戏称为母游戏(macrogames)。当以一种批判性视角反观游戏性(gameness)②本文对“游戏性”的理解基于塞巴斯蒂安·热沃(Sébastien Genvo)的观点,即“游戏导向的设备必须通过符合其行动的某些文化表征的实用标记来获取受众对其可玩性的信任,并促使受众将此对象视为游戏”。换言之,游戏必须包含着向玩家表明它是游戏的元素。热沃进一步定义和讨论了这些特征,特别是关于“游戏伦理”(ludic ethos)的概念,它“使我们理解个人如何在游戏活动中受到‘实用标记’(pragmatic markers)的引导,以及系统如何建构起一个被视为游戏的有着特定价值观念的宇宙”。参见Sébastien Genvo: Defining and Designing Expessive Games: The Case of Keys of a Gamespace, Kinephanos, 2016, page 90-106。和游戏时,即使留意到其中的戏谑元素,这类游戏也不一定会对幻觉造成干扰。
为兼顾“游戏中的游戏”所采用的不同形态的自反性模式,本文将先就游戏及其与幻觉③根据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幻觉不应被看作一种欺骗,而应被理解为一种创造与现实不同的世界的审美过程。虽然受众渴望沉浸在由媒介制造的这种幻觉中,但由于意识到它与现实的差异,一种反思、自觉和批判性的立场抵消了潜在的幻想。参见Werner Wolf: Ästhetische Illusion und Illusionsdurchbrechung in der Erzählkunst: Theorie und Geschichte mit Schwerpunkt auf englischem illusionsstörenden Erzählen, Niemeyer, 1993。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理论探讨,以求最终确证我们乐于玩游戏的原因,以及我们是怎样进入游戏所创造的世界之中的。在这之后,是关于“游戏中的游戏”所建构出的交错的虚构层级的讨论。我将区分出以下两种结构:中国套盒结构(Chinese-box structures),即一个游戏中包含着一个独立于主游戏的游戏;无限镜像(mise-en-abyme)结构,该术语意指被嵌入游戏的镜像性特征。这两者共同组成对各式各样的“游戏中的游戏”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同时构成本文的第三个部分。继而,我将进一步区分出不影响母游戏推进的和作为母游戏固有组成部分的两种子游戏。该分析以两个问题为导向,即对子游戏的合并如何影响我们对母游戏的游戏世界的感知,以及子游戏如何能(在不舍弃主游戏幻觉的前提下)被用于从游戏内部对游戏性进行批判性讨论。最终,本文会通过探讨各式典型的电子游戏案例,得到一个针对子游戏及其与幻觉概念之间关系的综合性分析结果。
一、我们的游戏意愿
游戏常常被视为一种用以分散注意力的消遣行为,就像是现实生活的多余之物。然而,只要对游戏的历史加以考量,便可看出它对文化的形成有着重要的贡献。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将游戏行为(play)视为以游戏(game)为目的的活动,并对其特征做了如下定义:
游戏行为是一种自愿行为,或一种消遣,它在某些特定时空范围内生效,按照自愿接受但具有绝对约束力的规则进行。它自身带有目标预设,并伴随着一种紧张感、愉悦感以及与日常生活(ordinary life)不同(different)的感觉。[1]
赫伊津哈并未对游戏和现实做出等级上的划分,但他认为游戏行为与现实生活确有不同之处。他的这一定义给“什么可以被认为是游戏行为或游戏的内含”这一问题留出了相对自由的空间。罗歇·凯约瓦(Roger Caillois)基于赫伊津哈的定义,在一些方面做了补充,并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以下六种游戏行为的特征:自由(free)——非强制性的,分立(separate)——存在于各自的时空中,不确定(uncertain)——有规则但不固定,非生产性的(unproductive)——从始至终情况一致,遵守规则(governed by rules)以及假想(make-believe)。[2]其中,最后一个特征在本文的语境中尤为重要。针对这种与游戏行为相关的假想,凯约瓦还指出,它“伴随着一种特殊意识,此意识关涉的是某种第二现实或自由的非现实,而不是现实生活本身”[2]。以上这些明确的特性与克拉拉·费尔南德斯-瓦拉(Clara Fernández-Vara)将电子游戏定义为演出(performance)相似,她提出了五个基本特征①这五个特征同时适用于游戏、比赛、运动、剧场以及仪式。正如费尔南德斯-瓦拉所说,这种定义仍有例外,比如线上扑克牌就包含货币收益,并因此含有生产性因素。参见Clara Fernández-Vara: "Play's the Thing: A Framework to Study Videogames as Performance",Proceedings of DiGRA 2009, Breaking New Ground: Innovation in Games, Play, Practice and Theory, vol. 5, Brunel University, 2009。:“特定的时间(time)顺序、特殊的目标(objects)价值取向、商品意义上的非生产性(non-productivity)、规则(rules)以及演出空间(performance spaces)”。在我看来,游戏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并不仅仅是就赫伊津哈和凯约瓦所说的“传统”游戏而言的,对于电子游戏来说也是一样:毕竟电子游戏也是对现实的方方面面的模拟,比如社会关系、谈判技巧或经济策略。以此观之,人们乐于玩游戏的原因就变得易于理解了:游戏与现实类似,但又不同于现实。然而,赫伊津哈、凯约瓦以及费尔南德斯-瓦拉给游戏附上的魔力圈(magic circle)观念近年来也颇受非议。正如米娅·康萨尔沃(Mia Consalvo)所指出的,有关游戏和玩法的外部知识和玩家的个体生命经验,总是会随着每一次新的游戏历程而被带入游戏之中。也就是说,尽管游戏被指定在特殊的场所(如拳台或控制台),但也并非完全独立于其他地点而存在。
想要投入游戏当中,必须沉浸于游戏世界所营造的幻觉,并接受游戏的规则,将之视为理所应当。游戏所创造的幻觉呈现了这样一个世界:看上去接近、又全然不同于我们认为的真实。②真实与游戏世界之间的相似取决于游戏对现实的偏离。游戏可以很大程度地偏离现实,而仍被认为是可信的;不过,这仅仅是在游戏遵循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的情况下,不论其与现实有多么不同。但这种幻觉并非一种消极隐晦的骗局,而是一个审美过程。非审美的幻觉大多被认为是负面的,其意义主要是揭露骗局,而虚构的或审美的幻觉则强调创造出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游戏世界的能力。[3]不过,游戏与主观感知中的现实永远不可能完全一致。它总是制造着幻觉。在文学领域里,沃尔夫(Werner Wolf)在这种幻觉的基础上分析了文本(游戏)和读者(玩家)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疏离”(Distanz)和“参与”(Partizipation)两个术语,用以描述读者(玩家)对幻觉的认知。③相似的概念有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的“怀疑的主动悬置”(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参见Coleridge, S.T.: Biographia Literaria, vol. 2. Claredon Press, 1907;沃尔顿(Walton)的“假想”(make-believe),参见Walton, K.L.:Mimesisas Make-Believe: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Representational Ar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彼得·拉马克(Peter Lamarque)的“思考理论”(thought theory),参见Lamarque, P.: The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 Blackwell, 2009;还有传播更为广泛的韦恩·C.布斯(Wayne C. Booth)的“虚构契约”(fictional pact),参见Booth, W.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这些理论是为了描述虚构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而发展出来的,而对于电子游戏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主要是由于玩家在故事创作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为了避免术语上的歧义,沃尔夫的“疏离”和“参与”的概念更有利于用来描述玩家与幻觉之间潜在的相互作用。
“疏离”指的是虚构性媒体的用户能够意识到幻觉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正如帕特里夏·沃(Patricia Waugh)在文学方面的主张,“我们当然知晓我们正在阅读的内容并非‘真实的’,只是我们抑制了这种认知,从而获得更多的愉悦”[4]。同样的,当我们察觉自己正通过屏幕或手柄进入游戏世界,或感觉某个游戏世界中有僵尸完全合乎逻辑,而这在另一游戏世界中就毫无道理,疏离就会由此产生。这种幻觉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也可以借由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的问题来理解,即“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认为事物是真实的?关于现实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对其真实性的感知,与那些缺乏真实性的事物给我们的感觉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人们才会问,这样的感觉是基于什么条件而产生的……”[5]。在将自身沉浸于虚构性媒介的过程中,疏离逐渐退居幕后,玩家参与进幻觉之中。戈夫曼将参与定义为“一种生物心理学过程,主体在此过程中会部分地意识不到其感觉和认知注意力的趋向”[5]。因此,疏离和参与都与幻觉相关,在幻觉中,二者首先遵循着一种先后顺序,因为疏离会被参与所取代。这个过程是交替的而非线性的,因为受众既可以通过无数次倒退,从疏离转变为参与,再回到疏离状态(例如暂停或重新加载游戏),也可以仅从疏离走向参与(例如一口气打到游戏通关)。如果没有这种进程,受众就参与不到幻觉中。
通常而言,电子游戏要求玩家承认游戏世界的虚构存在(as if)并愿意参与假想,只有这样,玩家才可能沉浸于游戏的幻觉之中。能够解释这一观点的一个例子是《生化奇兵》(BioShock,2007)的结局,揭示出主角杰克(Jack)其实受到了亚特拉斯(Atlas)的利用,在“能否劳驾您(Would you kindly)”这句话的操控下履行对方的指令。从这个意义上看,游戏允许玩家的化身同时被游戏中的其他存在物——如故事世界中的亚特拉斯,以及故事之外的玩家操控。尽管这种允许很难忽视,但《生化奇兵》还是创造出了完整的人物形象和前后连贯的游戏世界。即便能动性的概念已表露无遗,游戏建构起的幻觉依然得以存续。
本文的问题之一是,如果一个游戏出现在另一个游戏之中,那么玩家为接受该游戏的虚构幻觉而做的准备将受到怎样的影响?关注点在于,当某个游戏内部存在另一个与之类似甚至结构相同的系统,游戏的幻觉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差异就会被强调。然而,玩家似乎仍然愿意接受游戏世界,尽管它是虚构的。为进一步讨论这一观点,我将聚焦一种特定类型的电子游戏——叙事电子游戏(narrative video games)①虽然本文聚焦叙事型游戏,但非叙事型游戏中也可能存在幻觉。例如,在俄罗斯方块(Tetris,1984)中,玩家照样愿意接受他们所进入的世界是以将各种形状的方块叠在一起为目标的。然而,其中并无(复杂的)叙事可供讨论。,即通过语言或营造世界的各个方面创造出线性叙事或支线故事的游戏。之所以关注这类游戏,是因为它们具有产生强烈的虚构幻觉的能力,同时通过在原来的虚构世界中插入游戏,来质疑这种幻觉。此外,游戏世界中所呈现的叙事需要通过在故事世界中插入另一个游戏来加强效果,无论是与所嵌入游戏性质类似的游戏,还是与之不同的游戏。只要满足这两个标准,便可以进一步探究游戏中游戏可能具有的各种功能。而另一方面,有些游戏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比如《马里奥派对》(Mario Party,1998—2018),它相当于一个子游戏的合集。不过,在对典型游戏案例中交错的虚构层级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定义清楚什么是虚构层级,并明确其对我们关于幻觉的感知有何影响。
二、虚构层级的交错
任何包含多个虚构层级的人工制品(artefact)都不可避免地表明了其自身的虚构性。尽管最初看来,这或许表明虚构幻觉和接受者参与其中的意愿都存在被拒绝的风险,但实际上,这一点恰恰意味着,关于人工制品自身和虚构性的本质的批判性讨论可以由作品本身来引起。这一过程被称为自我反身性(self-reflexivity),在迄今为止相关研究动态最为全面的文学研究领域里,它被称为元小说(metafiction)。由于本文的关注点在于电子游戏中虚构层级的交错性,所以将这两个术语作同义使用。想要进一步确认自反性游戏的意涵,则需要围绕元小说展开更为细致讨论。帕特里夏·沃在其开创性作品《元小说》(Metafiction)中提到:
元小说是一个关于虚构性写作的术语,它自觉地、系统地引起人们对其作为人造物的地位的关注,从而引发对虚构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提问。这类写作在对其自身的结构方法进行批判时,不仅考察了叙事小说的基本结构,而且还探索了文学虚构文本之外的世界的虚构性可能。[4]
在本文语境下,这一定义中的几个要点是十分切题的,只是需要对其中一些部分进行修改以适应电子游戏的情况。第一,虚构性写作的概念可以扩展为虚构性人造物,因为元小说(作为一个术语和一个概念)同样可以出现在文学之外的其他媒介中;唯一需要被赋予的特性是,它们的主题必须是虚构的(正如电子游戏的情况)。第二,这种自反性过程绝不能是偶然发生的,而必须是程序员或游戏叙事的作者有意为之。第三,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并非必须像沃所主张的那样明确地主题化;相反,当人们批判性地参与进创造世界的幻觉,并对其如何被感知产生好奇,有关现实的创造和感知问题就已经暗含其中了。这一点与第四点有关,即这同时表明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反而可能是在感知过程中被虚构出来的。
以上这些初步思考表明,任何与电子游戏自身虚构性的互动,都会引发人们对其(与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的)幻觉的关注。达成这一点的方式之一就是采取增加游戏虚构层级的策略。换言之,一旦游戏中出现另一个游戏,母游戏的游戏性便会被凸显出来。在下一节中,我将从理论角度定义这些游戏被嵌入到主游戏中的两种模式,即中国套盒结构①布莱恩·麦克海尔(Brian McHale)将“岔路”的叙事结构描述为“嵌套或嵌入,就像在一组中国套盒或俄罗斯套娃(Russian babushka dolls)中”,参见Brian McHale: Postmodernist Fiction, Routledge, 1987。沃尔夫也谈到了“中国套盒结构”,参见Werner Wolf:Ästhetische Illusion und Illusionsdurchbrechung in der Erzählkunst: Theorie und Geschichte mit Schwerpunkt auf englischem illusionsstörenden Erzählen, Niemeyer, 1993。之所以采用这个比喻,是因为它生动描绘了各个单独的虚构层级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相互依存的状态。和无限镜像结构。同样的,我将以文学研究为基础引出本文的核心,即考察电子游戏如何增加其虚构层级,以及这对主游戏的感知有何影响。
“游戏中的游戏”构成了一重或多重独立于主游戏的游戏层级,从而建立起一种对所嵌入游戏的比喻。②这些增加的层级可能但不一定是次级叙事。只有当“游戏中的游戏”拥有自身的叙事元素,它才是主游戏叙事的次级叙事,正如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定义的:“对一个或多个真实或虚构的事件的描述(如结果与过程、目标与行动、结构与建构),事件由一个或多个叙述者向一个或多个倾听者(不同程度公开的)传达”,参见Gerald Prince: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又比如,由于《疯狂时代》中包含的《疯狂大楼》子游戏满足普林斯的定义,便形成了这种次级叙事结构,与之相反,《生化奇兵》中的连接管道游戏则没有。这类比喻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元小说技巧,作为游戏的核心来驱动游戏的进行。而游戏所呈现的世界创造过程具备这样的效果:可以在不表明它是一个游戏的情况下评论游戏的人造性,与此同时维持游戏世界的幻觉。在文学领域中,多里特·科恩(Dorrit Cohn)指出,这种多层次的叙事构成了一种“内部的……转喻(metalepsis),它出现在同一故事的两个层级之间”[6]。对于电子游戏而言,这意味着玩家的化身也可以在游戏中玩游戏(有时甚至可以控制另一个化身),相当于从一个虚构层面移动到另一个虚构层面,而玩家还始终控制着自己的化身。
类似于文学作品,“游戏中的游戏”的两种形式也可以这样来辨别:中国套盒结构,即嵌入游戏与所嵌入游戏的结构整体仅有微弱的联系;无限镜像结构,即游戏中的第二层级与第一层级极为相似,二者都在元小说的意义上表明了嵌入式游戏的游戏性及虚构性。游戏中的游戏则被用以“凸显出递归性结构的本体之维”[7]。嵌入游戏清晰地映射着自身,同时也暗中表明了其所嵌入游戏的虚构性和游戏性,也映射着后者与现实在虚构性和游戏性上的关系。
关于将一个游戏包含在另一游戏中的作用,可以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强调的镜子在艺术中的重要性联系起来。①镜子的隐喻后来也被卢锡安·达伦巴赫(Lucien Dällenbach)使用:“无限镜像是一切事物内部的镜子,通过简单、重复或似是而非的复制来反映出整个叙事”,参见Lucien Dällenbach: The Mirror in the Tex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米柯·鲍尔(Mieke Bal)提议舍弃无限镜像这一术语,因为它不描述“图像的整体,而只是文本的一部分,或某个方面。……我建议使用术语‘镜像文本(mirrortext)’来代替‘无限镜像’”。参见Mieke Bal: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福柯认为,镜子“起一种复制的作用:镜子只是在一个非真实的、被修正的、收缩的和凹陷的空间中,不断重复着画面中最初给定的东西”[8]。镜子扭曲了现实,因为观看者能够意识到镜子中呈现的只是一种映象,它并非真实世界的直接显现,而只是它的一种表象。游戏也是如此:“游戏中的游戏”是游戏进程本身的反映,因此也是对所嵌入游戏的反映。麦克海尔对无限镜像结构的看法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套盒结构:“无限镜像是另一种形式的短路,是对叙事架构的逻辑的另一种破坏,就像一个角色跨过本体界限进入另一个不同的叙事层次一样令人不安。”[7]
下一节将重点关注游戏性是如何通过“游戏中的游戏”得以凸显的。对此,我将结合具有上述特征的电子游戏案例来说明。
三、游戏中的游戏
基于以上对虚构幻觉和对“游戏中的游戏”的理论探讨,接下来我将借助一些游戏案例来讨论嵌入游戏的各种模式以及它们的功能和效果。我将按照一个频谱的形式来作说明,沿着频谱的一边,我们能够找到对母游戏的玩法几乎毫无影响的嵌入游戏,而从频谱另一边,我们可以定位出作为母游戏内在固有的(甚至可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的嵌入游戏。在频谱的两端,游戏分别呈现为常见的中国套盒结构和不常见的无限镜像结构。下面的分析将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所关注的“游戏中的游戏”对母游戏没有任何帮助,只是嵌入了游戏;第二部分则聚焦对母游戏有所助益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子游戏,其具体形式诸如帮助获取赏金或升级,作为达成百分百成就的必要条件,甚至是成为母游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一)不影响母游戏玩法的“游戏中的游戏”
第一类需要分析的,是那些不必为了母游戏的推进而玩的子游戏。不过,由于构成了所嵌入游戏的次虚构层级,这类游戏还是间接地强调了母游戏的游戏性。原因在于这类子游戏通常遵循非常简单的结构,或者类似于我们所知道的最寻常不过的游戏(例如捉迷藏);即便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去接近它们,感受还是会与所嵌入的游戏有所不同。为了进一步发展、研究和举例说明这一论点,本文将通过探讨由母游戏和子游戏共同构成的双重(或多重)虚构层级之间的关系,对各式各样出现在母游戏中的子游戏进行分析。
首先要考察的案例都出自经典系列电子游戏:《侠盗猎车手》(Grand Theft Auto,GTA)。此系列中,《侠盗猎车手:罪恶都市》(Grand Theft Auto: Ⅴice City,2002)、《侠盗猎车手:圣安地列斯》(Grand Theft Auto: San Andreas,2004)、《侠盗猎车手4》(Grand Theft Auto IⅤ,2008)、《侠盗猎车手5》(Grand Theft Auto Ⅴ,2013)和《侠盗猎车手在线》(Grand Theft Auto Online,2013)等游戏内部都包含有街机风格的电子游戏,它们在游戏中随处可见,在酒吧、餐馆、服装店、便利店等各个地方都可以找到。由于这些子游戏都基于真实的电子游戏,因此它们会立即唤起玩家的记忆,强调与游戏性的关联。例如《侠盗猎车手:圣安地列斯》中的《大黄蜂》(Let's Get Ready to Bumble)游戏,玩家在其中扮演必须收集鲜花的大黄蜂。这款2D 平台游戏的前身是Tehkan 公司的经典街机游戏《炸弹杰克》(Bomb Jack,1984),其目标是收集红色炸弹。这种与玩家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游戏之间的互文关系强调了“游戏中的游戏”的游戏性;但与此同时,母游戏创造的幻觉并未消失,相反,它得以维持。因为玩家面临着子游戏的虚构性,这与母游戏形成了鲜明对比,于是后者被视为一个现实的框架,嵌入游戏就存在于此框架中。
另一个例子是《侠盗猎车手4》中的《堆方块》(QUB3D)①该子游戏也出现在《侠盗猎车手 5》中,但同样不可玩。子游戏,它同样出现在游戏的两个资料片:《侠盗猎车手4:失落与诅咒》(GTA IⅤ: The Lost and Damned,2009)和《侠盗猎车手4:夜生活之曲》(GTA IⅤ: The Ballad of Gay Tony,2009)中。游戏目标是在屏幕被填满之前匹配到4 个或更多相同颜色的方块。该游戏的灵感来自《噗哟噗哟》(Puyo Puyo,1991),部分还受到《俄罗斯方块》(Tetris,1984)的启发。这两款游戏都具有标志性意义,并且与早期新兴游戏文化相关联。这两个子游戏以及《侠盗猎车手》系列游戏中的其他子游戏都与经典街机游戏有一些共同点,如直截了当的目标、简单的2D 图形、复古风格和高分榜单②游戏用户可以看见高分榜单,且榜单会被保存在每台同类型的街机上。这在现实中是不会发生的,除非街机联网。。此外,这些游戏对母游戏的进展毫无帮助,仅仅是一种消遣。尽管如此,所嵌入游戏的幻觉仍然完好无损(即它并未明显地表现为一个游戏),且它位于和嵌入游戏不同的层面上。
《辐射4》(Fallout 4,2015)中包含一个名为《红色威胁》(Red Menace)的游戏,就我们对虚构层级的感知而言,它与《侠盗猎车手》中包含的游戏有着类似的效果,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它的互文性。该游戏高度影射了《大金刚》(Donkey Kong,1981—2018),只不过将大猩猩替换成了外星生物。玩家通过终端或Pip-Boy 手环来玩这款游戏,在111 号避难所(Vault 111)中收集弹药筒。与《侠盗猎车手》中的街机游戏类似,该游戏与母游戏是物理分离的,这意味着它必须通过特定设备才能访问。这样一来,它的游戏性立即暴露出来,也因此需求着一种游戏的态度。
卢卡斯艺术公司(Lucas Arts)的《疯狂时代》(Day oftheTentacle,1993)展示了此类“游戏中的游戏”的一个特例,游戏中的一台计算机内包含着卢卡斯影业游戏公司(Lucasfilm Games)的《疯狂大楼》(Maniac Mansion,1987),该游戏完全可以免费游玩。将这款游戏包含在前一款游戏内,既可以理解为对原作的致敬,也可以看作是对游戏自身地位的一种自反性评价。这个游戏是元小说的典型案例,同时也可以视为对该行业自身的评论。它含有来自真实世界的元素,并将自己身在其中的前一款游戏重新定义为游戏。
很多子游戏是解谜游戏。在《蝙蝠侠:阿卡姆之城》(Batman: Arkham City,2011)中,解谜游戏扮演着重要角色。玩家在游戏中使用无线电扫描仪时,可以找到3 个未注册的电台,它们会显示一排排数字。通过密码,玩家可以破译信息,例如稻草人(Scarecrow)所说的“恐惧会将哥谭撕成碎片(Fear will tear Gotham to shreds)”。这一信息预示了他在《蝙蝠侠:阿卡姆骑士》(Batman: Arkham Knight,2015)中将扮演的角色,但它对所嵌入的母游戏并无任何帮助。
除了这种解谜游戏,也有很多赌博类的子游戏。《荒野大镖客:救赎》(Red Dead Redemption,2010)里就包含了许多不同的赌博游戏,例如扑克和投马蹄铁(horseshoe throwing)。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大话骰子(Liar's Dice)”游戏。玩家得到5 个骰子,他(她)需要在杯中摇晃骰子,把它们扣在桌子上,偷偷看一眼,然后说出是多少点数。为了击败其他人,就需要虚张声势和撒谎,一旦被看穿就会输掉游戏。这个游戏玩家想玩多久就玩多久,但它对于母游戏的进程却不是必需的。虽然它们不直接参与主游戏,但此类益智和赌`博游戏具有训练玩家分析能力的效果,而这反过来又可以在母游戏中发挥作用。
一些情况下,游戏中出现的游戏是不可玩的,因此可以说它们不是我们所定义的最严格意义上的子游戏。然而,由于这种游戏同样令玩家感觉到了与它们所现身的游戏世界的不同,从而确切地凸显出了游戏性,因此在本文的语境中也值得被进一步考量。《神秘海域4:盗贼末路》(Uncharted 4: A Thief's End,2016)中有这样一段叙事情节,即埃琳娜·费舍(Elena Fisher)向内森·德雷克(Nathan Drake)介绍原版游戏《古惑狼》(Crash Bandicoot,1996)。虽然玩家无法玩这个游戏,但鉴于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游戏,所以仍会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对待它。从它被包含在母游戏中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从游戏本身对游戏文化进行批判性分析,特别是当德雷克宣称“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迷上电子游戏(I don't know why people get into video games)”时。这种对消遣游戏态度的讽刺的、自反性的评论仅停留在《神秘海域》游戏世界的虚构幻觉中,因此并不会迫使玩家从参与转为疏离。
对母游戏的玩法没有影响的子游戏是一种补充,它允许人们在游戏中对游戏和游戏的地位进行批判。因此,它们可以被视为一种通过实践进行理论化的模式,因为它们一方面可被用作游戏之游戏性的试验场,同时也允许玩家站在游戏之外观察游戏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游戏中的游戏”是强调游戏的幻觉而又不抛弃这种幻觉的元素。
(二)影响母游戏玩法的“游戏中的游戏”
与上述子游戏不同,接下来要分析的另一类子游戏是母游戏本身固有的组成部分,而母游戏仍然有一个连贯的故事,因此不同于《马里奥派对》[9]这类“派对游戏”。由于与包含它们的游戏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类子游戏不同程度地强调着游戏中虚构层级的存在,这一点与不影响母游戏玩法的子游戏完全不同。以下的案例都支持这样一个论点:通过子游戏的游戏性强调母游戏的游戏性,并不必然导致游戏世界的幻灭。下面将详细讨论“游戏中的游戏”在各种表现形式下如何做到这一点。
《塞尔达传说》(The Legend of Zelda,1986—2023)系列游戏包含许多不同形态和形式的子游戏。这些子游戏都是《塞尔达》的固有组成部分。由于《塞尔达》系列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其解谜结构,所以这些子游戏也有着相似的结构。也就是说,《塞尔达》由一系列强制性的子游戏组成(主要位于地牢和神庙),这些子游戏由一个总体叙事框架串联起来,即主角林克(Link)必须帮助塞尔达公主(Princess Zelda)对抗盖侬(多夫)[Canon(Dorf)],拯救海拉鲁大陆(Hyrule)。此外,这些子游戏会奖励玩家心之碎片或技能升级。这些子游戏大致上可以分为三大类:(1)对现实生活中活动的模拟,如钓鱼或射击馆①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林克而言,这些活动是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因此它们被称为“模拟”而不是“游戏”。;(2)仿照“经典”游戏的模拟游戏,如捉迷藏;(3)赌博和赌运游戏,例如彩票或宝箱游戏。
此外,还有一小类更复杂的游戏,通常共享着以上三大类的特征。例如《塞尔达传说:黄昏公主》(Twilight Princess,2006)中的“明星挑战赛(STAR Game)”。游戏目标是收集悬浮在空中的光球,以获得箭袋升级奖励。游戏分为三个级别,必须连续进行,并且这只能在林克拥有钩爪和双钩爪②钩爪(Clawshot)是一种锁定装置,林克可以用它来让自己悬挂于半空中的物体,例如树木或墙壁。双钩爪允许他在挂在第一条钩锁上时发射第二条钩锁。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否则就无法收集到移动范围之外的光球。在比赛的第三阶段,林克必须打破个人最好成绩。该游戏因此具有许多前提条件和特点:林克需要拥有两个道具,而获得两个道具则需要掌握一些技能;该游戏是前面三大类游戏的组合,因为它融合了运气和技巧,同时也是对经典游戏特色和现实生活的模拟。明星挑战赛并不是获得《塞尔达传说:黄昏公主》完全成就的必需条件,但其巨型箭袋的奖励可以让林克持有最多100 支箭,从而易于击败更难对付的敌人。
在另一个广受欢迎的例子中,一个特殊的子游戏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母游戏的成功,这就是《最终幻想8》(Final Fantasy VIII,1999)。《三三牌》(Triple Triad)作为其子游戏中的一款卡牌游戏,构成了母游戏的一个支线任务。游戏在一个九宫格的棋盘上进行,目标是通过将一张等级更高的牌放在对面玩家的牌旁边来夺取对方的牌。这些卡牌可以通过羽蛇(Quezacotl)①在《最终幻想8》中,羽蛇(Quezacotl)是一种带翼的召唤兽。的卡牌变化(card mod)能力炼成道具,从而更容易获得稀有道具。因此,该游戏对母游戏的玩法产生了影响。这个子游戏非常受欢迎,以至于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游戏,可以在《最终幻想8》(以及包含该游戏的其他系列游戏)之外进行体验。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子游戏案例,因为除了在母游戏中构成一个补充性虚构平面外,它还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虚构世界,从而成为自己的主游戏,同时它仍然与原本的《最终幻想》游戏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子游戏可以作为母游戏所需技能的训练场。解谜平台游戏《凯瑟琳》(Catherine,2011),以主人公文森特·布鲁克斯(Vincent Brooks)为中心展开,游戏分为两种模式——白天的社交模拟和晚上的噩梦。白天的情节发生在“迷路小羊”酒吧,文森特可以在那里玩《长发公主》(Rapunzel)子游戏,它模拟着夜间游戏的玩法。通过将游戏某一方面的结构纳入该游戏的另一部分中,便创造了一个镜像,从一个元视角(meta-perspective)上强调了游戏行为。在《孤岛惊魂3》(Far Cry 3,2012)中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与前文提到的《荒野大镖客:救赎》中的赌博游戏类似,《孤岛惊魂3》中也加入了扑克牌游戏,并且这一次对游戏本身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这个子游戏包含教程,玩家可以在气氛紧张的酒吧这一逼真的环境中学习如何玩扑克。新学到的技能对于在游戏中取得成功并非首要的,但扑克游戏同样包含在游戏的结局中,对于练习过的玩家而言,上手会更加容易。因此,嵌入游戏所创造的次游戏层级对《孤岛惊魂3》的主游戏层级产生了影响,但这并不会致使两个层级中的幻觉消失。相反,子游戏贴合地嵌入,不会立刻产生与主游戏的分离感,而是被视为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最后一类“游戏中的游戏”是遵循解谜结构的游戏。在《生化奇兵》中,一些自动售货机允许玩家玩一个子游戏,玩家必须连接管道以形成连续的蒸汽出口。所获奖励有武器和弹药折扣。蒸汽流动得越快,及时连接管道的难度就越大,但折扣也越高。在此案例中,尽管子游戏对于母游戏的进展并不重要,但其对后者仍有积极的影响,例如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更强的武器。此外,在《乐高星球大战》(LEGO Star Wars,2005)中也有一个解谜结构的子游戏,但在与母游戏的关系方面,其地位有所不同。卡米诺(Kamino)的走廊中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必须解决谜题的房间,如果解谜成功,地板会变成迪斯科舞厅,播放迪斯科版本的《星球大战》主题曲。虽然这个彩蛋②彩蛋(easter eggs),指的是隐藏在游戏中的“宝藏”,本身不一定是游戏。例如,它们可以是额外的金钱,如《塞尔达传说:众神的三角神力》(The Legend of Zelda: A Link to the Past, 1991), 其中一个隐藏的房间“The Chris Houlihan Room”中包含额外的游戏货币卢比(Rupees)。虽然彩蛋不一定是游戏,但它们的发现遵循类似游戏的结构,因为它们是隐藏的,实际上并不是主游戏的一部分。发现彩蛋类似于寻宝,而且很多时候宝藏正在等待好奇的玩家来发现。不会直接影响母游戏,但必须完成它才能获得百分之百的游戏成就。这两个解谜结构的子游戏案例都遵循着与主游戏不同的构造。不仅如此,它们非常明显地以游戏的身份出现,使人们明确注意到其游戏性特征。因此,其效果恰恰是加强了游戏所呈现的虚构世界的幻觉,引领玩家参与到假想之中。
结 论
正如以上对两类子游戏的分析所表明的,“游戏中的游戏”比母游戏更为强烈地凸显着游戏性。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母游戏实际上试图通过创造出一种能够掩饰其非真实性的幻觉来遮蔽它们是游戏的事实。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子游戏并不会使母游戏的幻觉暴露以至崩塌。相反,游戏的特征可以近距离地展示,而不必承担玩家可能放弃参与幻觉的风险。以上两种“游戏中的游戏”都是如此,无论其是否对母游戏的进行与成就有所助益。
那么,关于电子游戏的虚构层级,经过对子游戏及其与母游戏的关系的考察,我们能够得出怎样的结论呢?首先,电子游戏通常会制造出令玩家自愿沉浸其中的幻觉(类似于文学或电影),至少在游戏进行中是这样。其次,通过在游戏中呈现另一游戏,游戏性的概念得以从一种内在视角来评估,从而促成对游戏特征的批判性讨论。再次,尽管在游戏中置入了第二重虚构层级,但母游戏所创造的幻觉仍然完好无损。最后,可以说子游戏为游戏理论的研究确立了一个实用性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