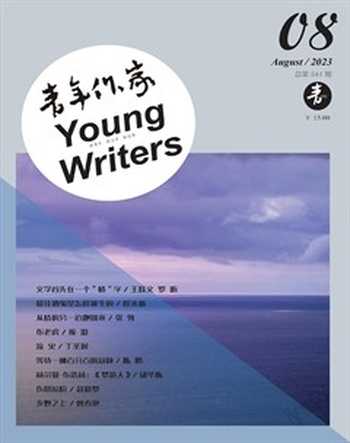等待一种百分百的寂静
陈鹏
你可以以为一切又将恢复正常
如果你只能相当安静地等待
——菲利普·拉金
我们活着,这件事和那件事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什么联系,相互影响到何种地步,是否会因为某个元素、某个意外、某次小断裂、某个逆转引发灾难性后果?你说不上来。反正面对鹿鹿病危的事情,你不相信它发生了。这件事情挽回不了,挽回不了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为什么又来一遍?你被按进烂泥里。活着就是个错误对吧。活着,老掉,死去,充满意外,也没有意外。没法面对鹿鹿,怎么解释呢?告诉她,再过三个月最多五个月你会被上帝带走?能解释吗?关于活着和死亡,你又知道多少?上帝为什么把孩子们带走?一前一后两个。你想不明白。和小安不一样,鹿鹿两岁七个月确诊恶性脊髓瘤,这个病她这个年龄非常罕见。她才四岁,就没法下床了,已经卧床半年多。你请了护工帮她翻身、擦洗、喂饭,最大程度呵护她,让她舒服一些。大块头的中年女护工人很好,临沧人,不是昆明人。眉眼低垂脸色黝黑,说话慢腾腾的就像房子着火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让鹿鹿平静下来,像进入超现实的现实——直面痛苦的现实似乎脚步非常缓慢,几乎感觉不到。足足四个疗程,你没法想象她是怎么扛过来的,那么小那么瘦的娃娃啊,肋骨戳在病服下面,恐怖地支棱着。你每天最多陪她三小时,从单位坐地铁晃荡过去已经够晚了,回到家你差不多散架了。但在医院,你明明什么也没做,只是坐在床边像傻子般看着她,你们经常陷入长长的白色寂静就像在仔细辨别一场雪的落下和地面青草彼此挨碰的刺啦声。你是她爹啊。谁让你是她亲爹。她遭的罪远胜你们全部人马,她才四岁,没上过小学一年级,还不知道声母、韵母和汉语拼音,没见识过学校长什么样,不知道红领巾代表什么意思,不知道品德课和自然课到底学哪些东西。但一切很快就要戛然而止了。到底好或不好,现在还不太好说。你的46年太漫长了,总的说来,最大失误是不该成为父亲,而且还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你得到了又失去了,到头来两手空空。这么说,所谓父亲,就是得到和失去的那个老家伙?
晚上9点40,你离开了。她黑漆漆的眼神像透明灿烂的匕首直刺你、恳求你、安慰你,你真受不了这个。实在受不了。她想回家,能看出来她多想回家。不,你回不了家了,鹿鹿,你没法回家,可能再也回不了家了。阿姨多好,对你多温柔呐。像苏粒?是,有点像。啊,为什么是有点?你答不上来。她用来自女儿的天性和本能的眼神告诉你:她是向着你的,必须是你,也永远是你。你太愧对她了。让苏粒带她走会不会好一点?或许你会少一点内疚和负担,她呢,苏粒,让她少遭点罪、少受点苦,或许比现在更好?不,你保证不了,苏粒也保证不了,你们连自己也保证不了。你们是糟烂的爹妈,你们糟烂透了。比如你总算顺顺当当失业了,你在裁员名单上,他们宣布的时候你心脏怦怦乱跳,差点把胸腔砸碎。你问最后期限什么时候。答曰,一个月。他们知道你不容易,家里房都塌了,儿子跑了,女儿重病。他们尽量温情地说,实在没有办法,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裁员概率是85%,非常可惜你不在那15%里。你没那么幸运,很多人都没那么幸运。你46了,上不挨天下不着地。市场分析师,听起来是很好的职业,其实呢,你甚至不明白什么人算核心,什么人又不算?你可以不要两手两脚单留住脑袋和心脏吗?你喝了多少杯茶水间免费咖啡?你和后勤部某女聊了很多人工智能,将滚烫的咖啡一点一点喝凉。她凝神看你,专注的微笑让你想起舒服的昆明初秋不冷也不热。多久没跟异性挨这么近了?多久没让一个散发暖香的异性听你说话了?她问你看没看过《三体》,你的回答是否定的,但你看过不少好莱坞科幻电影,讲的是人工智能怎么失去控制、丧失人性又突然拥有了人性,最后悲剧收场。这类悲剧你还是不太理解,因为你知道,也只有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悲剧。她围着故事转圈,毕竟她能讲的唯有故事,没办法为你总结哲学、生命学、外太空文明和地球人的关系。也许,人和AI的悲剧仅仅因为各自抱着很大希望又粉碎希望。没错。希望和粉碎之间的落差才是悲剧,就像鹿鹿被宣判死刑。凭什么他来宣判,凭什么?就因为他穿白大褂?难道他就很清楚生命怎么运行的,以及还要运行多久吗?生命不就像只小猫一样安静趴着么?是你和苏粒给了她这只小猫。她是后勤副主管,姓罗,大家都叫她罗姐,你只好也这么叫,虽然她年龄比你小七八岁。你们从人工智能忽然聊到UFO。是的,UFO。你是资深爱好者,算得上半个行家。你一边喝着不加糖的美式咖啡,一边眉飞色舞地讲述昆明两大著名UFO事件,就好像两只飞碟就在你面前停着,而你是唯一目击者。咖啡洒到裤裆上了,你赶紧说抱歉。罗姐吃惊地说,真想不到你热爱飞碟。你说每个人都有小秘密,比如——你突然说不下去了,想到鹿鹿的眼神,心里一阵刺痛。比如,你曾经和儿子跑去金殿山头,爬到一棵大枇杷树梢上眺望昆明。她笑了,说你好浪漫哟。你沉重地笑了,想到爬到树梢上的小安俯瞰昆明的画面,你什么也说不出来。罗姐低下目光告辞,你一个人呆在茶水间的时光才是最美妙的,再也没有比它更美妙的寂静了:微波炉、茶杯、咖啡、水壶靠墙摆放了一小溜,你坐在吧台椅子上微微转动身体,它们安安静静、处之泰然、沉默平和,像逆来顺受从不抗拒命运的一小撮泛着光亮的小宠物或者更低级别的东西。此刻,唯有此刻是真实的,寂静是真实的。多完美的寂静。你吞下最后一口咖啡,尝不出苦味了。你希望不再有人进来,你将和这些缄默之物一直呆下去,直到黄昏来临或至深夜。这种有点像担心,又盼望这种担心赶紧变现的自虐,难道不也是爱之一种?难道比不上不舍?你弄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就算明天拍屁股就走人,也没有什么遗憾,比起鹿鹿这算什么遗憾?你占据此刻的寂静,绝对的占据,钻石、罪愆、羞耻一样的寂静。它是你的,哪怕短短半小时,对吧。
鹿鹿做梦了。梦见什么了?梦见,一颗比大楼还大的亮闪闪的星星,像一颗大大的钻石。她笑着,嘴角弯成月牙,脸蛋粉红,皮肤是透明的。你大叫出来:“飞碟!你梦见的是飞碟啊!鹿鹿,那是UFO。”“真的吗?飞碟?外星人的飞碟?”“是飞碟,外星人的飞碟。”下午苏粒来了,使劲把她抱在胸前为她朗读绘本故事,描述托莱多圣母大教堂有多美。鹿鹿不感兴趣,她对她无法想象的东西没有兴趣。鹿鹿问苏粒西班牙有没有飞碟。她大吃一惊说:“应该有吧,反正我没见过,很可能一半以上西班牙人都没见过。”鹿鹿说:“我见过,我见过,又大又亮,钻石一样的飞碟。”你提议全家一起吃顿好的。苏粒来到走廊上,说:“怎么一起吃饭?她能下床吗?还是上场拿个奥運冠军?再跟你爬一趟西山吃蒙古包烧烤?”“我的意思是,苏粒,我的意思只是,我们可以在病房里面一起吃一个汉堡或者三明治也不行吗?我知道弄几个炒菜什么的味道太大,也不方便。”“哦,不好意思,我对三明治汉堡没兴趣,我在托莱多从不吃这些。拜托你别给女儿吃垃圾食品了,她都这样了你还给她吃垃圾食品。吃什么不吃什么麻烦你问问她,尊重一下她的意见行吗?总之我对饭局没兴趣,对医院里的饭局更没兴趣。”在无可挽回的气氛中,你感到死神就在头顶蹲伏,像只秃鹫塞满每一寸空间。你毫无办法。你要忍受恐惧,还要忍受仇恨,还要装作你们之间没有仇恨。好在恐惧比仇恨大多了。现在你和苏粒除了这个一寸一寸一厘米一厘米消散的小生命之外什么也没剩下。小安消失的速度快得多。三年前你把他交给你妈,你东奔西跑,直到你妈来电说你儿子眼神不对了,说天上面有个大大的火球滚过来,人要被烧死,我们干脆去死吧。你没放在心上,还嘻嘻笑了。你走的时候小安还好好的,怎么可能想死。孩子嘛,不是天使般的预言家就是满嘴胡话的蠢货。几天后你在上海又接到妈的电话,说小安在楼上放了一把火,幸好邻居防盗门结实得很,小安则稳稳当当坐家里剥橘子。苏粒明确说她不可能回来,马德里托莱多古城修复至少拖到明年年底。“总之,你尽力吧,一切靠你,我回来不现实,也没必要。”苏粒在电话里说。最后,小安没了。没了的意思是,消失了。不是死,是消失。从奶奶家消失不见了,没留个字条,什么痕迹也没留下。报警也没用,14岁的少年被拐的可能性不太大。你宁愿相信他骑一匹白鹿消失了,安安稳稳长生不老地住在另一个维度里面,他看得见你,而你看不见他。五个月后苏粒回来了,就是那次,就是她回来当晚,你让她怀上了鹿鹿。怀上纯属意外,不是因为痛苦和思念,而是仇恨和怨毒。你知道苏粒外面有人了,一个28岁的小子,是个滇剧演员。苏粒回来的时候,你差点认不出她了,黑了,瘦了,更结实、漂亮,全身洋溢着地中海气息,也不牵挂小安了,像全新的3.0版苏粒。她的小男友追着她扁扁的屁股直奔智利去了。
“哎,鹿鹿,我们来一次病房野餐咋样,给你买麦当劳?”鹿鹿高兴得蹦起来。得到医生护士的批准,你要了全家桶。苏粒不回来了。走了就是走了,像小安一样走了。“真是UFO吗爸爸?”“是的,我认为是的。”“UFO是透明的?”“是的,UFO有很多种,有透明的,有半透明的,也有不透明的。”“啊,透明的飞碟,是吗爸爸?”“是的,透明的飞碟。”“可它不像飞碟啊,像一块玻璃,一座山,亮闪闪的小山。”。“它就是UFO,很独特的UFO,外星人的东西都很独特,相信我,鹿鹿。”“爸爸你为什么那么确定?”“是的,我就是那么确定。”“为什么?”“因为,因为我也梦见过它。很大一团,闪着白光,呼啦飞下来,嘭——就是飞碟,外星人的飞碟。我们地球上不可能出现这么强大的光。”
罗姐说了一个陌生地名,让你陪她去一趟。为什么是我?因为——嗨,到那就知道了。你点头同意,由你开车。罗姐何必邀请一个下课的老家伙,一个倒霉透顶的前同事?你没想明白。但你暗自兴奋,因为就要离开了,要去挑战什么了,好莱坞英雄电影不都这么演的?鹿鹿需要你,她非你不可。至少你是父亲,你是爹。还怕什么呢?他妈的还有什么可怕?裁员名单早就不胫而走,很多人收拾东西,箱子撞得办公桌和地面砰砰响,人们小心翼翼绕开办公区域内杂七杂八的东西。最近后勤部似乎很忙,其实人都走一半了,哪来那么多事情要忙。她睡了片刻,也许只有十来分钟。醒来后她瞪着眼睛,好像来到了一个陌生星球。“到哪了?”“赛博坦。”你说。说完你就笑了,她知道你故意的,她嗔怒着瞪你一眼,拽一把长裙就好像你翻动过而她并不介意似的。你告诉她一个大概方位。她给你的导航定位在滇池某个小村庄外围。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像是对刚才睡着了感到抱歉。你又聊了聊UFO,告诉她你这辈子还没见过货真价实的UFO,要是遇见,这辈子就值了。她说没准,很多事情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生。没准今天我们就能遇见一个直筒飞碟。你有点懵,问:“什么直筒飞碟?”“亏你还热爱飞碟,居然没听说过直筒飞碟。”你惊呆了。从你们有限的几次茶水间交流来看,她不热衷也不了解UFO,此刻却连比带画地解释,说西藏和青海接连处,出现一种被称作38号的直筒飞碟,顾名思义,就是长得像个直筒,飞行轨迹直上直下眨眼就飞走了,快得像一道闪电,当地很多居民都见过。“这么说早就出名啦?”“对,38号飞碟,直筒飞碟。”“为什么是38号?”“这个嘛,就搞不清楚咯。”“你从没听说?”“没有。”“太神奇了,你这个UFO爱好者居然没听说过。”她笑着说,“我们眼皮子底下被忽略的东西还少吗?比如,老杜你在名单上。”你使劲点头,说:“对对对,你说得很对。”小小的困惑让你很难确定心情是沉重还是轻松。兼而有之吧,总之你走向未来,可未来张着血盆大口,能把你活活吓死。湿地公园到了,你们在一棵老槐树下停好车,走上栈道,来到尽头,湿地边缘一堆嶙峋的大石头黑乎乎的,诡异而凛然,你觉得它们是外星人故意安插的密探每天深夜向赛博坦发回信号。空气里有浓烈的水腥臭味,伴随某些水生小动物被肢解泡烂的恶臭。视线不算太好,像隔着一层脏兮兮的玻璃。后来视野渐渐开阔,至少看起来如此,滇池一角总体上有种罕见的饱满,就像飞船被肢解后扔在这里。
我们活着就死了,死人永远不会复活。你脑子里突然冒出这句废话。罗姐买了一大把烤串、两碗凉拌米线,算是晚餐,你们将就着栈桥边破烂的桌子椅子坐下来。风很大,风大的好处是不必忍受滇池边扑鼻的水腥臭气。远在栈桥另一头的小贩有种超常规的坚韧,像是要和此地同呼吸共命运到天荒地老。你偷偷问一个戴帽子的老家伙,有38号吗?他惊骇地望着你,像打量一个恶棍,说他不做任何毒品生意。你回去,坐在破烂木椅上的感觉就像一种训诫,让你怀念茶水间的圆形吧凳角落和几盆绿萝。你至今不太相信,也很难接受你被公司撤出了的事实,就像你只是度一个长假过几天还要回去,又好像是你呼吸不太顺畅,溜出办公室放松一下。总之,你的错觉是,你还得回去,没完没了地干这干那。你说:“人总不能一辈子憋在一个地方等死对吧。”罗姐笑了,说:“我没打算可怜你啊,看你说哪去了。”你不好意思地挠挠下巴想找补点什么挽回气氛。没提鹿鹿,更没提小安。他们跟她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你的一部分,而她只是你的前同事。女人嘛,最擅长夸大其词,就像苏粒擅长把小安的消失归咎于他或他的母亲,倒也有助于她继续修补她的托莱多破砖了。鹿鹿还有90天。3个30天。9个10天。你什么也给不了她。你低头看水面,但见星星点点的水生植物正在冒出雪白的六边形小花儿。也许是海菜花吧,又像小型睡莲,一点点、一片片,摇摇晃晃,有微小的浪花翻卷上来。它们翩然起舞。“他们呐,上面这些人,没想过公司怎么办,未来怎么办。”罗姐说,“一匹骆驼倒下还需要一段时间,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他们会后悔的,会因为失去老杜你这样有经验有能力的……”她欲言又止,似乎在暗示你太老了,没有多大用了,需要回家休息,而不是每天窝在茶水间里喝咖啡。你不想聊下去,因为没有意义,现在的意义,只是现在。你们吃完米线跳到那堆丑陋的赛博坦石头上拍照,大风撩起她的裙摆,她只能伸手将一大团紫色的布料(涤纶加纯棉加乔其纱)紧紧压住腿。她不算漂亮,也不算难看,你静下心来发现她保养得特别好,娇俏的鼻梁,嘴巴小小的,皮肤相当好,皱纹也很少。你为她拍了十多张照片。她笑着让你也摆拍几张,你没兴趣,也没心情。她要是知道鹿鹿就躺在病床上,该怎么想?出于礼貌你还是让她拍了几张,嘴角耷拉着,硬邦邦、傻乎乎的,像个囚犯。她想逗你开心,可你开心不起来。你死沉着脸,一团高气压坠在胸口,你能感觉到触摸它像撩拨一种极限。这种感觉在小安消失之后出现过,那个时候你不相信他没了。你不相信。你想肋生双翅遍地寻找他,发现他。你很快发现水面上细微的发光物,一种娇小的像草茎的小东西,微波流转,你用小树枝挑起来它就消失了,就像水和空气营造的幻象一样,不是真的。夜幕降临了,你们像一对又完全不是一对。此刻,对面西山山巅被一条条玫瑰色或紫色或蓝色的余晖勾勒出来,大而坚硬,仿佛形而上的世界边缘,越过峭拔的山头就是万丈深渊,是地球之外的太虚和茫茫宇宙,而你们是微末的小颗粒,随时可能消散。你无法想象这么低级的飘荡着臭味的地方半空中会出现任何庞然大物。38号,就像个超级笑话。罗姐带你出来寻开心吧,她没什么事情好干,没准也下课了,拿你这个更早下课的老家伙开涮呢。但是,你宁愿相信她嘴里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介于密友和爱人之间,就该互相倾诉。不过,心声这种东西到底几斤几两就不好说了,再者,她一直没跟你吐露过什么啊,你想起茶水间的沉默,那种自然的坦露和存在,那种安安静静的不妨碍、不干扰也不担心什么的松松垮垮,就好像事物间关系和谐稳定,没有背叛,也谈不上亲近,像石头和雨水一样。罗姐捡起小石子在水面打出水漂,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它们欢快爆响着奔向远方,又突然一头栽进水里。你也来了兴致,说,看我的!卷起袖子找到一片顺手的薄石片,你弯下腰,使劲扔出,让这片小东西贴着薄薄一层湖面刮擦过去,如同爱抚,亦或是另一种磕磕绊绊的倾诉。然后,更大的像天空或硕大气球的沉寂降下来,笼罩湖面,发出淡白色的胎膜般的反光,像油污,又像夕阳不情愿地趴在湖面上向人类呼吁哀告。哀告什么呢?寂静拒绝解释。你回头看一眼卖凉米线炸土豆的小贩,他们像睡着了一样呆站着,一动不动。整个大自然,我指的是昆明滇池一角的湿地公园某个静谧的角落,正在亮出冬眠般的温柔。你们停止打水漂。似乎累了。不是累,稍稍运动一下你已经呼呼喘了,当然不是累,还不是,是身体机能的蜕化和坍塌。罗姐身材圆润,红毛衣勾勒的身体曲线仍然是人生中最骄傲的宽阔优美,离衰败还早得很呢。她搓搓手,问:“你下一步什么打算?”你说:“什么什么打算?”她说:“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她还说:“我知道你的情况,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些嘛,关于复杂的人性,你什么也说不上来。你想了想说,你不知道,家里的事情嘛,不说了吧。你还没什么想法。暂时还没有。什么都没考虑,也许再也不考虑了,变化太快你已经跟不上了,不如原地待着,也许,原地待着也很不错。她看了看你,凑近了把你肩膀上一小片湿漉漉的枯叶弹掉。你闻到她身上好闻的气味,和车上闻见的香味很不一样,大概时间会让香味发生变化。她认真地说,她儿子的父亲以及儿子正从杭州回来。说完就不说了。你心里直犯嘀咕,干嘛说这个呢?儿子的父亲不就是丈夫嘛,她干嘛要绕着圈子说话?他们一起从杭州返回,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你想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
天色以极快的速度暗下去,像有人按下快播键。
它出现的时候你突然就醒了。你似乎睡着了被人带出去接受处决。你想跑到某个废弃的世界边缘一直呆下去,这样就没人处决你了。像小棺材一样的茶水间,最多三个平米,微波炉、电冰箱、热水器、马克杯、咖啡、水池。单纯的永恒的寂静围绕你、笼罩你,像一个地洞,你最终失去它。也许你已经待得太久了甚至让人误以为你患上抑郁症。这种错觉可能把你害了。他妈的,压死人的不就这些东西吗。你睁开眼睛,在短短几十秒,最多一分钟的时间里,你听见血液的流动和螟蛉小鸟的鸣叫,极其低微,可你听见了。接着眼皮发热发红,一束强光刺过来迫使你睁开眼睛。罗姐兴奋地拍了拍你,贴你很近,让你感觉到她甜丝丝的带有润肤霜味的呼吸和她温润身体的熨帖、丰满的热量。你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但见西山上冒出一团直苗苗的白光,拖曳、咆哮像一枚超大的烟囱倾斜身体砸向水波不兴的深灰色的滇池。你惊讶地喊出来。你听见它划破空气的嘶嘶声,像金属摩擦金属或碾碎石头泥巴的咆哮,准备和这个世界决裂。烟囱越来越大,越来越亮,像一枚火箭掉下来,但是滇池容纳不了它。根本塞不进去。罗姐差不多附在你耳朵上喊道:“你看见了吗?老杜你看見了吗?”你向她使劲点头,好像你们在面对一个巨大熔炉,耳畔全是啸叫,实际上它声音不大,甚至默然地以其卑微的低频分贝戳向湖面,然后炸开制造一记闷响,嘭……你不由自主扶住她的腰,略有赘肉,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你留意水面变化,然而它立即恢复平静,烟囱瞬间消失,唯有一簇簇透明的白光银箭一样地攒射。哦,鹿鹿的梦境!你终于见证了她的梦境。嗷,嗷——你也大叫。很快,水面上除了光什么也没有剩下,唯有寂静。百分百的寂静。是最初的滇池,也不再是熟悉的滇池。咋回事——你大喊。没人回答。你看见小贩们在打哈欠、为炭火扇风,什么变化也没有,什么也没看见、听见。UFO?是吗?38号?是不是38号?你大声问她。她没回答,小声问你看见了没有?看见了吧老杜,我没骗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