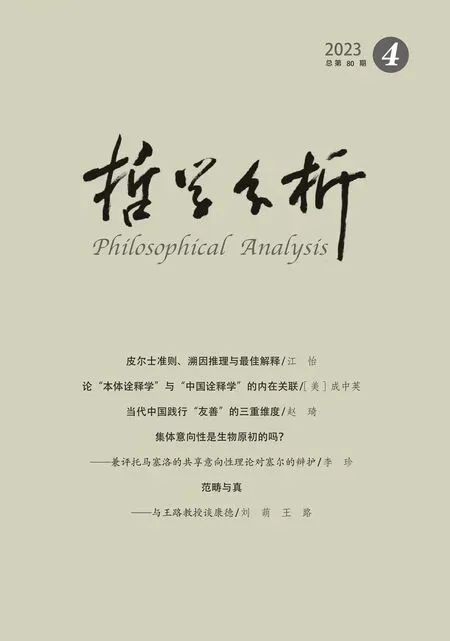逻辑学的伦理之维:皮尔士的洞见及其当代回响
张留华
在1903年于哈佛所作的实用主义系列讲座中,皮尔士首次公开提出:推理是一种受控行为,而以推理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学具有一种伦理维度,即逻辑上的好坏最终不过是道德上好坏的一种具体应用。这一论题不仅在皮尔士本人哲学体系中占据关键地位,而且对于我们在120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逻辑学的本性具有重要启示。本文尝试从“逻辑学研究对象”“逻辑理论的选择难题”两个层次为皮尔士这方面的观点重构论证,然后,针对可能出现的异议,援引皮尔士及当代逻辑哲学思想资源予以回应。这里的预想读者不仅包括皮尔士学者,更主要是对逻辑哲学有兴趣的当代分析哲学家群体。因此,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对皮尔士相关文本的评注训诂,而是对皮尔士哲学见地的阐发应 用。
一、“皮尔士论题”及其地位
自1878年首次提出“实用主义准则”(the Maxim of Pragmatism)近25年之后,晚年孤寂的皮尔士在哈佛系列讲座中接续和推进他的某些重要思路,并对当时学界流传的实用主义观念进行公开评论。皮尔士认为,自己与新近实用主义者的主要差别之一在于:“我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纯粹的逻辑准则,而不是什么崇高的思辨哲学原则。”①EP 2:134. 本文采用皮尔士文献的标准记法,EP 代表Charles S. Peirce, The Essential Peirce, Vol. 1—2,Nathan Houser, Christian Kloesel and the Peirce Edition Project (ed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1998,冒号前后的数字分别表示卷号和页码;CP 代表Charles 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 S. Peirce, Vol. 1—8, Charles Hartshorne, Paul Weiss and Arthur Burks (ed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1958,圆点前后的数字分别表示卷号和小节号(而非页码)。他重申了早期对于实用主义准则的表述(“考虑一下我们所持概念的对象具有什么效果,这些效果具有可设想的实践影响;然后,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一对象的概念的全部了”),依旧坚信它对于解决诸多棘手问题大有用处。然而,一种方法有用处,这并不能表明它就是对的。“一个概念可能具有的实践结果构成了这个概念的全部所有”,何以为此辩护呢?皮尔士早期为该准则提供的论据是:所谓信念(作为概念内容)主要是准备有意采用一个相信可以作为行动指南的公式,即以条件句表示的、结果从句具有祈使语气的“假言律令”。然而,我们如何知道信念不过就是准备有意按照所相信的公式行事呢?皮尔士认为,自己之前对于这个关键问题的回答不够清楚,更不能令人满意的是,他当时将这个问题还原为心理学事实(如“人有一致性行事的冲动”),可人的“自然冲动”会发生改变。这个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直接关乎我们对于“实践效果”(practical effects)的完整把握。无疑,一个人将按照他的信念行事,只要他的信念具有某种实践结果。但产生疑虑的地方在于:是否这就是信念的全部了,是否信念只要不影响行为就完全无效?譬如,相信正方形的对角线与边长不可通约,这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从测量经验上看不出什么“差别”,因为一种差异量ε不论是多么小,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可通约量(有理数)使得它与对角线长度之差远远小于ε。如果实用主义者不想因此清除掉数学上有关不可通约量(无理数)的整个学说,他必须说明其“实践效果”上的差别究竟何在?或许,一种带有诱惑性的回答是:把某一数量称作无理数而不把另一数量称作无理数,这种用词和表达上的差别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差别”(practical difference)。但如此不加限定地解读“实践效果”,无异于让实用主义的旨趣(即用于排除那些无意义的争论)“挥发殆尽”,最终退化为一种琐碎论调。②EP 2:141.
正是在尝试对实用主义准则的上述合法性问题进行一次“系统而科学的彻底考察”时,皮尔士在实用主义系列讲座第一讲中转而论及逻辑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实用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思想要根据我们准备去做的事情来解释,倘若是这样,逻辑学即有关我们应该如何思想的学说,必定是伦理学即有关我们有意选择去做什么的学说的一种应用。”①EP 2:142.随后第四讲和第五讲中,他对这个话题又展开论述。这是一种值得特别关注的观点,不仅是因为它对于多数逻辑学者显得陌生,而且是因为皮尔士自己当初提出实用主义准则时并未涉及这一点,在该系列讲座之后的多个场合却反复重申。譬如,1903年11 月在洛厄尔学院的讲座《推理何以可靠?》中,他说道:“在我看来,逻辑学家应该认识到何为我们的根本目标。似乎道德学家才有义务去发现此种东西,而逻辑学家只能接受这方面的伦理教条。”②EP 2:253.在1904年6月写给杜威的一封信中,皮尔士写道:“[对错之分和真假之分]只能通过自控来维持。正如道德行为是自控型行为一样,逻辑思维是合乎道德的或自控型的思想。”③CP 8.240.在1906年一篇题为“实用主义的基础”的手稿中,他继续表示:“对思想进行控制以便使其符合一种标准或理想,这是控制行动使其符合标准的一种具体情形;前者的理论[逻辑学]必定是后者理论[伦理学]的一种具体规定。”④EP 2:376—377.本文将把此种认为逻辑研究需要诉诸伦理学原则的观点称作“皮尔士论 题”。
需要指出,当由实用主义准则转到皮尔士论题时,他用的表述方式是“倘若是这样”。对此,我们不应理解为皮尔士是在拿实用主义为皮尔士论题作辩护,毋宁说他认为是实用主义准则本身承诺了逻辑学与伦理学的某种关系。单就皮尔士思想研究而言,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它提示我们,为了能够证成实用主义准则,或者,为了精准把握皮尔士版本的实用主义,我们需要将其置于更宽广的视域下。可以说,皮尔士论题为所有熟知实用主义准则的读者提供了一条进入皮尔士哲学思想大厦的秘密通道。在这个大厦中,读者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皮尔士的实用主义何以不同于同时代的唯名论者,也可以看到实用主义准则何以有可能得到证 成。
首先,通过将逻辑学与伦理学建立联系,皮尔士论题向读者进一步明确:实用主义准则中所关注的不只是行动,而是能自控即有目的之行动。如果实用主义准则是一条逻辑准则,而逻辑学所关注的乃是像道德行为那样的自控型思想,那么,“目的”理应成为我们解读实用主义准则所谓“实践效果”的一个关键点。事实上,皮尔士在1902年出版的《哲学与心理学辞典》中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实用主义准则何以会遭到误用的:“詹姆士出版他的《相信的意志》一书,后来又出版他的《哲学观念与实践效果》,把[实用主义]方法推向极端,令我们心生踌躇。该学说似乎以为人的目的就是行动……但倘若承认行动要有目的,而目的是带有一般性(of a general description)的某种东西,那么该准则本身——它是说为了能够正确把握概念我们必须去查看概念的结果——的精神将把我们引向一种有别于实践事实(practical facts)的东西,即把我们引向一般观念(general ideas),以作为真正能解释我们思想的东西。”①CP 5.3.公平而论,这里经由“目的”而引入的“一般性”成分,在皮尔士1878年对于实用主义准则的表述中已见端倪,即他所谓的“实践效果”不限于当前所见某些具体行动的特定效果,而是面向未来包括所有“可设想”的场景;但是,它在当时似乎并未得到充分强调,于是才有了詹姆士等人的误用,以及被认为无法解释关于不可通约量之信念的实践效果。②以这里的“一般性”作为线索,皮尔士本人给出的解释是:“关于对角线不可通约性的信念,关系到一个人在处理分数时有什么是可期待的,但它的意思完全不涉及物理测量时所期待的东西,后者就其本性而言仅仅是一种近似。”(CP 5.541)很多年之后,皮尔士试图彻底纠正对于实用主义准则的误读,这时他选择把这条逻辑准则纳入伦理学视域下,并由此凸显一般性(根本)目的之于理性活动的必要性,这对于当时乃至今天的广大哲学受众而言,可达到进一步澄清之效。一如他在1903年哈佛系列讲座第五讲中所揭示的:“如果[概念之作为]符号的意义在于它会如何促使我们行动,显然这里的‘如何’不可能是指对于它所造成的机械动作的描述,而一定是指对具有某某目标的行动的描述。因此,为了足够充分理解实用主义,以使其经受理智评判,我们有责任询问,什么是能够在持久的行动进程中无限期追求的最终目的。”③EP 2:202.
其次,皮尔士论题只是为证成实用主义准则而迈出的第一步,唯有循此继续追索至其哲学大厦内部,方能洞见实用主义的全部秘密。将实用主义作为逻辑准则置于伦理学视域下,是由一种规范科学通往另一规范科学,然而还有第三种被认为比逻辑学和伦理学更基本的规范科学——美学。他说:“伦理学说必须以[美学]作为基础方能建立起来,而伦理学反过来又要被逻辑学说攀登。”④EP 2:143.只有把所有规范科学都考虑在内时,我们才真正“踏上探寻实用主义秘密之路”⑤CP 5.130.。对此,皮尔士在1902年写给詹姆士的一封信中坦露:“直至[1898年剑桥系列讲座]之后,我才得以证明逻辑必须奠基于伦理学之上(逻辑学是伦理学更高阶段的发展)。即便那时,我有一段时间也很愚笨,甚至看不到伦理学同样必须依赖美学……”⑥CP 8.255.不仅如此,为了回答涉及规范科学的一些问题,我们还看到皮尔士1903年在哈佛实用主义系列讲座中多次论及现象学乃至数学。这与皮尔士本人对自己哲学思想的定位非常吻合,即遵循康德风格的“建筑术”,其哲学思想的诸分部勾连一起,任何片段(包括实用主义准则)都不可能孤立地得以恰当呈现。根据皮尔士的科学分类法,哲学是一类广义实证科学,其内部可分为现象学、规范科学和形而上学三块,在哲学之前是纯数学,哲学之后则是物理学心理学之类的具体科学。这一序列的诸科学门类,前一部门为紧挨其后的部门提供基本原理,后一部门为仅靠其前的部门提供反思素材。①这方面的更多详细讨论,参见张留华:《皮尔士哲学的逻辑面向》第一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当然,在指出皮尔士论题对于理解皮尔士本人哲学思想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对哲学大众(如本刊的预期读者群)来说,皮尔士论题(就像皮尔士那里其他独创性观点一样)是一种不够自然甚至略显奇怪的观念。这不禁让当代读者猜测,皮尔士论题即便不能说是错误的,基于仁慈理解原则,它之所以显得新奇,也很可能只是因为皮尔士预想的逻辑学和伦理学与我们今天的观念不一样。这的确是一种合理猜测。因为,从皮尔士文本来看,他本人也曾犹豫是要把伦理学定位为“规范科学”还是“前规范科学”,他甚至提出“antethics”(代伦理学)来指代他那种专注于行动与理想相符的规范理论,以区别于那种经常延伸至哲学之外的作为“权利与义务”(rights and duties)学说或研究“善行”(virtuous conduct)的传统伦理学;②CP 1.573, 1.577. 皮尔士本人在不同时期似乎抱有两种伦理学观念,一种是保守的情感主义,另一种是作为规范科学的伦理学。不过,里斯卡认为,二者之间表面上的冲突,可以通过皮尔士那里的“进化”概念来消解,参见J. Liszka, Charles Peirce on Ethics, Esthetics and the Normative Scienc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21, pp. 4—5。至于逻辑学,他则倾向于将其等同于符号学(semiotics),分为理论语法、批判论和理论修辞,这似乎也与当代侧重于形式系统建构的主流逻辑形态(即现代符号逻辑)相去甚远。③注意,皮尔士曾被誉为现代符号逻辑的奠基人之一。但对于这个断言,要谨慎接受。皮尔士的确从现代代数的角度对逻辑问题进行了研究,但他并不愿将其处理为数学的一部分。与弗雷格、希尔伯特等人倾向于把逻辑数学融为一体不同,他强调逻辑研究目标不同于数学研究。譬如,逻辑学上由以开展演绎的假说,并非纯理想性的,它们旨在符合确定性的事实真理;还有,数学推理只是纯演绎性的,而逻辑不只是演绎,甚至主要不是演绎性的。(EP 2:198)然而,笔者想要指出,皮尔士的“逻辑学”和“伦理学”与当代主流用法之间的差异不足以取消皮尔士论题对于当代学界(尤其是逻辑哲学领域)的相关性。因为,正如很多学科观念会随着时代发展出现某种变化一样,逻辑学和伦理学各自的边界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皮尔士本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伦理学是“一个最令人神魂颠倒的思想领域,却充满了陷阱”④EP 2:142.;而“逻辑学这门科学,至今仍未完成对其第一原理的争论阶段,……人们已经给出了近百种定义”⑤CP 2.203.。重要的是,皮尔士的观念跟当代主流观念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连续性。以逻辑学为例,皮尔士视之为逻辑学中心任务的“区分推理之好坏”,至今仍是当代很多逻辑教科书界定逻辑学主题时所提到的,即便是把当代各种纯粹或非纯粹的形式逻辑都考虑在内,通常认为,推理仍属于逻辑的“正统应用领域”(canonical application),区分有效推理与无效推理是一种核心关怀。①参见Graham Priest, Doubt Truth to Be a Li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65, p. 196; Daniel Cohnitz and Luis Estrada-González,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og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2—16。至于当今伦理学,不论是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还是应用伦理学,人类行为好坏的评价仍属于核心关注点,而这也正是皮尔士谈论行为与理想相符的初 衷。
在作出以上必要的澄清之后,本文接下来将不再囿于皮尔士所处的时代及其文本,转而主要从当代逻辑学和逻辑哲学的视角重思和评价皮尔士论题:先尝试重构对皮尔士论题的一些论证,然后看皮尔士论题在今天可能遭遇的挑战,以及能否得到合理回 应。
二、从皮尔士到当今逻辑哲学:重构对皮尔士论题的论证
从今天来看,逻辑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应归为逻辑哲学(即对于逻辑学本身的反思性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经常促使我们反思逻辑学的本性和范围。自19世纪末现代逻辑诞生以来,逻辑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一直属于热门话题。最常见的是由逻辑主义思潮所引起的逻辑与数学关系之争,以及与反心理主义思潮伴生的逻辑与心理学关系之争,然后随着现代逻辑向其他学科的应用和渗透,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语言学的关系也渐渐进入逻辑哲学家的视野。不过,皮尔士论题所涉及的逻辑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在当代逻辑哲学中很少被作为一个严肃话题单独予以讨论。如果询问身边的一位逻辑哲学家:“逻辑学与伦理学有何关系?”,他可能会提到:逻辑学训练有助于培养我们的某种伦理价值(如“审慎”),或者,逻辑学科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我们坚信某种伦理价值(如“客观性”)。②参见John Corcoran, The Inseparability of Logic and Ethics, Free Inquiry, Vol. 9, No. 2, 1989, pp. 37—40。这的确是有趣的话题,而且皮尔士本人也在这方面有过著名论述③皮尔士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观点有:“逻辑学首先所严格要求的一点是:任何确定了的事实,任何发生于一个人自我的事情,都应该对于他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凡是不愿牺牲自己灵魂以拯救全世界的人,其所有推理总体来说就不合逻辑。因此,社会性原则内在地根植于逻辑学上。”(EP 1:81)“为了能合乎逻辑,人们不应自私自利……”(EP 1:149)“信念受探究之影响渐趋得以确定,这可以说是逻辑学得以出发的事实之一。”(EP 1:169),但它们只是在谈论逻辑研究中所涉及的某种德性,尚未上升到逻辑学与伦理学的学科关系。本文所考察的皮尔士论题,是特定意义上的理论依赖关系。从皮尔士的科学分类法来看,伦理学与逻辑学是上位科学与下位科学之间的关系——伦理学为逻辑学提供某种“原则”(principle),而逻辑学为伦理学提供一些“素材”(data)。
对于一种严肃的哲学主张,我们期望它能得到严格论证。皮尔士自称已对皮尔士论题加以证明,从他的相关文本出发,我们也能在皮尔士本人的哲学框架内整理出一套详细论证。不过,本文的意图不止于此。①在皮尔士思想体系内部对于皮尔士论证思路的展开论述,参见F. Poggiani, “What Makes a Reasoning Sound?C. S. Peirce’s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Logic”,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Vol. 48, No. 1, 2012;Rossella Fabbrichesi, “The Entanglement of Ethics and Logic in Peirce’s Pragmatism”,in Rosa M. Calcaterra (ed.),New Perspectives on Pragmatism and Analytic Philosophy, New York: Rodopi, 2011, pp. 35—43。笔者认为,即便放在当今逻辑学研究前沿来看,即便不限于皮尔士学术圈而主要面向当代逻辑学人,皮尔士论题也仍能得到辩护。如果综合考虑皮尔士各个时期的相关思想,同时借鉴当代逻辑哲学中的若干思想资源,我们至少可以重构出关于皮尔士论题的两个——皮尔士本人会认同的——彼此关联但视角有别的论证思路。解析这些论证,有助于我们看到:为了维护皮尔士论题,一位当代哲学家有必要以及多大程度上可以与皮尔士共享什么样的基础观 念。
论证A:从内部研究对象来看,逻辑学是关于推理现象的一种理论,而推理本质是一种合目的因而自控型的思维活动,思想上的自控不过是自控型活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所以,逻辑研究要诉诸有关自控型行为的一般原则即某种伦理学原则。这是可以直接从1903年哈佛系列讲座第4 讲“七大形而上学体系”和第5 讲“三种规范科学”,1903年洛厄尔学院讲座《推理何以可靠?》,以及1906年手稿《实用主义的基础》相关解释中提取出的思路。②EP 2:188, 2:200—201, 2:249, 2:376—377.补上相关预设,可以重构为如下完整的论 证:
A1.逻辑学是关于人类推理现象的规范性科学。
A2.推理是一种自控型的思维活动。
A3.自控型思维不过是人类合目的行为的一种特殊形态。
A4.推理现象不过是人类合目的行为的一种特殊形态。(基于传递性,由A2、A3 得到)
A5.伦理学是关于人类合目的行为的科学。
A6.逻辑学所关注之现象是伦理学所关注之现象的一种特殊形态。(依据置换规则,由A1、A4、A5 得到)
A7.如果一门科学所关注之现象不过是另一门科学所关注之现象的特殊形态,前者(即便不属于后者的特殊分支)在理论建构上就需要诉诸后者的某种原则。
A8.所以,逻辑学的理论建构要诉诸某种伦理学原则。(依据MP 规则,由A6、A7 得到)
以上论证链条显示,最终结论A8 成立与否取决于前提A1、A2、A3、A5、A7 的可接受程度。如第一节所论,A1 和A5 至少是一种与历史上逻辑学和伦理学具有足够连续性的观念。A7 应该也是显而易见的,需要解释的倒是另一问题:逻辑学研究对象(推理)属于伦理学研究对象(即自控行为)的一种特殊形态,为何逻辑学没有被归为伦理学内部的分支学科?原因是,逻辑学之作为一门学科,主要事务是区分推理现象的好坏(并由此确定推理规则),但它本身并不对“行为目的问题”提出任何主张,后者是伦理学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并不一定仅仅按照研究对象来识别一门现代科学——心理学也可以研究推理现象,但并不一定因此而变成逻辑学。在皮尔士看来,科学家们自身彼此谈论一门科学时是指:“一个社会群体的总体活动,该群体成员全心致力于探明并相互协助探明他们有特殊装备加以研究的某一领域内的真相,他们的研究工作除获知神圣真理外不带任何外在目标,而且,对用以专门开展此类探究的通行方法以及对该领域事实上所已发现的东西,他们保持实质上的一致……”①EP 2:459.需要重点讨论的是A2 和A3。皮尔士本人对于这两点的确也谈论较多,但其中的道理在今天看来也不算费解,并可在当代学者那里找到呼 应。
先来看A2。其所涉及的“推理”观念或许对当代有些逻辑读者显得陌生,因为,形式逻辑教科书上提到推理时往往暗示它只是一种由前提和结论组成的公式序列或命题集。但只要我们坚守“推理主要是人的一种思维活动”和“逻辑学的核心工作是区分推理的好坏”,就有必要思考:推理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评价为好坏或是否有效呢?显然,并非人的任何活动都可以被如此评价。婴儿哭闹,你的头发和指甲会生长,他人打喷嚏,等等。这些现象,你可能喜欢或不喜欢,但若据此而评价婴儿、你自己或某个人的活动本身好坏或有效无效,那将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是处在主体的控制范围外的。正是这一点使得皮尔士每当谈到逻辑学时总是强调,推理是一种自愿(voluntary)、有意(deliberate)或自控(self-controlled)的思维活动:“我想说的是,有一些心智活动在逻辑上严格类似于推理,只是它们是无意识的因而不可控的,因此也不受批判。但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差别,因为推理本质上就是有意的、自控的。”②EP 2:188.
类似皮尔士那样对于“推理”的解释,在当代逻辑学中罕有人谈起,但之所以如此,或许只是因为它已在逻辑之作为规范科学这一学科性质中作出承诺,因而无需赘言。众所周知,规范性科学之不同于描述性科学,其中一点在于:规范科学所制定的法则“应该被遵循但不必已被遵循”①CP 1.575.。什么样的现象是“应该遵循但实际并非总是遵循科学法则”的呢?我们身外的万物运行,其法则是由物理学等描述性科学所提供的。在这些科学法则正确描述自然现象的前提下,任何自然现象(即便其中有人的参与)都不得不实际地遵循科学法则,试图一跃升天之人的失败,以及飞行工具的创造本身,都与是否遵循万有引力定律有关。而假若有一天果真发现有一种自然现象违背了先前信奉的某一所谓科学法则,也并不能由此认定科学法则本身实际未能得到遵循,毋宁说是先前对于科学法则的表述需要修改,或者先前被奉为科学法则的东西并非真正的科学法则。与之相比,我们的思维活动,即便逻辑课本已列出各种法则,但我们不难发现有逻辑法则“实际未被遵循”的情形,而且,面对这些情形,我们不必接着便去修改逻辑理论,因为,那只能说明逻辑法则本身就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规范性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我们已看到存在那样的现实情形,才要求有逻辑法则指引我们在将来尽量避免类似的情形。这就好像某些不道德行为的现实存在,它们反倒表明道德法则的必要性。但是,为何见到过去有不按某法则推理的情形却可以将该法则用于规范将来的推理活动呢?那是因为,我们跟皮尔士一样认为,不同于那些处在我们控制范围之外的现象,推理完全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自愿的、可控的思维活动,而且,过去所见到的推理现象并非总是好的。铭记这一点,我们很容易理解当代逻辑哲学家的下列说法:“思维法则……与其说像是物理法则,不如说更像是道德法则。它们确立一种关于何谓好推理的标准或规范,而我们正是对照此种规范才看到我们的推理有时存在缺陷。表达这一点的方式有时是说:逻辑法则是规范性的,而不只是描述性的。”②Samuel Guttenplan, The Languages of Logic,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6, p. 11.
再来看A3。理解它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自控型思维是合目的的。当我们说思维活动是自控的时,难以想象它是缺少目的或理想而仍属于自主控制的。然后,只要我们不在心理学意义上理解“思想”,而像皮尔士和当代很多哲学家那样,将其作为与语言符号密不可分的活动③人们常说“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这种过于平凡的表述容易让人低估语言对于逻辑的重要,因为它似乎给人印象:语言对于逻辑学的关注对象——思想——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载体而已;但实际上,语言是思想唯一的载体,思想与之密不可分。借用皮尔士的隐喻,思想与语言的关系犹如洋葱与层层包裹的洋葱皮的关系,当我们试图剥去一层一层的洋葱皮而寻找洋葱的内里时,发现除了这些包裹层,其他什么也没有。(EP 2:460),便可进一步把作为自控型思维的推理视作合目的行为(即所谓的“言语行为”)。受此观念激励,当代一些学者已开始在行为的层面上理解逻辑学所关注的推理法则,譬如,温奇在谈到“卡罗尔疑难”的寓意时指出:“……对于从一组前提推出一个结论,一种充分的辩护是:注意到其结论事实上的确能推导出来。坚持要作进一步的辩护,那并非额外的谨慎,它显示了对于何谓推理的误解。学习推理并非只是被人教导命题之间明晰的逻辑关系,它就是学习做事。”①Peter Winch,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London:Routledge, 2008, p. 53.赖尔把逻辑法则理解为一种类似火车季票一样的“推理券”(inference tickets),他指出:“说某种东西必须或必然怎么样,其功能类似我所谓的‘推理券’;它授权我们由该说法中可能已指定或未指定的一些情况推断这种东西如此这般。”②Gilbert Ryle,The Concept of Min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110.顺便指出,这种“推理券”称法已影响了普莱尔这样的主流逻辑学家,参见A. N. Prior, “The Runabout Inference-ticket”, Analysis, Vol. 21 No. 2, 1960。
论证B:如果逻辑理论的建构完全抛弃伦理考虑,最后会遇到逻辑理论的选择难题,而实际的选择策略,不得不引入一些伦理因素。这可被视作一种归谬法,与论证A 相比,论证B 属于一种间接论证的思路,而且主要借鉴当代逻辑哲学的相关讨论,从逻辑理论的比较层面着眼。不过,它可以在皮尔士本人那里找到某种预示,他的有关评论可以作为该论证的注脚。为完整呈现思路,可以把论证B 重构如下:
B1.若遵循宽容原则,逻辑研究可以完全抛弃伦理考虑,将会出现多种逻辑理论“百花齐放”。
B2.面对多种不同的逻辑理论,我们需要解决如何从中寻找“更好理论”的难题。
B3.为了解决逻辑理论的选择难题,不得不引入一些伦理因素。
B4.若逻辑研究完全抛弃伦理考虑,我们最终不得不引入一些伦理因素。(基于传递性,由B1、B2、B3 得到)
B5.所以,逻辑研究并非可以完全抛弃伦理考虑。(依据归谬原则,由B4得到)
这里,最终结论所依赖的实质前提是B1、B2 和B3。让我们依次来看它们何以可接受或者在什么程度上可接受。B1 涉及当代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卡尔纳普所提出的“宽容原则”:“在逻辑学上,没有道德可言。人人都可自由建构自己的逻辑,即他所想要的那种属于自己的语言形式。他所要做的一切只是,如果他希望探讨逻辑,他必须清楚列出他的方法,并给出语法规则,但无需哲学论证。”③Rudolf Carnap,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 London:Routledge, 1937, p. 52.提出这条原则的时代背景是,20 世纪初经由弗雷格、罗素等人得以确立起来的现代一阶谓词逻辑逐步被奉为经典,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其他几个“不寻常”的逻辑系统(如三值逻辑、直觉主义逻辑等)已被提出。在卡尔纳普看来,历史上最初偏离罗素那种逻辑理论的尝试无疑是大胆的,可惜它们一直受阻于争取要做“正确的逻辑”,而“宽容原则”可以让我们克服这种阻碍,逻辑之船从此将驶向一片包含无限可能的大海。现代逻辑后来的发展情况,的确如卡尔纳普所预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点只需查看一下逻辑学期刊或专著对各种非经典逻辑或变异逻辑的建构和讨论就可得到验证。
B2 涉及逻辑多元论与逻辑一元论的问题。面对形形色色的逻辑理论,并非所有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都认为它们总可以和平共处。于是就出现了一元论者和多元论者之争:前者认为,即便没有唯一正确的逻辑,也不能说所有逻辑理论都一样好,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经过综合评估从现有诸种理论之中找到或另外新构建一种“最好的逻辑”;后者认为,我们可以不必确立哪种逻辑理论是最好的,或许有多种不同的理论同样地“好”,或许每一种理论各有各的“好”。显然,B2 是一元论者乐意接受的。多元论者看似会拒斥B2,或许他们不认为有“更好的逻辑”,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很难找到有逻辑哲学家认为普莱尔所设想的那种包含tonk 联结词的逻辑是好的。即便是像贝尔和雷斯道尔那样被认为较为激进的多元论者,他们虽声称弗协调逻辑、弗完备逻辑可以与那些完备且协调的逻辑理论一样好,但仍坚持把那些后承关系不满足传递性和自反性而被其他人称作逻辑的理论排除在外。“我们是多元论者。由此并不能说不论什么都可以。”①JC Beall and Greg Restall, Logical Plu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91.笔者相信,他们这种说法代表了一切公开的多元论者的共同态度。就此而言,追求某种意义上的“更好理论”,应该也不会为他们所拒 斥,尽管他们认为其中会有多个理论同样好。
B3 是需要重点辩护的。单从当前有关逻辑理论选择问题讨论的表面看,它似乎无法成立。因为,在发现有必要选择更好的理论时,我们所面对的是逻辑理论,需要一种比逻辑学更基础、更牢靠的东西,而伦理学历来被认为其本身争议严重,不足以担此重任。就逻辑哲学家们目前所倾向于采用的选择标准来看,似乎也从未谈到伦理因素。譬如,奎因坚持认为经典一阶谓词逻辑是最好的,但他这是说它的益处很多:“一是外延性……还有高效简洁……还有完备性……还有[它使得关于逻辑真理的各种常用定义]高度一致”②W. Quine, Philosophy of Log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79.。威廉姆森继承了奎因基于“比较优势”的选择策略,并明确提出借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理论选择标准,来表明我们何以认为某一逻辑理论是更好的,他说:“对各种逻辑的评估是跟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的评估连续着的……[自然]科学理论的选择遵循广义上的溯因方法论(abductive methodology)。比较科学理论时当然是看它们跟证据的符合度,也要看强度、简单、优美以及统一处理能力。我们可以粗略地称之为最佳解释推理……”①Timothy Williamson, “Semantic Paradoxes and Abductive Methodology”, in B. Armour-Garb (ed.), Reflections on the Li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334.采取类似策略的还有普里斯特,他认为,不管在哪一领域,我们选择一种理论都是看它是否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用以确定一个好理论的那些标准,“其中首要的是跟该理论意在加以解释的那些数据的契合度。……其他经常被调用的还有:简单性、非特设性、统一处理能力、富有成果”②G. Priest, “Revising logic”, in P. Rush (ed.), The Metaphysics of Log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17.。
逻辑哲学家比较逻辑理论时惯常采用的选择标准的确未涉及伦理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因素不相关,相反,“把伦理因素完全排除在外”恰恰是当前逻辑哲学家所用策略的困境所在。因为,以上所提到的那些标准要么并不清楚究竟指什么,要么它们合起来也无法决定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逻辑理论。威廉姆森试图用溯因方法论表明经典一阶谓词逻辑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好理论,而普里斯特则用它来表明弗协调逻辑才是最好的逻辑理论。不仅如此,约特兰(O. T.Hjortland)在最近一篇论文中还试图论证:同样是基于溯因方法论所建议的那些准则,我们还能走向一种特定版本的多元论立场,即可以同时选定多种不同理论作为“更好的逻辑”。③O. T. Hjortland, “Anti-exceptionalism about Logic”,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 174, 2017, pp. 631—658.笔者认为,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我们考虑到逻辑理论的目的所在。正如约特兰所揭示的那样,威廉姆森和普里斯特之所以基于同样的溯因论却最终选择不同的逻辑理论,根本上是因为他们二人对于逻辑理论(包括但不限于其目的)的理解不同,这进而会影响他们对于选择标准中“简单”“证据”等具体内涵的理解。威廉姆森认为,逻辑理论中的真理并非关指语言或概念,而是关指我们这个世界;与之不同,普里斯特则认为,逻辑理论关指有效性、一致性、形式性等,而这些主要是元语言层面的概念。与之相关,前者认为逻辑理论旨在表征世界,后者认为逻辑理论旨在确立一套有效的论证模式并解释其何以普遍适用。这只是逻辑理论之目的的两种可能形态,其他明显受目的支配的逻辑哲学立场还有逻辑建模论(认为逻辑理论的目的是为自然语言中的各种论证提供一种抽象但精确的模型)、逻辑表达主义(认为逻辑理论的目的是使得我们清晰表达我们自己的某种承诺)。④皮尔士曾批评当时德国著名逻辑学家西格瓦特(Christoph Sigwart)把阐释对逻辑性的感觉作为目标(EP 2:166, 2:255),那显然是心理主义。当代逻辑哲学家大都是反心理主义者,但如这里所示,他们在目标上的分歧依旧很大。倘若把这些差别考虑在内,就不难理解为何不同逻辑哲学家基于表面相似的标准最终却选择了不同的逻辑理论。若要避免此种困境,逻辑学家必须正视逻辑理论的目的这一问题,唯有确定了目的,逻辑理论的选择难题才能真正得以解决。
当代逻辑哲学领域中所经历的上述“归谬”历程,并不是偶然的。皮尔士自己的经历,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早期教训,可惜未被后来主流逻辑学家们所吸取。1902年的皮尔士在《小逻辑》书稿中这样描述伦理学对其逻辑研究的助益:“在我把逻辑学归在伦理学指导下以前,它就已经是一扇窗玻璃,透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重要真理,但灰尘让其变得模糊,上面的沟纹也令细理扭曲。依照伦理学的指导,我把玻璃熔掉,令其变成液态。我把它过滤清澈,浇铸在正确的模子里;等它变硬时,我再不辞辛劳地将其擦亮。现在它成了一面相当透亮的镜子,能看出许多之前不能看到的东西。”①CP 2.198.为什么会如此呢?用皮尔士的观点就不难解释。因为,“逻辑学所研究的是达到思想目的之条件或手段,它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除非能够清楚知道那种目的是什么。生活只能有一种目的。而界定这一目的的正是伦理学。因此生活不可能完全合理地合乎逻辑,除非基于一种伦理基础”②CP 2.198.。皮尔士的一种更为具体的评论是:“没有认识到与伦理学关系的逻辑学,其方法论部分(即便不是在批判论部分)一定严重不可靠。”③EP 2:272.结合当代逻辑哲学上的有关争论来解读,逻辑学的“批判论”部分(即好坏论证类型的划分),或许跟伦理学没关系,但当问及这些区分如何推进我们的各类知识,便进入方法论部分,此时伦理学就是直接相关的。逻辑方法论所追问的是:要实现某一明确认可的目的所要具备的条件都有哪些?但逻辑学本身并不回答(倒是预设)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当逻辑学家们无视这一点而选择(像纯数学家那样)完全自由地建构逻辑理论时,便会出现多种不同的逻辑理论。一旦遇到有必要从多种理论中选一种“更好逻辑”的情形,每个逻辑学家又只好各自把所在共同体内的“良知”或“直言律令”作为目标并由此解读和使用常见的那些理论选择标准。但逻辑学家们自发提出的那些未经批判性审查的目标,完全不是伦理学上所追求的那种可以一贯追求的“最终目标”。如皮尔士所言,“道德上唯一的恶就是不具有一种最终目标”④EP 2:202.。
需要补充的是,当我们说逻辑学的最终目的要从伦理学寻找答案时,并不是说单靠伦理学就能提供一劳永逸的解释,也不是说伦理学内部就不存在任何争议。至少在皮尔士那里,伦理学作为对于我们所审慎采取(deliberately prepared to adopt)的行为目的的研究,它要探明有什么样的目的可能作为至好(summum bonum),而为了把握“至好”这一概念,伦理学还得诉诸美学,因为,我们审慎采取的最终行为目的必须是本身令人赞赏的“美学上的好”,即不因场景而变、可以完全不必考虑任何外在效果而被视作理想的状态。①EP 2:200—202, 2:272.伦理学之所以对于逻辑学显得特别相关,主要是因为,思想之目的是行为之目的的一种特殊形式,伦理学领域对于何谓行为之最终目的的争论,对于解决逻辑哲学层面上的逻辑理论选择问题具有最为直接的帮助。这一点正在被新近一些逻辑哲学家所意识到,他们在谈论“逻辑是什么”“逻辑的功能”等深层次问题时,就大胆将其与当代伦理学尤其是元伦理学上的讨论进行类比,并试图从伦理学讨论中获得探究逻辑哲学问题的某种新路径。譬如,对应于元伦理学上的非认知主义和认知主义路线之争,逻辑哲学上自然地出现逻辑非认知主义 (logical non-cognitivism)、逻辑规范主义(logical normativism)。②关于逻辑非认知主义,参见H. Field, “What is logical validity?”, in C. Caret & O. Hjortland (eds.), Foundations of Logical Consequenc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33—70; M. D. Resnik, “Against Logical Realism”,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ogic, Vol. 20, No. 3—4,1999, pp. 181—194。关于逻辑规范主义,参见R. Hanna, Rationality and Logic, MIT Press, 2006; J. Leech, “Logic and the Laws of Thought”, Philosophers’Imprint, Vol. 15, No. 12, 2015, pp. 1—27。也正是鉴于这样的趋势,我们听到有学者断言:“当代逻辑哲学中一个一直未被充分认识到的形势与我们在当代伦理学中的境遇完全一样。那就是:什么可以算作以及我们如何决定它能算作理想上的正确推理……我们不必非要成为逻辑无政府主义者……才会好奇逻辑标准被认为来自何处以及究竟什么确立了其资质……”③Dale Jacquette, Logic and How It Gets That Way, Buckinghamshire:Acumen, 2010, p. 8.
三、可能的挑战及回应
很少有什么哲学论证是决定性的。我们在尝试对皮尔士论题重构可能的论证时,预期会有一些“反论证”,从而对已论证过的皮尔士论题构成潜在的挑战。受篇幅所限,这里不试图对所有可能的挑战作出彻底考察和全面回应,仅挑选以下最为常见或不难预期的两种异议。笔者认为,依据皮尔士文本和当代逻辑哲学思想资源,这两种挑战可以得到合理回应,由此至少能显示第二节的论证具有一定的稳健 性。
(一) 对于深受现代逻辑滋养成长起来的分析哲学家而言,皮尔士论题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完全搞反了逻辑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他们似乎可以反过来论证:伦理学依赖于逻辑学,因为,思想先于行动,涉及行动的伦理推理必须用到逻辑,而现代分析伦理学更是直接伴随现代逻辑而诞生的,有些基本的伦理概念也在以“道义逻辑”“规范逻辑”之名重新得以研 究。
这或许是最容易想到的对于皮尔士论题的挑战。但其中包含着对于逻辑学本性及其当代实践的严重误解。首先,逻辑学成果主要体现为关于推理的科学理论。借用中世纪的术语,皮尔士称之为logica docens。与之相对的logica utens,是我们人在言语实践等日常活动自然习得的一种区分推理好坏的能力。①需要注意,logica utens 并非只是描述性,它明显具有规范性的成分。当代逻辑学家普里斯特曾特别强调这一点,参见G. Priest, “Revising Logic”, in Penelope Rush (ed.), The Metaphysics of Logic,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218—219。logica docens 从logica utens 出发并对其进行某种提炼,进而形成一套可以在学院传授的专门学问。当我们说伦理推理中需要用到逻辑时,主要是指那种作为人类自然本性的logica utens,但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依赖于逻辑学的基本原理。运用logica utens 的伦理推理,当然可能会出错,但要纠正这种错误,不必诉诸logica docens,有时只需多一些关注即可。其实,只要意识到这种区分,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声称比伦理学更基础的科学研究(如数学工作)也都需要用到(实际上也在用)logica utens,但并不必因此而认为逻辑学(作为logica docens)就是天底下最基础的理论。②在皮尔士那里,逻辑学不是伦理学和数学的基础,却是其他科学门类(如形而上学)的基础。这方面一个非常出色的研究实例是Cornelis de Waal, “Why Metaphysics Needs Logic and Mathematics Doesn’t”,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Vol. 41, No. 2, 2005, pp. 283—297.其次,关于“道义逻辑”“规范逻辑”的出现,这顶多是借助于现代形式化方法把伦理学家既有的某个伦理概念以系统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不意味着此种“呈现”对于开展伦理学研究有任何基础性作用,因为,依照此种做逻辑的方式,伦理学家们有多少种不同的伦理观念,便可以建构出多少种不同的逻辑系统,伦理学领域的那些关键争议不是在逻辑系统中得以解决,而只是在后者找到一种新的呈现方式。借用哲学家布兰顿的表达主义来看,正如当代各种其他形态的哲理逻辑(philosophical logics)一样,“道义逻辑”“规范逻辑”只是把伦理学家所承诺的某种理性观点以二阶方式清晰表达了出来而已。③Robert Brandom, Tales of the Mighty Dea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9—10.最后,现代符号逻辑本身的发展历程表明,逻辑学绝非像早期分析哲学家所预想的那样仅仅提供给我们一种纯净而无争议的“基石”。弗雷格、罗素的逻辑主义方案、希尔伯特的形式主义方案等那些一开始颇有野心的逻辑理论的命运启示我们:“逻辑学是人类境况诸多面相的一个缩影和寓言。当我们试图在逻辑学或生活中拥有我们想要的一切时,我们往往会在后来道路上的某个地方付出预想不到的代价。”④Dale Jacquette, Logic and How It Gets That Way, p. 265.
(二) 当我们一直在强调伦理学对于我们把握逻辑研究之目的的重要性时,有挑战者或许指出:当前大多数逻辑学家们对于逻辑研究目的已经有一种共识,那就是,逻辑学追求的是“真”本身。如果说普通经验科学主要是追求“事实真”,逻辑学家所追求的则是更具一般性的“形式真”。用弗雷格的话说,“‘真’一词可用来指示逻辑学追求的目标”,“发现真理是所有科学的任务,逻辑学所要做的是弄清楚关于真的法则”①Gottlob Frege, “Thought”, in Michael Beaney (ed.),The Frege Reader, Cambridge,Mass.:Blackwell, 1997, p. 227,p. 325.。“真”之对于逻辑学的重要性,体现在当代逻辑学家习惯于用“保真性”(truth-preservation)界定有效推 理。
对此,一位皮尔士学者当然可以回应:当代逻辑学家所谓的“保真性”仅限于用作界定演绎推理的有效性,而更多逻辑学家(包括皮尔士)所关注的不只是演绎推理,还有归纳、假说等其他推理类型。但信奉演绎至上的逻辑学家可能会说,所谓的归纳、假说等,若能被视作推理,它们也可以转变为某种形式的演绎(如贝叶斯推理)。这方面的争论当然可以继续下去,不过,姑且让我们限定在演绎推理上。②当然,当代逻辑学家还可能指出,即便对于演绎有效性,“真”也没那么重要,因为很多逻辑理论中是把有效性界定为“保特指值”(designated-values-preservation)。但是,坚信真之重要性的人会说,特指值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本文这里且将此按下不表。皮尔士以及一位同情皮尔士论题的当代学者会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呢?我们在《小逻辑》书稿第4 章(1902—1903)中发现了皮尔士对那种把“真”简单作为逻辑研究目标的读者的评论。若问这些人怎么来理解所谓的“真”,他们会回答“真就是与对象相符”。皮尔士提醒:这并不能让人理解,除非能告诉我们这里用于界定“真”的“对象”(object)是什么。或许,他们接着会说,那就是“实在”(reality),即这种东西拥有某一特征,不论我们是否认为这种东西拥有该特征。但这仍不能令人满意,除非他们指出一个东西“拥有某一特征”(has a character)是什么意思。此时,若要用一种更为人知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点,或许只能说,一个东西拥有一特征,是指有种东西对其来说是真的(true of it)。于是,穿过重重迷宫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一开始的“真”概念。③CP 1.578.当然不能说皮尔士这是要把“真”完全从逻辑学中排除出去,但他在此的担忧显然是:单说逻辑学追求真,然后不作任何解释,这并不能解决我们所关心的逻辑研究目的问题。④在皮尔士看来逻辑学目的究竟是什么以及此种观点在当今能否站得住脚,这些不是本文重点。相关的初步讨论(尤其是“真”与“目的”“满足”等观念之间的内在关联),可参见F. Poggiani, “What Makes a Reasoning Sound? C. S. Peirce’s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Logic”, Transactions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Vol. 48, No. 1, 2012。事实上,当代逻辑哲学家的相关研究已表明,倘若仅仅把“真”作为初始概念而不做任何解释,逻辑教科书上作为保真性的“有效”或将成为完全不值得追求的廉价(cheap)之物。譬如,假设UV 代表某一具有句法一致性的逻辑理论所授权的推理模式,不论它实际上看起来如何奇怪,运用当代逻辑学上广为接受的T 等式,ST“S”,T“S”S,我们最终都能证成它的“保真性”:UV↔T“U”T“V”,即,任何推理模式都是有效的。⑤Jody Azzouni, “A Defense of Logical Conventionalism”, in Penelope Rush (ed.), The Metaphysics of Logic,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44—45.
当然,那些哲学家们真正的担忧或许是:如果在“真”之外或就“真”本身再做进一步的探讨,会让逻辑学目的变得相对化,甚至会退化为某种类似感觉一样不可靠的东西。对此,皮尔士本人也作出过专门回应。他向我们澄清:把逻辑学的目的问题置于伦理学和美学下进行研究,绝不是要走向某种享乐主义,因为,将美学等同于感官上的快乐或痛苦,那完全是对美学研究的误解;伦理学中所关注的目的也不同于康德那种被宣告为不可挑战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反复无常的不理性嚎叫”的“直言律令”,而是我们在充分自控之下经过所有可能批判后审慎采取的最终目的。①EP 2:189, 2:202.必须承认,皮尔士所谓作为规范科学的伦理学和美学研究究竟容纳哪些具体内容,学术界尚未能获得足够清晰的完整图像。但不论怎样,皮尔士并不担心把逻辑研究受制于伦理学原则会使得逻辑学不够严肃。或许,逻辑学因此将变得不再那么神圣,但逻辑研究因此而获得的是重要的自控性。正是这种自控性使得他相信:“一如受控于伦理理由的行为趋向于确定某些行为习惯……并在此意义上可说是注定好的,受控于理性实验逻辑的思想也趋向于确定某些意见,同样可以说是注定好的……”②EP 2:342—343.与之相呼应,1908年皮尔士在给维尔比夫人的信中写道:“一个推理是‘合乎逻辑的’当且仅当它受制于一种长远来看必将通达真相的习惯。”③EP 2:480.
四、结语
作为皮尔士思想的一项拓展性研究,本文承诺了两条方法论原则:(1)为了对皮尔士思想得到尽可能融贯和完整的解释,不得不(至少暂时)忽略某些看似相关却与主体论述不一致的文本片段;(2)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推进皮尔士哲学,我们要在避免时代错置的前提下,主动将其置于当代哲学的问题域下,开展适当对话,并在必要时填补可能的论证。在这两条原则指引下,倘若上文的讨论没有致命问题,可以说,皮尔士论题并非只是一种过时的奇怪论调,它不仅可以在今天得到同情理解,甚至正在被当代逻辑哲学的研究进程所验证。
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逻辑哲学”分支④通常认为,现代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哲学,是伴随着多种不同于弗雷格、罗素的形式化系统的现代非经典逻辑系统被广为认可而出现的一门以“哪一种逻辑系统更好”为核心问题的学问。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传统意义上把“逻辑哲学”泛泛理解为对于逻辑学的哲学反省而不涉及现代形式系统之间的竞争,当代评论家对于皮尔士关于“推理何以可靠”等问题的考察,大多可归在此处。,在皮尔士时代尚未正式形成;但他几乎全程参与了现代逻辑的创立,并长期关注逻辑史和逻辑记法哲学,这使得他有资格也有可能对现代逻辑的本性和范围等较早提出诸多洞见。作为自称终生致力于逻辑研究的一位多面科学家,皮尔士坚持把逻辑学奠基于伦理学之上,他的重要关怀其实是当代逻辑哲学中的“规范性”难题,即,就当前流行的逻辑方法论而言,一个人不遵守当前理论所规定的逻辑规则(如分离律或矛盾律)却很难被指责为不理性。虽然这是一个在皮尔士逝世半个多世纪之后才被当代哲学界意识到真实存在的问题,但它普遍被认为是一个重大挑战。①对这一难题的出色呈现,参见G. Harman, Change in View: Principles of Reasoning, Cambridge: MIT Press,1986;John MacFarlane, “In What Sense (If Any) is Logic Normative for Thought?”, unpublished manuscript,2004, available at https://www.johnmacfarlane.net/normativity_of_logic.pdf。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难以解决,有哲学家甚至反过来声称逻辑学不具有规范性,如:Gillian Russell, “Logic Isn’t Normative”, Inquiry,Vol. 63, No. 3—4, pp. 371—388。逻辑学过去常被预期作为理性规范②即便是在公认的现代逻辑奠基人弗雷格那里,逻辑学也是被当作规范科学的。,为何今天却很难为自己的规范性地位辩护呢?这一难题的症结之一很可能是当今哲学家们过分解读了维特根斯坦那句话——“逻辑必须照顾它自己”③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D. Pears & B. McGuinness (trans.), 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 1974, p. 57.。只要我们继续相信这句话,逻辑学的目的就无望得以确定,因为,关注目的问题的是伦理学,而非逻辑学自身。应当承认,为了最终解决“规范性”难题,不论是皮尔士学者还是当代逻辑哲学家,在皮尔士之后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但皮尔士所给出的一个重要提醒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逻辑学范围内。即便在逻辑哲学层面上,也不能因为“逻辑哲学”一语的模糊而忽视重点。因为,对逻辑规范性之源头的哲学省察至少需要细分哪些是伦理学上的、哪些是美学上的、哪些是现象学上的,这些省察有义理上的先后之别。
最后,笔者愿意以皮尔士1902年手稿中的一段话,重申本文认为即便今天看来依旧发人深省的一种洞见:“逻辑学之所以争执不休,主要原因是关于这门科学的真正目标目前竟有[如此多]不同意见。但这不是逻辑上的困境,而是伦理学上的困境;因为伦理学才是关于目标的科学。……的确,伦理学历来都是且永远会是一个辩论剧种,因为伦理学研究就在于逐渐达成对于令人满意之目标的一种清晰认同。无疑,它是一门很微妙的科学;但真正创生并解决伦理学问题的并非逻辑学,而是对理想的详细阐述。”④CP 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