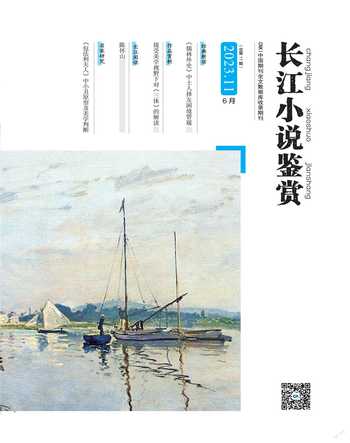库切“耶稣三部曲”中的“精神悬空”现象书写
[摘 要] 库切在“耶稣三部曲”中构建的乌托邦社会解决了人的外部需求,人们不会遭受战乱、贫穷、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等外部威胁。然而,超越了现实的乌托邦社会无法提供现实的价值源泉,移民们无法解决由外部地理空间的转移而导致的内部“精神悬空”问题。本文以尼采的消极虚无主义与积极虚无主义为理论依托,从家庭共同体和过往纽带的断裂以及信仰的虚空三方面分析库切“耶稣三部曲”中的“精神悬空”现象书写。
[关键词] 库切 耶稣三部曲 精神悬空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55-04
《耶稣的童年》《耶稣的学生时代》和《耶稣之死》是库切的“耶稣三部曲”(以下简称“三部曲”),讲述了忘记历史、姓名的西蒙和大卫移居到诺维拉,他们意外碰到伊内斯并选择让她成为大卫的母亲的故事。三人后因大卫的教育问题重新走上流亡的道路,到达了埃斯特雷拉社会。在经历了孤儿院生活和离奇的激情杀人案件之后,大卫患上了不可治愈的疾病而死去。国内外很多学者关注到了小说建构的乌托邦社会背景,但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一背景下移民呈现出的“精神悬空”状态。本文以尼采的消极虚无主义与积极虚无主义为理论依托,从家庭共同体和过往纽带的断裂以及信仰的虚空三方面分析“三部曲”中的“精神悬空”现象书写。
一、家庭共同体纽带的断裂
对人类来说,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家庭以爱为其基本规定,体现着自然的和谐。爱是精神对自身统一的感觉,这种感觉只能从他人身上找到;孤单的个人是残缺不全的,他要获得他人对自己的承认。”[1]但在“三部曲”的描述中,不管是主角一家建立的偶合家庭,还是在艾斯特雷拉建立的孤儿院,不仅表露出移民们的“精神悬空”状态,也体现了家庭提供精神支柱作用的失败。
“偶合家庭”一词最早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偶合家庭是现代资本主义都市家庭模式,呈现为一种虚伪的无根状态;它没有以家族公共价值为依托,更没有以古老信仰为依据。”[2]《耶稣的童年》中,库切直接建立了一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偶合家庭,西蒙意外找到伊内斯并选择让她成为大卫的母亲,双方未经肉体结合就组建了家庭。
这个偶合家庭的核心是大卫,成员之间并没有发自内心地认可彼此的身份。西蒙认为自己既不是大卫的父亲,也不是大卫的教父,他只是在帮助大卫寻找母亲,自己只是照看他的人,是暂时的监护人。西蒙在向别人介绍时极力否认大卫是他的儿子,他只是行使着父亲的职责,在没有更好的人选之前担当他的父亲。“他徒劳地试图描述自己与大卫的关系,却用了一连串不精确、疏远的词语:叔叔、父亲、男仆、帮手、教父、‘某种意义上的监护人。”[3]当蓬塔·阿雷纳斯的人想再一次把大卫带走之时,西蒙想要利用父亲这一角色争取大卫,但他也仅仅说自己可以说是大卫的父亲。伊内斯一开始对于抚养大卫就是犹豫的,她接受母亲这个身份是因为西蒙觉得孩子需要一个母亲,这样大卫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正常生活。伊内斯作为一个没有结婚的处女,并没有养育孩子的经验。虽然后来伊内斯声称自己是大卫的母亲,但是她并不认为自己和西蒙是夫妻关系。在伊内斯成为大卫的母亲之后,西蒙就搬出了原来的房子,还放弃了大卫。在大卫去孤儿院后,他们在家互相什么话也不说,没有任何共同的话题。在法律层面上,他们的关系也是不牢靠的。“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好说的:当然不是夫妻关系,也不是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伙伴可能是最接近的形容词汇:仿佛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劳动中,维持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纽带不是爱情,而是责任和习惯。”[4]而大卫也不承認西蒙和伊内斯是他的父亲和母亲:“我没有母亲,我也没有父亲,我就是我。”[5]他认为伊内斯不是母亲,只是一个女人。奥特莎太太认为,大卫在课堂上的不安分行为都源自他身份的模糊性,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尽管伊内斯爱他胜过爱这个世界,但由于亲生父母的缺位而造成的情感缺失和身份困惑是别人的善意和爱无法弥补的。《耶稣之死》中,大卫甚至想离开家住在拉斯马诺思孤儿院里。大卫是这个家庭的核心和纽带,伊内斯和西蒙是因为大卫才建立了联系,所以在大卫死后,伊内斯和西蒙就分道扬镳了。这种松散的家庭关系一方面不被法律承认,一方面也不被家庭成员自己所承认。这种家庭组合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并没有给成员提供坚实、温暖的归属感,身为难民来到陌生城市的他们仍旧遭受着身份困惑和精神支柱缺失的问题。尽管他们努力想要通过组建家庭来为孩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想要获得情感慰藉和安全感,但是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了。
这种精神纽带的断裂不仅体现在“三部曲”中主角的家庭模式身上,还体现在拉斯马诺思孤儿院的设立上。孤儿院总共只有不到两百个孩子,却请了很多老师来上课。孩子的年龄跨度很大,这里的管理者法布里坎特博士明明可以将这些孤儿送到公立学校,却选择经营一个孤儿院。作者并没有详细描述他们成为孤儿的原因,也许孤儿们和大卫一样,在迁移的途中和家里人走散了;另一种情况是孩子们并不是因为没有家人而成为孤儿,这里的“孤儿”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现实状况。大卫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孤儿,但是拉斯马诺思却不是一个真正的孤儿院。大卫的确失去了亲生父母,他死后,孤儿院被记录为他的居住地,孤儿院的院长是他的监护人,他的尸体的处置权掌握在法布里坎特博士手上,西蒙和伊内斯连看尸体的权利都没有,也不知道大卫埋葬的地方。但是这里的孤儿并不都像大卫一样,正如胡里奥博士所言:
成为孤儿意味着什么?它是否仅仅意味着你没有可见的父母?不,作为一个孤儿,在最深的层次上,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孤儿,因为在最深层次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孤独的。正如我对我负责的年轻人所说,生活在孤儿院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因为孤儿院是社会的一个缩影。[4]
孤儿院的设立为被清洗了记忆又尚没有完全融入新生活的异乡人提供了一个聚集地。他们没有获得自己与这个新世界的联系,心理的孤寂状态让自己就像没有根的浮萍。大卫来诺维拉时,脖子上挂着说明情况的信件,绳子断了,这封信就丢失了。大卫丧失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而又无法很好地把握当下,这让大卫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孤儿,孤儿院是适合自己的。所以他不顾西蒙和伊内斯的反对,想要住在孤儿院并为孤儿院的球队踢球。大卫一方面想要在这里寻求心灵的共鸣,一方面也想为自己和这些孤儿们寻求一个精神出路。身处孤儿院的孩子和大卫一样陷入了精神无所依托的境地。
二、过往纽带的断裂与信仰的虚无
每个来到诺维拉的人都被洗掉了过去的记忆,被赋予一个新名字,并被迫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记忆和过往的历史是人们了解自己的方式,但来到这个新国度的异乡人丧失了过去的历史,他们被抛掷在一个超越时空的国家,他们只能在这个地方努力学习西班牙语,努力把握当下,成为一个“新人”。
每个移民在来到诺维拉之前都要先在贝尔斯塔学习西班牙语。西蒙和大卫在贝尔斯塔上了六个星期的西班牙语课,而安置中心的安娜则待了三个月。西蒙刚到安置中心的时候为了咬字清晰,有意说得很慢,他学习西班牙语只是为了找个工作,还想找个住的地方。他们需要学习新的语言,需要努力工作才能融入这个新的环境。但是西蒙和大卫并不喜欢这门完全陌生的语言,西班牙语无法带给他们确切的归属感。西蒙向埃琳娜抱怨自己为什么要来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学习西班牙语,而这门语言并不是自己发自内心想说的语言。西班牙语的习得无法让西蒙和大卫找到熟悉的故土感觉,无法让他们明确自己的身份。尽管不喜欢,他们却无法拒绝学习西班牙语。如果不说西班牙语,自己就会生活在一个没有朋友的孤独世界里。为了在这个新国度生存并融入这里的生活,每个难民都必须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去学习这门语言。
“传统上,一位充分意义上的移民要遭受三重分裂:丧失他的地方、他进入一种陌生的语言、他发现自己处身于社会行为和准则与他自身不同甚至构成伤害的人群之中。而移民之所以重要,也见之于此,因为根、语言和社会规范一直都是界定何谓人类的三个最重要元素。”[6]丧失了母语的移民也丧失了原本的文化归属,出于沟通交流和适应环境的需要不得不接受新的语言模式,以语言为媒介去认识这个新的世界。
库切在“三部曲”中塑造的移民不仅忘记了语言,也忘记了过去的记忆和历史。失去了与过去联结的他们感受着不同形式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由旧信仰崩溃到新信仰建立的一种过渡状态。一方面,由于创造力尚不够强大,新信仰还建立不起来。另一方面,由于颓废仍在延续,尚未找到其救助手段,旧信仰仍发生着腐败作用。”[7]移民因为记忆和历史的缺失,其旧的价值体系全然崩塌,然而在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中,新的价值体系又尚未完全建立。一部分移民仍受制于以往记忆的模糊片段,在过去和当下的拉扯中感受着痛苦和纠结,另一部分移民虽然选择全然忘记过去,但是新生活的实践仍未提供根基稳定的精神支持。
第一类移民仍旧艰难地找寻自己与过去的联结。德米特里是埃斯特雷拉博物馆的总看管员,保卫着博物馆雕塑和绘画的安全。他喜欢在学校的门口等着,就是因为想看看那些年轻人,希望体验一下童年的快乐。他对于童年的记忆完全是空白的,这种忘却让他觉得悲哀。德米特里觉得自己就像一棵树,已经被生活的暴风雨连根拔起了。他会给舞蹈专校的孩子们准备糖果,享受跟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时光。德米特里想通过与孩子们的相处弥补自己失去的童年,并进一步找到自己的根基所在,但是完全空白的童年无法借由别人的经历去填补,童年的缺失所造成的空虚感一直伴随着德米特里。西蒙踏入了一个新的家园,但是还保留着对于过去的记忆和历史。西蒙没有摒弃过去的思维和情感方式,仿佛一个另类,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他不断地折腾和挣扎,模糊的记忆让西蒙无法判断其真实性。记忆的存在给西蒙的新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他为记忆而痛苦,困于记忆阴影之中的他在历史和当下之间来回拉扯。他迫切想要融入新环境,过去的记忆却成为他前进的障碍。西蒙觉得过去的记忆是一种负累,但是他仍旧不愿意失去那些记忆。他期待能从记忆的搜寻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但是一方面记忆的模糊性无法提供这一支持,另一方面新生活的体验也并没能让西蒙建立起新的认同感。西蒙和德米特里困在寻找过去记憶的痛苦之中而不能很好融入当下的生活。他们正如尼采所定义的消极虚无主义者一样,心中仍然怀有对信仰的热情和向往,竭力在记忆和历史中找寻往昔的荣光。但是他们既无力回到过去,又无法在现存的世界中凭借自我的力量建立起稳定的信仰,从而陷入了绝境。
第二类移民选择跟过去完全告别。当西蒙表达想要为大卫寻找母亲时,安娜却认为来到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兴趣找回过去的情感。她让大卫、西蒙和这里的人一样洗掉自己身上与过去联系的痕迹,跟过去告别。没有了过去情感的安娜更能接受这里的各种社会规范。这类移民不把自己困在过往的历史和记忆中,安然接受当下的新生活,接受自己是一个完全被清洗了记忆和历史的“新人”。表面看来安娜能够更好地接受新生活,但他们认为只有感官能感受到的是真实,其他都是人为编造的。他们融入新生活的代价是忘却观点、概念和历史所建构起来的真实,只生活在能触摸的生活本身。他们以实证主义的视角,向“事实”顶礼膜拜,实际上是在否认重建价值的必要性,这正是尼采所说的积极虚无主义。他们在抛弃记忆和历史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本应当激情洋溢、充满真实感和质感的生命本身。在历史和记忆中纠结的移民要么心存信仰而无法重建信仰,要么完全舍弃信仰而否认所有形而上学的意义,而这两种方式本质上都是陷入虚无主义的表现。
三、信仰的虚空
来到这个新世界的西蒙和大卫时时感觉到虚无。大卫来到诺维拉之时走路很慢,因为他总是犹犹豫豫地避开路面的缝隙,害怕掉入缝隙之中。他认为数字会从天空中掉下来,就像堂吉诃德掉进了缝隙,他对裂缝充满了焦虑。《耶稣的童年》第三章描述大卫是“悬在中间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卫失去了与父母的亲情纽带,另一方面大卫作为新移民还没有融入新环境,他的精神时时处于悬空状态。西蒙经常会感到晕眩,好像马上就要摔倒,一头栽到海里淹死,但是医生却说他的心脏还可以工作很多年,他一点事也没有,晕眩是一种心理问题,只要不向下看就好了。大卫和西蒙遇到的这些问题本质上都是害怕掉入虚无主义之中,害怕陷入一种精神无处依托的状态。西蒙往下看时就像是凝望着虚无的深渊,时刻觉得自己要掉下去了,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往上看,在确切的生活里找寻情感依托。但在这个新国度里,“移民主体处于一个矛盾的空间,介于一个无法居住的母国和一个临时的东道国之间,介于一个正在转化为记忆的前世和一个想象的未来之间”[8]。这个超越时空的临时世界无法给人足够的心理慰藉,大卫和西蒙时刻感到处于夹缝中的矛盾和痛苦,感到无所适从。
而这里的人似乎也并不需要信仰。西蒙认为安娜在安置中心工作是因为有信仰的力量支撑着,因为这个工作需要每天都接待络绎不绝而又一无所知的移民,但安娜觉得这跟信仰没有任何关系,安置中心的人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让一切都变得好起来就可以了,一切的成果都是可见的,不需要有信仰的参与。这个缺乏血性和激情的社会没有信仰力量的参与,人们只着眼于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如果说移民是他者,那么西蒙和大卫就是这个社会中他者的他者,他们的身份焦虑和“精神悬空”是显性的,这里缺乏现实生活的实在感,无法给移民提供足够的精神慰藉,这是一个缺乏激情与意义的平面世界。
四、结语
丧失了家庭共同体纽带、母语、记忆和历史的移民像是完全丧失了主体存在感和生存意义的“新人”,毫无预兆地被抛掷在“乌托邦”社会中。他们遭受着失去记忆和历史的痛苦,必须重新学习一门语言,必须接受新的社会规范,这一切都让他们感到矛盾和纠结。“小人物‘忍居于看似公平美好的乌托邦社会里,其实就是他们的不得不去适应的伦理”[9],这样的他们始终无法找寻到人生意义和最终归属。
参考文献
[1] 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许志强.《耶稣的童年》:新移民故事[J].书城,2013(4).
[3] Seshagiri U.The Boy of La Mancha:J. M. Coetzees The Childhood of Jesus[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2013(3).
[4] Coetzee J M.The Death of Jesus[M].London:Penguin Books,2020.
[5] Coetzee J M.The Childhood of Jesus[M].London:Penguin Books,2013.
[6] 拉什迪,黄灿然.论君特·格拉斯[J].世界文学,1998(2).
[7] 周国平.尼采与形而上学[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2年.
[8] Jacobs J U.A Bridging Fiction: The Migrant Subject in J.M. Coetzees The Childhood of Jesus[J].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2017(1).
[9] 胡忠青,蔡圣勤.倫理困境:《耶稣的童年》中乌托邦社会的表征[J].社会科学家,2015(9).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郑梦婷,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