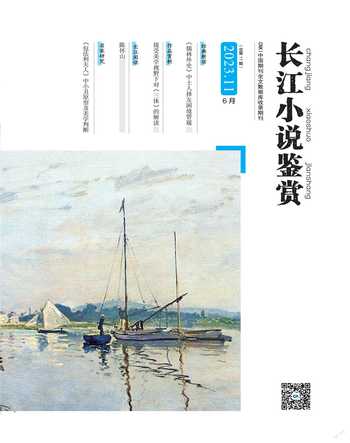斯捷潘诺娃《记忆记忆》中的“反记忆”主题
[摘 要] 斯捷潘诺娃通过家族先辈过往的遗迹追寻家族记忆,并将其对于记忆、历史与遗忘等主题的哲学思考融入小说《记忆记忆》中。作者最初希望能够“记忆所有人”,最终却因对过往记忆追寻失败而选择站在“反记忆”的立场去书写记忆。本文从记忆、历史与时空等角度对该作品进行解读:首先通过探讨记忆与历史书写、历史与遗忘之间的关系论证记忆之不可靠与记忆之不可追,进而从时空与记忆的关系角度对作者“反记忆”立场的叙事策略和思想内涵进行阐释。“反记忆”既是作者所选择的对过去的记忆方式,又作为一种认知方式引导读者思考该如何处理记忆与过去和当下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记忆 历史 遗忘 时间与空间 反记忆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11-0050-05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是俄罗斯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其2018年出版的富于哲思的小说《记忆记忆》包含了对记忆的追寻和思考。斯捷潘诺娃有犹太血统,她在十岁左右就开始构思要写作一部家族史,这部作品跨越了三十多年,最终将她对家族回忆碎片的整合及其哲学思考呈现出来。记忆是一个恒久的话题,尤其是对一个在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民族来说,对记忆的呈现和表达也体现出作家对待当下和未来的态度。斯捷潘诺娃自认为是“幸存者的后代”,她用追寻家族历史的方式对过去进行一种观照,表达了深刻的记忆主题。
《记忆记忆》有两条明显的线索:一条是作者通过对家族成员旧物的整理,将家族成员的过往一一呈现,在类似日记、照片、往来书信、博物馆的展品等具体的物质载体中,追寻家族的过去,并由此引发了一连串有关记忆的哲学思考;另一条是作者通过不断追寻家族历史遗迹,将家族的命运放到整个民族、国家的层面进行审视,探寻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个人记忆、家族记忆与历史记忆、时间等重要主题相联系,作为特殊历史的经历者的讲述也将成为那段历史的独特组成部分。因此,本文首先对记忆与历史、遗忘和时空之间的关系进行明晰,将记忆安置在一个适当的被讲述的场合,以进一步探讨记忆能否准确记录历史和過往,人们又该对记忆持何种立场,以及记忆与当下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一、记忆:何以留住历史
作为一种探究历史的途径,记忆借以各种载体被留存,从私人的旧物件、日记、书信、宅邸等到公共的博物馆、纪念碑、公墓、纪念馆……个人和集体的记忆通过各种形式保存,使后人了解某段历史。但如果仅通过这些载体去推测一段时期的历史,就有错误解读的可能——作为一种客观的实体,它们本身并不会主动讲述历史真实,而只能将自己展现在后来者眼前。海登·怀特认为:“人不可能去找到‘历史,因为那是业已逝去不可重现和复原的,而只能找到关于历史的叙述。”[1]
1.载体与诉求
关于《记忆记忆》一书的写作缘起,作者斯捷潘诺娃在中文版序中谈到,她在十岁或十一岁那年就开始在练习本上进行构思了,孩提时代的愿望是写出一部家族史,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这部家族史的书写自然而然也融入了俄罗斯的历史,作者自述追随家族先辈的行动轨迹,试图回到原点找寻早已消失在历史中的一百年前的族人的身影,将“记忆所有人”当作自己一生要完成的任务,她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形成有关记忆的思考并以富有哲思的随笔形式记述下来。
以“姑妈死了”这一令人震撼的短语作为开头,作者开始述说自己收集家族记忆的尝试:对家族成员留下的物件进行整理并试图从中还原家族的真实历史。首先是作为私人日记中的个人化、模糊不清的表述让作者不得不对姑妈过去的生活进行猜测和想象。除此之外,老照片、麻将牌、母亲的讲述等都像碎片一样时不时会出现在作者的记忆中,但这些零散的、虚虚实实的记忆并不能帮助作者还原清晰而真实的家族历史,于是她开始思考自己所要完成的到底是怎样一件事?搜集过去记忆的意义何在?随后斯捷潘诺娃意识到正是这些家族记忆的碎片组成了自己所构想的“纪念碑”——在朗西埃的使用中,它是“文件”的对立面:“就其初始意义而言,是以其存在本身维持记忆的,它虽然无法讲述,却可以直接宣告。……其对于人类事务的见证意义胜过任何编年史,它可以是日用品、碎布头、碗碟、墓志铭、箱子上的图画、两个人私下签署的秘密协定。”[2]它既非官方所讲述的历史,也不能通过拼凑而被完整还原,但它却包含了记忆的收集者、记录者对于记忆的构建和欲求。由此,作为历史载体的记忆碎片在这个层面上收获了它的功用和价值。
2.掩盖与重塑
记忆一旦被书写即被重新建构了,也就从一种客观的陈述转变为主观的想象和投射,偏转与歪曲发生在记忆被记录的那一刻,就像旧照片、一些书面文字的记述,如果照片中的那个人在面对镜头时有意迎合拍摄者的目光,如果书面文字为了某种原因而选择虚假讲述,那么这些旧物就不能真实地言说过去。
在《记忆记忆》中,作者摘录了作为英雄的姨外公(外祖父的姨弟)廖吉克在战争时期寄给他母亲的数封书信,但这些信上几乎都印有“已通过局势审查”字样,信中也无非是向家中报平安并且问候家中亲人的近况如何的内容,然而这并不是真实的情况。作者的父亲在参与秘密航天器的研发工作中给家人的书信“表现得完全像一位苏联电影里的主人公,一位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快乐青年”,但当作者询问父亲能否在她的书中引用这些信时,她的父亲竟然出乎意料地坚决反对。之后,作者明白了亲人信中呈现的内容并不完全真实,只是为了让亲人放心。由此可见,作为实存的旧物也并不能完全真实地讲述过去,作为个人记忆留存下来的书信必会受到当时时代环境的限制,受制于当时的集体性观念。
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强调了个人记忆的集体性和社会性:“事实上,如果人们不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也就无法对之进行思考。而一旦讲述了一些东西,也就意味着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所属圈子的观点联系了起来……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3]但从记忆留存的角度来看,只有将个人记忆定位于集体记忆之中才能更好地被理解和接受,记忆若仅仅作为一种个体性的存在,则极易迷失于历史中并且因其独特的记忆背景而被误解。当然,存在于集体之中的个体记忆也会保持其独特性,后来者若想要了解这些记忆,则需要沿着个体当时所处的路径,将自己置身于他们的历史定位之中去思考和体会。
记忆并不能等同于历史,它仅在某些方面为证实历史提供了一定支撑。家族记忆同个人记忆一样,从属于集体记忆,同样地为历史提供内容,并且作为家族内部的记忆,其成员也会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所流行的观念对其重新整合、讲述,由此,历史由一代又一代人书写和再讲述。总之,不管是历史中的书写者出于某些原因主动地选择隐藏真相而进行虚假的书写,还是事件在历经一代又一代的阐释中逐渐被歪曲,作者此刻得到的碎片化的记忆都不足以去还原过去的那段历史。
二、历史:在遗忘中书写
历史需要记忆和回忆的帮助才能被记录下来。亚里士多德将记忆视为对过去的保存,而回忆则是对过去的呼唤,并且相比记忆的时序不明,回忆更为有时序。他在对记忆与回忆区别的叙述中,已经让人可以隐隐察觉到另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遗忘。相较于对过去的保存,回忆是对已有记忆的再加工和有意识的记忆,因为人的记忆是有限的、时序不明的,甚至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会遗忘,所以需要回忆及时地将它按照一定的条理进行处理,以便在当下或未来的生活中能够留存并汲取过去的经验。不可忽视的是,遗忘总是在其中与记忆相生相伴,成为回忆和历史记录的天敌,如何理解遗忘、如何安置遗忘在历史中的位置,这将影响人们如何建立起与过去、当下以及未来的联系。
斯捷潘诺娃在追寻家族遗物和历史痕迹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一种叫作“小冰人夏绿蒂”的造价低廉的瓷娃娃,它们是贵重货物运输途中的“减震垫”,不论她在古玩市场、街头摊位看到的,还是网购的瓷娃娃,大都残缺不全,就连作者精心挑选的一个保存较为完整的瓷娃娃在最后也不小心被摔成了三瓣。
在作者看来,这个瓷娃娃就像是一个精妙的隐喻:“首先,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可以完好无损地流传下来,不是脚会受伤,就是脸会刮花;其次,空白和缺陷是生存的必然伴侣、隐秘发动机和加速装置;再次,只有伤痕将我们从批量产品变成独一无二的单品;最后,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瓷娃娃,20世纪集体灾难的批量产品,同时也是其survivor和被动受益人,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2]瓷娃娃就像是重大历史进程中无辜的大多数,他们的命运就像小冰人夏绿蒂一样,仅有少数可以成为那个保存完整的幸存者;同时,作为历史遗留物的瓷娃娃并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也隐喻了历史只能有限地留存下來,这其中必然经历了遗忘和丢失。“小男孩被摔成三瓣……原本他还好歹诠释了家族和自我历史的完整性,突然间却变成了一个讽喻。……而我,完全无法从他者过去的碎片中拼凑出自我,甚至不能将其据为己有。”[2]作者试图通过追寻家族成员的历史痕迹还原历史的尝试失败,也正是在这个不断追寻的过程中,她逐渐认识到,有些历史终究无法仅仅通过“幸存者”去还原,有些记忆的碎片已经被历史冲刷殆尽,遗忘不可避免。
在面对已然消逝的过去的时候,人们总渴望有一种超凡的记忆,可以将历史事无巨细地留存,于是在遗忘与丢失之下,拥有超凡的记忆力成为人们最为向往的事情。博尔赫斯的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丝》讲述了伊雷内奥·富内丝因偶然从一匹未被驯化的马上摔下造成瘫痪并且获得了超凡的记忆力的故事,自此凡是他所感知到的一切都不会被遗忘。在医学上,这种症状被称为超级自传性记忆症或超忆症(hyperthymesia),患者可以轻松回忆起过去的某一天中所发生的所有事情的细节。这种超强的记忆看似是一种令人羡慕的机能,但对患者自身来说却是一种无法承受之重负——没有遗忘的生活意味着他们要背负一天比一天沉重的过去。
正因如此,失去遗忘的能力对人类来说无疑是种巨大的痛苦,人类将无法摆脱过去的深渊,在这种意义上,人类也应该与遗忘本身和解。遗忘本就与记忆相生相伴,遗忘并不是对过去的背叛,其中留存的记忆让过去、当下和未来连接,这包含了对过去的释怀与和解,遗忘是一种更好的记忆,活在当下的人通过遗忘去记忆,记忆又通过有意识的筛选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三、时空:记忆的存在之所
斯捷潘诺娃在追寻家族记忆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最初想要“记忆所有人”的想法,而逐渐向记忆之不可靠和不可追妥协,最终选择将其放入时空中去保存,它们会通过各种物质载体使自身得到安放。就像作品中提及的艺术家约瑟夫·康奈尔的盒子——康奈尔创作的盒子全部镶有一层玻璃,仅能供人观看而不能被触摸,就像一个个博物馆中的小型陈列柜。
1.橱窗与时空
康奈尔的这些小小的盒子里承载着盒子主人所珍视的东西,“就像孩子用剪刀从绘本故事中剪下心爱的王子和白马”,他用各个精心挑选的物件共同构建成复杂而精密的结构,“在康奈尔手中,每一样物品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顺从,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彼此都是亲戚”[2]。对于他来说,这些盒子即是“相会的纪念碑”[2],可以产生他和作为艺术家的弟弟罗伯特·康奈尔交谈的空间,并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实现心愿和爱意。存在于社会文化生活之中的博物馆、纪念碑、纪念馆等具有承载记忆意义的场所亦是如此——历史中幸存的物件跨越时空最终被展现在现代人眼前,所历经的漫长时间被玻璃橱窗中的形象具象化。
“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4]在巴赫金“时空体”理论的相关叙述中,文学作品之中时间和空间不可分割,时间的展开必会在空间中进行,而空间则需要用时间来衡量并赋予内涵。在人类历史中,时空的关系亦是如此。透明陈列柜中的纪念品呈现为一种空间的形态而被拿来描述过去某个时段所发生的事件,此时断断续续的时间就穿插在空间之中,所诉说的历史也变为碎片式的历史。那么当时间在现下不可被追回时,就需要借助空间的呈现去挖掘其中的内容。
由此,作者选择将这些记忆一一陈列,像摆在橱窗的展示品一般,然后退后一步对它们进行审视。胡焕的《“橱窗小说”:斯捷潘诺娃小说〈记忆记忆〉的叙事艺术探索》一文中写道:“‘橱窗小说这一术语由俄罗斯学者奥莉加·亚历山德罗芙娜·格里莫娃在《玛·斯捷潘诺娃的‘浪漫曲〈记忆记忆〉打破叙事策略》一文中首次提出。”[5]格里莫娃将“橱窗小说”英译为“showcase-novel”,作者将与过去有关的物件一一陈列在透明橱窗中向读者展示,由于展示柜透明隔板的存在使得后来的观看者不得不后退一步,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行观看,而此时橱窗隔板的作用就像是布莱希特“间离法”中的“间离”,后来者因此与过去的历史保持了一种可以进行理性审视的距离,这也是作者选择将过去呈现给读者的方式,她希望读者以一种“看”的方式来认识这些来自过去的物件。
2.“看”与“反记忆”
“空间化”转换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于时间流逝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可抗的无力感,而“看”的动作则精准完成了空间化这个过程。“看”这一动词隐含着当下性,由存在于当下的人发出,它代表着一种对过去的凝视和观望,自身带有一种审视的距离,即在时间上与“过去”相对立,与记忆本身“相反”,或者说“看”本身就是一种“反记忆”的立场。
斯捷潘诺娃在书写家族历史的过程中发觉“历史无法言说,任何东西都无法保存”,于是选择将自己搜寻到的遗物、历史痕迹等实物通过“橱窗”的方式展示出来,让读者站在橱窗外隔着一层玻璃“看”,用“反记忆”的方式留存记忆。记忆作为一种基于个体的体验,呈现为一种破碎、零散、没有时序的状态,在片段与片段之间存在着的间隙足以让人产生新的联想空间和阐释空间,并且它作为一个有所选择、有所遗忘的机制,包含着主体的阐释和选择。而“看”站在记忆的反面,对事物进行客观的观察和审视,不干涉事物本身的样貌,但可以与之进行交互对话,这就是作者在叙述手法上体现出的“反记忆”立场。
在作者对待过去的态度以及作者对于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也能看到作者有意与历史的记忆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像书中说的:“没有人能回到过去”“忘却意味着开始存在”“冰人夏绿蒂,幸存者种族的代表,就像我的亲人——关于他们我所能讲述得越少,他们于我便越亲近。”[2]小冰人夏绿蒂的隐喻让斯捷潘诺娃认识到了历史中还存在着那些未能被保留下来的真实,作为探寻过去真相的后人只能试图用一种更为客观的观看者视角,才能更好地使这些遗留下来的物件自己发声,讲述真实的过去,这种对于过去的认知也未尝不是一种“反记忆”的模式。
四、当下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关系
记忆在形式上可以是主观的,但内容和最终被保存下来的方式却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掌控。斯捷潘诺娃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试图寻回家族的记忆,但最终因记忆之不可靠而选择放弃,最终她选择站在记忆的反面去“记忆”。通过对记忆主题的思考可以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如何记忆意味着选择怎样的认知方式去理解过去,而这样一种认知方式最终会指向人们对当下的生活采取怎样的态度。因此,对记忆的思考同时也帮助解决人们应当如何面对当下生活的问题。
在面对“我们是否有权决定应当保留还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而放弃某些记忆”这个问题时,斯捷潘诺娃认为,即使遗忘有时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可以让人们摆脱过去的伤痛而过好当下的生活,但遗忘和记忆都不该是主动选择而产生的结果,它应当以有机的方式消逝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人们不应该干预历史留下的苦难与伤痛,不应该选择一种视而不见或者有意躲避的态度,否则生活并不会因这种有意的遗忘而获得幸福。
那些在漫漫岁月中流逝的记忆,并不是真正地消失不见,而是以另一种不可见的形式延续了下去,就像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谈到的树和鸟的例子:“一棵树上落着一群鸟儿,把树砍了,鸟儿也就没了吗?不,树上的鸟儿没了,但它们在别处。同样,此一肉身,栖居过一些思想、情感和心绪,这肉身火化了,那思想、情感和心绪也就没了吗?不,他们在别处。倘人间的困苦从未消失,人间的消息从未减损,人间的爱愿从未放弃,他们就必定还在。”[6]记忆并不是绝对客观的,有时候看似被人们遗忘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但说不定它们会以其他的面貌融入历史的进程中,并且作为一种绵延不断的存在继续留存于现在和未来。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J].天津社会科学,1997(3).
[2] 斯捷潘诺娃.记忆记忆[M].李春雨,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
[3]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 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 胡焕.“橱窗小说”:斯捷潘诺娃小说《记忆记忆》的叙事艺术探索[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2(2).
[6] 史铁生.病隙碎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特约编辑 刘梦瑶)
作者简介:张茜,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學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