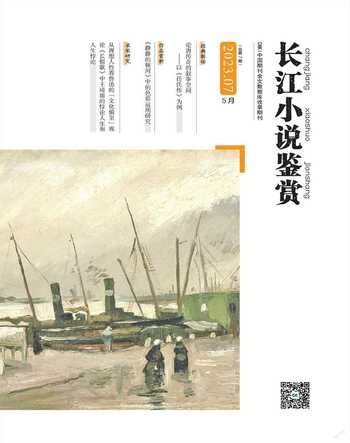石黑一雄《远山淡影》中的女性创伤叙事
刘瑞凤 齐雪艳
[摘 要] 《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创作最早的作品。这部作品以朦胧的笔触展现了现代社会普通人遭受创伤的内心世界。主人公悦子在经历战争后移居英国,又经历丧女之痛。本文结合创伤理论和女性身份,分析《远山淡影》中三位主要女性角色悦子、景子和藤原夫人的创伤原因以及创伤修复过程,这些女性在经历创伤后或走向毁灭,或重拾信心,勇往直前。通过探讨小说中女性经历创伤后的成长轨迹,人们可以了解二战后日本女性的生存状况,她们不同程度的反抗也给予那些仍被边缘化的女性鼓励与力量。
[关键词] 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 创伤 女性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07-0089-04
日裔英籍小说家石黑一雄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为“英国移民文学三雄”。石黑一雄的移民身份,使他擅长于书写战争文化与跨文化题材。不同于后两位小说家鲜明的后殖民主义色彩,石黑一雄的作品,常以模糊的笔触展现现代社会中普通人饱受创伤的内心世界,“创伤”是他作品中最鲜明的主题。关于《远山淡影》这部作品,国内有赖艳、梅丽、杨芳、张勇等学者展开研究,重心放在战争记忆、自我欺骗、离散文学、身份焦虑等方面。然而,关于《远山淡影》中女性创伤叙事的研究目前比较少,因此本文侧重于从创伤理论和女性形象的角度出发,分析文中三位女性主人公的创伤经历,并探究石黑一雄创伤书写的意义。
一、创伤的表现
1.战争创伤
创伤源自古希腊文,原义是“受伤”,指的是加之于肉体的伤害,弗洛伊德认为创伤不止在肉体,更是加之于心灵的难以愈合的伤害。创伤的呈现方式有很多种,如回避、噩梦、闪回、惊恐、解离和麻木等。石黑一雄在《远山淡影》中通过记忆闪回、主人公悦子与另一个自己“佐知子”内心对话的方式,塑造了这一历经沧桑的女性形象,描写女性成长的痛苦。
《远山淡影》中人物经历的实际时间是五天,而小说故事的时间跨度却有十几年,这主要来自悦子对战争的回忆。小说开头,悦子回忆道:“那时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个日子指的就是美国向长崎投射原子弹,带来灾难性毁灭的一天。悦子在战争中失去了她的未婚夫。在续方先生后来的描述中,他收留了悦子,悦子当时的表现像个疯子,甚至在半夜拉小提琴。这种类似“歇斯底里症”的表现,正是悦子深受战争创伤的证明。战争对悦子的情绪、认知和记忆都产生严重而长期的改变,从而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表现之一就是记忆闪回,即战争的伤痛始终挥之不去,即使早已时过境迁,受创者脑海里还是会不断浮现当时的场景。因此,悦子想逃离日本,但移居英国后却并未达到内心真正的平和,看似平静的内心下仍是灰暗的战争阴霾。
如果说悦子作为成人尚且被战争伤害得如此之深,那么年幼的景子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儿童是战争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战争中儿童的利益往往最容易被牺牲。五六岁的景子在战争时目睹了一个发疯的女人在水边溺死自己的孩子,从此,这一幕成为她的童年阴影,景子常常抱着喜爱的猫咪自言自语,一次次说着“对岸有个女人”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
因此,无论是悦子还是景子,她们都是战争这一集体创伤的受害者,都被这一集体创伤所裹挟。
2.家庭创伤
除了经历战争带来的创伤,《远山淡影》中的女性还在无形中经历了家庭创伤。悦子经历的是男权社会的思想压迫,特别是在恪守传统文化的日本更是如此,女性的地位很低,只能顺从丈夫的意志。悦子对丈夫二郎毕恭毕敬,即使怀孕也要事无巨细地侍奉丈夫和同事们吃晚饭。在探讨夫妻双方投票给不同政党之时,续方先生说道:“现在的妻子都忘了对家庭的忠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选举被看成是男性的特权,女性被剥夺了发表观点的权利。这种要求女子全盘服从丈夫、服从家庭的观念对女性的身心都产生了很大的压抑,所以悦子第一段婚姻并不幸福。悦子的第二任丈夫也并未真正理解她,他和其他人一样,认为日本这个民族好像无须多解释,就是天生爱自杀。这种“不理解”甚至是诋毁的观念体现了双方地位的不对等。
法国作家露西·伊利格瑞认为女性在长期的父权制体系压迫下会变得心理扭曲。二郎对悦子颐指气使的态度足以印证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伤害——“我希望你别老乱动我的领带。你在干什么呢?要知道我可没有一早上的时间。”怀孕的悦子对丈夫的指示言听计从,从未觉得有何不妥,甚至自我欺骗现在有了宝宝是最好的时机,丈夫有稳定的工作,自己很幸福。
不同于悦子的家庭创伤来自丈夫,景子的创伤主要来自父母的缺席。儿童时期遭遇的持续性创伤,会扭曲其尚未成型的性格,使其朝着不正常的方向发展[1]。危险发生时,儿童会向父母或兄弟姐妹寻求帮助。然而纵观景子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景子从未和家人成功建立起亲密关系。父亲角色丧失,而母亲一直热衷于与新的男友弗兰克交往,对小景子的内心世界缺乏关注。景子常常自言自语“河对面有个女人”,作为母亲的悦子不仅没有积极地帮助女儿摆脱阴影,反而把它看成景子发难时的小把戏。悦子甚至间接杀掉了景子最爱的小猫,只因为带着它搬家是个累赘。她从未真正走进景子的内心,作为母亲,她的角色实际上是缺位的。在悦子长时间的“放养”下,景子的内心创伤愈发严重,最后走上自杀的不归路。
3.身份焦虑
作为移民作家,石黑一雄小说中的主人公或多或少都存在身份焦虑问题,身份焦虑带来的孤独感和疏离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物的创伤。“身份问题”这一概念始于埃里克森,埃里克森注意到:身份问题是个体的社会归属问题。当个人能够取得所处社會的认同时,则可以建构身份,反之会产生身份焦虑。《远山淡影》中悦子借助回忆得以重新思考自己与女儿的身份问题。
悦子经历了两次移民,第一次是从中川搬到长崎,之所以“国内移民”,是因为和表姐安子闹了矛盾,她认为祖父家是一个有无数空房间的坟墓。悦子的“新家”是一所在战争炮火和政府推土机中幸存下来的小木屋,在这里悦子没有身份认同感,周围的女人对她议论纷纷。这种被孤立、被抛弃的感觉促成了悦子的身份焦虑。第二次移民是从日本到英国,与第一次移民不同,这一次体现的是东西两种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由于文化隔膜与冲突,移民不同程度地体会到一种文化和心理层面的身份焦虑。悦子移居英国后寡居乡村,过着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悦子并未加入任何组织,唯一能成为她和日本文化纽带的只有景子。景子的死切断了悦子与日本的所有联系,悦子回忆景子的过去也是对自己移民选择的反思。
悦子从未真正融入这个国家,她寡居乡村是因为她认为这是最像英国的地方,这个“像”证明悦子实际上并不理解英国文化,因此更谈不上融入。因此,作为纯日本血统的悦子,一方面经历丧女之痛后失去了与母国的唯一纽带,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融入当地文化。当初那个对异国满怀期待,期盼在新的地方大展身手的悦子终究还是陷入了新的身份焦虑。
二、创伤的修复
1.重演创伤故事
创伤性事件发生后,该事件会持续在受创者的大脑中重复上演。因为创伤事件的发生,人脑的保护机制被全面摧毁,受创主体为了理解当时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所引发的恐惧、忧虑等情绪,只能不断在大脑中重复上演受创的瞬间,这种主观意义上的不断重演也被认为是创伤的一种形式。
《远山淡影》中,叙述者悦子在回忆往昔和讲述故事时,总能被读者抓到把柄,她叙述的是一个当下的故事,即长女景子死后,自己在英国的生活。然而回忆的内容却是“我”在日本期间和万里子母女之间的交往,读者读到的故事是悦子把自己和景子的生活经历转嫁到虚构出来的万里子母女身上。景子的死一直萦绕在悦子心中挥之不去,但是悦子在女儿妮基拜访之后,提及秋千上的小女孩,才开始讲述过去的故事。悦子的叙述一直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跳跃。在回忆万里子母女时,她的回忆是片段式的,悦子本人也无法确定记忆的真实性:“可能一个人都没有,我不记得了。”悦子的回忆充满矛盾和空白。这种不确定的回忆一方面是由于时间的流逝,另一方面是她的情感选择,她不愿意承认内心真实的创伤,因此只能以含糊其词的语言重建过去的创伤故事。石黑一雄说:“我喜欢回忆,是因为回忆是我们审视自己生活的过滤器。回忆模糊不清,就给自我欺骗提供了机会。”石黑一雄关注的不是创伤记忆真实与否,而是人们复杂的内心世界。
小说中作为旁观者的悦子比母亲佐知子更爱万里子,佐知子是一个对女儿缺乏关爱的形象。当万里子和佐知子因为移民问题争吵时,佐知子对女儿说:“如果你不喜欢,我们会回来的。”这暗示了悦子对自己不计后果地把景子带到英国而感到后悔,她是在和过去的自己对话:如果当初没有离开,景子是不是就不会自杀了?景子在房间里上吊的画面一直出现在悦子的脑海里——恐怖程度从未减弱,但是她早就不觉得这是什么病态的事了,就像人身上的伤口,久而久之就会熟悉最痛的部分。库尔切写道:“创伤记忆是毁灭性的经历中无法被同化的碎片。”悦子对过往沉重事件的叙述是碎片化的,语气是冷静的,在回顾过去整理前因后果的过程中,从前的悲痛再度涌来,这有助于受创者宣泄压抑已久的情绪,往事得以梳理,自我得到解脱。
2.重建联系感
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是创伤修复的基础,也是受创者必须经历的过程。萨默菲尔德提出,受害者需要外界认可他们的创伤,因此关键不在于重返创伤记忆,而是在于重建文化身份。石黑一雄也提出当事者面对和接受创伤过去,是完成创伤修复的重要途径。
《远山淡影》中藤原夫人尽管和悦子一样经历了战争,失去了家人,但她积极地与周围环境建立联系,是唯一一个唤醒女性意识,实现经济独立的女性。通过做面馆生意,藤原夫人慢慢走出创伤。她的丈夫曾经是长崎的重要人物。炸弹掉下来的时候,除了大儿子以外,其他家人都死了。经历了如此之大的打击,她还一直在坚持。面馆生意使得她不再像战前一样,成为丈夫的附庸,而是勇敢地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与社会建立新的联系。相似的创伤会产生群体认同。同样经历战争创伤的悦子在与藤原夫人的对话中汲取力量,获得了继续向前的勇气,“每次我看见她,都对自己说:我应该像她那样往前看。”藤原夫人帮助别人的过程,是她寻求和肯定自我的过程,也是她传播独立价值观的过程。
创伤性事件破坏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而群体团结则是减轻创伤伤害的最好方法。创伤的复原只可能发生在受创者与他人交流的情况下,不可能在隔绝中独自完成。《远山淡影》中悦子与大女儿景子并没有建立亲密的家庭关系,悦子对景子的心理需求常常放任不管,所以景子的自杀使得她明白自己作为母亲是失败和自私的。她开始对二女儿妮基温和尊重,与二女儿沟通,理解她的生活方式,对女儿的需求尽量满足,建立起一段正常的母女关系。
当受创主体在经历叙述创伤、重建社会关系后,便实现与自己和解,在新世界中重生。悦子在小说结尾处坦然承认:“如今的我无限追悔以前对景子的态度。我一开始就知道她在这里不会幸福的。可我还是决定把她带来。‘前些日子我突然想到,也许现在我该把房子卖了。”悦子不再选择继续住在这里,沉溺在景子死去的悲伤情绪中,而是坦然地面向新的生活。
三、创伤的价值与意义
1.抚慰创伤
20世纪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战争、疾病等威胁着人类社会,创伤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广度影响着人的生存。文学由于自身的再现功能,为创伤书写提供了广阔的土壤。作为移民作家的石黑一雄更加能体会现代化语境下的各种创伤,他和另外两位移民作家奈保尔、拉什迪不同,他们的作品关注的重心是后殖民的种族创伤,而石黑一雄追求的是一种国际化写作,他关注的是战争对全人类的伤害,是以人道主义的关怀视角无差别地再现战争给双方带来的伤害。即使是发动战争的日本,平民也经受摧残,无论是妇女、儿童,还是成年男子,都或多或少地遭遇不幸。石黑一雄在撫慰创伤的同时也呈现了生命存在的意义。
对石黑一雄来说,创作从来都不是宣泄愤怒或狂躁的手段,而是用来纾解忧愁的,“现实世界并不完美,但作家能够通过创造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与现实抗衡,或者找到与之妥协的办法”。生活中的每个人都会遭受创伤影响,我们要敢于直面伤痛,积极地寻找自我慰藉,从而找到生命的意义。
2.探索战胜创伤新途径
关于如何治愈创伤,一些学者已经给出了答案。朱迪斯·赫尔曼在《创伤与复原》中提出创伤的复原阶段包括:恢复自主权、建立安全环境、回顾与哀悼、重建联系感等。如果说朱迪斯·赫尔曼从理论角度指出了修复创伤的方法,那么作为小说家的石黑一雄则通过作品中主人公的具体事例,给予心灵受创者摆脱创伤记忆进而抚慰心灵的新渠道。
在石黑一雄的小说中,人物经过努力,几乎都走出了创伤。治疗创伤的第一种途径就是帮助心灵受创者与外部世界积极地建立联系,《远山淡影》中,悦子通过与同样经历战争的藤原太太相处,被她积极乐观的心态所打动,进而勇敢地走向新生活。藤原太太战后重拾信心,以开小面馆为生,实现了经济独立,与战后社会重新建立联系。打破自我隔离,重建人际关系是进行创伤复原的重要途径,通过倾诉、交谈,把内心的创伤情绪发泄出来,最后直面新的生活。石黑一雄小说中创伤书写的意义,在于不仅表现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无差别伤害,并且给予人类治疗创伤的新途径。
四、結语
《远山淡影》是石黑一雄创作最早的一部小说。小说再现了悦子、藤原夫人、景子等女性经历战争创伤、家庭创伤、身份焦虑后,或走向毁灭,或重拾信心的故事。悦子借“佐知子”的故事把自己的过去与现在相联结,重建创伤故事,并与藤原太太积极交流,重新建立人际关系。悦子一改景子死后消极郁闷的情绪,转为设身处地为二女儿妮基考虑,最终走出创伤,直面新的人生。石黑一雄的小说无差别地再现了战争给全人类带来的伤害,抚慰创伤心灵,引导世人反思生命的意义,并给予世人走出创伤的新途径,即直面创伤,积极地与他人建立联系,实现经济独立。
参考文献
[1] 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杨大和,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
[2]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M].张晓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 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4] 周颖.创伤视角下的石黑一雄小说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4.
[5] 王伟.论石黑一雄小说的创伤叙事[D].西安:西北大学,2017.
[6] 王飞.石黑一雄《远山淡影》中的身份焦虑[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3(6).
[7] 陈莹.战争创伤·帝国挽歌·记忆母题——论石黑一雄对战后失序的道德思考[J].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8(1).
[8] 王娅姝.隐微、间性与世界主义——石黑一雄创作分析[J].文艺争鸣,2020(2).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刘瑞凤,伊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齐雪艳,文学博士,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