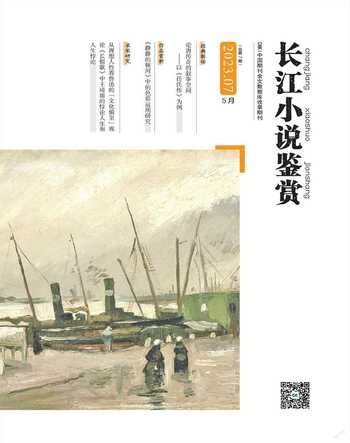唐·德里罗小说《零K》中的语言哲思
[摘 要] 在《零K》这部科幻性质的长篇小说中,唐·德里罗对语言的哲学沉思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将语言的危机作为技术滥用、媒体入侵的主体性身份困境的表征;另一方面,作品中的语言、命名之法又成为主人公重新把握自我的希望。唐·德里罗在对现代科技发展与人的主体性思索中,灌注了对语言本身问题的探讨。
[关键词] 唐·德里罗 《零K》 语言 主体性 科幻小说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07-0044-05
一、引言
如卡桑德拉·尼尔森所言,“怎样形容德里罗小说中命名的力量以及语言在协助个体形成意识和良知方面的能力都不为过”[1],对语言的关注一直是德里罗写作的一个核心。从写作生涯初期德里罗就非常关注语言问题,“我开始觉得语言既是我写作的工具,也是我写作的主题。”[2]此后他也多次在创作实践中表明语言的重要性。无论是《名字》还是《人体艺术家》,再到新作《零K》,可以说,对语言的思考一直贯穿在德里罗的创作之中,《零K》就是一部将语言的哲思放置于现代科技、媒体与生命主体性反思中的科幻小说。
小说故事发生在一个科技与生物技术极速发展的世界中,人们试图通过人体冷冻这一技术来获取永生。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罗斯是一位亿万富翁,他的第二任妻子阿提斯(Artis)是一位优雅、刚强、年轻但身患绝症的考古学家。罗斯为病入膏肓的阿提斯打造了一个叫作“聚合”的人体冷冻中心。罗斯带领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杰弗瑞来到人体冷冻中心,与即将进入冷冻状态的阿提斯道别,并试图劝说杰弗瑞接受人体冷冻,同他们一起进入永生的世界。作为《零K》的叙述者,杰弗瑞先后两次来到人体冷冻基地,在见证了继母与父亲接受人体冷冻实验之后,他独自回到纽约。全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中间有间隔,呈现一种对称的结构。第一部分讲述杰弗瑞应父亲罗斯的要求来到人体冷冻基地,与即将进入冷冻状态的继母阿提斯告别;第二部分讲述杰弗瑞在继母接受人体冷冻之后的生活,以及他的父亲最终决定接受人体冷冻。中间的间隔部分是对阿提斯处于人体冷冻状态时身体与意识分离状态的碎片式描述。
小说不仅表达了德里罗对技术和媒体滥用可能导致的后果的忧虑,还体现了他一贯的创作主题和哲思——语言就是本质。本文首先对人体冷冻技术之下的人的主体性危机进行分析,而后进一步探讨德里罗开出的将语言作为人类重新把握自我的药方。
二、超人类主义与身份困境
当人类生命与技术发展缠绕在一起,死亡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恐惧和负担已经变成不能承受的事情。超人类主义认为,人类可以充分利用科技力量,从社会、物质和精神上进行自我完善和提高。《超人类主义宣言》的第一条就宣称:“人类在未来将受到科技的深刻影响。我们正在考虑拓宽人类潜能的可能性,克服老化、认知缺陷、不自愿的痛苦和我们孤立于地球上的命运。”[3]科技进步,人类就拥有诸多延长寿命的可能,如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低温冷藏技术等均可以克服生物肉体脆弱易损的局限性。人类的思维意识也可以被提取备份,即使人造身体被摧毁,人类的思维意识也能够得以永远存续,不会消亡。
如小说的书名《零K》(Zero K)所示,人体冷冻技术作为永生的重要手段是小说主要的叙述内容。K氏零度是被称为“绝对零度”的温度,即零下273.15摄氏度,一些还没有达到正常死亡年龄的人将在这一温度下进行大脑或者是整个身体的冷冻,等待着百年后甚至千年后的苏醒。在小说中,这项永生技术的拥护者和参与者们坚信,只要自己的大脑可以被冷冻保存,在适当的时候科学家就能够重新解冻人体,唤起他们的生命和健康活力,那么永生的愿望就能够得以实现。
然而,实现永生的愿望并非超人类主义者想象的那样简单,人类身份的某些特性无疑会在这一冷冻永生的过程中丧失。从词源意义上来讲,“身份”( identity )一词,既是关于“本体、身份”的自我认知,也是关于“同一性、一致性”的对与自己有相同性、一致性的他人或社会的认知。因而身份认同就是“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4]。也就是说,身份认同意味着主体的意识与身体密切联结,并且主体不是孤立地站在他人与世界的对立面的。首先,建构主体自我身份强调自我意识和身体的统一体验,当肉体与意识的联结部分或完全丧失时,主体的身份也就瓦解了。在为实现永生而采取的冷冻技术的参与下,人的意识与肉身分离,人完全意识化时,人的物质身份和精神身份的内在联结和统一性就被破坏了。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小说借人物之口所说的:“什么是自我?你是自己的一切,没有他人……但是没有了他者,你还是那个你吗?”[5]小说的第二部分描写阿提斯进入冷冻状态后身体与意识分离,仅能依靠意识来获取身份的艰难处境。进入冷冻仓后,丧失了身体感知的阿提斯被囚禁在纯粹意识中,她的身份则成为没有凭借的悬浮之物。在只有抽象封闭的意识,没有具体的、物质的身体感知的情况下,她完全丧失了对世界和自我的把握。冷冻之前的那个生活在真实具体时空中的阿提斯,与现在身体与意识分离后,在意识的声音中不断重复的自我难以相合。她的意识不停地思索现在的自己是否还是曾经的自己,在这样的不断追问里,阿提斯陷入无穷无尽的自我纠缠中。
一方面是技術入侵造成人的主体性迷失;另一面,在封闭隔绝的人体冷冻基地“聚合”中媒体拟像世界的覆盖,也让人在真实与虚拟的世界中丧失获得本真生命体验的能力。小说中的人物对于永生的信仰,不仅来自人类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恐惧,更因为媒体影像的塑造。
小说中的金融巨擘罗斯建立在中亚沙漠地区的人体冷冻技术的秘密基地通过洪灾、火灾、飓风的灾难影像来煽动富人用巨额财富换取永生。基地中无处不在的灾难影像,无声地循环展示着人类死亡的种种恐怖场景,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焦虑在技术媒体影像的笼罩之下被无限放大。利用影像散播死亡恐惧,人体冷冻技术的功效也被放大,因此,依靠技术消除死亡恐惧就变得合理且迫切。在这种技术和媒体影像对人类心理的入侵下,生命与死亡被异化成可以消费的影像,人类的生命价值和对生活最本真的追求在恐惧营销催生出的虚假的消费欲望中渐渐丢失。此外,主人公杰弗瑞自小生活在单亲家庭,与母亲相依为命,也只能通过电视机和杂志等媒体塑造的模糊形象了解父亲,家庭亲缘关系也要通过媒体再现确认,这无疑加剧了主人公确认自我存在的困惑。
三、语言危机
小说并未止步于困境的表面描述,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场因为技术滥用、媒体入侵带来的生活虚拟化、具身感缺失、意识麻木、身份危机等灾难,在小说中都是通过语言来表征的。在人类丧失对自身的把握的时候,语言的枯竭首当其冲。自笛卡尔以来,在传统的身体和意识的二元论中,身体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而语言形同理性、知识,总是与意识联系在一起,语言与身体的关系正如意识与身体:身体不过是有缺陷可丢弃的皮囊,意识才是永垂不朽的存在。但事实上,语言的形成包含着自我对自身和宇宙万物及其关系的认识,人类是从自身出发去把握自我与世界关系的,人类以自我存在去标定宇宙万物的属性和位置,由此形成了关于语言的符号和隐喻。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性语言观、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观以及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观点都足以表明,语言的意义与说话者的生存状况和互动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就是身体与世界的关系。如果离开了言说的主体,词语就没有独立的意义。“身体是自然表达的能力”[6]的观点在语言层面上打破了以往在语言哲学界处于主导地位的身心二元论,将身体在语言中的地位凸显出来。语言对人类身份的主体性构建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一旦人的身份认同陷入困境,语言也走入没落的边缘。
小说中的人体冷冻中心“ 聚合”处于远离人类文明社会的荒无人烟的沙漠之中,是一个由高科技在现实沙漠中打造的非自然的封闭空间,这个空间需要特殊的许可和操作才能进入,首先就将进入者与周围世界和他者隔绝,而进入内部的人即将走入的是自身身体与意识的分离隔绝。主人公杰弗瑞进入“聚合” 之后,其内部房间低矮逼仄,房间没有窗户,并且所有的门均是闭合堵塞状态,在这样一个闭合排他的空间中,杰弗瑞没有任何向外探索和沟通的渠道,眼里看到的是末日影像,感受到的是虚构的恐惧,他试着推开看到的门,但是没有一扇门能打开。作为文学空间和建筑空间中的重要书写元素,门是交流与沟通的隐喻。杰弗瑞想推开“聚合”中心的门,其实是试图走出被技术异化的圈子,以及渴望与真实具体的人交流接触,但所有的门都无法打开,杰弗瑞被关在房间里,就暗示着语言的沟通交流功能在此处失效了。因此,在进入“聚合”之后,杰弗瑞失去方向,内心充满迷茫和恐惧。
小说的中间间隔部分,描绘了处于冷冻状态中的阿提斯对生命与死亡、意识与自我的怀疑。这一部分是由阿提斯的意识流独白话语构成的,呈现语言混乱的状态。阿提斯的意识在逻辑上断裂,语言形式漏洞百出,时态的倒置、语法错误、陈述句与疑问句不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混用,以及破碎的、不连续的、不确定的片段式的语句,都表明“她能说出她的感受,但同时处于感受之外”[5]。尤其是其中第一人称“我”与第三人称“她”的混乱使用,说明阿提斯在失去身体之后,本身处于撕裂状态,处于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原来的自己的精神分裂式的转换当中。值得注意的是,此处阿提斯的意识呈现混乱状况并不是德里罗在刻意使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或者说此处的写作重点不是意识如何流动,而是原本就流动变幻的意识在失去身体之后变得破碎。这种破碎的状态又是通过阿提斯意识里的语言来呈现的,小说的目的是想用语言破碎、枯竭的危机来呈现在人体冷冻技术介入之后,阿提斯对自己的身份难以确认的状况。也就是说,人物单靠意识难以捕捉语言并确认自身存在。语言以及语言所包含的逻辑有序性是人本身的完整有序性的重要来源,拥有了语言,我们人类才能够保持秩序,拒绝混乱。而阿提斯丧失身体只剩下意识之后混乱语言的呈现,正好说明其丧失了人的主体性面貌。
与永生世界相应,参与人体冷冻技术的人苏醒之后将使用新的语言进行交流。小说从一开始就预设了一种新语言系统的存在,新的语言系统“能表达出现在所不能表达的,能见现在所不能看见的,在统一中看我们自身和其他人,每一种可能性都得以拓展”[5]。可见,这一新的语言系统是开启永生新世界的希望,人体冷冻技术的拥趸都相信“我们有自己的语言可以指引我们走出恐怖的时代。对于脑海中想象的未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思考并表达出来”[5]。在这里,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不再依靠时间的沉淀、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演变、人类约定俗成的经验,而是完全沦为技术的产物,现代技术对语言的入侵和控制由此体现。正如19世纪德国哲学家、语言学家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中所呈现的,语言的差异永远不只是声音和符号的差异,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差异[7],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就是不同的世界观。经历人体冷冻之后的人不再用传统意义上的语言系统来解构感觉、梳理思想、表称事物,而是依靠技术植入,那么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到底是人类还是技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就是人类自身主体性危机的显现。小说中无论是语言的破碎还是新语言系统的设置,传达的都是人类难以把握自我的现实,其中也灌注着德里罗的这样一种哲思,即现实是由语言建构的。
四、自我探寻与语言的力量
在德里罗的大多数小说中,艺术都发挥着解救的作用,体现艺术救赎现实的信念。在《零K》中,德里罗把对抗的力量放置于语言之上。
如前所述,身体、语言和意义的關系密不可分。小说的第二部分,叙述杰弗里的继母进入冷冻状态之后混乱意识的呈现。在阿提斯失去具身后,也只有语言才能将她的意识和她的存在表达出来,“她知道这些词。她就是这些词,但她不知道如何从这些词中跳出来,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一个知道这些词的人。”[5]在德里罗看来,语言就是意义,语言是我们最终的救赎之物[8]。小说中阿提斯(Artis)名字的隐喻不言自明——艺术。阿提斯的身份是位考古学家,挖掘历史把藏于地底之下的秘密传递给当下和未来就是她的工作,她是“时间的对手和回忆的高手”[5]。可以说,阿提斯是连接过去历史与现在和未来的使者。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杰弗瑞最后一次来到人体冷冻基地时,看到了在冷冻仓中的阿提斯。在杰弗瑞眼中,“她的身体在冷冻舱内容光焕发,她身体的站姿与其他在冷冻仓中的身体站姿不同。”[5]小说结尾,阿提斯正是通过自己的身体,通过语言和艺术而非人体冷冻技术向死而生。可以说,阿提斯的隐喻就是语言证明了艺术的存在,语言和艺术才是超越任何技术永生不朽的存在。
另一方面,小说的叙述者杰弗瑞在媒体带来的幻象和陌生的父亲提供的财产以及永生的诱惑中,也在个人身份迷失的边缘挣扎。但是在迷失与挣扎的过程中,杰弗瑞通过词语和命名建立与世界的真实联系,回归身体体验,重建个人身份。小说中,杰弗瑞对为人命名、给事物下定义有着浓烈的兴趣,“定义人,我告诉自己。定义人类,定义动物。”[5]在技术和媒介侵袭的混乱世界中理解周遭环境、认识自我,杰弗瑞依靠的是语言。在基地面对种种神秘的无法理解的事物时,他说,“这是我在自然奇观面前保卫自我会做的事情:想一个词语。”语言不仅是杰弗瑞保卫自我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他与世界建立真实具体联系的手段。通过对“聚合”基地工作人员的命名、对陌生的地点的命名以及对语词的定义,杰弗瑞或多或少获得一定的主动权和确认感。小说中杰弗瑞对语言的痴迷可以追溯到儿童时期父母争吵时,杰弗瑞听到父亲曾说母亲是“fishwife”。为了知道这个词的意义,杰弗瑞反复翻阅字典,却发现每查一个生词时,字典的解释便会引出更多的新词,字典对词语的解释和定义使他陷入一个没有穷尽的意义指向。从那以后,杰弗瑞开始尝试放弃字典,用自己的感受定义世界,“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尝试着给物件或者概念的相关词语进行定义。定义忠诚,定义真理。”[5]在定义词语的过程中,杰弗瑞实际上是为自己组织了一场德里达式的延异游戏。德里达根据法语“延迟”和“差异”自创了“延异”这一术语。他认为语言和意义之间不是固定的合一的,而是永远处在不断被延缓的状态下,意义不可能自我完成,词语总是要互相依赖才能确定意义。所以德里达在《哲学的边缘》一书中说,“差异意味着只有存在确定的词语才会形成差异,然而,在语言内部,只有延异存在,没有确定的词语。”[9]在杰弗瑞试图把握词语和定义的过程中,一个定义滑向另一个定义,一个词语滑向另一个词语,意义不断被延缓也不断与其他意义相关联,意义没有固定指向的终点,而是在他不断寻找、不断发现的语言链条中若隐若现。也就是在意义的追寻过程中,杰弗瑞重新进入真实的世界,以自我感受来编织能指与所指的不断延宕的游戏,为语言和世界打上自身的烙印。
语言加深了杰弗瑞对现实的理解,在定义和命名的过程中,杰弗瑞更加坚定地把握生命价值和日常生活的真实确定性,语言使他能够维持自我认知,保持理智、感受力和洞察力。如詹姆逊所言,“我们具有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的能力才能被命名和概念化。”[10]杰弗瑞对事物的定义和命名使他用自己的真实感受来理解事物。以自我感受为中心,他可以在自己的坐标中标定其他人物的位置,以此来编织自己与周围人和周围世界的联系。命名的本质是语言的使用,通过对语言的把握,杰弗瑞对生活形成掌控,在这张由他的具体真实的感受建立起来的坐标网中,杰弗瑞得以真切地感受自己的存在,维持自己的主体性。
五、结语
近年来,科幻题材越来越多地呈现在世界严肃文学作家的书写中,作为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唐·德里罗的新作《零K》既延续了其一贯的创作主题又有对新的技术时代的沉思。通过《零K》,我们可以看到德里罗的语言哲思,即语言不是认识论的工具,而是存在自身。正如在小说结尾,杰弗瑞乘坐公交车回到纽约,看到了日落,当车上的智障孩子因为这一落日景象惊讶得哭叫时,杰弗瑞感叹:“我回到了座位上,面朝前。我不需要天堂的光。我拥有这个孩子看到奇观发出的哀嚎。”[5]至此,哪怕人类的语言最后变成了一声哀嚎,语言的力量也被推到了极限,因为语言是对现实的真实感知,拥有语言,就拥有了把握自身和现实的能力。在德里罗看来,在技术饱和媒体轰炸的时代,人的主体性有被弱化的危险,但语言艺术的力量始终不可忽视,因为语言就是存在自身,只有在语言之中才有救赎的希望。
参考文献
[1] Nelson C. Quotidian Wonder[J]. First Things,A Monthly Journal of Religion & Public Life, 2016(266).
[2] LeClair T,DeLillo D. An Interview with Don DeLillo[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82,23(1).
[3] 呂克.费希.超人类革命[M].周行,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4]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2).
[5] 唐·德里罗.零K [M].靖振忠,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6]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杨大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7] 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8] 周敏.语言何为——从《名字》看德里罗的语言观[J].外国语,2014(5).
[9] Derrida J. Margins of Philosophy[M].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10] 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 [M].吴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特约编辑 张 帆)
作者简介:詹宁静,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