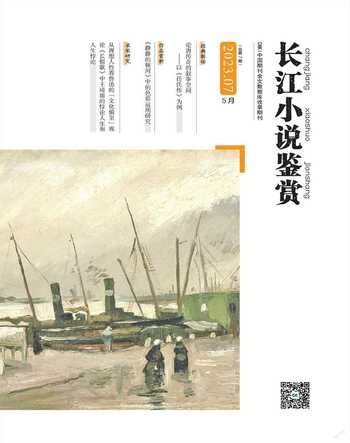以维特根斯坦“不可说”理论解读《都柏林人》
[摘 要]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首次提出了“不可说”理论:逻辑形式、哲学问题、伦理学、美学、神秘主义等都属于不可说的范畴,只有通过有形的具体事物才能获知这些东西存在的意义。与之相似,欧洲现代小说家在创作时,常通过语言描写“可说”的事物,从而传达事物所蕴含的“不可说”内涵。乔伊斯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把意味丰富的词汇进行艺术性结合,从而赋予作品深刻的象征涵义。乔伊斯的创作手法与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相契合。
[关键词] 维特根斯坦 乔伊斯 “不可说” 《都柏林人》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07-0025-04
一、何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20世纪著名哲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逻辑哲学论》是维特根斯坦前期语言哲学的成果,他称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思想的真理性是无可辩驳和确定的。维特根斯坦在阐述关于语言界限的观点时提出了“不可说”理论:用语言作为界限分别出“可说”之物与“不可说”之物。所谓“可说”之物,主要是自然科学命题,是可以说清楚的、有意义的命题。所谓“不可说”之物,就是伦理、美、生活的意义这类形而上之物。整本《逻辑哲学论》可以浓缩成这样一句话:“凡是可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1]
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也被比喻成“维特根斯坦之梯”,指向《逻辑哲学论》中的七大部分:世界、事实、思想、句子、真值、界限、神秘领域,这七个部分构成一把梯子,人们借助梯子向上攀爬登上顶端,到达一个神秘领域。“任何理解我的人,当他用这些命题为梯级而超越了它们时,就会终于认识到它们是无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高处之后他必须把梯子扔掉)他必须超越了这些命题,然后他就会正确看待世界。”[1]
二、《都柏林人》中的“不可说”
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是20世纪爱尔兰的著名作家和诗人。《都柏林人》是乔伊斯广受赞誉的作品之一,整部小说集由15部短篇小说组成,蕴含大量具有象征意义的隐喻。乔伊斯说:“我的意图是写我国的道德历史,我选择都柏林作为地点。因为这个城市处于麻木状态的核心。故事大部分都采取审慎的平民词语的风格。”[2]乔伊斯用“可说”的朴素词语传达都柏林群众“不可说”的麻木状态和灰暗底色,使每一个故事情节、每一个人物的塑造,都渗透着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
译者王逢振总结了乔伊斯写作的五个特征,笔者选取了与维特根斯坦“不可说”内涵相契合的三点:第一,小说集中使用的某些词汇,例如“徒劳”“无用”“厌倦”“绝望”等在多个故事中反复出现,其目的是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每个故事是普通人的道德构成。第二,小说使用“混乱”表示瘫痪,每当人物不得不面对选择某种积极生活的关键时刻,他们变得不知所措,像被吓坏的兔子一样静止不动。第三,小说以单色调的散文风格象征都柏林单调乏味的生活,产生出黑白照片的效果[2]。
《都柏林人》中富含深刻象征意义的短篇《阿拉比》和《伊芙琳》,故事的主人公都成长于阴郁的家庭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在命运“垂青”之际,他们对生活的热忱之心被点燃。为了追寻梦想,他们不得不与现实进行斗争,最终却因各种原因走向失败,高度契合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朴素的平民故事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内涵。乔伊斯凝练的语言无情揭示了当时社会背景下群众精神麻痹的状态:每一个人都处在瘫痪的核心。
三、《阿拉比》中的“不可说”
罗素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中指出,维特根斯坦理论的根本主题在于:“语句的结构和事实的结构之间必须有某种共同的东西……那种必定是语句和事实之间的共同的东西本身反过来是不能在语言中被说出来。按照他的用语,它只能显示,而不能说出。”[1]如果把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理论放到文学创作中来理解的话,作家的任务在通过故事推进、人物塑造、场景刻画将现实之貌呈现于纸上时就已经圆满完结,而对于主题的阐释,则是文本以外的事情。“人生之为无穷,正如视域之为无限”[1],意义的生成也是无止境的。由于读者个体经验的不同,阅读文学作品获取的审美体验也是大相径庭的,这也是文学作品的永恒魅力所在,英国文学批评家马修认为阅读乔伊斯的作品“不能望文生义,而要透过它苦心经营的现实主义去发掘象征意义或比喻意义”[3]。
《阿拉比》的开篇是对男孩生活环境的描写,“北里奇蒙街的一头是死的”[2]。男孩家后院里是被遗弃的苹果树、荒芜的灌木丛、锈迹斑斑的打气筒。孩子们玩乐的场所是泥泞的小巷、昏暗潮湿的花园、阴暗难闻的马厩。乔伊斯采用“寂静”“潮湿”“阴暗”这类“可说”的意象描绘男孩的生活环境,其“不可说”的内涵指向当时都柏林死寂沉沉的社会氛围以及群众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与男孩黑暗的成长环境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邻居家女孩的形象,女孩身着雪白滚边的衬裙,脖子有着优美的曲线,阳光照亮着女孩宛若圣女,与男孩所处的环境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
19世纪末期的爱尔兰被天主教严格控制,在宗教主导的社会里,爱情与道德处于极端对立面。乔伊斯也在小说中设置了一系列宗教意象,这些看似平凡的“可说”意象背后隐藏着“不可说”的内涵。例如,“甚至在最不适宜浪漫的地方,她的形象也总是伴随着我……我想象自己捧着圣杯,在一群敌人中安然通过。在我进行自己并不理解的祈祷和赞美时,她的名字时不时地从我嘴里脱口而出。”[2]圣杯、祈祷仪式和赞美诗,这些带有浪漫主义基督教色彩的意象完美契合邻居女孩形象:女孩宛如男孩手中的圣杯,赋予他与世俗对抗的勇气,使得他从一群敌人中安然而过,这些是男孩的幻想。而现实是怎么样的呢?男孩在大街上被醉汉和讨价还价的妇女们挤来挤去,街上充斥着劳工们的咒骂,街头卖唱的人哼唱着动乱的歌谣。世俗的景象与男孩的完美幻想格格不入,预示着男孩的幻想终将破灭的结局。
类似的“不可说”内涵还体现在“阿拉比”(Araby)这个词,“阿拉比”代表着一个带有阿拉伯神秘色彩的集市。在欧洲人眼中,中东地区充满着无限诱惑和幻想,是纵情享乐、异域风情的代表。男孩许诺倘若自己去了阿拉比,一定给女孩带一件礼物。在接下来的日子,阿拉比这个词不断向男孩投射出一种东方的魅力。
男孩于日思夜想中盼来了周末,在经历了种种意外,抵达目的地后,眼前的景象与他的想象截然不同:这里灯火昏暗、混乱不堪。摊位的女售货员和男子打情骂俏,面对男孩的询问,女售货员的态度并不友好。男孩感受到了现实与幻想的巨大落差,遂转身离开。他盘弄口袋里为数不多的硬币,货廊尽头传来灭灯的喊声,大厅黑了下来,男孩觉得自己像一个被虚荣心驱使和嘲弄的动物,他感到愤怒和痛苦。乔伊斯描绘了集市的混乱不堪、售货员的态度冷漠、大厅的灯灭等“可说”的意象,指向小男孩的幻想遭受现实的打击,最终破灭的“不可说”结局。
维特根斯坦指出,抽象神秘的东西不可能存在于具体的事实世界中,人们只能谈论具体的现实世界。具体到文学作品之中,涉及主人公的精神意志、社会伦理道德之类的东西也就属于形而上的,是不可说的。不可说之物并非无关紧要的东西,相反,它们正是传达作品深刻意蕴的东西。正如陈嘉映先生所言:“存在比存在者难说,时间比空间难说,内心感受比外表描述难说。人所共知人人会说的东西不稀罕,不易说的东西提示一种深度,不可说的东西提示一种更深的东西。”[4]《阿拉比》整个故事由明线和暗线交织构成,明线即小男孩前往阿拉比到离开的“可说”的故事,暗线即美好理想在实现过程中备受阻挠,最终彻底幻灭的“不可说”的结局。
四、《伊芙琳》中的“不可说”
19世纪,爱尔兰女性深受宗教和父权的压迫。“爱尔兰的天主教会期望女性能履行传统的女性角色——成为妻子和母亲,对丈夫顺从谦卑……”[5]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巴(Susan Gubar)指出她们“被孤立为一个个孤立家庭中的妻子”[6],受传统女性身份的桎梏,她们精神麻痹,自觉为家庭做出牺牲,处于一个“不可说”的困境——传统女性对自我实现的追寻往往难以冲破现实的枷锁。
《伊芙琳》的开篇描写了伊芙琳压抑的生活环境,“凝视夜幕笼罩的街道,她的头倚靠着窗帘,鼻孔里有一股沾满灰尘的印花布窗帘的气味,她显得非常疲倦”[2]。此处的“灰尘”属于现实世界中“可说”的实质灰尘,“疲惫”属于肉眼可见的人物状态,而背后“不可说”的是伊芙琳所处环境的压抑肮脏和她精神状态的疲惫不堪。这里有两处“不可说”的涵义,一是指伊芙琳生活中的琐碎是无法处理完的,她的努力显得徒劳,也使得她疲惫,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伊芙琳私奔计划最终会走向失败。二是指向当时爱尔兰女性深受父权和宗教的迫害,精神逐渐麻木的困境。“在有限的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出路的女性或进入修道院,或移民,或继续待在家里成为家庭的仆人,伺候男性。”[7]在那个社会,宗教和道德的束缚成为女性心中进行自我评价的准则。伊芙琳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将一生奉献给家庭,为家庭琐碎操劳,如此牺牲却并没有一个好的结局,最终发疯致死。伊芙琳母亲的“可说”形象背后其实是爱尔兰传统女性的缩影,暗示着她们被世俗道德观念约束,过着卑怯的一生,这属于“不可说”的传统女性困境。
伊芙琳有过对生活的反抗,在这个过程中她进行了痛苦的挣扎——一方面是对自我的追求,一方面是母亲留给她的家庭重任。伊芙琳的不舍之情其实是传统女性在父权社会中深受桎梏,从而彻底丧失自我的一种“不可说”的精神异化。精神异化的女性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权,被迫牺牲自我却变成了一种无法舍弃的责任。有机会逃离时伊芙琳竟生出一种不舍之情,为她的人生底色再添一笔灰暗。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伊芙琳对男友弗兰克“可说”的感情,背后也显示出了“不可说”的内涵。乔伊斯对故事中两个男性角色(父亲、男友)的设定,看似是截然不同的:父亲给伊芙琳带来压迫和痛苦,男友给她带来欢欣与希望,但本质上二者同为男性。伊芙琳对男友的爱恋是“可说”的,但是伊芙琳对男友的爱也是值得怀疑的,这属于“不可说”的。她也许仅将男友视作一个带她逃离生活困境的工具,对男友的感情也许只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畸形的依赖,而并非纯真的爱。伊芙琳逃离父权的牢笼,追寻自我价值实现的希望,最终只能寄托于另一个男性身上,故事最终的悲剧走向也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私奔之夜,在快要上船时,伊芙琳看见了无尽的大海和汹涌的波涛,在男友的催促声中,她无动于衷,留在岸上止步不前,“像一只孤独无助的动物。她双眼望着他,没有显示出爱意,也没有显示出惜别之情,仿佛是路人似的”[2]。“大海”“波濤”属于“可说”的意象,是现实的景观,其“不可说”的涵义在于二者象征着神秘和自由自在的新生活;同时“大海”和“波涛”也象征着混乱、不安定、死亡、漂泊。由于伊芙琳长期生活在家庭和社会施加的层层压力之下,她的精神世界早已经异化——丧失了追求新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留在岸上的她像一只“孤独无助的动物”,此处的“动物”则是暗示着那些意识上觉醒的女性,最终没有战胜行动上的迟疑,她们的精神早已麻痹,连对新生活的追求也是依附于男性身上,认为男性可以帮助她们脱离生活的困境,本质上没有真正地摆脱男权社会的压迫和束缚,这种行为无异于从一个牢笼跳进另一个牢笼,最终还是无法摆脱依附男性的命运,这属于“不可说”的。
维特根斯坦主张将不可说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乎同一性,比如摹画形式和逻辑形式;第二类是不直接关乎同一性,如哲学、伦理、美学等,这些都不可说。“……命题不能表达更高的东西。很清楚,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伦理和美学是同一个东西)。”[1]至于伦理学和美学为什么不可说,具体到现实生活中来,我们明白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一部分受到法律、法规等有形的东西所约束;另一部分是道德、伦理这些无形的东西所限定。“如果善的意志或恶的意志可以改变世界,那么它只能改变世界的界限,而不能改变事实,即不能改变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1]人们的道德伦理是受制于意志的,但是意志不通过语言来表达。在文学作品中,若作者仅通过教条式的说辞来对人们进行道德劝诫,那么作品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从“可说”层面上看,伊芙琳的故事揭露了传统女性深陷伦理与自我抉择的精神困境,传统女性意识上的觉醒也仅仅是依附于男性身上,是一种“不彻底的顿悟”。乔伊斯对“可说”和“不可说”界限的精准定义,带领读者顺着现实的梯子层层攀爬,最终上升到道德伦理的境界。
五、结语
我国伦理学学者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伦理学批判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判方法。”[8]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时,可以尝试从维特根斯坦“不可说”视角出发对作品进行深层解读,从不同的角度挖掘作品背后的深刻内涵。正如陈嘉映所说:“生活是活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人生的意义问题只能在生活中解答。我们不可能在课堂上给出人生意义的终极答案,这也许有点让人沮丧,但稍做思忖,却实在是件幸事:如果我们能在课堂上弄清楚人生的意义,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但人生不是无言的,言说不仅是人生的一部分,人生是在语言层次上存在。”[4]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不辞辛劳地设定各种隐喻和留白的动机,如果仅仅是用简单的、“可说”的平铺直叙式的语言来对读者进行道德说教,显然是令人兴味索然的,而“不可说”的巧妙运用,将作品赋予了高度的哲学、美学和伦理学特征,引导读者去掀开语言的外壳,发掘语言背后的深刻内涵,发现各个隐含的意义是连环相扣的,无形中达到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也就是维特根斯坦之梯想要引导人们攀登的神秘领域。
参考文献
[1]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 乔伊斯.都柏林人[M].王逢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3] Matthew H.James Joyce:A Students Guide[M].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1978.
[4]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 Scott K B.Joyce and Feminism[M].Sussex:The Harvester Press, 1984.
[6] Gilbert S,Gubar S.No Mans Land:The Place of the Woman Writ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7] Connery S D.The Irish[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1970.
[8] 聶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9] Ellmann R.James Joyce[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李乔歌,天津外国语大学欧美文化哲学研究所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