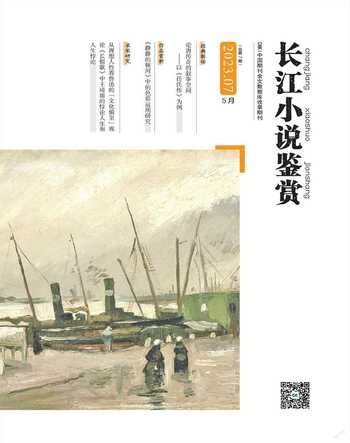谷崎润一郎小说《细雪》中“厌女症”分析
[摘 要] 日本唯美主义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大多以女性为中心进行书写,通过建构风格各异的女性形象体现对女性之美的追求,因此谷崎也被冠以“女性崇拜”之名。在《细雪》中,谷崎一改早期创作的妖冶、放纵的女子形象,转而构建高贵美丽的贵族女性群像。不少研究者视其为对现实日本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驳斥。但在女性主义视域下重新审视其中的女性形象,不难看出谷崎的女性崇拜之下暗藏着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实践着文学上的“厌女症”。
[关键词] 女性崇拜 男性中心主义 “厌女症”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07-0021-04
日本唯美主义代表作家谷崎润一郎一生创作颇丰,《细雪》是其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一部长篇小说,被日本文学史家加藤周一认为是谷崎文学的巅峰之作,被誉为日本小说史上的里程碑之一。作品以女性作为书写中心,塑造了四位性格各异的高贵美丽的女性形象。中日学界对《细雪》中女性形象的研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热度。不少研究者认为谷崎早期创作的女子形象大多妖艳、放纵,后期回归古典主义,笔下的女子形象高贵、优雅而含蓄,但共同的特点是她们年轻充满朝气,兼备标致和美丽的体态,魅惑并支配着男子。女性崇拜意识从始至终贯穿谷崎润一郎的作品,而这种崇拜被视为对日本传统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一种发声与反抗。但是通过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对作品中女性形象深入剖析,不难发现谷崎对于女性的审美倾向仍然是以男尊女卑的男权思想为主导,女性是由男性主体控制和支配的客体。虚假不实的女性形象囚禁着女性的自我意识,模糊了女性真实的生活状态。探析谷崎在作品中隐藏的男权思想下的厌女情结,有助于从多元的角度解读谷崎的作品。
一、另类的女性崇拜
无论是谷崎的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一直将女性作为书写中心,追求女性之美,延续女性至上的主题。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认为:“喜欢女性的男性也会有厌女症。崇拜女性,厌恶女性并不矛盾。”[1]谷崎对于女性的崇拜意识并非对女性的绝对崇拜和对所有女性的崇拜。谷崎崇拜的女性是其自身建构的女性。上野千鹤子提道:“厌女症表现为男性为了成为性的主体地位就会将对女性的藐视深植于自我确认的核心。”[1]而这种自我确认即将女性视为他者,以男性的价值标准去支配女性。谷崎作品以男性为中心建构女性形象,对于符合自身审美的女性就崇拜,对于不符的女性则厌恶。这恐怕并非真正的崇拜女性,而是一边崇拜女性一边厌恶女性的“厌女症”。
谷崎在回归古典主义之后,其短篇小说《春琴抄》《盲目物语》中的女性角色大多设定为出身高贵、容貌倾城。长篇小说《细雪》也延续着这种女性人物设定,作品中的四位女性人物都出生于世家大族,高贵的出身对应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从“见报事件”可以看出莳冈家族女眷的一举一动都能够引起当地报纸的关注。同时四姐妹还拥有着惊艳世人的美貌,接受過良好的教育,言行举止均优雅不凡。大姐鹤子就连写信,都要事先拿出名家字帖临摹练习,唯恐失了家族体面。
二姐幸子和女佣春倌的形象差距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作为芦屋的女主人幸子成长于家族最鼎盛的时期,受过良好的旧式贵族教育,嫁给了父亲精心挑选的赘婿贞之助,受到丈夫的呵护与关爱,过着美满安稳的生活。幸子的生活带着浓厚的贵族阶级享乐情趣,赏花时偏爱京都的樱花,钟爱关西特产的鲷鱼,谈话时倾向大阪话以显示复古高雅。而春倌出身贫苦,在芦屋帮工,粗俗不堪,经常与附近的用人一起议论家常,搬弄口舌,甚至在言行上隐隐有些蠢笨。作为婢女的春倌在无意中议论了雪子相亲之事,从而使消息走漏,幸子和雪子姐妹两人因此盛怒。面对主人的盛怒,春倌不安地跪伏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一个高贵典雅,一个粗鄙卑微。就连谷崎自己也曾说:“他将女人看作是在自己之上的人,自己仰望着女人,若是不值得一看的女人,就觉得不是女人。”[2]谷崎崇拜的女性是有苛刻条件设限的,将女性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划分开来,满足自身审美标准的女性则推崇,否则便不值一提。建构审美上完美的女性以达到满足自我的目的,这从本质上来讲是将女性视为男权文化中迎合男性的工具。谷崎一味推崇出身高贵的贵妇人,对于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女性不屑一顾,正体现日本近代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厌恶与蔑视。
二、男性凝视下的视觉快感
弗洛伊德在《性别三论》中提到人具有窥视的性本能,强调对女性身体的官能书写似乎能够迎合视觉上的快感。而在男性的视域中,美丽则成为女性的第一张通行证。《细雪》的叙事采用限制视角中的第三人称,以幸子夫妇交叉作为视角人物来推动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更是以二姐夫贞之助的在场,嵌入自己男性的视角去直接凝视作品中的女性。文中有大量的笔墨描写莳冈四姐妹惊为天人的美丽容貌。四姐妹的美丽各有风情,大姐鹤子身长玉立,面容姣好,高大威严,宛若平安时代的王朝丽人,极其符合旧时代的审美标准;二姐幸子圆润丰满,调和了日本韵味和西洋趣味;雪子清冷温婉,高雅怯弱,常着和服,典型的京都式美人;妙子聪慧开朗,大胆开放,极具西洋趣味。四姐妹的年纪都在三十岁左右,但在容貌上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看起来远远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而以“濑越先生”为代表的男方相亲者对于雪子容貌的鉴赏则是男性对于女性的间接凝视,例如“井谷对我说:我一点没注意,但是男人们却出乎意料地看得仔细。昨天你们走后,有人说小姐的左眼圈上有点褐斑,有人同意是斑点,也有人否定说不是斑点,是光线使人产生了错觉。各有各的看法,他们问我究竟有没有褐斑”[3]。这一群拿着放大镜的“鉴赏家”们如同在欣赏一件待价而沽的艺术品,一遍又一遍仔细查找瑕疵。而这一点时隐时现的浅褐色斑,之后就成为姐妹之间足以焦虑的话题,她们多次谈论如何采用医疗方法或化妆来遮掩。
在双重男性凝视下,作品着重强调与年岁不相符的美貌,暗自强加给女性年龄与容貌的焦虑。年轻貌美似乎成为女性的第一特征,失去年轻美貌女性就会贬值。正如作品中的雪子,哪怕依旧看上去年轻貌美、娇媚可人,但家族却将其视为大龄且出生年份不吉利的女子,将其择婿的标准一降再降。与雪子相亲的男性大多都是四十岁以上的年纪,由于各种原因大龄单身或丧妻,他们绝大多数都尽显老态。男性的老态与着重强调的女性幼态形成强烈对比。谷崎笔下多次强调这种不切合年纪的幼态美与女性身体的官能美,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男性凝视的视觉快感。女性身体的官能美成为男性审美的第一取向,将女性的外貌编码成强烈的视觉冲击与欲望符号。哪怕是女性年岁渐长,也强求她们能够留住美丽。
三、性双重标准下“圣女”与“妖妇”的不同命运
上野千鹤子认为:“男性自我核心的确认中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母亲。厌恶侮辱生下自己的女人,会进而引发出身身份认同的精神危机。”[1]而在性的双重标准之下,一边崇拜女性,一边厌恶女性的矛盾就迎刃而解。“所谓的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性与女性的性道德有所不同。男性的好色被肯定,视为理所应当。而女性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女性在性的双重标准下被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等常见的二分法。”[1]男权社会中男性厌女症则进一步表现为一边崇拜“圣女”,一边厌恶“荡妇”。《细雪》中也将主要的女性人物分化为这两类形象。
1.理想的“妻子”幸子
幸子身上有着传统日本女性的贤惠善良。幸子的贤惠善良在于努力调和家族矛盾,看护照顾幼妹们。她收留因与大姐夫不和的三妹、四妹,多次费心帮雪子张罗婚事,操心被家族视为败坏门风的妙子。在自己小产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幸子依然坚持带雪子出席相亲宴会。在社交上,幸子有着如同西方人那样的热情与开明,拜访卡德丽娜家时,她灵活化解了饮食文化差异上的尴尬,与不少外国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幸子的言行举止处处展现出名门望族主妇贤惠大方的风范。同时从文中幸子大量的内心独白来看,幸子在思想上是一个男性价值观的遵循者、同化者,在女性的婚姻观和价值观上都是男性中心思想的传声筒。对于雪子的婚事,幸子也看重男方的门第与经济是否能给女性提供良好的生活,认为女性的价值场域在于家庭,将女性依附于男性视为寻常。幸子对于准妹夫奥畑的寻花问柳予以忽视隐瞒,而对于妹妹妙子的未婚先孕、不合礼法的男女关系表示厌恶与排斥。幸子更像近代日本明治时期提倡的贤妻良母式女子教育下的完美产物,恪守传统的妇道,又有一定程度的知识素养和较为开阔的视野,能够在家庭的场域中做好相夫教子的工作,完成被男性所赋予的使命。正因如此,在谷崎的笔下,幸子衣食无忧,女儿聪明可爱,丈夫温柔体贴,过着中产阶级富裕安稳的幸福生活。
2.好逑的“圣女”雪子
雪子作为作品的中心人物,她的美貌惊为天人,在诸姐妹之上。在多次的相亲中,雪子的美貌都是话题的焦点。出行途中,雪子的美丽能让对坐的青年看红了脸,害羞得低下了头。尽管已经三十多岁了,雪子依旧那么年轻美丽,仿佛岁月格外宽容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美人。性格上雪子延续着日本传统女子溫柔顺从、矜持娇羞的特点,每次被姐姐姐夫催问相亲意见时,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含糊其词,柔柔弱弱地说全凭姐姐们做主。在桥寺打来电话约会时,她害怕得接电话都支支吾吾。
雪子除了有美丽的外表之外,身上还带着母性的光辉。不管是住在二姐幸子家还是被大姐鹤子叫去东京,雪子都是帮姐姐们看护孩子的一把好手。每次家里有病人需要看护也是雪子主动担起重任。当幸子的独女悦子患上传染病猩红热时,雪子也毫不畏惧,极力说服姐夫将书房腾出来专门辟做隔离病房,自己衣不解带地照顾悦子。二姐夫贞之助对云英未嫁的雪子怀有莫名的情愫,时常心神荡漾,可以窥见雪子是君子好逑的淑女,是男性最为理想的结婚对象,是成为慈母的最佳人选。因此,整部作品以雪子的婚嫁作为故事的主线,但雪子却对自己的人生大事处于一种沉默失语的状态。看似寂静无声的美丽人偶雪子,在家族预备的声势浩大的婚典与堆积如山的嫁妆的裹挟中,顺应家族的安排嫁给彼此都无好感的贵族庶子御牧。即使小说最后雪子对于不能自主的婚姻以腹泻作为生理上抗拒的表现,但最终也被隐晦无声地一笔带过。
3.离经叛道的“妖妇”妙子
相较于雪子的羞涩含蓄,妙子更加开放大胆,是一个极富西洋趣味的美人,就连在穿衣上也时常选择时髦的西服洋装。妙子追求经济独立,不屑依附家族与男人。从做人偶开设工作室到后期萌生去法国学习西服制作的想法都体现了妙子想成为职业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妙子一直在试图打破男权的束缚,在婚姻、人生、性等诸多层面都要自主选择,主动权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从相继与奥畑、板仓、三好交往来看,妙子有着自己的一套择偶标准,那就是“实用主义”。妙子从思想到行为都是完全西化的新时代独立女性,与男权社会中构想的女性是相背离的,被男性视为离经叛道的“妖妇”。因此,谷崎笔下的妙子经历坎坷,命途多舛。先是想成为职业女性遭到家人和贵族恋人的反对,与家族决裂,与恋人分手;经历水灾险些丧命,与板仓相恋后,板仓却突患重病离世;后又因食物中毒而重病不起;与酒保三好交往,未婚先孕,遭遇难产,生下死胎;最后草草嫁给三好,匆匆离开芦屋。妙子的遭遇也隐含着谷崎对于妙子这类具有自主意识女性的不喜与厌恶。
同一家族的美丽女性,结局落差却如此之大。谷崎以性的双重标准来区分和支配女性,幸子对于男性来说是最理想的贤惠妻子,雪子则是男性想追求易支配的纯洁圣女。幸子、雪子这类被视为“圣女”的女性就被谷崎所崇拜,生活衣食无忧,富贵体面。而未婚先孕、力求女性独立自主的妙子则被谷崎视为“荡妇”,给予不幸的结局。幸子、雪子这些女性形象都是男性逃避公共社会,而在内心私人空间建构的女性文本。而这些文本来源于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又服务于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带有厌女情结的男性作家一直以男性的凝视与话语建构女性形象,而男性受众会强化自我确认,加深对女性的蔑视,女性受众会在男性的建构中产生同化,加剧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的固化。
四、结语
通过《细雪》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谷崎并非对女性一味地崇拜,而是在男权思想主导下以自身审美标准建构女性,将女性视为客体,表面看似在写女性的美好,实则蔑视女性。谷崎欣赏女性身体的官能美,却束缚女性的自主意识,崇拜女性,却压抑女性。谷崎一直在其作品中追求女性之美,笔下既有妖冶放纵的“妖妇”,也有高贵美丽的“圣女”,无论哪一种女性都是男性欲望的牺牲品。谷崎笔下的女性更像是男性幻想中建构的女性文本。女性是被建构的他者,是美的符号,是唯美理念的承载者,而赋予这个文本意义的却是在父权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那些看似是崇拜女性的完美女性形象仅仅只是用于区分和支配女性的工具,用以模糊女性的自主意识,维护男性的绝对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上野千鹤子.厌女[M].王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2]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M].叶渭渠,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3] 谷崎潤一郎.细雪[M].储元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 谷崎润一郎.吉野葛[M].林少华,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5] 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6] 梁琛婧.谷崎润一郎的人生经历与女性崇拜思想[J].文学教育,2014(7).
[7] 张能泉.谷崎润一郎国内译介与研究评述[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2).
[8] 武凤娟.浅谈《细雪》中的女性形象[J].作家,2012(24).
[9] 张晓宁.“异端者”心灵的故乡:《细雪》《古都》主题新论[J].郑州大学学报,2011,44(4).
[10] 周萍萍.承传与摒弃:论日本女性文学中的道德观衍变[J].外国语文,2012,28(4).
[11] 杨越.试论谷崎润一郎作品《细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以莳冈家四姐妹为中心[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7.
[12] 翟明雪.论谷崎润一郎《细雪》中的古典美[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9.
[13] 诺敏.雪子に見る和の美-谷崎潤一郎『細雪』の女性像[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0.
[14] 上野千鶴子.家父長制と資本制ーマルクス主義フェミニズムの地平[M].東京:岩波書店,1990.
(责任编辑 夏 波)
作者简介:胥杨,长江大学人文与新媒体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与文化。
——以《细雪》《春琴抄》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