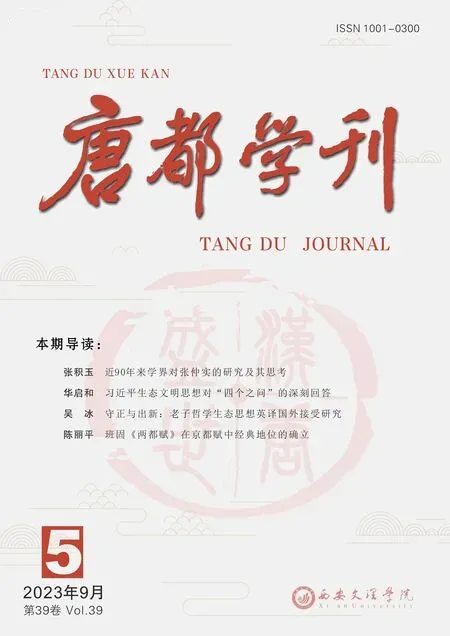汉灵帝末期地方州牧制度的重建与效果
王煜焜
(上海理工大学 沪江文化研究所,上海 200993)
秦统一六国,疆域既广,管理难度增加,则于旧制诸多改进,设有御史负责监察,称监察御史。汉文帝时,御史职责履行不力,丞相则被命令派遣代表前往各郡国进行巡视,这些代表被称为“刺史”,但并非专职。武帝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彼时的刺史为监察官,秩较于郡守为低。州仅为监察区,非地方行政区,至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哀帝则改归旧制。王莽将十三州调整为九州,刺史又变为州牧,权力也有所扩大。至东汉时,刺史逐渐成为郡守上级,但由于刺史的职责是治官而非民众,因此州仍然被视为监察区域,而非地方的行政机构,但反复更改,颇感混乱。东汉末年,由于黄巾起义等多方面的问题,朝廷采纳刘焉的建议,提升部分刺史为州牧,并赋予他们民政和军政权力。值得注意的是,历来的关注多在评价灵帝此举为导致汉朝覆灭的根本所在。本文则旨在通过研究中平五年之前的州牧制度演变以及灵帝的战略意图,来梳理东汉末年地方州牧制度的重建及其效果。
一、从想象到现实:汉灵帝中平五年前州牧制度的演变及其背后的政治博弈
“牧”,在我国古代有统治、管理之意[1],虽有想象之嫌,但言上古时九州之长即为牧[2]。所谓“黄帝立四监,以治万国。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为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3]然因年代久远、史料匮乏,上古治世的地方官制仍待考察,难以追溯真假。今时可知的是《礼记》在汉代的学术地位[4],在彼时官僚眼中,“牧”一职的设置多与“想象”中的三代的制度有关,其建构价值远超其是否曾存在于历史长河中。郡县制度(1)王夫之言“两端争胜,而徒为无益之论者,辨封建者是也。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秦始皇》,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从中可见,先贤学者亦认为郡县制乃理之然也,不值一辩。本为战国之际解决贵族血缘统治的良好对策,而官员的任命多出于中央政府,但承平已久,地方容易产生家族化的倾向,而东汉的豪族庄园化(2)最早提出东汉政权的本质是“豪族政权”,东汉时期官僚泰半出身于豪族的学者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杨联陞《东汉的豪族》,载于《清华大学学报》1936年第4期,第1011页)。因为建立东汉帝国的光武帝刘秀是南阳的豪族,功臣也多出身于豪族,故此说法貌似无差。日本学者五井直弘则认为东汉是与豪族共享天下,其中央政权的实力仅为一般而已(参见五井直弘著,姜镇庆与李德龙译《东汉王朝与豪强大族》,收录于《中国古代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概而言之,东汉自开创之后就中央权力孱弱,不得不依靠地方家族化的势力,与其共同统治天下。即矛盾之集大成,故此中央依旧需要某种方式来监督地方化难题的出现。
战国时期,诸国所采之地方制度多是务实,法家颇有一席之地,毋须从想象的制度去寻找解决之道,各自皆摸索出程度不一而又适合该国的模式[5]。秦一统六国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6]239从职能看,“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监御史掌监郡。”[7]741-742从行政运行的效果言之,秦与西汉皆属上乘[8],因行政、军事和监督的机构互不相统,造成事实上之制衡。王鸣盛则言“监既在守之上,则似汉之部刺史,但每郡皆有一监,则又非部刺史可比矣。盖秦惩周封建流弊,变为郡县,惟恐其权太重,故每郡但置一监﹑一守﹑一尉,而此上别无统治之者。”[9]秦之监御史似与两汉刺史职能雷同,但两者所能监察之疆域范围则不可同日而语。秦朝地方的监察以相制为考量,决断性的权力完全出于中央,既非临时政策,效果理应尚可,但始皇骤然定鼎中原,天下虽一统,然未能及时调整版图扩张引发的制度矛盾(3)钱穆先生曾言:“秦得天下,尚沿旧制,如以会稽戍渔阳,民间遂为一大苦事。又有‘七科謪’与‘闾左戍’,陈胜、吴广即由此起。”参见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7页。,导致国祚不长,难以考察地方行政的有效性。
刘汉兴起,“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7]741。然《百官公卿表》所载过简,而《通典》之记述略详:“秦置监察御史。汉兴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监三辅郡,察词讼,所察之事凡九条,监者二岁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其后诸州复置监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4)参见杜佑《通典》卷32《职官典一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84页。《唐六典》言九条事为“辞讼者、盗贼者、铸伪钱者、狱不直者、繇赋不平者、吏不廉者、吏苛刻者、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者”。参见李林甫等编《唐六典》卷13《御史台·侍御史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9页。从史料可知,汉初监察松紧不一,未成惯例,随时事而更新。殷鉴不远,新政权解决秦帝国地方问题的方法是令传统封建的王国与郡县同时存在。当然,无法苛责开国之君(5)张传玺就提出秦汉鼎革是以刘邦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战胜以项羽为首的六国旧贵族阶级的过程(参见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尽管带有传统阶级史观的色彩,但所谓“旧贵族”阶级在地方依旧有相当的势力,且新兴的“刘邦”阶级的利益如何分配是一大政治难题,而刘邦能建立两种并行的制度已属不易,因氏族制的解体绝非一蹴而就(参见西嶋定生著,黄耀能译《白话秦汉史》,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1页)。,初始之际其稳定局势之效显著,后经文、景两帝的完善,至汉武登基时,汉帝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已初具雏形,但隐患不小,地方的离心力未随“吴楚之乱”的平定而减小。
刘彻对地方未能集权中央感到相当不满,地方也未能施行其政治要求。“天子(武帝)始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6]1438彼时正值各地灾荒,尽管刘彻已于前年奋力赈灾,但所巡之处并未尝试贯彻其号令。个案的背后是否是普遍的问题,这困扰着意欲大展宏图的汉武帝。显然,皇帝整年的在外巡视并非是解决困境的方法,加之通信往来并不发达,若地方有心隐瞒,中央亦难以及时了解地方存在的问题。故此,动员可靠的中央官员前往地方巡视成为了武帝为数不多的解决方案。执政多年后,武帝于“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7]741,成为汉代政治史上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武帝设置刺史的本意是监察地方官,以“六条问事”,得以更好控制地方,避免中央的行政命令难以实施,抑制豪强大族的发展,也方便获取各地的情报[10]3617-3618。并且,刺史秩仅六百石,远低于地方长官的二千石俸禄,但能监察郡守行为。顾炎武就认为“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11]一如晚清百日维新之际的年轻官僚,“秩卑”之官员多有政治抱负,意欲在地方履历之际有所作为,这确是武帝管控地方的上佳手段。“分科分层”提供了分配权力、责任和资源的等级架构,给予更多变动的官僚可能性[12]。除“六条问事”外,刺史还需监察藩国诸王,解决历史遗留的重大隐患。王鸣盛曾言:“历考诸传中凡居此官(刺史)者,大率皆以督察藩国为事”(6)王鸣盛举例说:“如高五王传青州刺史奏菑川王终古罪,文三王传冀州刺史林奏代王年罪,武五子传青州刺史隽不疑知齐孝王孙刘泽等反谋,收捕泽以闻。”参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4《汉书八》,第98页。,认为“盖自贾谊在文帝时已虑诸国难制,吴楚反后防禁益严,部刺史总率一州,故以此为要务”[10]98。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武帝设置刺史是权归中央后的结果而非其原因(7)参见井上雅裕《前漢中期における国家構造》仏教大学大学院研究紀要五,1977年版,第259-260页。,历经文景以及武帝多年的经营,此时只是水到渠成,体现出刘彻对权力的掌控达至巅峰。对于武帝而言,毫无必要将监察官与“想象”中的官职相连,经典中存在的事物无法强化中央的合法性。与此相对,随着汉武逝世,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掌控亦逐渐松懈,虽时有变化,难言绝对,但至灵帝前,总体的趋势是中央与地方间的持续博弈,未有改变。
成帝绥和元年(前8)改刺史为州牧。按《汉书》载:“(朱博)又与丞相(翟)方进共奏言:‘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奏可。”[7]3406从翟方进的奏言可知,彼时建议设置州牧的原因在于刺史的行政级别无法监察二千石的太守。成帝骄奢淫逸,费钱亿万,政令不彰,在中央权力涣散之际,刺史难以监察地方乃必然之结果。如此更改,无非出于利用“正名”之效果。然地方权力既隆,原本同中央又有争权,自然难以轻易就范。故此,不久后的哀帝建平二年(前5)又改州牧为刺史。原本建言改州牧的御史大夫朱博又言:“汉家至德溥大,宇内万里,立置郡县。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国,吏民安宁。故事,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丞相方进奏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7]3406显然,成为州牧的原监察官更是成为中央政治的新难题。事实上,拥有地方背景的官员进入“九卿”行列后更是跋扈难遏。这种转换只是体现了中央权力的强弱,而非通过建制的修改来强化统治,此后王莽篡位期间又有复位州牧之举[7]4199,而光武帝刘秀早期亦有设置州牧[13]70,皆属权力未稳而试图找寻统治依据。当光武中兴,掌控全局后,又于“建武十八年(42),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10]3617,直至灵帝中平五年(188)才复置州牧之制,然此时政局已回天无术。
当刺史奉“六条问事”监察地方时仍是中央官员,而其品秩不高,权力却重,能监察二千石的地方官,存在干涉地方事务之可能。如《汉书》载:“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7]3386从武帝设置十三部刺史始,其政治初衷本就是更好地控制地方,虽为监察,侵夺权力亦是制衡方法之一,但前提必然是中央的实力足以管控地方。刺史与地方的关系背后是中央的影响力,这随着皇权的变动而改变。明帝时,马严上疏曰:“臣伏见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不务奉事尽心为国,而司察偏阿,取与自己,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以刑法,不即垂头塞耳,采求财赂。”[13]860显见,随着时间流逝,东汉地方势力强悍,中央难以有效控制地方时,刺史也在从权力的真空中寻找利益。同时,拥有举荐之权的刺史亦使其侵夺太守之职,从中谋利,如《汉官旧仪》载:“刺史举民有茂才,移名丞相”[14],又如“刺史杨雍即表(盖)勋领汉阳太守”[13]1881。至东汉,刺史毋须每年赴京考殿最,故终年留在州内。文献记载:“建武十八年(42),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初岁尽诣京都奏事,中兴但因计吏。”[10]3617同书注引胡广曰:“不复自诣京师,其所道皆如旧典。”[10]3619尽管说常年坐镇地方使得刺史更易从监察官向行政官转化,但过往的研究多专注于监察官侵夺权力以及在职能上的转变(8)参见熊伟《秦汉监察制度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好並隆司《前漢後半期における皇帝支配と官僚層の動向》,载于《東洋史研究》26-4,1968年,后收录于《秦漢帝国史研究》,未来社1978年版;東晋次《後漢時代の政治と社会》,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5年版。,这忽略了背后重要的问题,即中央本身权力的动态变化。
至汉灵帝中平五年设置州牧前,刺史职能的内涵出现明显变化。在西汉武帝时,刺史职能仅监察一途。在运行过程中,随着中央权力的改变,刺史尝试在地方获得更多的利益,无论是政治资本或者金钱回馈。光武帝后,刺史获得军权和举荐官员之权,且不用赴京师考评,获得从监察权转向行政权的可能,但并非必然,现有之史料多是指出制度的缺陷,背后更值得考察的是中央权力的涣散。有学者指出灵帝改刺史为州牧,“若就行政权论之,亦不过于即成事实以法律上之追认而已”[15]。若灵帝设置州牧只是在法律上承认州牧在地方上的行政、军事权,那么缘何只是在部分地区进行变革呢?纵观汉朝历史,州牧废置无常,如前所述,“牧”一称呼在汉代人眼中是上古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面临内忧外患之际,灵帝的改制是有所指向的,希冀通过州牧制度在地方上的再建,强化中央政权在地方统治的正当性与神圣性。
二、“黄巾”“党人”与“豪族”:地方矛盾的加剧与汉灵帝重构州牧制度的战略意图
中平五年,西汉景帝后裔、时任太常官的刘焉担忧时局混乱而上疏灵帝言:“刺史、太守,货赂为官,割剥百姓,以致离叛。可选清名重臣以为牧伯,镇安方夏。”[16]865显然,因地方官员行政败坏,导致民间叛乱,而刘焉建议的方法是遴选名声上佳的重臣前往地方治理。尽管刘昭言刘焉居心不良,为己谋利而非为国(9)刘昭在《百官志》中言:“至孝灵在位,横流既及,刘焉徼伪,自为身谋,非有忧国之心,专怀狼据之策,抗论昏世,荐议愚主,盛称宜重牧伯,谓足镇压万里,挟奸树算,苟罔一时,岂可永为国本,长期胜术哉?”参见司马彪《续汉书》卷28《百官志》,收于范晔《后汉书》中,第3620页。,但其结论乃出于事后的考察,先勿论刘焉居心何在,灵帝当时面临的统治窘境是毋庸置疑的。
中平元年(184)爆发黄巾起义,且叛乱迅速蔓延各地,动摇了东汉的统治基础。灵帝暂缓“党锢”,与士大夫协作,命皇甫嵩为指挥,镇压起义。尽管张角不久后病逝,然其余部仍活跃各地,而雪上加霜的是羌族亦在此时入侵[13]350。从永康元年(167)以来,羌族未曾为祸东汉,且“党锢”的负面影响亦未消除,王室与士大夫间的矛盾犹在。地方上官员任用不当,如益州刺史郤俭横征暴敛(10)如“是时益州贼马相亦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进攻雒县,杀郗俭,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参见范晔《后汉书》卷75《刘焉传》,第2431页。,甚至还有趁火打劫之徒[13]2432。诸多叛乱使得政府在财政上也遇到危机。然而,除起义爆发时财政“悉出给军”[13]350外,灵帝宫中的支出有增无减。次年(185)二月又遇上“南宫大火”[13]351,为修复宫室,灵帝“税天下田,亩十钱”[13]351。汉代时,成年男子的人头税是一算,即一百二十钱(11)《光武帝纪》注引《汉仪注》曰:“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筭。又七岁至十四出口钱,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时又口加三钱,以补车骑马。”参见范晔《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第74页。,而灵帝所征之税已相当于其1/12,百姓负担颇重。然而,更荒唐的是“造万金堂于西园”,且“又铸四出文钱”[13]353。然而,由于内乱、羌人入侵、宫殿修筑,东汉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了,灵帝只得“另辟蹊径”,开始卖官鬻爵。《三国志·董卓传》注引傅子曰:“灵帝时牓门卖官,于是太尉段颎、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张温之徒,皆入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16]179曹操父亲便是在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13]2519。毋庸置疑,东汉王朝正面临建国后从未遇到过的难题,财政危机、叛变与地方行政失控等诸多问题困扰着灵帝,迫使其寻找一举解决所有困境的方法。
在如此恶劣的政治背景下,灵帝接受刘焉的建议改刺史为州牧,确有政治谋划于其中。据《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续汉书》载:“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或从列卿尚书以选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16]866又据《后汉书》载:“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13]2431观记载可知,于中平五年前后出任州牧的共有五人,即刘虞、刘焉、刘表(12)刘表实际并未在中平五年时出任州牧,而是在初平三年,详见下文。、贾琮与黄琬。实际上,这数人的选择体现了灵帝设置州牧的战略计划。
刘焉,江夏竟陵人,汉鲁恭王之后裔,“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后以师祝公丧去官。居阳城山,积学教授,举贤良方正,辟司徒府,历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16]865在接受其设州牧之建议后,灵帝“出(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16]865,这亦是刘焉招致批判的直接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刘)虞等皆海内清名之士,或从列卿尚书以选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16]866换言之,此时出任州牧的诸君皆是“海内清名之士”,或已担任“列卿尚书”,且刘焉还出为监军使者。这群官员业已身居高位,名声亦佳,若言其出任州牧纯为割据一方则有事后过度解释之嫌。
刘虞,东海郯人,光武帝子东海王之后,而“祖父(刘)嘉,光禄勋”[13]2353。刘虞通五经,举孝廉,稍后迁至幽州刺史。“黄巾之乱”时拜为甘陵相,后迁宗正,中平五年时拜为幽州牧。在幽州刺史与甘陵相任内的治绩为刘虞带来“人格高尚”之名,民众拜服而咸感其恩,甚至鲜卑、乌桓、夫余与秽貊等少数民族也因其德化而“随时朝贡,无敢扰边”[13]2353。甘陵,作为“党锢”的发源地而名闻天下,备受官场瞩目。黄巾起义爆发时,当地民众趁势揭竿而起,为了善后,灵帝拜刘虞为相,收拾残局。据史载:“中平初,黄巾作乱,攻破冀州诸郡,拜(刘)虞甘陵相,绥抚荒余,以蔬俭率下。”[13]2353由此可见,刘虞惯用的为政手段是“德”,而非暴力镇压。
刘表,山阳高平人,鲁恭王子孙,与刘焉同为西汉景帝之后[13]2419。“党锢之祸”时,刘表为“清流”一派的“八顾”之一,其名天下皆知。党事起,刘表逃亡,得以免祸。“党禁解,辟大将军何进掾”[13]2419,后任荆州牧。然而,刘表出任荆州牧的时间却非在中平五年。灵帝甫崩之际,刘表正代王叡为荆州刺史,时“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13]2420-2421。换言之,刘表任州牧的时间在初平三年(192)。然而,此时献帝正为李傕、郭汜所挟持,政不由己出,故刘表获得州牧是临时的中央政府对地方刺史获得权力的肯定,这同灵帝的改革不同。
贾琮,东郡聊城人,举孝廉,再迁为京兆令。彼时交州难题交错,如交州尽管“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然而)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址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13]1111在听取多方意见后,灵帝提拔贾琮为刺史,而“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傜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闲荡定,百姓以安。”[13]1111-1112贾琮处理日常事务的方式是“德化”,显然与刘虞和“党人”集团官员的行为类似。由于贾琮在交州取得相当的政绩,进而被灵帝任为冀州牧。
黄琬,祖父黄琼,与李固善,历任魏郡太守﹑尚书令﹑太常﹑三公。年少失父,以公孙缘故拜为童子郎,后迁至五官中郎将。黄琬与陈蕃的关系极佳,因而在“党锢”之时受到严重牵连。黄琬受禁锢二十余年,直“至光和末,太尉杨赐上书荐琬有拨乱之才,由是征拜议郎,擢为青州刺史,迁侍中。中平初,出为右扶风,征拜将作大匠、少府、太仆。又为豫州牧。”[13]2041尽管寥寥数语,但可知的是黄琬高官子嗣之身份,以及他同当时“党人”关系匪浅。
在崇尚儒学的东汉社会里,品格高尚的人是被各阶层所认同的,以上诸位在危难之际受任州牧的皆有高尚之品格,至少在社会风评中的体现是如此。然而,高尚的品德就是灵帝选取州牧的标准吗?值得注意的是,刘虞、刘焉、刘表都是刘氏皇族之人,刘焉和刘表还是西汉景帝的子孙。贾琮与黄琬则出身于二千石的世家大族,地位显赫。可见,灵帝选择的都是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人物。此外,必须注意的是出任州牧之人与“党人”的渊源。如黄琬与陈蕃交厚,他受“党锢”之累被禁锢二十余年。刘虞、贾琮似乎并非“党人”派系,但他们在地方上的施政模式与“党人”行为观念接近,在镇压叛乱、安抚少数民族、实行德政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政绩。宦官、外戚派系所行之事皆与此相悖,刘虞与贾琮在地方的声望获取方式同“党人”是一致的。刘表本人则是“八顾”之一,同“党人”联系绝难分割。
由于史料有限,难有更多文献考证灵帝设置州牧之战略思考,但据对以上出任之人的考察亦可侧面得知一二。首先,灵帝设置州牧只是应时之举,他并不希望州牧制度在此后成为常制。在中平年间时,灵帝遇到的政治危机交错复杂,如羌乱、黄巾起义、财政赤字、“党锢”等,迫使灵帝做出应对。然而,直至中平五年,灵帝尚未找到一劳永逸的方案。接受刘焉的建议去设置州牧只是暂缓眼前遇到的难题而已。从灵帝只设四州之牧可知,他未有扩及全域之意愿。并且,担任州牧之人原本所任之官职品秩与州牧相当,如“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13]2431。换言之,灵帝可将三公九卿外调州牧,反之亦可,为废除州牧留下行政可能性。此外,担任州牧的皆为德行高尚之人,加之出身皇室宗亲、二千石世家,彼等人士对德行名声的重视度颇高,灵帝应该意识到在诸多政治集团中,这个群体是较易控制的。
其次,灵帝希冀借此能缓和中央同“党人”间的矛盾。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使人告发李膺、杜密等人“皆为钩党”[13]330。结果,相关人士皆“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13]330,且大肆株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13]330-331“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13]2189熹平五年(176),“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13]338灵帝时期的 “党锢”牵连甚广,士大夫官僚阶层心中必有怨恨。从下列记述当可知晓灵帝对“党人”为祸政局之恐惧。“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帝惧其言,乃大赦党人,诛徙之家皆归故郡。”[13]2189“大赦”未必能解除“党人”长久以来的政治怨恨,而灵帝重用“党人”相关人士为州牧则能使众多“党人”进入其幕僚为之,自有缓解皇权与士大夫间矛盾之效果。
当然,灵帝通过设立州牧的主要目的是镇压黄巾及其它起义,而从起义爆发的区域即可知其原因。尽管史料记载起义“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发”[13]355,但各地情况有异,必有主次多寡之分,如河南颍川、南阳、汝南和陈国一带有波才、张曼成和彭脱等的起义[13]348-349,东郡各地有卜巳、张伯与梁仲宁等人的起义[10]3297。张角领导的部队主要活动在河北广阳、广宗和巨鹿等地。四川地区的情况更糟,“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13]349。虽说张角在起义后不久就病逝,而兄弟也接连遇害,但黄巾起义并未因此结束。中平五年二月,“黄巾余部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13]355。同年四月,“汝南葛陂黄巾攻没郡县。”[13]355六月,“益州黄巾马相攻杀刺史郗俭,自称天子,又寇巴郡,杀郡守赵部。”[13]356而且,起义军即便不称自己为“黄巾军”,亦是名目繁多,但基本活动的区域就在幽、冀、豫、益四州,而这四州与中平五年灵帝设置州牧所选之地恰好一致。
三、“急逝”“权争”与“割据”:汉灵帝重塑州牧制度对时局的影响与王朝的崩溃
中平六年(189),灵帝突然驾崩,中央再起权争风云。宦官集团诛杀外戚何进,而董卓又乘乱入京,不久就废少帝刘辩,另立刘协为献帝[13]2247-2253。旋踵之际,董卓便因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骄横,招致四方勤王之师蜂拥而至,兵败之下被迫挟帝逃窜,不久后被王允设计除去。原本应趋于稳定的政局由于王允未妥善处理董卓余部,导致情势反而恶化。李傕与郭汜则乘势而上,继董卓之后,继续把持朝政,挟持献帝。而董卓西迁,东部各路勤王之师未能深入追讨,而各自据地以自肥,打着州牧的旗号,合纵连横,互相吞并,局势至乱。至此,汉朝中央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再无能力讨平四方。灵帝原本希冀州牧制度同时解决诸多矛盾,但由于急逝,外戚宦官两大势力火拼后中央权力出现真空,而州牧制度的弊端便渐渐显现出来。
范晔认为正是刘焉建议后,“州任之重,自此而始”[13]2431,而清朝学者何焯则言“州任重而土地分裂。卒成鼎足之运”[17],将东汉之亡与其相连。为《续汉书》做注的刘昭言:“故(刘)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曹操)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乎此。”[10]3620概而言之,近代前的史学家已洞察到设置州牧所带来的恶果。然而,灵帝乃因内外交困而不得已改变既定的制度,是无奈之举,未有常设的意图。不过,历史事件有时显现偶然性,不会按照统治者安排的既有路线前进。如若汉灵帝未在中平六年时便匆匆离世,那么结果或许迥异。但历史无法假设,州牧的设置的确加大了地方的离心力,促进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汉王朝最终就是在军阀割据地方的局面下灭亡的。
灵帝重塑州牧制度最终促使军阀割据局面的进一步形成,原因有二:
首先,州牧具有辖区地方的最高行政权与统治合法性。利用州牧的统治合法性就可以使自己的扩张和割据顺理成章,不受社会的舆论谴责。在重视名声的汉代,很少有人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僭越王权,所以州牧制度就为其扩张提供了良好的借口。如刘焉就利用州牧的权力,“抚纳离叛,务行宽惠,阴图异计。”[16]866-867刘表则在献帝受到挟持的情况下,与郭汜等权臣合作,接受了州牧的册封。《后汉书·刘表传》载:“及李傕等入长安,冬,(刘)表遣使奉贡。(李)傕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以为己援。”[13]2420-2421陶谦也是在常常“朝贡”李傕与郭汜后赢得州牧的地位。史载:“是时四方断绝,(陶)谦每遣使间行,奉贡西京。诏迁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13]2366-2367其他割据地方的军阀亦趁乱而起,无不利用这个便利的政治手段(自称州牧)来增加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袁绍使外甥陈留高干及颍川荀湛等游说韩馥,举冀州以让绍,绍遂自领冀州牧[16]191。初平三年(192),黄巾余部侵入兖州地界,兖州刺史刘岱战死,济北相鲍信希望曹操能够帮忙剿灭黄巾,派人至东郡迎操领兖州牧[16]9。枭雄曹操利用了这个天赐良机,乘势崛起。武将吕布也是割据一处便称牧。《后汉书·吕布传》载:“(张)邈从之,遂与弟超及宫等迎布为兖州牧,据濮阳,郡县皆应之。……(吕)布自号徐州牧。”[13]2446-2447赤壁之战后,刘备与孙权则互表自领州牧,据《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209)……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16]118盘踞东北一隅的公孙度则“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16]252。
其次,建制后的州牧拥有了在地方上的合法统兵权。由于黄巾余部在灵帝逝后依旧活动于各地,“是时益州贼马相亦自号‘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数千人,先杀绵竹令,进攻雒县,杀郗俭,又击蜀郡﹑犍为,旬月之间,破坏三郡。马相自称‘天子’,众至十余万人,遣兵破巴郡,杀郡守赵部。”[13]2432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州牧统兵扫荡叛乱亦是必须所为,但这是破坏建制之举。在西汉时,未见有刺史领兵之记载,直到东汉情况才稍有变化。一般而言,汉代边郡有事,中央都是派遣将军出战的。据《续汉书·百官志》载:“将军,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10]3563从中可见,将军主要的职责就是征伐叛乱事件的。同书注引蔡质汉仪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10]3563东汉与西汉情况类似。“世祖(汉光武帝)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10]3563因此,汉代一般不用刺史领兵讨伐的,但既用刺史领兵,无疑是遇到紧急事件。既赋予其在州内的军事权力,等同削弱其原有的监察职能。灵帝末年时期矛盾交杂,政治、经济与军事难题迭出,州牧的设置自然可在一州之内便宜行事,迅速解决诸多问题,但必须赋予地方自由募兵、统兵之权。既然灵帝自初未曾想过州牧制度的常态化,自然难言其对既成事实的承认。表面施行分权的灵帝本是希冀通过少数地区的州牧设置来解决政治难题,但偶然的政治事件导致中央权力出现真空状态,更是给予处于困境的帝国最后一击,使其逐渐走向崩溃。
四、结语
至汉灵帝中平五年设置州牧前,刺史职能的内涵出现明显变化。在西汉武帝时,刺史职能仅监察一途。在运行过程中,随着中央权力的改变,刺史尝试在地方获得更多的利益。光武帝后,刺史获得军权和举荐官员之权,且不用赴京师考评,获得从监察权转向行政权的可能,但并非必然,现有之史料多是指出制度的缺陷,背后更值得考察的是中央权力的涣散。若灵帝设置州牧只是在法律上承认州牧在地方上的行政、军事权,那么缘何只是在部分地区进行变革呢?纵观汉朝历史,州牧废置无常,如前所述,“牧”一称呼在汉代人眼中是上古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面临内忧外患之际,灵帝的改制是有所指向的,希冀通过州牧制度在地方上的再建,强化中央政权在地方统治的正当性与神圣性。由于这是一种应时之举措,因此灵帝并不打算将州牧制度变为常规,此乃其一。其二,灵帝希望能够缓解皇权与“党人”之间的矛盾。其三,他还想通过这种措施来镇压黄巾起义余部的活动。尽管灵帝设想完美,并且预期结果理应尚可,但其突然的离世使得州牧制度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州牧的设置并未解决相应的问题,反而促使汉末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因此,尽管灵帝的州牧政策是一种应急措施,但其效果有限,并最终导致东汉王朝政治的进一步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