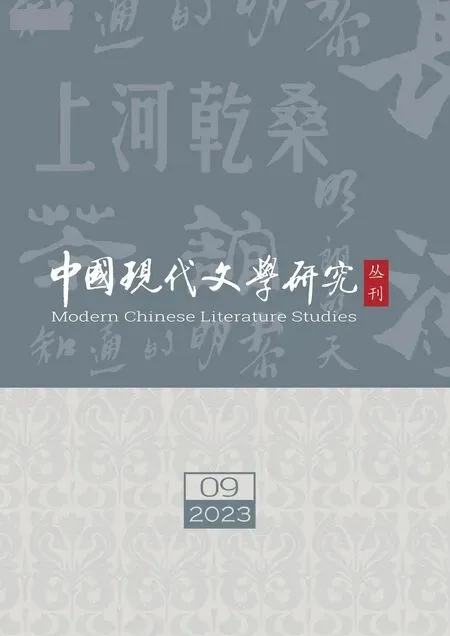契合与错位※
——法朗士《泰绮思》对于京派、海派创作的影响
张 勐
内容提要:拟以法朗士《泰绮思》中主要人物内心“灵和肉的冲突”为切入口,借由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方法,探析沈从文、李健吾、施蛰存、叶灵凤等京派、海派作家的某些创作与《泰绮思》之间的隐秘关联,及其主题范式、人物原型、哲学思辨的契合或变异。
一 复杂的历史意识与哲学思辨:鲁迅、江绍原对《泰绮思》的读解
1935年,鲁迅在《“京派”和“海派”》一文中,借法国作家法朗士《泰绮思》故事,揶揄所谓“京海之争”自论争伊始即是一场欲迎还拒、相搏相拥的伪斗。1鲁迅:《“京派”和“海派”》,《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页。文中,鲁迅自然是在戏说,有意思的是,无意间却触及了《泰绮思》对于京海两派作家其实更为深层、严肃的影响。有鉴于此,笔者拟以小说里泰绮思与修士巴福尼斯内心“灵和肉的冲突”为切入口,借由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方法,探析京海作家与《泰绮思》之间的隐秘关联,及其创作中每被忽略的主题范式、人物原型、哲学思辨的“合流”或变异。意在阐明:《泰绮思》对于京海作家而言,其真正的亲和性,并非信手拈来的文本之外延芜杂人事的附会,空间诗学的异同,而是文本的内在默契。
1924年,江绍原在《语丝》杂志发表《读法兰西氏的小说达旖丝》,最早介绍《泰绮思》给国人。江氏将此书视为“基督纪元第四世纪的最好的史略”。值此古希腊罗马文明将衰未衰,基督教文明之胜利隐约可期之际,从书中犹能听闻希腊时代“怀疑派,爱壁鸠鲁派,斯多噶派,智慧派”的众声喧哗及其对于基督教思想的回应。自然,如同江氏所说,上述史识“必要经过真正文学家的心灵,才完全人化”1江绍原:《读法兰西氏的小说达旖丝》,《语丝》第7期,1924年12月29日。,而修士巴福尼斯恰可谓“希腊的哲学和基督教”冲突融通之史略经由法朗士心灵实现的“人化”。
《读法兰西氏的小说达旖丝》一文引起了鲁迅的注意。鲁迅认为曾研究宗教史的江绍原是译介《泰绮思》的不二人选。原因无他,鲁迅深知“法朗士之作,精博锋利”,唯恐“少年文豪”“不屑译”,抑或翻译时难能有法朗士之笔力刻画出修士肉身的沉重与“内心的苦痛”;唯恐学养浅薄的译者将此文明史上复杂多维的哲学思辨化繁为简,失落了这部小说极其可贵的“历史气”。2鲁迅:《致江绍原(1927年11月20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597页。
某种意义上而言,“修士内心的苦痛”恰恰是作者深层次矛盾的投射。卡尔菲尔特在法朗士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曾谈及:法朗士创作的领域“介于异教和基督教之间”。早在他童年时代,便曾经沉浸于“圣徒传说”中不能自拔,而自然却不时诱惑着他。多年以后,当他师法伊壁鸠鲁、卢克莱茨等希腊哲人的学说放纵欲念,“对圣人的信仰”与憧憬作为童年的记忆依然令其在试图祛魅的同时,赋予圣徒以“染着金色光环”。3《我们为什么忧伤:法朗士论文学》,吴岳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89~296页。在《泰绮思》里,法朗士的思辨是复调的:他既听任那些人格化了的希腊诸神,随心所欲作合理享乐的示范;又让笔下那些希腊文明最后的幸存者们经受着基督教精神的拷问。
论及希伯来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的碰撞、合流,海涅指出:“尽管法国人理解的基督教”最初的教条就是精神高于肉身的“唯灵主义”,可是我们绝不抹杀这一观念对于唯感主义的克制作用。“在这罗马人的世界里,肉身已变得如此肆无忌惮,看来需要基督教的纪律,来使它就范。”1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编选:《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3页。然而,较之海涅历史主义观点之平正,较之卡尔菲尔特授奖词以及前述1920年代江绍原、鲁迅关于《泰绮思》的识见之体贴,此后的某些中外文学史著述却将书中那“介于异教和基督教之间”、人性与神性、唯感与唯灵的多维度思辨,简单化地置换成某种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二元对立、殊死斗争,体现了一种批评的倒退。如苏联学者编著的文学史一味渲染法朗士“怀念远古时代的希腊罗马古风”,而无视作者内心深处由来已久的对于希伯来精神的神往。该著断言:修士巴福尼斯纯粹“像投机商一样,尽可能多地抛出尘世的慰藉来换取天上的金锭”;“由于醉心于基督教的传说”,致使他落入“可怕的悲剧”。2弗·恩·鲍戈斯洛夫斯基等:《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史》第1卷,傅仲选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19页。出于相似的立场,柳鸣九也在其主编的《法国文学史》里认为:《泰绮思》“是一部反基督教的杰作”3梅鸣九主编:《法国文学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与此文学史书写的简单化相应,海派、京派的某些作家对于《泰绮思》的接受也每每失之于寓言化的理解。《泰绮思》中,多向度的“哲学的论辩超过事物的描写”;然而,作品的诗+哲学、充满“历史气”大抵被接受者所过滤,徒剩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故事,一个情欲最终将战胜道学(或贬之为“伪道学”)的主题模式,一个单向度、仅具单一性启蒙意义的寓言。
二 “道和爱的冲突”:海派作家施蛰存等的单向度演绎
1927年大革命低潮中,海派文人杜衡与戴望舒隐迹于施蛰存松江老宅,三人以译书、写作销愁。次年,杜衡译出法朗士的《黛丝》;又过了一年,施蛰存发表了以《泰绮思》为原型的小说《鸠摩罗什》4《鸠摩罗什》首刊于《新文艺》创刊号,1929年9月15日。文中引文均出自该刊,不再一一注明。。作品中,高僧鸠摩罗什所谓“即使有了肉体的关系,只要并不爱着就好了。正如从臭泥中会产生出高洁的莲花来”之自欺式辩解,分明袭自《泰绮思》里智慧派哲人的“在肉体上的放纵不至于有损他的精神上的纯洁……‘你的荒唐赛过粪堆,你的道行是这粪堆上开出来的百合花’”这一诡辩;至于“林里忽然惊起了一个狐狸,用着狡猾的眼对罗什凝望了一次,曳着毛茸茸的尾巴逃走了……他知道这是魔鬼的示兆,当一个虔诚的僧人想入邪道的时候,魔鬼是就会得这样地出现的”那一节描写,也显然是《泰绮思》如下文字“看见一头小豺狗蹲在他的脚前。这头野兽仿佛懂得神父在想什么,它像狗一样摇摇尾巴,巴弗奴斯用手划了一个十字,畜生便不见了。于是他知道这是魔鬼第一次溜进了他的屋子”的影响性再现。
自然,《泰绮思》对于《鸠摩罗什》的影响,并非仅仅停留于描红式模仿的层级,那个诱惑圣僧鸠摩罗什的风尘女子妖媚的女体,如同泰绮思原型从西方到东方、从基督教到佛教背景的一次东移,重演着“圣僧的诱惑”之母题。
爱欲如死一般强。鸠摩罗什寂灭举行火葬时,唯有那个遗留着对名妓孟娇娘意淫之刺激以及妻的亲吻之记忆的“舌头没有焦朽”,作为爱欲的象征,替代了宗教信仰的“舍利子”。恰如李欧梵所指出的:《鸠摩罗什》并没有展现爱欲“和宗教之间的强烈冲突”,至少不是“《泰绮丝》中的牧师永恒地在灵魂中经历和爱欲的抗争”。在施蛰存的小说里,“把弗洛伊德的‘未满足’转换成了‘文明’本身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它代表了施蛰存对‘五四’‘性解放’的回应”。1李欧梵:《上海摩登—— 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173页。是的,《鸠摩罗什》里爱欲和宗教之间的冲突远不及《泰绮思》那般强烈,那般深刻,因着施蛰存缺乏法朗士那种终极信仰的根深蒂固与沉重负担。相对“自由”的他便得以以其纤笔,轻灵(抑或“轻浮”)地将“五四”的反对旧道德思潮导向不无偏至的“性解放”角度。
叶灵凤的小说《魔伽的试探》亦是同类之作,其中佛门修行者难以抵挡“白晳晳的”“少女的裸体”,满以为其修炼足以替少女割去“肉尾”,却未料其实受伤的是自身的孽根。如果说,《鸠摩罗什》旨在诠释“道和爱的冲突”,爱欲终究战胜道行;那么《魔伽的试探》也如出一辙,立意图解所谓“魔念”乃是“自内勃发的人类的本性”,终将撼动“道心”。2叶灵凤:《摩伽的试探》,《现代小说》第1卷第5期,1928年8月7日。溯其创作的缘起,显然也与杜衡等人的亲密往来有关。
至于此后施蛰存等倾向的感官享乐的唯感主义观念渐次与其偏重叙述者感觉的形式追求相融合,而派生出文学史上的新感觉派潮流,这自然是后话了。
三 “灵魂的塞壬”:京派作家李健吾的唯灵之维阐发
《泰绮思》对于京派诸家也多有影响。朱光潜曾援引《泰绮思》描写修士“灵和肉的冲突”为例,剖析“一般宗教家的心理”,并印证弗洛伊德的意识与“隐意识”学说1朱光潜:《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观》,《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28页。;而众所周知,李健吾更是心仪法朗士,他的关于批评是批评家“叙述他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的主张与追求皆源自法朗士。2李健吾:《自我和风格》,《李健吾文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法朗士对李健吾的影响如此深刻,却因他的著述未曾提及《泰绮思》而成为既有李健吾小说研究的盲点。倘若拉开视野,恰可发现这一曲径通幽的影响轨迹:李健吾曾饱含感情地译介并撰写长文评析一部与《泰绮思》同构的法国小说——福楼拜的《圣安东的诱惑》。3李健吾:《〈圣安东的诱惑〉跋》,《李健吾文集》第10卷,第319页。西方评论家(如格里尔森)每每将二作相提并论:“在《苔依丝》和《圣安东的诱惑》中,阿那托尔·法郎士与福楼拜以一种学问、想象、心理和讽刺的微妙结合产生的效果”,其他作家难能接近4文美惠编选:《司各特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而柳鸣九也曾指出:“《苔依丝》深受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的影响。”5梅鸣九主编:《法国文学史》(下册),第348页。
圣安东与《泰绮思》中的修士巴福尼斯脱胎于同一西方宗教人物,只不过圣安东的诱惑是诸多有形无形的具象、幻象,适可谓一部法国意味浓郁的“神曲”与“浮士德”的合体;而巴福尼斯面对的诱惑则凝聚、幻化为泰绮思一人——“这是一位圣女的幻像”,抑或“是从魔鬼那里来的”6法朗士:《黛依丝》,傅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页。……《泰绮思》中,修士的现世试探大都源自“幻觉”形态;与之何其相似,李健吾也尤为关注《圣安东的诱惑》中所谓“诱惑”“都是以梦的形式出现”——“这是灵魂的塞壬;她唱,她喊;你去了,你再也回不来”7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李健吾文集》第10卷,第154页。。就这样,《圣安东的诱惑》以及《泰绮思》诸作教会了李健吾在小说创作中如何以梦幻体的形式,着重表现“灵魂的塞壬”的诱惑。较之前述海派作家偏至于唯感之维一端的演绎,李健吾偏重唯灵之维的阐发恰可谓一种矫枉过正。
李健吾的长篇《心病》悉心刻画男主人公陈蔚成的时代忧郁症。一介寒士身陷城市,“呈在眼前的十九带着淫欲色彩”,于是,一种“不可满足的欲望燃灼”着他,令他变得“那样猥鄙、那样绝望”。这忧郁或许源自社会的压抑,“或许大半由于性欲的压抑”。而早逝的芳便是主人公“梦中的女孩”,“永久活在”他的心里,挽住他“下沉的灵魂”;新妇绣云则是陈蔚成肉欲的随物赋形,不时幻化为“姿态多妖冶”的诱惑的“罂粟花”。1李健吾:《心病》,《李健吾文集》第5卷,第390、399、480页。这自然使我们联想起泰绮思,时而俨若梦中的圣女,时而化身为情欲的“罂粟花”。
而《最后的一个梦》则描写,初恋女孩死去经年却依旧隐伏在知识者“他”的潜意识界,令他“入魔太深”,遂开始寻觅“美丽的女性”之旅。借助“梦的形式”,寻梦者似乎找到了“她”。“她”似梦似真,周身披着“虚构的彩霞”,“又嫩又甜”的“红嘴唇”却明白昭示“我是你的”;然而,那脸又好像不是他“所醉梦的”,别有一种作为“灵魂的塞壬”原型超乎于红唇之象的神圣气息。她“是净罪所,在这里我可以洗涤我尘世的业障;是天堂,我可以息止我的彷徨”2李健吾:《最后一个梦》,《李健吾文集》第5卷,第249页。。如同《泰绮思》希伯来语境里关于罪与救赎、沉沦与升华的思辨灵光。
四 “神在我们生命里”:京派作家沈从文的申说与思辨
已有研究未曾发现《泰绮思》对沈从文《摘星录》《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扇陀》等小说的影响,殊不知其中或显或隐留有渗透的印记。
沈从文曾谈及《摘星录》受过法朗士《红百合花》的影响。研究者遂按图索骥展开比较,却忽视了沈从文在小说中借由红百合意象,不仅追步法朗士细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位”3沈从文:《生命》,《沈从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彰显《红百合花》式的都市女性的爱欲征逐;还包含以潜在层面频频出现的叙述者抵御诱惑的恐惧,折射《泰绮思》故事原型——“我摘了一朵带露百合花,正不知用何种形式称颂这自然之神奇,方为得体,忽然感到一种恐惧,恰与故事中修道士对于肉体幻影诱惑感到恐惧相似”4沈从文:《摘星录》,《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369页。。值得注意的是,《红百合花》里并无“修道士”这一人物设置及其故事,《摘星录》的上引文字适可印证所受《泰绮思》之影响。《看虹录》也在后记里谈及意在挑战“社会中那个性的道德的成见”对于爱欲的压抑,针砭“二千年前僧侣对于两性关系所抱有的原人恐怖感,以及由恐怖感变质产生的性欲不净观,即与社会上某种不健康习惯相结合,滞塞人性作正当发展。若五四以来这方面观念健康一些,得到正当的发展,民族品德亦必能重新见出原有的素朴与光明”1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令人联想起《泰绮思》中隐修士“性心理的畸变,意淫,虐人自虐”。
沈从文的小说《扇陀》依循《泰绮思》修士难敌肉体诱惑终神魂颠倒之原型,悉心将佛经故事《智度论》“加以改造”2沈从文:《月下小景·题记》,《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216页。。他不仅逸出《泰绮思》母题中“肉体”实乃“幻影”这一意淫,也一反《智度论》底本“性空幻有”的出世思想,而以扇陀“纤悉毕见”之肉身,尽显性的实相对于修士之诱人魅力。小说叙说某隐修士一日忽无端咒罚国境不许落雨,国家渐起恐慌,国王为此征募对策。有女子扇陀应诏,称:修士虽几近成圣,毕竟仍留存着“半神半兽”的天性,而既然修士“灵魂骨血,杂有兽性”,自己便有办法将其征服。遂对症下药,邀约三五美人“半露白腿白臂”,或身穿“单薄透明”长衣,“以激动仙人,使这仙人爱欲,不可节制”,频露傻相。仙人“神通既失”,国境内即刻大雨。3沈从文:《扇陀》,《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253~274页。
与施蛰存《鸠摩罗什》、叶灵凤《摩伽的试探》相似,《扇陀》也过滤了《泰绮思》中修士灵肉搏战的苦痛,而代之爱欲的挑逗与激活一类轻喜剧。结尾修士“一切法力智慧”在扇陀面前消灭无余,甘愿“充作坐骑”之叙说,形象演绎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东方化寓言,却又一次落入海派反复表现过的情欲战胜道学的俗套,彰显出京海作家接受《泰绮思》时的一度“合流”。只不过海派文人缘于未能脱出“中国人的想象”传统,笔下那些泰绮思型“裸体的女人”掺杂了一些轻薄趣味与狎亵目光;相形之下,“爱欲”化身扇陀纵然肉体透明无蔽,纵然邀约隐修士同浴嬉戏,却因其脱胎于作者源自边地文明的原始蛮性与天体观,未曾沾染汉儒文化固有的性欲不净观,反倒显得自然而然。王德威称:在沈从文的“浪漫小说中,爱欲时常现身于孩童般的天真之中”1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诚哉斯言!唯其生命哲学、审美趣味的“天真”,助成了作品格调的“无邪”。
如果说,1930年代以《扇陀》为代表的系列作品取材于民间故事化了的记载,犹不失乡野的自然、清明;那么,同样留有《泰绮思》影响痕迹、写于1940年代的《摘星录》诸篇,则是一度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在反城市中完成了自己的城市化”,“逐渐地与原来异己的城市环境认同了”后演绎的城市化的“两性之战”。2李书磊:《都市的迁徙——现代小说与城市文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遥想扇陀何其“坦然”无蔽,而回看《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里那些城市女子“肉体的造形”,却无一不遮掩着梦的暧昧轻纱。
布拉格汉学学派的代表学者马立安·高利克曾将《看虹录》诸作视为“《雅歌》对沈从文作品之创造性影响的最佳范例”3马立安·高利克:《翻译与影响:〈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刘燕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175页。,笔者却觉得高利克未免有些高看了《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诸作对《圣经·雅歌》的“创造性”转换。《雅歌》原是流传于民间的谣曲,编入《圣经》后即便未必尽然升华为表征“神人相爱的比喻”4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6页。,毕竟以其天真无邪彰显了“神在我们生命里”之寓意。如果说,沈从文的《月下小景》《月下》《神巫之爱》诸作曾以湘西民族文化特有的纯真性、民间性去接近同样纯真、民间的《雅歌》并产生共鸣;那么,到《看虹录》时期,已然失却了边地文明的“通灵宝玉”、变身为“有极好教养的年轻绅士”的叙述者,曾经的论敌的“性欲不净观”也在自身“心上占绝大势力”,故不得不以所征引的《雅歌》之圣洁来中和情挑色诱的世俗性。然而《雅歌》那种爱情抒发,自有其源自民间、山野的特定空间与语境。一旦被贸然移入都市,移入闺阁,难免会沾染几分都会、闺阁性意识的狭邪气息。
同理,沈从文受其影响的《泰绮思》“故事发生在一个高于或前于普通时间的世界中”1吴持哲编:《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尼罗河两岸的沙漠旷野,亚历山大的街巷花园,均连通着天国的阶梯与空间。尘世与天国、普通时间与神话时间两相照映,构成了小说所兼具的写实意义与寓言品性。这也许便是沈从文在小说中频频征引《雅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心存宏愿,企图将《看虹录》所凝视、定格的世俗时间——“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因连通《雅歌》古老的希伯来文明渊源而同时被纳入宇宙时间中,完成一个境界更其阔大的意义循环。然而,沈作中复沓出现的《雅歌》喻象、神性话语未能尽然沉潜于叙事深层,今事与古典、具象与抽象未能更其有机地统合,从而使“故事发生在一个高于或前于普通时间的世界中”。就这层意义而言,《看虹录》诸作只是《泰绮思》的浮华倒影而已。
如前所述,法朗士试图以希腊-罗马生命之美来滋润现代社会人性的干瘪,泰绮思有言:“把这个厄洛斯像保留下来吧”,“因为爱神本来就知道向天国的思想上升的”。2法朗士:《黛依丝》,傅辛译,第125~126页。文本中,泰绮思本身即是那希腊文明中“爱神”(准确地说应为“爱欲之神”)的化身。沈从文也从其脱胎的湘西世界的自然生命形式出发,去接近、铸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3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第2页。,以救正现代都市人性的“阉寺”。恰如解志熙所诠解的:“此时沈从文所谓‘人性’,实际上仍以他先前念兹在兹的‘爱欲’为根底。”4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看虹录》书中书题词:“神在我们生命里”5沈从文:《看虹录》,《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328页。,开宗明义点明了沈从文一度独尊自然人性的爱欲观。何谓沈从文文化辞典中的“神”与“神性”?有研究者对沈从文所标榜的“神在我们生命里”之观念望文生义,据此对他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作过度阐释。为此不妨细读文本,探究沈从文此题词的本意。
《泰绮思》曾将爱神泰绮思的胴体比喻为“就像一座美丽的雕像”,《看虹录》也以“古代希腊精美”的雕像来形容作者心目中“爱欲之神”的胴体。毋庸置疑,此处沈从文不过是借爱欲之神所凸显的肉体之精妙,来体悟“上帝造物”之完美。这一诠解自可从沈从文申说人性论与爱欲观的文论、散文中觅得佐证。如《美与爱》里,沈从文称:“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1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59~360、362页。
借助“神在我们生命里”这一引言,那些“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女子”的“肉体的造形”在“有学问”的绅士的窥探与想象中俨然已为“爱欲之神”,却未及深究“这些肉体中的灵魂”是否“有光辉”,能否化身为“清明无邪”的象征。2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06页。而《泰绮思》中修士肉身的沉重与“内心的苦痛”,在此时沈从文的笔下也异化成绅士与淑女“诱—拒”委婉轻巧的叙事游戏。作者有心将“性欲不净观”放大为人类的“文明病”与“都市病”,于是这两性之间不无矫情的诱和拒,“取和予”,“奖励和趋避”,3沈从文:《看虹录》,《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341、331页。似乎也正当地被寄寓了疗救人性病症的意义。然而,在这远离湘西自然人性的都市世界里,真能借那尊“艳丽与完整”的爱欲之神来重觅生命的肯定?作者的答案显然是犹疑的。《看虹录》《摘星录——绿的梦》诸作无力承担由美与爱的发现进而“发现了神”的题旨,无力建构“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更无力承载起“国家民族的重造”这一不无沉重的使命。4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全集》第17卷,第359~360、362页。
解志熙称:“30年代的沈从文所谓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爱欲’的替代性概念”,“只是如今经由周作人等京派大佬的影响而吸取了古希腊‘灵肉二元均衡统一’的人性理想”。5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如其所言,在名篇《人的文学》里,周作人曾提出“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之箴言。6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学步京派大家,1930年代及至1940年代沈从文的人性论或爱欲观中,明显可见私淑以周作人为护法的“人的文学”理念之处。而其要义便在于“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7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494页。。在宣泄人性解放、爱欲冲动的同时,毋忘神性(沈从文对此自有其超越宗教语境、更为独特的理解)对人性(或谓“魔性”)的适度规约与升华。
沈从文的《第四》便是形象地阐发了以上理念与追求的代表作。小说描写某朋友试图引诱一位美丽的牧师夫人,牧师夫人也沉浸在偷情的享受中难以自拔,而一场车祸却使她的心灵重新调整了灵与肉的失衡。知悉妻子出轨后,牧师不仅悉心照料妻子,感情上也极度体贴。他只说妻子的“自由并不因为嫁了他而失掉,但应当明白的做一切负责的事情”。朋友终于醒悟自己“只是用一种热情来把女人的身体得到,那无限温柔的心,还仍然是那牧师的”,遂落败而逃。徒有渔色猎艳、“俊辩雄谈”技能的情圣,终难敌牧师那“悲悯博大的精神”。道成肉身,如果说《泰绮思》里那狂热的修道士度人虽果,却自坠深渊,那么《第四》中这位平凡的牧师式的度人显然更“有道行有魔力”。1沈从文:《第四》,《沈从文全集》第5卷,第149~150页。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曾几何时,海派作家连同受其影响的沈从文一度将《泰绮思》中神魔统合的复调思辨化约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公式演绎,却在《第四》里以他对神魔对立统一说那有情的致敬、拥抱而颠覆了这一公式。尽管1940年代缘于历史的不安,精神的迷乱,生命的焦渴及痛感,沈从文其人其文每每临于“‘常与变’、‘进与退’之困局”2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他的“人性试验”诸作在展开神性与魔性维度的辩证时,也每每出现畸轻畸重的失衡;然而,《摘星录》《看虹录》毕竟像《泰绮思》那样,在“追究‘生命’意义时”,也开启了关于“情欲和爱,怨和恨,取和予,上帝和魔鬼”之类的哲学思辨3沈从文:《看虹录》,《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341页。,并潜在地意识到爱欲之神不能徒有“肉体的美丽”,“精神必尚有力向上轻举”4沈从文:《摘星录》,《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373页。,于自觉非自觉间呼应着《泰绮思》两希文明冲突交融、神性与魔性之维相克相生的主题。
——读《图像与爱欲:马奈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