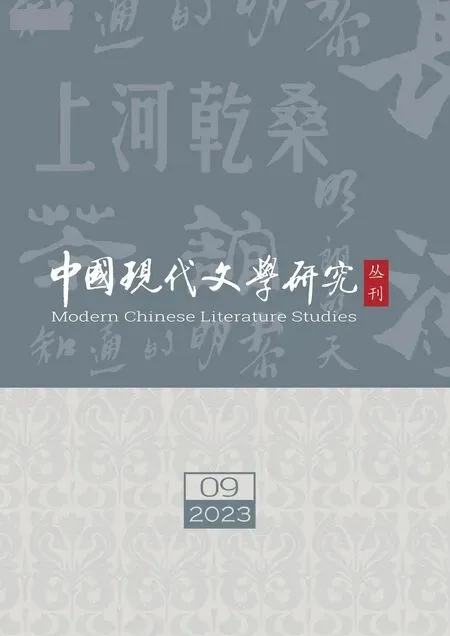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家园意识
高志栋
内容提要:地缘意义上的“家园”与文学意义上的“家园”,在现实纠葛与理想层面形成了一种异质合构的辩证互补关系,海外华文文学对生存图景的总体把握,为学界提供了观察家园意识的新视角。将文本置于“家园”语境中进行系统考察,探讨新旧家园意识的化感通变以及由此生发的文学意义,紧扣“乡土家园”“文化家园”“精神家园”的层次递进,解读作品文本展示的审美世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突出和彰显“中国故事”的海外言说,无疑具有积极的建设意义。
海外华文文学,若从1910年美国华工刻写在加州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汉语诗歌算起,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100多年来,海外华文文学之内涵与价值已经超越文本本身,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兴纽带,呈现出与传统中国之现代性变革相关联的特点,学术研究也从单一的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转向,“家园意识”是其中一个重要窗口。作家的行藏和笔触的神游,构成了富含个性化的文本空间,由此披露出融会中外文化元素的“家园意识”,亦可视之为异质合构的文本创制。它是海外华人生存活动的审美投射,也是作家创作之根脉在新语境中的生发。其间有一系列的伦理考验,也有生生不已的人文和合,使得流布于海外华文文学文本中的家园意识炽热而浓烈,抓住家园意识,就等于把握住叩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之门的一把钥匙。
一 文本语境中的家园意识生成
根据陈贤茂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中提出的文学概念,海外华文文学特指“中国(包括台港澳)以外的国家或地区,用华文(汉语)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文学作品”1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史》第4卷,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从文学地理学论,海外华文文学问世伊始,就是一种开放的跨界文学,将之理解为异质同构的精神产品,也是恰当的认知。确切地说,其是在包容与磨合、挤压与放达中形成的新文本,是多元文化衍生出的新语境,是海外华文作家在审美差异性方面的创作实践。一如所有文学创作及其理论生产一样,海外华文文学的“文本”与“现实”之间具有一种审美关联:一方面,“文本映现的是作家从历史和生活中提炼出的文化‘世界’,即使这个文本中的‘世界’是‘虚构’与想象的产物,也必然反映一定的社会性真实”2倪文尖:《文本、语境与社会史视野》,《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这种真实是通过特定的时空达成,比如此时与他日、本土与异域,即经由故事发生的场合展现,此所谓作品生成时“文”与“世”之间相摩相荡的关联性“真实”;另一方面,文本表现了作家丰富的知识积累、心理感受、思想探索与情感体验,包括审美意识与潜意识以及无意识之间的根脉性牵连,这是一种在创作中运行的精神性活动,有时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有时文思泉涌、新意迭出,吸纳且整合着作家脑海中的所有积储,包括边缘的、离散的、杂合的、多元的、内在化了的诸多元素,缘此创造出蕴含故土新地复杂文化的“家园”范畴。
无论是从认知立场还是从问题意识的角度切入,文本显然都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首当其冲”的部分。文本的字里行间都体现出作家奠基性的劳作,从文本出发,最终回归或落实于文学作品,说明文本在文学现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或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当然,海外华文文学“文本”,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包括具有世界性视野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和评论著作共同构成的文学形态,其生产受到文学所属的文学史谱系、受众反应与期待以及时代语境的共同影响,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家园意识”,作家在文本中总会预设一个不言自明的“家园”,这个“家园”往往通过艺术的想象来还原饱满的“现场”及“瞬间”,进而在身份、情感等“感觉结构”上呈现活泼、充实的存在价值;这个“家园”同时也是需要受众接受的文本,是通过文学的“注释”来阐发的特殊“思想情感”,在此意义上,“家园”不是外在的,而是“以文为本”的内生需求,也是生产和接受文本过程中必然关注的焦点。从海外华文文学早期在“他者文化”影响下的离散书写,到“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实践,包括其他非典型性的文学试验,其核心内涵均是文化的交叉与融合,即体现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的“跨界性”特征,隐含了一条“家园意识”流变的线索。围绕这一线索,文学文本践履了“跨界性”,文化语境也相应地“文本化”,文本与语境的交叉契合,实现了文化与审美的心物合一。
在文本、结构、意象、语境等诗学诸类相摩相荡的当下现实中,显山露水的往往不是罗织文学创作的技术门径1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5页。。因此,我们追问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须在文学的本根处着眼,即从文学与大道同启蔽、与命运相错杂的契合点上追索,而作家不忘故乡又植根新土的超界域“家园意识”,显出海外华文文学自成一体的独特格调。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海外华文文学生长于非本民族文化圈内,因而对于多元文化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黏合力,作家不仅永葆乡土家园经久不衰的本色,又演绎了行走世界时运交移的新陈代谢,通过阐幽抉微的“家园”经纬,文本深入人们的心里,甚至侵入潜意识领域,既消弭了某些“无法化约的政治复杂性与历史褶皱面”2吴晓东:《释放“文学性”的活力——再论“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2020年第5期。,也补充了文学叙事力所不逮的感性与经验场景。开阔的“文化视野”加强了对文学潜能的关注,展示出文本所蕴藏的单纯的“文学性”所无法呈现的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外华文文学中固有的“家园意识”大都具有得天独厚的特点,即“知”守其本、“情”植其体、“意”获其志,“知”“情”“意”都在文学与文化的共通性视野中,进一步拓展了新的“阐释空间”,得以在文学性的时空中显形赋形。作为背井离乡的文化人,海外华文作家都是辞乡去国、远徙异域的游子,他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飘撒在陌生的疆域。他们的文学,也与他们的身家性命一样,从单质和边缘走向杂合多元的新的文化环境。不难理解,海外华文文学诞生伊始就走上了一条寻找和建设“家园”的道路。因而,“家园意识”的引入和深入研讨,可以揭开这一特殊文学领域的生成性奥秘。
质言之,“家园意识”研究是伴随着海外华文文学文化研究转向,自觉形成的一种学术批评,呈现出“文本”与“语境”交叉的研究路向:寻找“语境”的过程即是寻找“家园”的过程,“语境”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现象不单单是进入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与视角,更是从话语机制层面构成理解这一文学样式的基础。因此,对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家园意识”研究不能停留在一般性的文学批评层面,而必须关注文本背后的主体身份,及其所处的多元文化语境和这种语境反过来对于文学表达的影响,更加集中地认识到“语境”与“文本”之双重价值,就研究方法而言,“家园意识”不仅能从客体层面把握海外华文文学文本,也能从主体层面把握作家的身份,真正实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创新。
二 文化迁衍中的家园意识溯源
人类的“家园意识”由来已久。从中西方哲学思想中追溯源头,《易经》可谓最早的一支,这部中华原典以天人关系为核心,揭示了“好生为德”和“生生不已”的上古生存智慧,阐释了东方“生生之为易”的海量胸襟与寰宇气象,蕴含着哲理性的化感通变,直逼天人通衢,透“几”入“神”,堪称探索“家园意识”的宏构伟制。其乾、坤二卦中关于“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27页。、“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2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27页。的论述,道出了天地生态作为人类生存之本的“自然家园”,千百年来为华夏文明提供了旷远迷离的时空背景和博大精深的存在场合,广袤的神州大地给予了中华先民繁衍生息的“家园”,使之完成氏族提升与文化启蔽,构筑起一个永远无法穷尽的精神后台;而《易经》二十四卦之“复卦”则概括了“易者变出”的东方哲学思想,阐释了万事万物必然回归根本的规律,展示了后天性的“人文家园”思想,是人文精神的耦合,属于在历史长河中提纯的“根性文化”,无论是审美的文道合一还是哲思的天人合一,“本根在兹”透露出的是对禀赋的虔诚,回归本根的运动,在终极意义上是一个过程,万象一收,浑然一体,不仅打破了文化疆域的界限,更是悬置了人生得失的佯谬,在不同地域酝酿趋于通化的映带,在深沉的灵肉古今与绵长的世情因缘之下,“家园”成为永远鼓舞中华民族迎接破茧化蝶和浴火重生的命运磨炼。因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家园意识”不仅有表层的“归家”之意,更有深层的阴阳复位、回归本真的存在之意,包含乾行坤载的奥秘,披露天人互动的底蕴,具有“肇自太极”的自然文化与人类文明契合的哲学内涵。
西方哲人智者对“家园”的思考也一直没有中断。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是西方“家园意识”概念最为强烈的哲学家之一,“家园意识”即是其存在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1927年,海氏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围绕“人之此在与世界”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2,1305、1312,282页。的在世模式,论述了“此在在世界之中”的意蕴,认为其中包含着“居住”“逗留”“依寓”,即“家园”之意,其强调“按照人类经验和历史,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有从人有个家并且在一个传统中生了根中产生出来”。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2,1305、1312,282页。是“此在与世界”“人与天”因缘性的呈现,代表了具有本源性的哲学与美学关系。但是,我们也看到,“家园”不仅仅是美好的、诗意的栖居之地,也是血泪书写的记忆:《圣经》将人类的无邪之家安顿在伊甸园,把上主的“应许之地”指画到耶路撒冷,实际上伊甸园中的邪恶与生俱来,“应许之地”至今杀伐不断;《奥德赛》是一部“归家”史诗,然而家园变故频仍,“家”成了恶斗的场所。毁人家且破人国的惨祸莫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日、意轴心国对世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文学史上不少品种顿失、显学湮灭和思潮消逝的谜团背后,隐约可现的往往是旷古罕见的文化灾区,“家园”在这一刻不仅需要应对文明恶化时的危机,更要与人为制造的文化隔膜分庭抗礼,面对暴虐,“家园”不是永恒的泯灭,而是含天抱海的守寂,是斗移星转的取静,是蓄势待发的冬藏,是东山再起的前奏3栾栋:《文学通化伦》,第234页。。
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跨界”的在地化书写,对于“家园”的认知有更加深刻的文化思考,“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同时也反对一体化整合的‘文化大同’思想,推进人类文化多元互补的和合启蔽”构成了21世纪海外华文文学重要的创作理念,这种理念基于祥和的创作,没有宗教恫吓,更没有“攻城略地”的恶嗜,而是海外华文作家继承了中华民族美善“家园”母题的“诗意栖居”,立于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下,呈现出美学意义上的个性化与递进性,从历史的变迁与时空的转换中,书写华人去国辞乡、负笈海外、域外谋生的艰难世事,描摹其心路历程和文化身份。但显然,海外华人作家重塑“新家园”的过程是艰辛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是被抛入特定社会的存在。”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2,1305、1312,282页。而命运正是那双看不见,却可以操控一切的巨手,在命运的“棋局”之上,作为“棋子”的海外华人即便是刚强柔韧、不屈不挠,即便努力想做落子的“施动者”,却似乎很难摆脱“被动者”的命运,在本质上仍然是被自然、造化、命运、社会、环境所抛之子,很难从自我与他者、故乡与新土的复杂“身份”中跳脱出来,独善其身,命运的起伏波澜使他们在思考如何认识“家园”的过程中,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这种选择,无非就是与存在状态的博弈,披露了个体与命运的纠葛,揭示着海外华人对于生存缺陷的不甘与补苴。由此论之,我们发现紧承东西方哲学思想的阐释,将“家园意识”引入“文学性”的话语批评范畴,或许能够构建起一种与跨族裔、跨地域、跨文化的文学范式相契合的新视点,观照处于这一文学范式中“被抛”和“断裂”生存状态中的海外华人对自身的寻根以及对存在意义的追寻。
三 文学创作中的家园意识流变
海外华文文学有两个端点,海外与华文。“家园意识”是沟通两者之间一个重要的交集之处。对于作家而言,“家园意识”是精神的烛光和灵感的渊薮,他们以笔为犁,耕播了在异国生存的善的“种子”,勾勒出在他乡扎根的海外华人个体或群体肖像。他们与所在国原住民始而求同存异,践履文化互补,继则相依为命且和衷共济,共同打造休戚与共的此在共在的“家园”;对于评论者来说,解析作家作品的“家园意识”,需要在两端交集之处擘肌入里地探索,论证海外华文文学“由他化而来,并化他而在,且通化而变的‘兼他性’生态”1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3、204页。,一如地下蔓延的根茎,莽原无心的游牧,不但克制了此在的我执,并且预留了他者的下家,2栾栋:《文学通化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3、204页。“家园”于海外华文文学而言,不应只是被界定为静态的森严壁垒,更应被视作盈科而进的交流兼合,才不致陷入自我封闭的象牙塔或死胡同。但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家园意识”嬗变研究付之阙如的现象客观存在,大量研究聚焦于作家与作品的“乡愁”表达以及“离散”书写,对全球化语境下,新“家园意识”的生成、更迭与确立缺乏深入肯綮的论证,疏忽了文本渐离伤痕与反思的文学新貌,未能有效把握“家园意识”在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特征。
针对以上研究现状,需要指出的是,海外华文文学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递嬗现象事涉生存、情系世态,揭示的是从“乡土家园”到“文化家园”再到“精神家园”的文学与文化身份互动机制1江少川:《全球化语境中“离散”与家园写作的当代思考》,《华文文学》2019年第1期。,其继承了“家园”母题丰富的内涵,从历史变迁与时空转换中,窥探出华人走出家园、负笈海外的心路历程以及文化身份的形塑。通过对“远行”“背影”“飞鸟”“漂流”等不存在文学普适性的“家园”意象梳理,可以发现特有的诗学内涵与文化意义,揭示了“原乡”与“异乡”的辩证关系。在文学文本中,“家园”的“原生态”与“新生态”,均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两者之间的嬗变过程一方面隐喻了作为文化个体的“人”向“他者”不断流变的现代性趋势,逐渐演化为“文化家园”与“精神家园”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毫无保留地呈现出对“乡土家园”的怀念,以及悲悯的道德情怀、严肃的人性追问及坚定的自我救赎等传统的“家园意识”形态。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它们在不同的文学表达中反复诉说的相似的心理诉求,使得“家园意识”不仅继承了既有的文化意义,同时也吸纳了新的现实话语,从而使自身不断得到丰富,具有超越世俗的精神意义。“流变论”尝试对“家园意识”的解蔽性投光,从本质上来讲,是超越逼仄的“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关系,突破文学生发与境遇的深层学术关捩,既为文化语境与审美范式的更替提供有力证据,又为搭建新的海外华文文学分期框架提供参照依据。通过对“家园意识”嬗变路径的观察,可以进一步观照海外华文文学长河流衍的最新动态,使之不再囿于某一时空条件下的“成说”,而更加遵从“间性”的对话,对嬗变过程中的文学与文化质素进行全方位的阐释,从而为寻找更广泛意义上的海外华文文学发展规律及不断变化的新特征奠定基础。
(一)乡土家园的形成
早期的海外华文文学,受到传统母体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对“根”文化的审视、反思与依恋,一方面讲述海外华人移居等空间迁徙经验带来的陌生感与不适感;另一方面通过描述冲突与变化所引发的心理震荡来传递海外华人在异国行旅中的身份、文化、阶层等维度扭曲错位的迷茫,表现出作家踯躅不前与转身回望的创作心态,他们对“乡土家园”的认知意识格外强烈,那种被陌生所逼迫的奋起,实际上是一种临界处的挣扎,亦是羁旅之愁的抒发。在文学表达上,这一阶段的海外华文文学多突出“怀乡”与“寻根”主题,叙事内容多呈现对“乡土家园”的思念,叙事技巧趋向平淡与朴素,从形式到内容均揭示出一种传统的“文化归根”现象。文学创作以中短篇小说或诗歌为主,代表作品包括於梨华的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查建英的小说《丛林下的冰河》、聂华苓的小说《桑青与桃红》、苏炜的小说《背影》、司马攻的散文《明月水中来》以及马华文学“天狼星诗社”1天狼星诗社是1970年代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现代主义诗歌团体,其领袖温任平以其笔下的文化中国书写开启了马华文坛的一个重要主题,其诗歌创作以一种现代主义技艺和文化中国主题的交融,体现出从文化乡愁向哲性乡愁演变的趋向。参见金进《通往哲性乡愁的途中——以马华天狼星诗社的中华文化书写为分析对象》,《汉语言文学研究》2020年第3期。成员的诗歌创作等。由此可见,早期海外华文文学的“家园意识”是单向度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2刘勰:《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欲近而常相远,表现了侨民“逐梦之后”的精神困境,“在他乡”的书写依然难以脱离“乡土之梦”,其被民族历史的精神负累所束缚,受制于本土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的强烈冲突,试图以文学之名的“笔触”划破地域的“围城”,回到乡土的家园。
(二)文化家园的演进
考察“家园意识”之演进,必然涉及身份重建与文化认同,随着海外华人日益融入现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其主体意识亦在不断发生改变,文学表现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它不是一般所说的文学创新,而是于歧异中吸纳众流,彻底地改弦更张。由此导致海外华文文学在保持原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同时,开始植根不同于“乡土家园”的文化空间,显示出一种新的“文化家园意识”,这一海外华文文学主体意识的转向,揭示了新一代移民从身份桎梏中跳脱出来,对异质文化的理性审视,其“家园意识”也在文化认同的趋势中,自觉形成了一种新的稳定性和适应性,试图通过文学视角构建一个包含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海外华人垦殖拓荒移民史与个人命运史交融的庞大历史图景,梳理出一条“异乡”变为“家园”的文化流变路径,代表作品包括曹桂林的小说《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王周生的小说《陪读夫人》、张翎的小说《交错的彼岸》、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陈谦的小说《无穷镜》等。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对现实性的关注,艺术表现形式不断创新,趋向兼采,重视象征,大量符合时代特征的海外形象与异国故事诉诸文字,呈现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合流思潮之特色,从思想赓续和体式兴替背后的哲理来讲,这是后起之秀对西方主流思想的抗争,是对传统“家园意识”的挑战,意味着审美趣味的改变,释放了无限的文学潜能,用平等视角讲好中外故事,在本质上冲淡了回归原乡的渴望,颇具多元文化交融之景观。
(三)精神家园的构建
在差异性逐渐弥平的信息化时代,人类正在经历迁徙、再迁徙甚至多次迁徙的“行走”状态,“家园”概念随着地域转换及多族裔共存原则,逐渐由文化的单一性向多元化转向,并汇聚起最为复杂的人类经验,尽管这种经验获取的背后往往伴随着无数家国破灭或种族屠杀的历史嗜血,其中也有中华民族悲辛的记录,但是大批华人远徙图存,脱开原发地,在地球的彼岸讨生活,在精神的空灵境界中寻寄托,其突破生存危机的战略转移,亦使得文学“他化”式的创造有待来者。于是人们发现,当外部世界的有限性被一一穷尽时,内心体验的无限性终于为“存在”的深层意义作出了诠释,一种具有新的美学气象与精神气质的“家园意识”随着海外华文文学创作题材、内容与创作方法的衍变自然生成了,新的“精神家园”显然不以国界为明显标记,而是要探索人类的共性与共存,它为“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的全体公民塑造“精神共同体”,为全球化“家园”提供稳定的指向与坐标,为一个“无界的世界”奉献一部正在生长并且能够持续生长的精神史,代表作品包括张翎的小说《金山》《劳燕》,陈河的小说《红白黑》《黑白电影里的城市》,少君的系列网络小说《人生自白》以及马华作家黎紫书的微型小说集《余生》等一系列凭借内心描摹与意识流动抵达人性深处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海外华文文学以独特的叙事方式,着重呈现了故国乡愁的淡化、世界的多元以及文化符码的祛魅等艺术品质,文学在意的不再是区域的故事,而是在艺术形式与精神世界层面探索无限、延展无穷的可能性;同时,对文学不断进行内心化、诗意化的实践,终于使其走向了更加深刻与宽广的天地。
综上所述,人类共同拥有的地缘意义上的“家园”与文学意义的“家园”,在多重文化的记忆与构造中,传递、铸造出更具张力的叙事形态、更具活力的身份观照以及更具“融合性”色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追索。“乡土家园”处于“物理”层面,具有明显的区域标记,该区域大都是双合性的混杂意识,既有故乡情愫牵系,也有新家此土冷暖;“文化家园”属于“身份”层面,是海外华人生存的新理念、新思想,传递的是身份认同的信息,揭橥的是新生活的诸多磨合及其当下性的人我交流场域;“精神家园”则处于“价值观”层面,或者说是超越了“家乡”“外乡”“国界”和身份意识等局限,营建的是人类共性共存的生态环境与通界共美的生活场域。由此构成的“家园意识”如同多重镜像,赋予作品“化”与“感”,“变”与“通”的微妙特质:一方面,通过对存在于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家园意识”嬗变路径的梳理总结,勾勒“自我”与“他者”的共在状态以及生命个体在跨越疆域之后的情感选择,表现海外华人在故国与现居地之间游移的美学思考与心理距离;另一方面,通过对“异质文化背景下多种叙事策略重构与裂变”的观察,提出“海外华文文学在未来极有可能以艺术及文化上的探索,消解民族文化之间偏见与对立”1张娟:《海外华人如何书写“中国故事”——以陈河〈甲骨时光〉为例》,《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的观点。
“家园”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预设了与“理想读者”共享的文本,也可以被想象成一种具有多维度的“语境”形态,同时表现为与文本语境通合且与故园新家交集的审美空间。其与近代以来传统中国的现代性变革,与21世纪中国的文化复兴,与当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的时代标志之间存在着深刻关联。海外华文作家背井离乡,扎根于异国他乡,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园”观,为“家园意识”增添了天下苍生美美与共的观念,推展出了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宏大格局。因此,将“家园意识”引入“文学性”的话语批评范畴,有助于提炼一系列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观念,构建一种跨族裔、跨地域、跨文化的新文论。家国天下,四海攸同。根在梦中故乡,志在异地新居,多元文化和合的新家园,应成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种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