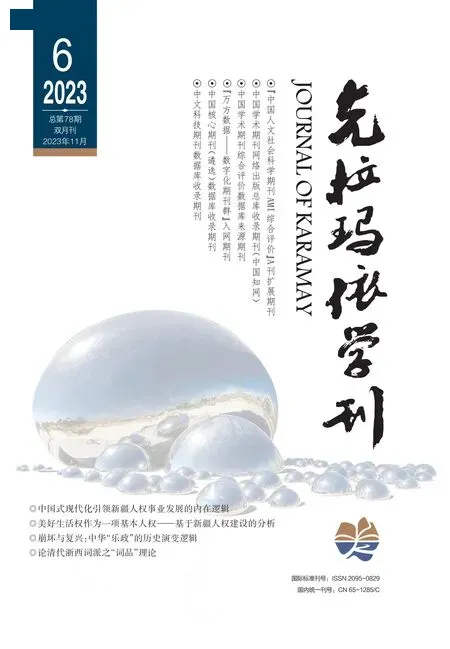《韩瑜墓志》典故书写抉微*
——兼论入辽汉族世家家风的形成
常志浩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玉田韩氏作为有辽一代声名显赫的汉族世家,历来为史家瞩目。但因《辽史》编纂疏漏,我们仅能对韩知古子匡嗣一系有大致了解[1]。幸而随着考古活动的深入,玉田韩氏后世族裔的墓志也渐次刊布,有近20 方,涉及匡嗣、匡美、匡胤三房,基本可以勾勒出韩知古家族的谱系[2]。其中,韩匡美一支如王民信所言:“匡美在契丹之职位并非不崇,而《辽史》中有关匡美一系之脉络竟而忽略,无怪乎受史家之讥矣。”[3]而百年前出土于朝阳县的《韩瑜墓志》补足了这一缺憾,其墓志录文先收于民国《朝阳县志》卷十一,后辑入北条太洋《热河》、松本丰三《满洲金石志稿》及罗福颐《满洲金石志》;又有园田一龟《朝阳县出土韩公墓志铭考》、毕任庸《辽韩瑜韩橁墓铭考证》两文加以考证,其后又有前引王民信《辽史韩知古传及其世系证补》一文再加利用。除考释外,陈述《全辽文》、向南《辽代石刻文编》均有收录,并作校勘。此后李锡厚、薛景平等人也对《全辽文》中的部分录文有所补订。近年来又有刘凤翥等编《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杜晓敏《辽〈韩瑜墓志〉考释》等录文考释[4]。
除上述涉及对《韩瑜墓志》文本本身的讨论外,利用韩瑜墓志研究辽代军事地理、社会风俗、职官制度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由此看来,《韩瑜墓志》似已无后学置喙的余地,但笔者在对照以上诸家录文时发现其中文字多有歧异之处,有碍学界利用。究其原因,一是,属于未见原石、拓本,文献传抄过程中产生的鱼鲁之误;二是,对某些俗写字的误读误识。笔者现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刊布于网上的《韩瑜墓志》拓片[5],参照诸家录文再作校勘,并对志文中所涉及之典故加以释读,为理解墓志所涉及之史实提供方便。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惠示。
一、《韩瑜墓志》录文校勘
(1)故内客省使、检校太傅、赠太尉、昌黎郡韩公墓志铭并序。
前进士郝云撰①。
(2)夫高门袭庆,列爵疏封。雄飞资庙食之文,鹿鸣叶②朝燕之雅。若乃真元③王之胄绪,大建侯之勋(3)庸。继世联芳,载书备简。韩之先与周姓④,武王封于韩原,号韩武子。后与⑤赵、魏灭范,贞子迁之平(4)阳,安王始为六国。自韩之后,因生⑥赐姓,族氏不迁。本大则枝⑦出惟繁,源浚则流长靡⑧竭。拜前封后,(5)从昔至今。宗⑨躅弥昌,豊⑩谍(牒)⑪尽纪。近代则起家于燕壤,仕禄于辽庭焉。曾祖为大司马,英气拔伦,(6)风襟特秀。讨恶助中卿⑫之典,若畴遵祈父之诗。王父讳知古,临潢府留守,守尚书左仆射、兼政事令。始(7)逢昌运,兼绾重权。如萧何独守于留司,孔光不言于温省。列考燕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管内处置⑬(8)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政事令、邺王。石驎禀⑭异,风虎腾祥。文武敌⑮万人之英,将相备累朝(9)之杰。三分上爵,一字真封。忠贞则元后腹心,仁惠则黔黎膏沐。公讳瑜,字,即邺王、夫人兰陵氏之长(10)子也。生而魁伟,幼有端良。雅好大谋,卓闻奇节。趋庭就傅⑯,学诗礼以检身;筮仕勤王,便⑰骑射而(11)成性。应历中,初补天雄军衙内都指挥使。寻诏赴阙,授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右金吾(12)卫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行止可度,必⑱以廉能。夙夜在公,曾非旷怠。景宗皇帝绍位之始,命选禁(13)卫,端求荩臣。以公壮志不群⑲,良图可用,授控鹤都指挥使、绛州防御使、检校司空,寻授金紫崇(14)禄大夫、检校太保、左羽林军大将军⑳。紫庭奉职,耀簪绂以输忠;红斾㉑御戎,森戈矛㉒而称略。迁授客(15)省使,□㉓膺㉔载励,循墙益恭。朝廷嘉之,改授内客省使、检校太傅、守儒州刺史。仁化冶于六条㉕,政声(16)驰㉖于双阙。自任复诏充内客省使、崇禄大夫、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昌黎郡开国侯、食邑一㉗千户、(17)食㉘实㉙封一㉚百户。遇圣明之代㉛,当要重之荣。束带立朝,有仪可效。对扬休命,发言盈廷㉜。洎统和间,以太(18)阶未平,渠魁作孽,曹、米㉝犯境,涿、易屯凶。及贼师既溃,诏公权涿州刺史。实谓当难安之秋,得惠和之牧。(19)次年,昭圣皇帝哀燕民之若子,忿㉞赵氏以如㉟雠㊱。北率天兵,南行国讨。仍观敌寇㊲,据彼长城。筑垒犹坚,(20)横戈甚众。公方当扈从,切在剪除。以夺人为先谋,以亡躯为尽瘁。因俯营擒㊳狡,释铠传宣。攻长城(21)口㊴,俄为流矢中首。然虽抱楚,尚更摧锋。金疮寻发于朝昏,委命几临于泉壤。承天皇太后愈怜忠(22)赤,爱之如母子之慈。皇帝复念旧勋,痛乎竭君臣之义。迭颁医诏,亲视殒伤。呜呼!乐尽悲来,(23)福盈祸构。贤愚并叹,今昔宁逃㊵?以统和五年十一月十日薨于行次,享年四十有二。寻载灵柩(24)而归,权厝于霸州之私弟㊶。皇上以阶㊷爵未峻,赗㊸赠有加,殊锡恩辉,载超伦等。追赠太尉,所(25)以旌忠孝也。国朝深论㊹吉地,凢㊺择㊻通年。邺王、夫人方承天睠,深被国恩,足以崇骨肉之(26)亲,笃家门之孝,率诸昆季,具窆如初。以统和九年岁次辛卯十月丙寅朔八日癸酉,改葬于(27)霸州之西青山之阳,礼也。始娶夫人萧氏,先亡,合祔于此。夫人生九男三女。长男曰越孙,早亡。次阿骨(28)□㊼,亦亡。次骇里钵,亦亡。次宝神奴,亦亡。次福孙,亦亡。次栲栳,亦亡。次三哥,年幼。次四哥,亦亡。次高神奴,亦亡。(29)长㊽女,杨佛喜,早亡。次㊾罗汉女,次堰弥吉,俱在室㊿,尚幼。继室夫人萧氏,诚叹未亡,礼无再嫁。公英雄(30)授爵(51),胆气过人。高贵相承,交游不杂(52)。宜乎萃谠言而致(53)寿,弘茷(54)绩以流芳。奈何过隟(55)兴嗟,临川(56)(31)告逝。必(57)使松楸间植,长(58)滋龟兆之占,陵谷纵迁,尚固牛眠之异。俾营豊(59)树(60),用刊贞珉。其词曰:(32)公之高贵,继世联芳。挺生魁伟,克蕴端良。礼乐是悦,骑射斯彰。历官(61)禁省,効节疆场。挥戈深入,(33)流矢横伤。魂飞战垒,骨归故乡(62)。皇情哀恸(63),宣赠弥光。事君事父,忠孝备昌。万载千秋,芳声不亡(64)。
二、《韩瑜墓志》典故书写所体现的玉田韩氏家风
墓志铭作为一种应用范围较小的题材,其文本格式在隋唐时期就已经相对固定。清人王行说:“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6]以上分析以墓主为纲,详列墓志13 个必备元素,可谓洞见,但却失于细碎,难免掩盖墓志撰者的创作主旨,使墓志成为一种格式化的文章。以本文讨论的《韩瑜墓志》为例,我们不妨另取标准,对志文重新分割,看看是否有新的发现。
众所周知,门第宗族观念在古人心中有着极重的分量,墓志文起首必先列叙祖先世系。笔者尝试从韩瑜世系入手对墓志重新划分,发现在墓志文格式化的语言下面仍贯穿着撰者的创作意图,展现了韩瑜及其家族亦文亦武的特质。
笔者认为墓志文可划分为如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韩氏祖先,其从墓志文开篇到“豊牒尽纪”,记载的是韩瑜缥缈的先世;第二部分是韩瑜父祖,本部分从“近代则起家于燕壤”到“仁惠则黔黎膏沐”,叙述的主体是韩瑜曾祖、祖父及父亲的品行履历;第三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即从“公讳瑜”到“用刊贞珉”,记载韩瑜的个人履历、家庭成员以及丧葬事宜。关于韩瑜本人,时贤已多有论及,笔者不再赘述,下文仅从韩瑜父祖的用典情况分析撰者对韩瑜家风的描绘和塑造。
(一)韩瑜的祖先
由于古人多有攀附先世的前科,更何况本墓志中对韩瑜先世的记载又多藻饰之辞,且中间还有极其明显的断裂,所以时彦多不注重这段文字。因而,如上勘正,我们会发现一些较为明显的错录,流误百年。仔细分析第一部分的典故可以发现,这段话主要提到了两个人物:一是,汉初的经学家、“韩诗”的开创者韩婴;二是,韩氏得姓始祖韩武子韩万,都是治史者熟知的人物。韩婴为汉文帝时的博士,韩武子以擒杀晋哀侯得封,是韩氏一文一武的代表。
雄飞资庙食之文,鹿鸣叶朝燕之雅。“雄飞”即代指《诗经》中“雄雉”一诗,其文曰:“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7]。但须指出的是,此诗出于国风,似不当是庙食祭飨之文,撰者可能是为了与下文“鹿鸣”之章强为对仗;无论是出自国风的《雄雉》,还是出自小雅的《鹿鸣之什》,皆是《诗经》名篇。此句已点出这位文学优长的韩氏祖先,当以《诗经》名世。这也有助与我们理解下文“元王”二字的含义[8]。
若乃真元王之胄绪,大建侯之勋庸。“元王”是指“元王诗”,即《诗经》。据《汉书》记载:“(楚)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9]那么,“建侯”又是指什么呢?《周易》云:“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10]可知此处“建侯”代指《周易》。韩氏族人中以《诗经》《周易》见长的经学家中,最著名者当属韩婴。《汉书·儒林传》云:“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淮南贲生受之。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燕赵间好《诗》,故其《易》微,唯韩氏自传之。”[9]由上可知,志文中“元王”当指《诗经》、“建侯”代指《周易》,此两句是前文“高门袭庆”的具体例证。后世学者不明“元王”“建侯”之典,又受王、侯二字和“列爵疏封”误导,认为此句是说韩氏出自王侯之家,故妄改“元王”为“先王”。其实不然,此句旨在说明,韩氏出自韩婴,乃经学世家。
统观第一部分可以发现一个“总—分—总”的结构:首先,由“高门袭庆,列爵疏封”总领全文;其次,列举韩婴、韩万作为韩氏文学武功方面的代表,并点出韩姓之来源;最后,总以“豊牒尽纪”,为下文韩瑜一族能文能武奠定基调。
(二)韩瑜之父祖
此一段详列韩瑜父祖风采,涉及典故有“中卿之典”“祈父之诗”“萧何”“孔光”等,下作解释。
讨恶助中卿之典,若畴遵祈父之诗。此两句仍是为彰显韩瑜曾祖父的武功,所谓“讨恶助中卿之典”盖指韩厥。据《国语》记载: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11]韩瑜曾祖父,墓志记载其为“大司马”,故撰者以韩厥比拟。又“祈父”是指《诗经·小雅》中的《祈父》篇,其文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转予于恤,靡所厎止?祈父,亶不聪。胡转予于恤?有母之尸饔”[7]。主旨是彰显王宫卫士刚烈直谏的形象。有学者研究发现,韩瑜曾祖父为韩融曾任蓟州司马,[2]原无事迹可称;且据《旧唐书》“司马掌贰府州之事,以纲纪众务,通判列曹”[12],可知韩融亦非军旅中人。撰者仍以韩厥治军事迹作不伦不类的对比,除广篇幅外,也是为树立韩氏一族武功卓绝的形象服务的。这也可从后文墓志撰者郝云对韩知古的描写中得到印证。
萧何独守于留司,孔光不言于温省。萧何、孔光,皆是西汉著名的宰相。萧何在楚汉之争时留守关中、力佐刘邦成就帝业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不必解释。孔光则是汉成帝时的宰相,史载:“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它语,其不泄如是”[9]。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温省”非辽金时期枢密院之别称[13],而是代指汉长乐宫温室殿。由上可知,撰者选用萧何、孔光两个典故,正是为了突出韩知古匡扶帝业、忠谨不语、不居功自傲的良臣形象,与韩融大司马的形象相辉映,展现了韩氏文武传家的家族特质。
另如韩瑜父匡美,墓志云:“文武敌万人之英,将相备累朝之杰”,更是身兼文武。而韩瑜本人也是“趋庭就傅,学诗礼以检身;筮仕勤王,便骑射而成性”,可谓文武兼通。而后对韩瑜一生的概括也是围绕此点,或冲锋陷阵、舍生忘死,或出居藩守、仁化黎庶。最后,志铭综括其一生为“礼乐是悦,骑射斯彰。历官禁省,效节疆场”,仍是赞叹韩瑜为文武全备之才。
还有就是韩瑜之子韩橁,其墓志云:“稟弓高之贵精,蕴斗极之武干。体貌魁硕,宇量渊弘。袭世禄不骄,修天爵以弥笃。尤工骑射,洞晓韬钤”。先是称赞了韩橁的武干;其后介绍其仕官履历时又以郤縠、窦宪作比——“考诗书而谋帅,无右郗縠;委车骑而命将,率先窦宪。”总之,韩橁是工于骑射,熟读诗书的儒将。不止如此,韩橁在家教方面,子孙仍是“闻教导于鲤庭;绍雄豪于马埒”[14]。也是要求子孙后代诗书、骑射并举。
总括而言,在玉田韩氏家族墓志的书写中,通过攀附韩万、韩婴等韩姓名人,借用《诗经》《汉书》中的典故,将其家族塑造成以文武传家的累代将相之家;并且,这种纬武经文的家风在韩瑜、韩橁父子身上得到进一步细化,即工骑射、学诗书。那么这种家风是玉田韩氏所特有的家族特质,还是入辽汉族世家普遍传承的一种家风呢?值得深思。
三、入辽汉族世家家风的抟成
对于上述问题,笔者以家族墓志出土较多的刘承嗣家族、王悦家族、耿崇美家族为例,以管窥豹。
其一是刘承嗣家族。刘承嗣为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之孙,刘守奇之子。天佑四年(907 年)刘守光强夺父位,自称卢龙节度使,刘守奇因而北奔契丹。刘守奇一系也成为早期入辽汉族世家之一。[1][15]墓志中关于刘守奇一支家风的记载详见表1。

表1 墓志所见对刘仁恭家族家风的部分记载
从刘承嗣五世的记载来看,经文纬武也是对其家族的共同描写。如刘守奇,墓志称赞其“白羽过于七扎,彤襜显于六条”。所谓白羽即指弓箭,《旧五代史》也记载“刘仁恭之子守奇善射”[15];彤襜即是彤幨,代指文事,可知此处也是称赞刘守奇亦文亦武。《刘宇杰墓志》记其幼年早慧、长而魁梧,所以有经文纬武、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刘日泳更是将门之后、不坠家风,在善骑射的同时还能够敦学诗书。由此可知,刘承嗣一族出自武将世家,在精于弓箭的同时,也不忘教导子孙学习儒家知识。
其二是王悦家族。王悦曾祖父是王处直,祖父为王郁,《新五代史》有传,也是世代将门[16]。《王悦墓志》记,祖父王郁“出征入辅,纬武经文。爰静爰清,美矣盛矣!”[17]王悦本人则:“布贰车之新政,且利于民;参六条之旧章,不犯非礼。罢任南征,为诸宫院兵马副都部署。共驱虎旅,同助圣谋。遣寇庭百战之师,畏骁六钧之艺。”他被塑造为既是布贰车之政、断狱如神的一方父母,又是力控六钧、驱帅虎旅的武将。还有王悦的堂兄弟王裕,“所精宣政,涉猎四经。豪气相高,□班超之投笔;雄材自负,笑李广之不□”[17]。王悦与王裕这样既能涉猎四经,布贰车之政,有能力控六钧、驱虎狼之师,正是其祖父“出征入辅,纬武经文”的延续。
其三是耿崇美家族。耿崇美原为上谷人,据其墓志记载:“祖讳用,字朋其,经纶伟器,文武全才,早事军门,累膺擢任为纳降军使,又为营田使,检校光禄卿。烈考讳去赋,刜钟利刃,构厦宏材。时推干济事之能,众谓方圆之器。军府以甲兵甚众,军储是忧。遂委为营田使。仓廪既盈,渥恩继降。又迁为卢龙军使节度押衙,兼御史中丞。旋值契丹国雄图大振,奇锋莫当。一旦深犯边疆,遂遭虏掠。因兹将家入国,乃为近臣”[18]。耿崇美祖父起家于军门,墓志称赞他是“文武全才”,其子耿去赋,继承父业,仍在卢龙军任职,后为契丹所掳。又因耿崇美通晓契丹语,成为阿保机的亲信重臣,耿氏因此成为辽代汉族世家之一。另据耿崇美孙《耿延毅墓志》记载,耿氏一族亦工骑射、学诗书,如耿崇美就“善骑射”[17]。又耿延毅子知新与耿崇美一样“善骑射”,所受家教就是“习将相艺,识番汉书”。[17]
综上来看,《韩瑜墓志》所言“礼乐是悦,骑射斯彰”这种纬武经文的家风可以视为入辽汉族世家的共同选择。之所以形成这种家风,既是入辽汉族世家为顺应辽朝政治特点而进行的自我改造,也有基于汉族文化传统的自我坚守。
第一,入辽汉族世家强调骑射,是对辽人崇尚骑射风气的效仿。契丹作为一个游猎民族,向来重视骑射功夫。例如辽顺宗耶律浚,从道宗出猎,连中猎物,道宗曰:“朕祖宗以来,骑射绝人,威震天下。是儿虽幼,不坠其风”[1]。骑射功夫不仅是契丹贵族世代相传的家风,也是国家选将择人的重要标准。如《辽史·耶律奚低传》记载:“耶律奚低,孟父楚国王之后。便弓马,勇于攻战。景宗时,多任以军事”,[1]又,萧夺剌“体貌丰伟,骑射绝人。由祗候郎君升汉人行宫副部署”。[1]可见在辽朝,一个贵族只要弓马精熟、勇于作战,在辽朝就可以成为一个合格乃至优秀的军事将领。面对辽代以武立国的环境,汉族世家也要有所改变。因此,玉田韩氏祖上虽是落魄文士,韩知古在辽也是参订仪法,都疏于军事,但在辽代尚武的环境中仍要教导子弟学习骑射功夫。
第二,汉族世家在强调以武干禄的同时,不忘学习诗礼,以培养文武全才,恪守儒家文化传统。表现在,相对于契丹择将偏重骑射功夫,汉族世家更推崇知书识礼的儒将。《武经总要》记载了中原选将的标准:
择将之道,惟审其才之可用也,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诈而疏,不以罪而废……是岂以形貌阀阅计其间哉?而庸人论将,常视于勇。夫勇者,才之偏尔,未必无害。盖勇必轻斗,未见所以必取胜之道也。大凡将以五才为体,五谨为用。所谓五才者,一曰智,二曰信,三曰仁,四曰勇,五曰严……所谓五谨者,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诫,五曰约[19]。
由上来看,中原的选将标准,其一,不问阀阅,认为这不利于选人得才;其二,不求勇猛,认为这无益于取胜,与辽代的选将标准大相径庭。《武经总要》认为将领应具备“五才五谨”即智、信、仁、勇、严五种道德品质;理、备、果、诫、约五种治军手段。在中原王朝,成为一个优秀的将领,仁义礼智信必不可少,而熟读诗书,研习儒学就是题中之义。故《武经总要》言:“诸葛亮不亲戎服,杜预不便鞍马;谢艾以参军摧石虏,邓禹以文学扶汉业。”[19]简言之就是,中原相对于勇将,更喜欢儒将;相对于武艺高强,更注重知书识礼。而如上述墓志所谓诗礼检身、骑射成性,这种经文纬武的家风,是汉族世家传承自中原的文化基因与其栖身于北族的现实需求的结合。可以说,玉田韩氏对自己家族文武双全的定位,正是尚文的汉族与尚武的契丹两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
四、结语
如上所言,古人多有攀附先世的流弊,所以学者对此类文字并不重视,仅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一种格式化的墓志书写体例,或是参证补阙、或是详辨其误,又或视作伪材料而捐弃不用。这样的研究自然有益于史实考订,但是不必讳言,其仍未摆脱传统金石学证史、补史的范畴,仅仅是做简单的史料分析。如有学者所言,把墓志从史料分析推向史学分析的途径之一就是“为墓志的叙述提供一个能够相关联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墓志中一些看上去似乎意义模糊的语句便具有了特定的内涵”[20]。陈寅恪先生早先曾说:“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21],亦是此理。就本文而言,墓志的时代和作者可信度较高,但作者未必不会作伪文;而探寻作者作伪的动机,则是我们将墓志材料推向史学分析的一种途径。
由此看《韩瑜墓志》,倘若我们转换角度,不在乎世系真伪,而是审视墓志撰者的写作意图,对于前贤不甚重视的史料,却能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在攀附先世、夸耀门楣之外,其透露出的就是墓志撰者所要体现的家族特质。这一特质或是出于墓志撰者对志主家族的了解,或是,更有可能地,出于家族的自我建构。就《韩瑜墓志》来说,所展现了亦文亦武的家族特质,不应是其家族特有的,而是刘、王、赵、耿等成长在辽这一二元制帝国羽翼下的汉族世家的共同特质。作为辽朝的统治阶级,辽代的尚武特性也融入到这些汉族世家的血液当中,作为燕地的土著汉族,对儒家文化的推崇,也根植于他们内心深处,对经史文学的爱好既是他们的优势,也能为他们以武进阶提供助力。不同于中原汉地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亦文亦武,文武并举就成为辽代汉族世家的家风,并传于后世。
注释:
①“前进士郝云撰”,此六字《县志》《全辽文》《家族》漏录;“撰”字,《热河》《志稿》未识别。
②《考释》误录作“葉”按:“叶”同“协”,与葉不同,见《金石文字辨异》。
③《县志》《考证》《志稿》《金石志》《全辽文》《文编》《家族》《考释》皆误录作“先”。
④“与周姓”,《金石志》《全辽文》《商榷》《文编》《家族》《汇辑》《考释》皆录作“与周同姓”,多录“同”字。
⑤《家族》误录作“兴”。
⑥《考证》漏录“生”。
⑦《县志》误录作“材”。
⑧《县志》误录作“莫”。
⑨《考释》误录作“京”。
⑩《考证》《金石志》《全辽文》《文编》《汇辑》《考释》皆录作“豐”,《家族》录作“丰”。
⑪《县志》《热河》《考证》《志稿》《金石志》《全辽文》《文编》《家族》《考释》均录作“謀”。本志第十与第二十行有“谋”字可为对照,字形并不一致,此处当从《汇辑》作“谍”,校为“牒”。
⑫《县志》《热河》《考证》《志稿》《全辽文》误录作“鄉”;《家族》误录作“乡”;此处应从《校录》作“卿”。
⑬《热河》未识别“置”。
⑭《家族》误录作“丙”。
⑮《家族》漏录“敌”。
⑯《家族》误录作“传”;《考释》误录作“傳”。
⑰《热河》误录作“使”。
⑱《县志》《全辽文》《家族》《考释》误录作“矢”;此处应从《校录》作“必”。
⑲《热河》误录作“详”。
⑳“左羽林军大将军”,《考证》误录作“左羽林军大将”,《证补》误录作“左羽林大将军”。
㉑《全辽文》《文编》录作“旆”;“斾”同“旆”,见《类篇》;《家族》误录作“旋”。
㉒《热河》误录作“予”。
㉓《热河》误录作“袹”;《志稿》误录作“袗”;《考证》《全辽文》《文编》《家族》《考释》皆误录作“祇”。“祗 ”同“祗”,见《龙龛手鉴》。
㉔《考证》误录作“候”。
㉕《县志》《考证》《金石志》《证补》皆误录作“候”;《志稿》多录一“□”。
㉖《县志》《考证》《志稿》《金石志》《证补》《全辽文》《文编》《家族》《考释》皆误录作“隆”。
㉗《县志》漏录“一”。
㉘《证补》漏录“食”。
㉙《热河》误录作“寔”;《家族》误录作“宝”。
㉚《县志》漏录“一”。
㉛《热河》《考证》《志稿》《文编》误录作“化”。
㉜《文编》《家族》误录作“庭”。
㉝“曹米”,《热河》《考证》《志稿》误录作“曾未”,《证补》《全辽文》《文编》《家族》《考释》皆误录作“曾来”。据拓片,“曹”字清晰可辨,“米”字虽残泐,但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三月甲戌,于越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彦进、米信由雄州道,田重进飞狐道,潘美、杨继业雁门道来侵,岐沟、涿州、固安、新城皆陷。”(第128页)所谓曹、米即宋将曹彬、米信。
㉞《志稿》未识别“忿”。
㉟《考证》误录作“加”。
㊱《热河》《考证》《志稿》误录作“师”。
㊲《县志》误录作“守”。
㊳《县志》误录作“检”。
㊴《热河》《考证》《志稿》《金石志》《证补》《全辽文》《家族》皆未识别,作“□”。
㊵《考释》在“逃”后误加“□”。
㊶《热河》《考证》《志稿》《全辽文》《文编》《家族》《考释》皆作“第”。按:“弟”同“第”,见《金石文字辨异》引《唐盖文达碑》。
㊷《家族》误录作“价”。
㊸《热河》误录作“赐”。
㊹《文编》误作“谕”。
㊺《县志》《热河》《考证》《金石志》《全辽文》《文编》《家族》《汇辑》《考释》皆误录作“允”;“凢”同“凡”,见《干禄字书》。
㊻《全辽文》《家族》误录作“泽”。
㊼文字大部残泐,难以辨识,《汇辑》作“□□”,《县志》《考证》《志稿》《金石志》《县志》《全辽文》《文编》《家族》《考释》皆作“儿”,似有所据,从疑。
㊽文字大部残泐,难以辨识,《县志》未录,《热河》《考证》《金石志》作“□”,《志稿》《全辽文》《文编》《家族》《汇辑》《考释》皆作“长”,盖据文义补。
㊾《校录》《文编》《考释》“次”字后多录“女”字。
㊿《考证》漏录“室”。
(51)《热河》未识别“授爵”。
(52)《县志》漏录“高贵相承,交游不杂”八字。
(53)《热河》《考证》《志稿》误录作“到”。
(54)《县志》《热河》《考证》《志稿》《金石志》《全辽文》《文编》《家族》《汇辑》《考释》皆误录作“茂”。
(55)《家族》误录作“隙”。
(56)《县志》漏录“川”。
(57)《热河》未识别“必”。
(58)《热河》《考证》《志稿》《金石志》《文编》误录作“表”。
(59)《县志》《考证》《志稿》《全辽文》《文编》《汇辑》《考释》皆录作“豐”,《家族》录作“丰”。
(60)《县志》漏录“树”。
(61)《县志》误录作“任”。
(62)“骨归故乡”,拓片“归故”二字缺,《热河》录作“□□”;《考证》《金石志》《县志》《全辽文》《文编》《家族》《汇辑》《考释》皆作“骨归故乡”似据文义补,兹从之。
(63)《县志》《全辽文》《文编》《家族》《考释》皆误录作“痛”。
(64)宣赠弥光事君事父忠孝备昌万载千秋芳声不亡,拓片残泐,多不可辨识,《热河》录作“宣赠弥光□□□父□忠孝伤万较千秋芳声不亡”《汇辑》录作“宣赠弥光事君事父兮忠孝备万载千秋兮声不亡”,《县志》《考证》《志稿》《金石志》《全辽文》《文编》《家族》《考释》皆录作“宣赠弥光事君事父忠孝备昌万载千秋芳声不亡”,兹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