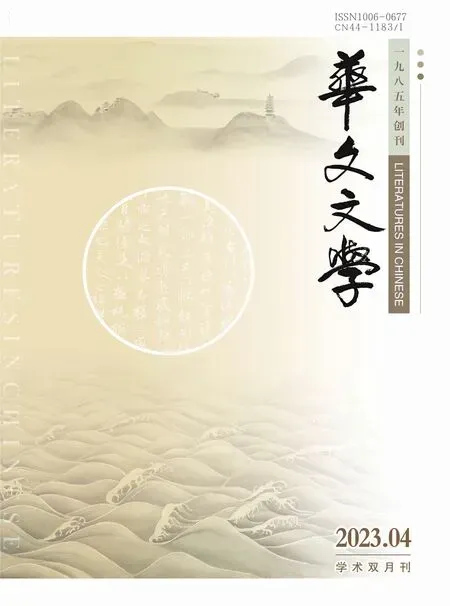想象香港的方法:葛亮短篇小说的香港书写及其文化政治
苏文健 普红
一、香港:城与人的文学镜像
追求人与城的和谐发展一直以来都是都市文学的中心关切。城市以其强大的工业化推力与迅猛的商业发展速度,让不断涌入的外来者,成为建设者、享受者。而紧随城市化而来的种种社会窠臼,也让城市变成了道德腐坏的失落之城。葛亮笔下的香港,既有国际性的现代大都会应有的繁华景象,也有破败不堪、匿藏嚣乱的昏暗城中村。卑微存活于这两道光之下的底层小民,没有生长于斯的正宗港人身份,也没有深厚的科学文化素养傍身,以至于从物质到精神步步垮台,沦为双重边缘的存在。
(一)香港城市的两个面相
香港繁华的一面在于它是色彩斑斓、包罗万象的国际性现代大都会。
如果说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车辆,到灯红酒绿的繁华夜色,某种程度上是衡量一个城市现代化发展程度的话,那么香港无疑是最为摩登的。对这种现代化的描摹,葛亮倾向于从视觉上来呈现。首先是香港这座海滨城市气派的夜景。入夜后的香港,从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到泛着魅惑光芒的广告牌,四下里灯火通明,整个城市就像苏醒过来一般,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黑夜与白天,于这里不过是几盏灯的距离。在汽笛阵阵的维多利亚港口,阑珊的灯火勾勒出海的轮廓,一湾窄窄的海水,映衬着撩人的夜色,也倒映着香港辉煌灿烂的现代价值。在以城市经济文化为唯一导向的香港,强调的是物欲与狂欢,只有四周都亮起来,港口也才有了气势。其次是直冲云霄的摩天大楼。发达的经贸网络与交通系统撑起了香港这座钢铁森林的现代化。摩天大楼扶摇直上,俯仰之间让人只能看到其间悠悠的天光。不断拔高的大楼也带动了香港都市价值的攀升。这些楼里有繁华又昂贵的商区,有闪闪发光的巨型荧幕,所有的一切都被注满了奢靡、巍峨的气息,让人惊叹。
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下的香港亦是一座极具包容的国际性大都市。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这里,面色黧黑的南亚裔男子、身着纱丽的印度女人等异国面孔出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形成了香港混杂的人口情势。而各色人种在香港的汇集或许只是表面,其内部更为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火种的融合与衍生。这里有意大利前卫画家米尼亚思的画作展出,有菲律宾乐队的演奏以及古印度梵画的展览。中西杂糅的香港,俨然一片文化的绿洲,香港文化也因此变得越发包容和开放。
除了被繁华包裹着的现代都市价值,香港的城市组成还囊括混杂破败、暗含多种不安全因素的城中村。它们或在高楼的夹缝中求生,或在城市的边缘苟延残喘。葛亮经常叙写到一个视角:巍然林立的高楼与灰暗惨淡的城中村一线之隔,里面的人拥有的却是天上与地下的悬殊人生。这种卧在繁华阴影之下的城中村便成他笔下世情描摹和人情冷暖的表现场。
城中村里老旧的唐楼,它们因地制宜见缝插针,如簇拥的蜂蛹稠密地挤在一起,阴暗潮湿已然常态。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种破败的楼就成了哪怕是寄居也感到满足的底层人的住所。这些楼也曾是香港城市力量的代表,但随着年久失修,日渐颓败的它们连同楼里的人,被高速运作的城市速度所摒弃、遗忘。
通风不畅光线又差,长满铁锈的房门还残破不堪,就因为通身布满了衰败的势头,这些隐蔽性极强的楼盘内部早已沦为法外之地。而往来居民的形形色色,也使这里的违法犯罪行径五花八门。为了生存,明目张胆地抢劫斗殴已然常态,不少街道还发展成了远近有名的“红灯区”。与外面五光十色、真正的风月场所不同的是,它们竟然和居民楼相安无事地混杂在一起。这些楼里,更有网罗密切的地下黑色产业链。贩毒、吸毒、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频发。严重的毒品泛滥问题,使得葛亮在小说中几次提到了“道友”一词,意味着“白粉佬”,也就是吸毒者。
在这种法律触不及的逼仄城中村,人身安全始终得不到有效保障。然而愈是盘根错节,愈能引发种种不安全的社会因素。住在里面的人无法改命,只能麻木地沦为不安稳局面的帮凶,再次让整个生活环境向着恶的一面发展。
(二)香港人的生存图景
葛亮小说中的主人公并非十足正宗的本土香港人,从身份上来说是外来的。他们大多是纯粹的体力劳动者,知识阅历都很浅薄,对赴港生活的规划更是片面,往往只为一时冲动,抵达香港后长期处于被动的局势,受时局摆弄,慢慢沦为港漂。港漂在香港的生存形态有别,对香港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可以说,这些外来者一直都是边缘的存在,从未真正属于香港。对偷渡者而言,寻求政治承认是他们在港生活的中心关怀。葛亮对偷渡的外来者着墨较多,偷渡问题在小说中屡屡被提及。有些人出于大陆时政、生活前景等,离开了大陆,冒着哪怕付出生命危险的代价也要来香港。偷渡意味着在香港没有合法身份,无法正常地享有公民的合法权益,行事处处受限。《阿德与史蒂夫》里写到阿德没有合法身份,只能打黑工,被抢劫也不能报警,受伤只能去医疗设施简陋的地下诊所治疗;没有合法身份的女友曲曲,只能终日待在不见天日的家以躲避审查。这些偷渡者,深受融入过程中合法身份问题的困扰,脚下虽踩着香港,但他们应得的人身权益却一直游离在外,撑不起他们在港的行动。其次,就是在香港谋生的过客。如《德律风》里的丁小满,《街童》里持有双程证的内地女孩宁夏。出于某些原因,他们来到香港,领教了大都市的繁华与落魄,却也无动于衷。除了金钱和欲望,香港的万千变化一直无法牵动他们的心。从始至终,他们对香港都带着一丝过客的观望心理。因为香港能给他们提供的仅仅是机遇与平台,虽然在这里工作、生活,但他们的根不在岛城,无需呕心沥血求融入。
外来者认知层面的狭隘,也造就了他们只能继续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边缘化生存处境。香港这样的大都市,经济科学等诸多领域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各领域精英汇集到这里,无论是对城市发展的需要还是精英自身才华的施展都是彼此需要的。融入者大多来自乡下,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不具有主流社会需要的价值。这些人来到香港仅仅一念之间,对香港的城市生活没有很好的了解,对时政更没有良好的把握。到香港之后,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匮乏、强有力的社会人脉关系网络缺失,人微言轻,他们只能继续走上廉价的体力劳动输出老路,从事最低贱的底层劳动,甚至是见不得光的黑市生意。本以为到香港就是换了天堂,没想到生活现状依旧没有改变,连身份都是不合法的,更别说要依靠双手实现阶级的跨越。与正常的经济社会逐步脱轨,越发得不到社会认可的他们,只能继续在社会底层挣扎。眼见生活糟糕前途渺茫,他们愈发苟且度日,最终沦为物质与精神双层次上的边缘存在。
色彩斑斓见证了香港的现代都市价值,而混杂破败也成了香港边缘之地的当下写照。“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中,城市/乡村对立是最常出现的主题之一,指向一个被激烈争夺的文化生产场所,一个彼此竞争的话语、价值观汇聚的地方。”①繁华与没落、核心与边缘,表面上看香港繁华的街区与城中村是互为对立的的两极。其实,城中村里携带的传统文化因子会散落于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夹裹下的现代化速度也会改变城中村,二者混杂交融,早已超越豪华与破败的建筑地标的区别。
二、香港书写的精神旨趣
一边是包裹现代价值的摩天大楼,一边是保留文化传统的城中村,繁华与破败共存的局面使得香港都市里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互相掺杂,混合丛生。但现代化取得压倒性胜利的势头却越来越明显。处境边缘的主人公,抓不住现代化发展的尾巴,更没有能力守护传统文化,只能被滚滚向前发展的城市车轮碾压,沦为金钱与欲望的奴隶。
(一)传统与现代互相渗透
岛上浓到化不开的诸多传统要素留存在现代都市的车水马龙之中,诉说着岛民的家国情怀与岛城的历史更迭。本土居民强烈的家与族的观念,是烙印在血肉里的精神符号。一座古旧的家族祠堂,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记载着家族的起源与流变,而始终不变的是人丁兴旺、光宗耀祖的信念。作为漂泊在外的同乡,《阿德与史蒂夫》中老虎叔与阿德母子守望相助彼此照应;作为邻里,眼看龙婆的家就要被暴力拆迁,《杀鱼》里的村民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患。在这些人物身上,依旧能看到闪闪发光的传统美德。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传统节日也深深扎根于本土人生活的土壤,作为活化石世代相传。
小说中提到的香港传统节日,有中元节、端午节以及年度盛事“太平清醮”等。这些节日都以传统农历来纪年,表达的都是国泰民安、福慧双增的期盼与祝愿。农历七月十四的中元节,人们摆祭烧纸,纪念已故的人。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黄昏时的海滩缤纷一片,龙舟竞渡的呐喊声久久不断。农历四月的“太平清醮”,醮期三天,“抢包山”是它的压台节目。以竹条建起支架挂满包子,抢到的包子越多,福气就越大。
同时,现代化的高速运作,也为城市的边缘之地带来了新的改变,城中村正在被推着向前发展。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现代化的话,“速度”无疑是最贴切的。一个有速度的城市,从生活节奏到城市建设都是忽然的。信息传递、交通网络、工业建设,香港的现代化气息总能从各个方面渗透进来,对城中村的落后与低速做出应有的改变。
科技进步带动网络媒体的发展,让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拥有更多可能。《鹌鹑》里偏僻的旅社,弯弯绕绕犹如迷宫,地方冷僻破败,在这样的地方出现了Wi-Fi、针孔摄像头、电话和电脑,而MSN、Facebook 等网络社交媒介又可以让远在天涯的人犹如咫尺之间。纸质媒介与互联网齐头并进,新媒体技术又日益发展,其高效而低成本的特点让任何消息都会被快速地传播而无处遁形。香港与深圳之间日益便捷的交通网络,让香港人由此兴起北上消费的热潮,内地人也渐渐反客为主,将大包大包的商品带回去。便捷的城市交通、发达的网络科技把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间与空间的边界在速度的加持下都慢慢淡化了。
城市化要发展,城市的占地面积就要外扩,边缘之地就会不断被开发利用,工业区与住宅区的边界就会日益模糊。繁华的街区大厦取代了幽暗破败的小楼,市容市貌得以改变,香港的经济文化建设更是水到渠成。葛亮在小说中提到了香港仍然处在建设中,到处都是地基,机器打桩的轰鸣声屡屡不绝。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力下,征地、拆迁随之而来。为了种植有机蔬菜,小岛已经被开发;为了建设度假村,朴实无华的小渔村就要迎来改头换面的新机会。
工业化的步伐层层逼近,使得香港的城市规划日趋完备,日益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统一步伐紧跟时代潮流的发展势头之下,边缘之地长久以来稳定的一方平静便被打破了。虽然有一定的滞后性,但现代因子源源不断地汇入,逐渐将偏僻之处的封闭与落后覆盖了,同时,也将人的视野和欲望铺开了。在这种内外交互的过程中,人不再是独立又单一的个体,而是与环境丝丝相扣的复杂动物。
(二)理想与现实彼此背离
葛亮以青少年的视角来打开香港的本土画卷,见证一批大陆赴港人士的沉沦史。这些人,不是单亲家庭里的少年,就是中年丧偶的寡妇鳏夫。社会地位不那么突出的他们,受限于文化认知水平低下和经济实力薄弱等诸多因素,慢慢走向了悲剧的人生道路。本质上的普通与性格上的诡谲不啮合,使得他们的出场与结局严重背离。
小说中描写到的人物都是普普通通的升斗小民,没有伟大的人生理想,小富即安,他们虽有自己的私心和隐晦,但却不是作恶多端心肠歹毒的大恶人,总体而言依旧属于“好人”之列。《阿德与史蒂夫》里,时局艰难,却也挡不住老虎叔、林医生等同乡之间的友爱互助。《猴子》里靠政府综援生活的父女二人,在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还是将食物分给一只猴子。而当清楚了猴子的身份,窝藏它势必会对自己不利时,父亲狠下心赶走了它。
但是,所谓好人有好报在葛亮的小说里是行不通的。这些好人,生活的不幸加之唯利是图的商业经济发展趋势煽动,让他们只关注眼前的片刻体验而不留退路:为追求金钱利益不惜舍弃做人的尊严,以牺牲人伦道德来排解失控的个人欲望。本性善良却受限于后天环境,以至于思想渐渐松动,面对选择时的道德挣扎就让他们将人性的复杂与机变展现了出来。
为了维持生活,有的人选择了出卖身体,比如《阿德与史蒂夫》里的阿德母亲;有的人哪怕接受了高等教育,却依旧堕落地耽于金钱名利,例如《浣熊》里的女孩Vivian;有的人也因为长久以来的性压抑,出现了过度依赖、乱伦等病态心理,让性与道德接受赤裸裸的考验,如《退潮》里的女主人公。等待他们的,便是在绝望中等死、悔过,为自己的错误付出应有的代价。
急速发展的现代化使得城市的更新换代频率加快,这意味着对传统要素的侵蚀与稀释也在加快。普普通通的“好人”,在城市中谋生谋爱,却没有收获和秉性相匹配的结局。这种亟待扭转的城与人失衡发展的局势,也让葛亮开始思考当下香港的城市价值与精神,促成他笔下对香港都市书写的文化政治表达。
三、香港书写的文化政治
一直以来,中国现代作家对城市都存在爱恨难明的矛盾心理,因其既是拥有强大现代力量的光明之城,也是黑暗的道德渊薮。这种矛盾困境使得葛亮在情感上是亲近香港的,对书写香港也是热爱的,而不断涌现的香港城市问题却是对这种亲近与热爱的一大冲击。基于此,香港便成为了他内心深处文化碰撞最激烈、情感涌动最频繁的一方文学孕育沃土。
(一)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无论生活在哪,城市对葛亮来说都是和成长紧密相连的文化烙印,是身份上的认同。从小成长于南京的文化内核里,南京情结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葛亮笔端的香港城市书写走向,为他提供独特的文化审视角度。
葛亮的文学创作道路是从香港开始的,但小说中最开始写的却是故乡南京。虽远在千里之外,可岛城香港的物事与人情,无不在提醒着他回望故土。拥有百年历史的香港大学,带着些古朴的意味,更有张爱玲这样的校友。港大附近的旧屋宇,总让葛亮想起南京老城南的房子。此外,香港生活节奏之快,步伐匆匆的行人、比肩接踵的十字路口,岛城局限之下土地寸土寸金且逼仄,这些时空上给人的压迫感,也让葛亮想到了南京。南京紧挨着长江,地势平坦,腹地广阔,给人的感受是开阔明朗的。其次,南京人的闲适,南京生活也悠悠然,与有速度的香港相比,冥冥之中让他对故乡的思念愈发强烈了。城与城之间游移的人生轨迹,遥遥回望之下都是对城市的款款深情,“有对故乡的躬身反照,有对成长的念兹在兹,有对陌生的回避与触碰,有对熟稔的疲倦与眷恋”②。
香港触发了葛亮的南京情结,南京便反作用于他笔下的香港都市书写。同为依托江海成长起来的中国著名大城市,南京有六朝古都典雅浓厚的历史余韵,香港有百年商埠溶汇中西的文化色彩。从小伴随着耳濡目染的历史文化成长,青年时代乍然置身香港,环境的变更、心态上的扭转,让葛亮愈发注重融以传统的内核,注重香港本土地域文化的挖掘,才会把历史底色放到香港的小说叙述当中来。
香港与南京,从饮食风格到历史底蕴都是迥异的。葛亮只能从普通人身上窥见一点一滴的传统文化烙印,挖掘岛上的文化魅影以感怀南京。南京有五香豆、糖藕粥、鸭血粉丝汤这样远近闻名的民间小吃,面对香港,自然是地道的粤式菜肴。有粉葛煮鸡脚汤、西柠鸡和清炒虾球,以及《街童》里林布德、宁夏二人到“陈记”粥粉店里吃的状元及第粥、生滚鱼片粥、叉烧肠粉。
《朱雀》是葛亮居港怀乡的创作结晶。这部作品里的故事时间跨越几十年,在历史关隘中刻画出的满满都是南京历史烟云的细节。葛亮书写香港,对历史事件的影射依然可见。1972年,很多广东人把香港看成唯一的出路,这就有了小说中屡屡被提及的偷渡问题。1980 年后,香港特赦取消,居留权问题成为很多赴港人士的中心关怀,演变成了历史事件“入境处纵火案”。这样一来,就有了《阿德与史蒂夫》里,一批像阿德一样没有合法身份的人,组织大规模静坐绝食,冒雨请愿政府的描写。1997 年香港回归,《德律风》里提到电视上在转播香港回归仪式,《告解书》里“九七”的到来使得酒吧大换血。虽然有空间上的阻隔,但家城南京给予的历史反照始终在鞭策着葛亮笔端对香港城市的探索与叙写。站在南京的肩膀上,葛亮的香港书写多了几分历史的厚重和回望的消沉气息,而在港写港的我城身份言说,则表明了他对香港当下城市生活的游刃有余与自豪。
将南京唤为“家城”,香港唤为“我城”的这一心态,显露出了葛亮对融入香港之后身份的认可与情感的贴近。“我城”一词,最早可见于香港作家西西的同名小说。西西以一种十足的自信与优越姿态来展现出对香港的归属感。“我城”这一亲昵称呼,从中足以晓见葛亮内心深处对香港是极具归属感的。因而,他才以主人翁的姿态,来记录这份归属感,仿佛香港的一切都已经深深刻印在他骨子里,没有了时间的距离与认知的参差。
小说中,香港民风民俗、地理街道名称的引用再现了葛亮在港生活的日常纹理。除了太平清醮、端午赛龙舟和中元节这样的传统习俗,从尖沙咀、皇后大道、德辅道,到维多利亚公园、红磡地铁站、九龙塘、长洲岛等,这些都是香港重要的街道地名。此外,语言的使用也是葛亮融入香港本土的见证。在香港的语言政策中,书面上是中文和英文,口语上是粤语、普通话和英语的混杂使用。语言政策的影响,使得葛亮在小说中穿插使用了英语和“投下”“水鱼”“黐线”这样的粤语、粤俚语。也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了掌握香港语言的重要性。小说《猴子》中,女艺人谢嘉颖来自台湾,经纪人给她找来老师苦练广东话,并告诉她,想要变成当红明星,就得先过语言关。葛亮融入香港,日常交流是要趋向香港本土语言环境的。进而言之,从小说文本语言的运用到人物对语言的执着与敏感上来看,可以理解为是他在香港语言体验的再现。
虽然对香港有一种殷切的归属感,可与从小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香港人相比,葛亮身上多了一重大陆背景,深厚的传统文化要素始终伴随左右;而居港时间之短,又不能让他完全了解到香港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时之间,难以摆脱的故乡情结与陌生环境下的彷徨与无措,就寄生在了带着大陆背景到香港谋生的小说人物身上,成为他融入过程的个人经历书写。
(二)双城经验与文学伦理
切己的双城经验累积,使得无论是对故都南京的描摹刻画,还是岛城香港的细腻表达,葛亮都能将两个大城市游刃有余地运转于笔端。因为城市经验丰富,集中于城市的书写才会念兹在兹。
1978 年,改革开放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于大陆来说其意义不言而喻,同年生于南京的葛亮,城市成长起来的过程对他来说是始终伴随于成长左右的。又在知识分子家庭长大,作为矜贵之后,高楼大厦、市井民生是他生活场所体验的绝大部分。2000 年来到香港,尽管文化上出现了轻微的断层,但于高楼大厦间的城市经验累积来说却也是换汤不换药。
因为香港的工业化建设起步早发展快,由此带来的是都会的大发展。“都会同样是香港文学的本命,香港文学的形态无不可以见之于都市的流动。”③香港文学的发展和城市建设始终是关联在一起的,城市书写于香港文学而言是本命般的存在,而城市于葛亮来说又是经验之内的东西。其次,本土的中华文化底色再混合着英属殖民地的历史遗留,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给予葛亮的是开阔的叙述视野和强有力的城市书写形态塑造。这些取之于香港又用之于香港的城市体验,便助长了葛亮的香港书写,让他写就了繁华与黯淡共存的现代都市。
切己的城市经验也促成了葛亮笔下本真的城市伦理表达,让他着眼于香港城市发展“利”与“义”的深层问题。首先,中西混杂的文化环境使得香港部分本土文化发生变异。以端午节为例,竞渡的龙舟通体都是绚烂的色彩、卡通的大眼、憨态可掬的龙面,花枝招展的打扮失去了几分庄严;鼓乐的负责人穿着雪白色的制服和黑裤,有的还穿着斑斓的苏格兰裙子,中西合璧的赛龙舟却是浓浓的英伦风。其次,娱乐化、商业化毫无限制地发展,是对失去保护的传统文化的再一次扼杀。《杀鱼》里张天佑爷爷有着高超的杀鱼技艺,杀起鱼来行云流水手起刀落一气呵成,这种极具欣赏性的宰杀技艺,在商业旅行社看来是圈钱的好方法,却看不到,在机械化运作风靡的当下,手工劳作由于市场狭小已经面临着没落的危险。唯利是图的商业经济,也让一波又一波的“拆”流进各个小渔村,对附着传统文化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祠堂、祖屋等载体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最后,蒸蒸日上的城市经济建设热潮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造成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留守儿童问题突出以及城乡建设差异愈演愈烈。《阿德与史蒂夫》里阿德出生便跟在奶奶身边,直到十一岁到了香港才得见母亲;《猴子》中,童童从小由奶奶照看,与父亲各在一方。而阿德与童童的父母,这些流入城市的人,却已不具备城市所需要的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成为一种“过剩”的劳动力而惨遭淘汰。而在农村,他们却是劳动的主力军。城市发展不需要他们,而乡村没有了他们这样的建设者却只能停滞不前。农村越是得不到发展,乡下人越往城里走。如此,城乡差距只能愈演愈烈,形成恶性循环。
“由于与滋养自己的外界源泉切断了联系,城市成了一个封闭的熵增系统,这导致了文明的衰退:为理性而牺牲本能,因科学而祛除神话,物物交换让位于金钱的抽象理论。”④借助现代技术手段,传统习俗“抢包山”被改良,竹架变成了钢筋,包子也是循环利用的塑料制品,参与的人赛前还要进行攀岩训练。理性的人身安全保障与环保的需要战胜了文化传承的原目的;科学的视野下,城市代表先进生产力,祠堂和祖屋与“有机菜”和“度假村”相比,被视为神话遗留、封建病症,得不到重视;过度追求金钱的后果就是被它渗透、腐蚀,颠覆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基本功能。在这场不论精华与糟粕的传统文化要素和现代化的拉锯中,现代精神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香港都市书写,说到底有葛亮自己作为城市一份子的骄矜内含其中。无论是站在南京立场,还是立足香港当下,城市对于他都是一种身份言说。所以,他写香港,有成长经验使然,也有社会责任感召。同时,书写香港对葛亮自己、对香港乃至对大陆来说,都有着深层的文学意义与文化价值。
四、香港书写的文学意义
南京的成长记忆与特别行政区里切肤的生活体验之间“异”的触感,成就了葛亮笔下双城书写的小说叙写格局。同时,从都市书写的历史文脉浸润到多元文化视角下的都市文学表达,从南来作家的文化互鉴作用到与时俱进的香港多元都会描写,葛亮始终继承与创新并举。南京和香港是葛亮小说中分庭抗礼的两大城市,双城叙事互相推进,紧密联系而缺一不可。香港都市书写,是双城叙述格局下和南京书写遥相呼应的存在。
一直处在南京的内核里,让葛亮对这座典雅的老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话语权,有生于斯的骄傲,也有长于斯的情感维系。他以一种自小耳濡目染的熟悉感,让读者看到了许多南京的历史与当下。在一些有关南京的短篇小说中,从人事、物事到城事,葛亮都以小男孩“毛果”的视角来打开砥实的南京生活形态。“写自己的家庭、成长环境,成长路上遇到的人和事,他们往来于毛果的生活,一方面见证着毛果的成长,另一方面,毛果又以‘一双少年的眼睛’记录一切的变化与沧桑。”⑤
如果《朱雀》里氤氲着的是古都南京的烟雨风情,那么《阿德与史蒂夫》呈现的则是港味十足的香港都市。所处人生阶段的不同,再到生活环境上的迥异,这种城与城之间“异”的感触,让葛亮在创作上有了清晰的指向:典雅的南京,秦淮河如画的景致。香港的书写,没有像南京一样有生长于斯的熟悉,也没有匆匆一别的过客心态。定居于此,来自岛城破碎飘零的孤独感受,让葛亮的香港书写略显抽象,难以捕捉:破碎的离岛、咸腥的海风以及多元共存的文化。
“城”的书写一直以来都是香港文学的底色。葛亮积极地向香港文学靠拢,延续了关乎“城”的书写倾向。同时,多元的文化视角也让他融入了自己的创新点和新风格,进一步拓伸了都市新生代作家的创作空间。
“香港文学的都市新生代大致指20 世纪60年代后在香港出生,成长于香港高速都市化的七八十年代,而在90 年代后的都市资讯时代产生影响的作家。”⑥与同一代际的作家相比,葛亮的香港体验是不完整的。来到香港的时候,展现在他眼前的已然是城市化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于这个城市成长起来的过程,他的参与感没有那么强。然而,他的文学创作依旧继承着香港文学中关于“城”的书写坐标,不仅写香港,还写南京。
新生代作家们延续并加深香港城市书写题材的“在地化”,语言环境的巧妙运用和随处可见的香港标志,让人一眼认出了故事的发生地是香港。葛亮在语言运用和地理坐标的清晰指向上,也在回应着这一点。他以香港文学中的“新三及第”来展开,白话文、粤文、外语(英语)穿插使用,香港岛屿、街道名称、港粤菜肴、节日风俗等人文社会和地理风情的融入,使得浓郁的香港气息跃然纸上;同时,新生代作家也在不断拓展香港城市价值的普世性。城市化深入发展,城市成为了社会活动的主场,市场的融入,意味着涌入更多关于欲望与自由的因子,这也在变相放大城市的弊端。本就是享受着城市福利成长起来的一代,葛亮对后香港工业化时代涌现出来的种种城市窠臼,对人性的异化、贪婪,都给予了不遗余力的展现和批判;城市的高节奏发展,文学理念也在积极与时代潮流相适应。受都市资讯影响,新生代作家对城市的书写方法变得更多元。到了葛亮这里,他将现代传媒手段运用到书写中,让电影感与文学性巧妙地结合,希区柯克式的电影氛围传达,使得小说中关于压抑、恐惧、悬疑、惊恐的内容大量呈现,也将文学对人与城的思考更深入化。
最后,葛亮以新一代南来作家的身份,以在港写港的书写模式复刻了香港与内地之间文化互鉴的沟通传统。
一个融入型的城市,多样化的人口组成,使得香港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混杂型的。在这种历史趋势下,纵观香港文学史,其作家群体的组成亦呈现出跨地域的面貌,其中就包括大陆南下香港的“南来作家”。
“所谓‘南来作家’就是指具有内地教育文化背景的、主动或被动放逐到香港的、有着跨界身份认同的困惑及焦虑的香港作家。”⑦1978年生于南京,2000 年赴港深造,这中间的22 年时间里,从咿呀学语到翩翩少年,葛亮的思想文化浸润过程与高校教育接受都是纯内地范式的。到香港后,与大陆不一样的政治环境与生活模式,使他在对乡的特殊情感与对陌生的回避与接受过程中,关于城际游移的感触与对比无比深刻,从而引发对身份认同的思考。南来作家的普遍感受与心理挣扎也便出现在了他的身上:“一方面,他们为了生存和进入所在地区的商业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香港的商业文化相认同,另一方面,隐藏在他们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传统文化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新的商业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⑧
这种新的交融与互动,让葛亮有别于1949年前后南来作家强烈的中原心态,也不同于六七十年代“文革”影响下南来作家浓厚的刻意美化香港的意识。作为改革开放浪潮下的年轻一辈,他对港城的融入不彻底,故土又远在千里之外不可及,葛亮只能让自己处在内地精神与香港文化的中间地带上,成为沟通两岸的桥梁,拉近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互动与联系,以排遣融入时期盼中夹杂几分黯淡的失落。这便让他写就了荟萃多元的香港:本土元素与异域风情共存,古典传统与现代科技齐驱。
五、结语:葛亮与小说香港
“小说香港”来源于王德威“小说中国”。在王德威看来,“小说中国”不仅仅停留在以小说来看中国这样的观念,而是“强调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像、叙述‘中国’的开端”⑨。“小说香港”也是从小说的虚构叙述中想象香港的一种方式。
从香港的城市精神宣扬、政治体制发展到历史的编写,叙述都是必要的。小说意味着叙述的虚构性。话语掌控者的叙述角度不同,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不同,事实本身就会被抬高重视,或者压制贬低。换言之,掌握了小说文本操纵权力的作者也变相拥有了判定事实价值的话语权。从小说维度来看香港,基于不一样的意识形态立场就会有不同的话语体系。近代历史上,香港在英国和中国的叙述语境下是不一样的。前者总会为自己的殖民手段进行美化,维护自己的既得殖民利益,而后者则是批判蛮横无礼的侵略行径以表达自身的愤恨。
葛亮笔下的香港,没有赤裸裸的殖民冲突、中西对抗,只有浓厚的殖民历史遗留色彩之下本土普通小民的日常百态。他努力挖掘这座城市中的本土经验,试图在传统的中华文化底色上,找到海岛与大陆之间、现代化与古典传统之间的内在精神联系。然而,香港本土的传统文化在殖民文化遗留的排挤下日渐凋零,再在城市化发展的侵蚀下风化流散,如火如荼的现代化建设浪潮也将大城市的冷漠与贪婪、个人欲望的扭曲与失控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如今的香港,“既不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没有建立起现代西方文化精神,由此成了一个失去了文化根基的、纯粹实利化的城市。”⑩对葛亮来说,成长于文化底蕴浓厚的南京,这种现代化与传统之间撕裂的感受是无比深刻的,对香港不免透出叹惋之情。
或许,在家园的建设热情和对未来殷切的期盼心态影响下,本土人眼中的香港是完美无缺的,眼看高楼林立,眼看岛城变化万千,他们以之为荣。而在葛亮的创作中,他以“半个香港人”的视角反观这座城市,表达的却是对城市化的深沉反思,对传统回归的呼喊。
①[美]张英进:《前言:探索城市的邀请》,《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年版,第3 页。
②葛亮:《忽然一城(自序)》,《阿德与史蒂夫》,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 年版,第3 页。
③⑩赵稀方:《小说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11 页,第191 页。
④[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第8 页。
⑤金理:《有风自南:葛亮论》,《当代作家评论》2013 年第1 期。
⑥黄万华:《百年香港文学史》,花城出版社2017 年版,第177 页。
⑦⑧计红芳:《香港南来作家的身份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10 页,第34 页。
⑨[美]王德威:《序:小说中国》,《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1 页。
——关于葛亮研究的总结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