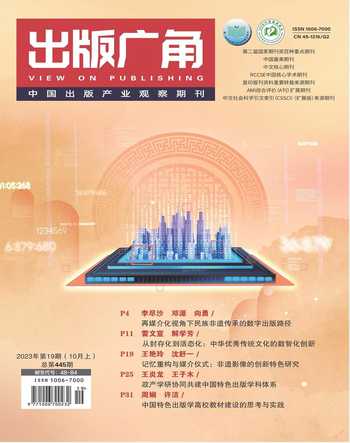智能出版的技术图景:产业链、伦理困境与纾解路径
刘宁?周宇豪
【摘要】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出版行业,削弱了编辑个体的主观性,在内容供给上更加贴合读者与市场,知识服务精准化、个性化,智能印刷数字化、系统化,发行营销精细化、智能化,实现了出版全产业链的增值。然而,对智能技术的过度依赖,会造成出版人对出版产业把关不足的危机,出版内容文化属性偏离的风险,以及私域伦理冲击公共伦理的隐忧。因此,必须树立技术向善的智能出版理念,强化出版企业、主管部门、社会等相关责任主体的伦理意识,使智能技术正向赋能出版产业。
【关 键 词】智能出版;出版产业升级;伦理风险;技术向善
【作者单位】刘宁,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周宇豪,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中图分类号】G239.2【文献标识码】A【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3.19.009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5G、区块链等技术的持续发展,其应用场景已从实验室、科研领域向产业场景和日常生活场景推进,带来产业的颠覆性变革,因此,技术视野的转向成为目前学界和业界日益关注的焦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1]对出版业而言,这种以新技术、新平台、新链条为基础的全新发展逻辑,必将带来传统出版业边界的消融和新兴分支市场的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知识的呈现和获取方式不断更新,人工智能、大型模型自主适应复杂的环境和场景,数字出版逐渐迈进智能出版时代。
一、技术赋能:智能出版的全产业链升级
学者傅国华认为“产业链的发展关键在于技术”[2]。随着前沿技术的应用,出版领域形成了以内容生产为核心的智能出版产业链,在产业链中又形成了全新的细分市场。出版业虽并未脱离内容创作、内容加工与制作、出版物传播与营销的基本链条,但技术的应用却实现了智能出版产业链的升级与增值。
1.内容供给与知识服务的迭代升级
传统出版时代,编辑对出版内容的生产占据绝对的主动权,出版物质量与编辑的个人观念和素养息息相关,但由于缺乏对市场和读者的动态追踪导致一定的出版风险。数字出版时代,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开始辅助编辑流程,但是弱人工智能只能承担部分的计算和逻辑运算,在出版的循环系统中,技术始终无法占據主导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智能出版场域,技术开始摆脱辅助者的角色,与编辑协同工作,成为编辑流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信息哲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认为,如果人造物显示互动性、自主性和适应性,那么他就可能成为一位能动者[3]。机器深度学习和出版模拟系统可以在编辑的众多备选选题中分析最优作者、读者反馈等综合信息,还可以将拟出版的选题与畅销书数据库进行对比,模拟、量化分析畅销书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帮助出版企业发掘最有市场潜力的出版项目。我们也可将区块链技术引入选题策划和内容创作环节中,建立出版行业的区块链,具体包括两方面:在历时层面,梳理一定时期以来某一细分专业领域内的数据库,包括完整的作者信息和确权时间戳,便于选题的整理和归纳,当市场对某一选题有需求时可迅速匹配到最合适的作者;在共时层面,向出版区块链联盟发布拟好的出版选题,利用代币奖励机制,集中全体的智慧和力量,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高效地完成组稿工作。
智能技术的运用使数字出版企业向知识服务商的角色演化,也促使数字出版行业形成智能化、精准化、伴随式的全新知识服务生态。总体来说,智能知识服务是指利用智能技术,将知识以更加形象化、立体化、趣味性的方式呈现,在特定的场景中满足用户的实际需求并挖掘新的需求,提供一整套系统的知识解决方案。智能技术在数据搜集、整理和分析领域有绝对的优势,而知识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数据的融合互通,包括出版数据、用户数据、行业数据之间的联通和共享。通过数据的循环和及时反馈,实现精准匹配和按需服务。“构建知识服务生态体系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知识服务个性化和有效化”[4],智能出版的知识服务生态能够有效供给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包括虚实符号结合的产品形态,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内耗,提升生产效率和用户体验满意度。
2.自决策自适应的智能印刷
在智能出版的语境中,传统纸质出版物的占比逐渐降低,数字出版物或许是未来的主流出版形态。但在从智能出版迈向智慧出版的漫长道路中,纸质出版物依旧无法缺失,甚至是特定人群的主要阅读载体。长久以来,受到技术水平和投资水平的限制,印刷环节的智能化水平难以突破。作为典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传统印刷业,其智能化水平影响着出版产业链的智能化进程。201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了《中国印刷业智能化发展报告(2018)》,对我国印刷行业的智能化发展作出系统总结和未来谋划。《印刷业“十四五”时期发展专项规划》将数字化、智能化作为“十四五”期间印刷业发展的基本原则。人工智能技术持续赋能印刷行业,提升印刷行业的自动化流程,加速各生产模块之间的融合,升级印刷策略。
传统印刷工艺需要多个流程,各个流程之间形成的信息孤岛需要人工去弥合,这成为制约印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巨大瓶颈。实现设备和工厂信息的数字化是智能化的前提,通过智能化的印刷系统将数字整合流通,可实现生产、物流运输的自动化。在智能化的背景下,数字化仅仅是进入智能制造的第一步,智能出版依托EPR信息管理系统统筹生产,优化生产组织流程,提升产品质量,减少人力物力用量,“使印刷设备具有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自执行和自适应的新功能”[5]。智能印刷不是针对单一设备和工厂的升级,而是全系统的升级,实现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最终建立一个按需印制、高度灵活、高度数字化、高度协同化的印刷服务体系。
3.智能平台中的全流程精细化营销
营销作为出版企业与市场接触,实现经济利益转换的关键环节,始终随着市场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时转变策略。传统的发行营销渠道有着高额的空间和物流成本,一旦预期销量与实际销量形成偏差,会造成库存压力和经济损失。智能营销、精细化营销将更加精准地定位用户,实现企业与用户之间的有效沟通与连接。智能出版的精准营销依托智能技术进行市场调研分析、目标读者确定、个性化推送和广告精准投放。具体来说,首先,智能营销通过海量的数据挖掘和分析,了解市场需求、竞争对手的状态以及读者的行为习惯,从而制定营销策略。洞悉读者的行为习惯要深刻理解读者的媒介接触情况、阅读偏好、购书途径、阅读动机等。其次,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用户进行画像,这里的用户画像不同于弱人工智能语境下的粗颗粒度画像,而是真正做到“千人千面”,基于对读者的立体洞察,进一步理解读者的阅读意图,挖掘读者潜在价值,寻找高质量的潜在用户。最后,在智能投放与交互环节,通过确定读者的行为特征和需求,判断最有可能发生购买行为的平台和时间,然后进行广告智能投放,并根据实时数据分析,不断评估投放方案,自动调节投放策略。同时,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客服在与用户的互动与反馈中不断提高智能化水平,“扩大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范围,提升处理效率和准确率,以此减轻人工客服的负担”[6]。
由此可见,技术的日臻成熟使出版企业通过资源配置最大限度降低生产成本,减少生产损耗,提升生产效率,无穷逼近最优生产路径。在出版产业链的各链条内部元素和链条之间,探索最优组合方式,“实现出版企业生产函数的全要素赋能”[7]。
二、技术景观:智能出版的伦理困境表现
智能技术在重构出版产业链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技术风险和伦理失范隐忧,这威胁到智能技术嵌入出版行业的合理性。技术带来的行业颠覆很容易使从业者产生技术崇拜,陷入“唯技术论”“唯科学论”的陷阱,忽视出版行业的文化属性和价值引领。尼尔·波斯曼指出,“技术统治时代的公民知道,科学技术并不给人提供生存的哲学基础”[8]。智能技术形成的景观霸权可能会突破传统伦理遵循,普遍化、隐秘化的技术景观提供虚假的图景,出版相关主体很难看清楚这一点,景观有可能成为合法的社会现实。
1.出版主体的身份危机
人工智能的内在逻辑与人的智能并无二致,通过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类人类”的思维属性逐渐显现。人工智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模仿阶段,具有更高级智能价值的技术将改变人与技术之间的从属关系,如果不加以限制,技术将会突破人类的安全屏障,以及目前的附属地位,从“人机协同”转向“人机共存”。在人与技术关系的移位过程中,技术对人在出版产业链中的主体地位构成挑战,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定位都将发生改变。
对主体性危机感知最为深刻的当属编辑,利用智能技术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编辑,其主动的编辑意识逐渐消解。编辑仅需遵从技术的判断和结论去忠实地执行,个人的编辑敏感、判断能力、职业素养让渡于技术,导致对出版内容把关不足,这实际上打破了传统出版中编辑的角色伦理场域平衡,造成编辑主体角色移位。除了编辑环节,在校对、审查环节,这种主体性的丧失也会造成审查的僵硬化与模式化。人工智能固化的审稿模式在消解艺术审美的同时,还会造成出版人才供给端的生态失衡,会进一步动摇人在出版行业中的地位。
2.文化属性偏离的风险
我国出版业是文化属性与商业属性兼具的行业。出版工作是科学文化事业,具有传承知识和启迪民智的作用,出版以商品销售的方式向大众提供精神文化食粮,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服务性。同时,出版企业又多是文化出版企业,是独立的商业法人,从事文化商业经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这双重属性中,出版人要坚守出版事业的文化本位,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双效发展。传统出版人的文化情怀使编辑着眼于更多惠及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读物,这也是出版人安身立命、立足社会的根本遵循。但智能出版的内容生产流程对传统出版的文化坚守提出了挑战。智能出版全产业链关注用户需求和企业效益,在内容生产编辑阶段,通过对用户个人信息的抓取,生产迎合社会热点、市场需求的产品;在发行营销阶段,依托算法向用户精准营销、定制营销。我们可以看到,大数据和算法的介入使不断优化出版营销策略成为可能,但是对算法一味依赖,又难以避免出现信息茧房和算法偏见现象。
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认为,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人类社会异化和失控,最终使人类失去自我认知和自我掌控的能力[9]。算法是对数据的获取和加工处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信息,由于算法脱胎于真实的世界,所以其充斥着不平等性。算法推荐机制促使平台向标签化的用户推送投其所偏好的信息,这种智能化的“投喂”和“饲养”,使讀者在自己的舒适区内获取极大的精神满足且无法自拔。信息茧房的自我实现使用户很难探寻兴趣以外的其他知识,长久以往将导致个人知识结构不合理,进入“文化孤岛”,对个人价值观的塑造和正常社会交往造成影响。
3.公共伦理失范的隐忧
基于算法的智能推荐影响人们价值观的构建,其衍生的信息要素影响社会的进程与发展,所以算法设计者的态度与伦理规范至关重要。在出版流程中,算法偏见与网络社会所推崇的个性解放等私域价值取向耦合,将有可能带来公共价值取向的偏差。在网络环境中,个人网络出版成为重要的出版形态,个体的主观性创作和用户的自由选择取向成为智能出版时代的重要特点之一。与网络的开放性相契合的是个性伦理,个性伦理遵从于人的内心,将个人作为社会生存的主要主体,个人的社会身份、经济身份都可以摒弃。个人网络出版过分强调自由和个性,以庸俗化甚至是媚俗化的内容吸引公众眼球,而大数据挖掘对这些内容又有天生的“敏感”,这些格调不高的内容经二次创作后广泛传播,影响了智能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当一些个性化内容涉及侵权和违法犯罪时,出版行业面临的出版风险也随之增大,因此其伦理边界亟待规范。
三、技术向善:出版场景中主体责任的伦理嵌入
施普林格·自然公司联合德国法兰克福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算法,并于2019年4月出版了一本完全依托该算法撰写的书Lithium-Ion Batteries: A Machine-Generated Summary of Current Research。人工智能和大型模型赋能智能生成,开创了出版内容生产的新纪元。但是如何评价利用技术手段生成的内容,谁该为内容负责,版权问题如何界定,这一系列问题都需厘清责任主体。保罗·古德曼强调:“无论技术是否利用新近的科学研究,它总是道德哲学的分支,而不是科学的分支。”[8]技术的善用不仅体现在赋权与普惠上,更指向相关主体的伦理遵循。
1.技术向善的逻辑与未来图景
工业化产品更加凸显工具性,使用者与工具之间是纯粹的主客关系,在智能化时代,这一使用逻辑发生了变化,虽然智能化产品的基本属性仍是工具性,但其主流属性是体验性与交互性。这种动态发展的产品形态使技术向善的评价标准变得复杂多变,出版责任主体超越主管部门和企业的范畴,将用户和社会囊括其中。
首先,对企业而言,工业化时代的产品经过监管部门审批之后便可进行批量生产,但是随着企业大量使用智能化技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随之改变。由于产品多处于动态变化中,产品生产者(企业)需承担管理义务,根据用户的反馈和交互数据不断进行动态调整、算法升级和产品迭代。其次,对用户而言,个体的生物学特征、受教育程度和兴趣爱好迥异,其对待同一产品的体验和好恶评价各不相同,因此,技术向善的标准也呈现差异化特征,企业应根据用户特征形成多元化的评价标准。最后,对主管部门而言,规制与管理责任依旧是其核心使命,但是面对个体差异化的喜好,主管部门应从整体和全局着眼,督促相关企业引入专家预估机制,通过用户调查和数据推演,洞悉产品的社会影响以警示用户,撰写前瞻性的“产品使用说明书”。总之,技术向善将以人为本作为最终评价尺度,把技术标准纳入法律准则和伦理框架,真正实现为人类服务。
2.出版实践中出版参与主体的伦理调适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委员会于2021年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明确了人在出版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要求保障人类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确定利益相关主体的责任[10]。先进技术介入出版行业产生的长尾效应,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的善与恶,更取决于人类如何看待和使用技术。在出版产业链的各个链条中,相关责任主体必须坚守责任底线,遵循人类共同的伦理价值。
从编辑视角来看,必须明确其在选题审定、编辑加工、人机协同中的主导地位。在酝酿选题环节,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挖掘选定符合市场需求的拟出版选项,但是在此过程中,存在数据模糊和侵权的风险,因此,编辑需要树立风险意识,不断提高合理合法使用数据的职业素养。在审校环节,应坚持包容性,切实尊重和保护各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不同群体和组织不同的思想及利益诉求。在营销环节,要在智能分发的基础上介入人工干预,不应将用户的喜好作为唯一的推送标准,而应通过人工推送非定制内容来打破过滤气泡,帮助用户构建合理的知识体系。
从出版企业视角来看,要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协商问责机制。在传统出版领域,人是出版流程的唯一责任方,责任界定明确清晰。但是技术的使用使这一责任伦理发生了改变,技术让人类获得搜集和使用数据的能力,但是却无法消除滥用数据和数据失策带来的恶劣影响。因此,要将数据和技术使用的各个环节与相关责任人绑定,由相关责任人来回应责任审查,主动承担责任义务。另外,出版企业应加强编辑对最新技术的使用培训,使其精于利用技术简化工作流程,擅于洞察技术漏洞带来的潜在危机,乐于接受前沿技术所创造的新出版图景。
从主管部门视角来看,建立规制是其工作的重点,应组织人员广泛讨论相关责任方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尽快健全法律体系,维护人与技术的合法利益。由于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快于规制建设的速度,因此在规制之外,还要引入面对变化的快速反应机制。可集合技术、法律、出版等各领域的专家开展前瞻性的研究,对出版物可能存在的问题作出全方面评估,达到提前告知、引导用户的目的。同时,要推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人类技术伦理的良性、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前沿技术与出版业深度绑定,给出版业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出版产业链因为技术的革新衍生新的生产场景和细分市场,出版从业人员的工作逻辑和着力方向也随之改变,这大大提高了出版从业人员的工作效率,出版與用户、出版与社会的融合逐渐深化,全产业链实现了价值增值。但在以技术为新基建的出版框架中,商业逻辑愈发凸显,伦理困境制约了智能出版的发展潜力。因此,必须强化出版产业链中各主体参与者的伦理意识,树立技术向善和科技向善的理念,使技术成为智能出版中“人体的延伸”,正向赋能智能出版。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EB/OL]. (2021-10-19)[2023-09-16]. 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19/content_5643653.htm.
[2]傅国华. 运转农产品产业链 提高农业系统效益[J]. 中国农垦经济,1996(11):24-25.
[3]卢西亚诺·弗洛里迪. 第四次革命:人工智能如何重塑人类现实[M]. 王文革,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4]李玲飞. 人工智能背景下数字出版知识服务生态体系构建[J]. 行政管理改革,2020(10):75-82.
[5]宁廷州,葛美芹. 智能印刷设备的历史回顾、发展现状及有效战略[J]. 包装工程,2019(19):230-238.
[6]朱国玮,高文丽,刘佳惠,等. 人工智能营销:研究述评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7):86-96.
[7]杨旦修,王雨诗. 数字出版产业的增值:数据挖掘与算法应用的发展取向[J]. 中国编辑,2023(5):34-39.
[8]尼尔·波斯曼.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 何道宽,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9]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 NewYork:VintageBooks. 1964.
[10]《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发布[EB/OL].
(2021-09-26)[2023-09-16]. https://www.safea.gov.cn/kjbgz/202109/t20210926_1770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