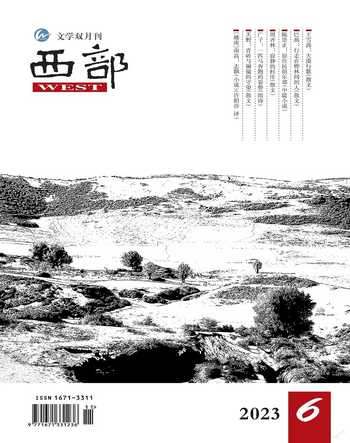青砖与铜镜的守望(散文)
天野
怎么说呢,登长城不是件容易的事。
每迈出一步,脚下所踩青砖都是有名字的。名字可不是一个符号那么简单,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些人里有普通的士兵,也有将领。
每一批修筑长城士兵的名字都写在了册页上,也刻在即将进入砖窑的砖坯上。不知有多少将士的脚印留在了长城上。真是没法说清楚的事。要是哪个人,拍着脑门和胸脯,像相声演员在台上报菜名一样,说得门儿清,倒觉得可疑了。
青砖是有记忆的。
一九八一年的暮春时节,父亲陪同祖父回了趟酒泉。酒泉城里有六十多公里的明代长城。祖父是喜欢旧物的人。没能找到要寻的亲戚。在昏暗简陋的招待所里,祖父以他惯常的慢动作,卷了一支莫合烟,点着抽了一口,又夹在右手食指与中指的指缝里,青烟挡不住他的目光,他看着街道上的行人,向父亲提议去看长城。
父亲嗯了一声。
祖父跟着父亲走出招待所。公交车加步行,在晌午时分到了长城。父亲想给祖父在长城前拍张照片留作纪念,可那时候,照相须去照相馆。待有摆摊照相的人,那都是十来年以后的事情了。
祖父清瘦高挑,目光悲慈。我得知祖父回来后,风一样蹿进他的屋里,他放下手里的搪瓷茶缸,慢悠悠地说起那不成样子的土墙。
我才知道,不是所有的长城都是青砖修筑的。说实话,心里多少有些失落,甚至觉得这个消息不实,怀疑祖父看到的并非真正的长城,而是一座故城的旧址。
世界上的事情很奇妙,有的事情很早就为人所知了,而有的事情至死也无人知晓。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没有哪一个人能穷尽天下所有的事情,包括神仙。
是的,只有在有黄土的地方才有可能烧制青砖,沙质土无法完成窑温一千度裂变的光荣使命。这是一次重生。如此看来,重生是需要条件的。
我第一次面对长城青砖,是祖父见到长城后的第十二年。我像熟悉脸上的雀斑一样熟悉这个日子。
九月十日,空气里挤满果香。我与新婚的丈夫从杭州坐绿皮火车抵达北京。绿皮火车九号车厢的一号座位是靠窗的位置。半开的窗户,视野虚晃飞驰,我一次次想象登临长城的心情。
我们坐车到了八达岭长城。
心情这种东西真是不好说,在滚烫的人流中推搡挤压后,所有期许的美好瞬间被瓦解撕碎。
我胸腔里翻滚一股难以抑制的气流,大有将我就地撂倒的图谋。脸色煞白的我,吓到了丈夫。一脸焦急的他,要我就地休息。粗大的手搀扶我在就近冷饮摊前的凳子上坐下。
姑娘,来瓶汽水吧,瞧你这脸色,还没登长城呢,就这样了,可不敢急着上去。那个大眼睛、短发的中年女人,从冰柜里拿出一瓶橘色汽水。
喝了汽水,又点燃了我登长城的信心。在一个个背影中,我看不清长城的模样,眼前是一块块宽窄不一、高低不一的挡板。
裹在风里的香水味、汗味、玉米味、草木味,还有青砖与黏土的味道,争先恐后挤进鼻孔。我无意辨析更多的味道,只是觉得这青砖味里有一种气息,似乎很久之前遇到过,如今又在这里重逢了。
太阳晒爆了我的皮肤,这是之前未曾料到的事。按说入秋后,阳光就友好温和了,哪里想,偏偏刀片似的,似是一层层揭去皮肤,这疼痛令人无处躲藏。
我扶着青砖继续向上走。
丈夫愧疚地说,太粗心了,应该戴顶帽子,或者带把伞。过去这两样东西并非我日常生活的标配,甚至觉得多余。
我說没事,要不了命,回去缓几天就好了。
我趴在城墙上,端详着青砖砌成的长城,青砖从齐整的墙上走下来,向着东面集结而去。再看,那山谷低处,七八列士兵队伍向上而来,他们身穿布衣,传递青砖,徒手接过来,再送过去。
初夏的风拉长了我的视线,清楚地看到士兵黑红的脸,有的是更浓一层的黝黑。手也皴裂了,掌心一道道深浅不一的裂纹里是黑褐色的泥。若再细看,那个阔面士兵的胡茬里都据守着尘土。
他们那么年轻,想来也不过十七八的年纪,青涩稚嫩得很。在长时间的修筑过程中,他们不止一次望着夜空,想家,想他们的父母和姊妹兄弟们。想来有的也娶了妻,有了尚不会叫爸爸的幼儿。
我望着他们的面庞,不是经年累月从时光里走来的人,而是巷子里和村子里走来的人,也就那么一瞬间,眼窝发热,泪珠落在城垛的青砖上,以万马奔腾的速度散去。泪水是咸的,汗水也是咸的。我没有被别人撂倒,却被这看不见的咸扎扎实实撂翻在地。
一个女人,不管你多大,没有谁要求你必须成为好汉。那是男人们的事情。好汉,不是评判女人的标准。
但我在右脚趾磨出血泡后,咬牙坚持,一点点挪动到写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牌子前,禁不住泪奔,一个胸肌发达的男人蹲下来,拍了拍我的右肩说,不哭。
我想从嘴角挤出一缕笑容,可吝啬的笑容始终不肯出来感谢这个给我鼓励的好心人。
丈夫右手搭在我的肩头,头靠拢过来,蜜月登长城的照片,在宝丽来一次成像相机的咔嚓声中跳出来,穿马甲的中年男人很快把照片交到我的手中。背景就是那块已经疲惫得不成样子的牌子。
风撩起我额头的刘海,脑门亮闪闪,恍惚间觉得那不是我的脑袋,而是一面镜子,发亮的镜子,照出我的脸,以及脸上的疲惫、泪痕和兴奋。
风的肌肤上有可追溯的密码。我的解码从一枚铜镜开始。
提到镜子,真要说一下一九九八年六月在嘉峪关新城乡长城村墓葬出土的魏晋“位至三公”铜镜,这铜镜体量不大,直径9厘米,厚0.2厘米。背面没有几何图案,或者花卉及人物图案,真是素净。许多时候,你会发现,越是素净的器物,越能启动想象的链条。
我站在展柜前,铜镜身影孤零零的样子,唤醒了我的思乡之情。外出三月有余,返回的途中,犹豫再三,我在嘉峪关下了火车。去干什么呢?起初没有清晰的目标,只是想随意走走,毕竟这地方没有来过。
嘉峪关这个名字,无论从历史层面还是文化层面去讲,它都像一枚纽扣,系在大地的门襟上,不管你怎么走,总有一次要经过这里。何况我这个从新疆来的人,出入都需从这里经过。
这座城市与其他北方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穿行在街道上,从不亏待嘴巴的我,打听着当地的名小吃。从早晨开始,烩麻食、搓鱼面、油爆驼峰、烧壳子、丝路驼掌、炮仗面、浇了陈醋的酿皮,一样样在牙齿下碾碎。在血液里我再次与它们相会。熟悉的不仅是眼神,还有共同的美食、文化。别浪费时间,去看看长城,看看铜镜,看看博物馆里的宝贝。
我坚信,脚印就是信使。
年轻的解说员露出职业微笑,为游客讲解:中国新疆、甘肃、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北方长城地带等区域出土的铜镜则多有带柄的草原元素动物纹饰。总体来看,几何纹铜镜和素镜是中国早期铜镜的主流。我对他如此不带感情的描述很不满意,怀疑一次次敲击心房。我选择了沉默,蓝色中加了糖的沉默,以至于在整个午餐时间,我咀嚼青菜的声音胜过铡刀砍下头颅的声音。
是谁?那个按下铡刀的人是谁?那个被砍下头颅的人是谁?难道真是那个没有按工期完成修筑长城的年轻士兵?我的眼里,他不过是一个少年,十六岁或者十七岁,也许会更小一点。暮秋的塞外,寒气带着刺,穿透的不仅是枯黄的叶片,也切碎了这些劳碌了半年,甚至更长年月的稚嫩躯体。
我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里徘徊,偌大的展厅,我和几个陌生人游荡漂移在一件件文物简短奥秘的文字里。我试图揭穿不为人知的秘密,却是超越宇宙的妄想。在那一刻,我靠近箭镞陈列的柜子,握住那枚锈迹斑斑的箭镞,刺向我的胸膛。我甘愿流干躯体的血,只为缝合一块长城青砖的裂缝。让年轻的士兵早日回家,与铜镜前的亲人团聚。
我狭隘地以为,这样会让我的子嗣们在多年后的深秋,不经意间路过这里时,听从长城青砖的感召,进入深邃幽暗的另一端,看到最初修筑长城时,年轻士兵青春的模样。
站在青砖城墙前的我,似已被时光侵蚀。慌张是有的,不过压制在血管与怦怦跳的心里。我并没有漠视过,从来都没有。我小心、乖巧地注视铜镜,亦如我注视长城的青砖一样。我坦诚面对它,正视它的残缺、暗淡、凋敝、颓废与不安。亦如面对自己出生到现在的悲伤、怯懦、恐惧、无知和期待一样。
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宁静忠实地面对自己,每一块青砖也是一面铜镜,清晰照出我清醒的心绪,不再畏惧那可怕的嘲笑、蔑视、焦虑和谎言。我接受一切,亦如长城接受坍塌、溃败、侵蚀、冷落与消亡,铜镜接受暗淡、锈蚀、遗弃与忘记。我与它们有一样的终极宿命,只是它们演化成一种精神,无色有声地进入人们的血液里,任何溢美华丽的词对它们都不过分。我只是想,我这个比尘埃都微小的人,多么渴望在某年某月的一天,在空气里风驰电掣般扑向一个附着物的时候,会有幸落在青砖上,落在任何一处长城的青砖上或者腐朽的铜镜上,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
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女儿,是一个妻子,是一个母亲,也不能忘记,我是一个姐姐。妹妹小我四岁,属虎,凶猛不代表她真实的表达,我甘愿在她遍体鳞伤后守护在她身边。
我那矮小戴着流苏耳环的妹妹喜欢照镜子,随身带着镜子,她没有铜镜,是一枚小小的普通镜子。看着她照镜子的模样,仿佛回到我们年少时手拉手买冰棍的幸福时光。她是一名边疆卫士的女儿,她的刚烈、勇敢、旷达遗传自那个在边境线上驰骋守边的父亲。
我想送妹妹一枚铜镜。何止是妹妹,那些千百年以来,家中有男子奔赴边疆的女人们都渴望一块铜镜,铜镜里有亲人熟悉亲切的面容。一次次月缺月又圆时,她们不会孤单寂寞。
在慕田峪,修葺一新的长城,机械化生产出来的青砖依然保留着原来的模样,可断然失去了烧制工匠的体温,也没有留下一枚工匠的指纹。
我背弃了对同伴的承诺,逃兵似的,偷偷向右转,急切地买了一张缆车票,向六号垛口的方向跑去。
座椅式缆车,朴素静温的椅子,悬浮在空中,零距离接触树木,分外欢喜。俯视山谷里的侧柏、紫椴、蒙古栎、糠椴、胡桃楸、葛藤、小叶白蜡、山杨、油松,以及林间的酸枣和荆条。
我将远山与缆绳收纳起来,轻放进我的口袋里。
一方垛口就那么大,相机锁定的画面也那么大。用物理的概念来描述没有意义。当年驻守这里的将士们熟悉了長城内外深深浅浅的景致。
他们中,戚继光是最为人熟知的一位将领。明隆庆二年(1568)夏,从南方快马飞驰来的他,是蓟镇总兵,带领兵卒民夫,东起山海关、西到居庸关,完善了长城防御设施。
这个初夏,我从西北以北的地方再次登上慕田峪长城,立于楼台里,目光抚摸残缺的青砖,它似乎早忘记了伤痛,那藏着秘密的豁口,已经成为伤口愈合后的一块印记。向我诉说曾经在这里响起的震耳的炮声、佩刀出鞘的声音、鼓手敲击军鼓的声音,以及远处古刹里传出的雄浑绵实的钟声。
我必须记录下此时正欲搭乘阳光的羽翼向西而行的云朵,它不会偏离航向,在嘉峪关以西,还有众多的烽燧、青砖砌成的城墙和锈迹斑斑的铜镜。它们与我脚下的这段长城血脉相连,都在扼守边防。
谁能告诉我长城青砖的数量,谁又能告诉我将士们亲人手里有多少面闪着光芒的铜镜。这样无解的追问,一次次令我感伤,虚无的想象倒是绵密悠长。
一只松鼠,从楼台一角跳到椴树枝上,以报信者的身份告诉我,每一块长城的青砖都是一枚图章,不是盖在北方辽阔的山川,是盖在修筑者妻子和亲人的心上。
我也是丈夫的妻子,我也会跟他们的妻子一样,心中的夙愿是登上长城,不是看冒着寒光的剑戟炮枪,是想确认那个刻有亲人名字的青砖,以及墙缝间编织井然的蛛网。
丢开时间的鞭子,我和更多的人,走向长城深处,那里你我不再孤独。这里有青砖,有铜镜,也有安抚彼此的狂风、星辰和熟悉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