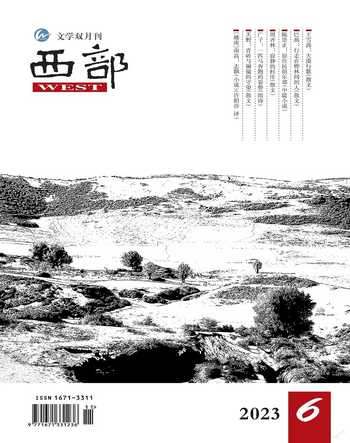他写诗的手多么镇定(组诗)
周舟
羽毛在飘
羽毛的每一次离开
都会有一种沉醉
仿佛夜晚对梦境的信任
——一个任性的词语
身体的边缘
镶着有弧度的金边
林中空地
为了证明林中有一块地是空的
树木后退了一大截
中间又多出一块石头
树木这时几乎不明白自己
是杉树槐树抑或红松
他们热爱的影子与影子
重重叠叠
鸟在拉一张大网
辨不清是什么鸟
鸟只把声音落下来
但空地上什么也没有
整整一个下午
太阳在森林头顶行走
地上卻没有什么变化
而林中空地的石头上
已多出一副安静的棋局
舒家坝一夜
黄昏时分我们
才到舒家坝
你躺在那儿
让我们感觉黄昏
就这样来临
好几次来看过你
只有这一次让人觉得多余
坐下来不对
站着
还是不对
一只手握着一只
越来越凉的茶杯
一只手
把香烟卡在手指间
像是盛着时间的盒子坏了
手一抖动
就掉下你的声音
殡仪馆
没有暮色也下沉
事物下沉
只显现灰蒙蒙脊背的生活下沉
此刻是早晨
早晨下沉
这里不只我一个人
但我一个人盯着青烟自高高的烟囱
鸟伸展羽毛那样往上飞
我很听话
站在山上
九点钟的太阳不升起来
哦,殡仪馆的空旷照着我和我们
蜘蛛
墙角的那团网状物什
因为并没有蜘蛛
还不能算是蛛网
也许是一些不愿离开的尘埃
相爱着
当我这样想
马上意识到
我在这个房间已经住了
快二十年
此刻的我就位于它的右下方
但此刻的寂静
正把某个关节捏得咔吧响
像是持续了一会儿
我看见光的粉尘飘浮着
又在我身上歇下来
于是我猛地战栗了一下
可我的战栗似乎有着
腾挪的技巧
就在我扭头去看的时候
发现一只蜘蛛恍惚之间
已经爬到了蛛网上
洗杯子
洗到最深处
杯子可以只剩下玻璃
一遍一遍
玻璃也可以消逝
只有水
越来越具体
伸一下水的脖颈
并看不见水的脚趾
看见的时候
一只鸟
在左手与右手的枝条间
跳过来又跳过去
死亡的体积
他们在侍弄一只盒子
专注紧张
袅袅香烟绕过手指
接着绕过众人的面孔
很多事开始模糊又开始清晰
清晰了又变得模糊
直到盒子与土地融为一体
这些绳子绾在一起的烟缕
还不解开
还不散去
像有人反复将手
填进火焰里去
这时死亡才仿佛渐渐形成
让包括一排杨树
一朵云一只落在树上的鸟
和一片空旷地带在内的所有事物
秘密集结
像是死亡有庞大的体积
早间日记
摸黑吞下一粒药片
踅身再次躺下时
竟有点恍惚
新的一日
是否已经将药片吞服
多年了
这些耀眼的颗粒状物体
在漆黑的胃里
仿佛一直拒绝融化
作为一方浩渺的星空
它既与我疏离
又与我明显对峙
净土寺
从寺院出来的时候
香烟袅袅
他敲钟,只把手臂抬起
他叩头,头尚未着地
香烟袅袅
寺院的寂静尚未到来
我离开
只是给寂静让开一条甬道
在医院门诊大厅
在熙攘的医院门诊大厅
一个埋头写诗的人看过去有点孤独
他在手机屏幕上开着这个世界
从未曾见过的处方
大厅的人不断增加又不断消失
寻找着窗口,房间,白色床单和药片
医院的光线会不会
把他的脸一直涂成白色的
他写诗的手多么镇定
看上去就像一只剧毒蜘蛛
孤独的光
昨天晚上
他和自己一生里所有的事件在一起
他惊异所有的事件一件一件
都是砖块
有人命令他用它们
盖一间房子砌很大的窗
把月亮也砌进来
可是他的手里还有一件事
像是用尽所有事件之后剩下的一件事
他不知该把它搁在哪儿
试试所有办法
最终他把它隐藏
不留线索
盖好的房子一下子空起来
桌子上落满灰尘
看不见的月亮用低音说话
听不清它在说什么
但他身上有一种孤独的光
一瞥
从殡仪馆出来
能看得见
背后的天空
正被什么覆盖
死亡待在房子里面
像盒子套着盒子
死亡在盒子里
讲一个死亡故事
这时候的声音
是死亡给的
他带好死亡分给他的那一点点
站在院子里
有点茫然
前方的天空
正没入黄昏
但一扇门
还卡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