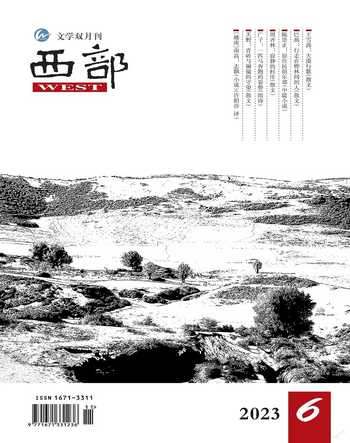小海子之冬
骆娟
1
11月17日。早上7点,我们乘坐的夜班车抵达了福海县城,第一个目标,是直奔距县城15公里的福海渔场。渔场住着渔翁哥,我每次来福海时都能见到,这次便也是先奔着他而去。
从我们到达县城开始,他已经和我们通过几次电话,掐着时间把狗鱼、红眼鱼轮番炖进了锅里。等到我们几个人呼啦啦涌到他家里,他正端着鱼往桌上摆呢!
下午,按照计划,我们要先去南大湾,那里有渔翁哥和同事的巡海小屋,可以打尖落脚,然后去寻找天鹅。我前一年春天来时,渔翁哥他们住在盐池那边的巡海小屋,现在又轮换到了南大湾这里。
被人们称为小海子的吉力湖,与大海子乌伦古湖相距很近,省道318线从两湖之间穿过,看起来倒像是两个海子间的一道界线。小海子和绵延数公里、素有“海上魔鬼城”之称的雅丹地貌相映相照,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总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因为地势的影响,小海子的西岸形成了蜿蜒的湖湾,这些背风和暖的湾岸,便成为天鹅迁徙途中栖息嬉戏的地方。
我们跟着小鸥到了南大湾的小屋,按照渔翁哥的交代,从一个秘密的地方找出了屋子的钥匙,一开门,竟然有一只黄狗蹿了出来。黄狗冲着我们几个陌生人狂吠,但没多久,它就和我们成了朋友。
已是傍晚,天空浮涌着浓重的云层。站在南大湾小屋的位置上,空旷的沙滩从海子边向上方倾斜,远处是更宽阔的旷野和隐约的远山,而天空正携带着翻卷的云翳向着地面倾斜,整个天宇仿佛不再是一个混沌的空间,而是只留存着云与海的两个平面,在地平线的位置交接。此刻,我们所处的位置,便是海子边,是天空自地平线开始,用巨大的荫翳最后覆盖的地方,也是天空自海面开始,用细微的波浪最先掀动的地方。
我们决定留下来了。因为赶上过古尔邦节,巡海值班的人有休假的,我们便借用了南大湾这个小屋——里外两小间,客、卧、餐、厨一体。欧阳老师歪到床上休息了,小鸥穿上水裤到海子里去打水。我和阿倩站在门口,面对的是南大湾的海子沿,说话间,小鸥提着水桶上岸向我们走过来,那只被我们乱起名字叫作阿洪的黄狗紧紧跟在他的身旁。他边走边张望着察看天色。
好像就在这时,我们才注意到,阴云之下,黛色的湖面上微微翻涌着波浪,小小的水花像鱼儿在水面穿梭,一只长腿黑鹭绕着一片芦苇丛在低飞徘徊。那其他的鸟呢?那些在我们的期待中比翼高飞、盘旋嬉戏的鸟儿呢?
小鸥自然是明白我们的心思,他左手一个桶,右手一只壶走着,用力摆动头向我们示意着远处,我们抬眼向西北望过去,原来,在前方的一个湾子里,可以隐约地看到——天鹅。
那应该是一家子。我们隐约看到的两只白色的,自然是天鹅爸爸、天鹅妈妈,还有半隐半现的三个深色的小东西——那应该是这家的三只天鹅小宝宝了,黑灰色的小身体,几乎被波浪淹没。
夜幕很快就要降临了,我们决定等第二天天好了再去拜访这天鹅一家。小屋里热乎乎的,一台小得很夸张的黑白电视机播放着唯一能收到的中央台新闻频道节目——亚运会的实况。时而有人向炉子里添些煤,那用铁钩拨开炉圈的声音突然间把大家都拉回了小时候。
三张铁床,我们搬移了一番,做了分配——里屋我和阿倩挤一张,外屋欧阳老师单独一张,小鸥和渔翁哥挤一张。这个巡海人的小屋,改变了我們在海子边露营的计划。我们便偎着这旺旺的炉火,聆听着窗外的海风。
夜里,我们睡得并不踏实,除了黄狗阿洪奇怪的呜咽声,还有欧阳老师凶猛的呼噜声。我们在半睡半醒间,期望风向转为东南,这样就可以吹开倾覆在海子上的云层,给我们一个晴朗的天空和安谧的海子。
2
11月18日。不知是谁先醒来的。“天还是阴的!”第一个跑出去看天色的欧阳老师通报了这让人有点沮丧的消息。“可我夜里出去过一趟,明明看到很多星星啊!”阿倩蜷在睡袋里动都懒得动一下,但说话的声音却很大。“有风就好了,有东南风就可以把云层吹开!”小鸥的这句话,我们从昨晚到今早已经不知听他叨咕过多少次了。
天阴着,也许鸟儿们此时是在那些晴朗的地方,是在从另一个栖息地迁徙于此的路上,是在天空更高、海子更远的那些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这就意味着,我们还需要等待。
海子边上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单调。将近中午,小屋里的四个人都悄无声息,时间到底是飞逝而过,还是游移彷徨,我们似乎并不关心,因为这间小屋好像凝滞在时间之外,并没有任其载动。
突然传来欧阳老师兴奋的喊声:“看窗子那边!”原来,这屋子唯一的那面窗户,正透进来一缕阳光,它没有直射进屋里,而是斜斜地投映在窗户旁的墙壁上——是光线过来了!
还没等大家都兴奋起来,先跑出屋的人就发现,天依然没有晴,从云层中漏下来的几束光很快就消散了。但我们还是决定出发了,先去看看南大湾西北岸的天鹅一家。
南大湾这一带,在我们之前的观鸟经历中,是鸟儿们比较集中的一带。几年前的清明节时,我们就在晓华和小鸥的带领下,在这里看到过大群的赤麻鸭、赤嘴潜鸭、灰雁,还有天鹅。但此时这个季节,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飞掠而过的鸟儿们,却踪影全无。
正午过后,海子上的波浪慢慢地平息了。我们伏着身子悄悄地潜到岸边,一边走还一边轻声嘟囔着:“我们不是来拍你们的,我们是路过,我们是路过……”据说这样子可以把信息传递给天鹅,让它们相信不会被我们所惊扰。阿倩猫着腰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还不忘说上一句:“想起一个成语——掩耳盗铃!”
我倒是没想起啥成语,蒙着头根本看不到前方,只顾得上一步一步往前挪,嘴里轻声说着:“我们是路过,我们是路过……”没想到欧阳老师却童心大发,紧跟着说:“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弄得大家憋着笑差点栽到地上。
我们到达了事先看好的位置,轻手轻脚地架好了机器,缩着身子坐了下来——天鹅,一家五口,就在我们对面的海子里,漂着,它们好像是到了午休的时间了,竟然都不怎么游动。
天色阴沉,海子里的水是像天空一样灰暗的色调,微微的风摇动着水面,泛不起白色的浪花,只是缓缓地涌动,那巨大的涟漪恐怕延伸到了整个海子,否则我们面前的水面不会只是一道道平缓的波纹。
天鹅一家五口,就在这宁静的湖湾里,在我们的面前漂来游去。它们交替着排列,却与岸边始终保持着一致的距离。羽毛洁白的天鹅爸爸、妈妈,还有三只灰扑扑的天鹅宝宝,叫它们什么呢——就叫老大小白、老二小小白、老三小小白爱斯吧!
浪潮轻轻地向着岸边推拥着,一些细小却坚韧的芦苇根茎在浪潮一遍遍的冲刷中形态显出近似于鸟雀的奇异,似乎是曾经在这岸边踱步啄食的鸟儿们赋予过这些根茎更生动的生命,又似乎是它们原本就是这样变幻着的。
那么,现在,海子边上,还有什么呢?那些在海水涌来又退去的时候,遗留在沙滩上的小卵石,那或面对海子,或朝向天空,或半陷在沙滩,或沾满了沙粒的小卵石,它们的颜色——纯粹的黄或者黑、白,最多的是掺杂着红色的,大约是此刻海子边上最璀璨的色彩了,而那被潮水细致地抚摸着、被沙滩温情地承托着的小卵石所泛出的,大约是此刻海子边最亮丽的光泽了。
在我们的注视中,天鹅一家渐渐放慢了漂浮的速度——本身就很慢,到后来就像静止了一样。
这是一家疣鼻天鹅——它们棕黄色的头部、赤紅色的嘴和前额上的黑色疣突是最好辨认的标志。它们号称最重的能飞的鸟类,也是天鹅中体态最优雅的。它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哑天鹅”,因为它们是天鹅中最少发声的。果然,在后来我们与这一家天鹅的相处中,自始至终没有听到它们的鸣叫。
3
天鹅一家还是按照先前的队列,保持着距离,然后,各自做出了睡觉的姿势,天鹅爸爸、妈妈长长的脖颈枕在自己的身上,头埋进了翅膀里面,安心地睡着,小天鹅们也学着父母的样子,乖乖地各自睡着。
隔一会儿,天鹅爸爸或者妈妈会轮流抬起头来,四处张望一下,又放心睡去;而小天鹅们都一动不动酣睡着。
那时,整个海子都好像处在静止的时间之中,湖面凝滞得如同蓝玻璃的镜面。天鹅——就像我小时候喜欢的玻璃天鹅瓷器,晶莹剔透地摆在桌面上。
天鹅漂浮在湖面上,微风吹不动波澜,也吹不起尘埃,它们沉睡着,在这样美好的午后,我们伏在岸边,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既怕惊动了它们又想弄出一点动静看看它们的反应。
我想此后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想起这个海子,我一定就会想到守在岸边的这一刻。
天空没有云彩和光线,海子没有波澜和喧哗,天宇沉静广阔到无限,又好像全都包裹在蚌壳那么大的一点空间里——没有鸟群飞过,没有猛禽聒噪,没有狂风卷浪也没有冰封雪锁,没有乌云沉落没有灼光炙烤,没有风沙追云逐月,没有时间飞速掠过。
除了沉睡在海子里的天鹅一家的白色,除了天空和湖面交融在一起的深沉凝重的蓝色,除了脚下的湖岸沙滩和远处的旷野呈现着沙粒和土质的原色,竟然,再也没有其他的颜色。没有芦苇青翠的颜色,没有草叶嫩绿的颜色,没有野花鲜艳的颜色,没有季节交替和日月轮回的颜色。
而声音呢?我们一直没有听到天鹅的叫声,没有那高昂的鸣叫,也许就意味着它们的生命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暂时,没有奔波,没有辛劳,没有离别,没有如漆似胶,没有嗷嗷待哺。天鹅一家,已经成为稳定而安宁的生命结合体,正有这样的一隅,安置它们平静的生活——哪怕只有一天,或者一刻。
当大家以放松的状态站直身体准备离开岸边时,天鹅们警觉地醒了过来,也许它们很快就感觉到了我们的善意,并没有慌张地游走,而是舒展了身体,又开始在海子里游动。
已是下午时分,从东南方向吹过来的风,缓缓地掀动着南大湾的这面蓝玻璃。一些越来越明显的波纹泛动在天鹅身旁,但奇怪的是,湖面竟依然是那么平静,湖水甚至比之前还要清澈,于是,天鹅们游动的身影,便倒映在湖面的波纹上,它们的游动并没有搅乱波纹,而那波纹的延展也并没有模糊它们的身影——我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了,边走边回过头望向湖中。
天鹅爸爸、天鹅妈妈一直以守护的姿势游动在小天鹅身边,小天鹅们此时都乖乖的随从着,身影也倒映在湖面上。
湖面的水波缓慢地闪着细微的光亮,可能是周围一直太寂静的原因,此时总觉得可以听到一点声音——是什么声音呢?也许,就是水波摇动的声音,是光亮划进水波的声音。这声音是风从幕墙一样矗立在对岸的海上魔鬼城刮过的声音,是水蜿蜒而来自河口汇入湖中的声音,是云层之上阳光闪耀拨动时光的声音。这声音就来自并不遥远的阿尔泰山,来自自东向西奔流的额尔齐斯河,来自天上飞鸟迁徙的路途,来自牧区畜群转场的路途。也许,这声音,就来自我们自己吧!
那一瞬间,我们都面朝海子伫立着,面朝着天鹅一家和天鹅置身的天宇;那一瞬间,我们屏息沉默,聆听着那海子的寂静,并不担心那寂静会消失,因为,就在它从我们的身体穿越而过的时候,我们也将自己交给了它。
我们改变了下午返回县城的计划,决定留在海子边上,留在南大湾的巡海小屋,守着天鹅一家,等待天鹅群的归来,等待阳光灿烂的新的一天。
4
傍晚,欧阳老师穿上水裤准备去打水,我们也先后出了屋子,黄狗阿洪围着我们几个的裤脚扯来扯去,在前方的那个湾子里,还可以看到天鹅一家的影子,因为距离太远,只能想象它们此时的活动了。
阿倩逗着阿洪蹦跳着跑向屋子西面时,突然发现了晚霞——是满天的晚霞。 欧阳老师第一反应就是冲进屋里端出相机和角架,小鸥也接过欧阳老师的水桶边往回急走边喊我们:“快拿相机!”
大家统统取出了各自的家伙什,面朝西面一字排开,晚霞每一分每一秒急速地变化着。几乎是一喘气的工夫,天就变黑了。
到现在想起来,我都说不清楚我们所拍下的,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美的晚霞,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不是天空所展现的,那么美的瞬间。
那是在海子边的巡海小屋前,我们面西而立,原本在阴霾的下午向着地平线倾斜的天空,此时不知是被什么支撑着,竟然展开了巨大的天幕,厚厚的云层开始浮动,光线从更远的地方投射而来。而此时海子里的水依然是深沉的蓝,那天空不知是被什么如泼墨般地染成艳红。像一团熊熊的大火在燃烧着,用尽了空气中所有可能燃烧和散射的成分,又像一匹新染的红绸在招展着,用尽了地底下所有可能添加成颜料的成分,还像一个瑰丽的梦境在呈现着,用尽了我们所有可能达到的想象、释放的感觉、奔涌的渴望——我们只是静静地站立在那里,架在角架上的相机所使用的那几分之一秒如何能记录下来——这寂静的海子边从天而降的惊艳!
这是我从没有见过的晚霞,或者它早已出现过,可我从没有在这样开阔的地方——这样如海面如山峰如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见到这般景象。
晚霞消失了,我们依然站立在飒飒而起的风中,眺望着远方,黑夜的脚步似乎訇訇而响,向我们大踏步而来。是黑夜向我们走来,还是我们随着脚下的沙滩、巡海小屋、南大湾、整个海子,一起转向了黑夜。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我带着疑问的腔调念叨着这一句朝向欧阳老师,他肯定地点点头说:“晚霞行千里!”
那明天,不就是一个晴天吗?!
我们揣着一种小小的激动,从里面紧紧地扣上了巡海小屋的门,期待一觉醒来之后的惊喜。
渔翁哥临时有事回渔场去了。风是从半夜刮起来的。那会儿,阿洪在屋里不停地呜咽,又到处翻动,不时传来什么东西被顶翻扯倒的声音。等到早上我们才看清它把屋里弄得乱七八糟,桶子打翻,菜筐扣倒,也许是天气让它这样焦躁不安。
无法表述我们的沮丧心情,因为天依然阴着,风并没有减弱的势头,东南方向的地平线上露出一抹鱼肚白,等了半上午也不见有什么变化,原本是希望风把云层吹开,此时反而是风在压制着云层的变化。海子就这样被包裹在阴霾之中。
我们站在门口远远地眺望着天鹅一家的那个湖湾,风大浪急,隐约觉得它们还在那里,却怎么也看不清楚。
是走还是留,我们都看着欧阳老师:“谁说的晚霞行千里?!”小鸥拿出手机给渔翁哥打电话:“我们没吃的了,断粮了,给送点吃的来吧!”
算起来,这是在海子边的第三天了。我们已经吃完了渔翁哥给打包的鱼,吃完了渔场带来的大白馍头和自带的方便面,最后一顿饭是煮了巡海小屋的挂面和大白菜。几顿饭虽然清淡,但是几个人在小屋里围着小桌子,坐的坐,蹲的蹲,还给阿洪也吃了馍馍蘸鱼汤,其乐融融。
快中午时,渔翁哥大衣棉帽围脖全副武装地骑着摩托给我们送来了食物,又联系了渔场的车来接我们,把这些交代好,他就匆匆巡海去了。
看风势,如果待下去,沒准天气会糟到把我们困在海子上。撤吧!只有撤!我们离开的时候,像收拾自己家一样把小屋拾掇好,又按渔翁哥的吩咐在炉子里压好了煤,只有一件没听渔翁哥的——他让把黄狗锁在门外,大家不忍心,还是把它留在屋里了。
离开海子前,还有最后一件事——大家已经有了默契,要去那个湖湾再看看天鹅一家。
当我们顶着风来到湖湾,只见风卷浪急,在没有任何遮蔽和依靠的海子上,天鹅一家正随着浪涛浮动着。
夜里,在县城宾馆的房间里,我被狂风肆虐的声音搅扰得无法安睡,没有想到惯常在吐哈盆地和南疆风口见到的大风也会出现在这里。
在海子边上都没有感觉到的恐惧,这时候越来越深地渗进了我的心里。好像此时我正在一个小船上,几乎要被风浪淹没,我竟然没有任何力量抵挡这一切。很久未犯的偏头痛也像风一样袭了过来,而令我辗转难眠的,还有南大湾的天鹅。
这风显然是比我们离开南大湾时要大很多,而且根本没有停缓的迹象。
我用了所有想象到的可能来猜测天鹅一家五口的状况。就算是有一小丛芦苇也好,也能让这家天鹅有点遮挡,可是海子上除了风只有浪。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无所躲避的天鹅,只有用它们自身的体质抗拒风寒,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它们万里迁徙之中所历练到的力量。
但是,这样巨大的像要把房子都吹倒的风和在海子上掀风鼓浪所产生的后果,会不会伤害到天鹅一家呢?它们会被风吹散吗?
5
11月20日,我们迎来了此行到福海后的第一个晴朗的早晨。
风平浪静了。虽然我想象了天鹅的各种不测,但趴在宾馆的窗前看阳光洒向街道和行人,远方的天空碧蓝如玉时,我相信,天鹅一家一定安然无恙。
在我们的行程计划中,这天是要在县城休整,到傍晚时坐夜班车返程。其实,真想再去趟海子边上,去看看那天鹅一家。
等我们再见到小鸥时,他竟像知道我们的心思一样,抢先说:“走吧,收拾装备,咱们去海子!已经跟老渔翁联系好啦!”这意外的惊喜让我和阿倩都欢呼起来。如果不是昨天撤离巡海小屋,我们今天早晨一定会拍到特别美的海子日出。想到这一点,虽然有些遗憾,但能立刻出发到海子边去看天鹅一家,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弥补了。
乌伦古湖一年南来北往迁徙停留的鸟类无数,天鹅也有数百只之多,而此时我们所挂念的,只有这五只,因为它们是我们在海子边守了三天所见到的唯一一队天鹅,因为,它们是一家。
到渔场后,按我们的想法,本来想第一时间就去南大湾看那天鹅一家。但小鸥沉得住气,带着我们先去了中海子——天鹅湖。
中海子在渔场的南面,省道318公路旁边。每次坐夜班车来福海,都会在路过中海子时迎来黎明。这里也是小鸥最钟爱的地方,因为他就是在这里拍到了最完美的照片——一对天鹅情侣。
按说大风降温之后,海子边沿会结冰,冰水交接又没有封冰,是天鹅最喜欢的地方。中海子的湖边倒是结冰了,枯黄的芦苇荡和蓝得让人心疼的天空是拍天鹅的最好的背景,但奇怪的是,竟然一只天鹅也看不到。
“难道它们还没有回来?”小鸥说着转身问我们,“今天几号?”“20号。”“去年我就是20号这一天在海子边看到的大批天鹅,今年……”
乌伦古湖的季节、气候、环境都已经到了最适宜南迁的天鹅休栖的时候了,可,天鹅到底在哪儿呢?
离开中海子,我们转从小海子的东北方向前往南大湾。这里有一处面积不小的水面,当地人都叫后泡子。
我们沿着湖边的土路向前行驶,路旁是引湖水开荒种植的葵花地,大家不停地向后泡子方向眺望着,突然间听到欧阳老师大喊一声:“停车!天鹅!”大家的心一下子都揪了起来——随着他手指的方向,我们真的看到了一队天鹅。
这是大天鹅,它们爱结群活动。与它们相比,南大湾那边的一家疣鼻天鹅是喜欢独处的。我们远远地停下了车。因为怕惊扰到好不容易发现的这群天鹅,相隔很远大家就开始俯下身子向前挪动,最后蹲在后泡子外沿的土丘下面观察。
后泡子的水面上,有十几只天鹅,还有许多野鸭,它们自在地游嬉着,丝毫没有察觉到端着器材伏在土丘后的我们。
透过云层的光线似乎对后泡子有着特别的眷顾,刚好将这一带的水面笼罩在光亮之中,加上湖水自身的反光,整个后泡子显得比周围都要亮。而周围低矮的土丘和起伏的灌木,竟然像是这幅画面的一个天然的框边。
于是,不远处的渔场建筑、顺着公路和湖滨布设的电线杆、高耸的烟囱吐出的浓烟,都在背光的地方成为一种带着虚拟效果的背景——尤其是那些建筑和电线,这种人类社会的痕迹在这样的光影交错中,似乎并没有显得突兀。
云层在半空浮动,光线也慢慢地产生着微妙的变化,水面上泛起波纹,是那种细碎的吸纳着光线的波纹,湖水随着这波纹向岸边涌着,直到结冰处又向湖中涌回,而在与湖岸相结合的地方,那些冰面也按着一定的规律分布着,形成了一道宽大流畅的弧形,在阳光下显得晶莹透亮。
后泡子里有一道苇丛,原本暗淡的枯黄芦苇,在光亮的映照和湖水、冰层的衬托下,显出了一种极生动的黄色——像依然附着了生命一般,带着向上生长向四周扩展的力量的黄色。
接近中午时分,可能也是鸟儿们吃午饭的时间吧,不少天鹅都把头潜入水中,捕捉着食物。几只灰褐色的亚成鸟跟在各自的天鹅爸爸、妈妈身边游动,长颈扭转,一副未谙世事离不开照顾却又以为自己成熟了的样子。偶尔,有一只大天鹅在水面上挺起身子,扇动着翅膀——也许它并不想飞,只是想这样表示它的好心情吧!
这样的一个中午,谁的心情能不好呢?
我们慢慢地爬上土丘,蹲在那里继续按动着快门——距离并不近,那快门清脆的响声自然惊扰不到天鹅,但我却希望它们能听到这声音——除此之外,我们又能用什么来表达对它们的爱?
如果也有和它们一样洁白的羽毛,有和它们一样宽大的翅膀,有和它们一样优美的脖颈,我们一定不会像这样偷偷地伏在土丘上,一定会展开翅膀,向它们飞过去。或者,不需要和它们一样洁白的羽毛,不需要和它们一样宽大的翅膀,不需要和它们一样优美的脖颈——我们只需要成为这海子里一种最最普通的鸟类,就能够和它们在一起了吧——就像此时正游动和飞舞在大天鹅身旁的那些野鸭、灰雁、海鸥。
突然,蹲在我们前方不远处的阿倩指向天空,向我们示意着——那是天鹅,是一队从海子的西北方向飞来的天鹅——我们都差点叫出声来——天鹅飞过来了,虽然是排成了一队,却只有三只,它们从我们的眼前飞过,从我们屏住的呼吸和急骤的心跳中飞过——这羽族里的最善航者,这大自然中最美的航行者。这是我第一次这样真实而确切地看清它们的飞翔——它们长长的脖颈笔直地伸向前方,翅膀有力而稳健地扇动,它们的方向坚定、神态安详。虽然看不到它们的眼神,但已经完全可以感觉到,它们视千里迢迢狂风雾霭霞光霓虹如平常,在那万米高空之上,它们的身体映着正午的阳光,它们携带着这光亮和内心的航标,目光如炬,心无旁骛地从我们面前飞过,经过前方的云层之后,在我们的视线中,越来越远,越来越小。
这时,欧阳老师走过来问:“注意到这群天鹅中最后的那只吗?” 我摇摇头。他把相机举起来,让我们看显示屏,在放大的照片上,最后那只天鹅的毛色明显地和前面两只不同——一只亚成鸟——原来,又是一家子。
这一家子,让我们更惦记南大湾那一家子了。那一家五口现在怎么样了?
6
十分钟后我们就赶到了南大湾。远远地,看到了天鹅的身影,数了数,一家五口一个都不少,奇怪的是,旁边竟然又增加了几只。
我们依然用近乎匍匐的姿势接近了南大湾的岸边。欣慰的是,在拉近的镜头中,天鹅爸爸、天鹅妈妈,老大小白、老二小小白、老三小小白爱斯,这一家依然像我们第一次看到时那样,安然、温情。
在天鹅这一家的旁边,还散游着几只天鹅,是两只疣鼻天鹅和一只亚成鸟——三只,十分钟前我们在后泡子看到的,从天上飞过的,不就是这样的三只吗?难道它们落在了这里?
对我们的疑问,小鸥肯定地点了点头——一定是它们。我们喜滋滋得像自家迎来了贵客那样看着这个变得热闹的湖湾。
才经过了一晚风雨的小白、小小白和小小白爱斯,紧紧地凑在一起,好像一夜的风雨让它们更加懂得了手足之情,天鹅爸爸和天鹅妈妈略显得有些疲惫但丝毫没有松懈地守在小天鹅身边。对于新来的那家,它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热情。
那么这新来的天鹅一家三口,那只小天鹅,叫它什么呢?还记得在显示屏上放大的照片中,它身体黑黑的,那就叫它小黑吧!
小黑显然要顽皮一些,自个儿游着远远地离开爸爸妈妈,玩一会儿再游回来,再过一会儿又游走,看着它不知疲倦的样子,让人真想去轻轻拍拍它那小脑袋。
我们正在美滋滋地看着这两家天鹅。半空中突然传来特别的响动,抬眼一看,原来是一群野鸭。它们扑腾着胖乎乎的身体,人字的队形排得稍显凌乱,像赶场子一样有点慌张地从海子上飞了过去。
还没等我们从半空收回视线,又有一群鸟自西北方向飞来,待稍近点大家都看出来了——那是一队大天鹅,它们排成人字形,整齐地飞来。
天鹅朝海子的东南方向飞远了。从天色上看,从南大湾往东的地方都在厚重云层的覆盖下,往西的后泡子方向则还处在晴空之下。我们决定先追着天鹅向东,看看它们的落脚处。
距离码头湾子东南将近二十公里的地方,是海上魔鬼城最后延伸处,雅丹地貌已经不明显,却还是像一堵城墙一样挡在海子边上。这自然也成了天鹅栖身地。等我们奔到这里,果然看到了几群天鹅。它们在冰层围绕的一处狭长湖滨休栖着。云层越来越厚重,在海子的上方蔓延着,湖水也因此变成了凝重的深色调,仅仅是在我们来的方向,还有一片晴空。
向那片晴空望去时,才发现,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似海市蜃楼一般的奇景——海子的上方竟然有两道堤坝悬空而起,相向延伸。
其实,那只是海子上的水汽和光线形成的视觉效果,但在我们看来,却像是一道正在搭建的长桥。不知还要多久它们才能完工,一旦這桥修成,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在这小海子上没有了时间的限制和地域的阻隔,可以往复自如,行走如飞?
如果是这样,那这真的就成了人间与天堂之间的一座桥了。只可惜我们没有时间等候到它们修成,因为,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去赶夜班车了。
一队天鹅在海子上漂浮着,光线不佳,距离又太远,我和阿倩决定留在原处,让小鸥带着欧阳老师向它们靠近。
只见他俩端着相机,猫着身子,轻轻地跨过几处冰滩,最后停在伸向湖中的一处浅滩——这是正对着那群天鹅的方向。天鹅显然是察觉到了他们的接近,只见它们不安地鸣叫着,有的摆着翅膀,有的仰颈张望。
不知哪一只是领队的天鹅,也不知它是如何发出集体撤离的信号,只见天鹅突然间呼啦啦一起向湖中俯冲着,踏着水面拍起了浪花,身体像斜射向天空的箭一样,纷纷飞了起来。而这时,另一队天鹅也接收到了信号,用同样快的速度,集体起飞。
几群天鹅都飞起来了。它们并没有远走,只是列着队形,在不远处的湖滨不停地盘旋,它们白色的身体盘旋飞舞着,像极了谁写下了诗句又散落开的信笺——是那些从云层中透映出来的霞光来读,还是漫天铺卷而来的寒风来读,或是粼光细密波涌潮动的湖水来读。
突然之间感觉到时间的急迫,那时,距我们坐夜班车返程还有两个小时,而我们好像还有好多事没有完成。这似乎跟拍照已经没有了关系,把我们的心情紧紧地系在海子边上的,并不是拍照。
我们调转了车头返程。赶回南大湾,是想在临走之前最后再看看这里的天鹅一家。
中午时飞来此地“做客”的天鹅夫妻和他们的孩子小黑已经不见了踪影,估计是另外找到了安身之处,海子里依然是天鹅一家五口。见到它们,我们就像见到亲人那样熟悉和激动,甚至已经可以分清那三个“丑小鸭”——哪个是小白,哪个是小小白,哪个是小小白爱斯——虽然它们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但只要是它们的亲人,就一定能分得清楚。
有点舍不得离开南大湾,离开这天鹅一家。尽管小鸥催促我们抓紧时间去追赶正移向后泡子那一带的光线,但我们还是蹲在岸边,举着相机对着这一家左拍右拍,而这家天鹅显然已是认识我们了,神态中已经不再生分。
此时从我们身后的天空中,投射下来几束光亮,因为天色暗沉,它们是从厚重的云层中穿出,又打在海子对岸的魔鬼城,那光亮便有些探照灯的效果。
那真是一幅绮丽而又诡异的景象——天空浓聚的云层开始游离,露出一些蓝得透亮的天空,那些光线从云层中射出,落到海上魔鬼城的崖壁上,在不同地段形成了光晕,整个崖壁便被调出了魔幻的色调——谁能说清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天空之下,云层奔涌,如海浪悬天,迅疾地向着那城垣方向集聚,像是一整面海子都倒置在了天上,而湖中水波起伏,如云翳排空,舒缓地自那城垣方向离散,又像是全部天空都转落到了地上。而使这时空倒错的魔境如此严丝合缝的,竟是那海上魔鬼城在海天之间绵延的形迹。
于是,那少有的映在城垣上的几段光亮,既如同通透了时空,又如同更加一重的封锁——若是穿越,之后不知,是回到了最初的平静,还是,又坠入到更深一层的迷幻。
这些在我们寻找天鹅的途中出现的奇境,让我们的旅途变得更加繁复又充满了诸多的隐喻,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加安详又抛开了全部的羁绊。那光影游移的海上城垣,如半步之遥的仙境,又如隔着一面玻璃却永远都无法抵达的,另一重梦境。
而这海子中的天鹅一家呢,它们到底是漂浮在仙界,还是踯躅于凡间,抑或,它们是来自天上人间的信使,或是飞落于人间的精灵。它们的停留与远翔,都带着它们自己都不知的秘密——像是有几只来自未知远方的漂流瓶,落在了我们的面前,而我们,将它们重新送入海中,却并不曾打开过。
只一瞬间之后,它们就将自我们的眼前飞走,此刻它们的不语,是因为,我们所有守望着小海子的心意,它们全都懂得。
我只想象到一点,等这天鹅一家人再飞回来的时候,可能我已经无法认出它们了——因为,那时,“丑小鸭”已经变成了真正的“白天鹅”,我又如何能分得清楚那曾经灰扑扑的小白、小小白和小小白爱斯呢?
我想,在离开渔场时一定要拜托渔翁哥一件事——明年春天,如果在南大湾这片湖湾里见到五只白色的疣鼻天鹅,一定要通知我。
我们终于还是上车离开了,随着车的行驶,散落在魔鬼城垣上的光晕也似乎在移动,在恍惚之中,似乎可以看清,那魔鬼城中的堡垒坚壁、秘道深院,却又未及细看,就已经将它们全都撇到了身后。
在赶往后泡子的路上,欧阳老师不停地察看天色,边说:“晚了,晚了一点,晚了五分钟。”
果然是晚了,当我们再次匍匐到后泡子的土丘后面时,光线已经从这个湖面移了过去。仰头望天,太阳正在云层后面移动,那些光线透映着云翳的行色,给海子边这将近黄昏时的天空增添了许多动人的韵味。
后泡子里,天鹅和野鸭子们依然在闲游、嬉戏着,它们凫水、寻食、振翅,享受着黄昏时分的安宁。就这样离开小海子吗?我们的心里都有几分不舍。
这时,天空传来了一阵嘈杂的鸣叫声,呵,原来是一队天鹅飞了过来,它们排列成“人”字的队形,由远而近,当它们飞过我们的上方时,霞光和云彩也正好移来,成为一幅巨大的天幕背景——我们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天鹅群向小海子深处飞去。
小鸥又问了一句:“今天是几号?”“20号。”“20号,这就是天鹅每年冬天回到小海子的日子……天鹅回来了。”
正说话间,又有一队天鹅从远处飞来,它们从云霞之中穿过,似乎被赋予了神性的光泽,又像是它们自身的光亮回映在天宇之间。
这些天鹅大约是从西伯利亚、斋桑湖等地南迁而来,从行程上看,天鹅群自阿勒泰最西端的哈巴河一带入境,到福海的乌伦古湖这里,应该是它们入境后的第一个栖息处。天鹅大约会在这里停留半个月,待乌伦古湖封冰之时,再向南迁。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应该是第一批在小海子看到天鹅南来的幸运儿了。此时,仰望着天宇,聆听天鹅在云层中展翅的声音,我们真想挥动双臂,大声喊出:“欢——迎——回——來!” 可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静立在那里,在天鹅飞过的小海子边,想再多一点的,享受那样一种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