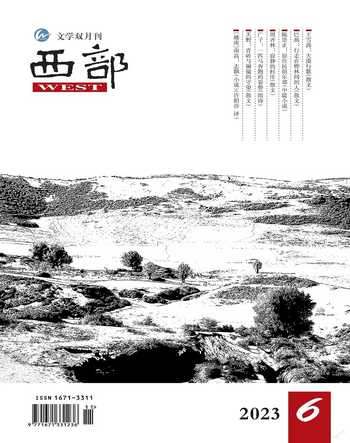寂静的村庄
周齐林
凤娇婶
五额娘和我家是面对面的邻居,相距不到百米。五额娘住的是新房,凤娇婶独自住在紧挨着五额娘家后面的那栋百年老屋里。
那日,不知睡了多久,一阵熟悉的谩骂声传至耳尖,凤娇婶浑身禁不住一阵颤抖,挣扎着爬起床。她颤颤巍巍下楼,刚走至楼梯间,果然,一个熟悉的身影闯入眼帘。是香妹,她大儿媳。香妹一直在深圳一家制衣厂打工。每次回来前都会电话告知她,她就会把捡的破烂卖掉。凤娇婶没想到儿媳这次来了个突然襲击。
“什么东西都往家里捡,房子弄得脏兮兮的。老不死的。”香妹说。
自老伴去世后,凤娇婶就养成了捡破烂的习惯。她把捡来的破烂分类,整整齐齐摆放在楼梯间的空当里。每天清晨或者午后,她都会绕着村子走一圈,捡一些破烂,囤积起来,然后再拿到镇上的废品收购站卖掉。卖破烂得来的钱可以买一两斤猪肉来改善伙食。
这栋三层小洋房是五年前建好的。大儿子昌隆和儿媳香妹外出打工时,凤娇婶就从老屋搬到新房里,帮忙照看屋子。凤娇婶平日里常自嘲是看门狗。
儿媳香妹性子烈,凤娇婶体弱多病,再加上没什么经济来源,一切都要看儿媳脸色行事,骨子里就愈加怵她。
只听哗啦一声,香妹把破烂废品全部甩了出去。香妹的动作瞬间激怒了凤娇婶。凤娇婶气得脖子上的青筋暴露。
“你这死没良心的,你这是要我的命啊。”凤娇婶边说边颤颤巍巍走到水沟边,挽起裤脚,下到水沟,把沟里的瓶瓶罐罐一一捡上岸来。这些在他人眼底不值一提的废品,却是凤娇婶的命根子。
凤娇婶和儿媳对骂了很久,脸色愈发苍白,她顿觉浑身酸软,几乎要晕倒,便捡起放在地上的破烂,颤颤巍巍地回到住了一辈子的老屋。
凤娇婶育有两儿一女,女儿养到八岁不幸夭折。大儿子昌隆比较省心,二儿子昌盛年过四旬还未成婚,一直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在厂里做了近二十年。自从前年老伴去世后,小儿子就愈发成了她的心头肉。昌盛四年前查出尿毒症,一直靠透析度日。一周透析两次,每次都需要请半天假。老板不敢炒他,作为厂里二十多年的老员工,炒掉昌盛估计要赔几十万。
拧开药瓶,吞下两粒治哮喘的白色药丸,喝下两口温开水,她孤坐在床沿,两只满是老茧的手因生气还微微颤抖着。时节进入深秋,窗外是一片金黄。她呆呆地望着窗外,看久了,疲乏了,回过神来,眼神落在墙上挂着的老伴的照片上。照片上的老头子憨厚地笑着。
“铁匠,你怎么这么狠心,丢下我一个人在世上。” 凤娇婶叹息了一声,眼角溢出一滴浑浊的泪来。
铁匠叔参加过抗美援朝,在世时每个月有近四千元的退休金,完全够他们两个人开销。菜园里种满了各种时令蔬菜和瓜果,吃不完,凤娇婶就摘了拿去墟上卖。若不是每个月省出一千五百元给小儿子昌盛透析买药,退休金倒还有不少盈余。
老伴在世时,凤娇活得有尊严,老伴去世后,她感觉自己腰杆子也跟着弯了下去。平日里有个病痛,只能干忍着,她不想看香妹的脸色。
老伴去世那一年成了凤娇婶命运的分水岭。彼时,凤娇婶和铁匠叔一起帮忙给昌隆和香妹看房,他们住在一楼的偏房里。每天饭后,老伴去茶馆打纸牌,回来时恰好是午饭时间。午饭后,午睡一两个小时,醒来在院落里打一套太极拳,而后抽着旱烟慢悠悠地往茶馆走去。日子过得十分惬意。凤娇婶则终日在菜园子里拾掇着,不时会提着蔬菜和鸡蛋去赶集。街坊邻里都十分羡慕他们。
那个看似平常的夏季转瞬却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密不透风的夏天,炙热的阳光把整个大地烤得滚烫。一直到薄暮时分,阵阵凉风来袭,空气中弥漫着的阵阵热意才如潮水般渐渐退去。经过一整日的曝晒,刚收割上来的稻谷已晒干,地上一片金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稻谷的清香味。村里家家户户正忙着收稻谷时,凤娇婶因腰椎间盘突出,正躺在老屋灰旧的床上歇息。她静静地看着窗外,光线由亮变暗,很快敞亮的屋子就淹没在无边的昏暗里。疼痛稍微缓解了一些,她挣扎着起身。以往这时铁匠叔应该从茶馆回来了。他在昌隆的新屋里炒好菜,热好一壶酒,接着会慢悠悠来到老屋叫她过去吃饭。今天却没有。屋子里静悄悄的,不知名的虫子匍匐在草丛深处发出尖锐的呐喊声,愈发显出屋子的寂静。
凤娇婶颤颤巍巍走出门。黄昏的渡口,白天耗尽,黑夜已降临。凤娇婶走在稀薄的夜色里。走走停停,五分钟后,走至昌隆新房处,隐隐约约看见大门敞开着,屋子里却黑漆漆一片。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铁匠,死哪里去了?”凤娇婶拖着躯体疾步至门口,摁亮门后的开关,大声喊道。啪嗒一声,灯亮了,眼前的黑暗瞬时隐匿起来。凤娇婶又大声喊了几句,依旧是空荡荡的回声回应着她。铁匠仿佛眼前的黑夜般,正跟她玩着捉迷藏,隐匿在别处。
她一一摁亮灯光,整栋屋子瞬时亮堂无比。仿佛只有如此才能驱散她内心涌起的恐慌和焦急。
凤娇婶强忍着腰痛一步步走上三楼。这几天日头好,香妹叮嘱她有空把三楼仓库里的稻谷拖出来晾晒一下。摁亮三楼的灯,却见晾晒的稻谷收了一半,不见老伴的身影。三楼一直没有弄栏杆,她担心老伴一不小心掉下去,缓步走到边缘,四处张望,却不见老伴的身影,悬着的心似乎又平静了许多。
从楼上下来,恰好遇见五宝叔从大门前走过。五宝叔与铁匠叔同龄,常一起结伴去村头的茶馆喝茶打纸牌。
“五宝,有看见我家铁匠吗?” 凤娇婶焦急地问道。
“他早就回来了。”五宝说道。
凤娇婶坐在门前的矮凳上喘息,等着铁匠叔回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凤娇婶越等越来气,想着等他回来一定要狠狠地骂他一顿。“这个死铁匠,七老八十的人了,还这么不让人省心。”凤娇婶咬着牙,自言自语道。她一边骂却又一边担心着。她在门前焦急地走来走去。碰到有人走过来,就迫不及待地问一句。
一直等到屋子里左右摇晃的钟摆敲击了九下,凤娇婶依旧没有看到老伴的身影。隔壁的六额娘见她心神不定的样子,不时安慰她。
夜色苍茫,寂静的村庄,零星的几盏灯火在夜风中左右摇曳着。灰旧的大门已紧闭,狗蜷缩在黑漆漆的洞穴里,一见风吹草动便汪汪汪地吠起来。
凤娇婶孤坐在床上,望着墙壁上挂着的时钟发呆。时钟发出嘀嗒嘀嗒的响声,声声敲打着她的胸膛。
时间仿佛静止了。忽然,屋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凤娇婶,不得了了,你快来,铁匠叔摔倒在两栋房子中间的过道里。”六额娘的小儿子银龙面色恐慌地冲到凤娇婶面前,身子前倾,步子差点没刹住。
凤娇婶跟着银龙疾步走到过道中央,适才剧烈的腰疼仿佛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六额娘闻声也从门口冲了出来。她们三人走进杂草丛生,乱石林立的过道里。月光如一粒粒白盐洒在路上,铁匠叔一动不动地躺在一堆乱石上,嘴角溢出一丝血。凤娇婶瞬时扑了过去。
银龙小心翼翼地把铁匠叔抱在怀里,一步步移到屋子里的床上。铁匠叔尚有一丝鼻息。银龙把铁匠叔放在床上,铁匠叔微睁开眼,看了凤娇婶一眼,想说什么,口中忽然吐出一口鲜血,转瞬头便耷拉了下去。
凤娇婶顿时跪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你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哭喊声惊醒了寂静的村庄,附近的村里人循声而来,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人影缭乱,他们纷纷行动起来。
对于铁匠叔的死,村里人议论纷纷,都把主要责任归咎于三楼的护栏没有及时安装。家家户户都安装了护栏,就她儿媳为了省几个钱,没有装。
原来那日铁匠叔从茶馆喝茶回来正是薄暮时分,天色渐渐暗淡下来,晒在楼上的稻谷正等着收仓。铁匠叔上三楼收稻谷,一个不慎,双脚踏空,从三楼坠落下来,重重地掉落在两楼之隔的过道里。逼仄的过道还没有铺上水泥,满是棱角的鹅卵石密密麻麻地分布其间。
铁匠叔死后,凤娇婶终日把自己关在老屋里,闭门不出。半年后,她才从悲伤的河流里走出来。每年春节过后,儿子、儿媳以及两个早已长大成人的孙子都外出打工,家里就剩下她。心里实在憋得慌时,她就沿着山间小路,走到铁匠叔的墓地前,跟他说话。
六额娘和凤娇婶同龄,虽都年过七十,但身体状况却相差甚远。六额娘身子骨依旧硬朗,家里的三亩地春夏两季还种着,每次赶集,总会提前去县城批发一些农产品拿去市场卖。凤娇婶多病缠身,哮喘病、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哪一样都会趁她不备置其于死地。六额娘在广袤的田野里挥汗如雨时,凤娇婶则在清凉的老屋里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如瓷般的身体。
六额娘收割完那几亩种了几十年的稻谷已是薄暮时分。她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喘息了片刻,喝了几口水,朝天边吆喝了一声,阵阵晚风仿佛听到号令般,迅疾从远方吹了过来。六额娘弯腰,在水渠边蹲下来,打湿毛巾,擦了把脸,浑身的疲惫被清凉的晚风一丝丝地吹散。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不远处的屋舍由清晰变得模糊,转瞬就被黑暗吞噬。六额娘弓着身、握着镰刀,往回走。
回到家,见香妹一个人在院子里吃饭,不见凤娇婶。
“这么晚才回来啊,六额娘,还是你身体好,不像我家那个老不死的。”香妹端着碗,看了一眼六额娘说道。
六额娘尴尬地笑了笑,没吭声。
打开灯,温柔的光线瞬间照亮了整个屋子,四处亮堂堂的。在灰旧的老板凳上喘息了一会儿,六额娘转身去厨房端出锅里一直热着的酸菜蒸肉和清炒白菜。六额娘喜欢喝一口,干活累了更要喝一口酒解乏。她上二楼打了一碗酒下来。酒是陈酿,有劲头。每年寒冬时分,她都要用自己种的稻谷酿几坛子酒。三楼的房间里堆满了稻谷,层层叠叠,是这几年的收获。儿子儿媳外出打工后,她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坚持一人种稻田,舍不得拱手让给别人种。
昏黄的灯光映射出六额娘孤独的身影。喝了一口酒,她忽然起身,端着酒和菜,打开后门,走入一个昏暗的胡同。借着如银的月光,她缓步朝前走去,在一个斑驳的木门前停下来。木门虚掩,灯光透过门的缝隙逸出。
门嘎吱响着,像老人痛苦的呻吟声。凤娇婶正在吃饭,她微微探头一看,见是六额娘,脸上露出灿烂的笑。
桌子上摆着两个菜,清炒白菜,一小碟酸萝卜。“你天天就吃这个怎么行?” 六额娘边说边把带来的酒和菜端到桌上。
“多吃点肉,你这身子骨要多补充营养。”六额娘边说边夹了一筷子肉到凤娇婶碗里。
“没想到老了落到这个地步。”凤娇婶深深叹息了一声,肉刚夹到嘴里,眼角便溢出一滴浑浊的泪来。
吃完饭,一直聊到深夜,待凤娇婶情绪稳定了许多,六额娘才起身回家。
六额娘和凤娇婶的娘家都在三十里外的南塘村,她們打小玩在一起,一起割猪草,一起放牛,一起踢毽子。到了婚嫁的年龄,六额娘前脚嫁到文竹镇,凤娇婶后脚也跟着嫁了过来。以前在南塘村,她们一个住在村头,一个住在村尾。嫁到文竹镇后,没想到成了前后邻居。平日里生活上遇到什么难处,彼此都会照应,感情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愈加牢固起来。
六额娘回到家,想起适才凤娇婶说的,她孤坐在饭桌旁的长板凳上,对着墙壁上挂着的老伴的遗像发呆。三十年过去,老伴去世那一年的点点滴滴依旧深深镌刻在她的骨子里。这几十年,六额娘的儿女都已成家,现在大孙女和孙子正念大学,小孙女还在读小学。
香妹的身份证弄丢了,她是回来补办身份证的。在家里住了不到一星期,她就返回深圳了。临走前,她把钥匙给了六额娘,让她帮忙转给凤娇婶。除了钥匙,她还给了五百块钱,让六额娘代为转交。五百块钱捏在手里薄薄的,六额娘自己又添了五百块,拿着钥匙往凤娇婶家里走去。六额娘每年卖蔬菜和一些盈余的稻谷能存下七八千块钱。
“这是香妹临走前让我交给你的。她刀子嘴豆腐心,你赶紧收下吧。” 六额娘说道。
“我就是饿死了也不要她的钱。”凤娇婶说完,双眼通红。
六额娘不再多说什么,放下钥匙和钱,起身出了门。走至庭院,一阵浓郁的桂花香扑鼻而来。桂花树是老伴去世那年栽种的,几十年过去,小树苗早已枝繁叶茂。六额娘站在桂花树下,深吸了一口,那些纷繁的往事不由浮现在脑海里。桂花树下是石桌和石凳。日复一日坐与磨,石凳变得光滑无比。老伴还在时,日落时分,她们一家五口常在院落的石桌石凳上吃饭、喝茶、聊天,盛夏的夜晚,晚风轻拂,繁星满天,月光潮水般涌入村子。如今只剩下她孤独的身影。
六额娘
香妹回深圳没多久,在六额娘的几番劝说下,凤娇婶始终不肯回昌隆那栋新房里住。
“你住在这里,我心底更踏实一点。这几天隔壁的狗叫得厉害,怕是有小偷。”几天后的晚上,六额娘再次来到老屋说道。
“真的吗?”凤娇婶迟疑地看着她。
“还煮的呢,难道我还骗你不成?” 六额娘说道。
六额娘这么一说,凤娇婶当晚就回到了儿子昌隆的新房居住。跟着她回去的还有那条形影不离的老黄狗。
六额娘也养了一条狗。狗是墟上买的。
去年年初,六额娘夜半起来上厕所,刚起身,微弱月光的映射下,隐约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头正趴在窗户边,往屋内打量着。六额娘见状心底一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见惯风雨的她迅速让自己冷静下来,她小心翼翼地下床,挪到靠窗的墙角边,而后起身大声怒吼了一句:“是谁?” 只听窗外“啊”一声,一个瘦削的身影迅速逃离。摁亮灯光,回想起适才一幕,六额娘禁不住笑起来,过后,依旧感到恐慌和不安。她欲打开门跟凤娇婶说说话壮胆,才想起凤娇婶住在老屋。一整晚,她一直让灯亮着。次日,六额娘从村头卖豆腐的李婶家买来一只养了半年多的黑毛狗。细心喂养了一年多,狗终于成为家中的一员。暗夜里,蜷缩在大厅门后的狗一听到门外有风吹草动,就会狂吠。狗的存在,是陪伴,对于窃贼也是一种威慑。
时节已进入深秋,空气中依然弥漫着阵阵热意。广阔的田野里是连绵起伏的稻浪,一台崭新的机器正在稻田中央孤独地收割着稻谷。薄暮时分,一股浓郁的稻谷气息弥散在空气里。六额娘家里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却无人接听。凤娇婶正欲出去看个究竟,这时手机响了,一看是六额娘她大儿子金龙打来的。
“婶子,你帮我看看我妈到底去干吗了,怎么打电话没人接。”金龙有些焦急地说道。
凤娇婶放下电话,半瘸着腿走到六额娘的屋子里,却见屋子里黑漆漆的,六额娘七岁的孙女正在屋外徘徊,昏黄的灯光映射出她稚嫩黝黑的脸。
“你奶奶回来了吗?”凤娇婶问道。
“还没回来,以前六点多就回来了。”六额娘的孙女露露说道。
凤娇婶迅速掏出手机,把情况告诉给金龙。听说六额娘还没回来,他心里一下子慌了起来。赶紧打电话给他的堂兄弟斌发,让他去地里找找。漆黑的夜色里,斌发打着手电筒走在前面,凤娇婶碎步走在后面,急匆匆往山脚下的稻田里赶去。夏季时分,远处山间的坟墓地闪着磷火。斌发疾步跑到地里,往稻田中央翻看,果然看见六额娘晕倒在田里,脸埋在潮湿的泥土中。
斌发略懂医术,他用手掐了掐六额娘的人中,一分钟后六额娘苏醒过来。只是身子无法动弹,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凤娇婶,你在这里看着她,我去把板车拉过来。”
斌发背着六额娘缓缓把她放到板车上,在漆黑的夜里沿着山间的小路慢慢把她推回家里。原来那日黄昏时分,正在稻田里收割稻谷的六额娘忽然感到一阵剧痛从腰间传来,她顿时栽倒在地,呼吸也变得虚弱起来。
金龙匆匆从东莞横沥回到了老家。在县人民医院,六额娘被诊断为腰椎骨腐蚀严重,还有一个鸡蛋大的缺口。住院半个月后,六额娘出院了。医生特意叮嘱她以后不能干重活。在村里人眼里铁一样身板的六额娘整个人突然间苍老了许多。
六额娘闲不下来,对医生的话置若罔闻。六额娘忙了一辈子,只有忙起来她才感觉全身活泛。一闲下来,她就闷得慌。在家里休养了一个月,她感觉全身都发霉了。年后,儿子儿媳出去打工,六额娘把荒芜的菜园子重新翻土、施肥、种上菜籽。忙完这些,她又去县城批发农用家具到村里的墟上卖。
“老婆子,不要命了啊,还这么吃苦干吗,这么着急要去见阎王爷。”路人见到她热火朝天的样子说道。
“停下来就闷得慌呢。” 六额娘说道。
两个月后的傍晚,六额娘从地里干活回来没多久,腰部一阵剧痛袭来,她扶着墙想坐下来,忽然一个趔趄重重摔倒在地,人瞬间晕了过去。在屋子里看动画片的孙女露露闻声出来,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她疾步跑到隔壁大声呼救:“凤娇奶,我奶奶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凤娇婶正在厨房吃饭,闻声急忙放下碗筷,半瘸着腿出了门,拐过去一看,六额娘嘴角溢出了血。
凤娇婶一下子慌了神,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斌发。斌发赶来把六额娘抱到车上,连夜送到县人民医院。
“上次一再叮嘱要静心休养,怎么又干上活了?”医生面无表情地说道。
斌發看了六额娘一眼,没出声。
经此一遭,六额娘不敢再乱动了。她儿子金龙不时打电话过来询问她的身体情况,叮嘱她不要再去做活,好好在家休息。
时光仿佛停滞了下来。六额娘每天早早地起来看太阳升起,薄暮时分又坐在门口的长凳上看太阳缓缓落下。
看着往日马不停蹄忙碌的六额娘变得病恹恹的,凤娇婶心里五味杂陈。六额娘在村里人眼里的印象,仿佛任何疾病都侵蚀不了她的身体。突然间,变成了摇摇欲坠的瓷器,在疾病的频繁攻击下,不仅裂开了一道缝,缝隙随时有扩大的可能。
凤娇婶悲喜交织。喜的是孤独的日子有了六额娘的陪伴而多了一些温暖。悲的是她时常想象着六额娘有一天离开人世的场景,眼角禁不住溢出一滴浑浊的泪来。
大片大片的时光空余下来,像发霉的稻草,堆积在一起。六额娘感觉自己被抛在了时间的荒野里。晒干的稻草摆放在屋檐,天晴的日子,六额娘经常和凤娇婶坐在稻草上,静静地看着眼前的村庄,一直坐到日落西山,草垛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屁股印,才缓缓起身。她们坐在草垛上聊过往的事情,聊着聊着就陷入长久的沉默里。六额娘时常会上楼取一些往年酱好的酱萝卜、酱姜和陈皮下来,就着温开水和柔和的阳光细细咀嚼。
没生病前,她的时间都聚焦在稻田里的禾苗上、菜园子里的一瓜一果上,她经常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堆积的时间压得她无法喘息,一种窒息感郁积在胸口,挥之不去。时光的重压落下来,压在她干瘪的身体上。时光静静地流淌着,不管不顾,对此,她已无能无力。她静静地发呆,一整天无事可做,仿佛一场病,就把一辈子的事情全部做完了,只剩下死亡这一件事。
坐在草垛上晒太阳,凤娇婶常会不由自主地看着六额娘。六额娘生性敏感,瞬间就捕捉到了,盯着凤娇婶笑着说道:“要看现在就看个够,等我哪天走了,你想看就只能看墙上的照片了。”凤娇婶听了,心底不由咯噔一声,顺口说道:“你这个乌鸦嘴。”
太阳西斜,她们从草垛上起身,缓缓朝各自家里走去。一连好几日晚上,凤娇婶脑海里回荡着六额娘那句话,要看现在就看个够,以后就没得看了。
昌隆
2017年盛夏,凤娇婶的大儿子昌隆因患腰椎间盘突出日渐严重,回到了千里之外的老家。
昌隆提着行李下车后,即将走至家里,看见一群老人和妇女聚集在家门前的那块空地上,议论着什么神秘的事情,神色凝重,面露恐慌。调皮的小孩流着细长的鼻涕在人群的缝隙中钻来钻去。
“昌隆回来了啊。” 人群中有人向昌隆打招呼。昌隆如一块石头投入哗哗的河流里,他本以为自己的归来会打断村里人的议论,不料众人跟他热情地招呼了一下,转身投入新的议论中。昌隆站住听了一会儿,总算听出一点端倪。
村里人正在议论村里卖豆腐的老丁头。老丁头已完全不能进食,只能靠打点滴维持生命。他曾经肌肉紧绷的身体已瘦骨嶙峋。在外打工的一众亲戚都回来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哀悼的气息,屋内的喧嚣映衬出老丁头的孤独。
两个月前,老丁头只喝了两碗排骨汤,排骨肉一块都没沾。他喉咙不舒服,总是打嗝,这几天都是吃稀饭喝汤。
一个月后,老丁头已吃不下饭,他低着头蜷缩在灰旧的沙发上,面色恐慌地看着众人。他把食指伸进自己的喉咙,蹲在地上,上身剧烈起伏着。老丁头使劲咳嗽着,像是要把整个心都咳出来。老丁头气喘吁吁地停了下来,他眼角咳出一滴泪来,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满脸煞白。
几天后,在县人民医院的胃镜检查室,医生把一条细长的管子伸进老丁头嘴里。管子伸入一半,医生哦了一声,说道,原来是这样。医生示意老丁头先出去休息一下。
“食管癌,回去让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医生面无表情地说道。诊室的门半掩着,透过门缝,老丁头正坐在弥漫着药水气息的走廊长椅上,他那双青筋暴露的手微微颤抖着。医生充当着审判官的角色,老丁头被确诊为食管癌晚期。
“不知道下一个是谁呢?”
“是啊,谁知道下一个是谁呢?”
“听说建秋他儿子金宝得尿毒症七八年了,一直靠透析续命,听说前几天情况很严重,不知道下一个会不会是他。”昌隆冲完凉,顿觉浑身轻盈了几许。走出门,他听到几个人的议论。
昌隆蹲在门槛上静静地看着门口的人,他母亲凤娇婶也在人群里津津有味地议论着。昌隆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二十多年前盛夏的夜晚,整个村庄的人晚饭后聚集在这块空地上纳凉唠嗑。这里成了村里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所有的最新消息都是以这里为中心,迅疾流传开来。现在,当年的那些年轻人都远在异乡谋生,只剩下老弱病残坚守在家里。死亡如一块巨石砸入寂静的深湖,掀起阵阵波澜。一个人的死让寂静的村庄变得热闹起来。
昌隆是回来做腰椎间盘突出手术的,珠海的那家别墅已装修完。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打游击一般居无定所,也没有社保,回来做手术可以用农村医疗合作的保险报销。他准备手术后在家里休息一个月再返回深圳。
连续抽了几根烟,人群渐散。凤娇婶进屋煮饭,把早上买的新鲜排骨洗净,放上切好的冬瓜。冬瓜是自己种的。很快,厨房里就传来阵阵炖汤的香味。晚饭前,凤娇婶端了满满一碗冬瓜排骨汤给六额娘。六额娘笑着接过碗。
一番检查后,手术时间定在下周二。手术前两天,凤娇婶焦急地找到昌隆,跟他说把手术时间改一下。
“为什么要改?” 昌隆疑惑地问道。
“老丁头早上去世了,那天是他出殡的日子。”凤娇婶说道。
昌隆听了心里一咯噔。
老丁头卖了一辈子豆腐。每天清晨挑着个担子走街串巷吆喝:“卖豆腐呢,新鲜的豆腐,又嫩又便宜。”昌隆记忆里回荡着老丁头的声音。
出殡那天,凄凉的唢呐声回荡在村庄上空,全村的老人和妇女稀稀落落地走在路上,身着白衣,缓缓朝山脚走去。
老丁头死后,村里人的关注点聚焦在谁会是下一个。晚饭后,年迈的老人聚集在空地上议论纷纷。
次日下午,昌隆正在房间里午睡,屋外忽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他起身循声走出去,看见花妹正跪在地上哭泣着。很快村里人聚集在一旁,一脸凄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花妹的男人海华被从急救车上抬下来,他的两个堂兄迅疾把他抬入屋内的床上。海华在深圳打工,半个月前,他与同事发生口角,一天下班后,同事找来帮手把他堵在墙角,三人顿时扭打在一起,海华被二人打成肾脏破裂,造成肾脏急性衰竭,七天七夜的紧急抢救之后,气息微弱。海华年迈的父亲雇上一辆急救车把只剩下一口气的他从深圳拉回了家。鼻息微弱的海华回到家已近中午,他伯伯匆忙跑到学校把海华八岁的女儿小银子叫回家。小银子跑进屋,泪流满面地叫了一声“爸爸”,海华嗫嚅着,扭过头看了女儿一眼,头就永远地耷拉了下去。整个屋子的人顿时乱作一团,花妹因伤心过度,晕了过去。
海华的死让整个村庄弥漫着一股悲伤的气息。
凤娇婶回到家中,孤坐在老板凳上发呆。她有点担心在深圳打工的小儿子昌盛。昌盛透析八年多,前幾天天冷感冒,引起肺部感染,呼吸衰竭,一股浓痰堵在喉咙口,差点窒息而死。
孤坐了一会儿,凤娇婶来到昌隆的房间,让昌隆微信视频给昌盛,她想看看他现在病情如何。视频拨过去,昌盛刚透析完,正在医院外面的饭馆吃饭。
“孩子,现在还好吧?”凤娇婶问道。
“妈,还好着,死不了,你放心。”昌盛扒拉了一口饭,故作轻松地说道。
凤娇婶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她转身又去看六额娘。六额娘正在屋子里忙着酿酒。
一周后,昌隆顺利做完手术,往日腰间频频传来的那股酸痛和僵硬感已不见踪影。
凤娇婶这几日左眼皮一直跳个不停,她劝昌隆这几天哪儿也不要去。
在家里待了五六天,昌隆感觉有些闷。他闲不下来,在外时陀螺般从早忙到晚。次日他去了县城发小丙卫那里帮忙搞装修。丙卫也是木匠,这几年一直窝在家里搞装修。
到了县城,在丙卫的安排下,昌隆做的也是轻松的活。一个上午在敲敲打打中过去,偶尔停下来站在窗户前抽几根烟。
“在外面这么多年,你以后不出去了?”昌隆狠吸了一口烟,看着丙卫说道。
“还出去干吗,土都埋到脖子上了,在家能照顾老人和小孩。”丙卫看了昌隆一眼说道。昌隆听了一时无言。
午饭后,稍作休息,昌隆和丙卫又忙了起来。
“下午我们早点完工,晚上带你去吃点羊肉和兔肉补补。”丙卫摁灭手中的烟头,咧开满口黄牙笑着说道。
残阳如血。沉闷的响声回荡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丙卫闻声赶来,看着眼前的一幕,顿觉天塌了下来。他浑身战栗不已,呼喊着人一起把昌隆往外抬。昌隆在踩着人字梯安装柜子时,一不小心踏空,后脑勺重重地摔在地上。
这日凤娇婶一早起来,右眼皮跳得厉害。她隐隐感到不安,仿佛老伴去世那天一般。消息传到凤娇婶耳里已是深夜,她顿时晕倒在地。六额娘不停掐她人中,她才苏醒过来。六额娘看着凤娇婶端坐在板凳上,无言地流泪,满是皱纹的手微微颤抖着。六额娘想说些劝慰的话,话到嘴边又吞咽了回去。空气仿佛凝固了,一切变得轻飘起来,却又沉重无比。
次日清晨,凤娇婶忍着疼痛,颤颤巍巍地走到小镇的汽车站,搭乘一辆满是灰尘的中巴来到了县医院。
“后脑勺着地引发脑出血,幸亏及时送医院,不然会导致下肢瘫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说。命运突如其来的重拳,让凤娇婶猝不及防。凤娇婶的世界像一堵经年失修的墙,一夜之间坍塌了。
香妹得到消息,连夜从深圳赶了回来。昌隆睁开眼看到的第一个人是香妹。香妹紧握着他的手,一脸心疼地看着他。
看着香妹那张憔悴的脸,昌隆眼角溢出了泪。
半个月后,昌隆在香妹的搀扶下出院了。下床的那一刻,昌隆感觉双腿有点酸麻感,不怎么听使唤,仿佛两条腿不是长在自己身上。
“回去多给他按摩,也可以去针灸,恢复时间看他体质。也有恢复不了的。”医生叮嘱道。
香妹把深圳制衣厂的工作辞掉,去了小镇新开的鞋厂上班,朝九晚五,工资三千元一个月。
平日里,都是凤娇婶做饭炒菜照顾昌隆。晚饭后,洗漱完,香妹就端来温开水,一遍遍地给昌隆擦洗身子,而后给他按摩。
两个儿子结婚在即,面对高额的彩礼,昌隆被压得喘息不过来。
残阳如血
夕阳的余晖洒落在一栋栋崭新坚硬的洋房上,老人独坐在门口看着夜一点点降落下来。深夜的村庄寂静无声。千里之外的城市灯火辉煌。
昌隆常陷入失眠的深渊里。夜半醒来,苍白的月光映射在他颧骨突出的脸上,他静静地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耳边响起香妹均匀的鼾声。只有在这寂静的夜里,所有人都睡着了,他才感觉沉重的肉身变得轻盈起来。那些附着在身的压力暂时隐遁而去。
白天,看着鬓边发白的老妈瘸着腿照顾他,一阵阵酸楚潮水般袭来。
几日后,昌隆午睡醒来,见他老妈推着个半旧的轮椅出现在他面前。
“这轮椅是哪里来的?妈。” 昌隆问。
“你睡着时,我去卖破烂,看到这张半旧的轮椅在处理就顺手买了下来,很便宜,几十块钱。”凤娇婶有点忐忑地说。她担心儿子会生气。
看着老母亲局促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昌隆的心隐隐地疼。
“别总躺着,我推你出去走走。”凤娇婶一脸心疼地说道。
一直躺着也不是个事,身体迟早要报废。在凤娇婶的软磨硬泡下,昌隆终于起身坐上了轮椅。
凤娇婶推累了就停下来休息片刻,走走停停。昌隆日夜躺着的房间里空气浑浊压抑。而此刻旷野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清冽的气息,吸入鼻尖,昌隆感到一阵久违的清爽感。抬头看了老母亲一眼,昌隆心底颇为感激。半小时前,他还如一条躺在死水里的鱼,如今他顿觉如回到了广阔的大海,身心也随之充盈舒展開来。
凤娇婶推着昌隆在距村两里路的庙宇中停了下来。这是一座半废弃的庙宇。庙里供奉着一尊菩萨。菩萨面前的陶罐里香气缭绕。庙虽废弃,但每逢初一或者十五,村里人遇到过不去的坎都会来这里烧香。
回来的路上,昌隆由他老母亲凤娇婶推着,天色阴沉,他的心却感到一丝欢愉。时值初冬,广阔的田野裸露在深邃的天空下,缓缓进入休眠阶段。晚风吹拂着田野里一些残余的草垛,发出呼呼的响声,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在内心流淌。
凤娇婶这段时日悲喜交织,喜的是儿子昌隆日渐恢复如初,悲的是六额娘奄奄一息。
一个月前,六额娘的腰疼越来越严重,疼得整夜整夜睡不着。送到医院,医生让他们把老人带回家好好修养,想吃啥就吃啥。
屋外寒风呼啸,六额娘已一周未进食,靠打点滴续命。她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提前回来了,终日陪伴在她身旁。
凤娇婶每日蹒跚着来到六额娘跟前同她说几句话。到最后,六额娘不能说话了,只能轻微张开嘴。凤娇婶低头俯身,却始终听不清她说什么。最后,六额娘瘦骨嶙峋的手颤抖着指了指枕头下。凤娇婶伸手一摸,取出一千块钱。六额娘指了指钱,又指了指凤娇婶,做出一个给的手势。看着六额娘,凤娇婶眼角溢出一滴浑浊的泪。
三日后,六额娘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按照六额娘的遗愿,大儿子金龙把她葬在了山脚下的那片小土坡上。小土坡不远处就是六额娘耕种了一辈子的稻田。
六额娘一辈子未曾出过远门,这个村子就是她生命的半径。去世后不久,金龙拿着户口本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注销了六额娘的户口和身份证。看着这个在户口本上待了几十年的名字消失,金龙不由心酸。
六额娘走后,凤娇婶完全苍老下来,她终日孤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望着如黛的远山发呆。天气好时,她带上一瓶六额娘生前爱喝的桂花酒,缓步走到山脚下,在六额娘的坟前坐下来说几句话,老黄狗乖顺地蜷缩在她身旁。
老黄狗偶尔从悠远的睡梦中醒来,缓缓抬头朝她张望一眼,又埋下头。
缠绵一年多的病好后,昌隆顿觉一草一木重新变得光亮起来,薄暮时站在门槛前,看着不远处缓缓升起的炊烟,那些久远模糊的记忆滋润着他日渐干涸的心,让他感到生活的诗意和美好。
重新站起来后,世界的怀抱仿佛重新向他打开。昌隆和香妹收拾行装,在一个落雨的清晨踏上了前往深圳的大巴。凤娇婶坚持着送他到车站。车启动后,迅速在晨风细雨里疾驰起来。透过车窗,昌隆看着他老母亲年迈憔悴的身影。凤娇婶正颤颤巍巍地走过马路,往那条通往家的小路走去。
六额娘去世后,昌隆家新房屋前屋后的五家邻居都常年大门紧锁。为了老母亲的安全,昌隆在屋檐下安装了监控视频,监控与手机连在一起,他可以时刻通过手机查看家里的状况。
回到深圳的出租屋已是深夜。夫妻俩匆匆洗漱完倒头就睡,醒来已是早上九点。窗帘紧闭,屋内依旧黑漆漆一片。
回到广州,上班一月有余,这日黄昏时分,吃完晚饭,昌隆回到宿舍躺在床上,依着惯性,打开手机查看监控视频。他看见年迈的老母亲端着饭碗缓步走到院内,在小板凳上坐下来。昌隆看了一两分钟,正欲滑开页面,监控视频里却出现惊悚的一幕:凤娇婶端着碗从小板凳上起身,走了两步,忽然步履踉跄,重重地摔倒在地。
眼前的这一幕顿时让昌隆的心悬到了嗓子眼,他紧握手机的手颤抖着。
昌隆匆匆拨斌发的电话,斌发的手机却打不通,焦急地连续拨了两次,依旧没打通。他来回在屋子里踱着步,正欲重拨时,手机忽然黑屏了。
昌隆拉开门,疾步朝楼下的电话亭走去。
此刻,窗外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