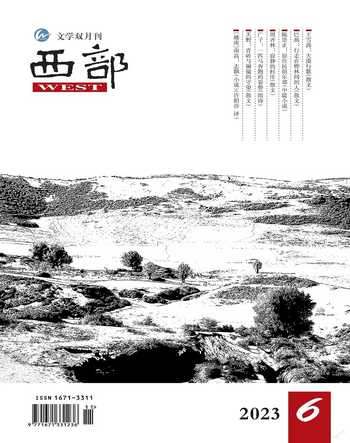大雪小雪(短篇小说)
王新梅
一
夜里,张海峰又从梦中惊醒了。
他回忆着,试图串起梦的碎片,梦里是一群男孩在堆雪人……他听到了簌簌的响声。是窗外传来的。原来真的下雪了。
梦里的雪也很大,石理也在梦里。他笑着的样子,还有笑声,和小时候一模一样。张海峰陷入一种平静的纷乱中。
你和石校长是同学?
你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谁让你去推车子的?
你当时推车子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不一样没?
……
三个多月过去了,张海峰依然记得对面那个年轻警察问他的问题,还有自己当时的回答。他预料到会有这个环节,甚至猜到过有的问题。他比想象中镇定。就是有点紧张,那也是正常范围之内——眼睁睁看着儿时的伙伴摔成了两截,谁能不失魂落魄?他呢,经过那个被狗撕咬的黑夜,与其说是更镇定了,不如说是惊吓后失智了般的木讷和迟钝。
我没干什么。他一遍遍暗示自己是无辜的。无数次的回忆中,他不愿确认自己真的在那天感觉到什么:在双手抓住车把推动笨重的雪地摩托车时,在车轮开始转动时——凭着以前修过车的敏感,或者就是第六感觉——察觉到什么。当时他也没想那么多。没有谁让他想那么多,他也逃避去想那么多。当时,那两个校服的供货商也过来推车,继续夸赞石理滑雪的技术好。他们说好,让石哥先示范一个。他们有时喊石校长哥。哥,哥,亲得好像他们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他对那两个精瘦的口里人没有好感,这是一开始就确认的。小时候就听母亲说,两腮无肉不可交。不过,当年别人给他介绍他现在的老婆时,母亲又说,瘦点没事,女人一结婚就胖了。那年他已经二十八岁了,母亲急于促成这桩婚事。
他看到他们弓着腰给石理说话,总觉得他们没安好心。电视上这样的人多了,都是“黄鼠狼”。但当警察问他对两个商人有什么印象或者判断时,他却说,没什么,没发现什么不对。他擦了下嘴角,被狗咬伤的那边脸,筋膜层被破坏了,话说多了,口角就不可控制地溢出口水。
那天确实是石理答应去滑雪的。确实是石理让他去推摩托车的。确实是石理自己开车下去的。包括中午吃饭时喝了点小酒,也是石理自己要喝的,没有人灌他。滑雪场有监控,他们三个人口径也一致,调查也就简单。他没有对当时两个商人一唱一和极力怂恿石校长骑雪地摩托车的事实过多强调,滑雪滑得顺溜,尝试下雪地摩托车,男人嘛,不都喜欢逞强。一切都是人之常情。他也隐瞒了石理对他嘀咕了一句:“自行车我骑过,摩托车我可没骑过。”他更不敢说,推车时自己那莫名其妙的第六感觉。要是这没有说出的一切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或者,他能彻底遗忘该多好呀!这样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各种噩梦。
梦里,常常是事发当日的情景:宁静又空旷的滑雪场里,十几米外,那个刚刚还热乎乎的身体被甩出摩托车又迅速消失在视野里……那天,不知是出于愧疚还是说起石理对自己的好时真的难过,有一刻他眼角渗出了泪水。恰到好处的伤心。
一个是校长,一个是保安,可因为是儿时玩伴,关系好也属正常。片刻的沉默后,警察问他耳朵怎么了?他轻描淡写地说,小时候被狗咬的。这是事实。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没什么问题。警察让他在口供上签字按了手印,又说再想起什么要立即汇报等等。
追悼会是一周后举行的。
学校能去的人都去了。石校长的头经过处理后又被安在躺平的身体上。殡仪馆的入殓师用白色围巾掩饰着那块的残相。涂脂抹粉的面孔毫无血色,那个儒雅的、英俊的、温和的石校长,再也不会回来了。许多人掉了眼泪,包括那个英语老师,那个叫张海峰“卡西莫多”的女人。女人被晕湿的睫毛膏残留在脸上,嘴唇发青。往日的光彩没了一半,一瞬间,张海峰对她的恶意也消失了大半。
石理的爱人因为哭得太多,脸有些水肿了。她的表情在悲伤、焦灼和倔强之间徘徊。
她来过学校,听说还去过教育局。在丈夫是不是工伤这件事上,她执拗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许多人觉得她已经神经了。他们认为:她丈夫出事纯粹是在八小时之外,并且是从事和学校无关的事情时出的事。她所说的为考察学校体育器械而丢命的这个结论明显站不住脚。可石理爱人坚持说,如果没有学校购买器械一事,她丈夫就不会在休息时间外出,他外出也是为了学校的事。那段时间,学校加班加点已是常态,哪有什么休息日。这倒是说到学校一些人的心坎里了。
追悼会后她找了张海峰,约他吃饭,问他那天的情景。她说石理喝酒不行,那天为什么会喝酒?二是,石理小时候因为目睹过大舅的车祸惨状有心理阴影,排斥一切机动车,怎么会去骑雪地摩托车?还有,她听石理说过,那两个商人非要让学校高价购进一批体育器械,石理一直是拒绝的。她总觉得这些都和石理的死有关系。她想让张海峰仔细回忆那天的每一个细节。但张海峰给不了她更多的细节。“没有了。”在又一次说完给警察说的那些细节后,他说。她一时无语。张海峰那张风吹日晒的面孔上显示着老实人特有的憨厚。她还是第一次见到丈夫小时候的这个玩伴,也是丈夫生命最后一刻在身边的人。她满腹疑虑怔怔地看着张海峰,又看了眼他带着伤疤的耳朵和脸。之前她装作不经意地偷偷看,还掩饰住惊讶来着。张海峰此刻的缄口不语,在她看来是人走茶凉事不关己的冷漠。她的脸色已经到了生气的边缘。她不满地看着他那张有点丑陋的脸,包括张海峰的耳朵,仿佛要从他狰狞的肌肉里找出蛛丝马迹,以证明自己猜测的正确性。一秒、两秒……在她犀利的目光下,张海峰的脸皮都要抖了。
好吧。她忽然侧过脸望向一边说。张海峰瞥见了侧过脸的她鬓角新长出的半截白发。是要就此放弃追究因果的无奈,还是不再指望对面这个人的果决?她没说。
她当然不知道张海峰的伤疤是因为那个冬天,为了贏石理才留下的。从小到大,石理什么都是第一,什么都做得好,老师喜欢,父母夸奖,就是春梅也夸他。他滑冰的速度就差石理一点点了。他想赢石理一次,他才在他们都走后偷偷返回,一个人反复在冷风呼啸的水库边练习。结果独自回来的黑夜被那条恶狗抓伤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秘密。他恨石理。
饭馆就在学校附近。正是那年他初到学校报到时,石理带他来的饭馆。他说过要回请石理,但一直没有机会。趁石理爱人去卫生间时,他把钱结了。
后来,教育局给石理爱人换了所离家近的学校工作,算是表达组织的关怀和慰问。她再没来过。
二
五月,春暖花开,石校长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像什么也没经历过一样,学校又恢复了过往的节奏。只是橱窗里的领导小组石理的名字被换掉了。每逢上面来领导,出门迎接的是那个副校长。那个岁数比石理大、肚子比石理大、派头看上去更像领导的马成斌。
两个商人不久后又来了学校。他们提着一兜饮料,都是保安们爱喝的“绿茶”“可乐”,还特意拿给张海峰一瓶。保安们客客气气地接过,告诉他们马副校长的办公室。张海峰一直斜靠着门边,看着两个商人轻车熟路地上了教学楼,消失不见。
又过了几个月后,马成斌副校长转正了。正式做了校长后,他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校门口添了人像识别的考勤机、校园内外环境的美化、食堂的治理、年终的绩效考核等等。校服样式也做了调整,由原来松松垮垮千篇一律的蓝白相间的运动装,变成了英伦样式小西装、小西裤、格子裙。学生全部站在操场的时候,看上去是洋气多了。
对保安也有了要求。要求他们见了上面的领导要敬礼,要问好。直到教育局的一个领导阻止了敬礼的环节。新校长的热情显得多此一举,老师们私下里幸灾乐祸。
张海峰的孩子今年上初二了,家长会也明显增多了。为了中考成绩在全市学校里排名靠前,学校总是不定期给家长“拧螺丝”。他们对症下药,先开大会,再开小会。全校八个初二班级,根据排名分成三波:前一百名一波,中间二百名一波,剩下的则是第三波。东子排名不稳,一会儿一百多名,一会儿二百多名,基本在第二波。家长会一直以来都是东子妈妈去的,偶尔张海峰也会去。这次,东子居然考到了八十多名,顺理成章上了第一波孩子的名单。周五又是开家长会的日子,老婆要去照顾生病的岳父,家长会是张海峰去的。
开会的场地在学校的多功能厅,每把椅子上都写着老师的名字。听说,马校长也计划这样弄。他未雨绸缪,打算直接照搬一些模式对学校进行管理。
前面坐满了女家长,张海峰在最后面找了个位子坐下来。他前面的几个家长早早掏出了笔记本准备记录。他斜眼看过去,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那些家长手里的笔记本简直就是孩子的成长档案。他之前听老婆说过,现在看到真的了。都是厚厚的大本子,因为离得近,详情一目了然:月考的成绩单一条条贴着,下面是各科成绩的分析,和上次考试成绩的对比。红蓝色钢笔涂得又整齐又密集。孩子的卷子、作文都夹在里面。即便没这么齐整的,手里也都有个本子,一看就是专门开家长会用的,以保证孩子各个阶段表现的完整性。只有他是空手来的。张海峰心里生出对不起儿子的惭愧感。
教务主任首先开讲。她分析了这次月考成绩。既有学校自己的,也有和其他学校对比的。说到个别竞争对手,她很是不屑。对于下次月考成绩在全市的排名,她信心满满。谈到未来,更是意气风发。怪不得每次家长会后,老婆会更加起早贪黑给孩子做饭。
接下来,教务主任安排了这次月考年级第一名的学生家长进行演讲。前三名学生的名字和照片都在学校入口处贴着。东子说过,这个吴佳芮每次都是前三名,很牛。
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女人走上了台。“大家好,我是吴佳芮的母亲……”张海峰心里就抽了下。熟悉的声音一下唤醒了记忆。他想起了一个人。許多年前,坐在他前面的那个女孩,常常转过身和他说话。暑假,在村子的巷子里,她和几个女孩在墙根打倒立,每次赢了后她都会开心地笑。这些年想起她时,他会一遍遍在脑海里描绘她的样子。主席台距离张海峰大约有十几米。张海峰眼睛没有以前好了,他抻着脖子盯着看了两秒,就确认那个作报告的家长就是李春梅。她也老了,比年轻时瘦了好多。以前扎马尾,现在是齐耳的短发。她脸色不怎么好,看着有些憔悴。李春梅不像下面这些家长想的那么虎妈。相反,她温和谦虚低调。她说,自己对孩子的管教很少,因为她很忙。她是一个野外工作者,孩子一直是奶奶照顾的。她常常是一个月左右才能见孩子一次。孩子从小就很自立,都是自己管自己。她没有谈太多家庭教育,更多是谈孩子的成长,孩子的好习惯。她简短地发了言。那些打算好好记笔记、以为要得到教育秘籍的家长露出了失望的表情。教务主任及时凑到话筒前说:“可见,一个对工作高度负责对生活高度负责的家长,会给孩子树立自律的榜样,吴佳芮妈妈自强自立就是给孩子最宝贵的财富,如果你们整天拿着手机……”教务主任巧妙地将话题转到父母身正胜于言教的话题上,就此叮嘱家长多关注孩子。
家长会散会后,李春梅就被一群家长包围了。他们凑到她跟前,跟她套着近乎。特别是几个女家长,她们不相信这个每次考前三名的学生的家长没有法宝。他们向她请教一些具体问题,比如,孩子脾气古怪、玩手机、早恋……俨然把李春梅当做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无敌家长。李春梅显然习惯了被好学上进的家长求教,浅浅地微笑地说着什么。班主任护着李春梅,好像生怕她会说错什么似的。
李春梅被淹没在一群家长中间,偶尔在几个人身体的缝隙中透出她的蓝格子衣服、头发,还有青灰的脸庞。张海峰远远地看着,心脏紧张地跳动着,从看到她开始,他就不能平静自己的心跳。他原地坐着,站立,又坐下。那些家长越围越多,连她的头发丝都看不到了。他走出了会场。他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和她相认。出门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向窗户上的玻璃望去。他看到一个丑陋又慌张的自己。他越发气馁,坚定了不去找她的想法。
有个优秀的孩子,有份工作,知道她还不错他就满足了。他为她高兴。走出大门后,凉风灌进了他脖子里,脸颊和身体的热度都开始降温了。以后不会再来开家长会了。他想。
他还见过吴佳芮。那次是在学校门口等儿子放学,恰好看见女孩出来,他毫不犹豫地走近,把给儿子买的饮料塞给她。女孩冲他一笑说,谢谢叔叔。那个笑脸,竟然和小时候的李春梅一模一样。
三
马校长的一些改革起先还是赢得了老师们的认可,比如,校园的美化、食堂的管理。可渐渐地,大家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尤其是考勤制度最让大家反感。以前多好,公事私事两不误。那些中年老师,个个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一身慢性病,仅凭周末不足以缓解生活的焦虑和忙碌。他们需要一周中有那么一两次可以早走或者迟来的机会,去医院、去社区、去后街……办完那些不大不小的琐事,以便让生活正常进行下去。马校长呢,最早还在大门口守着,迎接到校师生。但老师们不买账,觉得他就是监督大家考勤的。
在新城区居住的老师每天开车或坐车,路上堵不堵车,家里有没有突发事情,都说不准。为了刷脸打考勤,有人在路上急赶出过车祸;有人为了找个停车位和别人吵过架;还有人下午一节课也没有,但也得在办公室等时间到点。诸如此类鸡毛蒜皮的琐事像蚊子的叮咬让他们奇痒无比。最关键的是,校领导用这个机器把他们禁锢住,动辄就扣他们年终评优的积分。而校长、副校长……那几个领导却不参加考勤,这使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发泄牢骚。有几个语文老师较了真,从私下嘟囔到扎堆说。他们想起了石理,念起石校长的温和和人情味。
学生的行为管理也没有跟上。本来计划打造小绅士小淑女,可学生习惯养成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套衣服几个活动几次训话就能完成的。学校百分之九十的孩子都是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大部分缺失,沒有父母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很容易就是5+2=0的恶性循环。一到下课,那些学生追追打打、连走带跑的毛病依旧如故,暴露原形。“个个都是穿西装的土匪。”保安们说。
在大家的期盼中,考勤机在某天终于坏了,显示屏不动弹了。怎么坏了?大家佯装不解又暗自喜悦。有人猜是谁谁谁砸坏的。好几个因为这考勤机倒了霉的人是重点怀疑对象。坏得好。没有谁敢正大光明地这样说,但大家的心思却是相同的。
校长说要修好,但管后勤的那个人太忙或者别的原因一时没顾上。机器坏了后,考勤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为了避免迟到时被领导撞上,老师们常常把电话打给保安们,问马校长在不在?走了吗?有的还加了保安的微信以方便联系。就连那个给张海峰起外号的英语老师也加了他的微信。
有一天,大家突然发现好几天没见到马校长了,才知道他去内地考察了。要去一个月,不用再纠结每天的考勤,学校又短暂地进入一种旧秩序的平静中。
一个多月后,马校长回来了。回来不久,就宣布学校要采取一项大举措:修建塑胶跑道。这算是个新鲜事,县城里除了两所高中学校修了塑胶跑道,其他学校都还是老旧操场。学校也将有那么漂亮的跑道了!老师和学生们陷入了新的期待中。
东子又考了年级前一百名,张海峰和老婆的微信就被拉到学校为前一百名孩子建的群。群名叫“将军群”。顾名思义,不想考好大学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所有家长的名字都要求改为学生姓名加爸爸或妈妈样式。他很快在头像中找到了“吴佳芮妈妈”。但没有吴佳芮爸爸。难道她是一个人?不过,也有别的学生只有父母其中一人加入的。
李春梅的头像是和女儿吴佳芮的合影。他点开照片看。虽然和记忆中的女孩不像一个人,但眉毛、眼尾的一大一小的黑痣都没变。眼神也依稀可辨。是李春梅。变化可真大呀!他感慨着。二十多年没见了,他猜,如果路上擦肩而过,他们得互相打量一会儿才能确认彼此。他潜藏在群里,不说一句话。有要回复的,也是他老婆回复。
每次月考成绩一出来,他也会点开看。之前只看儿子的,现在还看吴佳芮的。这孩子成绩好找,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群里自是免不了老师的夸赞和点评,也少不了别的家长的羡慕嫉妒。李春梅呢,真的很忙,她很少回复那些善意或者酸味的话。别的家长慢慢相信了,真如她自己所说的,孩子的学习,她管得很少。这更让他们有了加倍的羡慕,甚至是嫉妒。
除了李春梅,为吴佳芮的好成绩由衷开心的,也只有张海峰了。
有一天下午,那两个商人又来了。他们进去后不久,马校长和他们一起出来了。他们像以前那样,又“哥,哥”地和马校长称兄道弟。他们上了门口油光锃亮的奔驰——之前两人开的是辆桑塔纳。他们的打扮也更洋气了,从头到脚各种名牌。但脸上的谄笑没有变。就像张海峰脸上的疤痕一样,改变不了。
没过多少天,学校大门口来了辆大车,车上装满了东西,修跑道要用的材料到了。
学校操场被围了起来。至少要围三个月。学校暂时取消了跑操等环节。跑道还没修好,又开始修操场的主席台、智能化的大门……那几个月校园里琅琅的读书声里,终日伴随的是叮叮当当的施工声。
半年后,学校变了样。钱花到哪里哪里好,这话真不假。那两个商人早就像学校的员工,出出进进,毫无障碍。他们喜眉笑眼的,擅长和各种人打交道。李老师张老师的,嘴巴很甜。见了男老师递烟。学校是无烟环境,被拒绝后,他们一点儿也不恼。见了女老师,总是美女美女喊着。财务上那个四十多岁仍然穿着少女装的李老师最受用。
一些人在这个时候又想起了石理。比较之下,他们觉得这马校长魄力还是有的。要是石理,学校的变化不会这么大。甚至打考勤的事情也被部分人解读为马校长有事业心的表现。虽然着急了点,出发点还是好的。反正,已经不再打考勤了,大家忘记了之前的各种不满。在全县中学里独一无二的塑胶跑道面前,大家只剩下沾沾自喜。
篮球场原先是露天的,现在那块地往后扩展建了气派的运动馆。夏天不晒,冬天不冻,那些爱好打篮球的人都给马校长微信朋友圈晒出的运动馆点赞。
比运动馆启用更早的是球场和塑胶跑道。赭红色四百米跑道,白色的分道线,整齐划一的人工草坪,白红绿三色互相衬托,清新气派。这个操场还是教育系统五十多所学校的试点,电视台做了报道。
这更加剧了别的学校动工修建操场的迫切心情。附近的五中、张海峰儿子的学校等好几所学校也热火朝天地开始修建了。
最早是有人闻到了难闻的气味。是那种大家熟知的类似胶皮的气味,刺鼻子。新东西嘛,有味道很正常。学校有这么好的跑道,许多爱好跑步的人课间空闲时就来跑步,那个英语老师健美的身材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过,她很快吐槽每次跑着跑着就想咳嗽,不想再去了。
大家等着气味散掉,就像新买的衣服新买的包新装修的房子,最初的气味不都很大吗?生活经验告诉他们,那些让人不舒服的气味最终会散去的。跑道天天在大太阳下晾晒着,啥味散不掉!许多人都说。
不知道是习惯了,还是味真的淡了,慢慢地人们不再谈论。不过它的关注度也在降低,因为别的学校的跑道也修好了。像流水线制作出来的,颜色一样,材质也一样,透出的高级感也是一样的。
四
大约两个多月后,味道散得差不多了,操场的使用率又高了。
但很快出现了问题。
先是高一二班的一个家长反映,自己孩子近期回到家后昏昏欲睡,伴有头晕恶心症状,要请假去体检。紧接着老师中出现了皮肤过敏、鼻炎加重的现象。那个英语老师甚至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起了一层小疹子的胳膊。
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附近学校几个孩子因为高烧或者呕吐等症状住进了医院。医院检查结果是铅中毒。张海峰儿子学校的三个学生也因为发烧住了院,两个是气管炎,一个是红眼病。有一天,儿子带回来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一个学生居然得了白血病。“妈妈,你猜是谁?”不等张海峰老婆问,东子说出了名字,“就是学校每次考前三的吴将军。”儿子之前也喊过吴佳芮在学校的外号。张海峰起初还瞅着电视里那个小品,当听到孩子说出吴佳芮的外号时,他电打般坐直了。“吳佳芮?”他问。“嗯,就是她。”吃了一口菜的儿子说。他怔住了,眼前是女孩接过他给的矿泉水时腼腆的笑脸,还有穿蓝格子衣服的李春梅被一群家长包围的情景。
为什么是这个孩子呢?他呆住了,陷入巨大的悲伤中。真是天要塌下来的难过,那种难过他体会过,对,就是那年看到自己被毁的脸时心里才有的难过。
儿子还说了几个孩子的名字,说学校已经停了体育课。
他拿过手机,点开将军群,点了李春梅的微信头像。他想加她好友,说点什么。他想着可能会有的对话。很唐突,只要说说孩子,就没那么尴尬了。他想。张海峰老婆也啧啧可惜着,摸着儿子的脸和头,问他有没有觉得哪儿不舒服,忧心忡忡的样子好像大难来临。张海峰犹豫后又放下了手机。
坏消息很快传开了。一个本来要考名校的孩子得了白血病,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就是灾难。脆弱的家长们都共情了。有个公众号发了文章披露这事,还配了家长号啕大哭的照片。张海峰点开同事发的链接。是吴佳芮的奶奶。那篇文章是从孩子第一天不舒服写起的,孩子如何坚持上学,家长怎么做的,医院咋处理的。在那篇文章里,张海峰才知道吴佳芮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得病死了。父亲的病花掉了家里所有的钱,是孩子的奶奶一直在照顾孩子。妈妈常年在外打工。之前老师说的野外工作,不过是在另一个城市的工厂上班。不知真的还是假的,记者还提供了一堆令人心酸的信息:奶奶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也是一身病,一直忍着。
看着图片里老人抹眼泪的照片,张海峰呆呆地坐在门口,脑子里反复是那些让他意外和惊讶的话。
校长马成斌坚持认为这和学校跑道没关系,仍然让体育老师按时上课。不过他很快就改口了。据说是因为几个女教师“造反”了:一个女老师走到校长面前,撸起了袖子,她白皙的胳膊上涂满了药膏,药膏下面是密集的小疹子。还有那个英语女老师晒出了自己起了疙瘩的腿……也许是被女教师“造反”的行为吓住了,马校长这才暂时停了体育课。
与此同时,儿子学校建的“将军群”里,许多家长开始自发为吴佳芮捐款。捐款持续到深夜。老师发来李春梅妹妹申请的筹款链接,大家又是纷纷转发。还有人联系了北京的医院。李春梅呢,说了许多谢谢,也偶尔在群里报告着孩子的检查结果和病情。他想象着李春梅该有多么焦灼和痛苦。她咋那么倒霉呀!比他还倒霉。他无法想象如果是儿子病了……
那天的夜晚,似乎比任何一个夜晚都更沉重。回家后,他拿出了放在床下面的钱。那钱从第一天拿上,他就一张也没动过。他记得石理摔下去那天,两个商人第一件事不是报警,而是抓着他的手要他隐瞒让石理多喝了酒的事实。还说,车是他推来的,上面有他的指纹等等。慌乱、恐惧、惊吓中,他仅剩的一丝理智也没了,稀里糊涂地听从了两人的安排。事情过去后,他们又塞给他五千元。这一万元他没花,又去银行取了一万元,拿着两万元去了医院。
李春梅看到张海峰时,一张被痛苦折磨到憔悴不堪的脸上先是出现了惊讶的表情,然后是流着泪水的惊喜。她顾不上更多了,噙着夺眶而出的泪水,凭着残存的理智抓着张海峰的胳膊推着他出了病房。她家的事在抖音上也传开了,这几天不断有陌生的好心人来过,也有好几年没有联系过的人来到医院看孩子,安慰她。张海峰的到来让她很惊讶,她节制地将手扶在张海峰的胳膊上,捂着嘴哭号了几声。“海带,我咋这么倒霉。”李春梅说。被唤儿时的小名,张海峰的身体里像是有股电流震颤得身体抖了下。他很想给这个一直藏在心里的女人一个拥抱,让她在自己的怀里好好哭一场。可他并无张开怀抱的勇气。与此同时,他想起了石理。这之前,石理也喊他小名。在这个城市里,喊他小名的人没有几个了。
等说完孩子的病情,她平静了些,在医院走廊尽头的椅子上,他们聊起了小时候,说到开心的记忆,李春梅还会暂时忘记了眼前疾难,咧嘴笑笑。也说了石理。看着张海峰的耳朵,她忽然想起一件和石理有关的记忆。说小时候有一次她也碰到过恶狗,石理还帮她打退了恶狗。“好险呀,狗快追上我了,是石理拿了块大石头打退了狗。”张海峰听了这句话后愕然地盯着地面僵住了身子。李春梅继续感慨石理死得太惨了,又掉了眼泪。不等他接话,李春梅很快又陷入无尽的自责中,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孩子,让孩子遭这么大罪。她说:“海带,人活着好难,为什么总会遭遇厄运?你,我,还有石理,现在又是我的孩子。”
从医院出来,张海峰步行走了好久。他眼前是吴佳芮灰白发青的脸、没有血色的嘴唇,和李春梅极力克制悲痛的眼睛,还有李春梅的诘问:“人活着好难,为什么总会遭遇厄运?”他想,他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到家后,他拿起手机,翻出了几年前那个警察的电话……
五
吃完晚饭,他打开了电视。电视上“法治人生”节目讲的是一个民事案子。主持人是个短发美女,结尾她以旁观者的视角发表着评论:“如果嫌疑人多一点常识,多一点法律意识,悲剧就不会发生……”她两只纤细的手在镜头前比画着,带着不容辩驳的锐利和果断,像又冷又尖的钉子。他还是耐着性子听完了。
他老婆给窗台上几盆开得正好的天竺葵浇水。她现在果真是个胖人了,原本的尖下巴陷在两圈肉里。她耐心地擦拭着花盆缝隙间的窗台。因为跛足,她不爱出门,空闲下来就收拾房子。家里干干净净的。
几天后,马校长消失了。有人说,他是从家里被带走的。是那两个被公安部门带走的商人供出来的。后来又抓了教育局一个副局长。消息陆续传来。原来,那两个商人是教育局的副局长介绍的。他们想给所有学校都铺上他们的塑胶跑道。原本想贿赂石理,石理一直不同意,马成斌和副局长是亲戚,如果马成斌来当校长一切就水到渠成了。他們说,那天只想着把石理摔成残废,他也就当不了校长了,没想到,竟把人摔死了。
张海峰记得,出事那天,他顺手推的是第一辆摩托车。如果不是第一辆就好了,他无数次后悔过。现在才知道,后面两辆摩托车也有问题。
石理翻下沟的时候,轰地撞到一棵老松树。老松树上落满了一冬天的雪骤然间扑簌簌地落下,先是几秒钟碎石大小的大雪团,然后是白砂糖般密集的小雪沫,它们急遽划过冰冷的空气跌在地上。
从那以后,张海峰的梦里经常在下雪。大雪、小雪,一场又一场。
张海峰因为隐瞒破案线索和接受嫌疑人贿赂也被警察带走了。
那是个雪后的傍晚。天空清澈,月光皎洁,雪地里弥漫着仿佛祝福的光晕。走出门外,一阵寒风扑过来,张海峰打了个冷战。但他很快平静下来。
警车驶出小区,上了马路汇入车流中。路灯的光倏忽闪进车内,打破沉寂的空间。盯着一明一灭的光,张海峰脑子里闪现出刚才在小区门口看到的雪人。是下午几个放学的孩子才堆的。和所有的雪人一样,它有着大大的头颅、黑洞洞的眼睛,还有被胡萝卜装饰的鼻子。脚步匆匆的人来人往中,它们孤单又互相陪伴。他想起那年腊月,也是一场雪后,他和石理在麦场上堆了两个雪人。那天,石理开心地指着雪人说,一个是我,一个是你。石理的笑脸像电影中的特写画面浮现眼前,那么清晰!那时,一切厄运尚未到来……张海峰干涸的眼涌出泪,凝结成水珠,一颗又一颗,仿佛心里的冰块融化后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