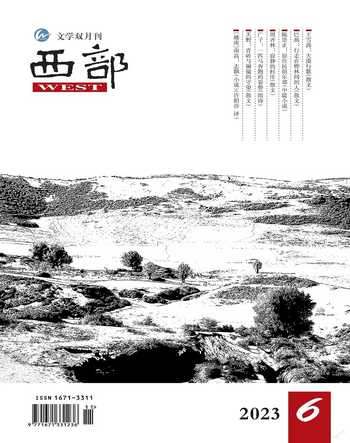无法抵挡的爱情
王亦北
我对爱情的想象是从一场婚礼开始。1999年的冬天,在仪陇县九龙乡的一个小山村里,刚满七岁的我,经历了记忆中的第一次婚礼。
我们居住的小院,在矮山脚下的一个凹凼里,说不清是从哪一代开始,王家人便倚靠着矮山筑屋修路,把日子安顿在了这里。这次的新郎是屋后的小叔。小叔是幺公公(爷爷的亲兄弟)的小儿子,又高又瘦,特别是他的一双手,垂在裤缝处,像极了没处藏的两只大烧饼。我喜欢尖起手指,一边抠小叔的手,一边说,小叔,你的手比所有人的手都大。
“手大气力才好!”小叔抱起我,一把将我举过头顶,骄傲地说。山里人靠天吃饭,最要紧的,是有一把好力气。小叔长得高,干起活来不管不顾,没有人会怀疑小叔是块种庄稼的料。
小叔就要结婚了。幺奶奶请人给小叔说媒是在夏天。亲事定下来以后,小叔日复一日地变得沉默。他不再和我们这群小不点嬉笑打闹,不再高门大嗓地在田间地头晃悠。每天天还不亮,小叔都跟在幺公公的后面,一起去翻整山梁上、山腰上、山脚下那些被幺公公日日呵护、放在心坎上的泡酥酥的土地。他们翻山越岭地去找水,把玉米、胡豆、花生、红薯、高粱喂得肥嘟嘟的,风一吹,老远就能看见茂盛的秋意。秋天结束的时候,小叔把手摁在裤腿上揩了揩,摊开在我的面前,说:“小小,你看我的手还大不大?”
我把手伸出来,用食指轻轻地按了一下说:“小叔的手……很硬,像石头。”村子里的男人和女人都有一双石头一样的手,到了冬天,那双手会变成紫红色,隆起无数座矮丘,比以往的每一天都更加坚硬。
父亲说,男人就是要先成家,成了家就懂事了。“那女孩子呢?”我问父亲。“女孩子当然要先找点事干咯,手心朝上的日子多难熬!”母亲撇撇嘴,总结似的说道。
大人的话,小孩子听过了也就听过了,却真心实意地喜欢香甜的糖果,喜欢两块钱的红包,喜欢铺天盖地的热闹,喜欢看紧抿双唇的新媳妇。在这个院子里,小叔家与我家就是最亲的亲人了。亲历亲人的婚礼,在我还是第一次,没有哪一天,我不在焦灼地惦记着。可恨的是,孩子的日历总是格外漫长,时间被锈住了一样,好不容易把上午熬过去了,剩下的黄昏又拖长了影子不肯走。我的冬天比村子里的冬天来得更早,我要母亲给我穿上最厚的冬衣,一边跺着脚,一边往手上哈气,明明冬天已经来了啊,小叔为什么还有一个月才办酒席。
大概是地处偏远的缘故,夜晚被矮山和树木更长久地留下。结婚那天,幺公公屋檐底下的白炽灯朦朦胧胧,晃荡出一个似是而非的清晨。小叔新剃了头发,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土蓝色中山装的裤缝笔直地垂到脚底,像是在下面系了一块大石头。大人们举着火把,抬着箱奁,背着早早准备好的猪肉、鸡鸭鹅,挑着鱼,拥挤在幺公公屋后的那条陡斜的羊肠小道上。我跟在后面,一直把他们送到了大马路上。
迎亲的队伍渐渐走远。小叔跟着他們走进浓雾,从一个高大的背影到身份难辨,几乎是一念之间。我看着小叔越走越远,生出了一种失去的感觉。“为什么人长大了就非得结婚不可呢?”我很想问问小叔,是不是以后都不再跟我们玩了?白霜簌簌地从柏枝上落到了我的鼻尖,又被细细的唢呐声带走了。寒意顺着脸颊一路小跑着钻进了我的脊背骨,我叹了一口气,连忙下意识地捂住了嘴。叹气不好。尤其是小孩子。母亲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今天是小叔的好日子,怎么都要讨个好彩头才是。
从小叔家到新婶婶家有十来公里。幺奶奶早早地就教过了我流程。等新婶婶到了,办完了仪式,送到了新房里,我就要进去说祝福语。还有,最好是一直陪着新婶婶,给她倒倒水,递递东西,让她有个使唤的人。院子里十几个小孩,幺奶奶唯独把我喊到屋里,郑重地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满口答应。这有什么难的呢?你们就等着看吧。
新婶婶穿着红西装、红裙子,胸前佩着红花,涂着红嘴唇,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踩着红色高跟鞋出现在幺公公家的院子里。小叔站在她的旁边,双手捏着烟盒,笨拙而殷勤地把香烟递给近邻亲友,也把围着新婶婶的人群涟漪一样地往外送。院坝里,激昂而欢快的唢呐声横冲直撞,配合着村里人总想一探真假的隐秘心事——那些或真或假的说法传了那么久,今天正好做个验证。谁都想把新媳妇看得更真切一点。
提起这门亲事,听说的人都忍不住感叹小叔命好。至于婶婶为什么偏偏就答应了嫁给小叔,村里众说纷纭。广为流传的是,小叔模样周正,又有一副好身板子,正好是个顶梁柱的料。不然,婶婶家又是在镇上,又是开磨面坊,怎么会瞧得上一个只有点薄田地的穷门穷户,还自降身段嫁到了村上。不寻常。一桩事一旦跟日常拉开了距离,想象就开始了。所有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抵达谜底。
“让一下。”新婶婶高门大嗓,两只手象征性地往外一推,便侧身从人群中泻开的小缝里走了出来。我的小叔没来由地埋了埋头,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活脱脱像跟在婶婶身边的一个小弟。那天的祝词,我到底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太能想得起来了。只记得,我接过新婶婶的红包,便飞身从新房里跑了出去,以及,新婶婶左边脸颊上的那颗醒目的黑痣和含笑中利刃般锋利的眼神。
办完婚礼不到半年,小叔干脆利落地和幺公公分了家。以堂屋为界,幺公公住右边三间屋子,小叔和新婶婶住左边两间屋子。两代人照旧从一道门槛上进进出出,却各自遵循各自的时钟,既不结伴出门,碰面了也不过多言语,俨然一个屋檐下的两家人。
在家里,幺公公对幺奶奶的不满从一日三餐延伸到了喂鸡养猪。一闲下来,幺公公总爱歪坐在屋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在青石板上磕着铜烟杆,嘴里不停地嚷幺奶奶活了一把年纪,做的事没一件着调的。所有的话小叔都一字不落地听见了。婶婶也听见了。到了赶场天,天光还未赶到,小叔就已经等在老丈人家里的磨坊门口了。
婶婶娘家的磨面坊总共两台磨面机,一台挂面机,一台打米机,再加上位于出入场镇的必经之地,又是镇上唯一的一家磨面坊,轰隆声不仅贯穿了赶场的日子,也贯穿了磨面坊的每一个寻常日子,和婶婶出嫁前的日与夜。薄雾似的面粉漂浮在岁月的河床里,整座房子和房子里的主人终年在雾茫茫的日子里打转,周身挂满了麦子的味道。婶婶还有一个娘家哥哥,因为不愿意日复一日地在面粉里扑腾,早早地便和场镇上的年轻人去了浙江打工。哥哥走后,家里磨面坊的主力就成了婶婶和父亲。直到婶婶出嫁的前一天,父亲还穿着那身早已磨出了卷边的宽大的天青色罩袍在磨面坊里忙个不停,他要赶在迎亲的队伍到来之前,给女儿准备好一百斤挂面,两百斤面粉,三百斤白大米。这些粮食足够两个人从年头吃到年尾。
幺奶奶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直到小叔跟着婶婶去了浙江打工,才在一个洗衣服的晚上,停下来问幺公公,以后怎么得了?漫天的星辰忽明忽暗,有些潦草地应付着这个夜晚,一如许多年前的那些夜晚。
“你为什么会着婶婶的魔呢?”我曾经这样问过小叔。小叔抬起手,用食指和中指在我的额头上轻轻敲了一下,回答我说,你还太小,不懂爱情。那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起爱情。爱情。多么奇怪的两个字。村子里的人从来不会谈到爱情。在他們的世界里,不管男人女人,到了二十来岁,自然就是结婚,生子,把田地种好。在那个世界里,有怨怼,有疼惜,有认命,有不甘,就是没有爱情。多少年的日月都这样过来了。以前是这样,以后必定还是这样。
我当然不相信小叔的话。其实,哪怕是算上左边脸颊上那颗黄豆大小的黑痣,婶婶也是村里新媳妇中数一数二的标致人物。吊着眉梢的柳叶眉,微微往外鼓的大眼睛,高鼻梁,细薄的唇,比挂面还直的黑头发。婶婶所有的脸部线条直来直往,即使在笑,浑身依旧散发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距离感。如果要找一个词语来形容婶婶,那一定是石头,刀劈斧砍的那种,坚硬,我行我素,绝不菩萨心肠。我没法想象小叔的爱情。那个时候,我还并不知道,在小叔漫长的一生里,将会用几十年的光阴在这两个字里泅渡。
再次见到小叔,是在堂哥的婚礼上。那时,距离我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了十六年。小叔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小小,你看我的手还大不大?”在小叔的手掌上,密密麻麻的纹路或深或浅的交错,缠绕,和那些经年的旧纸一样,在历经岁月的风尘之后,小叔手上的沟壑愈渐开阔,一个男人的中年也顺势潜入手掌的深处。那只手掌褪去了青年时代略带粉调的羞涩,只留下再也磨洗不掉的浅黄色和结茧的硬壳。
我摊开手,在小叔的手上比画着,想象着曾经的那个女孩也是这样窥探她的青年。
小叔还是一个人参加婚礼。在涌动的人群里,我并没有找到婶婶。自从婶婶嫁给小叔,逢年过节,小叔家所有走亲访友的日子里,都鲜少见到婶婶的身影。最开始,小叔还能拿新媳妇怕羞当借口,时间一长,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避开婶婶。然而,不是每一次都能避开的,尤其是有了孩子。有一年过年,小叔带着孩子去走亲戚,婶婶照常回了娘家。小孩子眼皮浅,看不得别的孩子有妈妈哄着,撒泼打滚地也要找妈妈。在儿子声嘶力竭的哭声里,小叔身体里的大河终究是挣脱了所有的理智,轰然决堤,毫无回旋的余地。他丢下儿子,不顾亲戚父母的错愕,一个人迈着大步走回了家。婶婶到家的时候,小叔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她收拾完小叔呕吐的秽物,也不闹也不骂,手一甩就把脏衣服扔到了院子里。婶婶只用了一根火柴,火星子便挟带着燎原的架势把那团衣物啃噬个精光,最后剩下一团坚硬的黑色。时间可以作证,当婶婶的影子从墙壁上端端地剥下,在火光照不到的那条小道上,小叔和婶婶收拾好行李去了浙江。从那以后,在这个村子里,小叔的爱情下落不明。
这次的婚礼,即便小叔不来,也情有可原。举办婚礼的地方,选在堂哥的老屋。如果再早上二十年,从小叔家的祖屋走到这座房子,也就十来分钟的样子。二十年过后,再想从小叔家过来一趟,得开车沿着长张高速、龙吉高速、恩广高速、张南高速跑上一千来公里。小叔会赶在我们之前到达,显然出乎我的预料。
我到达的时候,小叔正坐在堂屋正中的一个矮凳上。堂哥家的老屋是一座两层的水泥楼房,盖于2002年左右,在那座老屋里,有水泥的墙面,水泥的地面,水泥的颜色和水泥的气味。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们始终执着地忠诚于它们的那个年代,以最闲散的姿态把时间拒之门外。白炽灯泛黄的灯光从房顶洒下来,小叔坐在半明半暗的光里,卖力地搓着手,活像在完成一个郑重的仪式。在他的面前,搪瓷火盆里的木炭将要燃尽,灰白色的草木灰挂在上面,看上去,比废旧的古道上经年的积雪还要落寞。所有的人和物再次回到旧时光里,一如多年前小叔结婚的那个清晨。
真的会有爱情吗?从仪陇的小山村,到去浙江务工,再到湖南定居,在小叔和婶婶的爱情航线里,婶婶都是唯一的舵手。一个男人,在遇到一个女人之后,交出全部的自己,如果不是爱情,那又会是什么?我困在小叔的爱情里,近乎固执地找寻答案。
小叔为什么选择定居湖南成了我心里的一个谜。一个只有小叔才知道谜底的谜。要知道,那时,父亲已经在成都郊区的农村买下了房子。小叔把移居提上日程,也是受了父亲的启发。他把第一站放在了成都。小叔托幺公公来过我们定居的地方看过几次,找房子,谈价格,近乎固执地关心土地里的收成。
一切似乎都在朝所有人预判的方向走,小叔也会在附近买一套房子安顿下来。毕竟,这里离老家不会太远,条件又远远好于仪陇的老家,最重要的是,还有亲人在这里。三年以后,小叔告诉我们,他们在湖南岳阳买下了房子。我指着地图上的岳阳问父亲,小叔为什么要去这里?父亲只是摇头。那是在我们想象之外的地方。
我偶尔也会从父辈的口中得知小叔的近况,在只言片语里,更多的,是一些结论,要么言之凿凿,要么似是而非,无一例外的,都关乎婶婶。故事风一样地流传,小叔永远都是说好的那一个人。从和婶婶在一起的那一天开始,他删除了所有的拒绝。他只能说好。也只会说好。没有人会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曾经对我说起了爱情。
我无法抵挡爱情。在堂哥的爱情面前,我甘愿放弃半年前就计划好了的旅行,驱车六个多小时,只是为了回来参加他的婚礼。至此,从一个词语出发的爱情,带着二十四年的颠沛流离,又一次回到了它的原点。
堂哥的爱情故事并不新鲜。年轻时候的恋人,因为所有能够想象得到的现实原因选择分开,而后结婚,离婚,兜兜转转,中年重逢,不顾父母反对,抛开世俗偏见,最终走到一起的故事。堂哥的婚礼没有任何仪式,连办酒席都只是为了满足父母的一桩夙愿。我见到堂哥的时候,他身穿一身黑色西装,胸前别着一朵带有“新郎”绸带的胸花。旁边的堂嫂,则是一身极简的红色羽绒服,家常的淡妆,如果不是胸前那朵象征“新娘”的胸花,也许也和人群的人一样,湮没于人群。他们端着酒杯,缓慢地在他们的爱情里挪动。
是他们让我相信,面对爱情,哪怕是有再多的铁证如山,很难有人不会选择原谅。原谅自己,原谅爱人,原谅所有被错付的时光。我也愿意选择相信,这样的婚礼,便是他们年轻时候共同憧憬过的——纵使山重水复,历尽繁华,只要依旧是你,那我宁愿用最朴素的方式去迎接和拥有。
我不清楚小叔是否知道堂哥的婚礼背后的艰难曲折,能够想象到的是,婚礼上的小叔,一定不会想到,在二十四年后,一个下雪的冬天,我、他,还有堂哥,会因为爱情重逢。只关于爱情。这近乎一个童话了。
我只想和这个爱情的启蒙者谈谈爱情。我摘下帽子,拍掉了身上的积雪。淡黄色的羽绒服上,还是留下了深浅不一的水渍,仿佛在明示我曾历经风雪。该怎么开口呢?我学着小叔搓手,跺脚,就是讲不出口爱情。
“就数你的变化最大。”小叔开了口。他从我的童年开始讲起,越过我的少女时代的断章,直接跳到了我的现在。那么,你过得好吗?小叔如是问。
“挺好的。你呢?”
“我也挺好的。”
之后,就是長久的沉默。唯有沉默。漫长的学生时代结束后,我的少女时期也一去不返,我已经很久没再想起爱情了。多么幼稚的一个词语。就在这时,小叔的大哥径直走到了小叔身旁,他猫着身子,几句耳语过后,小叔倏地埋下了头。我看着小叔的大哥走了出去,又看着小叔走出了门。小叔依然那么高,依然那么瘦,他的肩背微微前倾,从后面看,那颗花白的脑袋像一只停错了渡口的渡船。
后面发生的事情都是父亲告诉我的。父亲说,小叔抱着他哭了。为了四百块钱。
小叔的大哥进来是跟小叔商量给一位长辈送个红包表达下心意的事。倒也不那么亲,只是山遥水远,见一面是一面。父亲说,回来前,婶婶已经把哪家的老人要给红包计算好了,小叔兜里的钱该怎么支出,全得按照计划来,多余的,一分也没有。小叔的大哥提到的这位长辈刚好在计划之外。小叔消失在风雪里。他对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想一个人走一走。
“要是雪能一直下下去该有多好。”我等着父亲继续往下说。“你该去看看他们的新房了。”父亲丢下这句话,便沿着小叔消失的方向离开了。雪地上,在那些父亲脚印经过的地方,褐色的污渍不断地朝外晕染开去,像是一场洁白的自证。远处的天空下,树梢顶上的雪依旧白得耀眼。
堂屋里闹哄哄的,所有我童年熟悉的面孔都已经老去,或者正在老去。他们或沉默着,或哄抢着谈论彼此的青年、中年、老年,就是没有人谈论婚礼。堂嫂坐在矮凳上,背对着陌生的人群,面朝大雪,专注地玩起了手机。堂嫂的父母没有来参加这场婚礼。只有她,为了心目中的爱情,不顾一切,单刀赴会。新房在二楼。我是在爬上第一级楼梯的时候停下的。就在那一刻,我听见心里有一个声音在问自己,真的要继续往上走吗?我不确定。
成为堂哥爱情的旁观者,纯属意外。八年前的夏天,堂哥经过我读书的城市,我们约在一条小巷子里吃了一顿麻辣烫。那年正是堂哥工作的第四年。我念大二。我们只好谈爱情。一个失去爱情的人,和一个臆想爱情的人。失去爱情的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家境普通。她说,她在他身上看不到未来。她用一句话结束了他们的四年。
那就去领证算了。八年过后,她因为堂哥的一句闲话,回归了他们的爱情。八年没有结束爱情。四百多公里的距离也没有让爱情走失。堂哥请了假,开了近五个小时的车去了堂嫂的城市,赶在民政局下班前领了证。堂哥笑着对我说。
一切都似真似幻,现在想起,连同以后的日子都隐约着朦胧着。在爱情里,小叔早已渐行渐远,只留下一个恍惚的背影。要是真走进了那间新房,日子扑面而来,再盛大的爱情也会变得单薄。在那条不归路上,谁又会知道,该如何安放爱情?
我只能躲。我几乎是小跑着钻进了车里。遥远的山顶上,风裹挟着风,吹薄那些沉重的铅灰色的云群,惨白的日光正慢慢地从那道豁口里漫出来。在雪光的映照下,这个白日比所有的白日都要明亮得更为彻底。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也是这样跑着离开了小叔的新房。只是爱情,在雪融化的时候,不知道又将去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