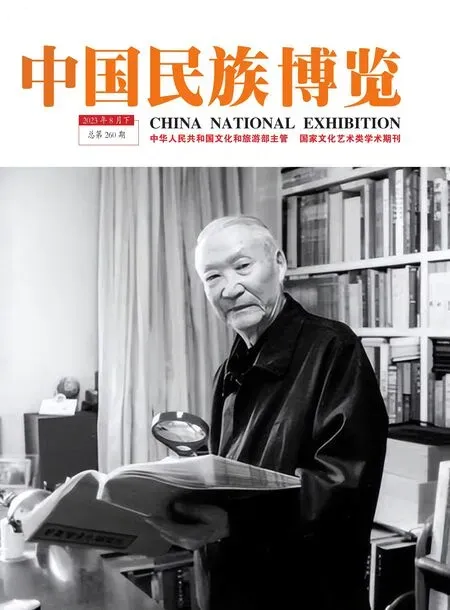简论新视域下的中国画审美嬗变
——以王建的山水画创作为例
王晓韵
(同济大学,上海 200092)
一、中国画审美嬗变的线性轨迹
中国画的发生发展有一个基本的公认的文化脉络,它就像中国山水画的本质特征一样,有它自己的独特的纹理,历代的作画者和观画者共同的审美关照,给了它们各自图通的皴法,使它最终形成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美学系统。
概括地说,它有五个阶段、五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两宋以前。也可以说,它使原始社会就开始了的一个艺术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画的孕育与生成期,包括原始美术、商周青铜器、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帛画,以及南北朝时期、唐及五代时期的绘画等等。个性奔放、无拘无束、追求象形是其主要的风格范式。
第二个阶段是两宋时期,也可以表述为北宋、南宋时期。以“似”为终极追求,开启了中国画的写实时代,艺术地再现山水、花鸟的生存状态与生命精神,铸就了范宽的精神领袖位置,院体山水正式走向前台,并处于主导地位。骨法用笔渐成主流评介标。以北方山水形象生成为主诉求,中国山水画以斧劈、刮铁、豆瓣等皴法为主的面皴法体系基本成型。
第三个阶段是元代集群肇始的士夫画或者叫文人画时代。赵孟頫引领下的“元四家”登峰造极,竖起了书画同源、以书入画的大旗,中国画以线造型的观念被奉为圭臬,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的出神入化的笔墨演绎,造就了中国山水画的座座奇峰。哲学意蕴与个人际遇的交织,形成了文人画的迥异于院体画的艺术底色。气韵生动的根本源流在骨法用笔的基础上,升华到了中得心源的境界,文人画的审美取向正式确立。
第四个阶段是明清时期的“四王”与“四大画家”交相辉映时代。“四王”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画院体画一路最后的高光时刻,此后,院体画便逐渐式微,一蹶不振。而以石涛、八大山人为代表的“四大画家”矩阵则独占江湖,并长久影响后世。
这一长时间的审美融合,其实是审美观念上的一次大碰撞、大对峙、大交锋。结果是文人画的彻底胜出,线条审美之上上升为中国文人画。
第五个阶段是五四以后至今的阶段。这是中西绘画相互融合借鉴发展的时代,黄宾虹一生鞠躬尽瘁,身体力行弘扬国光,开辟了中国山水画的民学篇章,同时,又积极向西方绘画尤其是印象派汲取营养,树立了笔墨独立审美的新典范,耸立起中国画的近现代巅峰。林风眠、潘天寿、傅抱石等也另辟蹊径,在中国画的审美升级过程中发挥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八五思潮之后,中国画更是进入了一个笔墨当随时代的国际化视野和现代绘画的物理与精神空间,审美张力空前扩展,中国画审美价值的内涵急剧丰富、外延迅速泛化。中国画作画者与观画者的审美冲突空前激烈,多元化、多极化、多式化的审美共鸣与撕裂同处一室,形成了艺术史上令人惊讶的一个奇观。
二、艺术观的迭代引领中国画审美嬗变的方向
艺术观是一个作画者或者一个观画者的审美引擎,更是一个阶段乃至一个时代的审美引擎,它引领着中国画沿着一条崎岖的山道螺旋式上升、渐进式前进。
“正像印象派完成了西洋古典绘画传统的现代转化一样,中国山水画的古典传统的现代转化是由黄宾虹完成的。”【王鲁湘语】但是,黄宾虹孙然吸取了印象派的一些油画技法,他的目的却是使他的山水画更能寓情于景,更能完美的体现他的浑厚华滋的审美追求,更好地去写他的胸中逸气。
和黄宾虹一样,支配中国画发展筋骨的东方审美精髓是“意境论”,“意境论”是中国山水画审美思想的重中之重,是作画者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是中国画作画者的核心艺术观,是他们美学思想的中心,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
中国画的审美工具和创作利器是以形写神,线条和笔墨是它的基本语汇,也是它的程式化的东方式的话语体系,它是有特殊表现力的笔、墨、水、色以及纸的神奇合力。
苏东坡在评价王维的画时说“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一语道出了中国画的意境密码,即写意的艺术观。画中有诗境,也就是画的诗化,诗平面艺术的文学化表达,是视觉的二维触达与思维的立体生发的化学反应,这是一种极为高级的审美活动,是中国画千古流传、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意境是一个美的陷阱,它让一切可以被美所打动的人,不能自拔。
王建是一位深知其中三昧的作画者,他特别推崇傅抱石的作画方法,作画之前,临纸凝思,一语不发,直到在白纸上看出画来,方才解衣盘礴,酣畅淋漓,一气呵成。通俗的笔墨语言,不俗的意境,跃然纸上,撼人心魄。
作为一个散文家,他对意境的理解,与齐白石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有在画中彻底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精神,作品的意境才是独一无二的,才是有人格印记的,也才是有艺术史价值的。书写自己的胸中逸气,逸气来自于对道法自然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的妙悟,因为写意,是中国画最本质的艺术观。
三、时代性的凸显是中国画审美嬗变的推进器
石涛提出的“笔墨当随时代”,对后世的作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下的审美语境下,讨论中国画的时代性,实际上是在讨论它的继承性。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画的兴起兴衰兴旺的波澜壮阔的传承之路,就是它的时代性嬗变的曲折历程。时代性的凸显,是中国画执着前行的不竭动力。
中国画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意境的内涵,二是笔墨的衍变。从意境内涵的集群性规模性演变路径来看,如果以中国哲学史的学术架构为基本依托,就会清晰地发现,中国画的意境内涵的演进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它基本围绕着当时的主流哲学思想作极端的两极运动,要么与之高度匹配,要么与之高度离异,甚至反叛,时代的痕印十分鲜明,生动可感。研究历代优秀的绘画作品,不考察这些绘画背后的时代背景、人文结构以及诸子百家文化渗透状况,几乎寸步难行,无从谈起。
比如从唐宋宫廷山水画中主宾思想的孵化与强化,主山、宾山、母山、子山、靠山形象在画面中的位置排列与面目地位的隐喻,一股“理学”的气息扑面而来。从知识论角度而言,中国画自北宋时期强调“状物形”,到元代以后重视书法用笔,专注于自我个性抒发的“表吾心”。
所以说,艺术史就是在不断变幻的历史语境中,界定艺术家及其作品与其所处的时代中诸多关系尤其是与哲学思潮纠缠关系的历史。
从顾恺之、吴道子、范宽、郭熙起,一直到达今天,中国美术史就是一部活的中国哲学史,是一部活的中国文化史,一部活的笔墨史。
笔墨是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的精髓。元代画家的最大的艺术史贡献,就是强调书画同源,以书入画。元代著名画家赵孟頫,不但享有极高的画名,其书法艺术也一直为历代所重。其《秀石疏林图》《古木竹石图》就是把书法融入绘画从而使绘画笔墨极具书法意味的经典范例。
笔墨作为中国画的核心造型手段,是中国画独有的艺术语言,也是中国画审美的第一要件。离开笔墨,中国画的审美也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董其昌在《画旨》一文中说“以境界之奇怪论,其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中国画成熟的笔墨语言已经自成体系,并且成为中国画审美的极端重要的文化标尺。
到了近代,一些富有革新精神的作画者,开始有意识得对中国画的传统笔墨程式进行反思,并在创作实践中冲破传统,创建出属于自己的笔墨符号,建构了中国画新的笔墨语言系统,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等人的探索为中国画的时代性变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为中国画的现代性进程发挥了师范性作用。
王建的山水画创作,注重汲取前人的探索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传统,看世界,看当下,既与传统一脉相承,又与传统拉开距离。这个距离,就是要体现作品的时代性,因为传统的笔墨语言已经变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能创造性吸收,创新性转化,而不能抱住不放。王建说:“就像我们的文学和戏剧,不能再用文言来表达一样,表现今天的世界和当代的生存秩序、生命伦理,必须用新的宇宙观自然观生命观去关照,必须导入全新的价值理念和生命精神,当然,更必须更新笔墨语言符号,为新的中国画审美世界洞开一扇既面向传统又面向未来的窗口。点线面与黑白灰的交响,应该奏出新时代的新乐章。”
四、国际化的融通是中国画审美嬗变的催化剂
林风眠将中国画的笔墨效果与细化的色彩技法融为一体,创造出具有独特视觉效果的彩墨画,灰色调的运用独树一帜;徐悲鸿将西画的速写以及素描的手法借鉴过来,运用到中国画的人物造型手段中去,形成了前无古人的造型语言。西画的造型手法以及色彩、构图、透视、光影、明暗等艺术工具的介入,使中国画的创作理想和作品格局、审美格调发生了颠覆性的巨变。
全球化的浪潮无孔不入,不光深刻地影响了人的生命本体、生存意义和生活状态,更深刻地重塑着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人的审美层次和审美趣味,深刻地改变着人的美学追求和审美规律。
中国画艺术的民族性面临着沉重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何去何从?吴冠中的答案是其中的一个路径选项,他说:“笔墨等于零”。在他的作品中,中国的民族化艺术符号依然存在,而且被夸张和放大了,比如南方的民居、水、树枝、少女等等,中国画的线条意识甚至得到了极端化的强化,但笔墨的意蕴大大弱化了,笔墨的象征性价值几乎消失殆尽,笔墨的哲学统统被驱逐出去了。他的画,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中国风格的西洋风景画,一览无余的画面结构与单调乏味的画面寓意不中不西,索然无味。当然更谈不上逸品的诗意、意境与宏大气象了。
徐悲鸿则在开创中国画另外一种走向可能的同时,葬送了中国画的生命根基。
拿着毛笔,在宣纸上画水粉、水彩、油画,不是不值得尝试的一种创作形态,但是离中国山水画的创作原点与创作旨趣已经相去甚远。中国画的本质属性与精神指归缺失以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那么,中国画在国际化的审美融通大趋势中,如何才能走出自己的既有民族血统又有国际范的现代化之路呢?
八五思潮之后,中国画研究与创作领域一直在形形色色的实验与嫁接的探索中艰难前行,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必须面对必须回答。
王建在自己的中国画创作语言更新过程中,努力向当代世界美术的最前沿不断攀岩,以求在最高峰上洞察最前卫的艺术风景,感受最先锋的创作时尚,顶礼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洗涤身心,积聚精神的心理的素养的能量。同时,他也在不断兼顾自己的审美堡垒,固守中国画的底线,构筑中国画的审美高线,把笔墨的神力与水墨的神奇演绎到出神入化的境界,推向艺术图腾的自由王国。把中国画的民族化引向极致,把中国画的国际化引向极致。那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是中国画的又一个巅峰时代。他说:“中国画走向世界没有悬念,但任重道远,道阻且长,这需要一代代作画者的不懈努力。”
中国画的事业古老而又年轻,中国画的创作充满诱惑与陷阱,中国画的审美嬗变清晰而又杳然,大化无机,草蛇灰线,需要前瞻性的理论与理念招引,需要对审美规律的精准认识与精确把握,更需要在创作实践中不断试错,反复修正,持续深化。
在艺术观、时代性和国际化的新视域下,中国画的自我蜕变、自我革新、自我升华,是中国画走向新生的必由之路,舍此,没有其它捷径可走。
多元碰撞中洁身自好,八面来风时和而不同。东方文化的哲学变现时中国画不朽的精气神,是中国画的精神之钙,是中国画的母体与母题。所以,中国画的作画者与观画着都要站在全球化的基石上,回望从前,放眼未来,以千百年来的人类审美嬗变的重山叠嶂、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为考量和审视的经纬坐标,把中国画的创作与欣赏、品鉴与传播当作一门科学去学习和研究和实践。这样,才不会急功近利,不会指鹿为马,不会误入歧途。
中国画创作与欣赏的艺术观迭代、时代性介入与国际化审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十字路口,理应引起各方的关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