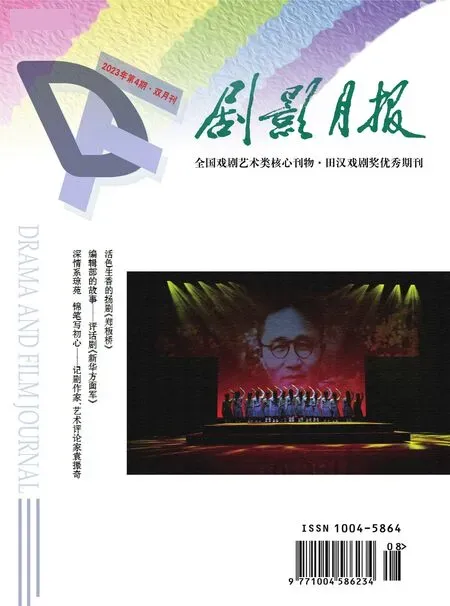论《北京法源寺》编创视角下的民族自觉性
■牛俊玲
20 世纪以来,话剧经道日本传入中国这百年间,经历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造就了中国话剧独具一格的发展历程。回眸历史的长河,从“五四”时期,就有关于“新剧”“旧剧”问题的讨论;到20 世纪50 年代焦菊隐导演在北京人艺进行了大量民族化的舞台探索,再到80 年代“戏剧观”大讨论后,黄佐临导演用《中国梦》对他的“写意戏剧观”进行了生动的实践。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百年话剧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话剧民族化的奋进史。时至今日,民族话剧正在朝气蓬勃地发展着,学界对于“话剧民族化”的讨论也仍在继续。
一定程度上当前我们依旧面临民族话剧的现代化创建问题,在这样的语境中,田沁鑫导演近些年在话剧舞台上的上下求索无疑为这个问题探索了多种解法。从其处女作《断腕》以来,她将自己的创作始终扎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秉持着中国传统的美学理念和民族精神,致力于创建专属于中国故事的舞台表达。同时,她的话剧作品在吸收现代派戏剧的基础之上,极大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戏曲的美学特征。其2015 年改编自著名文学家李敖的长篇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以一种极富创造力的手法,在高度还原原作精神的基础之上,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田氏”改编,并成了田沁鑫导演民族话剧探索的里程碑式的代表。田沁鑫导演曾这样评价这部作品:“这部戏,在戏剧结构上践行‘中国戏剧’之品格,之审美,之义理,之精魂。”因此,本文试图从导演的编创视角出发,探析《北京法源寺》民族化的自我构建。
一、文本编创:对民族历史的深刻体察
小说版《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学家李敖所著的一部“破格”之作,他通过对大量历史细节的搜寻,以一种超脱的视角,将戊戌变法这一事件与京城皇家寺院法源寺巧妙结合。以古庙为纵线,串联起历朝历代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的历史人物,形成了一张具象化的历史网络。最终以15个章节、一楔子一尾声,对中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段真相进行了复刻。并且涵盖了400 个子题在内,小说的密度和容量无疑是惊人的。这也给田沁鑫导演的改编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她在做前期的改编工作时坦言:“做这个戏,就跟鬼打墙似的,觉得非常难以突破。”导演翻阅了四十多套书籍,花费了近两年时间反复改稿十二次,最终以一种政论体的形式让参与戊戌变法的人物,汇集于北京法源寺,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去讲述戊戌变法事件的始末。于是观众在话剧舞台上看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想交锋,一种多视角的历史叙述。
从编创的文本层面来看,田沁鑫导演对原作小说《北京法源寺》的内容进行了较大的取舍。她将全剧的核心焦点放在了戊戌变法的“变法”上,而不是原剧的反清革命。李敖在原作中无疑有对戊戌变法这段历史的叙述,但他仅仅将戊戌变法作为基石,为的是探讨变法失败后的变革论题。而话剧版将变法事件作为全剧的核心,并且在展示事情始末的同时,给予了谭嗣同较大的笔墨,着力突出他的民族大义精神。同时导演打破了小说的线性叙事,对剧作的结构进行了全新的调整,呈现出了极大的跳跃性。整部剧包含了三重叙述,这三重叙述之间有着独特的叙述组织。第一重:1921 年法源寺的寺院主持普净向自己的弟子秉义讲述关于晚清末年戊戌变法的故事;第二重:戊戌变法事件本身,从戊戌变法前期的筹备,到戊戌变法开始实施,再到最后戊戌政变,“围园劫后”失败,以慈禧为首的保旧派对戊戌六君子的清算;第三重:叙述者普净和秉义穿越当下的时空,在叙述1898 年戊戌变法的同时还与晚清末期的历史人物进行了对话。不仅如此,在这三重叙述之间,导演并非按照常规、回顾历史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而是对其进行了别出心裁的重构。例如在一开头的人物登场时:
普 净:寺庙有形佛门无形,我叫普净,法源寺现任方丈。
谭嗣同:当修佛心远离有形,我叫谭嗣同。
普 净:我是1921年这座寺庙的方丈。
谭嗣同:我死的时候是1898年。
一场由1921 年与1898 年的对话由此开始。普净在剧中从对话人的视角来与戊戌变法的关键人物进行对话,同时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自报家门”与普净的串讲为整场故事开了头。在内容上,导演将各个人物的核心观点进行了提炼,并让人物在观众面前进行激情昂扬的公开辩论。于是,观众看到了苦心求学、誓死也要发动变法的康有为,看到了想要救国救民但百般无奈的光绪皇帝,看到了少年英才、有拳拳报国之心的梁启超,看到了变法不成、舍生取义的戊戌六君子。这场绘声绘色的视觉呈现中,家国大义,侠胆衷肠,变得清晰可见。同时,剧中不仅有戊戌各派人物之间的思想交锋,还有1921 年人物的对话。从而形成了1921 年和当前的两个时间的双重叙述。同样是第一场,除了普净和秉义之外,几个关于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已经以“牌位”的形式正式登场,他们对自己的结局已然心知肚明,从一种超然物外的视角共同开启了这一场庙堂高耸的人间戏场。最后一场与第一场进行呼应,故事的谜底已然被揭开。关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各方记载也被搬于舞台之上,故事从1921 年进入当下。观众走进的是戊戌变法那个充满动荡与未知的时刻,但是面对的却是当下的每一个革命性时刻。我们在触摸历史的同时历史也在触摸我们。我想,这就是导演想通过这场风云激荡的历史带给观众的最大启示。
田沁鑫大胆打破原作的叙事结构,以多维度、多侧面的立体化呈现,揭开了晚清这段众说纷纭的历史面纱。导演自己曾言:“中华民族走到今天,这个国土之大、人民之众的国家走到今天,是数以万子民和数不清的明君贤相努力而成的,我觉得只有晚清这出大戏是可以做出一部有形式感的戏,就是中国大戏的精神。”《北京法源寺》这部能够代表中国的历史大戏,通过舞台化的视觉呈现传达了一种极其强烈的思辨精神,实现了当代话剧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民族化表达的完美统一。同时展示了导演对于这段历史的全新解读,足以见得田沁鑫导演在话剧创作上高度的民族自觉性。
二、舞台编创:对传统戏曲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话剧的拓荒人欧阳予倩先生曾指出:“在中国舞台上表现中国人民,不能脱离中国戏剧艺术的传统,必须继承并发扬这个传统。”毫无疑问,对传统戏曲的学习和借鉴,在话剧史上历来被看作话剧民族化的核心。不同于其他导演在编创之时的生硬照搬,田沁鑫导演从其创作之初就一直在自觉地对民族戏曲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利用,亦不自觉地在其作品中注入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学特征和艺术品格。“超以象外”是中国戏曲虚拟表演和舞台时空转换常用的表现手法。它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身”的体认世界的方法,也是一种得神遗貌、得鱼忘筌、物我交融的艺术手法。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戏曲以对外部事物的“表现”为主要原则,这与西方艺术讲究对生活进行“再现”有很大的不同。这种表现的原则使我们不必还原实物的全貌,只需要得其“神”。对“神”的刻画和描写则显示出了很大的“写意性”。在具体的舞台上演员的虚拟表演和时空的自由流动则是“写意”之美最大的外部表现。
《北京法源寺》所涉及的空间十分复杂,包括寺庙、宫廷、民间,为了使多重时空下的叙事能够自然地在舞台上展开,导演放弃去营造叙事空间的高度逼真性,与中国传统戏曲一样以一种高度的时空假定性、流动性,让舞台留下大量的自由空间。随着演员的上、下场和演员的虚拟表演而转换时间、空间,由演员的表演带领观众进入特定的时空场景之中。纵观整场表演,舞台上并没有出现宏大的实物布景,取而代之的是灵活自如的椅子,一把把椅子排列在舞台的两侧,随着人物的上下场而随取随用。同时导演对椅子的巧妙编排,使得舞台呈现出中轴线的对称结构,这样的视觉呈现非但不显得单调,反而非常契合舞台上辩论的气氛,也预示保守派与变法派两个阵营之间的较量。舞台上单设的话筒则是他们为自己发声的武器,无论多少夜以继日的奔忙、秉烛夜谈的辛劳,还是没有挡住变法的失败结局。如果说光绪唯一还能为变法做点什么,那一定是告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快快离开。导演在这时特意编排了一场生死诀别的“煽情戏”,充分利用舞台的假定性,让人物进行了一番历史性的会晤。在大雨如注的暗夜里,光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踉跄地迎着最后的一抹光亮跑到舞台正中央,在这样紧要的关头,导演没有用宏大的场面去渲染,而是化繁就简,让舞台上仅剩下他们四个人。全场做暗部处理,利用灯光划分演区,他们两两相拥做最后一次的陈情,在此刻,演员的情感被推向“爆发点”,并以此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在假定性的舞台时空中,之所以依旧能够让观众置身于导演所营造的情景之中,是因为“情境的假定”与“情感的逼真”在这一瞬间的相撞。导演充分调动演员的逼真的情感进入这一情景,并为观众所信服。这正是戏剧演出的魅力,也是田沁鑫导演多年来深谙舞台空间调度之道的硕果。
整部剧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当属“谭嗣同密会袁世凯”,导演对传统戏曲中“一桌二椅”的运用可谓发挥到极致。这一场戏舞台上的聚光灯聚焦到以一桌二椅为核心的舞台正中央,在紧锣密鼓与战马嘶鸣声中,人物出场,开始了一场生与死的较量。谭嗣同和袁世凯两个在历史上评价完全两极的人物,他们先后诉说起自己的苦衷和无奈。一文一武,一念之差却造就了他们完全不同的历史结局,道德的评判无法衡量政治棋局,历史总是这样复杂多变。这一场戏无论是表演方式、调度还是节奏都完全是化用了戏曲的方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人物对话。导演对舞台假定性的运用,为人物创造出多重碰撞的可能。同时,这样唯美空灵的舞台,则契合了中国戏曲美学的“超脱之需,意境之美”。
三、主题深化:对人物之“情”的细细雕琢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谈到戏曲时,他说“传奇妙在入情”,一个“情”道出了中国传统戏曲的核心。与西方不同,古希腊戏剧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提出了艺术的本质在于模仿,并把情节(行动)放在悲剧六要素的首位。此后,“动作”中心论占据西欧戏剧史很长时间。这是因为在再现真实生活的西方戏剧中,动作是内部情感、思维的直接显现,而中国传统戏曲则讲究在“另一个世界表现生活”。表现生活则需要借助他所使用的媒介,中国传统戏曲是用歌、舞、诗为主要的创造材料,在表现故事时就会“长于‘直取心肝’地表达人们的内心状态和情感活动”。而不太擅长去描绘具体的行动细节和叙述事件本身。因此,历来多少中国传统经典曲目无不把“情”字放在创作的第一位,“论曲之妙”唯在‘能感人’三字”。
导演田沁鑫在访谈中曾多次谈到想要做情感叙述,让戏剧与观众直接关联,以“情”来打动观众。但是在一部人物众多、故事复杂的宏大叙事里,想要以情动人绝非易事。原著中李敖采用的是分章叙事,由多个小的独立章节综合而成形成一个大的叙事整体。如何割舍?在话剧中,田沁鑫则突出了谭嗣同这一“英雄”人物,将谭嗣同的选择和思想作为全剧发展的核心线索。这就使得谭嗣同作为导演“入情”的主要发力点。谭嗣同这一人物的塑造无疑是成功的。他感人,首先在于他是一个有情人。谭嗣同上场时,他说:“我想以我的个人之躯打破数亿国众的意识桎梏,用生命化作一道闪电,去惊醒沉睡的人。”谭嗣同很清楚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怎样的劫难,慈禧独断专政,官员为求自保选择忍让赔款,义和团的大刀更是对准了百姓。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我们废君主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这是他维新变法的初心。而真正将谭嗣同这个有情人烘托到极致的还因为他是一个敢于直面生死的人。当戊戌六君子变法即将被捕、罪名深重之时,其他人纷纷给自己的亲信发急电求救,“求救”“救命”“救命”,谭嗣同大喝“丢人现眼”。在这里,导演专门宕开一笔,写了谭嗣同与梁启超在法源寺“结义”的场景。贪生怕死乃人之常情,人生在世谁不想长命百岁呢?学富五车的康有为、有满腔爱国之志的梁启超,他们在“逃离”“拯救”“殉难”中,选择了“逃离”,但谭嗣同却选择留下来,明知留下来就是死路一条。他本可以不死,但是在他的信念里,死才是当下唯一一种救赎国家的方式。袁世凯说他是“真狂徒也,真义士也”。正是他对大清的爱、对中华的爱,才让他死得毅然决然。在这样两相对比的情景设定中,将谭嗣同这一为国殉难的大义之举烘托到了极致。
在这习惯了趋利避害、贪生怕死的时代里,谭嗣同大义凛然,坦坦荡荡赴死显得格外动人。随着这一情节高潮处的到来,观众的情绪也随之点燃,因为在这一刻,观众所能看到的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和道义甘愿赴死的谭嗣同,还有亿万万像他一样为了民族和未来舍生求死的人。在这里,话剧的主题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正如导演徐晓钟所引:“戏剧艺术的内涵除了轻松和新奇之外,还可以让人感受强烈的情感,让人体味深刻的思想,让人领悟命运和观照灵魂,让人被一种社会责任感和生命激情所震撼、所感召。”领略完《北京法源寺》的穿越时空、对话古今、超脱生死,无疑不让今天的观众对这段历史、历史当中的人物有所感念。田沁鑫导演坦言想通过这部剧,试着做一个中国的大戏,“这个戏连佛教、带宫廷、带民间,完成了关于生死的讨论、关于家国的讨论、关于民族出路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我觉得确实很有意义,对国家很有意义。”《北京法源寺》讲述的是历史,洞见的却是我们当下每一个瞬间。从小说到话剧,每一次对历史的解码和再读都是一种立足于时代的解构与结构,于历史于当下都有深刻的民族启发意义。
四、结语
《北京法源寺》不同于田沁鑫导演以往的作品,这是一部集民族历史、民族心理、民族传统于一身的现代化剧场表达。纵观田沁鑫导演的多部作品,她总是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去思索民族的当下与未来,以经典的文本为依托,充分融合中国传统的美学理念,结合东西方舞台的戏剧手段,传达出属于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田沁鑫导演曾多次提到焦菊隐先生对她的影响,并直言她的最终理想是:“建立具有更多民族风格的中国话剧的新的演剧体系。”这样的民族自觉性,是基于她对民族文化、传统戏曲的深深热爱,更是基于她对中国话剧发展道路的清晰认识。时至今日,她始终在用自己的方法提笔书写着话剧舞台上的“中国故事”。她的作品不仅将东方美学和西方现代剧场技术进行了融合,更深刻地挖掘了民族传统美学精神,形成了一种深深根植于民族土壤的自我言说,而这种“言说”不仅仅是想要塑造中国现代剧场的辉煌,更是在当下的国际视野中,发展中国戏剧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