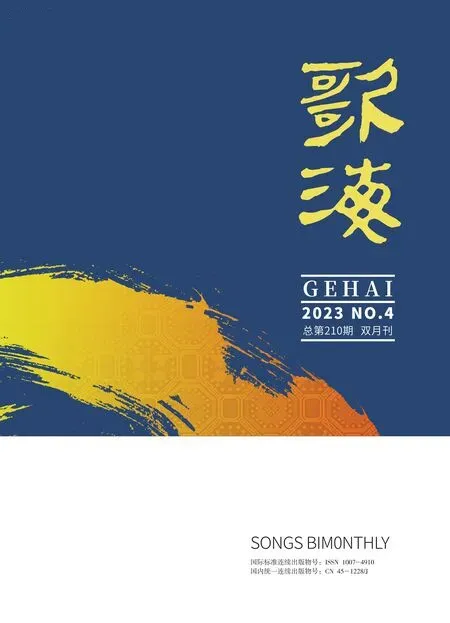论壮族服饰展示方式与服饰美学的相互关系*
●周雨童
由于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观者无法直接对少数民族艺术进行全方位的融入性审美体验,只能通过不同民族艺术的展示媒介进行欣赏,获取对民族艺术的审美体验。因此,处于壮族服饰生存环境之外的“他者”便通过绘画作品欣赏、影视艺术观看、博物馆观览等方式对壮族服饰进行艺术欣赏,获取其美学价值。从清代的《皇清职贡图》到如今的生态博物馆、电影作品等,壮族服饰的展现方式不断多元化。壮族服饰展示方式与服饰美学的相互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展示方式全方位展现壮族服饰美学,另一方面,展示方式的变迁表现了不同时代进行民族艺术欣赏的途径,拓宽了观者的审美方式。古今观者以“器”入“道”,通过不同的方式了解、欣赏壮族服饰,感悟壮族服饰的美学特征,克服时空阻碍,进行融入性较强的审美体验。
一、《皇清职贡图》中壮族服饰的视觉呈现与明清服饰美学的流露
《皇清职贡图》以展现少数民族服饰的地域性、综合性、活态性与政治色彩为主要原则,较为全面、动态地将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服饰美学进行了视觉传达。通过欣赏画作及其图说,观者跨越时空获取到清代壮族服饰的美学特征,借助《闲情偶寄》中对服饰美学的研究与记录,可以进一步欣赏清代少数民族服饰绘制的原则与民众的服饰审美追求。
(一)地域性、综合性、政治性、活态性:壮族服饰绘制的主要原则
《皇清职贡图》以独特的采风方式、绘制原则与主旨思想收集与记录极具流变性与个性化的民族服饰,是研究清代服饰美学的重要艺术资料。“仿其服饰绘图……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①〔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广陵书社,2008,第1页。乾隆十六年(1751 年)六月初一,乾隆谕旨昭示了《皇清职贡图》创作的发端。但学者庄吉发发现四川总督策楞所进的奏折中记载:“奉上谕命臣将所知之西番……形状,并衣饰、服习,分别绘图注释。”②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一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第910-911页。可知,《皇清职贡图》的前期准备工作至少在乾隆十五年(1750 年)就开始了。③庄吉发:《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第11页。同时,上述材料也可推断得知《皇清职贡图》中的图像先“照式绘图”,再送往军机处汇总,这一绘图方式就像一部“自下而上”的人类学影像,更具真实性、权威性。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皇清职贡图》彩绘本正式绘制完成。④祁庆福:《〈皇清职贡图〉的编绘与刊刻》,《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如今彩绘正本已不复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完整的谢遂摹绘本。
《皇清职贡图》中对族群的命名表明清代已经注重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差异;以绘画的形式展现了清代全国边疆各地和相邻国家的民族风貌,分段式地将每个民族一男一女两个人物形象展现在画面上。其中,第四卷对广西壮族人的描绘主要集中在贺县壮人、兴安县壮人、融县壮人、思恩府属侬人、西林县央人、岑溪县俍人、贵县俍人、马平县伢人、西林县皿人。⑤佟颖:《清代前期朝贡关系考辨——从〈皇清职贡图〉说起》,《满语研究》2011年第1期。《皇清职贡图》一改以往职贡图以队列觐见的构图,采取族群所聚居区域在前、民族名称在后的方式对同一民族的不同族群进行命名,如对贺县壮族“居深山中”⑥〔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9页、435页。的生存环境描写,图册特别观照了民族及其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在描述西林县央人衣着时,特别说明“与皿人相类而服饰稍别”⑦〔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9页、435页。,注重同一县同一民族服饰的不同。由此可知,清代绘制民族服饰时已经注重民间艺术的地域性差异,且表明服饰差异与地理环境存在密切关联。
《皇清职贡图》中的图说补充了图像的信息漏洞,以文字说明了壮族不同支系的历史迁徙过程、生活场景、日常习性、民俗特征、文化交流等。例如,兴安县壮人作为图册中第一处对壮族人的描绘,其中写到壮人元代自楚、黔到粤,蔓延到桂平、梧各地山谷中,与瑶杂居,且性格彪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兴安县壮人“被化最早,习俗较醇”①〔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6 页、420 页、399 页、426 页、406页、399页、420页。。此段描写总体论述了清代广西壮族人的迁移历史、居住环境等,也展现了兴安县壮族人的独特习性。随后,图说介绍此地民众以耕种、贩卖为生,席地而炊,紧接着将其服饰特征进行展示:“男蓝布裹头”“妇椎髻银簪,悬以花胜,抹额悉缀以珠,衣裳俱缘以锦绣”②〔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6 页、420 页、399 页、426 页、406页、399页、420页。。由此可见,清代对民族服饰的绘制已注重表现服饰与民族历史、地理环境、生活习俗之间的关系,力求展现综合性、活态性的民族服饰。
《皇清职贡图》的成书出于彰显国威、描绘边疆的政治意图,因此,清政府与各地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此图册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到了清代,中央政府更加注重与少数民族的和谐共处,制定政策,加强政治、文化、经济上的联系,《皇清职贡图》呈现了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的盛世景象。另一方面,《皇清职贡图》中的文字说明也侧面反映了当时广西的壮族较为主动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有粗知汉字者”③〔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6 页、420 页、399 页、426 页、406页、399页、420页。“本朝以来壮人安耕织、慕文物”④〔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6 页、420 页、399 页、426 页、406页、399页、420页。“奉法与齐民等”⑤〔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6 页、420 页、399 页、426 页、406页、399页、420页。“颇知奉法”⑥〔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6 页、420 页、399 页、426 页、406页、399页、420页。等图说,说明广西壮族民众在清代遵纪守法、勤劳且有良好的文化传统,也较为广泛地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对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服装进行绘制,生动、活态是艺术化表现的首要原则。《皇清职贡图》虽以自上而下的视角进行资料的收集与绘制,但其眼光关注到民间,尽量完整、真实地记录少数民族的人文风情,其中不乏对劳动大众的赞美。古籍中有一段对贺县壮人充满爱意与生活气息的描写,介绍当地女性“喜能织壮锦及巾帕,其男子所携必家自织者”⑦〔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6 页、420 页、399 页、426 页、406页、399页、420页。,不仅表现当地女性勤劳手巧,更是展现夫妻间的和谐相处——织物联系了男女之间的情感。图册展现每一族群一男一女两个形象,男女之间的互动成为图画生动表现的重点。在图册中,男性或专注望向女性、或深情与女性对视,如贵县俍人女性正插戴发饰,男性望向女性,配文“歌声互答以相欢悦”⑧〔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6 页、420 页、399 页、426 页、406页、399页、420页。,生动活泼地将和谐、甜蜜的男女关系绘制而出。除此之外,图册还记载了各地的壮族人日常生活,有的手拿竹篮、有的戴竹笠而行、有的戴笠挑筐、有的戴笠且着履时携巾扇……说明已注意到对少数民族服饰所适用生活场景的描绘。
(二)以人为本、和谐自然:壮族服饰与《闲情偶寄》中服饰美学的契合
借助《闲情偶寄》所传达的生活美学思想,可以较为全面地体察清代壮族服饰的美学特征。《闲情偶寄》于康熙十年(1671 年)刊刻,《皇清职贡图》彩绘本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正式绘制完成,二者创作年代相近,流露的服饰美学也高度契合,皆着重关注社会大众的世俗生活,展现了清代的服饰美学思想。
《闲情偶寄》“声容部”中“治服第三”集中表达了李渔对服饰的审美情趣,也较为整体地呈现了清代民众的审美心理、服饰的流行风尚与搭配技巧等,是清代服饰美学的代表作。书中主张“衣以章身”,认为衣服主要表现了人的精神意义、文化蕴含、道德风貌与身份做派等①李渔:《闲情偶寄》,杜书赢译注,中华书局,2021,第300页、316页、316页、310页、311页、306页。,更为注重服饰背后的人文因素。《皇清职贡图》没有将少数民族服饰以呆板的形式展示,而是注重其背后的综合系统,同样是“衣以章身”主张的艺术化表现。另外,《闲情偶寄》中以人为本、和谐自然的服饰美学思想与壮族服饰的美学特点高度契合。
清代衣服的流行趋向为“大家富贵,衣色皆尚青”②李渔:《闲情偶寄》,杜书赢译注,中华书局,2021,第300页、316页、316页、310页、311页、306页。,这种崇尚青色的流行趋势是胜过古昔且可以作为审美法则的。李渔充分肯定了青色的妙处及作用:青色“宜于貌”,适合各种肤色;“宜于岁”,长幼皆可穿;“宜于分”,不同等级穿着可以彰显不同风格;“宜于体而适于用”,可以容纳污渍。③李渔:《闲情偶寄》,杜书赢译注,中华书局,2021,第300页、316页、316页、310页、311页、306页。除此之外,青色衣物在贫寒之家与富贵之家都是衣服搭配、衬托颜色的最佳选择。《皇清职贡图》中对广西壮族服饰亦重点描绘了“青”,如“男蓝布裹头”④〔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9 页、420 页、396 页、416 页、420 页、426页。“青衣绣绿”⑤〔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9 页、420 页、396 页、416 页、420 页、426页。“女青衣”⑥〔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9 页、420 页、396 页、416 页、420 页、426页。等记载都彰显了清代壮族对青色、蓝色的偏好。青色易于在自然界中提取,是最富大众性和平民化的颜色,正是青色给人的这种心理感受,可以转换成服装美学上青色衣服的审美效应——不论身份贵贱,身着青色衣物褪去繁华,尤显素雅之风。如同《大学》所提及的“富润屋,德润身”,李渔认为人的文化内涵可以跃出衣服鞋子之外,彰显人的气质,服饰的作用主要在“饰”,更加突出人的主体性。同样,清代广西壮族民众根据劳作方式的不同制作了适合自身地理环境、劳动模式的服装,并采用大自然的元素装饰自己的身体,相宜相适。
寄情自然,和谐共处,除簪环,李渔认为鲜花也可装饰鬓发,强调要“渐近自然”⑦李渔:《闲情偶寄》,杜书赢译注,中华书局,2021,第300页、316页、316页、310页、311页、306页。“结实自然”⑧李渔:《闲情偶寄》,杜书赢译注,中华书局,2021,第300页、316页、316页、310页、311页、306页。。李渔用“雅”“生”,即高雅、鲜活来形容鲜花,女性用鲜花装饰可以“随心插戴,自然合宜”,达到“两相欢”的效果。⑨李渔:《闲情偶寄》,杜书赢译注,中华书局,2021,第300页、316页、316页、310页、311页、306页。如同“妇椎髻银簪,悬以花胜”⑩〔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9 页、420 页、396 页、416 页、420 页、426 页。“妇……以茜草染齿”⑪〔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9 页、420 页、396 页、416 页、420 页、426 页。“喜簪花亦喜以茜草染齿”⑫〔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9 页、420 页、396 页、416 页、420 页、426 页。“常刺额为花、草、蛾、蝶状”⑬〔清〕傅恒等:《皇清职贡图》,辽沈书社,1991,第396 页、399 页、420 页、396 页、416 页、420 页、426 页。等描述,都展现了历史上生活在广西的壮族女性热爱花草、蝶蛾等动植物,并取材于自然、设计于服饰中。由此可见,壮族民众对自然的艺术化利用、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李渔“渐近自然”之追求的完美展现。
除此之外,对于裙子制作的精细程度,李渔认为看“折纹之多寡”①李渔:《闲情偶寄》,杜书赢译注,中华书局,2021,第232页。即可,折纹多则行走随意、飘逸多姿,折纹少则活动限制、呆滞难移。在《皇清职贡图》中可以发现,壮族女性裙装折纹多,绘制出的服装自然飘逸。或因中华民族共同的审美取向,抑或因同时代的审美风尚,壮族服饰与《闲情偶寄》中的服饰美学高度契合。
二、当代壮族服饰展示方式的多样化发展与服饰美学的转向
各艺术门类的作品愈加重视民族艺术元素的展示与创作,给予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多方面接触民族艺术的机会。根据观者欣赏的空间,可以将当代壮族服饰的展示方式分为实地观赏与线上观赏两类,其中实地观赏的展示方式包括民族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场馆的游览,线上观赏包括对影视、美术作品、文创产品等媒介的艺术欣赏。通过参观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博物馆、观赏反映壮族题材的艺术作品、购买关于壮族服饰的文创产品等方式,观者在感受壮族服饰多样化的同时,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少数民族服饰美学的转向。
(一)互动体验、渗入日常:当代壮族服饰的多样展示方式
从民族博物馆中的展品,到影院、美术馆中的艺术作品,再到文旅产业中的文创产品,当代壮族服饰在继承如《皇清职贡图》等传统展示方式展示原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互动体验,利用多种媒介宣传、展现壮族文化及服饰,力求让观者融入壮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民族博物馆利用各种展示方式,营造适合交流的氛围,尽量展示壮族服饰全貌,不断增强体验感,力求打破观者与壮族服饰之间的界限。首先,基于空间要素营造少数民族文化氛围和情境。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建筑设计突出壮族文化、花山岩画文化特色,主体建筑外形为大型铜鼓,左右配以小型铜鼓,场馆内外采用褐色的统一色调,将各具特色的文化符号设计在主体建筑、正门、天窗、走廊等明显的位置,用整体空间的主要符号与色彩给人以视觉冲击,易于使观者进入完整的壮族文化空间。其次,利用图像叙事展示民族服饰搜集过程、服饰的适用场景、少数民族的世俗生活与精神世界等非正式信息的内容。民族服饰的搜集过程极具人类学学科色彩,研究人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搜集展品的同时与当地人对话交流、共同生活,了解展品背后的文化语境、所蕴含的民俗事项以及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系,这个过程成为博物馆进行展示的关注点。此外,少数民族民众作为表演和行为主体在民族博物馆中得到诸多体现。广西民族博物馆采用场景复原的方式,较为直观地还原少数民族民众穿着民族服饰的日常生活场景。空间叙事、图像叙事与身体叙事三种叙事手段有机结合,营造了讲好民族故事的氛围,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壮族服饰、民族生活全貌,增强观者的体验感。
反映壮族文化题材的影视作品成为当代对外大范围展示壮族服饰的重要媒介。其一,影视作品直接展示壮族服饰,强调服饰作为民族的重要标识。如电影《布洛佗河》围绕设计师从壮族服饰中取得灵感进行服装设计这一事件展开叙事,电影中的演员皆穿着简化版的壮族服饰,其中,黑色、蓝色是壮族服饰最常见的颜色,斜襟或对襟绣花是最有特色的衣服款式,同时,数套主人公设计的时装也有意识地传达少数民族服饰是如今时装设计的重要元素。其二,展示壮族服饰相关民俗活动、穿着场景等内容,以整体文化氛围烘托活态的服饰文化。如《布洛佗河》中“矮马节”的盛大场面、《又是一年三月三》中“三月三”的节日习俗、《刘三姐》中的山歌对唱……诸多壮族题材影片利用具有代表性的壮族文化符号打造自身亮点吸引观众。如影片《夜莺》通过对桂林、三江、阳朔等地自然生态之美的细致描写,让观众更加直观感受广西景色与民族风情的魅力。一系列电影或直接描绘壮族服饰、或侧面展现壮族服饰民俗活动与民众所生活的自然环境等,通过大众媒介将民族服饰文化渗入观者的日常生活。
与《皇清职贡图》的绘制目的、绘画方式、绘制原则不尽相同,当代对壮族服饰的绘制更加注重艺术化表现、个人风格的表达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的展现。以水墨画人物画对“黑衣壮”服饰的描绘为例。“黑衣壮”是广西壮族的一个支系,集中在广西与云南毗邻的那坡县,以黑色为美,穿着蓝靛染制的黑色衣服。“黑衣壮”的审美观念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艺术特征高度契合,艺术家在具有简洁、朴素、古拙美感的“黑衣壮”服饰中汲取灵感,运用在绘画的题材、构图、色彩中,探索与传播少数民族审美意识。黎小强的《黑衣壮印象》、王巍的《黑衣壮少女》、谈龙的《黑衣壮族少女》、赵晨的《黑衣壮》等作品,都是将传统水墨画的意境美与“黑衣壮”的人物、服饰、精神相结合创作而成的,彰显了民众的朴实无华、服饰的古拙之美和民间艺术强劲的生命力,成为广西地域美术创作的重要特征。
(二)大众化与雅化:当代壮族服饰美学的趋向
注重互动体验、渗入观者日常生活的展示方式日益多样,这些方式所展现的不仅是传统的壮族服饰,还有或再度创作、或经过艺术化加工的服饰,服饰展示方式的变化体现了壮族服饰愈加重视少数民族审美意识和观者体验的创作重点,也体现了其大众化、雅化的美学转向。
从众多展示方式中可以看到,如今机械复制、艺术化加工的新式壮族服饰体现了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困境。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的再度创作与艺术化展现了对少数民族审美意识的重视。美术、影视等艺术创作更加注重选择少数民族元素、借鉴少数民族审美意识,体现了欣赏文化差异、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戏剧、影视等一些面向大众的艺术化加工曲解了壮族服饰的核心美学思想。如鲜艳的大红色服饰、偌大的牛角状帽子等夸张元素,改变了传统壮族服饰的面貌,过度迎合外界对壮族服饰的刻板印象。
当代壮族服饰展示方式的变化体现了壮族服饰大众化、雅化的美学转向。壮族服饰已借助诸多媒介从专属于壮族民众的自我欣赏物品逐渐走向世界。传统壮族服饰的主要欣赏者便是其创作者,壮族女性依凭民族特色、周围环境、舒适程度、自身喜好等因素,形成一套个性化的美学法则,由自己设计创作、自己穿着展示,在欣赏自身的同时不断改进服饰。由此,服饰成为她们性格与品德的展现,亦是她们之间评价“心灵手巧”之美的标准。随着对外展现方式的增多,壮族服饰逐渐成为壮族聚居区外大众欣赏的艺术品。这种来自多角度的“凝视”使得壮族服饰的创作与展示更加迎合观者、注重观者的审美体验。壮族服饰的审美大众化一方面让壮族服饰的接受空间得到扩大,但另一方面,大众化仅关注最具代表性的服饰类型,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壮族服饰的地域性差异。
美术、戏剧等艺术化创作难免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雅化”。在如今的审美风尚的影响下,“人们对‘精致’的程度要求更高,‘雅化’后的民间艺术更容易在现代文化市场上受到青睐,获得较为充分的文化共享性”①张娜:《论民间艺术“雅化”转向及其文化逻辑》,《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可见,“雅化”是一种较为被动的选择。然而,除去“雅化”的影响,原汁原味的壮族服饰是否仍符合当代审美取向,以广西民族博物馆馆藏的龙胜壮族妇女清代服饰为切入点思考这一问题便会发现,传统的壮族服饰深蓝、浅黄、浅绿、淡褐的主体配色达到视觉的淡雅、端庄效果,宽松的对襟衣与百褶裳在满足劳作舒适的同时追求美观,对称、平铺等图案排列与细小白线刺绣展现平衡、精致的设计原则,历经百年仍具有当代美学价值。因此,传统壮族服饰本身具有的“雅”元素等待被关注、挖掘,假若一味追求商业价值、迎合大众审美,反而会在不断“雅化”的过程中丧失自身的美学意蕴。
三、壮族服饰展示方式变迁对服饰审美方式的影响
民间艺术是强调文化持有者的审美观念、文化背景、表达方式的艺术类型,其美学特征展现民众的个性与文化区域内部共同的审美理想。囿于条件限制,历史上的艺术创作者只能借助文字或图像展现少数民族服饰。随着外界对民间艺术的关注与利用增多,民间艺术的展现方式逐渐多样,而艺术品的展现方式对艺术品的审美欣赏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民族服饰美学随社会变迁而发展与变化,决定了服饰展现方式应随势而变;另一方面,展现方式的变化体现不同时代民众进行民族艺术欣赏的特征,拓展了民众的审美方式,使得观者可以相对透彻地掌握服饰美学。
据上分析可知,从单一到多元,壮族服饰的展示方式不断增多,体现了时代发展中民族艺术欣赏途径的多元化。从文字记载到单一的绘画记录,再到博物馆、新媒体等多种展现方式的出现,壮族服饰的展示目的、原则、价值、受众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其一,展示目的从以政治需要为主到以审美需求为主。“图像被不同的人、因不同的原因、以不同的方式创造和使用,而这些对于图像所承载的意义至关重要。”①〔英〕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章浩、沈杨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第68页。正如清政府与如今画家对壮族服饰的描绘,前者因政治原因,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绘制,而后者出于艺术创作动因,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创作,其展示目的自然出现差异。其二,展示目的的差异导致展示重点的不同。当代艺术创作中借鉴民族服饰之“美”,如服装设计中引入的少数民族服饰图案、戏剧舞台上标准化的舞美等,弱化了少数民族服饰“真”或“俗”的方面,展示方式从注重展现真实生活原貌转变为更加关注艺术效果。其三,展示方式更加注重观者的参与与融入。“互动式当代文化展示的一个主要特点”②〔英〕贝拉·迪克斯:《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冯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0页。与《皇清职贡图》使民众被动接受信息不同,博物馆、大众传媒等方式注重观者主动进行信息互动,打造“沉浸式”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氛围。不同时代壮族服饰展示方式的差异决定了民众进行民族艺术欣赏途径的不同,如今,民众进行民族艺术欣赏的途径特点体现为多媒介、多角度的欣赏。
与此同时,审美方式因展现形式的多样化而变化,融入性审美、多感官联动审美等,拓宽观者进行艺术欣赏的方式。首先,服饰不能仅仅摆放在博物馆进行远距离观赏,而应依靠远观、触摸、身着等方式进行体验与欣赏。因此,博物馆多以“多感官联动审美”来帮助观者理解民族服饰的审美经验,如设置模拟或真实穿着民族服饰、参与民俗仪式与服饰制作活动、品尝当地美食等模块,强调审美活动中嗅觉、触觉、味觉以及整个身心的融入。①季中扬:《民间艺术的审美经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95页。其次,民间艺术的审美体验混同在其他生活体验之中,观者需要借助多种展现方式了解民族服饰所混同在其他生活体验中的美。因此,博物馆多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为观者提供虚拟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生活体验、采用场景复原的方式较为直观地还原少数民族民众生活场景等手段,让观者主动构建自己的体验,达到融入性审美、多感官联动审美的效果。
虽然服饰的展示方式一直在不断变化,但其主要目的为全面呈现服饰的文化信息。“道”“器”关系是中国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艺”对应的是“道”,“术”对应的是“器”,印证了《周易·系辞上传》所说的“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②李倍雷:《中国艺术史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艺术百家》2014年第1期。并且,“道”“器”永不分家,“器”是达到“道”的方式与途径——以“器”入“道”。③李倍雷、赫云:《中国当代艺术:图像、观念、风格》,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第22页。这种以“器”入“道”的艺术欣赏方式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追求,亦是如今进行民间艺术欣赏的重要方式。同时,“道”代表抽象的高层次文化,包括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而“器”代表具体的文化,包括器物文化、技术文化,那么,展现形式、欣赏方式等条件的改变让观者更易以“器”入“道”,尽量全面地获取服饰美学,感悟他者文化的魅力。
结语
艺术品无法脱离展示方式而独立存在,少数民族服饰的呈现方式随着社会变迁逐渐增多,受众从远距离的接受到零距离的体验,这种变化能让观者更加准确、全面地捕捉到不同民族的服饰美学,同时,展示方式的变化亦让观者的审美方式产生变化。壮族服饰凝结了壮族民众的审美能力、审美创作力,其展示方式的艺术表达效果随时代变迁而增强。清代《皇清职贡图》对壮族服饰的绘制遵循地域性、综合性、政治性、活态性的原则,展现了以人为本、和谐自然的壮族服饰美学;当代则通过博物馆、影视剧、美术作品等注重互动体验、渗入日常的多元展示方式,展现了壮族服饰的大众化与雅化趋向。从单一到多元,壮族服饰展示方式的变迁展现了不同时代进行民族艺术欣赏的途径,拓宽了观者的审美方式,使得观者多方位获取服饰美学,感悟他者文化的魅力。综上所述,壮族服饰与其展示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道”“器”关系,展示方式全面、整体地展现了不同民族服饰的美学特征,展示方式的变化也在不断改变观者的审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