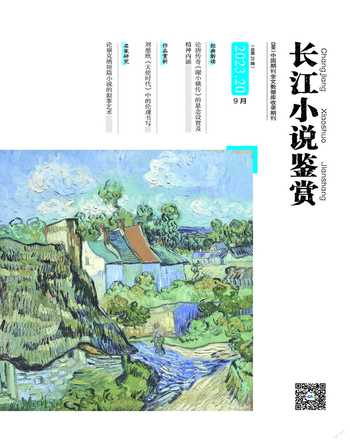庄子生态观下迟子建小说的精神向度
黎淑怡
[摘 要] 作为东北作家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代表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回忆视角展现鄂温克族人百年历史变迁的民族史诗。本文以庄子生态观为观察视域,发现小说致力于对原生态边地风情的描摹、对群体文化的探寻与关怀,体现出作者敬畏万物的自然观、死生一体的生命诗学、和谐共生的文明想象等精神指向。
[关键词] 庄子哲学 迟子建 《额尔古纳河右岸》 精神向度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20-0040-04
庄子是战国中期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也是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战争频仍的动荡现实使其对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等主体关系进行了本质性的敏锐思考。庄子将自然、社会两方的生态困境上升至“道”的宇宙观层面,构建起一派极具人文关怀、致力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体系。在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群体中,迟子建是较为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女性作家对都市生活图景的聚焦,她始终致力于在对自然的温情观察与理性思考中谱写东北乡土的文学世界。作为自然孕育出的文学精灵,在迟子建的眼中,“大自然是这世界真正不朽的东西”[1]。她也曾直言:“我想没有童年时被大自然紧紧相拥的那种具有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经历,我在读大兴安岭师专中文系时就不会热爱上写作。”“我恰恰是由于对大自然的无比钟情而生发了无数人生的感慨和遐想,靠着它们支撑我的艺术世界。”[1]可以说,“自然”是迟子建文学创作的启蒙者与常伴者。作为一部“面对着山峦完成”[2]的长篇小说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无疑是迟子建饱含自然体验与社会思考的创作实践,从庄子生态观思想出发,读者或可打开一扇观察迟子建创作精神向度的窗口,能深层次地挖掘小说文本中对自然本质、社会文明的双重思考。
一、“天人合一”:敬畏万物的自然观
“就‘自然之天而言,‘天人合一即是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3]西方哲学常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天”与“人”的关系,并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强调“人”可以改造、征服“天”。庄子则以“道”观世,就本体论层次探寻天、人、物三者的关系,建构起“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的生态整体观,强调天人关系、物我关系在精神层面的合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合则成体,散则成始”(《庄子·外篇·达生》),天地间充斥的阴阳二气不断分合,形成了世界的生生不息。所谓“通天下一气耳”(《庄子·外篇·知北游》),作为“气”的产物,人与自然万物都由天地生发而出,以天地为最终归宿。天地是无形之父母,父母即有形之天地,人类与自然内在的生命关联便在其同一性中得以彰显。与庄子“天人合一”的共生体意识契合,自然在迟子建心中与人一样,是有呼吸的、有生命的。正是以这种温情观照为立场,迟子建笔下的自然既是人类诗意栖居的自然,亦是具备灵性品格的自然。
从整体处着眼,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关于鄂温克族祖辈至孙辈近百年苍凉变迁的叙述中,作者以“清晨”“正午”“黄昏”“半个月亮”作为文本上、中、下部及尾声四部分的标题名,巧妙地将自然物象的变换规律与群体历史的演变过程联结起来,体现出两者的内生关系。在民族史诗的谱写中,作者有意以口述史、民族志的第一人称叙述方式进行文本的构建,九十岁鄂温克族老妇人“我”作为故事的叙述者,既是部落历史的亲历者,又是人类与自然文明共处的见证者。当“我”以一句“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2]开篇,文本世界的自然基调由此奠定,自然物不是冷冰冰的客观物质存在,而是与人精神共通的伙伴,迟子建为读者展现的便是这样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
“自然崇拜是鄂温克族萨满教信仰世界中产生的时间最早、包括的对象最广、延续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信仰领域。”[4]鄂温克族人以牧养驯鹿、狩猎为生,对自然的依赖度极高,以对万物的原始崇拜与敬畏为信仰核心的萨满文化传统又进一步深化了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呈现出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生态特征。“火”在鄂温克族人眼中是光明和温暖的象征,代表着跳动的心脏。从“我”记事起,营地的火便一直燃烧着,从未熄灭过。鄂温克族人在营地上燃起篝火,喝酒吃肉,绕着篝火手拉手跳“翰日切”舞欢庆喜事,“篝火”是他们的聚集点,护佑火种延续的“火神”赢得了他们无上的敬畏。“火中有神,所以我们不能往里面吐痰、洒水,不能朝里扔那些不干净的东西”[2],在黄尘雪引发的大规模瘟疫中,林克保存下的三十几头驯鹿也被叫作“火种”,每当因事迁徙之际,驮载玛鲁神的白色玛鲁王身后最先跟着的都是驮运火种的驯鹿。“我”新婚时,母亲达玛拉赠予“我”的新婚礼物是那吉勒耶业在她与父亲结合时送她的火种,尽管经历了多次迁徙,母亲从未让火种熄灭,而后火种又被“我”传给女儿达吉亚娜。不难看出,“放到埋着厚灰的桦皮桶里”[2]的火种始终寄寓着鄂温克族人对生活的美好期许。在“火种”的代际相传下,鄂温克族人实现了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此外,鄂温克族人还有许多有关狩猎的风俗。例如出猎前,大人们常常要在玛鲁神神像前磕头祈求平安与丰收。行猎时,若发现刻有山神“白那查”神像的树,经过时不能大吵大嚷,需“给他敬奉烟和酒”[2],并“摘枪卸弹,跪下磕头,企求山神保佑”[2]。如果成功猎到野兽,还要“涂一些野兽身上的血和油在这神像上”[2]。若是猎到熊或堪达罕时,则要在尼都萨满的希楞柱前做三角棚,进行玛鲁神祭奠仪式,食用熊肉之前,需要仿照乌鸦“呀呀呀”地叫上一阵,佯装是乌鸦而非人吃它的肉。鄂温克族人始终敬畏自然生命,并将这种敬畏贯彻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母亲达玛拉将死去的驯鹿崽当作孩子般装进白布口袋里,扔往向阳的山坡;达西给猎鹰取名“奥木列”,鹰在其绝食时为他叼来山鸡,并助他成功复仇;金得殉情时因不想连累一棵生机勃勃的树与他一同葬身火海,选择在一棵枯树上上吊;伊万在山中放过的一对白狐狸为回报他,化作他的一双干女儿为其吊孝。在這些温情对望中,作者为读者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化图景。
二、“方生方死”:死亡之常中的生命观
如叔本华所言:“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哲学了。”[5]庄子从“道”的永恒运动中思索生死,在对“生死同状”本源探寻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越之法。战国时期因社会动荡,生命如草芥般轻贱,庄子认为“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庄子·内篇·大宗师》),人应当明了自然宇宙中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以本真的状态,既不刻意折损,亦不刻意优养地对待生命。庄子认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内篇·大宗师》),他将人的生死置于“道”中思考,生与死的转换正如天地旦夜的变化,生从无中来,死又归于无,这是个体产生于自然又归于自然的过程,亦是无法抗拒的命运规律。因此,在生命时限内好好生活,顺应自然之“道”,面对自然大化的“死”也应泰然处之,通达安息,既“重生”,又“乐死”,“破除对生的执迷,对死的忧惧,才能安于自然的变化,无送终之悲”[6],在对命运的安之若素中达至心灵自由之境。
戴锦华曾评价迟子建对于死亡的书写:“在迟子建的世界里,生与死与其说是相互对立的两极,不如说是彼此渗透的生命之维自身。”[7]迟子建对于生死有深刻的认识,其看待死亡的惯常化视角超脱了常人对死亡之恐惧,所以常以博大、悲悯的关怀视角进行死亡书写。《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她运用大量笔墨描绘了人物的死亡情境。就话语描述而言,人物出于各种原因的死都与自然联结起来,死亡被赋予一种本体回归的意义。父亲林克在茂密的松林中被雷电击中,“弯曲着身子,趴在一个断裂的树桩上,垂着头和胳膊,好像走累了,在休息”[2],即便是雷击导致的意外死亡,也如同休憩一般静谧而安详。作者常以“带走”二字来形容死亡,如父亲“被雷电带走了”,哈谢“让一个大蘑菇给带走的”[2],在承认生命脆弱、被动的同时,又隐含着“死即回归自然”的生命诗学。
值得注意的是,死亡在文本中并不意味着终结,而是生命状态的转化,死亡的人重新进入“生”的序列,“生”与“死”在一来一回中呈现出自然的平衡状态,具备超然和谐之美。萨满是鄂温克族人眼中神的使者,击神鼓、跳神舞、唱神歌的“跳神”仪式是萨满与神沟通、发挥神力的重要手段,“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的状态转换便在这种仪式中得以充分展现。“我”四五岁时,姐姐列娜高烧昏睡,尼都萨满为生病的列娜跳神。最终,小驯鹿的死换回了列娜的生,原本活蹦乱跳的小驯鹿一动不动倒在地上,列娜则恍若无事般清醒过来。这种交换方式在妮浩成为萨满后愈加频繁,她每次跳神救人的行为都以牺牲自己孩子的性命为代价。果格力代替何宝林的孩子死去,交库拖坎代替马粪包死去,耶尔尼斯涅代替作为母亲的她死去。
文本内除了有出于主观目的,将有意识的生命状态转移外,还内存一套无意识的循环逻辑。当列娜跟随代替她而死的驯鹿崽去往黑暗的世界时,灰色的母驯鹿枯竭的奶汁再次如泉水般涌流出;老达西与鹰在完成对狼的复仇后去世,长久不孕的玛利亚拥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这是老达西灵魂护佑的结果,因而将未出生孩子的名字也取作“达西”;“我”因为制止拉吉达捕杀水狗幼崽,三年未怀孕的我肚子里孕育出了新生命;老玛鲁王驯鹿死后,本应在一个月后生产的母鹿诞下一只雪白的小鹿崽……死亡在与新生的精神交汇中,达成了哲学意义上的延续与重构。
所谓“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内篇·人间世》),“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庄子·内篇·德充符》)。迟子建没有消解或过度渲染死亡带来的个体情感层面上的悲凉与痛苦,而是以一种冷静的宿命式的笔触正视“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外篇·达生》)的无法趋避性,同时,她又建构出“人离开这个世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了,那个世界比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要幸福”[2]的叙述,通过温情的描写,赋予死亡以超越性和希望。正如妮浩离开母亲风葬之地时所说:“她的骨头有一天会从树上落下来——落到土里的骨头也会發芽的。”[2]当生、死在彼岸世界的文学想象中获得永恒的延续性,浸润上自然神性的光辉,个体便能安然处之。
三、“至德之世”:历史追思中的文明观
世界是包含社会与自然的生态场,“至德之世”既是庄子对人类家园的诗意建构,又是其文明批判的旨归。从“道”的角度观照人类发展历程,当物质文明快速进步的同时,人性与道统却显现出遗落之势。对道德的过度推崇,使仁义脱离世俗品质本身,成为庸碌之人追名逐利的工具。知识技术的产生与推广使人建立起对外在技巧的依赖,不仅消解了人的自然天性,更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在这种现实情境下,庄子建构起“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庄子·外篇·马蹄》)的文明社会想象,在这一生态乌托邦中,社会个体无知无欲,自然生机勃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顺应道则进, 违逆道则退,万物在对“真知”与“道”的本真回归中走向圆满。
乡土无疑是迟子建心灵的乌托邦,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北疆景色、奔流不息的漠河,都是迟子建对自然的温情观照与热爱。然而,文明发展带来进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传统的失落,《额尔古纳河右岸》便是迟子建在现代与传统间徘徊的反思与建构。“我其实想借助那片广袤的山林和游猎在山林中的这支以饲养驯鹿为生的部落,写出人类文明进程中所遇到的尴尬、悲哀和无奈。”[8]生于自然、取自自然、最终归于自然,鄂温克族是以一种极为原生态的面貌进入文本叙述空间的,他们从来不砍伐鲜树,每次迁徙时也极力收整,不落痕迹。与自然相依的鄂温克族人,即便在丛林生活时常被雪灾瘟疫袭扰,常被猛兽外族入侵,他们仍能保持原始的活力。然而,这种民族文化一开始便有其边缘化的特殊性。当现代文明的脚步走入传统部落的生活领域时,与世隔绝的传统生存面临着“变”的抉择。当鄂温克族猎民的孩子拥有了免费上学的机会时,针对是否将达吉亚娜送去上学,“我”与丈夫瓦罗加态度相反。与他将知识当作看到光明世界的唯一入口不同,“我”认为光明出于自然,自然才是最好的、孩子最需要的老师,孩子应学习如何识别自然物象、与自然和谐相处。向物质的知识技术与向精神的自然天性,两者的选择讨论正是鄂温克族原始文明的瓦解、向现代趋融的印证。
现代文明建构了新型的物质居所,又一定程度上加剧着个体与自然的剥离、精神寻归的危机。可以说,鄂温克族人的命运融入了迟子建对城乡文明碰撞的感知,是其对不愿与传统之根割裂,却亦不能拒绝现代文明这一两难处境的认识。作为部落的第一个大学生,都市生活中的人流、房屋、车辆、灰尘等令依莲娜深觉无聊,她因而重新回归到与驯鹿、星星、风声、山峦溪流、花朵飞鸟相伴的山居状态。然而,山中联系的不便、基础设施的缺乏又使她烦乱焦虑。依莲娜在传统与现代间徘徊的矛盾和痛苦正是两种文明碰撞的结果,她出生于原始文明的胞体,又经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因而也脱离了一元立场,拥有了审视两种文明的可能。她既没有像老一辈的“我”一样,发出“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2]般对传统文明的坚守,也没有完全与自然隔绝,自觉加入现代化的洪流。这种抉择的犹豫与精神的焦灼体现在她的作品中,题材的选择总是出于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汲取,而又常常忍不住向代表现代文明的都市进行展示、求取认同,这种割裂是对传统与现代的交互审思,亦是文明发展的阵痛所在。当依莲娜葬身清流,彻底回归自然;当妮浩因扑灭由林业工人乱扔烟头所引起的山火而死去;当“我”发出“只要我活在山里,哪怕是最后的一个人了,也不会觉得孤单的”[2]的慨叹,迟子建最终在对家园理想状态的追忆、原始与现代的思索中发出一种呼喊——文明的脚步无可阻挡,但“上帝让我们寻求的是和谐生存,而不是攫取式的破坏性的生存”[2],在自然被挤压至难以呼吸的当下,读者或许能够在文明历史的重溯中寻找心灵的出路。
参考文献
[1] 方守金,迟子建.自然化育文學精灵——迟子建访谈录[J].文艺评论,2001(3).
[2]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3] 国家教委高教司,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 汪立珍.鄂温克族萨满教信仰与自然崇拜[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6).
[5] 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 陈鼓应,蒋丽梅.中信国学大典:庄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7] 戴锦华.迟子建:极地之女[J].山花,1998(1).
[8] 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J].艺术广角,2006(2).
(特约编辑 刘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