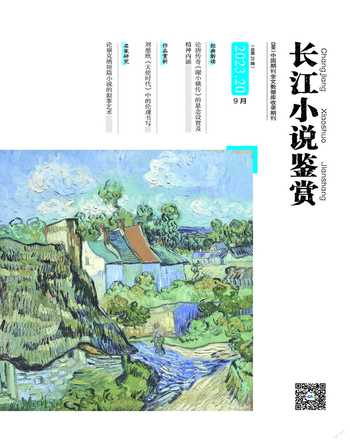混杂性理论视域下《长歌》中七月的文化身份建构研究
宋婷
[摘 要] 安德烈娅·利维是牙买加裔英国当代女性作家,其小说《长歌》呈现了牙买加黑人奴隶尝试冲破種族歧视的屈辱生活,以及他们为追求独立平等的身份认同所做的努力。为深入探讨女主人公七月的身份问题,本文基于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中的四个核心概念:混杂性、矛盾性、模仿、第三空间,分析七月的文化身份建构过程。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混杂性群体提供一种建构文化身份的新范式,对消解文化霸权、促进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融合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 《长歌》 霍米·巴巴 混杂性理论 七月 文化身份建构
[中图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20-0082-06
一、研究背景
安德烈娅·利维,1956年出生于伦敦一个普通的牙买加移民家庭。作为第二代移民,她因种族和肤色受到当地白人的歧视,而这也正是许多黑人移民在英国的真实处境。当利维踏上牙买加的土地、追寻祖先的历史时,她发现英国殖民时期的牙买加奴隶史在主流历史中是沉默的。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她在30多岁时开始了写作生涯,并迅速赢得了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她的作品以种族、身份和历史问题为中心,在推动弱势群体的斗争、填补主流历史的空白、促进流散文学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目前为止,安德烈娅·利维已经出版五部小说,前三部作品《屋里灯火通明》《前途渺茫》《柠檬果》带有较强的自传色彩,背景设置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的英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出生在英国的牙买加裔移民遭遇的种种社会、家庭和心理问题,但并未引起较大反响;第四部小说《小岛》一出版便好评如潮,荣获当年的奥兰治文学奖和惠特布莱德年度最佳小说奖。
《长歌》出版于2010年,是安德烈娅·利维的第五部小说。这部小说于2010年入围了布克奖短名单,还获得了2011年沃尔特·斯科特历史小说奖。这部小说生动地再现了一段人们遗忘许久的牙买加奴隶史,激起了加勒比海沿岸移民后裔心中的惆怅与感伤。《长歌》的故事背景为19世纪30年代,讲述了奴隶制废除前后发生在一个名叫阿米蒂的牙买加甘蔗种植园里的故事。小说的“前言”与“后记”的叙述时间在1898年,以牙买加印刷商托马斯·金斯曼的口吻叙述,向读者交代了故事的来源。
小说正文以回忆录的形式,通过女主人公七月的叙述,讲述了种植园岛上奴隶制的兴衰,展现了一幅19世纪牙买加种植园生活的生动画卷。七月是一个黑白混血儿,母亲基蒂是在田间劳动的黑人奴隶,因被苏格兰白人监工塔姆·杜瓦强奸而生下七月。七月九岁时,被种植园主约翰·豪沃斯的妹妹卡洛琳·莫蒂默强行收为贴身女仆,并被改名为“玛格丽特”。在此后的数年间,她们一起经历了1831年由萨缪尔·夏普领导黑奴发起的圣诞节起义、1833年奴隶制废除等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期间,约翰因不满殖民当局对奴隶起义的残酷镇压而开枪自杀。为保全颜面,卡洛琳将哥哥约翰之死嫁祸给黑人尼姆罗德,他当时是七月的恋人。监工塔姆为给死去的种植园主约翰报仇,在随后的追捕中,击毙了尼姆罗德。为救女儿七月,基蒂杀死了塔姆,并被判处绞刑。后来,七月生下与尼姆罗德的孩子,送给了英国传教士詹姆斯·金斯曼夫妇抚养,他们为孩子取名托马斯,并把他带回英国接受教育,托马斯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印刷商人。约翰死后,卡洛琳继承了阿米蒂种植园,嫁给了新来的英国白人监工罗伯特·古德温,企图在他的帮助下重振种植园经济,但是罗伯特爱上了七月并与其生下了私生女艾米丽。最后,因奴隶制废除后劳动力不足,古德温夫妇无奈将种植园出售,偷偷带着七月的孩子艾米丽离开牙买加返回了英国,而七月则一个人历经劫难,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数年后,七月的儿子托马斯从英国回到牙买加创办出版社,偶然遇到了七月,母子二人相认,从此七月在儿子的家里住了下来,安享晚年。
二、理论基础
起初,“杂交”或“杂化”被用来描述一种特定的生物现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混血儿”的研究仅与生物学相关,后来,这一概念很快被引入政治和文化领域。
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复调理论是巴巴混杂性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作为苏联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成功地将“混杂”概念引入语言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他提出了“混合话语”与“专制话语”之间的自然对立学说,认为语言和话语的“杂交”是一种抗议独裁和权威的有效方式[1]。在语言杂化研究领域,巴赫金认为言语具有二重性,它包括个人的声音和他人的声音,“看似相同的句子可以表达两种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意义”[1]。巴巴正是利用了巴赫金语言的复调理论,运用语言的混杂性分析了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之间的矛盾,以及被殖民文化如何通过语言杂化对抗殖民文化并构建第三空间。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作为20世纪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启迪了巴巴。解构主义的出现是为了反对符号中心主义和二元体系,其中“différance”在法语和英语中都不存在,是德里达创造的新词。传统上,写作代表“在场”,而说话作为附加元素,意味着“不在场”。德里达的différance是对存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打破了符号中心主义的神话,解构了存在与不在场的二元对立。巴巴正是受到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启发,将解构主义和différance理论置于政治世界和后殖民语境当中,颠覆了殖民者的权威,赋予被殖民者话语权和抵抗权[2]。
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对巴巴的影响也很大。法农的著名作品《黑皮肤,白面具》主要描述了戴着白色面具的黑人在面对白人和白人文化时表现出的痛苦和矛盾的心理状态[3]。人们通常认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但法农认为,他们处于一种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共生状态。虽然被殖民者害怕殖民者的权威,但殖民者在进行殖民活动时也存在矛盾心理。受法农影响,巴巴颠覆了传统上对殖民主义的两分法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
除了混杂性概念之外,巴巴对于文化身份认同也有其独到之处。巴巴认为,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认同具有流动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第一个完整而具体地讨论文化认同的人是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在《文化认同问题》一书中,霍尔认为身份认同“受到激进的历史化的影响,并不断地处于变化和转化的过程之中”[4]。受霍尔的影响,巴巴在他的文化身份认同研究中引入了混杂性的概念。巴巴的混杂性理论主要关注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的身份认同困境,强调文化的流变性。
受上述理论家的影响,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提出了混杂性理论。巴巴的混杂性理论中有几个重要的概念,包括混杂性、矛盾性、模仿和第三空间。前两个概念可以看作是文化身份混杂的表现。“混杂性是通过重复歧视性身份,来对殖民身份假设的重新评估”[5]。当不同的文化接触时,两种文化相互碰撞,从而产生了混杂的文化。“混杂”的概念被认为是对殖民话语的颠覆或混淆,它“打破了自我与他者之间权力结构中简单化的二元对立”[6]。巴巴认为,“这种差异结构在后殖民语境中产生了种族和性别的混杂”[5]。在面對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时,巴巴提出矛盾心理的重要性,这种矛盾心理表现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不确定关系。他强调“被殖民的人有可能利用符号的不确定性来抗议殖民者并解构殖民话语”[5]。他认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双方都存在着一种矛盾的文化状态,具体表现在被殖民者害怕殖民当局,而殖民者也困扰于殖民活动时的矛盾情感。
后两个概念可以看作是重建文化身份的两种策略。在巴巴看来,“模仿代表了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妥协”“几乎相同,但又不完全相同”[5]。模仿与矛盾心理是分不开的,模仿过程总是伴随着矛盾状态。一方面,模仿作为一种文化同化策略,是殖民者控制和同化被殖民者的一种方式,使被殖民者认同殖民者的文化和价值观,从而疏离自己的本土文化。另一方面,被殖民者作为有意识的主体,除了被迫接受殖民者的观念外,还有自己的文化策略——殖民模仿,即被殖民者往往以反抗的方式介入殖民权力空间,从而颠覆殖民者的文化同化意图,这也是瓦解殖民权威、反抗殖民强权的一种方式。
第三空间是一个混合的空间,是一个超越二元对立的间隙空间。第三空间可以看作是一个文化交流和协商的空间,在这里所有的意义都被重新整合并形成新的意义。在巴巴看来,“通过探索这个第三空间,我们可以避开两极政治,并作为我们自己的他者出现”[5]。
三、七月文化身份混杂性的表现
本文以霍米·巴巴的混杂性理论为基础,从两个方面分析了七月文化身份混杂性的表现。一方面,从个人的角度来研究混杂性,即七月自我身份的混杂;另一方面,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角度来看,七月文化身份的混杂性表现为矛盾状态,这主要体现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不确定的关系之中。
1. 七月自我身份的混杂性
《长歌》中,七月的自我身份充分体现了混杂性的特征。从生物学意义上而言,她是一个黑白混血儿;从文化意义上来讲,七月的文化身份也是混杂的,她既认同白人文化,也认同黑人文化。
从生物学身份来看,七月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其母基蒂是牙买加种植园里一个勤劳的黑奴,其父塔姆是来自苏格兰的野蛮白人监工,七月是基蒂被塔姆强奸所生下的黑白混血儿。因此,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七月本身就带有混杂性的特征。虽然她有部分白人血统,但她的肤色仍是黑色的,作为一个女仆,她经常用羡慕的目光看待比她肤色更浅、外表更迷人的家仆克拉拉小姐。
从文化身份来看,七月在黑人和白人文化之间摇摆不定,因为她既吸收了英国白人文化,又吸收了牙买加黑人文化,并形成了对这两种文化的混合态度,这反映了其文化杂交性。七月对白人文化一直保持着既顺从又反叛的混合态度,自从九岁时被迫与白人一起生活,成为卡洛琳·莫蒂默夫人的贴身女仆,七月逐渐养成了狡猾而精明的性格。一方面,七月看起来很顺从她的主人,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努力满足卡洛琳的各种需要;另一方面,七月对卡洛琳和白人文化充满了反叛、憎恶之感。例如,在那个奴隶起义的圣诞之夜,卡洛琳的哥哥约翰为了镇压奴隶起义不得不离开,卡洛琳恐惧地说:“我被遗忘了,只剩下黑人。”[7]七月假意给予卡洛琳安慰,陪伴着她,让她不要感到恐慌,实际上,七月却对黑人奴隶争取合法权利和自由的斗争感到激动和振奋。卡洛琳逃走后,七月开始快乐地庆祝暂时的自由,甚至在她的白人主人约翰的卧室里与获得自由的黑奴尼姆罗德发生了性关系,这反映了七月对白人文化的反叛态度。
2. 七月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矛盾性
七月的混杂性文化身份也表现在与他人的矛盾和不确定的关系上。从巴巴的观点来看,“殖民者‘自我与被殖民者‘他者的对立维持在虚假的二元关系中”[5],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界限模糊的身份转换。七月与罗伯特·古德温和七月与卡洛琳·莫蒂默的关系之中都体现了这一点。
在七月与罗伯特的关系中,七月既有后殖民文化意义上的自我身份,又有他者身份。新来的白人监工罗伯特·古德温被七月所吸引并爱上了她。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声誉,罗伯特表面上与卡洛琳结婚,实际上与七月发展了婚外情,甚至让七月生下了私生女。在这段关系中,七月和罗伯特是恋人关系,七月天真地认为她可以被视作一个与白人罗伯特平等的人。“丈夫是七月对罗伯特·古德温的最喜爱的称呼”[7],因为罗伯特告诉七月,她是他真正的妻子。然而,罗伯特最终还是抛弃和背叛了七月。罗伯特实际上又回到了殖民者的地位而七月仍然处于被殖民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七月成了被边缘化的他者,她认识到罗伯特与自己的关系仍然只是主仆关系。
七月在与卡洛琳的关系中也是自我身份与他者身份兼而有之。七月和卡洛琳是毫无疑问的主仆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七月处于他者的状态,她不得不服从夫人的命令。然而,这种权力结构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因为掌权者和被权力统治的人之间的关系是含混不清的[8]。七月和卡洛琳也是情敌的关系,因为她们都爱上了罗伯特,七月甚至是更受偏爱的那个。特别是在1833年奴隶制废除后,七月掌握了一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她拒绝了卡洛琳的无理要求,比如陪伴她直到她丈夫回来,等等。
四、七月文化身份之混杂性的成因
从巴巴的文化认同观来看,身份建构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动态过程。本文主要从两方面探讨七月文化身份混杂的成因,一是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即牙买加种植园的殖民历史;二是从文化角度来看,英国白人对牙买加黑人仍有文化霸权。
1. 牙买加种植园的殖民历史
牙买加种植园的殖民历史为七月的混杂性文化身份提供了历史前提和基础。《长歌》的故事背景是19世纪30年代,大约在牙买加废除奴隶制前后。牙买加作为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与英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原为印第安人阿拉瓦克人的居住地,哥伦布于1494年来到牙买加,1509年,这里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在西班牙与英国的战争中,由于西班牙战败,牙买加在1655年被英国占领,成为英属殖民地。
在英国白人眼中,牙买加黑人是“野蛮、肮脏、粗俗的”。在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下,牙买加黑人渴望得到英国的认可,渴望与白人平等。1831年的圣诞之夜,在一位名叫塞缪尔·夏普的浸信会传教士的带领下,奴隶们发誓,如果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就不会回去工作。在这场奴隶起义中,奴隶们愤怒地抢劫并焚烧种植园,熊熊大火燃烧几天几夜。英国殖民当局为了镇压奴隶起义,将包括其领袖塞缪尔·夏普在内的三百多名黑人奴隶残忍杀害。这场运动极大地推动了牙买加奴隶制的废除,正如安德烈娅·利维在《长歌》中所描述的那样,“殖民地奴隶制于1838年7月31日消亡,享年276岁”[7]。这段时期,英国白人殖民者在牙买加与黑人奴隶生下了许多混血儿,七月只是千千万万个黑白混血儿之一。
2. 白人对黑人的文化霸权
白人对黑人的文化霸权也是七月文化身份混杂的主要成因之一。自英国白人殖民牙买加以来,白人文化在牙买加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文化霸权可以体现在肤色、语言、服饰、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更糟糕的是,那些牙买加黑人甚至会想尽一切办法模仿和吸收英国白人文化。长此以往,黑人或主动或被迫地疏离自己的文化。
作为一个黑白混血女孩,七月具有强烈的嫁给白人的意识,非常渴望跨越当前的阶层,就像克拉拉小姐一样。克拉拉小姐作为一个长相貌美的黑白混血儿,她极其自豪自己嫁给了一个富有的英国白人,原因是“只有和一个白人在一起,才能保证孩子的肤色不那么黑”[7]。同样,七月也倾向强调她父亲的白人身份,她不仅向克拉拉小姐炫耀这一事实,而且对她的爱人罗伯特·古德温也一次次重申:“我的爸爸来自苏格兰。”[7]七月时刻提醒罗伯特她的身份是黑白混血儿而不是黑人,她对此感到自豪,仿佛黑白混血儿要比黑人的地位更高。在不知不觉中,七月已经陷入了英国白人强加的文化霸权陷阱,即沉浸在对白人肤色的迷恋之中。
五、七月混杂性文化身份的重构
七月的混杂性文化身份可以通过霍米·巴巴提出的两种策略来重新构建。一是模仿策略,二是第三空间内的协商策略。
1. 七月文化身份重构之模仿策略
模仿是一种文化策略,不仅使被殖民者适应了殖民者的文化,也颠覆了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在这部作品中,模仿主要体现在七月对女主人卡洛琳外在行为的模仿,以及七月对男主人罗伯特内心思想的模仿。
七月试图模仿她的女主人卡洛琳的行为,以缩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距。卡洛琳为了躲避奴隶起义而离开阿米蒂后,七月感到了久违的舒适与安逸,变得异常兴奋,仿佛这座没有太太也没有主人的房子是独属于她一人的。“七月,从一个杯子里啜一口空气,伸出她的小指,就像白人把那神圣的瓷器倒在他们瘦弱的嘴唇上一样。”[7]这是七月对像卡洛琳这样的英国白人女性饮茶风格的拙劣模仿。除此之外,在与尼姆罗德调情时,七月装作卡洛琳平时对待自己的口吻,命令他:“给我拿点茶来,快点。”[7]在这一刻,七月仿佛是尼姆罗德的女主人,她可以命令他做任何事情,甚至可以惩罚他,就像卡洛琳对待七月一般。
七月第一次见到罗伯特就对他很欣赏,并想模仿他的内心思想。他英俊的外表和丰富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引起了七月的注意。在她与罗伯特的谈话中,七月故意表现出对圣经的极大兴趣,这与罗伯特作为虔诚的基督徒的身份相匹配。更重要的是,七月倾向于模仿罗伯特的民主思想,即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处理白人与黑人奴隶之间的冲突,并尽可能地公平对待他们,奴隶制被废除的时候,他努力给予那些在种植园工作的黑人关怀和安慰。正如他向卡洛琳描述的那样:“牙买加黑人坚定地站在人类大家庭中,他们是活生生的灵魂,他们都是上帝的孩子,就如同你和我一样。”[7]在七月看来,尽管这并不是后来成为种植园新主人的罗伯特的真实目的,但这些善良的想法和对黑人文化的尊重是值得她学习和模仿的。
2. 七月文化身份重构之第三空间内的协商策略
第三空间内的协商也是重构七月混杂性文化身份的重要策略。巴巴认为,文化协商发生在第三空间,作为不同文化的混合区,主要有两种协商方式,一是同一文化内的身份协商,二是不同文化之間的文化融合。
七月的身份可以通过在同一文化中建立第三空间来重新定义。这可以从七月与其他黑人奴隶的协商中体现出来,因为他们同属于黑人文化,了解自己的本土文化有助于他们走出文化混杂的困境。例如,在奴隶起义的圣诞之夜,卡洛琳命令黑人管家戈弗雷尽快把她从阿米蒂带走,但戈弗雷冷冷地拒绝了她,他甚至告诉七月不要帮助或陪伴她的女主人。他提醒卡洛琳“你的女仆不叫作玛格丽特,而叫七月”[7],并强迫卡洛琳不断地重复七月的名字。在戈弗雷的帮助下,七月的自我身份得以恢复和重建,她有自己的名字,应该像成千上万被解放的奴隶一样享受法律赋予的自由权利。
此外,在被罗伯特背叛和抛弃之后,七月失去了一切,包括她心爱的女儿艾米丽。在饥寒交迫的绝望处境下,七月在流浪的路上被曾经在牙买加阿米蒂种植园工作过的其他黑人奴隶所救,并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直到她偶然遇到了自己儿子托马斯·金斯曼,一位出色的牙买加出版商人。这段经历让她确信,她的自我身份认同仍然是牙买加黑人。
面对英国白人与牙买加黑人的文化差异,七月与罗伯特在第三空间内进行文化融合。通过频繁的联系和交流,七月和罗伯特相爱了,并生下了他们爱情的结晶艾米丽,这是互相尊重彼此文化的结果。七月对苏格兰文化很感兴趣,罗伯特便送给她一本关于苏格兰岛的书作为礼物,并愿意和她同坐一辆马车回去,不希望她淋着大雨前来送信,这既体现了他对七月所代表的黑人文化的尊重,也体现了他对殖民主义剥削黑奴的厌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实现了文化融合,但两者又出于不同的意图,七月的目的是改变自身现状,实现阶层的跨越,而罗伯特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爱欲。另外,在罗伯特与其他黑奴相处的初期,罗伯特的初衷也是好的。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真心希望改善黑人的待遇和生活状况,并与他们进行文化融合,为阿米蒂种植园的未来发展规划美好蓝图。
六、结语
《长歌》中,七月的文化身份可以根据巴巴的混杂性理论来构建。当英国白人文化和牙买加黑人文化接触时,七月的文化身份就会出现混杂性和矛盾性并存的状态。混杂性可以体现在七月的自我身份上,她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并吸收了黑白混杂的文化;而矛盾性体现在自我与他者身份的变化和不确定的关系上。本文从历史和文化两方面探讨了七月文化身份混杂的主要成因,进而发现其通过两种策略重构了自己的混杂性文化身份,一是模仿策略,包含了七月对卡洛琳外在行为的模仿,以及七月对罗伯特内心思想的模仿;二是同一文化内或不同文化间的第三空间协商策略。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始终处于流动和变化的状态。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与文化认同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研究七月的混杂性文化身份,有助于建构全球化背景下边缘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归属感。对他者的模仿与第三空间内的协商,不仅为黑人提供了发声的场所,还有助于弱化殖民权威、消解文化霸权,对促进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融合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 康孝云.霍米·巴巴对殖民主义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及其意义[J].国外理论动态,2014(10).
[3] 法农.黑皮肤,白面具[M].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4] Stuart H,Du Gay P.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6.
[5] Bhabha H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M]. London:Routledge,1994.
[6] 刘媛媛.霍米·巴巴后殖民混杂性理论评析[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4.
[7] Levy A.The Long Song[M].London:Headline Publishing Group,2010.
[8] Karenjit K.Bhabhas Ambivalence and Hybridity in Andrea Levys The Long Song[J].International E-journal of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2018(11).
(特約编辑 刘梦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