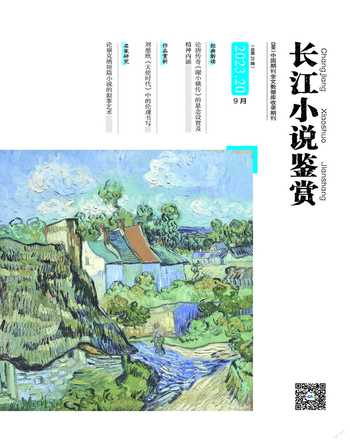天亮之后如何
朱清如
[摘 要] 丁玲小说《夜》以何华明回家和妻子一起入睡,在心烦意乱中度过一夜为结尾,留下了“天亮之后如何”的丰富想象空间。实际上,新的革命形势并没有给主人公的工作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即天亮后一切照旧。本文从小说结尾出发,在20世纪40年代初根据地农村基层建设的大背景下,将文本细读和社会史视野相结合,通过对何华明一夜之中行动轨迹和心理变化的追溯,追问天亮后“照旧”的原因,试图理解丁玲在延安时期独特的创作观念和思想逻辑。
[关键词] 丁玲 《夜》 结尾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2881(2023)20-0011-04
《夜》写于1941年初春,是丁玲离开中国文艺协会后,在延安川口农村体验生活时创作的短篇小说。故事以农民指导员何华明一夜之中的工作生活为主线,生动展现了主人公真实、曲折的心理图景,以及在新旧交替之际延安农村村民的精神面貌。小说自问世以来即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骆宾基曾将其誉为一颗“完整而且有光润”的“玉珠”[1];冯雪峰则认为它“完满地表现了过渡期中的一个意识世界”,因而是丁玲小说中“最成功的一篇”[2]。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结尾处,何华明在夜晚产生了种种或奇异、或嫌厌、或悸动的感觉过后,最终选择回到家中和妻子一起入睡,直至“天渐渐的大亮了”。故事在天亮中进入尾声,看似收束之笔,实则引起了读者的进一步追问——天亮之后,何华明的生活工作会发生什么变化吗?一方面,何华明和妻子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夫妻关系岌岌可危;另一方面,他手头上的工作繁杂,常使他精疲力竭、举步维艰。作为新一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农村崭新的革命形势能否给他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本文以小说结尾为切入点,通过回溯何华明一夜之间的行动轨迹和心理变化,将文本细节与20世纪40年代延安农村基层建设、作家下乡创作等社会背景进行对照,有助于解读丁玲延安时期独特的思想意识和写作逻辑,为“天亮之后如何”找到答案。
一、固定的生活模式
小说《夜》的故事是从傍晚会议结束后,农村指导员何华明意外地被准许回家开始的。小说开头,区委委员向何华明解释了批准其回家的原因:一是他家唯一的牛即将生产,二是他的妻子因年老而无法帮忙。其实,这正是何华明个人生活中的两大烦恼,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固定的生活模式。首先是以“牛-土地”为中心的生产活动。对何华明而言,那只将要产崽的母牛不仅是他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更代表了他心目中理想的生活模式,即传统的、以土地为核心的小农生产方式。回家途中,当何华明看到村民牵牛耕地的辛劳场面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想到自己家的土地,随后是“说不出的一种痛楚”——因为忙于革命工作,家里的土地已经荒废了很久。小说中写何华明不愿意、也从未和他人提起这一秘密心事,因为他害怕被人取笑,从中,读者也可以看出何华明身上根深蒂固的土地意识和小农精神。作为后沟土生土长的庄稼人,何华明始终能够感受到土地对他的深情呼喚,这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的希望和慰藉,也是他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因此,村里的选举工作一结束,他就要迫不及待地投向土地的怀抱,重新加入小农生产者的行列,回到其心目中理想的固定的生活模式。
其次是主人公独特的婚姻家庭形态。何华明的妻子是一个大他十二岁、体弱多病且丧失生育能力的女人,她同何华明之间存在着年龄、身体状况、思想和社会身份等方面的巨大差距。虽然二人的夫妻关系已经破裂且难以缝合,但整个家庭却能够在主客观多重条件的作用下,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中。一是从主观上看,尽管妻子已经年老色衰,但在何华明的回忆中,仍然不能对妻子“搜出一个难看的印象”:他们曾经生养过一双儿女,孩子夭折后,都极其希望能够再生育一个孩子,对未出生的小牛的幻想和憧憬,以及对家中灰猫的依恋,正是他移情的表现。而将离婚称作“坏念头”,并且“又一次”在自我想象和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法”中放弃离婚,更体现出何华明内心深处对传统农村婚姻模式的认可,以及对旧有家庭生活方式的习惯。二是在客观上,何华明最后打消了和妻子离婚的念头,理由是“闹离婚影响不好”。实际上,在《婚姻条例》颁布后,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曾掀起了一阵“离婚潮”。那么,何华明作为一个常常因自己的党员身份而感到骄傲的新一代农村干部,自然非常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可能对个人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他难以掩饰对家中老妻的嫌弃和厌恶,但还是倾向于维护自己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因此他最后仍选择回到家中,在又一次自我宽慰中和妻子一起陷入沉睡。
而在何华明的日常生活之外,还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它们是何华明固定生活模式中的异常因素,对其原有的婚姻家庭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一个是十六岁已“发育得很好”的少女清子。何华明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落到她身上,尤其是那倚在门边赏花的亭亭倩影,给他带来一种“很奇异的感觉”。另一个是早已对他芳心暗许的邻居侯桂英。每当何华明晚上起来喂牲口时,她总会跟着来喂,再轻声细语地说上几句关心的话,极富暗示性的举动骚动着何华明焦躁的心,“恨不得抓过来把她撕开、压碎”。然而,何华明最终没有踏出那一步。他对清子朦胧的欲望和想象仅仅停留在“妇女落后”的一面,拒绝侯桂英的示好也是因为作为干部“要受批评”。在何华明心里,任何诱惑都无法打破他固定的生活模式,即“开始工作-思念土地-回归家庭”。与其说是他的理智战胜了情感,倒不如说这些不安定因素只是他生活中的小插曲,并不能起到动摇和瓦解他既定的生活模式的作用,正如小说结尾写道:“现在他做了乡指导员,他明天还要报告开会意义。”
二、双重的革命阻力
1.来自群众的阻力
《夜》中展现的社会问题是多面的,其中一个问题涉及群众与革命工作之间的复杂关系。小说中,令何华明感到头疼的日常工作之一是“冬学”,即20世纪40年代初的冬季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群众性识字扫盲运动。1940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冬季举办新文字教育运动,并于同年11月在川口创刊出版了以“新文字扫盲”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字报》,同年12月发布了《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当时《新文字报》的编辑李绵曾回忆到,同汉字相比,新文字在扫盲运动中成效更加显著,边区政府由此“决定是年冬在延安县、市举办新文字冬学,再次开展新文字扫盲教育的试验”[3],强调了边区扫盲和新文字教育的重要性。
《夜》中,何华明说清子:“连一个多月的冬学都动员不去。”而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的延安十分常见。据统计,1940年延安县、市共有新文字冬学63处,报名1952人,实到学生1563人,其中女性只有224人,占比仅14%左右[4],可见冬学运动在实际开展的过程中有其困难之处,尤其是在群众的宣传和动员上成效不佳。一是由于冬学形式本身不受群众欢迎,尤其是强制性动员参加的方式,容易引起群众反感,有些群众将冬学视作一种负担;二是一些农民受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质的限制,往往不能理解边区开展革命工作的意义。就像何华明的妻子想要的一直是“安适的生活”,而丈夫的工作是她所不能理解的,“简直是荒唐”。同样,在何华明的眼中,自己的妻子是“落后、拖尾巴”的典型。这就使普通农民群众站在了革命工作的对立面,不仅没有加强群众对革命形势的认识,还加深了革命活动与群众之间的隔阂,这成为当时延安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2.来自干部的阻力
事实上,除了农民群众之外,负责革命工作的干部自身也存在着问题,即在任务的执行和觉悟上和实际革命要求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陕甘宁边区,像何华明一样的许多政府下层工作人员,都属于“从未过问过‘公家事的工农分子”。他们往往由于“文化程度的低浅”和“习惯于直接了当的摊派命令” [5]的僵硬的工作方式,而成为健全民主政治路上的阻碍。小说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何华明等人正在准备的边区选举活动。作为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何华明并没有理解会议上的许多政治术语和政策问题。同时,因为高强度、持续性的选举工作,他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休息过了。小说中,作者多次提到何华明在工作上的烦恼,例如“被很多问题弄得疲乏”“会议上弄得很糊涂”等,可见边区政治运动中的繁杂任务使何华明心力交瘁、难以承受。然而,这种辛苦并没有转化为他对革命的认同以及热情。在何华明看来,自己是“为着这乡下的什么选举”,才让他心爱的土地变得荒芜,而当他一想到明天的会议,就不自觉地陷入焦急和烦躁的状态中,甚至将这种负面情绪迁怒给他人。除此之外,从他对于清子因“不够法定的年龄”迟迟不结婚感到不屑、生硬地使用“物质基础”这一新术语来辱骂不能生育的妻子等场景中,都可以看出何华明这类地方干部在自身能力上的缺失,以及对于正确革命方向认识的偏离。
因此,在小说结尾,从何华明入睡前的所见所感中,作家用夜晚放大了主人公白天的烦恼,直接指出了当时农村革命工作中的双重阻力,一是在群众工作上,有“宣传工作不够”“妇女工作等于零”等方面的问题,反映出农村基层政治文化建设的薄弱。如果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教育不够深入、群众参与民主政治的条件也没有得到保障,那么群众将无法很好地理解革命工作,其积极性不足也会导致政策推行困难,农村将无法发展。二是在干部队伍中,“这里没有做工作的人”。由于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的低下,许多农民出身的新干部不仅没有发挥领导、教育群众的带头作用,还无法适应、配合革命工作的实际需要,甚至在很多旧思想观念的束缚下,自己成了革命路上的绊脚石。所以,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农村革命建设的整体进程中,其内部仍然存在着从下到上、从群众到干部的现实障碍。这是当时难以轻易扭转的传统意识和难以治愈的社会痼疾,也是何华明在“天亮之后”仍旧无法解决的难题。
三、农村革命建设的实际困难
20世纪40年代初,延安正处于基层革命政权建设的火热时期,但各根据地如火如荼的民主建设运动和群众高涨的政治热情,却并没有在《夜》中得到展现。小说仅仅讲述了农民干部何华明生活中的普通一夜,并将叙述重点放在对主人公隐秘心理的挖掘上,而非着力刻画政治环境。作家这样写作的用意何在?实际上,作者以何华明曲折多变的心理活动为中心,不仅从侧面反映出其工作时遇到的阻力,更揭示了在新旧交替时期延安农村革命建设的实际困境。
最典型的例子体现在《夜》的结尾处。何华明在睡前有这样一段意识流般的心理独白:从“牛又要侍候了”到“宣传工作不够、农村落后”,再到“他自己是个什么呢”,最后以“他明天還要报告开会意义”作结。他的内心挣扎看似杂乱无章,实际上分别对应了“牛”“工作”“自我”和“明天”四个因素。其中,将要被伺候生小牛的“牛”属于何华明所熟悉的传统生活模式,但在他的脑海里,这种“旧”的生活念头很快被“新”的革命工作所取代。然而,当时的农村因缺乏知识型干部人才和农民群众的配合支持,所以难以孕育出革命所必要的政治激情和斗争精神。在烦恼中,他开始了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表面上,他反省自己能力不足、无法胜任手头的任务,实际上,他在发泄对革命工作的不满和抱怨。中间穿插的一句“他连儿子都没有一个”,更暴露出在何华明心中,以传宗接代为主的个人“旧”观念始终占主导地位。相较于集体革命事业上的不顺利,个人生活中没有儿子的事实更加令他失望。如前所述,妻子心中对“安适的生活”的理想,其实也是何华明潜在的心愿——耕种土地、照料牲畜,最好能有一个儿子作为帮手,这难道不比整天处理繁杂的政治问题更吸引人吗?
小说最后,何华明在经历了“旧-新-旧”的挣扎后,再次回到了关于明天的烦恼中。实际上,在1941年《解放日报》发表的初版《夜》中,何华明将要参加的会议有具体的实践背景:“第一,要发扬民主才能抗战胜利;第二,三三制就是……”[6]其中涉及1940年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提出的“三三制”原则。“三三制”规定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分子各占三分之一,后来也成为边区民主选举的重要原则之一。但在实际执行中,农民“对于参政不很积极”、干部“自己文化低,对于政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7]的现象屡见不鲜。《夜》中,结合何华明入睡前的具体语境,读者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革命工作与现实之间错位的张力。一方面,何华明所在的延安农村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间,当“新”的革命工作突然闯入他的原有生活,那些“旧”的观念习气在客观上阻碍了他投身革命事业。但另一方面,作为新一代干部中的一员,何华明已经丧失了身为革命主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其曲折多变的心理和他的实际行动之间也存在鸿沟。在他看来,“明天”是缺乏激情、令人烦躁的,令他无法理解和接受的革命工作还得继续下去,但关于“如何能把农村弄好”的问题却仅仅停留在“想”的层面。这既反映出在新旧观念混杂的影响下,农民作为革命主体身份上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也反映出革命主体内部以革命为驱动的发展动力和政治激情的减退。这一现状不仅反映了边区民主政权建设的困难,还容易导致农村革命落入被动的局面,使农民思想获得解放、生活得到改善、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变得更困难。因此,新的方向和新的变革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显得尤为重要。
四、结语
《夜》是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创作的最后一篇小说,她结合自身在川口农村的生活体验,以极短的篇幅传达出深广的社会内容,为读者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其实,天亮后,何华明的工作生活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虽然何华明的一夜里充满波动,但他的生活模式、工作现状和所处环境是难以改变和颠覆的,因此在天亮之后只能是一切照旧。同时,革命的力量是否能够真正介入农民生活内部,并作用于传统生产活动、家庭结构和基层建设的变化与重新建构十分重要。实际上,怀着敢于书写、敢于战斗的革命激情,以及对延安革命现状和未来前景的敏锐胆识,此时的丁玲已经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去迎接思想立场以及创作方式上新的改造和转变。
参考文献
[1] 骆宾基.大风暴中的人物——评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J].抗战文艺,1944(5-6).
[2] 雪峰.从《梦珂》到《夜》[J].中国作家,1948(2).
[3] 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西安文史资料 第17辑 忆延安专辑[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4]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教育志 下[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
[5] 打破贯澈政策的阻障[N].解放日报,1942-02-17(1).
[6] 丁玲.夜[N].解放日报,1941-06-11(2).
[7] 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所.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 陆晓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