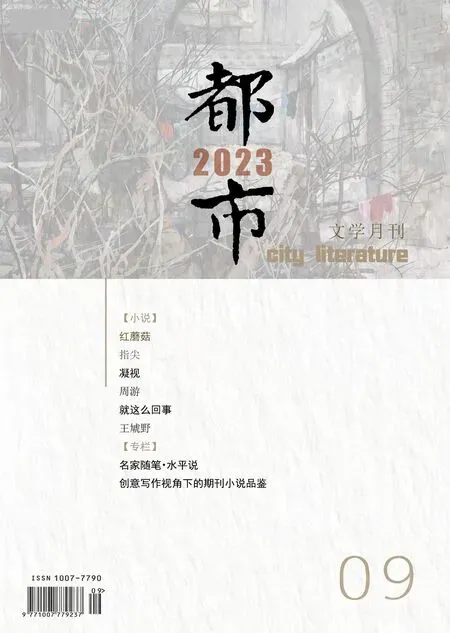蒲公英的人间家园
文 赵明威
1
我那年二十六岁,人生一路兜兜转转,最终把家搬回了儿童福利院。
以至于后来,我每次领着小蒲从那儿路过时,都会聊起我们的初见,还有那个戴着围裙的胖妈妈。
都说因缘际会,人各有命,命运的碾盘不会放过任何一粒麦子。我能来到福利院,全得益于当年高考填志愿时“时运不济”,滑档到了学前教育,也姑且算是个因缘吧。
当年,我成了全班唯一的男生。不过毕业之后,我却找了份售楼处的工作,三年专科的学前教育让我幡然醒悟,小孩子实在是太吵了!我不会在售楼处被抱着腿求陪玩游戏,西装上更不会被拉上一泡屎。来买房的人几乎全都是年轻夫妇,生孩子的事还没提上日程。
可这售楼处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在那待得久了,脾气不减反增,生活压得我戾气直往外冒,顾客经常因为各种原因投诉我,老板便把我给开除了。那些日子真是被搞得灰头土脸,每天厚着脸皮去外面公司投简历,又频频被拒,最后甚至想着,干脆去大马路上讨点吃的算了,总不能饿死在外面吧?别的同事没工作还能回家啃老,可我没有家,更没有父母。哦,也不能这样说,我那时其实有父亲,不过和没有也没什么两样,若即若离。
总之,我在大街上晃荡了大半年之后,不知由谁牵着我的脚步,把我引回了处在郊区的那座福利院。事后回忆起来,好像只是公交车坐过了一站。那里没有具体的名字,光秃秃的门墙上,粉刷着“福利院”三个颜楷大字。时隔多年,白漆已经发灰。那儿贴出的条件确实还不错。包吃包住,工作体面,工资可议。
十几年过去了,前一任院长早已离开,往事如烟般散去。当时我虽有些妈妈留下的积蓄,但明白积蓄需要留给人生大事,眼便没有那么高,心中也丢掉了过多的顾虑。于是,在我徘徊许久,一遍遍地假装路过之后,最终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敲开了门。
了解完情况之后,我拿着毕业证书和资格证书去应聘。我在学校学得不怎么样,但毕竟还算是个专业人士。我应聘的是福利院自招的专技岗,也就是个合同工,当时和我竞争的人不多,因为那家福利院实在是太小太简陋了,算上职工都凑不成一支球队。院里只有两栋三层的小楼,还有一片长满槐树的园子,处在城市的边缘,平时安静极了,要不是门口的大字,真没几个人能找到。
院长就是那个喜欢戴着围裙的胖妈妈,姓宋,叫宋桂花。不过在这里没人叫她的名字,孩子们都是喊她胖妈妈,我们年轻职工也跟着叫胖妈妈。还别说,一开始我还真不习惯,嘴里像被塞了颗核桃,毕竟,多少年没有开口叫过妈妈这两个字了,梦里可能有过,不过当着院长的面儿,说出来总觉得怪怪的,感觉自己真幼稚。
我把家(其实不过是一床皱巴巴的被子)搬到福利院的第一天,便遇到了小蒲。她那时正站在楼梯口,朝外面扔着泥巴,大喊大叫的,可没人愿意去劝她。我也是倒霉,那天为了见胖妈妈,特意换的新衣服,一下就被她扔来的泥巴砸中了。刚开始,我还气汹汹地喊着,是哪个调皮的小男孩儿这么不长眼。可眼睛扫视一圈后,就只有脸上沾着臭泥巴的小蒲,站在楼梯那儿,好奇地看着我。当然,名字是后来从胖妈妈嘴里喊出来的,胖妈妈出办公室迎接我,正好碰见了这一幕,她低声喊着,小蒲!你又搞什么幺蛾子,快回去。眼神搭配上动作,流露出来的责备恰到好处,成功地让小蒲消失在我眼前。
那是我第二次见胖妈妈,第一次就是招聘的那次。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其实挺好的,脸红红的,干事麻利,偶尔对孩子的责备也只是做做样子。后来在与她的相处中,也证明了我的看法。
当时我没有告诉她,将近十五年前的一个夏夜,我曾披着红色被单从这里出逃,更没告诉她,院里最大的那棵洋槐上的疤,就是我砍的。
十五年前,我被送到了这里,当时的院长是个精瘦的中年男人,头发没多少,抽烟、喝酒,在我们面前也不避讳。至于我的家,它陨灭在了烟尘里,在熊熊烈火中,我告别了我妈妈。出事之前,虽然只有我妈一个人工作,生活拮据,但还算幸福,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安稳清静。她在纺织厂裁布,往家里带回了好多碎布,像战时囤粮一样,把布堆在家里快堆成了山,我们的衣服皆从中取材缝制。布匹架起了我们的生活,却又似乎在隐约中将我们两人隔开了一层膜。妈妈和我从未向对方袒露过心事,也从未吵过架,家里一直很和谐,和谐得有点儿像互不熟悉的合租客。
我被遣送到福利院时,完全不知所措,所有事物似乎都和我隔了十万八千里。直到院长领着我弯弯绕绕来到办公室,我双手举着儿童福利证被拍了一张照,才恍然明白,我原来是个孤儿。
远离城市的日子并不好过,围墙把热闹挡在了外面,也把苦痛拦在了里面。我那时感觉,我丢掉了本该属于我的人生,好像是坐在我妈的车篮子里,路上碰着一个石子儿,“哐当”一声,我妈骑车走了,我摔在了地上。在那里,每天一到饭点儿,大家就会把搪瓷碗敲得震天响,院长一来,都哑声了,害怕被打,我没敲过碗,但并不妨碍我因为其他事被教育。不高兴了,我就到槐树林里撒气,用尖锐的石块儿对着槐树砍砸。我玩石头有一手,之前家里的墙上,就被我刻满了“我想你,爸爸”。别人说我没有眼力见儿,我就是傲气得很,打死也不给院长好脸色看,想着总有一天,我得离开那里。
终于,在我十一岁那年,我趁着过节的嘈杂,小心躲开大人的视线,翻越围墙,逃回了熟悉的地方,还意外地找到了我妈的妹妹。曾经不顾家人反对,远嫁外地多年的小姨因为姨夫工作的调动,不久前重新回到了家乡。她见我孤身一人,昔日姐妹间的龃龉终是没敌过心软,将我收留了下来,使我一路完成了学业。因此,现在我才有机会回到这儿,对于我,已经变得陌生的福利院。
那天,胖妈妈给我安排了宿舍,由于这福利院只有我一个男职工,所以宿舍里也便只有我一人。这样也挺好的,稍加打扫,买点生活用品,也算是个家了。
刚开始,胖妈妈没有给我安排工作,而是让我在院里随便转转,适应适应环境。从外面看,福利院被苍郁的树木包围着,在都市圈里算是个“小透明”,到了里面才发现,这地方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太吵了。那些小孩儿哭笑无常,和泥的,打架的,爬树的,干什么的都有。变了,一切都变了,我那时不是这样的。
那几天我闲得无聊,常常吃完饭就去槐树林里转悠。那里的槐树长大了,个个都差不多有五六根电线杆子那样粗,树干扭扭曲曲的,长势不太好,也没人修剪。当年我砍下的那个疤痕还在,只不过随着树的生长,变浅了。摸着那块疤,我心中涌起纷杂的思绪。来这里的时候刚好是春末,正是槐树开花的时候。有几个男孩子,每次都要在我面前,比着往树上爬,让我给他们当裁判。估计是想在我这个新来的人面前耀武扬威,神气着呢!女孩子大都爱干净,在地上捡槐花玩儿,也挺美的。想当初我家里也有槐树,爬树掏鸟窝的事我也干过,比他们玩得疯多了。那时,还单纯地听信了我妈骗人的鬼话,常常坐在树杈上等我爸回来。可谁知还没等回来我爸,倒是我妈先和那棵大槐树一起葬身火海了。
总之,即使有那些不讨人喜的小家伙,槐树林也还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
2
小蒲被安排给我照顾,是我没想到的。那天,胖妈妈把我叫去了她办公室,笑呵呵地问了些,适应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之类的话,我照实回答了。之后,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档案给我看,我一开始没认出来照片上的小女孩就是那天用泥巴砸我的小蒲,可能是因为,照片上的她看起来最多只有两岁,和那个满脸沾满泥巴的样子,差距太远了。胖妈妈说,你也来了几天了,也了解咱院里的情况,人手不够,老师和护工只能是混着当,我知道你大学学的是教育,可也得照顾着孩子,她你看怎么样?我当然只能点点头,没说什么。
从办公室出来后,我就正式变成院里的“内部人士”了。胖妈妈告诉我,小蒲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不到一岁就被她爸妈丢在了福利院门口,被她捡了回来,一直养到现在。小蒲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朝别人撒气。难怪,那天她那么闹却没人管她,原来是大家都习惯了。胖妈妈还说,上一个年轻女护工被小蒲气走了,这次看我俩这么有缘,所以把她托给我试试。果然,在紧要关头,一块泥巴的缘也算是缘。
我能行吗?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想了很久。
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再没接触过小孩子了。成人的社会更适合我,有需要时大家默契地走到一起,需要达成了就默契地分开,没有什么纠缠。每天出租屋里空落落的,安静且自在。可孩子不一样,成人世界的那套法则,在他们那儿不管用,只要他们想,你就别想摆脱他们了。
缠人是他们的基本功,号啕大闹是他们的必杀技。
真正照看了小蒲之后,我发现,她真是我的冤家对头。
由于小蒲只有四岁,所以我得按照学前儿童的标准照顾她。每天要帮她打扫卫生整理床铺,天气好时,要晒被子带她在院子里玩,培养她的生活自理能力,按胖妈妈的话说,我要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养。当然,晚上全是由胖妈妈照顾的,我只需要负责白天的照看。毕竟男女有别嘛。胖妈妈答应我,一旦来了愿意照顾她的女护工,就让我安心教课。
可小蒲真不是那么好伺候的,我简直接手了个万岁奶奶。给她晒被子时,她不捣乱就奇了怪了。她会用手拽着被子不放,有时候还用上小嘴,就是不让我拿走她的东西,我好不容易给晒上了,她还得用泥巴把被子弄脏,真是搞不懂她怎么想的。她心情变化万端,这会儿还跟你生着气,等会儿又非要嚷嚷着带她出去玩,那些天,整座院子都被我们转遍了,哪里有个蚂蚁洞我都知道。可似乎每一天每一处地方,对她来说都是新的,总有用不完的力气,这样一比,那些男孩子逊色多了。
可毕竟她有心脏病,有些地方胖妈妈下了死命令,绝对不能让她乱去。比如那片槐树林,如果她到那儿,看到那些男孩子爬树,她也一定非爬不可。有好几次,她都想偷偷地潜进槐树林,所幸都被我发现了。她每次被阻拦都要瞪大眼睛问我,是不是我爸妈被藏在了林子里?这可让我伤透了脑筋。说不吧,她会号啕大哭;说是吧,就更拦不住她了。最后我只能告诉她,爸妈其实不是必需品,有些孩子并不是爸妈生出来的,还给她讲了女娲造人的故事,好不容易才蒙混过关。说来也是奇怪,她不到一岁就被送到了这里,是怎么知道爸妈这个概念的?真不知道,等她长大一点又该怎么跟她说。
当然,我这么年轻一小伙子,突然多了一个“女儿”,搁谁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适应得了的。她有她的脾气,可我也有我的脾气。尤其是,她特别喜欢在我忙的时候,来我跟前胡搅蛮缠,消磨我的时间,这真让我受不了。可打她吧,又有点不舍得,她都那么惨了,我也不想落个虐待小孩的口实,每次只能皱着眉头吓唬吓唬,最多是低声说她几句。
我最不愿看到的情况是,当我好不容易提起兴趣,想领着她玩时,她突然一泡屎,打乱了所有的计划,我只能狼狈地去喊胖妈妈,来给她收拾残局。但当我懒得陪她玩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就盼着她能把屎拉裤子里,这样,我就能幸灾乐祸地看着她被胖妈妈抱回房间。所以对我来说,小蒲拉屎,有好有坏。我还跟她说过这件事,气得她小嘴噘得老高,说,等我长大一点看你还笑不笑。
小蒲最爱干的事是玩泥巴。一次下大雨,她用泥巴垒了一下午的房子被水冲了,第二天一早,我便看见她在园子里把垮掉的泥往一块儿聚。你快过来,快过来。小蒲离得老远就喊我。我走近看了看,发现小蒲仿照福利院的样式,垒了一座两层的小楼,已经快成型了。小蒲你打算盖几间房子呀?我问她。不知道,但得够我们住的,你看,下面最大的一间是我的,我旁边是胖妈妈的,上面还有豆豆的。小蒲说。叫豆豆的孩子是她好朋友。那我的呢?我试探着问她。嗯——就这儿吧。她用手指了指最上面的一间房子。就咱几个住,人多了不好,小蒲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是啊小蒲,房子里的人不在多也不在少,自己心里的人齐了就行,我说。随后,小蒲用树枝在沙地上画了一个笑脸,将房子给围了起来。
那个画在地上的笑脸看着很拙劣,就像曾经我爸画在玻璃窗上的一样。他被关押在市第二监狱,我妈只领我去过一次。当时我哭得稀里哗啦的,临走时,他用嘴在玻璃窗上哈出一口水汽,画了一个并不圆的笑脸。可能是照着他自己画的,他的脸就不圆。
和小蒲垒完房子之后的几天,我一直在想,要是给我和我妈建一个大房子,我爸算不算房子里的人呢。丢掉的还能不能补回来,这谁也不好说。
3
我和小蒲相处半年多,吵闹有过,欢笑也不少,但依然是小蒲的“局外人”。直到那次的感情危机,才让我真正走进了她的内心。
我还是第一次见她发那么大的火。那天正好是国庆节,我和胖妈妈正在忙活着把孩子们画的宣传画贴在走廊里,小蒲气呼呼地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捏着小拳头,来到我面前,一把将一个男孩的宣传画撕掉了。这可把我和胖妈妈气坏了,没想到,小蒲又朝后面追上来的男孩挥拳砸去,把他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可怜巴巴地看着胖妈妈。这下着实把胖妈妈惹恼了,她大喊道,小蒲!你又干什么!没看到我们在忙吗?回去!给他道歉!我站在她旁边,耳朵被震得生疼。
为了缓解胖妈妈的火气,我识相地把这个万岁奶奶,抱离了现场。到了人少的地方,我指着她鼻子气得说不出话,美好的一天又被她毁了。可没承想,没等我哭,她倒先哭了。她挣开我的手,抹着泪跑回了宿舍。唉,这个小祖宗。
要不是那个男孩来找我坦白,我可能就一直误会小蒲了。他在胖妈妈那儿挨了一顿训斥,红着眼来宿舍找我,小心翼翼地站在门外,不敢进来。那男孩我没照顾过,但也听过其“大名”。我把他让进了屋,他吞吞吐吐地说了声,对不起。随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觉得小蒲讨人厌,在福利院里带头孤立她。
个子不高,鬼心眼儿还不少。我说了他一句也就没再追究。
过了几天,我趁孩子们睡午觉的时间,去外面买了一些糖豆,五颜六色的都有,小卖铺老板还送了我一个竹蜻蜓。当时感觉,一个大人拿着糖豆去道歉,心里总不是个滋味儿,可谁让她是四岁的小蒲呢。
我趁着其他小孩子不注意,把糖豆和竹蜻蜓塞给了她。可还没等我说话,她就把我拉到了楼梯下面。问我,你能不能带我去一个地方?我问,去哪儿?她说,去养院老。养院老是什么地方?是养老院吧?我笑了。对对,养老院,去那儿,去看我奶奶,就是因为我有奶奶,那些男孩才不搭理我的。
这令我惊奇不已,她怎么还会有奶奶。小蒲似乎也看出了我的疑惑,咧着嘴说,我和奶奶是在栏杆那里碰见的,她每次从栏杆那儿过,都会给我带这样的糖,我之前喜欢在栏杆那儿玩。哦,原来是外边路过的老人。那你怎么知道她在养老院?我问她。我奶奶给我说的,她说以后不能来看我了,她要被送去养老院了,所以,你能不能带我去见她。她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我最受不了小孩子这样了,这让我失去了“拒绝”这个选项。
我决定,趁着胖妈妈给孩子们洗被褥的时候,带她溜出去。这还是我入职以来,第一次坐公交车跑这么远。
我给她戴上小帽子,牵着她的手,穿过高楼大厦,从城市的这个边缘来到了那个边缘,我俩都没来过那儿。由于不知道老人的名字,门卫老头不让我们进。我俩在养老院周围转了好几圈,隔着栅栏不停地往里瞧,小蒲还非要闹着让我把她举起来。就这样,我举着她,让她坐在我脖子上,在那儿待到了天黑,直到气温降了下来。
小蒲在我脖子上坐习惯了,我也驮习惯了,所以没有感觉累。之前院里活动,我们去了附近的动物园,小蒲看到外面很多的小孩子都坐在大人脖子上,也拽着我的裤腿往上爬,我无奈地把她抱起来放肩上摇来摇去,逗弄得她不停地笑。当时我想,在其他游客眼里,我们俩应该就是一对假日出行的父女,正等待着妈妈买零食回来。小蒲玩得累了,就赖在椅子上让我给她捏腿,我嘴上说她懒,心里却感觉到一种别样的高兴。
正当我准备带她回去时,她猛地拍了拍我的头,高兴得两腿不停地踢着我的胳膊。看!你看!那就是我奶奶!我抬头眯着眼,看到公寓楼里有一位老人,正趴在栏杆上发着呆。奶奶!奶奶!小蒲大声喊着。我四处看了看,驮着她,站到了最近的一个路灯底下,情不自禁地随着她一起喊了起来。老人似乎听到了我们的呼唤,朝我们这儿摆着手。奶奶,奶奶,喊着喊着小蒲又哭了,把眼泪和鼻涕都抹在了我头上,我用手极力地把她举高,在路灯底下摇摇晃晃。可现在是老人的睡觉时间,她下不了楼,这可把小蒲急坏了。这时我灵机一动。小蒲,你看!我把她放下,从包里掏出了那个竹蜻蜓。咱们把它飞给你奶奶好不好?小蒲跳着拍手,我靠近围栏,瞄准公寓楼,用手使劲一搓,竹蜻蜓缓缓地从面前离开,向高处飞去。我俩看着竹蜻蜓,两手紧紧地握着,终于,它精准地落在了公寓楼上,我抱起小蒲,她在我脸上亲了又亲。
回去的路上,小蒲给我讲了她和她那位奶奶的故事。她说奶奶是世界上最好的人,第一次看见她一个人在栅栏边玩,就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彩色的棒棒糖,可把她高兴坏了。从那之后,她每天都跑栅栏边,等着奶奶,她还用泥巴给奶奶捏过小人儿。不过她没敢告诉胖妈妈,她怕胖妈妈不让她去。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小蒲并不是一个爱吵闹的人。一路上她小声地给我讲述着,似乎生怕别人听见她的奶奶,最后,躺在我怀里睡着了。真是没想到,她还会有这样的一面,在福利院里她动不动就发脾气,朝别人扔泥巴,大喊大叫。现在想来,似乎她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罢了。四岁的小孩子,正是需要被关爱的时候,福利院里,纵使胖妈妈再好,也不能只照看她一个小孩子,总有忽视的时候。
那位奶奶,让她感受到了来自外面世界的关爱,那和福利院里任何人的关爱都不一样,因为那是独一份的,只属于小蒲自己。
我笨拙地把手放在小蒲头上,看着她挂着泪痕的脸颊,不知道她在梦里会梦到什么。
4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眼年就到了跟前,福利院里也开始张灯结彩。虽然经费不多,但用卡纸一装扮,还是挺喜庆的。孩子们欢闹着绕着院子嬉戏打闹。胖妈妈还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件棉服,根据我的建议,他们每个人的棉服都是不一样的。小蒲的那件是粉白色的,上面还绣着小猫,当我拿给她时,她毫不客气地收下了,脸上挂着腼腆的笑。
大年三十下午,我那个好久没有见过的父亲找上了门来,隔着栅栏笑着,想从我这儿借点钱过年。我上次和他联系,是带着小蒲从养老院回来后,犹豫了好久,我最终给他发了个信息,告诉他,我换了份新工作,活得还算不错。如果没记错,他回了我好长一段话,错别字百出,一看就是用语音转的文字。不知道他怎么找来这儿的,他突然站在我面前,我差点儿没认出来,直到他喊出我的小名,我才敢确认。和上次比,他老多了。他不知所措地搓着手,说工地上干的活,年前怕是结不了账了,想问问我,能不能借给他点儿钱,用来走亲戚。说实话,我那时手里拿着糊好糨糊的春联,看着他,着实心软了。
他之所以进监狱,听我妈说,是给厂子里开车,过失撞死了人,不懂法,一着急害怕地跑了,结果加重了邢责,判了好多年。直到我大二的时候,才被放出来。一开始,对于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在我生活中的父亲,我本能的态度是排斥的。我早就习惯了没有父母的生活,何必再硬插一脚呢?所以,我明确地跟他划清了界限,大学没怎么回去过,工作了就在外面租房子,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在哪儿不是家呢?可来到福利院之后,这个想法似乎逐渐被改变了。
当时我脑袋空空,从钱包里数出了一千块钱,隔着铁门递给了他,等他走后,我才出去贴了春联。那一幕,正好被找我去买糖吃的小蒲看到了,她歪着头,好奇地问我那是谁,我含含糊糊地搪塞了过去。
那天晚上,我和胖妈妈组织小孩子们热热闹闹地吃了年夜饭。胖妈妈跟我说,幸好这些孩子们没有家的概念,不知道想家,不然,年夜饭上不得哭成一片哪。我低着头应和了几句便没再说话,感觉耳朵有点烫。
年夜饭吃的火锅丸子和一些蔬菜,是胖妈妈去外面买来的,由于害怕孩子们吃了拉肚子,所以只买了番茄味的火锅底料,对于一向口味较重的我来说,也只能将就顾着孩子们了。在饭桌上,我们共同举杯,庆贺新一年的到来,小蒲双手捧着塑料杯,小心翼翼地舔着杯沿,搞得脸颊上都是饮料,看得我哭笑不得,一顿饭中不停地给她擦嘴。
隔着不断升腾起的雾气,胖妈妈给我讲了她来这个福利院的缘由。十几年前,她本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小学教师的工作,丈夫在远洋的船上当大副,日子里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自己的孩子。后来丈夫在海上出了事,掉进海里淹死了,尸体也没有捞上来,公司便给了胖妈妈一笔赔偿金,她把赔偿金全都分给了丈夫的家里人,本以为日子还能重新回到轨道,慢慢过下去,可学校里的工作也并不顺心,让胖妈妈身心俱疲。最后,爱孩子的她选择了福利院,一直干到现在。
我忽然有了一种感觉,觉得小小的福利院似乎变了一种模样,孩子们笑得更灿烂了,火锅咕嘟咕嘟的沸腾声更响了,上升的烟雾堆满了房间。似乎,这里更有了家的模样。幸好有那烟雾,不然,我流泪的狼狈样儿,可就要被胖妈妈和孩子们看到了。
外面的烟花响了,小蒲拉着我跑出去看烟花。可我们这里离城区太远了,看不清,于是我带着小蒲上到了屋顶的天台,空气很寒冷,我俩呼出的气流在空中碰撞交汇。我问,小蒲你知道烟花是什么吗?她说,就像我的名字一样。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我疑惑不解。嘿嘿,胖妈妈说我的名字是蒲公英花,和烟花是一样的。只不过,烟花会消失,我的名字不会。哦!原来如此,小蒲的名字是蒲公英的意思,蒲公英飘到哪里都能活下来。胖妈妈起名字时真是用了心。
我俩抬头望着远处绽放的烟花,听着隆隆的响声,突然小蒲戳了戳我的胳膊。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今天那个老头儿是你爸爸吧?这令我震惊不已,难道小蒲已经知道人都会有父母了吗?她扬着下巴,得意地对我说,当然,我长大了,你骗不了我了。那好吧,那是我爸爸。我还是第一次念出爸爸两字。那你为什么不让你爸爸进来呀?小蒲都没爸爸。她歪着头问。是啊,我有什么理由呢?嗯……小蒲啊,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大人的世界里,事情总是很复杂的。胡说!事情很简单,你只是有选择而已。“选择”这个词她刚学会,说得很生硬。小蒲的一句话怼得我无言以对。这是我从来没考虑过的问题,竟被她这个小鬼无意间给说出来了。我笑着看着小蒲,烟火映过来的光,在她脸上忽闪忽闪的,她怎么那么可爱!
过完年没多久,来了个女护工,我把小蒲交给她看护,从福利院暂时离开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去见了我的那个爸爸,他接到我的电话,激动得不得了,硬是要请我去饭店吃饭。我拉着他,去到饭馆,告诉他,我准备相个亲,请你给把把关。他听到我说这话,立马便趴到桌上哭了,嘴里嘟囔着,好好好。
我相亲找了个生不了小孩儿的女生,长得还算是清秀,我俩眼缘也合适,正好,她没人娶,我没人嫁,我俩便凑成了一对儿。其实,我结婚除了是想有个家之外,还有些小心思,想把小蒲给领养了。因为福利院有规定,必须结了婚才能领养孩子。和未婚妻商量后,她也很高兴,正好弥补了她生不了小孩儿的遗憾。
很快,我俩便领了证,回到了福利院。那天胖妈妈和小蒲早早地等在门口,我来时,小蒲惊奇地看着我身旁的妻子,小手拧着,害羞得不敢说话。
我蹲下抱着她,问,小蒲愿不愿意我来当你爸爸?这样从此以后你就有爸爸妈妈了。她害羞地在我肩膀上点了点头,动作很小,不过我能感觉到。办好手续后,我领着小蒲离开了福利院,临行前,我摇下车窗,朝胖妈妈挥了挥手。胖妈妈正俯身看着车里的小蒲。我告诉她,槐树林该修剪修剪了,疤痕多了会生虫。她不知所以地应了一声。我踩下油门,车慢慢往前开动,看着“福利院”三个大字逐渐变小,我又探出窗去,卡在喉咙里的一句话终于说了出来。
妈妈,咱们福利院应该有个属于我们的名字,干脆就叫“人间”吧!
现在想想啊,那时真是奇怪,我竟然在这城市最孤独的地方,治好了我的孤独病,在最边缘的地方,遇见了小蒲。
好了护士,话到这里就差不多了,真感谢你能听我絮叨。现在,我想请你去看看,我的小蒲快从手术室里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