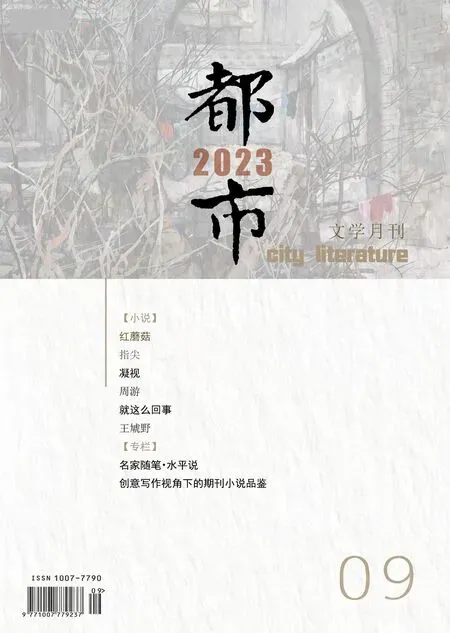就这么回事
文 王虓野
赵小亮不是个东西。下午在我家喝的酒,七八点说有事先走。我骂了几句,大过年的,啥事啊,场子进行到一半,你跑了。赵小亮端起分酒器,把里面剩的二两都干下去了,说,哥,成不成。
我摆摆手说,成,去吧。赵小亮套上羽绒服,晃悠了几步,推门走了。走楼道里,我听见他嘴里呕出一大摊,吐电梯门上了,我跟剩下几个人继续喝,把他们送走以后,我拿簸箕清理赵小亮的呕吐物,又埋了点花盆里的土。
媳妇出来看,说,这赵小亮不咋能喝啊。
我说,逞能呢,不喝不让走。
媳妇说,你把电梯收拾干净,楼上楼下的,吐了不少啊,这对联也用不成了,都湿了。
我说,对联凑合吧,年没过完,还能给撕了?
媳妇瞅了我一眼,我知道她想说啥,无非就是老三套:少喝点得了,喝完净是事,以后出去找个地儿睡,别回来了。我打住她马上出口的话,我说,大过年的。
媳妇回屋睡了,我把家里里外外拖洗了一遍。头有点疼,喝得不多,四个人三瓶,正常量,媳妇弄了几个下酒菜,猪耳朵丝,拌牛腱子,木耳黄瓜啥的,总共六个菜,要双不要单。媳妇不喜欢家里搞这种场合,但面儿上不动声色。
几个喝酒的嘴上功夫不断,张口闭口:酒是粮食的精,越喝越年轻。顺口溜一上来,气氛搞得乐呵,媳妇说我本来嗓门就大,喝点酒拍桌子提板凳,一点不收敛。我其实酒风好,喝完酒一睡就着,刚把家拾掇干净,赵小亮来电话了,非要出去打几杆台球。
我说,你喝成那样,打啥台球?
电话里说,出来,就楼底下等你呢。
我说,你得了吧,快十一点,睡觉了。
赵小亮挂了电话。
我爬到床边上,媳妇靠在床头捣鼓手机,我说,一年能过几回年呢,过一年少一年。媳妇从面膜的挖空里眯着眼睛瞪我,想干啥?
我说,地刚拖先别下,碗也刷好了。
媳妇说,别支支吾吾的,谁打的电话?
我说,赵小亮说出去打会台球,俩小时。
媳妇说,赵小亮还欠两万块钱,你别充好人。我说,行行行。
赵小亮把我家拖鞋穿走了,我找了个塑料袋,把他落的皮鞋装里头,出了门,外面有几个小孩在放炮,九楼的,学习不行,三天两头挨打。跟我倒熟,有回他爸满院子追着打他,我正好下班,给救了一次。我给他爸装了两支烟,说,消消气,成绩好不好的没事,关键这小孩儿机灵有礼貌,他爸放下电饭锅绳,跟我抽了一支。
我问小孩要了两根小花炮,比大拇指头粗一倍,装兜里。小区里的树都缠着彩色灯带,哗哗闪,不怎么好看,审美不行,一棵树上弄七八种颜色,能好看吗?要么一顺色,要么弄点花样。据说今年赤字大,灯怕费电,十二点准时关,都是楼下老太太说的,啥都知道。
路上雪还没化,车轱辘轧得瓷实,没十天半个月化不了,今年这雪挺大,前后下了三场,一下就连下两天,前脚雪还没化后脚又堆上了。我把重心放低,稍微助跑了一段,往前溜了四五米,电视里搞冰上运动的,就这个姿势。我把重心压得更低,这次溜了七八米,俯式,不过停的时候没控制稳,屁股摔青了。我又想起喝酒的事:喝酒是门哲学,边喝边观察,边总结,跟溜冰似的。
我低头俯冲,两只胳膊张到最大,双腿拉开弓,不错,渐入佳境。小区里隐隐的灯带飘闪,不亮,街上没影,人都在家。我继续溜,马上到大门口的拐角了,这是个视野盲区,车看不清,常出事。我按照溜冰要领,一顿,二保持平衡,三依照惯性,缓缓停住,停稳,一抬头,瞅见赵小亮在拐角黑处。
我说,吓我一跳,你不是在楼下吗?
赵小亮说,刚刚在,我也溜冰过来的。
我说,去哪打,老地方?
赵小亮转过墙角,说,先走。
过拐角就上了大街,大街路灯不怕费电,特亮。我和赵小亮手拉手往前溜冰,马路上车不敢走,人倒溜得快。他溜得不行,我给他教点技巧,慢慢能跟上节奏了。我回头一瞅他,脸上一道长口子,从右耳朵划到下巴沿上了,血糊糊的,路灯照得特瘆人。
我差点跌倒,我问,你干啥去了,动钢管了?
赵小亮说,摔的。
我说,啥玩意儿能摔成这样?
赵小亮说,黑,摔树沟里了,树枝给划了。
我一时不知道该哭还是笑,说,你也太不当回事了,你好歹洗一下啊。
我们往前走,有个小停车场,车前发动机盖子上有干净的雪,我把雪捧起来给赵小亮,他脸埋进雪里,脸滚烫,雪水从颧骨流下来。我掏了几张纸给他,说,到底咋弄的。
赵小亮说,别问了,你媳妇让你出来?
我说,那不是出来了。
赵小亮说,那行,咱哥俩说说话。
我说,你咋听起来这么伤感。
赵小亮没说话,我俩继续往前溜,一路溜得心事重重。赵小亮媳妇回四川过年去了,没一块,具体原因没问。中年男人,这半死不活的婚姻,问它干啥。要么闹了,要么打架了,不愉快了,分开过了,就这么回事,过两天又好了,婚也不离了,感情也重圆了,就这么回事。你如果在一边搅局,打听这打听那,最后只会落得自己脸上不好看,我和赵小亮十几年的关系,从不提这个,等于是心照不宣了。
赵小亮跟他媳妇是大学同学,自由恋爱,自主选择,最后他媳妇跟着来这边找了工作,也有十年了。我说赵小亮,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孩子都老大岁数了,不容易。
赵小亮拐进商店,提了打啤酒出来,还有几袋花生米。他说,走,边打边喝。
我说,你脸是不是被球杆给呲了。
赵小亮说,是是,刚去台球室跟人冲了,给我戳了一杆。
我说,谁啊。
赵小亮说,你还真信。
台球室门帘一揭开,一阵臭烘烘的热风扑出来,夹杂着呛鼻的烟味,赵小亮带着脸上的血口子进了屋,半截脸还是脏的,人都朝这边看过来,以为是黑恶势力余孽,不体面。打中式8 球,照例是赵小亮开球,他打得菜,让他。他把塑料袋里的罐装雪花拿出来摆桌上,说,一局一罐。
我说,你能喝不?
赵小亮说,没把儿的不能喝。
他开球,进了一颗,紧接着打了几个袋口球,停了。我说,手艺还得练啊。我球型不错,一杆清,赵小亮拉开啤酒环,倒进嗓门眼儿里去,眼神呆呆的。
我问他,想啥呢?
赵小亮说,你说冬奥会咱能上个啥项目?
我差点没笑出来,赵小亮沉思了半天,冷不丁放了个这屁。我说,你想上啥项目,溜冰队主教练给你当呗?
赵小亮说,教练拿不了奖牌,要弄就弄拿金牌的。
我说,拉倒吧,打球。
赵小亮说,你说女人这是咋回事?
我愣了一下,这小子终于来正题了。赵小亮擦上壳粉,俯下身,长吸了口气,又站直,反复了几次,说,不得劲。
我也开了一罐啤酒,陪他喝两口,脸刚白了点,灌了几口下去又红了。我说赵小亮,还不是钱的事,两年多了,干生意的哪有那么多过得顺的?
赵小亮说,你媳妇没提两万块钱吧?
我说,没提,都难,能理解。
赵小亮说,他妈的,买了点基金,也赔进去了。
我听见赵小亮买基金,把杆杵在地上,差点骂他。我说,你别瞎折腾了,有点钱把厂子周转开,日子还得过啊,你咋自暴自弃了?
赵小亮说,工人工资开不掉,货压了一大批,咋周转?
我说,都是老工人了,工资不能先缓缓?共克时艰他们不懂?你这阵子不行,下阵子行了,多给开点。球馆靠窗户走了两桌人,我跟老板叫了一声,换台。换到窗户跟前,我把不锈钢推拉窗推开,吱的一声,风立马灌进来。赵小亮说,媳妇过不下去了,咱也不忍心人家跟着遭罪,问人借了点钱,每天上门要账,有回差点动刀子了。
我说,咋回事?
赵小亮说,几个破玩意儿给我儿子堵楼底下了,媳妇刚接儿子回来,要账的在楼门口蹲了一下午,死等。我媳妇吓坏了,给我打电话,我提着菜刀下去了。那几个不依不饶,我把刀朝他皮包上划了一下,他看我要来真的,就跑了,后来没来过。我哪敢来真的,一刀把肉给割了,人进去了,娘俩谁管?
我说,操。
赵小亮说,从那以后,媳妇不敢出门了,儿子都是我接送。我又得跑资金,还得管一家老小,资金也跑不出来,银行一看是搞水产的,理都不理。我想索性把厂关了,资金回出来,工人工资给发了,债清了,可不甘心呐,厂子办了小十年,刚有点名堂,气不过。
我说,你老丈人那还有多少?
赵小亮说,老丈人半年都没打过电话,以前老亲儿子亲儿子地念叨,现在脸一翻,不认了。初二我给拜年,丈母娘接电话,没好气,我挂了,不就六万块钱吗,能把人逼死?媳妇说今年回四川过年,我没吭声,哪有脸见,她就带儿子走了。这不摆明过不成了吗?
我说,你别这么想,天无绝人之路,咬咬牙啥事都能过去。
赵小亮说,你少跟我来这套,不死就赖活着?连人起码的尊严都没了,每天跟孙子一样,到哪都是孙子,人变化快啊,生意场上,好多人不来往了,还指望着人家给救一命。你要是做生意的,咱俩怕现在也臭了。
我说,打球吧,落了好几杆了。
赵小亮俯下身子,右臂屈得很夸张,整个人铺在台泥上,杆子回缩了三分之一,一杆下去把蓝色10 号球打飞了,砸在窗玻璃上,玻璃咔一声碎了。老板从吧台探出头望了一眼,又低头刷短视频。碎玻璃窗里天空显得清晰透亮,把三楼路灯的暗黄色光微弱地滴进来,冬天是深蓝色的,割碎在玻璃缺口上。
我说,少一个球,咋整啊。
赵小亮说,不碍事,让你了。
我摆了自由球,下一个球加了高杆左旋,白球吃了一库,朝反方向滑过去,最后急停在左侧库边。
赵小亮说,上个月我去洗脚城,认识了个女的。
我说,洗脚的?
赵小亮嗯了一声,把杆柔推出去。
我说,有意思,干啥了?
赵小亮说,没干啥,喝多了,跟我聊天,我最烦去那地方聊天。该干啥干啥,你挣你的钱,我按我的摩,有啥可聊的。
我说,结果呢?
赵小亮说,你慢慢听。
我坐在旁边椅子上喝了一大口,说,你边打边说。
赵小亮说,后来那女人她硬跟我聊,说以前怎么怎么的,后来怎么怎么的,我没听,我就说,你别跟我来这套了,我不加钟。她眼泪刷地一下下来了,我正纳闷呢,她说,没让你加钟,我就是想说说话,没叫你听。我头疼,躺着睡,我最见不得人哭,我说,你说吧,不关我的事。
她站起来拿纸巾擦了脸,说,现在人手头没钱,来洗脚的少,洗脚城都倒闭了两个,就我们这儿还勉强能干。有几个一块来的,都做别的去了,招呼我一起,我差点也去了。最后没去,她们都没小孩,我有小孩。说着她眼泪又吧嗒吧嗒掉,掉在脚盆里。
赵小亮说,我给那女的递了两张纸,让她擦眼泪,说别洗了,想聊就聊两句吧。
我说,你还聊上了,她能有实话吗?
赵小亮说,咋说呢,陌生人一块聊天,有些话反而能说,你要让我去找熟人倒苦水,倒不出来。况且这女的长得挺好看。
我说,你早说得了,就长得好看呗。
赵小亮说,她说她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哥哥妹妹。她们一块的那几个女的,以前是搞特殊服务的,后来转了几个地方,都被打掉了。这两年洗脚城生意不行,那几个又跑了,东跑西跑,她没去。
我说,你信她?
赵小亮说,有啥信不信的,信能咋,不信能咋。她又没骗我啥,她说她老公不上正道,不着家,后来晚上喝醉开车掉河里了,捞上来人就没了。反正说了这么些,我都信了,关键是她眼泪掉得快,我还安慰了她几句。
我说,咋安慰的?
赵小亮说,我把我的事也跟她说了。
我长吸了口气,说,你可真行,啥都往外说,你跟她说得着?
赵小亮说,我又加了一个钟,跟她聊,一个钟198 块钱,我把我和我媳妇都跟她说了,厂子的事也说了。她靠在沙发上,手支着脑袋,她化的妆不浓,脸还挺清秀。我跟她说,我现在手头欠了大几十万,吃一顿少一顿。她说,男人都喜欢在外面搞?不过,你不是这样的人,有些人一进来像是君子,不到十分钟就要脱裤子了。
我说,你脱裤子了?
赵小亮说,没脱,穿着呢。
我说,没啥精彩的,继续。
赵小亮说,后面没啥。
我说,你媳妇在的时候你去洗脚不?
赵小亮说,应酬多,但没啥意思,去了就躺着睡觉。钟到了,她叫我,我就回家。有次喝太醉了,有个女的给按摩,我没好意思睁眼,假装不省人事,时间到了她叫我,我起来一摸裤子全湿了。
我说,赵小亮啊你小点声,人丢外面了。
赵小亮说,和媳妇都没性生活了,没啥感觉,白天在外面累得像头驴,晚上回家扯过被子就睡了,你呢,啥情况?
我说,我没问题啊。
赵小亮说,得了吧,谁还能没点问题,你和你媳妇就那么好?
我说,也不是,该办的时候就办。
赵小亮说,也是,你大龄结婚,新鲜感还没过,再过两年你试试,我和我媳妇以前也好啊,大学谈恋爱那会,每天晚上睡觉,睡一次不行,睡三次,没出大学校门就领证了,婚龄十四年,弹指一挥间。人生能有几个弹指一挥间?按道理,俩人也不能说没有共同语言,后来生孩子,拉扯生活,慢慢就隔得远了,总之婚姻这玩意儿……
赵小亮说得来劲,话里情绪倒越来越低落。桌上的啤酒剩下两个,我开了一听,又开了一听给他。我说,喝吧,你媳妇啥想法?
赵小亮说,啥啥想法,我现在顾不上那些,厂子得管吧,钱得找吧,能扛过去就扛过去,扛不过去就死路一条,到时候媳妇带上儿子另过,我自己过。
我说,悲观了啊。
赵小亮说,银行这两天透了个风,说半个月以后能给放点款,先把工人工资发了,再说别的。
我说,你今天着急出去是这事?
赵小亮说,不然呢。
我说,这事你明说啊,扭扭捏捏的不像个爷们儿。弄钱的事,不比喝酒重要?该啥啥,大过年的。
赵小亮的贷款有了谱,我心里稍微落了点,这两年没少给他操心,要债的前几个月常上他家门,我也给挡了不少事,有回腿上挨了一钢管,半个月没下来床。
我说赵小亮,你以后少洗点脚,省下那198 块钱,吃点羊腰子多好,别老跟人家聊,聊进去了,你咋收场?
快一点半了,赵小亮去洗手间撒尿,我给媳妇发了微信,照了张台球桌照片,让她先睡,快了。媳妇没回,应该已经睡了,或者是不搭理我。赵小亮半天不来,又去厕所吐了,喝点就吐,早晚得胃出血。我去厕所找他,喊了一声声控灯,没亮,借着玻璃窗的路灯摸黑进去,喊,赵小亮,在哪个包间儿呢?
没人说话,我又喊了几声。从厕所出来,我往楼底下瞅了一眼,也没人。上哪去了?我给他打电话,正在通话中。我回了球台,坐了两三分钟,再打,还是正在通话,狗日的赵小亮,玩呢。我靠在椅背上,打开微信工作群,又是99+条消息,没完的事。有几个表格要填,截止时间是昨天晚上十一点。我在工作群连续回复了三个收到,管理员说,不要刷屏。等着赵小亮还没来,我给他发信息:不来我回家了。
赵小亮响电话了,说在楼下等,我说你等啥呢,上来啊。赵小亮说让我下去,我说你干吗呢,等老半天了。我结了账,从楼道往下看,赵小亮站在路边上,怀里抱着个孩子。我跑下楼,赵小亮听见我下来,站在马路牙子上冲我傻笑。
我喷他,说,你干啥呢?
赵小亮说,这小孩下午发烧,我带她去医院看病,她俩在门诊输液,刚回来,正好路过。
我说,谁小孩?
赵小亮说,她的。
我往背后的台阶上望了一眼,一个瘦高的女人穿着白色长羽绒服站在门框边,两只手插在衣兜里。
我把头靠过去,问赵小亮,谁?刚你说那女的?
赵小亮点头。
我说,你真行,还是脱裤子了。
那个女人从台阶下来,走到我们旁边,和我差不多高低。我吸了支烟,看着他俩,赵小亮很久没这样笑过了,那个女人也露着牙齿笑,样子很好看,在路灯底下带着清冷的气味。
我说,那你俩聊,我先撤?
那个女人说,我家就在旁边,去坐会。赵小亮也点头。我转过身,往她指的巷子口走,赵小亮抱着孩子,四处望,明显是做贼心虚了。
我喊他,说你快点,找啥呢?他突然往反方向跑,我又叫了几声,他在隔着一百多米的地方停住,蹲下,接着转过头小步地踩着冰面,胖脸一抖一抖的。我跟那个女人说,你往前走,我等他,女人点着高跟鞋,小心地往前挪,两只手轻蜷起来保持平衡。
赵小亮溜过来,笑得特大声,说,看,蓝色10 号球。
我说,捡这玩意干啥。
赵小亮把蓝球上的泥雪用棉衣擦干净,递给怀里的小孩。我问,你去过她家?
他说,下午七点多看病,第一次去。
我说,你嘴里没实话。
赵小亮像抱着自己的孩子,在冰上转圈。那个女人转过身看,像是一家三口。我站在旁边,里外不像个人。
女人走在前面,赵小亮跟在中间,我搂底。巷子里几盏路灯还亮,大约走了四五十米,那女人拐进了一个院子,从院子口左侧上了台阶。听见吱呀一声,铁皮门开了,女人开了灯,我在台阶下面站着,昏黄色的灯光往外映出来,雪地上面有融融的星星点点。
屋很小,估计是三百块钱一个月租的,收拾得干净。我朝四周望望,坐在沙发上。女人不合时宜地打开了电视,已经两点过了,找了几个台,没啥好看的。最后落在了一则冬奥会快讯上面,漫天漫地都是谷爱凌的名字,拿了两块金牌,才十八岁。女人端了两杯茶来,说,家里也没别的饮料,喝点水。
我说,行行,把杯子往赵小亮那边推了推。
赵小亮不说话,脸上泛着红光,我瞪了他一眼,他好像在自己家一样,不把自个儿当外人。赵小亮把小孩放在沙发靠背上,左亲右亲,看得膈应。我假装没看见,眼睛盯着电视,余光瞪在赵小亮身上。女人进了里屋,念叨了几句什么,像在跟人说话,然后她在里屋门口脱掉了高跟鞋,露出半截脚踝,脚踝上套着浅肉色的打底裤。我盯着电视看谷爱凌,套屋里传过来几声鼾,我张大嘴看赵小亮,给了他一个眼色,说,怎么还有人?
赵小亮说,是她的大儿子。我这才透过门帘往里面望,那个女人在叠衣服,放进塑料衣柜里。
我闻到一点香水的味道,和女人身上的一样,她在里屋喷了一点,似乎在遮盖什么臭味,我坐着没事,谷爱凌切成了广告,我又换台,免得他们看我尴尬。这个女人看起来像三十岁出头,但是一举一动却像个女孩。赵小亮这小子,怪不得,跑这儿给人家当爹来了。
女人进进出出,端着一个小盆子洗东西,从沙发前经过的时候,不好意思地抿嘴笑。最后她去洗了手,带着玫瑰味的洗手液香气坐到了赵小亮旁边,侧着脸看赵小亮。电视机声音略小,现场气氛冰冷,我也不知道说啥,职业呢已知,家庭情况呢已知,况且这俩人的关系,我能说些啥?赵小亮不是个东西,他也不说话。
女人看了一会赵小亮,让我喝茶。我心说大晚上的喝啥茶,说话。女人轻叹了一声,说,里面躺的是我儿子,过年就十周岁了,先天性骨骼发育不良,两只脚像棉花,站不起来,我老公说再生一个,结果生了没一年,老公死了。我一个人照顾两个,他们家人不管。她接着说,白天我脱不开身,这俩小孩一刻不能没人,只好找了个晚上的活干,给他俩安顿睡了,我再出门。
我看了一眼女人,她的眼睛很亮,有点眼泪溢出来,我搓着手听她慢慢地说。这样一个陌生清冷的大年初三,没想到我们几个人会坐在一张沙发上。这女人辛苦,我不知道赵小亮从她身上得到了什么,也许是看到了自己,世人皆苦啊。
媳妇来微信了,说,你要不要脸,两点多了干啥呢?
我说,跟赵小亮一块呢。
媳妇回,钱要回来,要么别回了。
我说,不回上哪?
媳妇说,随便你。
我说,马上回。
赵小亮说,你媳妇催你了?
我说,惯的,不管她。
赵小亮说,我今天到这儿的时候,突然看见自个儿了,一切都陌生得很,而我的心却踏实,我的脚也暖和,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生活。
我说,大晚上的,你咋还抒上情了?
那个女人咧嘴笑,她说,我和小亮哥没啥,他有媳妇,我说你别来了,他发信息说非来,我说来就来吧,也看看不同的生活。
我喝了口杯里的茶水。
女人又说,我也想重新活一次,但命呢就这么回事,开始不了啊,俩小孩不管不行,钱不挣不行,我说我也跟那几个姐妹一样儿,跑,搞点来钱快的,心里又过不去,俩小孩知道了,咋想呢。屎尿拉床单上,得换吧?这小的明年上幼儿园,得给教育吧。有时候见小亮哥,我心里难受,不是滋味。
赵小亮把头放在沙发背上,他摸了一下女人的发梢,叹了一小口气。小孩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女人给围了块毯子,抱床上,灯泡老化严重,闪了几下。我说,我先撤。
女人披上羽绒服,说,走,小亮,咱们也下去。
我说不用送,赵小亮从塑料袋里掏出他皮鞋,把我们家拖鞋装袋里,他挽起女人的胳膊,然后送我出去。屋里暖和,一出来风呲呲的,雪又开始落,从路灯罩下面轻扫下来,微微闪着晶光,融在头发里,带着略甜的花香味。我张开手臂,空气清冷浪漫。从巷子转到大街上,赵小亮问女人,你滑过冰吗?
女人说,小时候滑过。
赵小亮抓着女人的左手,让我抓她的右手,然后拉开一点距离。女人踩着毛绒拖鞋,我和赵小亮小步跑,女人在中间滑了起来。我攥紧她的手,手指纤细,留了一点指甲,冰冰的。她半蹲,头发往后面飘,我和赵小亮加快了速度,她的脚底发出与冰面摩擦的悦耳声音,路逐渐黑下来,下面的十字口没有路灯,树郁郁葱葱,背后的暗黄色灯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们三个一起溜,女人在中间,我把左手搭在她肩上,赵小亮用右手抓着我肩膀,数一二三,向前滑出去六七米,嘴里哈出的热气,瞬间就散开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一群院里的孩子,也像这样在巷子里溜来溜去,一溜就是一下午,脸红彤彤的,没人提回家的事。我们仨慢慢有了默契,一次一次向路的尽头溜过去,什么都再看不见,连树的影子都挤在一块。
羽绒服里都是汗,我说,不玩了。女人哈哈地喘气,赵小亮蹲在路边的道牙上。我说,赵小亮,过来,你俩站一块。
赵小亮好像闪了腰,扶着胯骨走过来,和女人站在一块。我往后走了十多米,朝他们喊,别动,站在那儿别动。
我掏出兜里的两个小花炮,放在路边的铁皮垃圾桶上,点燃,黑暗的天色变得亮了些,一圈一圈的彩色光晕往四处弥漫,小炮管扑射出电火花,在有限的空间里灿烂地纷飞,雪斜下来,落在地上啪地绽开,把十字路口映得透亮。
我用力向他们挥手,直到火花熄灭。
赵小亮在背后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烟花。
的确,许多年没见过这么美的烟花了。
回到家,媳妇已经睡熟了,我从背后抱着她,媳妇转过来,说,又喝了?我说,赵小亮非喝。
媳妇说,钱呢?
我说,过几天给。
媳妇揉揉眼睛,说,没让你真要,等他以后有了再说吧。
我亲了媳妇一口,她眯着眼睛笑,说,来,生活一下。我关了灯,把她按在床沿上,媳妇说,你能行吗?
我堵住她的嘴,说,就这么回事。
过了一个多月,赵小亮打电话请我吃饭,我说,拉倒吧,我请你。赵小亮说,贷款批下来了,趁这次机会,打个翻身仗。我们约在城西的农家乐,没叫别人,就我俩,我说,就俩人你整这出干啥。
赵小亮说,工人工资给结了,爽快。
我说,行。
赵小亮打开了卡拉OK,点了一首《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唱了两嗓子,有进步,唱的时候,还似乎流了几滴眼泪。
我说,赵小亮,你那位呢?
赵小亮说,哪位啊。
我说,装啥,那位。
赵小亮说,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
我说,说啊。
赵小亮说,说了啊,就刚那句歌词。
我说,你那天脸到底咋回事?
赵小亮说,她在医院给女儿看病,我说给她儿子换尿布,结果被他拿尺子划拉了一下。赵小亮把声音调到最大,震得耳朵疼,我朝他喊,你了解她吗?
赵小亮没说话,一遍一遍地唱。
我从玻璃棱镜里看见,赵小亮又掉了几滴眼泪,我说,你别哭啊,这有啥的,那个女的人挺好。
赵小亮冲着话筒喊,都过去了,就这么回事。他跟我间隔十米,我看见他手里攥着一个东西,他张开手掌,蓝球10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