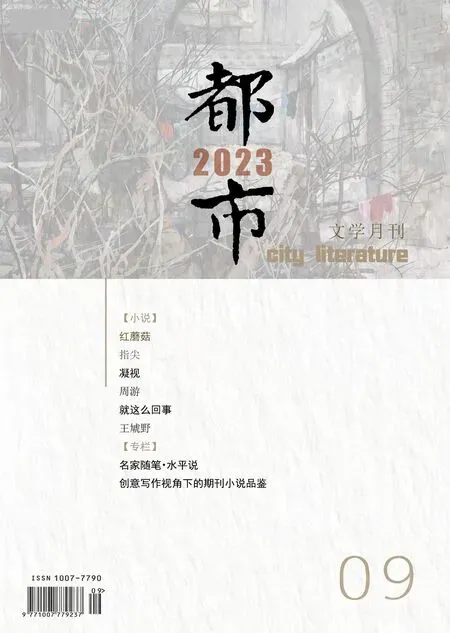童话创作的门道
——读莫言《小亲疙瘩》
○张敦
作家莫言在2023 年6 月的《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童话,题目为《小亲疙瘩》。我读完后,感觉很有意思,可以聊一聊。主要聊两个问题:一是童话应该怎么写,二是童话不应该怎么写。
《小亲疙瘩》的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位独居的老婆婆,无意间把自己的血抹在一根破旧的炊帚疙瘩上,让这炊帚疙瘩有了生命,变成了一个袖珍的小孩。老婆婆家受到黄鼠狼的骚扰,小疙瘩和老婆婆并肩战斗,打退黄鼠狼的多次进攻。最后,黄鼠狼被打退,小疙瘩也被撕碎,失去了生命。
童话故事,是想象力的结晶。当然,我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需要想象力,只不过童话作品尤其需要你的想象飞得更高一些,尤其是要有“独特的创意”,作为故事的基础。如果没有好的创意,童话故事就不成立。翻看安徒生的童话集,你会发现他的每个作品都有极好的创意。比如总会作为开篇故事的《打火匣》,其创意是打火匣和那三条大狗——只要一打火,狗就出现,为你实现愿望。
莫言的这篇童话,有两个创意:一是炊帚疙瘩有了生命;二是黄鼠狼会说话。可以说,只要想好这两个创意,故事基本就成了。我觉得,莫言的创意是不错的,将炊帚疙瘩和黄鼠狼拟人化,够独特,尤其是炊帚疙瘩成精的创意,我是第一次看到。而且,也非常“中国化”,带有鲜明的中国北方民俗特色。
那么,好的创意从何而来呢?首先,肯定是来自现实的生活,不要凭空去想,你的创意,一定要与你有关。从前的农村,谁家都有炊帚。莫言要写童话,他的思绪在童年的老屋里翻腾跳跃,最终落在灶台上那把不起眼炊帚上。那种炊帚,是高粱穗扎的,并不耐用,用久就秃了,会被人随手丢弃。如果这个炊帚疙瘩成精了,会怎么样?莫言的想象由此出发,构建出整个故事。
还有个问题,那就是童话故事如何解决超现实情节的逻辑问题。很简单,为你的故事建立一个自身内部的逻辑。这个逻辑不可忽视,肯定要有,没有就显得虚,不讲道理。莫言不会简单地写炊帚疙瘩突然就成精了,他会先设定一个逻辑,让这个变化说得通。因为老婆婆的血抹在炊帚疙瘩上,所以炊帚疙瘩就变成小男孩了。这个逻辑独属于这个故事。还有黄鼠狼会说话的创意,莫言也不是平白无故地让它们说话,而是说黄鼠狼是因为听人言听多了,学会了说话,而且说的都是“大词”,让人讨厌。
如果实在想不到新鲜而独特的创意,还可以到别人那里“借”。光安徒生一个童话作家,为后世提供了多少创意的模板。《拇指姑娘》中花盆里长出来的小姑娘,《夜莺》里那只能唱出最美妙歌声的鸟,还有《小益达的花儿》中会跳舞的花……这些创意都可以与我们自己的经验结合,生成新的创意,从而构建出我们自己的童话故事。
创意有了,故事如何展开?这时应注意,矛盾冲突必须跟上,要相信孩子们的接受能力,他们需要的是热烈和精彩,而不是温暾和矫情。在《小亲疙瘩》里,莫言让小疙瘩和黄鼠狼大战多次,直到最后被撕碎。而且,这篇故事的结尾,莫言也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小疙瘩有没有成功复活,他把想象的空间留给了读者,这是非常高明的写法。
下面说第二个问题,童话不该怎么写。这个问题是我陪女儿看动画片,阅读童书和儿童杂志后想到的。我觉得,当下有些童话作者的写作太不用心,非常偷懒,在故事创意层面毫无新意,也不考虑逻辑问题。你是不是读到过这样的故事:小猫早起去上学,到校门口见到狗老师,又碰倒鸭子同学,还有小熊同学……这类故事,只是把该是人名的地方换成了动物,就披上了童话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发表了。
如果童话可以这样写,那么就太容易了,不需要费尽心思搞什么创意了,只要随便找一篇小学生的作文,把里面的人名换成动物,就成了。我觉得,这样写很没意思,童话就不该这样写。我们看安徒生的童话《坚定的锡兵》,锡兵有了自己的思想后,仍然是一个玩具。还有《丑小鸭》,丑小鸭的生活环境就是野外和农场,它所遇到的鸡鸭鹅也都是真正的鸡鸭鹅,只不过安徒生让大家都会说话了。《拇指姑娘》里小女孩遇到的燕子、田鼠和鼹鼠,都做着他们本该做的事。
莫言的这篇《小亲疙瘩》,黄鼠狼成精后,还是会偷鸡,会放大臭屁。小疙瘩变成人后,仍是很小,用袜子当睡袋,火柴盒当枕头。小疙瘩要与黄鼠狼战斗,他用的武器是老婆婆的缝衣针。最后,他还是会被黄鼠狼撕碎,因为他本来就是炊帚疙瘩。
所以我认为,写童话故事时最好遵循一个原则:万物可以具备人的特质,还仍要保留其原有的特质。如果反着来,把人变成动物,也要让人具备该动物的特质。
最后说一点,莫言在题为《为孩子写个故事》的创作谈中写道:“我认为好的童话故事里对坏的人物或动物往往有一种‘道德宽容性’,也就是说,童话故事里的坏人或坏动物,往往不似成人文学里的形象那样复杂。”
毫无疑问,这是经验老到的创作者的真知灼见,他是这样思考的,也是这样写的。在他笔下,作为反面角色的黄鼠狼就没那么坏,他们捣蛋之余,还会相互打闹,有其可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