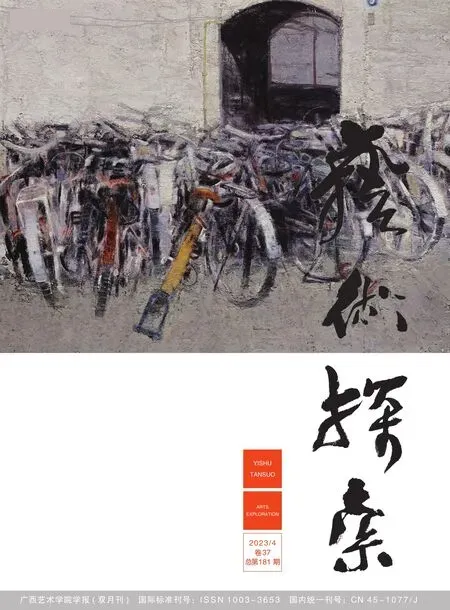明清南曲谱收录、辨改明人散曲情况分析
——兼论曲谱编纂者的意图与心态
刘英波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在中国古代曲谱制作史上,明清时期是曲谱发展的兴盛期,出现了《太和正音谱》《南曲全谱》《南曲九宫正始》《南词新谱》《北词广正谱》《钦定曲谱》《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南词定律》等一批影响较大的曲谱。在南曲发展、兴盛的过程中,南曲谱得到了长足发展,如《南曲全谱》《南曲九宫正始》《南词新谱》《南词定律》便是明清时期颇具影响的南曲谱。这些南曲谱中存有丰富的曲学文献,其中散曲是曲谱中收录较多的曲体之一。关于明清南曲谱中散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学界多是借助曲谱所收散曲做了一些辑录、校释、补遗等方面的工作,对其中所收散曲数量变化特点、宫调曲牌的辨改以及相关现象发生的原因等涉及较少。本文选取明清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南曲谱作为考察对象,在梳理、统计其中所收明人散曲数量变化、宫调曲牌辨改情况的基础上,探究这些现象蕴含的原因与意义,兼论曲谱编纂者的编纂意图与心态,以期有助于认知与理解明清南曲谱所收明人散曲情况及相关问题。
一、南曲谱所收明人曲家、曲作数量及相关问题考察
基于南曲谱的实际状况与问题考察的需要,我们选取《南曲全谱》《南词新谱》《南曲九宫正始》《南词定律》四部不同时段的南曲谱作为考察对象。①沈璟《南曲全谱》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出版(徐朔方观点)、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以前成书(周维培观点),沈自晋《南词新谱》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 年)刊刻(俞为民观点),徐于室与钮少雅《南曲九宫正始》于顺治八年(1651 年)得以定稿(钮少雅标注时间为“大清顺治辛卯”的《自序》中云:“计前后共历二十四年,易稿九次,方始成之。”),吕士雄等辑《南词定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成书。我们之所以未选“现存完型南曲格律谱中最古老的一种”即蒋孝编纂的《旧编南九宫谱》,原因是该曲谱收录的86 首散曲中可稽考出作者为明代曲家者仅唐寅的[月儿高]一首,不便比较,因而未把它列为考察对象。不过,由蒋孝《南小令宫调谱序》中云“余遂辑南人所度曲数十家,其调与谱合及乐府所载南小令者,汇成一书,以备词林之阙”,结合南散曲的发展、兴盛特点,我们认为《旧编南九宫谱》中所收的86 首散曲中应有明人散曲,但一时不能稽考出来,以待后补。为了清楚地了解南曲谱所收明人散曲的基本情况,我们对四部曲谱所收明人散曲的宫调、曲牌、曲作数量予以梳理、统计。(见表1)②在所选的四部南曲谱中,由于《南词新谱》对所选明人散曲标注作者的较多,而《南曲全谱》《南曲九宫正始》有的注明作者,有的未予标注,《南词定律》均未注明作者,因此我们在确定《南曲全谱》《南曲九宫正始》《南词定律》中的明人散曲及作者时,参照《南词新谱》注明作者的资料。另外,表中所列明代曲家,陈子龙于《全明散曲》《全清散曲》均收,据其生卒年(1608—1647 年),这里视为明代曲家;沈自晋(1583—1665 年)、沈自继(1585—1651 年)被收入《全清散曲》,这里依据他们生活时段多在明代,明亡后均隐居山林,且明亡后他们的情感仍倾向明朝,故把他们归入明代曲家统计。
根据表1 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各南曲谱之间所收有名姓可计的明代曲家曲作的数量不一:《南曲全谱》收7 人16 首,《南词新谱》收30 人107 首,《南曲九宫正始》收10 人25 首,《南词定律》收17 人45 首,与之相应的是,各曲谱所收曲作宫调、曲牌的数量也存在明显差别。这其中的差异及原因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析。
(一)明代散曲的发展与曲家曲作的收录
结合明代历史时段与文学发展的基本状况,根据我们对明代散曲曲家曲作数量的统计及散曲创作的实际分析,我们认为明代散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成化、弘治以前基本处于低谷期,包括由元入明的16 位曲家在内,此时段可统计的曲家数量约有26 人,存曲810 多首;成化、弘治期间稍有起色,曲家数量约有32 人,存曲830 多首;正德、嘉靖间则蔚为大观,可计曲家约101 人,存曲3 730 多首;随后隆庆、万历间达到鼎盛期,约有曲家108 人,存曲4 000 多首;天启、崇祯间有所衰落,约有曲家33 人,存曲600多首。③关于明代各时段曲家、曲作数量统计,参阅刘英波《明代中后期南、北方散曲比较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的《附录》部分。需要说明的是,2013 年以前学界增补的明代散曲家及其曲作数量,该论文已经统计在内,近年来虽有少量增补,但不影响我们对明代散曲发展趋势的认识。而南散曲的兴盛与成熟则是在嘉靖年间魏良辅昆腔改革之后,与明代散曲的发展态势大体一致。据表1 可知,各曲谱中所选曲家的生活时段与曲作数量绝大多数集中于正德、嘉靖(含)以后,这表明明代散曲(南散曲)发展的兴衰状况影响了曲谱的选录情况。由此看来,散曲的发展状况影响曲谱对曲家曲作的选录,而依据曲谱选录曲家曲作的情况可以了解散曲发展的基本态势,二者之间呈现出促进与制约共存的互动关系。
(二)选录标准与曲家曲作的收录
在影响南曲谱选录曲家曲作的因素中,选录标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譬如《南词新谱》,沈自晋奉行“一人有一人手笔,一时有一时风气”的思想,在选录曲家曲作时,“凡有新声,已采取什九。其他伪文采而为学究,假本色而为张打油,诚如伯良(王骥德)氏所讥,亦或时有特取,其调不强入,音不拗嗓。可存以备一体者,悉参览而酌收之”,他还说:“词家作曲而每讳之,或曰无名氏,或称别号某以当之。嗟乎!曲则何罪而讳之若是……曲何负于我,而藐忽视之也哉。然则先词隐于诸集中,每称无名氏以相掩覆,亦复未能免俗耳,今悉改正而表其姓氏云”,[1]34-36反映出沈自晋与时俱进的选曲观念和尊崇曲体的进步曲学思想。因此,《南词新谱》选曲在关注前人曲家曲作的同时,十分注重时人曲作的收录,且尽量标注曲家的姓氏,相较于沈璟“隐于诸集中,每称无名氏以相掩覆”的做法,除了彰显二者曲学观念与选录标准的差异外,也为我们说明了《南词新谱》所收明人曲家曲作数量多于《南曲全谱》的原因。除此之外,由于沈璟编纂曲谱时可供借鉴的资料相对较少,“多从坊本创成曲谱,致尔后学无所考订”[2]1390,这也是《南词全谱》收曲数量少于《南词新谱》且很少标注曲作作者的原因。
(三)曲谱编纂的延承性特点与曲家曲作的收录
从沈璟《南曲全谱》对蒋孝《旧编南九宫谱》的借鉴,沈自晋《南词新谱》对《南曲全谱》的继承等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前人曲谱的延承影响了后人编纂曲谱时对曲家曲作的选录。如沈自晋编纂《南词新谱》时,虽然“搜讨”“采取”了不少当时出现的“新声”,但他一再强调“先词隐三尺既悬,吾辈寻常足守。倘一字一句,轻易动摇,将变乱而无底止。作聪明以紊旧章,予则何敢”[1]27,表明自己遵从沈璟所纂《南曲全谱》的体例、选曲等。由表1 所见这两种曲谱所选曲家、曲作的交叉状况也可以看出,《南词新谱》对《南曲全谱》的继承十分明显。再如,《南词定律》相较于《南曲九宫正始》继承《南词新谱》中所收曲家、曲作的数量较多,因为《南词定律》是在兼采以往曲谱的基础上完成的,且得力于胡介祉的《随园谱》较多,而《随园谱》为增补《南词新谱》而成,仍属沈璟曲谱的裔派。④参阅周维培《曲谱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172-173 页。至于《南曲九宫正始》承继《南词新谱》相对较少的原因,与曲谱编纂者“词曲始于大元,兹选俱集大历、至正间诸名人所著。传奇数套,原文古调,以为章程,故宁质毋文。间有不足,则取明初者一二以补之。至如近代名剧、名曲,虽极脍炙,不能合律者,未敢滥收”[2]17这一“崇元”观念指导下的选录原则密切相关,从表1 的统计也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延承关系。
(四)曲家地位及与曲谱编纂者的关系影响曲家曲作的选录
由表1 统计的情况来看,四部曲谱所收的明人曲家,绝大多数在曲坛上颇具影响,如陈铎、唐寅、文征明、梁辰鱼、沈仕、金銮、沈璟、王骥德、冯梦龙等。王骥德在《曲律·杂论》中云:“近之为词者,北词则关中康状元对山、王太史渼陂,蜀则杨状元升菴……南则金陵陈大声、金在衡,武林沈青门,吴唐伯虎、祝希哲、梁伯龙,而陈、梁最著。……余未悉见,不敢定其甲乙也”[3]162,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些曲家的地位及在当时的影响。虽然王骥德没有提及自己与后出的曲家冯梦龙,众所周知他们二人亦都是闻名于时的曲家。选录有地位、有影响的曲家曲作,应是考虑到他们通晓音律、创作的曲作既合乎格律又颇具文采,如时人评价陈铎的曲作:“其韵严,其响和,其节舒,词秀而易晰,音谐而易按。言言蒜酪,更复擅场”[4]743,因此其被称为“作家”“乐王”[5]36。同时,选录名家曲作便于读者学习接受,利于扩大影响也是考量的因素。曲谱中还收录了一些名望不著的曲家,譬如《南词新谱》中的赵宽、张积润、沈瓒、沈珂、沈静专等。这应与沈自晋“以备一体”的选录目的有关,同时沈自晋与这些曲家的关系也是值得考察的一个层面。如赵宽的【锦春堂】(目前所知他仅存此曲),仅《南词新谱》予以收录,其他三种曲谱均未收录,后出的《钦定曲谱》等也未见收录。沈自晋在所录赵宽曲作的页眉处标有小注:“冯(梦龙)录一旧曲,予易此词”[1]201。此曲作的音律、词采并没有特别之处,而且赵宽主要生活于成化、弘治年间,与沈自晋根本不在同一历史时段,似乎无法解释沈自晋为何改换冯梦龙的例曲。但考虑到赵宽是吴江人,与沈自晋为同乡,我们便大胆猜测沈自晋选录赵宽的曲作很有可能是崇尚本地先贤的情愫起了作用。这种推测并不是没有依据,《南词新谱》收录吴江沈氏20 位曲家的戏曲与散曲曲例⑤关于《南词新谱》收录吴江沈氏曲家曲作情况,参阅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137 页。以及吴江同乡吴古还、尤本钦、外甥顾来屏(昆山人)等多人的曲作,这一事实促使我们做出这一推测。沈自晋这种大量收录本族、同乡曲家曲作的行为有提携后学、显示沈氏及其周围曲家实力的目的,其中具有内隐特点的家族血缘、乡土情怀也起到了较大作用,客观上为我们保存下了丰富的曲学文献。
二、南曲谱对明人散曲宫调、曲牌辨改解析
通过对四部南曲谱所收明人曲家、曲作的梳理、统计,我们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所收曲家、曲作数量的变化上,还表现在对所收曲作宫调、曲牌的辨明、改动上。
(一)辨明宫调、牌名
《南曲九宫正始》所收张凤翼的小令【南仙吕·九回肠】二首其一:
【解三酲】一从他春丝牵挂。到如今多少嗟呀。秋波望断蓝桥下。锁春山又阻巫峡。音书未托鱼和雁,凶吉难凭鹊与鸦。成话靶。【三学士】当时镜里花难把。更那堪尘掩菱花。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黄龙衮】只索向无人处,把鲛绡看。【风入松】盟言在,不觉泪如麻。[2]353-354
《南曲全谱》《南词新谱》均收录了此曲,曲牌标为【九回肠】,并于曲牌下标注“用仙吕、南吕、双调”,且归于“不知宫调及犯各调者”之列。其中,曲牌【黄龙衮】为【急三枪】,未有【风入松】曲牌。《南曲全谱》在所收此曲后面标注:“ 【急三枪】即在【风入松】后,如《琵琶记》:‘他去空山里,把裙包土血流指,感得神明助与他筑坟台’几句也。今世相传为【急三枪】,但旧谱未明开耳”[6]91,但未予考述、厘清。《南曲九宫正始》把它归入仙吕宫,不像前面两谱所注“用仙吕、南吕、双调”,而是改其曲牌名为【六花衮风前】,改【急三枪】为【黄龙衮】,添加曲牌【风入松】,并给予了考释说明:
此调今俗名曰【九回肠】,盖因首词有【解三酲】,腹中乃【三学士】,束处错谓是【急三枪】,共得九数,故取其名,不知《元谱》何曾有【急三枪】。按《元谱》古传奇每于【风入松】套间有此二段不曰【急三枪】,皆名【犯衮】,甚至犹有【犯欢】【犯声】之类。余今亦于【仙吕入双调】谱中,【风入松】后注得其详。然此【犯衮】之全章共有八句,其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句皆犯【黄钟宫】之【黄龙衮】,其第四及末句仍为【风入松】,故曰【犯衮】也。今本,曲末【煞】止用得其下半截,今人不识其义,妄起【九回肠】之名。谬甚。[2]354
在此段文字中,《南曲九宫正始》介绍了曲牌被称为【九回肠】的由来,按照元代曲谱,“古传奇每于【风入松】套间有此二段”,但不叫【急三枪】,而是称为【犯衮】,或称【犯欢】【犯声】,并简单说明了【犯衮】的句式特点及其为何称为【犯衮】,最后指出时人称呼【九回肠】是非常错误的,具有正本清源的特点。关于【犯衮】,徐于室、钮少雅在【仙吕入双调·风入松】后面,借助例曲描述自己是如何发现问题的,并介绍【犯衮】的特点,[2]1034-1035再结合上文,加深了我们对此曲牌的认识。
(二)辨明曲牌
祝允明南套曲《月景题情》的支曲【油核桃】:“论夏月可人心性。对莲池红妆临镜。柳梢头才上天街静。却早人约黄昏。”[7]880《南曲全谱》《南词新谱》《南曲九宫正始》均收录此曲。在《南词新谱》《南曲全谱》中该曲曲牌标为【油核桃】,且标注“油核桃,或作油葫芦,非也”[1]138,[6]116,只是点出问题,并未予以考述、辩正。而在《南曲九宫正始》中,改【油核桃】为【孤飞雁】,且交代了改为【孤飞雁】的因由:
此调按元谱一名【孤飞雁】,又名【油葫芦】,乃一词二名也。今因罕识,多谓此【孤飞雁】,与【油葫芦】各为一调。致以祝枝山“金盘玉饼”套之“论夏月”,四字皆于首句之衬字上妄加一掣板,又于第三句“柳梢头”之“柳”字上点一正板,焉有虚文实板乎?况时谱亦效之,且又讹为【油核桃】,而又误置于仙吕宫。余今试以此曲依律按调,剖分正衬,详备一阕于下,而证向来之谬。[2]1110
在此段话中,《南曲九宫正始》的作者通过稽考《元谱》,认为【孤飞雁】【油葫芦】实为一调,后来因为人们不熟就里,便分为二调,而时谱又将其误为【油核桃】,同时,还谈到了点板方面的错误。这种辨析既可“证向来之谬”,又使我们认识牌调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更改曲牌归属与曲牌名
《旧编南九宫谱》与《南曲全谱》均未收录【三仙序】曲牌及其例曲,沈自晋《南词新谱》收录自己的曲作《三仙序》,并注明“新入”,归于【南正宫】名下,而吕士雄等人编纂的《南词定律》则将其归在南吕宫名下。我们查考《新定九宫大成南词宫谱》,它把【三仙序】收于南吕宫名下,而《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钦定曲谱》均未收录此曲牌。由此,我们认为【三仙序】为沈自晋新创曲牌,因其尚属草创期有可能被归错宫调,后出曲谱的编纂者经考订后将之归于南吕宫。又,《南词新谱》收录沈自征的曲作《新样四时花》,标识“不知宫调及犯各调者”,《南词定律》中却标明该曲属于“正宫犯调”,而且曲牌改为【四时八种花】,《新定九宫大成南词宫谱》收【四时八种花】于正宫,《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钦定曲谱》未收。究其原因,这应与沈自晋收入自己所作【三仙序】的情况大致相同,也属新创之作,后出曲谱收录时予以考订后明确其所属宫调。而且,其中以八种花名作为曲牌名,更改为【四时八种花】是比较合理的。
通过对曲谱所收曲作宫调、曲牌变化的梳理,我们认识到时人在称谓、使用牌调时,因标准混乱或不够严谨,以致“各以耳目所见,妄有述作,遂使宫徵乖误,不能比诸管弦”[8]4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便促使通晓音律的曲家积极编纂曲谱,以纠正时弊、规范曲坛。但是,毕竟当时可资参考的资料较为有限,且有些工作尚属首创,以致“多从坊本创成曲谱,致尔后学无所考订”[2]1390,难免出现疏漏,属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为后出曲谱提供了修改、完善的空间。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宫调、曲牌的变化与当时的文化场域是分不开的,其中有所改动的曲作多为集曲作品,而集曲是明代中后期曲坛兴盛后的衍生品,加之人们对待曲体既不屑却又热衷、赏听的矛盾态度等,缺少严谨的治曲态度,所以创作中出现宫调、曲牌使用混乱不拘的现象无法避免。《南词定律序》中的一段话:“至九宫之过曲、犯调,多采诸传奇、散曲,引子多采诸诗余,其中有精有确,有俚有文,总因操觚者不屑与梨园共议,而梨园中又无能捉笔成文,遽自著作是以苟延,至今终不能令人开卷一快”[9]7-8,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个中原因。
我们并不否认创新,正是勇于创新才迎来了明代中后期曲坛的繁荣,可是为了出新而出新则会影响对待事物的严谨态度,而过于拟古,一味尊奉前人的观念、范式则会故步自封,对于“度”的掌控有时很难做到恰到好处。譬如,上文所举沈自晋的《南词新谱》对本人、沈自征等许多新曲的收录,虽说他想“取舍各求其当,而宽严适得其中”,但为了“以备一体”而“参览酌收”的标准则相对宽松,[1]33-34,加上出新、求变的动机,很难不出差错。又如,《南词新谱》对张凤翼曲作《九回肠》的收录,它完全继承沈璟的《南曲全谱》,未对存疑问题细加考订,所以给《南曲九宫正始》提供了订正、阐释的空间。至于《南曲九宫正始》崇尚“元音”,以《元谱》考订后出曲作宫调、曲牌使用的正误,常常诘问“时本”之“谬误”“坏体”等,但有时因为过于强调遵从前人的体例与范式,以致出现“一味以《元谱》为是,拘泥刻板,不注意南曲格律的历史变化”[10]179的情形,如上文所举《南曲九宫正始》对【急三枪】的考订,对《南曲全谱》新入集曲牌调【山渔灯犯】的考订并改称【天灯魚雁对芙蓉】的现象,等等。对于这类改动与评价现象,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它毕竟是一种传统曲学观念的呈现,有其个性特点,一定程度上还能纠正创作、演唱中的偏误,但也不能全盘接受,因为其保守、泥古的思想会扼杀一些新鲜的活力,影响格律、创作方面的创新。以开放、谨慎的态度予以批判地接受应是我们对待这类现象的正确姿态。
三、南曲谱编纂者的编纂意图与心态
“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1]247在南曲谱的编纂过程中,对明人散曲的收录与辨明、改动宫调曲牌行为的发生,也是有“意图”与“目的”的活动,而这些“意图”“目的”的存在与编纂者的文化心态密不可分。
崇古与创新。人们的崇古心态由来已久,如《诗经·烝民》云:“古训是式,威仪是力”,而且这种心态影响深远,历久不衰。曲谱编纂者屡屡提及“崇尚源流”,不断追攀“风骚”“大雅”的行为,应是崇古心态渗透后的表现。譬如,徐于室、钮少雅编纂《南曲九宫正始》,为了说明自己编纂曲谱的依据是“汉唐古谱之源”,在《自序》中不惜用神化之笔交代曾得到一王姓老翁的传授,又说见到一汉唐古谱,而且编纂曲谱时常以《元谱》为尊,选曲实践中坚持“兹选俱集大历、至正间诸名人所著传奇数套。原文古调,以为章程,故宁质毋文……至如近代名剧、名曲,虽极脍炙,不能合律者,未敢滥收”[2]17,以致出现了上文提到的“拟古不化”的情形,即与崇古、慕古的心态密切相关。其实,沈自晋在《凡例·禀先程》中所说的“先词隐三尺既悬,吾辈寻常足守”,也是崇古思想影响下尊崇先人旧制的一种态度与表现。可喜的是,沈自晋较之徐、钮二氏的编选要灵活得多。虽然《南词新谱》对《南曲全谱》继承许多,但它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在择调、选曲、评注等方面均有突破。他在编纂过程中做到了继承中有所创新,正是其编纂曲谱的价值所在,也因此赢得了时人与后人的赞许。《新编南词定律》《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曲谱虽然各有优缺点,但也均是在继承与创新中建构而成的。
崇古与创新不只是为满足慕古心态及呈现与众不同的新意,也与曲坛“妄有著述”“宫徵乖误”的状况密切相关,因此编纂曲谱还有纠正时弊、规整曲坛的目的与意图。如蒋孝编纂《旧编南九宫谱》感叹“大雅不作”,乃“汇成一书,以备词林之阙”;[8]4,5-6吕士雄编纂《新编南词定律》有感于“岁月既久,不无好奇穿凿之弊,或以正字外多加衬字,正体外作为犯体,九宫之谱迭兴,各出臆见,不能画一。填词家正衬既尔淆讹,度曲者板拍岂无舛错耶!”试图通过编纂曲谱纠正“淆讹”“舛错”之弊,“使填词度曲者,开卷瞭然”。[9]15,16在纠弊、规范的同时,曲谱编纂者还表现出文化传承者的担当心态。这种担当有的是个体主动行为,如蒋孝《旧编南九宫谱序》云:“是集也,余实有俟于陈采,以充清庙明堂之荐。彼訾以为慆湮心耳之具者,斯下矣”[8]6-7,表明自己编纂曲谱有“充清庙明堂之荐”的意图。还有的与统治阶层的教化意识密切相关,如成书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的《新编南词定律》便是一部带有官谱性质的曲谱,为当时宫廷御用文人通力合作的产物。⑥周维培《曲谱研究》(第172 页)中介绍:《新编南词定律》有内府刻本及香芸阁刻本,两种版本面貌相同,惟卷首序文,内府本题“恕园主人”,香芸阁本题“榖旦主人”。“恕园主人”是雍正帝胤禛即位前的自号。编纂该曲谱已不是个体行为,具有明显的政治教化色彩,正如榖旦主人《新编南词定律序》云:“至于传奇则声色俱备,实足动人,一咏一歌间,虽妇人女子、山童牧竖,无不欣然于忠孝、奸佞、善恶之间,或为赞扬,或为唾骂,面目虽假,啼笑若真,未尝不可以感激人心,助宣教化焉。”[9]3-4吕士雄也说:“予闻凤皇鸣而律吕谐,诗颂作而词曲生,皆所以调阴阳,宣教化也。乐府关乎世道,岂浅鲜哉。”[9]13其中“宣教化”的意图十分明显,与蒋孝“俟于陈采”的心态有所不同。这种编纂曲谱的行为与上层意识形态之间已经形成了“共谋”[12]215关系。这种“共谋”关系的组建具有主从特点,其目的不是通过曲谱选曲等表面行为来实现,而是通过编纂曲谱规范、推动戏曲艺术发展,并借助被输入意识形态的戏曲活动为载体实现教化民众的宗旨。这正是雍正帝欣然为《新编南词定律》题序的根本原因。
在曲谱中寄寓编纂者超然脱俗、抑郁不遇的复杂情怀。李鸿在《南曲全谱·原叙》中云:
(沈璟曰)吾固知吾之落落难合,然惟子与吾应答,如响世之所称同调。岂必取材异世,苟非漫然无当,自可悬书以俟知者。夫高山流水岂为子期发奏,苏门长啸岂为步兵遗响。吾与子不暇扣角以干时,亦和歌以拾穗,聊供适其适耳,又何虑之深耶![1]11-12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睹见沈璟落落脱俗的气质,以及追求“自适而适”的闲情雅趣。然而,从他“不暇扣角以干时,亦和歌以拾穗”的表态,我们亦体悟其隐匿于内、不合时俗的磊磊郁气。由此,我们认为沈璟编纂曲谱有实现自身价值、彰显自我风趣的意图,也有“解愠襄《九叙》《九歌》,韵严周子《中州》,反骚夺《九怀》《九辨》”[1]17的深刻寄寓之意,显示出其编纂意图的复杂性。事实上,沈自晋继沈璟之后,编纂《南词新谱》也有深切复杂的情怀蕴含其中。沈自晋身处明清鼎革之际,目睹兵祸惨烈,深感世事沧桑。曲谱编纂完成后,他与儿子沈永隆言及往昔志向,而“转眼沧桑,功名灰冷,秦淮明月与烟雾同销,玉树清歌并悲笳互奏,能不顾怀周道伤心昔游”,以至“泪且交下”。[1]912其中的悲苦、孤独、感慨、不平等复杂的弦外之音,却是我们难以从曲谱内容中体悟的。
不仅如此,沈璟、沈自晋编纂曲谱还表现出弘扬区域文化与提携后学的意图与心态。沈璟辞官归乡后,“隐于震泽之滨,息轨杜门,独寄情于声韵。常以为吴歈即一方之音,故当自为律度”[1]7,他认为“吴歈”为“一方之音,故当自为律度”的思想,蕴含着对兴盛于吴中一带、具有乡土特色的昆曲艺术的认同与期许,并想通过“采摘新旧诸谱”“益广之俗”编纂成书,实现规整、促进、弘扬地方文化的目的。沈自晋继沈璟之后,除了继承其衣钵,传承具有地域性特点的文化艺术外,他还具有提携后学、弘扬家学的心理。前文提到沈自晋在《南词新谱》收录20 位沈氏曲家的曲作,同时还收录了许多当时参与校阅曲谱的外姓人氏以及吴江本地与之有亲属关系的曲家曲作,便是这一心态的具体体现。另外,我们认为沈自晋对这些曲家曲作的选录可能还有一种微妙的动机,即以此表达对他们参与校阅曲谱辛劳工作的认可。
南曲谱的存在既是对传统曲学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曲学发展的一种规范。其中,对明代曲家曲作的选录及对宫调曲牌的辨改与考述是多重因素影响制约下的一种文化建构活动,蕴含着编纂者纠弊、规范、传承、教化的目的,崇古、创新的意图以及磊落、娴雅、郁愤、悲慨的复杂情感,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