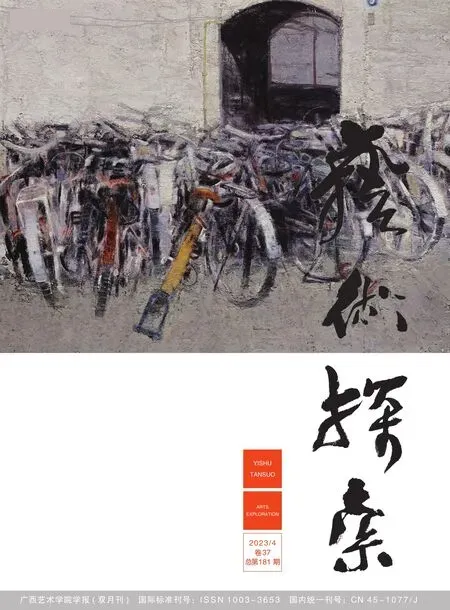“旋宫转调”谬说再辨
刘永福
(扬州大学 音乐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自古以来,由于受阴阳五行、周易八卦、天文星象等谶纬之学的干扰和误导,“并不十分复杂的古旋宫问题”,“被弄得复杂万端、无人能通”。[1]122为解决历史疑案,还原旋宫古法之本义,黄翔鹏先生根据曾侯乙钟乐律铭文及其他史料记载,同时结合近现代以来的乐调实际,对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旋宫转调”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提出了“两个概念”的理论,并将其作为《旋宫转调》条目内容 写进了《中国音乐词典》。黄先生指出:
“旋宫转调”一词,对于不熟知传统乐律学的人们说来,往往单纯把它理解作:调高的变换——宫音位置在十二律中的易位。其实“旋宫”与“转调”应该是两个概念,“旋宫”指调高的变换,而“转调”指调式的变换……这一点,对于大小调体系的欧洲音乐,没有太大的区别意义,对于自古至今始终是多调式体系的中国音乐说来,实在有严格区分的必要。[1]110
正因为黄先生认识到了中国传统音乐所具有的“多调式体系”这一基本特征,故而明确强调了“两个概念”划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黄先生“‘旋宫’与‘转调’应该是两个概念”的内涵界定,虽然不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却消除了学界长期在此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构建中国传统宫调理论话语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旋宫之图”中的“旋宫转调”之谬说
杨文说:
古代所谓“旋宫”,往往都是结合旋宫图或直接在十二律管上进行。熊朋来《瑟谱》“旋宫之图”后有说明,谓为“以宫字加所用律,则商角徵羽皆定”。朱载堉在其“十二律吕旋相为宫之图”下面有类似说明,谓为“何月之律为宫,即将内层宫字转于本月之上,则知某律为商、某律为角,余皆仿此”。……唐代《乐书要录》对顺旋的表述为“旋相为宫法,从黄钟起,以相生为次,历八左旋”,在所列乐调表后又说“十二宫尽中吕,中吕生黄钟,又起黄钟,终而复始”……所谓“旋相为宫”中的“宫”,表面上的确是指宫音,即《中国音乐词典》“十二律轮流作宫音”。……但是“十二律轮流作宫音”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形成不同的调高”。[2]48
在杨文看来,“形成不同的调高”是古代还相为宫之法的主要目的,如此一来,包括唐代《乐书要录》中的“旋相为宫法”以及朱载堉的“十二律吕旋相为宫之图”在内的古代文献,统统与《中国音乐词典》中的“旋宫转调”概念无关。如果杨文说的是史实,无论是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还是朱载堉“新法密率”,都将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因为,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周代就已经有了七声音阶和十二律,新音阶形式在春秋时代也已经出现[3]88,“形成不同的调高”早已不是什么理论难题,根本无须历朝历代的乐律学家们在所谓这一问题上进行反复论证和探索。随着十二律和七声音阶的广泛运用,想必调高问题早已解决,不至于到了清代还为“形成不同的调高”而绞尽脑汁,否则,先秦时期就已产生的十二律也就真的毫无价值可言了。因此笔者认为,唐代《乐书要录》中的“旋相为宫法”,并非旨在“形成不同的调高”那么简单,朱载堉的“十二律吕旋相为宫之图” 也不只是为“形成不同的调高”而创制。至于“以宫字加所用律,则商角徵羽皆定”,主要强调的是宫的定调作用,同时揭示了商角徵羽各声的律高转换。即使“十二律轮流作宫音”的目的就是“形成不同的调高”,那么“形成不同的调高”的目的又是什么?
不存在调高及调式的转换,“形成不同的调高”又有多大意义?可以肯定,京房“六十律”、钱乐之“三百六十律”、《乐书要录》中的“旋相为宫法”以及朱载堉“新法密率”,其真正目的就是从数理(学)的角度揭示和论证音乐实践中“还相为宫”存在的可能性。况且,唐代《乐书要录》及朱载堉《律吕精义》中对此说得既清楚又简洁,即“终而复始”“循环无端”。如果仅为“形成不同的调高”或“彼此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转换关系”,也就没有“终而复始”“循环无端”的必要。另要说明的是,由于记谱法等原因,古人不可能通过作品实例来详尽阐述“五声六律还相为宫”之法,只能通过旋宫图或文字形式来揭示“调关系”,以此证明旋宫古法的存在及其原理和方法,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两个概念”的依据。
二、“律声关系”中的“旋宫转调”之谬说
杨文认为:
凡是一个确定高度的声或调,都有其所属的均,都是某个均中的声或调……一律七声分别属于不同均中的七声,是七个均中的不同的七声。七声与其所在的均紧密关联,明确了某个声也就可以明确声之所在的均。实际上,旋相为宫即是按照这样的声、均关系,而以宫音作为七声代表用来表示调高的。一均有七声,除了宫音,其他各声也同样可以作为音列代表用来表示调高。[2]48-49
不难看出,杨文上述将均、宫、调三层次概念完全混同,将它们各自的功能属性扼杀殆尽,其目的仅仅是证明“旋相为宫”“旋相为声”“旋相为均”是一个概念。首先,如按杨文所说,五声(音阶)是没有声或调的,因为五声无法确立其所属的均。其次,所谓“七声与其所在的均紧密关联,明确了某个声也就可以明确声之所在的均”,完全混淆了整体与一般的概念关系。中国传统音乐有三种不同的七声(音阶),即使明确了某个声(如黄钟宫),也并不能“明确声之所在的均”,黄钟宫既可以是仲吕均,也可以是无射均,还可以是黄钟均。杨文以雅乐七声(古音阶)为正统,公然否定清乐七声(新音阶)的存在,从理论上讲,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从乐调实践的角度讲,根本不具有代表性,其观点不成立。另外,杨文不仅将律与声完全混同,而且彻底否定了“夫宫,音之主也”的理念和自古以来形成的以宫定调的传统。西方的“音列”术语虽然被国人借用一个世纪有余,但很少有人将宫、商、角、徵、羽等称为“音列”。因为大家知道,音列指的是有固定音高的音律,如C、D、E、F、G、A、B,而不是毫无音高标准作用的宫、商、角、徵、羽。关于律与声的关系,古人解释得十分清楚,即“十二律为定名,宫商角徵羽为虚位,故朱子审音之难,不在于声而在于律”[4]139。作为毫无音高意义的“虚设概念”,单纯的宫商角徵羽五声是无法“定均”的,当然也就不具备作为音列代表的资格。再次,以宫定调(高)是自古以来所形成的律声系统规则,具有无可辩驳的实用性和影响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简谱记谱法来说,长期统一使用的用以表示调高的调号为1(宫)=C 或1=D,而不是2=D 或3=E。早年虽偶尔出现6(羽)=D 的情况,也旨在强调调式类别(羽调式)和主音(D)高度,而不是为了指明调高,但这种现象早就销声匿迹。如按杨文所说的“其他各声也同样可以作为音列代表用来表示调高”,是不是意味着用以表示调高的调号可以随心所欲?4=F 或7=B 是不是也可以作为调号而存在?常言道:“没有规矩,何成方圆?”因此,代表音主和调高的音只能有一个,这就是宫及其所在的音律,否则,“夫宫,音之主也”的理念将无法得到体现。
由此可见,杨文将宫的调高作用转嫁给其他各声的做法,完全是在调高问题上制造混乱。从古至今也尚无一位理论家发表过此言论,相反却一致认为:“‘音主’的‘宫’,就相当于现今C 调、D 调中首调唱名之‘do’,乃是调高的代表”[5]121。如按杨文所说,宫以外的其他各声也能定调高,那么,被杨文作者推崇的“宫角关系”的实践来源、具体作用、实际运用[6]217-247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总之,其他各声皆由宫所定,而不是相反。关于宫的定调作用,很多古代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比如,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夫宫,音之主也”外,被学界公认的《管子·地员》所载“三分损益法”,即“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强调的就是宫的“音主”地位和定调作用。宫确定之后,才有徵、商、羽、角等其他各声的产生。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违背文献本义的恰恰是杨文,而不是黄翔鹏。
7.大力推进渔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突破性发展水产流通业和水产品加工业,引导鼓励加工企业加强技术改造和调整产品结构,开展产品深度研发,走精加工、深加工之路,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同时大力发展休闲渔业,着力培育休闲渔业创新经营主体,积极开展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创建。拓展营销渠道,积极推进订单水产、农超对接、直供直销、电子商务等新型水产品流通模式。
为进一步强调“旋宫”与“转调”是一个概念,杨文除了否定宫的调高作用外,还大谈“旋相为宫”与“旋相为声”之间的关系,指出:“旋相为宫主要是以声表示均,均中有声、有调;旋相为声主要表示所在律上的声、调,而声、调涉及所处的均,同样也可用来表示均。从都能表示均的角度论,旋相为宫与旋相为声二者是相通的、一致的,所以古代理论便以均的表达为主,将二者统一以‘旋宫’相称了”[2]49。但时隔不久,杨文作者又声称:“旋相为宫与旋相为声两种旋宫法与其所形成的乐调用何调名,本属不同层面,不可彼此相混”[7]5。而为了否定“两个概念”理论,此时却说“旋相为宫与旋相为声二者是相通的、一致的”。其问题是,既然是“两种旋宫法”,而且“调名”不同、“层面”不同,又“不可彼此相混”,为何不能属于“两个概念”?可见,杨文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理论说教很难令人信服。
三、“古代文献”中的“旋宫转调”之谬说
针对《乐书要录·论一律有七声义》中的逆旋表述,杨文也发表了一些极具“创造性”的观点:“‘旋相为宫’中的‘宫’,表面上说的是宫音,实质上是指以宫音为代表的作为七声整体高度的调高(均)。所谓‘旋宫’就是‘旋均’,‘旋相为宫’就是‘旋相为均’”[2]48。
关于“均”的概念,朱载堉早已作出明确界定:“律吕有十二个,用时只使七个是也。假如黄钟之均,则黄生林,林生太,太生南,南生姑,姑生应,应生蕤……又如大吕之均,则大生夷,夷生夹,夹生无,无生仲,仲生黄,黄生林……余均仿此”[8]928,另有“声生于律,律生于辰”“黄钟一均,惟用七律”[9]346,“七律者,黄钟一均之律也”[10]471等文献记载。可见,所谓“均”无疑指的是七个音律。如上所述,杨文所高调宣称的“‘旋宫’就是‘旋均’”,已与五声没有了任何关系,因为“五声是不能定‘均’的”[11]255。然而,《礼记·礼运》明确记载的是“五声之旋”,即五声音阶的旋宫,起码包含“五声性”的“还相为宫”。而杨文则一味以雅乐七声(古音阶)作为中国传统宫调理论的正统和唯一,将古代文献中的“旋宫”臆造为“旋声”,只承认“七声十二律八十四调”的“一律有七声”的“旋均”,而否定“五声十二律六十调”的五声范围内的旋宫。
令人费解的是,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杨文却大谈“旋宫转调”的出处及应用:“‘旋宫转调’之所以在清代使用,与‘转调’一样,也是与古琴上的转弦换调有关,而且常与‘转调’交互使用。这一术语也正是在琴调的转换中经常使用,并于琴调的转换中明确其概念含义的”,同时昭示学界:“清代王坦《琴旨》对‘旋宫转调’有一专门的阐述”,即“五声既以相生之声相转,则五调亦以相生之声相转也”。[2]49-50然而,无论杨文如何大谈王坦《琴旨》中的“旋宫转调””,以及为“五调间的转换关系”所列举的“旋宫转调之图”,都与“一律七声”无关,根本不存在“一律得七声”之说。因为,宫、商、角、徵、羽五声是琴调的定调基础,而且也是其“旋宫转调”之根本。如按杨文的“一律得七声”的“调高论”和“旋均说”推理,不仅五声无调高可言,而且被杨文一再推崇的王坦《琴旨》中的“所谓旋宫转调也”也根本不存在。因为,无论采用何种调弦法或弦音转调法,都无法建立起“一律得七声”的“调高”概念,更无法达到旋均的目的。即使能得七声,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七声,恐怕无人能够说得清。杨文虽然一开始就谈道:“‘旋宫’一语源于《礼记·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还旋为宫’”[2]48,却对其缺乏起码的理解。从古至今,五声及其旋宫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本质和主流。无论调弦法中的“慢三弦”“紧五弦”,还是乐调实践中的“变宫为角”“清角为宫”,以及民间术语中的“压上”“隔凡”,都是以五声为实践基础的,根本无法体现杨文所说“‘旋宫’就是‘旋均’”。“变宫为角”“清角为宫”中的所谓“变宫”或“清角”在音乐中并不存在,旨在通过“借声论律”,强调律位变换,实为另一“调”(高)的角音或宫音。《礼记·礼运》之后的很多古代文献也都秉承了这种理念,如唐杜佑《通典》明确记载:“五声六律还相为宫,其用之法,先以本管为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声令足,然后为十二律还相为宫”[12]3638,徐养沅《管色考·辨异》中也明确指出:“盖五声之旋,不出一均”[13]441。但杨文置这些史料和技法于不顾,轻而易举地得出了“‘旋宫’就是‘旋均’”的结论,且理论言说自相矛盾,反而批评黄翔鹏的论述“不符合古代理论,也没有文献依据”。
在旋宫与转调问题上,如果一味将唐《乐书要录》中的“一律有七声”作为唯一的立论依据,就会使概念的界定误入歧途,至于杨文试图通过此“获得一套科学、严密而明确无误的概念系统”的期望,则更加难以实现。不说别的,就“一律有七声”而言,包括唐《乐书要录》在内的诸多文献史料,均局限于“三分损益”和雅乐七声(古音阶),直接或间接地否定了乐调实践中被广泛应用的清乐七声(新音阶)的存在。然而,杨文作者在否定“同均三宫”时,却极力推崇新音阶。比如,针对陕北民歌《高楼万丈平地起》的记谱(清商音阶),杨文作者说:“古音阶、清商音阶记谱的乐曲不但不多,而且往往存在争议”[14]22。另外,杨文作者还对杨荫浏译谱的由南宋姜白石创作或填词、用俗字谱记写的17 首词调歌曲进行了校正和重新译谱,其中,将多首古音阶曲调改记为新音阶,甚至宣称:“要成功解译这套乐谱,必须按照音乐自身的规律,解决好谱字校勘、调性音列及节奏句法等问题”。只要不符合杨文作者的意图,其就认为是“误写误刻所致”,或指责原谱“完全违背了音调的自然性,也不符合调性逻辑,根本无法进行演唱”,并认为自己的改动“使得内容表现得到深化,情味倍感深厚,曲调也起伏跌宕、富于变化了”。[15]57-61其甚至断言:“在民间借字转调体系中,也就根本没有古音阶、清商音阶的存身之地。”[14]23既然如此,又为何套用唐代《乐书要录》中的“雅乐七声”来建构“旋宫转调”话语体系?
毋庸讳言,笔者虽然并不否认七声音阶的“还相为宫”,但从古至今,尚未见有一位理论家能够把“七声之旋”讲清楚,且符合当今的乐调实际。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七声音阶有三种结构形式,然而,古代文献中却只承认古音阶,与当今以新音阶为主的乐调实践并不完全相符。因此,对于杨文以《乐书要录》中“论一律有七声义”而阐发的“调高论”和“旋均说”,学界应仔细加以审视和辨析,以免因受其影响而误入歧途。
四、“乐调实践”中的“旋宫转调”之谬说
在如何看待旋宫古法问题上,杨文除了对今人的认知提出批评外,所发表的有关旋宫实践的一些观点也令人难以置信。比如,杨文说: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古代旋宫有一误解,以为旋宫说的就是音乐中的调性转换,甚至将顺旋的旋相为宫当做是乐曲中的调高变换或同宫系统不同调式转换,逆旋的旋相为声为同主音调式的变换。首先,古代旋宫是为适应实践中用调的需要,而在旋宫图上或十二支律管上对各种均、调用音及其关系进行推衍和明确的,至于实际应用中是否形成转换并未涉及。……其次,就实际音乐中的调性应用来说,无论旋宫、转调还是旋宫转调,虽然涉及诸多不同的均、调,但都不是指的乐曲中如何转换,而是指的不同调高、调性的分别应用,或是分别用于不同的乐曲。这些不同的调高、调性都是独立使用的,彼此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转换关系。[2]50
显而易见,杨文上述观点完全是脱离音乐实践的主观臆造,竟然说“这些不同的调高、调性都是独立使用的,彼此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转换关系”。如前所述,旋宫古法作为一种基本原理,不可能针对某一首具体的音乐作品,黄翔鹏的“两个概念”理论,也并不针对具体的音乐创作及作品实际。但是,这种整体性的话语表达,是有实践依据的,而非简单的凭空想象。就旋宫古法而言,也根本不像杨文所说,“是为了适应实践中用调的需要”而进行的理论推衍,而是对中国传统音乐中本已存在的旋宫实践做出的概括性论证。试问,如果“不发生直接的转换关系”,理论推衍的目的何在?既然“是为了实践中的用调需要”,为何“彼此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转换关系”?即便古代的旋宫理论没有明确说明调与调之间的直接转换关系,但谁又能否定音乐实践中本已形成的调的转换关系的存在?无论如何,先有实践后有理论,这是一切事物发展所遵循的必然规律。再者,如果“彼此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转换关系”,朱载堉费尽心思计算出的“新法密率”(十二平均律)岂不毫无价值可言?
然而,杨文前面刚阐述完“不发生直接的转换关系”,后面在解释“犯调”概念时却又说:“如果这样不同调的转换是发生在一首乐曲中的话,那就是‘外则为犯’了”[2]51。既然“不发生直接的转换关系”,又怎么会“发生在一首乐曲中”?另外,杨文作者为否定“同均三宫”,在分析传统古曲时,曾大谈“调的转换”。如关于姜白石词调歌曲,其曾多次谈及由某宫转入另一宫。又如关于福建南音,杨文作者说:“南音五空管是个综合调性的管门,它包含了五度关系的两个五声音阶。这两个五声音阶是不同调高的关系,而不是两种音阶的关系”[16]5。再如关于二人台牌子曲,杨文作者说:“未加改动的《出鼓子》系新音阶的三个调高转换”[16]12。杨文甚至还说:“唐以前是不用犯调的”[2]51,言下之意,唐以前在一首乐曲中是不存在“调的转换”的。对于杨文这些荒谬至极的观点,笔者实难恭维。唐以前只是不用“犯调”这个术语,而不是不用“犯调”这类旋宫技法。试问:难道“外则为犯”等旋宫技法及实践,是到了唐代才突然冒出来的吗?作为一个当代人,仅凭零星的“文献记载”,就能将一种技法原理的时间概念划分得如此精准,实在令人怀疑。
针对王坦《琴旨》中的“所谓旋宫转调也”,杨文解释说:
《琴旨》“旋宫转调”中的“旋宫”是指宫音的移动(角声旋宫声),“转调”是指宫音移动、其他音的音级性质改变而引起的整体调高的变动(而即转为某调)。简而言之,《琴旨》所谓“旋宫转调”,也就是改变宫音以形成调高变换的意思。
如此看来,清代所用“旋宫转调”不是两个概念,其中的“旋宫”不是“调高的转换”,“转调”也不是“调式的转换”。“旋宫转调”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旋宫”与“转调”是这个完整概念中体现因、果关系的两个因素。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旋宫转调”实质上也就是古代的旋宫、清代的转调。[2]50
从杨文的上述言说中,人们根本无法准确判断出旋宫与转调的各自属性及内涵关系。既然是“改变宫音以形成调高变换的意思”,那么,旋宫不就是调高的转换吗?既“不是‘调高’的转换”,“也不是‘调式的转换’”,那究竟在“转换”什么?又有何意义?既然“旋宫”与“转调”是“体现因、果关系的两个因素”,为何不能是“两个概念”?在杨文看来,“旋宫”就是“转调”,“转调”就是“旋宫”,只是不同时期使用的不同称谓而已,既然如此,又何来“一个完整的概念”之说?应该是一个“等同”的概念才对。而且,清代王坦《琴旨》中明确使用的是“旋宫转调也”,根本不是杨文所说的“古代的旋宫、清代的转调”。另外,王坦《琴旨》中的“旋宫转调也”,虽然并不是针对具体作品而言,却从整体性的角度揭示了民间借字手法中的调式转换(转调)规律,即宫转徵、商转羽、角转宫……就调弦法来说,任意一弦的降低或升高,都会带来五声阶名整体上的律位变化,但不能因为整体性的律高改变,而否定调高与调式两种属性的存在,调弦法毕竟不同于实际音乐作品中的调式转换。总之,由于杨文的模棱两可和自相矛盾,根本无法体现“旋宫”与“转调”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相反,“两个概念”的属性十分明确。
余论
至此已经充分表明,杨文对黄翔鹏“两个概念”的否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其很多观点并非史实,更多是表象而已。按杨文的思路解读古代文献、研究传统音乐,是根本行不通的,构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将永远是一句空话。
正如杨文所说,黄先生“两个概念”的划分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对构建“旋宫转调”话语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黄翔鹏的“两个概念”理论并非独创,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异宫系统”(旋宫)和“同宫系统”(转调)之说。黄先生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系古今、辨名实、重实践。
在《宫调浅说》一文中,黄翔鹏先生从传统宫调理论的律学基础、宫调乐学范畴的基本概念、律声命名系统的宫调关系等几个方面,对宫调及宫调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突出强调并系统梳理了律高、调高、调式、音阶等宫调范畴内的各种概念关系。此后,特别是自黄先生将《宫调浅说》写入《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1989 年)以来,学界对中国传统宫调理论有了根本性认识,推动和促进了宫调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宫调”概念的基本内涵,杨文作者也曾撰文指出:“宫调,是中国音乐历史形成的一个有关音乐构成中音高逻辑体系的重要范畴,具体包含音阶、调式、调高、调性及其发展变化,既涉及理论形态,又涉及实践应用,是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核心内容”[17]48。既然调高与调式是宫调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那么,旋宫与转调就不能脱离调高与调式而孤立存在,其关联性毋庸置疑,但不能因为二者有关联就认为是一个概念。黄翔鹏的“两个概念”理论,以观照历史和现实为前提,以音律逻辑和乐调实践为依据,不仅厘清了旋宫与转调的各自属性及内涵关系,而且为宫调理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思路。
首先,历史上出现的两种不同的调名系统,决定了“旋宫”与“转调”是两个概念。通过对曾侯乙钟乐律铭文等古代文献的考证研究,黄先生认为,先秦时期已经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调名系统,即为调系统和之调系统。无须否认,两种调名各自均含有调高和调式两种属性,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但仍属于两个概念。就调的转换而言,如果以相同的律高为划分标准,为调之间的调转换强调的是旋宫,如黄钟为宫与黄钟为徵(仲吕宫)为两个宫系统的调高转换,之调之间的调转换为同宫系统内的调式转换,如黄钟之宫与黄钟之徵(林钟徵)的转换。
其次,历史上形成的“六十调”“八十四调”等涵括“律”与“声”两种属性的“复合性”术语(即律声系统),决定了“旋宫”与“转调”是两个概念,否则也不可能构成“六十调”或“八十四调”。而且,各种调之间的转换,也必然产生两种情形,要么是单纯的调高(旋宫)或调式(转调)转换,要么是调高与调式的同时转换。但无论如何,都说明“旋宫”与“转调”是两个概念。
再有,历史上已有的调关系术语,完全证明了“旋宫”与“转调”是两个概念。笔者认为,相和歌与清商乐中的平调、瑟调、清调(相和三调或清商三调),与荀勖笛律中的正声调、下徵调、清角调(笛上三调)为同一属性,均为调关系术语。杨文作者也承认:“三调之间便以正声调为主构成了四、五度近关系调(亦即我们常说的主、属、下属三调)。这种近关系的三调正是中国传统音乐中经常使用的三调。”[18]34既然古代文献中的三调是主与属、主与下属的关系,乐调实践中就存在不同调(高)之间的转换。“不发生直接的转换关系”,又何来主调、属调、下属调?换言之,如果乐调实践中既不旋宫又不转调,这种调关系术语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黄翔鹏的“两个概念”理论,并不局限于对古代文献的考证和梳理,而是结合20 世纪以来的有关理论学说进行理性思辨的结果。比如,丘琼荪《燕乐探微》一书专门设有《旋宫乐与转调乐》的内容,指出:“用十二律旋宫者为旋宫乐,用七声转调者为转调乐。……以七声转调,必转成随调音阶,一调一式,各不相同。以十二律旋宫,其情形便不是这样。……七声不可以旋宫,十二律却可以转调。……用十二律者旋宫,用七声者转调,这是古人的成法”[19]409-416。又如,20 世纪50 年代末期,黎英海先生在《汉族调式及其和声》一书中明确提出:“按宫音关系来看各调,总的可分为‘同宫音系统调’和‘不同宫音系统调’两大类(其中还包含着‘同主音’或‘不同主音’、‘同调式’或‘不同调式’)的关系”,同时阐发了“同宫犯调”和“不同宫音系统调的变换”等手法。[20]46-47此后,“同宫音系统转调”和“不同宫音系统转调”等概念被广泛应用。随着中国传统宫调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也为了沿袭古人留下的传统术语,黄翔鹏先生将以往“不同宫系统的转换”称为“旋宫”,而将“同宫系统的转换”界定为“转调”,这样,便有了“旋宫”与“转调”是两个概念的理论学说。有的理论家将其视为“两个系统”来认识,指出:“我国传统音乐理论中自成体系的‘宫调’,是由‘宫’和‘调’两个字组合而成的。顾名思义,就可知‘宫调’是一个体系的整体,其中包含着‘宫’和‘调’两个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宫系和调系是两个不能互相取代的系统”[5]121。为了使内涵的界定更加全面且严谨、规范,黄先生又对“转调”的两种情形作了补充说明,指出:“在调高变换外,同时还兼做调式的变换,即为‘转调’。在宫音已定的某均音阶中,即在调高不变时,改动调式主音的位置,产生同宫异调的变化,也叫做‘转调’”[21]442。可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讲,黄翔鹏先生的“两个概念”理论体现了系古今、辨名实的学术理念。
除此之外,曲调考证是黄翔鹏先生宫调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现存的民族民间音乐(特别是五声音阶)作品中,直接发生调的转换关系的作品极为丰富。正如杨文作者所说:“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不仅有着丰富的旋宫转调实践,而且还形成了相应的逻辑概念体系,如我国东北鼓吹乐中即将旋宫转调称为‘借字’。”[14]22其中,为学界所熟知的东北鼓吹乐中的“五调朝元”,就是“以基本旋律为基础,在同宫系统内进行五声性同步移位,并由此产生同宫系统的调式变换”[22]92,使“转调”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概念。正是自古以来留存至今的大量的民间音乐作品,为黄翔鹏“两个概念”等一系列宫调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是其重实践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综上所述,古代文献中虽然没有出现过“调高”与“调式”两个术语,但其内涵是明确的,并且自20世纪初以来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黄翔鹏将调高与调式的转换分别界定为“旋宫”与“转调”并无不妥。由于记谱法等因素的制约,古代的旋宫与转调很难通过某一具体的音乐作品加以论述。西方乐理在阐述转调问题时,也主要提及与此相关的“近关系”“远关系”以及主、属、下属等概念,具体的调高或调式转换主要看作品,但并未否定调高与调式的转换属于两个概念,即不同音列转调与同音列转调两大类。不能因为音乐作品中存在调高与调式的同时转换,就认为“调高”与“调式”是一个概念。况且,中国民族调式有五种之多,同一调高(宫系统)范围内的转换是经常发生的,因此不能笼统地将单纯的调式转换称为“旋宫”。强调概念界定的准确性,是构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必然要求。至于杨文所例举的王坦《琴旨》中的“五声既以相生之声相转,则五调亦以相生之声相转”,不仅包含调高因素,而且调式含义更加明显。因为,宫、商、角、徵、羽五调是通过宫、商、角、徵、羽五声来体现的。还是那句话,没有调式含义的五声或五调没有太大意义。退一万步说,即使古代文献中的“旋宫”与“转调”,只是为了“形成不同的调高”,而“不发生直接的转换关系”,那么,将它们分别视为“两个概念”也并没有什么不妥。
总之,通过对杨文的剖析和辨正可以确信,黄翔鹏先生的“两个概念”理论,不仅有文献依据,而且有实践基础,是一种符合音律逻辑关系的理性表达。的确,在构建中国传统宫调理论话语体系过程中,对于古人留下的遗产必须十分重视和深度挖掘。“旋宫”这一术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有别于西方大小调理论中的“转调”概念,应该将其整理好、利用好、发展好、传承好。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语境的变化,我们也不能一味毫无理性地复古、泥古,既要不忘本来,更要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况且,对于古代文献之本义,今人“向来是‘猜一半,懂一半’”[23]19,其中的深刻含义我们很难真正做到完全理解。正如樊祖荫先生所说,在“旋宫转调”问题上,同样存在古今与中外的关系问题,具有“音乐术语的表象与内涵关系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在解读和“应用传统音乐术语时,一定要首先弄清它的原意,并注意术语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24]186我们要像黄翔鹏先生等老一辈民族音乐学家那样,力求做到系古今、辨名实、重实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像杨文作者所期望的那样,“以求获得一套科学、严密而明确无误的概念系统,从而为构建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