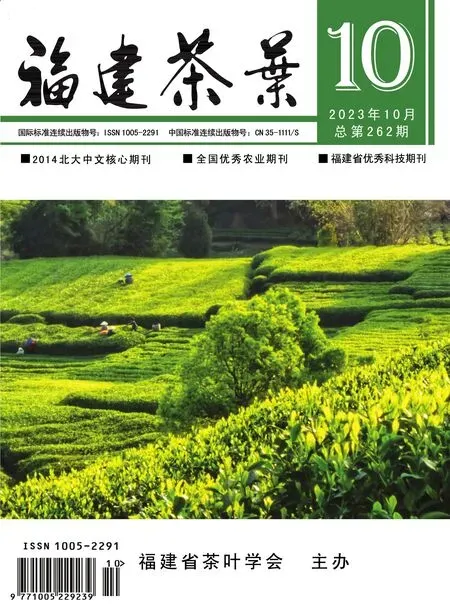中国茶叶传入英国及其对英国产生的影响
亢丽芳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西 朔州 036001)
清代中英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之一是茶叶。优质茶叶受自身属性限制,对自然地理环境有较高的要求,中国南方许多省份因适宜的气候、土壤、温度和湿度成为世界著名的产茶区,其中浙江的绿茶和福建的武夷茶最负盛名。此外中国还有精湛的制茶技术、卓越的制茶师、精美的茶具以及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作为茶的故乡,中国是茶叶最大的出口国。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园艺学家及冒险家罗伯特·福钧深入中国优质茶叶产区,获取了中国的优良茶种和生产制作技术,并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印度实现了规模化种植,中国对茶叶的垄断地位才被打破。
1 英国人渴望打破中国对中英茶叶贸易的垄断
地理大发现之后,首先来到东方并学会饮茶的是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后来旅居亚洲各地的英国人受他们的影响,争相效仿,并将购得的茶叶带回本国馈赠亲朋好友,茶饮料也由此传入英国。1607年,荷兰海船首次从爪哇岛来我国澳门贩运茶叶并转销欧洲。此时英国虽未与我国进行直接贸易,但描述茶叶以及饮茶功能的文字已出现在通讯笔录或订货单上。如在日本平户东印度公司任职的英籍经纪人R·威克汉姆于1615年6月27日致澳门同行的信中写道:“请替我购买一些上等的澳门佳茗,必须各花色品种齐全,……我将不惜重金支付。”[1]
中英茶叶贸易正式开始于1637年。这一年科腾商团来到中国,在广州第一次运出了112磅茶叶。17世纪后,在一些报刊上也出现了传播饮茶知识或广告宣传之类的文章。如1678年伦敦《政治周报》周刊两次刊登饮茶广告,第一次提及茶是医师们推荐的优良饮料,可见这时饮茶的保健功效已经或多或少被英国人发现;第二次广告则提到了一个信息——伦敦各条街道均有咖啡和茶出售。[2]说明在伦敦市场上茶叶已经不算多么稀缺的商品了。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62年,西班牙的凯瑟琳公主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她的嫁妆中包括221磅红茶。凯瑟琳王后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饮一杯红茶,她还经常邀请她的朋友们一起喝茶,宣传红茶的功能,并将自己的苗条身姿归因于饮茶的好习惯。就这样,饮茶的风尚传入了英国宫廷。顺此潮流,东印度公司董事1664和1666年先后两次向国王献茶。
终其17世纪,因为价格昂贵饮茶还只是上流社会的专属享受。一磅武夷茶在尼德兰的价格是一盾,而在英国却要出三倍的价钱。[3]1657年,平均一磅茶叶的价格在6至10英磅之间,而平民一年的收入也不过20英镑。茶价如此高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英国经常卷入战争财政极度紧张,而重税是其缓解财政困境的唯一办法,如查理二世制订“液量税法”,对茶等饮料每加仑加税8便士。另外,东印度公司赚取的高额垄断利润也是推高英国国内茶价的重要原因。1699年东印度公司进口每磅茶叶的费用为2先令4便士,但伦敦市场上的售价却高达14先令8便士。[4]
直到18世纪中期以后,茶才真正进入一般平民的生活。英国上流社会风行的时尚逐渐平民化,下午茶风俗开始盛行于饭店和百货公司之间。据1792年英使斯当东的记载,在18世纪中叶,“茶叶已经在英国各饭店和咖啡店懂公共场所大量销售,并已成为国家征税的对象。”[5]饮茶在英国全社会得到普及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大幅降低税收导致的茶价下降。1689年,英国修改了“液量税法”,降低了茶税,茶价下调,饮茶习俗开始向全社会普及。1784年,英国被赶出爪哇岛,东印度公司向时任首相小威廉·皮特建议降低茶税,结果税率从119%降至12.5%。大约一年后,英国的红茶消费量便提升了66%。到18世纪末,在贫民住的茅草屋,都会见到一家人从早到晚喝茶,同时,英国的大众化茶馆骤增,数量多达两千家之多。
随着茶价下降,茶的消费群体扩大,英国每年需要进口的茶叶数量越来越多。进入18世纪,英国的茶叶消费和贸易便出现了较快的增长。1704-1715年,英国人每年购入茶叶约在500—1300担之间;1716年,英国人从广州运回茶叶在3000担以上;1729年英船运回的茶叶突破10000担,1730年高达32000担。这时英国市场饱和,茶叶大量积压,东印度公司在接下来的几年减少了茶叶的购买量,1732年—1740年每年购入的茶叶也在4000—13000担之间,1750年高达21543担。[6]1741—1759年,英国船购入中国茶的数量最少13345担,最多则是1754年达到29310担。进入70年代,英国一跃成为欧洲最大的中国茶叶贩运国,每年运载茶叶均超过50000担。从80年代到世纪末,年均运载茶叶最少69952担,95—99年达到154366担。1834年,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垄断权,那一年英国的茶叶进口增长了4倍。[7]
那么,英国要为如此巨大的茶叶输入量支付多少白银呢?仅仅在1710年-1760年的50年间,英国购入茶叶数量不算多的年份,英国就向中国支付了2600万英镑白银,如果要折算成当时中国的计量单位“两”,至少要在后面乘以4。让英国人感到更加痛苦的是,随着北美和拉美殖民地的独立,他们获得白银的三角贸易链被彻底切断,原本源源不断的白银来源完全中断。同时,中英茶叶贸易逆差随着对茶叶的需求与日俱增不断扩大。这一切迫使英国人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打破中国对茶叶的贸易垄断便是治标之举。为此,英国人想尽一切办法摆脱对中国茶叶市场的依赖,实现本土化种植。
2 中国茶叶传入英国
文艺复兴以后,学术界通过广泛收集、分类和归纳研究动植物,希望以此达到认识自然界的目的。在英国,植物学、园艺学、农艺学等相关学科相继兴起,一批海外植物园纷纷涌现,例如西印度群岛的圣文森特植物园、英国皇家园林邱园等。这些植物园里栽培着植物猎人们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奇花异草。英国人推广和热衷于植物学研究并非从单纯的观赏性出发,而是有着很强的经济因素考量。他们绘制了一幅植物狩猎地图,可是在这张地图上遗憾地留下了一大片空白地方——中国。他们明白有些不可思议的神奇植物为中国所独有,这些植物可能为大英帝国的未来带来丰厚的收益。
当中英茶叶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趋势越演越烈,英国意识到这种中国独有的植物对大英帝国的重要性已经迫在眉睫。在窃取中国茶种和制茶技术的道路上,东印度公司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早在1780年前后,东印度公司从广东搜集到一些茶种,在印度殖民地第一次尝试种植。另外,东印度公司还在广东特派茶叶探员,专职收集茶叶以及其它动植物。[8]20年后,东印度公司雇员在喜马拉雅南麓的加德满都地带发现茶叶植株,这一地带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中国最好的产茶地几乎一致。这使得英国人确信能够在印度成功种植茶叶,结束中国对茶叶的垄断指日可待。
1848年9月,英国皇家园艺学会罗伯特·福钧乘船从香港到达上海,并雇佣了两个仆人。在仆人的帮助下,福钧乔装打扮成中国人的模样。他决定首先赶往盛产绿茶的浙江省和安徽省,然后再前往红茶之乡——福建武夷山。10月,福钧到达了浙江杭州,出于安全考虑,一行人并未在商贾云集的杭州城停留,直奔安徽的产茶区。一路上,福钧不断采集植物标本,并放入专门用来做活体植物移植的沃德箱中。福钧还参观了一处制作绿茶的工厂,他了解到制茶方法沿袭了两千多年流传下来的工艺程序。整个生产流程复杂繁琐,包括晒青、炒青、揉捻,最后是挑拣,按品质优劣区分茶叶等级,如果要加工成红茶的话,还得经历一道发酵程序。[9]随后,福钧一行又到达了上等好茶的产地,松萝山。
1849年1月,福钧将13000株植物幼苗和10000颗茶种分为四份,分别托运于4艘货轮,送达加尔各答植物园,交给其主管植物学家法尔康纳照料,这时茶种和树苗看上去状况良好。但是在从加尔各答转运到位于喜马拉雅山麓的萨哈兰普尔茶叶实验园的时候,13000株茶树苗的成活率只有3%。茶种全军覆没,没有一颗种子发出芽。
1849年5月和6月深入了极品红茶的原产地——福建武夷山。这时英国人更加偏爱红茶,英国市场上充斥着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加勒比海的蔗糖也对红茶的日益流行推波助澜,因为冲泡红茶时要加糖,而绿茶不加。武夷山最著名的红茶大红袍在英国1盎司的售价高达数千美元,有时甚至比黄金还要昂贵。同年秋天,福钧带着他丰厚的战利品,回到了上海。为了避免这次的红茶茶种再次遭遇不测,他先在沃德箱里装上泥土,然后将颗茶种塞满这些泥土。当这些沃德箱被运到喜马拉雅上的茶叶实验园的时候,茶种早已发芽,并且长势良好。福钧在茶种运输上的创意使茶树苗移植不再必要,植物猎人变成了种子猎人。福钧还雇佣了一批愿意跟他前往印度的专业制茶师,搞到了一批专业制茶工具和一批诸如茉莉和香柠檬之类的香料植物,这些植物常和茶叶包装在一起,以增加茶叶的香气。
这批红茶茶种的一部分被送到了大吉岭,是首批在大吉岭生根发芽的红茶树苗,这就是后来大吉岭红茶——被誉为红茶中的香槟——的开端。70年代印度茶便开始受到世界市场的欢迎,中国茶垄断货源,主导国际市场茶叶价格的优势不复存在。90年之后,中国出口到英的茶叶只占对英出口总额的9%[10],茶叶贸易的重心从中国转移到了印度。
3 茶饮对英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茶叶首先推动了高桅帆船的诞生。旧帆船由于航速缓慢,新采下的茶叶要在海上漂浮9个月,甚至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能到达英国。1834年,随着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的结束,新的贸易公司相继涌现,他们都要从茶叶贸易这块大蛋糕上分一杯羹,提高帆船的航行速度便成为了竞争焦点。恰逢此时,《不列颠航海条例》的撤销,使得运输茶叶的美国舰船可以直接在英国进行茶叶交易,而美国舰船由于有更快的航速,可以提前几周将茶叶送到英国码头,在茶叶贸易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成为了英国设计新的快速帆船的推动力,于是,高桅帆船应运而生。
由于茶叶分量很轻,运输茶叶的船只需要相对笨重的物体做压舱物,产自中国的瓷器因为不怕船舱底部的污水,成了最好的选择。由此,茶叶在英国越来越大的需求量带动了英国瓷器工业的发展。温润如玉的中国瓷器以及瓷器上带有浓郁中国风格的图像,比如垂柳、宝塔和娴静的妇人,向英国人展现了一个未知世界的美好形象,而且这个世界还充满了商机和财富。
比起英国人之前的饮品咖啡和酒,茶在当时具有这二者不可取代的优势。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入进展,英国城市的污染程度越来越严重,疾病传播率也随之上升,霍乱就是其中一种致命的传染病。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霍乱数次袭击英伦,夺去了数以万计的伦敦市民的生命。霍乱是水源性传播疾病,市民由于饮用不干净的水而染病。喝茶因为要用沸水冲泡能够保护市民免于这一灾难,因为将水煮沸可以杀死传播这种病菌的微生物。当茶的这一功效被发现后,茶成了军队配给标准的一部分,这大大降低了英军在东南亚热带地区感染水源性疾病的比率。
跟酒相比,茶的优点更加突出。在机器大工厂,醉酒的工人操作机器会出现经常性失误,导致工伤事故频发。饮茶不但没有醉酒的弊端,还能醒目提神,让工人们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完成工作。可见喝茶的习惯能够为工业革命提供更为理想的劳动力,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我们还要提到孕妇这个群体。孕妇如果以茶代酒,婴幼儿的健康状况就会发生显著改善。婴儿出生后要以母乳喂养,如果母亲饮酒,婴儿的健康状况和智力水平都会下降。所以,茶不仅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致畸率,还提高了免疫力。今天,随着科技的进步,饮茶的更多益处被发现,比如抗氧化、抗癌、缓解糖尿病、提高新陈代谢等。
综上所述,中国茶传入英国,成为举国上下的主要饮品,改变了英国人的饮品结构,不仅带动了瓷器、造船等行业的发展,改变了英国人对异域文化固有的落后印象,还降低了工伤比率,改善了英国人的健康状况,并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更为理想的劳动力。茶,这片小小的树叶,带着它独有的清新和芳香,成为了齿轮滚滚向前不可忽视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