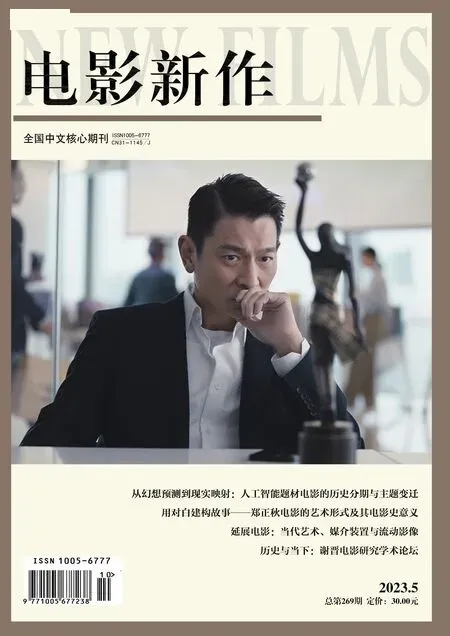“说书”传统与电影民族形式及其反思
——从徐昌霖的电影理论、创作谈起
詹少尉
近年来,有关“中国电影学派”的探讨日益热烈,各路学者通过回溯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脉络,以期探寻中国电影学派生成的本土语境和文化资源,试图建构起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体系。在此过程中,一个时常被提及,但未受到充分重视的电影人,便是徐昌霖。徐昌霖生于1916年,出身书香世家,少时受慈母教导,通读古典文学,博览传统文化;抗战期间,他从杭州之江大学辍学只身前往后方学习戏剧,广交文艺界名流,创作话剧《重庆屋檐下》初露锋芒;抗战胜利后,他随中国电影制片厂来到上海,逐步开始自己的电影事业,先后在各时期编导了《天堂春梦》《十三号凶宅》《群魔》《方珍珠》《情长谊深》《球迷》《美食家》等知名影片。在电影创作之外,徐昌霖笔耕不辍,留下了许多与电影相关的散文随笔和理论文章。其中最常为学界提及的便是他于1962年在《电影艺术》第1、2、4、5期上连续发表的《向传统文艺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下称《探胜》)一文和1981年与他人合作的《电影的蒙太奇和诗的赋、比、兴——吟诗观影随想录》(下称《赋比兴》)一文。从已有研究来看,《赋比兴》的影响较大,它同刘成汉出版于1982年的《电影赋比兴集》一道,开辟了一条由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贯通中国传统审美理念的民族电影美学体系建构之路。反观《探胜》一文,则响应者寥寥,学者们往往只是肯定作者“文化自立的初衷”1,而并未对该文内在的思想作进一步的理论阐发。在《探胜》一文的楔子部分,徐昌霖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即“除了古典文学和戏剧之外,我认为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的另一部门——民间曲艺(评话、弹词和相声等)也特别值得我们电影创作借鉴”2;在此文后续的论述中,民间曲艺的“说书”传统之于中国电影民族形式的借鉴意义的确被一再强调着。从当前学界围绕“意境”或“意象”建构“中国电影学派”的努力和积极性来看,对传统的强调似乎过于追求“阳春白雪”的高尚境界,而与“下里巴人”的民间通俗传统渐行渐远。因此,本文致力于从徐昌霖《探胜》一文出发,结合其电影作品,探讨民间“说书”传统对中国电影民族形式的借鉴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以现代电影“怎么讲”为基点,进行相关的现代性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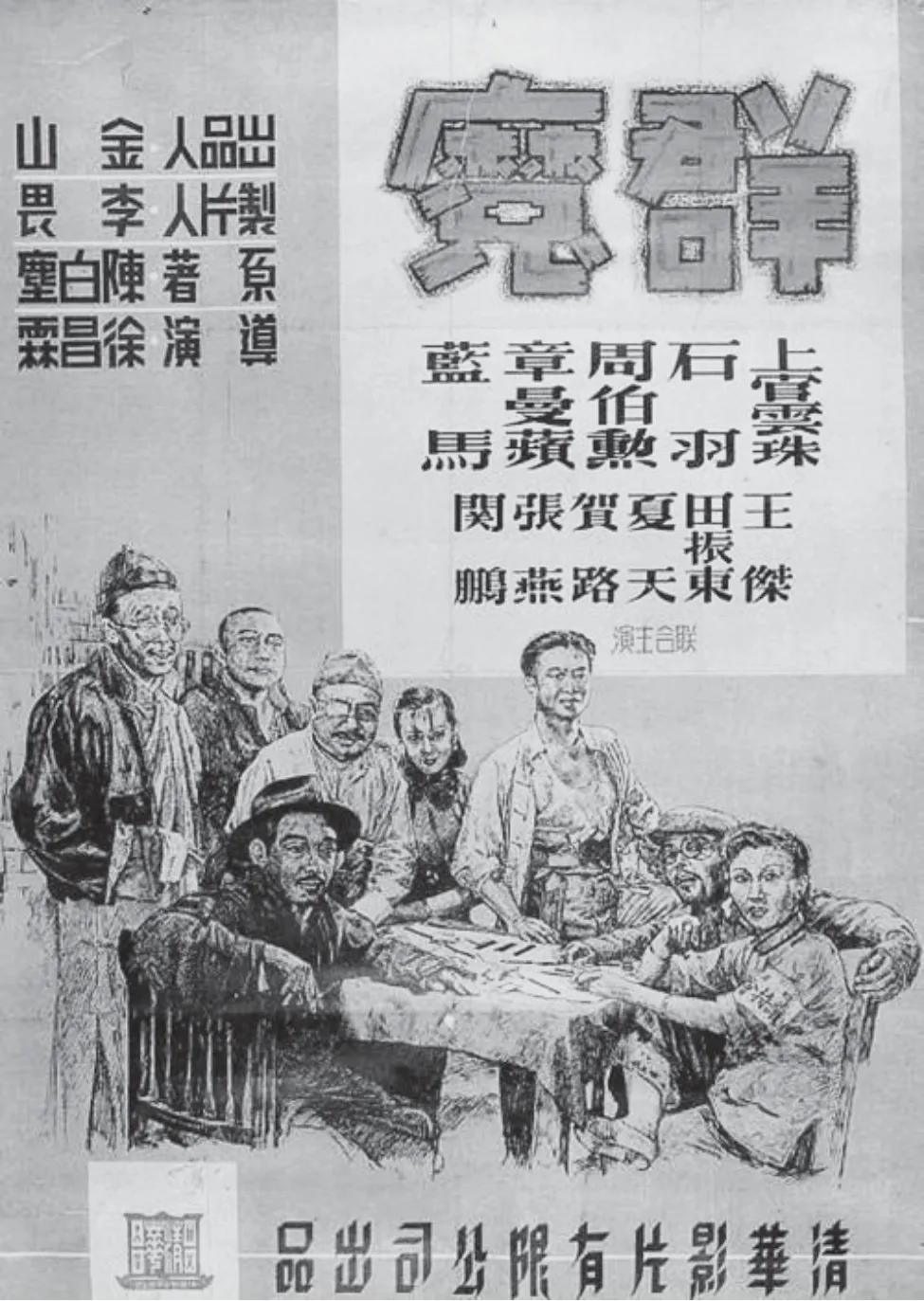
图1.电影《群魔》海报
一、向传统文艺探胜求宝:“说书”传统与平民立场
何谓“说书”?说书,一般又称作评书,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口头讲说表演艺术形式,萌芽于唐朝寺院讲经中的“俗讲”。随着宋朝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繁荣,“话本”作为其书面形式为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确立了基本的文体形态和叙事传统;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通俗小说作为统一“话本”又反过来推动了民间说书的进一步繁荣。“说书”作为民间通俗艺术,其传统在徐昌霖的电影理论与创作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人物塑造上,徐昌霖特别强调人物出场的重要性。他首先用“某些同志称之为‘叫板式’的蒙太奇”来予以说明,认为沈浮导演在《老兵新传》中介绍老战出场时的“叫板式”蒙太奇——“大家正在谈论派谁去北大荒当农场场长最合适,结果是一个近景——老战推门而入,大叫‘我去’”3——运用得简洁、清楚且漂亮,颇具民族形式。在他看来“这其实就是民间说大书中的为了加重语气的手法”。4他将民间说书艺人口中(笔下)人物亮相的基本原则归结为两点:一、脸相明白;二、性格见彩。“脸相明白,就是人物的年龄、姓氏、阶层、环境、经历以及眉毛鼻子眼睛交代得一清二楚;性格见彩,就是人物的特定性格的火花一上场先来一个闪烁。”5由此可见,徐昌霖对电影人物的塑造有着鲜明的脸谱化倾向,这一点在他编导的电影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影片《群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部影片中,主要角色有6个,无论是毒贩、流氓、兵痞,还是泼妇、屠夫、师爷,各个脸相明白、性格见彩,几乎从人物亮相的第一刻起,观众便能从他们极具标志性的行头打扮、言行举止中将其与民间说书艺术中的经典形象一一对应起来,甚至章曼萍扮演的泼妇便干脆与“母夜叉”孙大娘同名。再如影片《球迷》,人物的脸谱化倾向则更为明显。影片一开头并未开始剧情的铺垫,而是在一个圆形镜头中让人物在规定情境中一一亮相,并以字幕形式对应伴随着各自的角色名字和演员信息。这些角色的名字分别是:球迷司机、司机妻、球迷医生、医生妻、胖球迷、小球迷、球迷兄、球迷弟等,人物没有具体的姓名,只有根据职业、身材或称谓而确定的抽象代号,每个人物的形象、动作、语言则完全依照脸谱化的规定贯彻。同样的特点也见诸《方珍珠》《情长谊深》等影片中,譬如破风筝(江湖艺人)、方珍珠(烈女)、老周(忠仆)等人物形象同样称得上是民间说书传统中脸相鲜明的典范。

图2.电影《方珍珠》剧照
叙事编排是徐昌霖在《探胜》一文中尤为关注的重点。在情节结构的整体布局上,徐昌霖提倡“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缝”,即是要抓准“立言之本”,像我国古典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那般做到“有头有尾、层次分明”;同时要剪去无关紧要的乱头繁绪,通过人物、道具、场景的细致安排将经脉缝扎严实。徐昌霖的上述观点主要源自李渔的戏曲理论,与电影的艺术特性关联不足,所谈有些空泛。具体来看,徐昌霖在此方面表现出的电影本体意识主要体现在“横断面的复杂的大场面”和“过场戏”中。在他看来,民间艺人在说表头绪纷杂的大场面时,其“叙述形式和安排得好的电影蒙太奇句子很相似”。6他举王少堂代表作《武松》之“狮子楼”这场戏为例。武松得知西门庆在狮子楼吃酒,便直奔而来,但到酒楼,只见酒客云集,鱼龙混杂,打手、师爷、客人、酒家、跑堂不一而足,面对如此复杂的场面,说书人的嘴如同一架开麦拉一般,“必须有本领分层次、分先后,抓住每块小戏和武松、西门庆这块主脑的联系,纵横驰骋,详尽描述那一刹那间酒楼上下内外以及桌肚底下和楼梯脚边每个人物的各种具体不同的动作”。7类似的场面处理在徐昌霖的电影作品中比较常见,譬如影片《方珍珠》中“向三元带人砸场”一戏便十分注重以景别的变化、正反打镜头、剪辑速度等手段区分场面的层次,同时兼顾众多人物的动作与关联。至于“过场戏”,一般是指戏曲结构中重点场子之间的过渡性场子。一些缺乏过场戏、四幕八场话剧化的电影是徐昌霖所不能忍受的。在他看来,“至少在分场形式上,电影与古典戏曲接近,而与话剧是毫无血缘,千万沾不得边的……研究一下中国戏曲的分场艺术和民间评话弹词的分回特色,对我们会有很多益处。”8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于徐昌霖认识到“评话与评弹的说表极为自由,忽东忽西、忽万马奔腾、忽空谷人静,在表现手段上,与电影艺术具有同样广阔的天地”。9因此,电影创作在进行场景切换时可以充分借鉴民间说书艺术中对过场戏的处理。
思考民间说书艺术对电影画外音设计的借鉴意义,是徐昌霖《探胜》一文的亮点。说书艺术的说白分为六种,俗称六白,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说书人(第三人称)身份进行的叙述,又可分为表白、托白和衬白;一类是以角色(第一人称)身份进行的叙述,又可分为咕白、官白和私白。具体来说,表白是说书人刻画人物、叙述情节的主要手段,包括介绍事情的来龙去脉、描述人物的相貌、行为、动作等;托白是说书人对人物言行举止所进行的说明或评述;衬白是说书人对语言含蓄或不易理解的内容所进行的解释、补充或强调;咕白是书中人物的自言自语;官白是人物的白口,主要指人物之间的对话;私白则是人物的思想活动和内心独白。徐昌霖举《草船借箭》为例,以说明通过咕白、私白的形式表现电影人物的内心活动是再合适不过的:“如果我们有机会拍《三国》的电影,不妨完全采用评话的方法……内心活动用画外音讲给观众听,会大大增加影片的民族味。”10而在他自己导演的电影《两个营业员》中,也频繁使用咕白和私白的手法表露营业员小张表里不一的心声,使人忍俊不禁。至于以说书人(第三人称)身份进行的表白、托白和衬白,叙述之中穿插了大量的解释、说明和评论,“夹叙夹议”的特点极其鲜明。徐昌霖以《三国》开头的先表(“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草船借箭》结束的后表(“……骤雨飞蝗来战舰,孔明今日服周郎”)以及王少堂在《金莲挑帘》中以第三人称对西门庆的评论(“这畜生对他娘要有这么好,便算是孝子啦”)为例,说明画外音旁白在烘托主题和刻画人物性格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徐昌霖看来,“只要在加强画外音的主观作用和它的艺术感染力的时候不强调到唯一重要的地位,不因之去抹杀电影贵乎以视觉形象取胜的特点,大量地丰富电影的旁白和画外音,作为影片样式的一种,也未尝不是风格别具,另成一派。如果我们姑且认为将来可能会出现所谓‘文学电影’这一种新样式的话,那这种未来的新影片样式看起来也无非是更接近我国的民间评话体裁。”11由此可见,徐昌霖在思考电影民族形式问题时,对民间说书传统的重视。
整体看来,徐昌霖在电影理论和创作中对民间说书艺术的借鉴,其根本的落脚点在于对电影艺术的定位和电影观众的认知。关于这一点,他在《探胜》一文的楔子部分便提前透漏,即“民间说唱艺术跟电影最共同的特点是都最具有群众性,而且恰巧都是‘一次过’的艺术。”12民间说书是面向平民大众的通俗文艺,在他看来,电影也同样如此,需要符合最广泛人民群众的观影需求,对民间说书传统的借鉴可以极大地提高电影对观众的向下兼容性。尽管这种观点的时代局限性尤为明显。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物形象之所以要强调脸相明白、性格鲜明,既在于从下层民众的生活、心理和想象出发进行塑造,又在于做到让说书场中的观众过耳不忘、印象深刻。徐昌霖对这种平民意识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受到老舍的影响。在《追忆老舍》一文中,他回忆起老舍给《方珍珠》影片中“‘破风筝’被迫与全家骨肉分离”一场戏提的建议:“一个江湖艺人,长期在旧社会打滚,遇到天大的打击也是不会哭的”13,并认为该建议极大程度上加深了他对人物性格刻画的理解。也许正如老舍在谈及民间说书的人物塑造时说的那样:“人物的描写要黑白分明,要简单有力的介绍出;形容得过火一点,比形容得恰到好处更有力。”14除此之外,徐昌霖之所以强调电影对复杂大场面的表现应该借鉴说书传统,并注重人物关联,则是因为下层民众更重视视觉经验;而“过场戏”说表自由、忽东忽西的时空特点也与人们脑海上所经历的“过电影”般的感受颇为类似,既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又容易调动现场听众的兴趣。最后,平民意识同样表现在说书艺术“夹叙夹议”的叙述特点中。“评论”之所以重要,在于说书场面向的观众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理解能力有限的下层民众,说书人不断插入的点评、议论,一方面可以解释听众可能产生的疑惑,另一方面有利于揭示人物言行或事件本身所隐含的深意,另外,说书人爱憎分明的立场则更容易感染现场的听众。
二、电影民族形式问题:程式化与“说书人”叙事
徐昌霖基于电影艺术的平民立场,在向民间说书艺术学习并思考电影民族形式问题的过程中,容易陷入程式化的陷阱。所谓程式化,通常是指戏曲艺术形式的总体构成,用来说明戏曲的演剧方法的个性特征;程式,则具体指一切自然形态的戏曲素材,按照美的原则予以提炼、概括、夸张、变形,使之节奏鲜明,格律严整的技术格式。而在徐书城看来,“程式化”的美学特点,也许是中国传统艺术所共有的一种普遍性。15如此,民间说书艺术同样存在程式化的特征,这一点从扬州评话艺人的口诀中便可见一斑,即“记住地址、人名、府城、情节,一辈子说书有吃喝”。16于是那些用于描绘人物、场景的韵文赞表,皆是可以互相套用的程式化的语言构件。程式化通常还意味着高度的假定性,作为面向平民大众的通俗文艺,一开始便从受众接受的角度规定了人物形象、叙事编排、语言风格等文本特征。杨义就曾将说书人用的话本视作“曾经是市井技艺、因而高度程式化的文学体式”。17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徐昌霖仅用类比思维,通过电影与说书在直观层面的艺术共性来进行电影民族形式问题思考时,他的民族电影理论便自然而然地继承民间说书艺术的程式化特点。其中最为可惜而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在于他对说书人“说白”和电影“画外音”的探讨仅停留在后者对前者的直接移植上,而没有对电影艺术中说书人的主体位置做进一步阐发。
在民间说书艺术中,“说书人”作为故事的叙事者,主要有以下特点:首先,“说书人”是说书场中从事说书表演的具体艺人,他直接在场地面向观众,表演过程中会不断以“说书的”“在下”等称谓进行自我指涉,并频繁地通过发表看法确立自身作为权威阐释者的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说书人”非常明确地作为超越故事层面的叙事者而存在;其次,“说书人”拥有全知视角,享有高度的视点自由,可以在不用交代任何信息来源的情况下对发生于不同时空的情节分头道来;最后,“说书人”能够随意地进入并占据故事内人物的第一人称视点,通过咕白、官白、私白等形式表现人物的对话、情感和内心活动。以上三个特征,完全类比移植到电影艺术中,最能标志“说书人”在场的主要是第一点,盖因第二点所涉及的视点位置,均可由更为自由的摄影机实现。摄影机完全可以通过蒙太奇、角度、景别、主观镜头等设计以影像叙事替代说书人的“嘴”——口头叙事;而第三点则可以通过演员的对白、独白和表演实现,这更是电影中极其普遍的一种基本艺术元素。此外,之所以第一点更重要,就在于当说书人的“嘴”(叙事)由镜头替代之后,电影的画外音还可以充当另一张“嘴”,这张“嘴”以“说”(评价)的方式直截了当地暴露了“说书人”的位置。
中国电影中,类似对“说书人”叙事的简单移植非常普遍,在无声电影时期,这主要体现在影片的字幕中,一些字幕往往并非呈现人物的对白,而是以“说书人”的身份发表评论。例如《一串珍珠》(1926)的片头便以一首七言诗入话:“君知否?君知否?一串珍珠万斛愁。妇人若被虚荣误,夫婿为她作马牛”,如同“说书人”的定场诗一般,点出整部影片的主题和观念。进入有声电影时期,“说书人”往往化身为影片中出场的具体人物形象,他们一般出现在片头和片尾,不参与故事的发展而以置身事外的立场或谈论人物的遭遇或发出自己的感叹。譬如《船家女》(1935)中的两位下棋老者,便是这类人物形象的代表。故事在片头处他们对世道的感慨中开始,也在片尾处二人对世道的感慨中结束,影片成功地在观众与故事之间建构起了作为叙事中介的“说书人”,为观众营造了一种类说书场的叙述情境。有学者指出,作为繁荣于民间的通俗文艺,“说书人叙事应该说是中国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古老‘讲故事’模式的延续和变体,这种模式也形成了中国人善于把任何叙事作品纳入一种‘讲故事’的框架的思维习惯。”18这从晚清时期中国译者对域外小说的翻译中便可见一斑,譬如《新小说》刊出的国外侦探小说《毒药案》,便被有意识地“还原”为“余老友‘萧君’讲故事”的说书人叙事模式。表现在文学改编电影中,一种常见的做法是抹除小说中第一人称的叙事痕迹,代之以第三人称(画外音)的全知视角,将原作的叙事规范为“被讲述”的形式。影片《祝福》(1956)的叙事处理便是如此。片头画外音用“很早很早以前的事”等追忆性语汇将观众带入听故事的情境中,在片尾又以画外音——“这样的时代,终于一去不复返啦”——来升华主题,直白地感染观众的情绪,以极为鲜明、具体的观念性消解了原著中第一人称叙事对自我的审视以及主题思想上的深刻性。总而言之,电影艺术以第三人称画外音形式直接照搬传统的“说书人”叙事模式,一方面确实可以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实现“影以载道”的目的,创作者甚至能够占据“说书人”的位置成为一个时代的发声人。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一批电影(《小街》《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苦恼人的笑》等)中,那些受理想主义光辉烛照的启蒙者便假借“说书人”之口进行宣泄和呐喊;另一方面,这种直接的移植使电影艺术在面向大众不断通俗化的过程中,也使其叙事观念和叙事立场受到制约,从而削平了思想的深度,同时还使视听影像本身的暧昧性大打折扣,即是说电影艺术的媒介特性在移植“说书人”叙事传统的过程中被简单忽略了。
三、“说书人”叙事传统的现代性转换
如何实现“说书人”叙事传统在电影艺术中的现代性转换,需要从现代电影观念谈起。在陈林侠看来,“从世界范围来看,叙事艺术‘讲什么’让位于‘怎么讲’,成为古典与现代分野的关键。所谓现代电影,是以媒介产生自我意识为前提,并充分发挥媒介自身的特殊性形成的艺术形式和美学风格。”19“怎么讲”?这首先是一个叙事立场的问题。事实上,徐昌霖在《探胜》一文中对电影媒介特性的把握,一定程度上抓住了现代电影区别于其他叙事艺术的关键。他在谈到对重场戏的处理要做到“说足输赢”时指出,“电影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能将时间特写并拉长,能够用开麦拉将空间扩大,是显微镜似的观察生活,像陈翠娥小姐一步一徘徊细腻的下楼梯的功夫,便值得学习。”20这句话充分说明徐昌霖已经意识到,长镜头(将时间特写并拉长)和景深镜头(将空间扩大)所形成的连续、统一时空,非常适合用于对人物内心活动(一步一徘徊细腻的下楼梯的功夫)的探索。这种观点与巴赞的观点不谋而合,在后者看来,之所以《公民凯恩》(1941)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正在于该片对景深长镜头的创造性运用——“景深镜头要求观众更积极地思考……蒙太奇在本质上是与含义模糊的表现相对立的……反之,景深镜头把意义含糊的特点重新引入画面结构之中”21——激活了电影对现代人复杂心理的表现潜能,而与古典的观念性叙事分道扬镳。一句话,景深长镜头回答了现代电影“怎么讲”的疑问,即现代电影更倾向于在连续统一的时空中去表现一个或多个非观念化的个性化的人,在对人物复杂内心的呈现中突破类型化、公式化的框架。其次,现代电影“怎么讲”也意味着要激活电影媒介的自我意识。景深长镜头之所以被视作电影语言的革新,不光体现在所呈现内容意义的暧昧性上,更表现为镜头在连续统一时空中的运动所暗示的自我意识与人物意识之间存在的张力所带来的另一层次上的暧昧性。正如《小城之春》的现代性,更多地体现在镜头运动与人物运动的分离上,那个从破洞中穿墙而过的镜头便被视作镜头主体意识的明证。

图3.电影《公民凯恩》剧照
景深长镜头的现代性主体意识对“说书人”叙事传统有何借鉴意义呢?前文我们提到了“说书人”叙事直接移植到电影中,会有两张“嘴”:一是镜头,二是画外音。从景深长镜头萌发的主体意识中我们受到启发,镜头的影像叙事和镜头自身的运动需要被区分看待。一般说来,经典好莱坞电影所确立的正反打镜头和缝合体系,在以视觉匹配为主导原则的基础上,总是试图尽可能地消除叙事主体的痕迹。于是,镜头运动在最大程度上附属于影像叙事,并自我隐匿。正如克里斯蒂安·麦茨所言,传统电影倾向于压制话语陈述主体的一切痕迹,其目的在于使观众自以为是该主体。22也就是说,经典好莱坞电影的镜头机制致力于让观众产生对故事人物的自我认同而陷入沉迷。然而,在现代电影中,电影自身的媒介意识得以激活,于是镜头自身的主体性开始彰显。譬如在影片《重庆森林》中,片头部分从叙事内容来看,呈现的是林青霞在重庆大厦中的游走和金城武在人群中对罪犯的追捕;而从镜头的运动和剪辑来看,却并没有表现出“配合”人物运动的意图,极其摇晃的镜头(并非人物的主观镜头)和抽帧的影像仅在较小程度上保留着叙事信息,观众难以在镜头有意的隔膜下寻求到认同人物的视点。如此看来,现代电影与传统电影相比,要注意从镜头中区分出两张“嘴”,一张“嘴”负责叙事,一张“嘴”通过有意味的形式(运动、景别、角度等)进行自我表达或仅仅是让观众注意到它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觉醒自我意识的镜头与“说书人”的功能是相似的,“说书人”经常会通过程式化的套语或评论在叙事的间隙中自我暴露,打断听众对故事的沉迷;不同的是,传统“说书人”只有一张嘴,只能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兼顾叙事和自我表达,而镜头的两张“嘴”是彼此独立且可以同时说话的;此外,“说书人”的自我表达和叙事立场往往会观念先行、合二为一,这也是与现代电影互相抵牾的地方。
在确定现代电影的镜头在影像叙事功能之外还具备主体意识之后,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很容易得出另外一个结论,即画外音同样可以独立于影像叙事而存在。聂欣如就用德勒兹的“感知—影像”理论来解释《小城之春》中的声画对位现象:“所谓‘感知—影像’就是那种既非主观(主人公的背影出现在画面中),亦非客观(除了主人公的背影之外,几乎全部是主人公的视线所及)的摄影机影像。”23在他看来,《小城之春》的影像叙事内容(第三人称的客观叙事)往往与画外音的第一人称彼此逆反,“这种感知上的冲突势必会打破观众的沉迷,从而进入德勒兹所谓的‘感知—影像’”。24也就是说,声画的对位使观众感觉到画外音的存在并不需要完全服膺于影像叙事。此外,《小城之春》给我们的另一个提示,在于“说书人”玉纹既是故事的讲述者,又是故事的当事人,这不同于传统“说书人”或从虚空发声或只是故事中的次要人物或为一个超越视角的见证者,且无论是哪种传统“说书人”的位置都无法像玉纹所处的位置那般,具备独立建构完整内心空间的优越性。因此,“说书人”叙事传统的现代性转换,其中一点应该表现为“说书人”的身份由单纯的故事讲述人“他”到亲历者—讲述人“我”的转变。这其实也契合了现代电影“怎么讲”对表现个性化的人和现代人复杂心理的倾向。另一方面,说书人“我”还可以在几个主要角色之间流转,分时或嵌套登场,进一步扰乱观众对叙事的沉迷。譬如《重庆森林》中的何志武在画外音中的那句“我对她一无所知。六个钟头之后,她喜欢了另一个男人”,便以一种既主观又客观的暧昧性陈述将第二段故事囊括进了说书人“他”的说书之中,而“他”又作为两段故事中的一个主人公和另外三个主人公一起,通过说书人“我”将影像叙事之外的故事情节讲述完整,并以内心独白建构起各自完整的内心空间,暴露出“元叙述”的特征。总而言之,较之镜头有意味的形式,画外音作为说书人的“嘴”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度强调自身对影像叙事的介入。
在分头论述镜头和画外音之后,我们发现现代电影媒介意识的苏醒,事实上意味着传统“说书人”一元主体的消解。于是敏锐的电影创作者们开始激活镜头和画外音的自我意识,试图建立起多主体多层次的多重“说书人”结构。之所以还要强调“说书人”的身份,在于这些占据不同位置的“我”有超出叙事的强烈自我表达意愿,他们完全可以表现出彼此对立、认同、疏离的个性化态度,而无法被观众所忽略。从主体性来看,镜头分化出两种主体,分别负责影像叙事和运动形式;而画外音既可以固定在一个具体位置上(大概率是处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位置),又可以处于一种游牧状态中,占据任意角色进行第一人称限知表达,此时画外音背后的主体往往会与负责影像叙事的主体分时重合,共同将整体情节拼凑完整,并随时跳出发表评论来挑战影像。从层次来看,如前文所述,画外音位置上的主体因为采用最直接的言说方式更容易成为一个更高层级的“说书人”。当然,这一位置也可以存在其他主体(可以存在多个人物的画外音)。但可以确定的是,镜头运动形式位置上的主体所处的层级需要根据其在电影中所持续的具体时长占比做出判断,例如《小城之春》中表现出自我意识的运动长镜头所占比例其实并不高,那么镜头运动的主体性便难以处于高于画外音的层级;而一些将运动长镜头发挥到极致的影片,我们便要格外注意其中镜头运动所表露出的主体意识的层级。比如《路边野餐》中长达43分钟的运动长镜头会突然调转方向拐入一个小巷,或在不同人物交集的瞬间随机选择一个人物跟随而去,这种情况下镜头运动的主体层级可以说完全与影像叙事和画外音并驾齐驱甚至凌驾于后两者之上。如此,在现代电影的媒介意识苏醒(镜头和画外音产生自我意识)之后,电影创作者可以将许多个性化的个体或个体精神分裂产生的多个自我安排到镜头运动、画外音等不同主体位置上进行叙事功能之外的或隐晦或直接的自我表达。当然,创作者本身也可藏匿于诸多主体之中,甚至在不同主体之间游离。而这种“说书人”结构往往因为主体、层次上的多元而显得叙事松散、主题暧昧,需要观众独立于影片之外深入思考其中的内涵,从而实现现代电影在形式上和立场上“怎么讲”的统一,这也是“说书人”叙事传统实现现代性转换的一条路径。
结语
徐昌霖在《探胜》一文和其电影作品中尤其重视民间“说书”传统对中国电影民族形式的借鉴意义,这一点提示人们在围绕“中国电影学派”进行争鸣的过程中需要将目光适当转向更接地气的通俗文艺传统。王富仁就曾指出,中国文化就其根柢而言乃是平民文化。25当然,应该承认的是,徐昌霖在《探胜》中对电影民族形式的思考大部分停留于对“说书”在内的通俗文艺传统的直接移植,这一点在“说书人”叙事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电影媒介主体意识的苏醒,要求传统“说书人”叙事由一元主体性转向多元,从而实现现代电影在形式上和立场上关于“怎么讲”的统一。从中我们得到的启发在于,“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构不应该仅仅是看向过去(传统),而应该结合当下电影艺术的发展进程和所处的时代语境做好传统资源的现代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