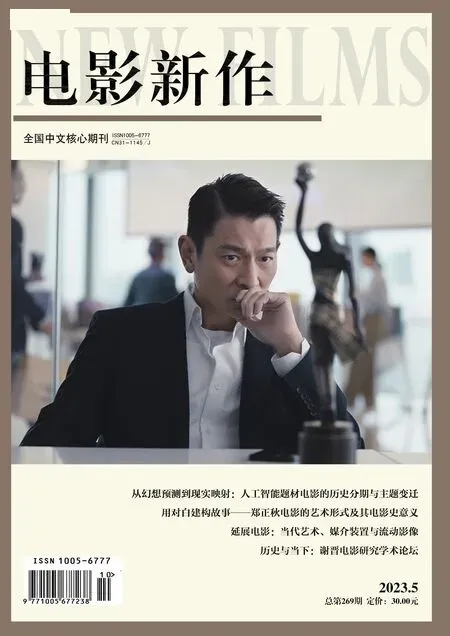中国当代电影研究的问题取向
——程波《问题、地域与历史:中国当代电影研究的三个向度》阅读感言
贾磊磊
一位学者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这种研究方向上的选择,实际上表现出的是学者在研究活动中所秉承的基本价值取向与人生方向。虽然研究对象的性质归属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学者学术水准的高低,但是,就基本的学术立场而言,一位学者在相同的领域内所确定的研究方向,依然能够看出他的兴趣与个性所在。诚如程波在他的当代电影研究中所关注的电影的底层叙事问题、电影的地缘文化问题以及电影的媒介本体论问题。
一、底层叙事
程波论文集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就在问题研究的框架内以《先锋的底层悖论——中国新生代电影的“泛底层”现象研究》《底层何以喜剧:中国当代城市底层喜剧电影意识形态研究》《从认同危机到伦理困境——19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中“农民工形象”流变》《身体、叙事与悖论:当代中国电影底层形象的性别转向(1992-2019)》四篇论文集中分析了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底层叙事问题。这种选择表现出他对中国电影创作的关注是从一个与社会现实关联度极高的视域展开的。作为一个学院派的学者,他既没有走进象牙之塔去钻研那些佶屈聱牙的抽象理论,也没有汇入众声喧哗的宏大叙事领域去迎合他人的声音,而是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在与电影与现实具有直接关联的底层叙事范畴,为我们呈现出他对这个充满着百姓情怀同时也不乏争议的话题的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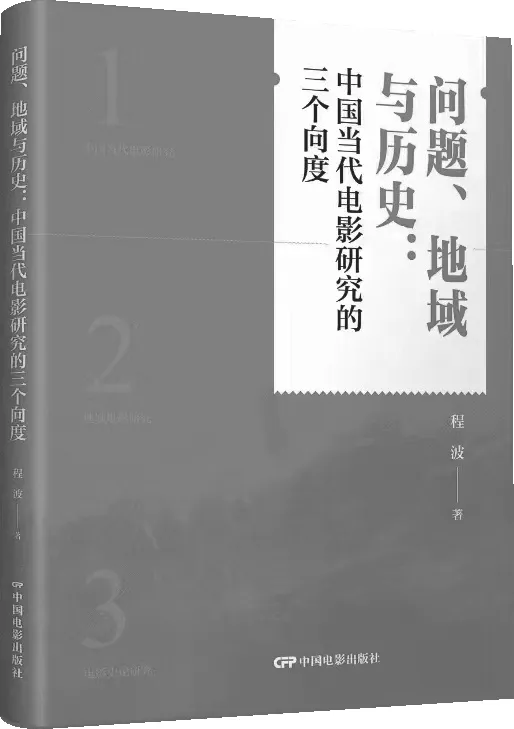
图1.程波《问题、地域与历史:中国当代电影研究的三个向度》封面(中国电影出版社,2023年11月版)
我们知道,底层叙事是中国电影批评界的一个“高频词汇”。它特指那些以普通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为故事题材的影片,以及那些以低调的、纪实的、客观的影像语言为主体的电影叙事方法。特别是指那些集中表现处于困境中的普通人在温饱、安危、生死临界点上的现实生活。所以,人们对底层叙事的印象往往就带着灰暗、冷峻甚至痛苦、失望的感觉。其中有某些被命名为艺术影片的作品,在底层叙事上呈现为一种激进以及偏执的文化态度,使底层叙事与某种负面的、消极的文化情绪勾连起来,进而混淆了在底层叙事的视域下所呈现的积极的、正面的社会因素。然而,随着底层叙事日渐成为当代电影创作中的一种显学。电影学术界对底层叙事的关注也日趋深入,这种学术视域的深入特别体现在学者对中国电影在底层叙事方面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与对于底层叙事之所以产生的现实语境的阐发。如程波在他的论文中曾经提出:“中国当代电影长期以来特别缺乏对当下生活的底层表述,加之如今拍摄电影的青年导演们不再享有体制内的各种特权和好处,他们要么是单枪匹马的奋斗,要么处于‘地下’的状态,没有被社会和大众认可和普遍的接受,所以对底层、边缘人群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先锋电影对底层的关注正是他们自身的生命体验与他们的社会人生关怀的融合,借底层说出他们想说但没说的话,‘底层’进而成为少数电影人生存和先锋探索的双重领域。”对于底层叙事之所以形成的文化社会语因素,应当说程波的论述给予了客观、中肯的分析。可见,尽管底层叙事是一种被诸多电影用于揭示社会不公与现实困境的电影工具,但是,底层叙事本身并不是一个既定的负面词汇。它对普通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的描写也并不是就意味着要刻意地去表现他们失意、失落乃至窘迫不堪的生活。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因某些电影的成功而产生的“示范效应”,使底层电影“变得越来越标签化、符号化,独立意识变成了这一小部分人的集体无意识。他们镜头下的‘底层’,以及如何用镜头展现‘底层’都出现了同质化的倾向”。程波的这些论述无疑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电影底层叙事的真实意图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程波在其底层叙事的研究中敏锐地感觉到“如果底层生活图景和底层人物命运只是被用来作为精英意识自我感动、自我标榜的工具,那么这样的底层,在电影中实际上已经被泛化和颠覆了”。我想程波的意思是指有些名义上写普通人现实生活的影片,以表现底层人民的生活为名,实际上是以现实中某些负面的现象作为他们刻意表现的创作空间,通过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某种被扭曲的人性来宣泄个人的情绪。这种所谓的底层无疑是被颠覆了真实意义的底层,是失去了认知价值的底层。我们看到在这种负面的、极端的思维逻辑的误导下,人们已经将一种越黑暗越深刻,越消极越真实的叙事逻辑植入到表现底层现实生活的叙事机制之中。我们看到在有些电影中,作者几乎将人生所有的不幸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让她尝尽了生活的种种苦难,几乎就没有任何希望,更不要说生活的快乐。有的影片中所展现的整个社会就是一个骗子的大本营,剧中的所有人物没有一个不在撒谎。这种“顺拐”式的编剧法则不仅与整个中国的现实生活在本质上大相径庭,而且就电影的创作规律而言,也严重地违背了艺术的审美原则,进而对当代中国电影的国家品牌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其实,底层叙事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灰色版本。比如说影片《今天明天》,其中讲述的是居住在北京远郊的外地打工仔的故事,他们因低微的社会地位,窘迫的工作境遇与贫困的物质生活,被媒体称之为“蚁族”。影片中三个青年被诠释为蚁族的典型代表——他们蛰居在狭窄的民房里,终日里为生计而奔波。影片在充分展示他们艰辛的现实境遇的同时,同样充分地表现出他们身上最为可贵的精神品格,既对自我梦想的顽强坚守:对他们而言,最怕的不是贫困,不是劳累,不是辛苦,而是怕在这种遥遥无期的苦熬中丢失了自己对梦想的追求,这是真正的草根族奔向梦想的道路。他们身边不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不是而是街边的暗影中游走的女郎,是随时都可能出来斗殴的群氓。处在这样的氛围中,有时他们不做什么有时比做什么更重要。与《中国合伙人》那种对梦想的高歌猛进式的追求相比,《今天明天》对梦想的追求,更显得坚贞甚至苦涩。这是中国电影对于人生梦想的两个不同的版本,一个高亢激昂,一个低回沉郁,它们同样都是人生理想的奏鸣曲。
二、地缘电影
关注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人都会注意到,在我们的电影学研究中位于时间轴向的论著要远远超过位于空间轴向的著述。应当说,“在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历史中,电影的创作与生产与地域风貌、地缘文化呈一种‘共生’状态,电影的发展也深受地缘关系的制约和影响。正如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现在,我们将地缘关系看作电影艺术的生成、发展、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不仅对某一地区的电影乃至艺术创作有着重要意义,而且采用地缘文化的观点对中国电影艺术进行空间范围的文化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电影艺术在特定文化语境下历史走向的科学性总结。”1
程波在论文集的第二部分,以《从苏州河到黄浦江——上海城市影像的空间呈现与文化想象》《被摄取的风景:电影中的“东方明珠”及其文化表征》《上海艺术院线发展策略及其在地性研究》《身体经验与策略性想象——近年两岸三地女性导演华语同性恋题材电影的一种阐释》《“高雄人”电影:高雄电影的补助政策及在地美学实践》《“过界”与“破界”之喻:粤港澳大湾区电影的建构与突围》六篇论文集中分析研究了中国电影地缘文化问题。他基于自己所在的地缘优势首先指出:“在上海的影像呈现中,相对于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大世界游乐中心等地理坐标意义的上海标志性建筑所结构的空间,苏州河与黄浦江的影像表达更为自然地诠释了上海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因河而兴、通江贯海的精神气质。具体来讲,河水奔流所代表的时间流动性与两岸带有历史错落感的建筑在空间上的固定性,决定了苏州河与黄浦江在上海城市叙事中的独特地位。正如黑格尔所讲过的那样‘地理是民族精神表演的场地’。苏州河与黄浦江的影像不只是静态的单一呈现与单向度表达,更多的是对城市文化想象的岁月易逝的动态心理及情感体验的深入刻画。”经过考证,程波提出,“在老上海,苏州河居于公共租界的北端,很长一部分是公共租界与上海辖区闸北的分界线,其一方面带有“界河”的意味,一方面又是从文化和阶层上区分人群的依据。”程波所展开的电影的地缘文化研究除了强调地理空间上的依据外,国家、民族、历史、文化依旧是他判断地缘空间的重要考量。他没有在强调时间的时候忘记空间,也没有在强调空间的时候又忘记时间。正如我们不应当在强调地理的时候忘记历史,而在强调历史的时候忘记地理。他敏锐低感觉到“在现实的时空里,苏州河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苏州河两岸逐步成为上海中产阶级生活的空间想象之一——‘苏州河景观公园’和‘河景房’的载体,是‘黄浦江沿线贯穿工程’和‘江景房’的延续。原本文化和阶层上的固化形态随着空间的变化被打破,并结合着物理空间变化被重新编码,这样的苏州河现在或者未来会以怎样的方式进入电影?”程波的提问无疑是一个电影地缘文化研究的重要命题。他不仅将地缘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作为特定的社会阶层来考量,而且将这种地缘文化的符号意义与历史的发展统而观之,表现出在电影的地缘文化研究中所采取的多重维度的思想方法。
笔者曾经讲过,如果我们将某些地域作为中国电影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文化区域来判定,它的主要文化依据是要具备四项条件:其一,这些地域除了在地理位置上的共同性之外,在地方语言、文化传统、社会风俗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的通约性。由此便可以将这些具有同一性的文化属性的地区的电影统而观之,并且按地缘文化的分类设定为相对独特的电影地缘文化空间。其二,在自然地理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关联以及相同的自然地貌特征与自然气候特征。像中国东北各地在自然地理上都属于温带季风气候,由于纬度高,冬季寒冷漫长,农闲的时间较之东南地区明显要长,为东北地区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这些地域的电影最容易形成文化表达的延续性。其三,由于自然的地理地貌并不是按照对称的空间结构形成的,尤其是文化的生成更不是按照一对一、二对二,抑或是东对西、北对南这样的结构来变迁。我们不能因为有了西部电影就要有个东部电影,有了东北电影就要有个西北电影,电影的形成除了地缘的因素之外,我们还必须要考虑到它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政治因素。其四,我们不能以单一的地理因素作为中国电影地缘文化的划分依据。因为某些地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中取得了在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优先权,并且成为一个引领时代和国家发展的引擎地带,在地缘文化学上它类似于一种国家发展的枢纽地带。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空间。目前,对中国电影具开创性的地缘空间是粤港澳大湾区,它是由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等9座珠三角城市构成。其中特区是湾区建设中最具有活力的“轴心地带”。在它的背后是无数奔波与奋斗的追梦人的故事,是无数跌倒后继续前进的故事。特区人、特区故事、特区模式、特区精神是中国人逐梦路上的成功实践,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重要能量来源。特区既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也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民族文化概念。尽管深圳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广东周边地区的客观条件相差无几,可是它在地缘政治上却获得了其他地方不可企及的优势。“特区电影”包括电视剧有着在相同的地理区位上得天独厚的文化特质。为此,电影不可能不关注中国这个最具有文化活力与精神动力的地带。程波在其论文《“过界”与“破界”之喻:粤港澳大湾区电影的建构与突围》中提到“深港之界,也是身份的界、情感的界”,以这种多重的视点分析了影片《过春天》及展示了关于“跨境学童”身世情感的路径。影片通过佩佩决定回到深圳继续读书,回归正常生活,进而完成了她成长过程中的“春天”经历。他特别指出的是,“不论是‘赴港生子’‘跨境学童’还是‘水客’‘假结婚’,这些跨境现象的产生与消散,都指向了近年深圳与香港地区在世界经济大潮中形成的一种‘倒错关系’。它似乎暗示着港人已经多少察觉到了深圳、香港地区经济地位的变化。”程波的这种论述使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当今的电影评论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电影的镜头分析与影像研究的范畴内,电影批评的视角除了立足于电影的叙事层面之外,已经嵌入现实的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变迁之中。在这种意义上电影研究已经成为我们观察现实社会生活的立体透镜。
三、媒介本体
电影的学科归属是电影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就目前中国的分类而言,电影通常被置放在文学、艺术学、新闻学、传播学的不同框架内。不同的学科归属造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不同的本质定位。同样面对的是电影,在不同的学科语境中便被命名为不同的意义。程波在传播学的学术范畴内,强调“媒介是一种强力,它调动人类的感知方式,建构一种感知偏向,从而形成一种认知模式。人类的交流与互动,人类感知经验的传达与表述,人类思想文化的建构与传承都需借助媒介”。这样就将电影的研究与人类的信息传播方式与传播内容联系起来,是我们能够从一个更加专门化的维度看到电影的多重属性。
其实,电影传媒属性与它的艺术属性同样都是与生俱来的。媒介,自古也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对周幽王来说是烽火,对拿破仑来说是报纸,对邱吉尔来说是电报,对布什来说是电视。谁想控制世界,谁首先就得控制媒介——这已经是一种被历史印证的事实。周幽王当年为博得褒姒一笑,竟然点燃专门报敌入侵的烽火,让大军集结到城下,是媒介帮助周幽王引起了美人难得的笑颜。拿破仑曾经说过:“给我三家报纸,胜过三千骑兵……”,可见,这位法兰西帝王对于传播媒介的精通之术一点也不亚于军事谋略。布什更是一个懂得利用电视媒介进行自我宣传的总统……
事实上,传播学对于电影乃至电视研究的贡献在于它彻底看清了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导向功能,即它们能够全面实施对社会、对大众的心理控制。让你看什么,不让你看什么,有些时候几乎就等于让你想什么,不让你想什么一样。从这种意义上讲,传播媒介控制着这个世界。现在没有人否定媒介的力量和作用。这是一个媒介的时代,或者说这是一个被媒介左右、控制的时代。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它没有被媒介报道、记载,它就不会被大众知道,更不会被他们关注。从这种意义上讲,一个没有被媒介报道、记载的事件,就不能够进入历史,即便它可能是一个改变人类历史命运的巨大发现。如果没有媒介的报道,它有可能湮没无闻。如是观之,没有“媒介化”的事件,就如同没有发生的事件一样。所以,我们说:历史正在被“媒介化”。诚如程波所言:“今天的电影或者影像所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在艺术、语言、文化层面上的影响,它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进入人物的心智世界,进入到了混沌的潜在领域’,并且呈现和塑造了‘我们大脑的内在世界’。”恰恰由于“大脑被搬上了银幕”,观者可以窥见一切视界之外的存在,比如《记忆碎片》《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等,它们无一例外地展示了日常经验之外的“不可见”现实。现实与梦境,客观与主观,意识与无意识,过去与未来,大脑与宇宙,彼此交叉互动,电影孕育着大脑中可能存在的一切思维过程。应当说,程波此番对于当代电影的文化表述已经进入到电影深刻的存在本质。
毋庸置疑,人类通过影像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大众文化传播形式,是一种继印刷文化之后将艺术、娱乐、商业和科技融为一体的新兴媒体。它们的视听表意形式符合现代大众的观赏习惯,能够满足他们不同的心理欲望。对大众来说,看电影、看电视不仅已成为他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已经“成为一种体验和解释同代人或家庭的共同价值观的新方法”。所以说,“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点。”2电影以其自身特有的多重审美属性,弥合了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的鸿沟,消解了艺术与商业的矛盾,化解了艺术的思想性与娱乐性的冲突。尽管谁都不能断言,每一部影片都是这种相互矛盾的对立面的完美统一体,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电影艺术在总体上实现了对于这些冲突的有效“中和”。所以,我们赞同程波的观点:“现代媒介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渗透和影响以一种主导性的力量改变着社会结构,它甚至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于时空的传统认知。”
一部学术论文集,能够从几个重要的维度切入当今电影理论批评界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且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深入的阐发与辨析,已经表明作者的学术能力与理论功力。然而,比我们在作者的论述中所看到的学术能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在字里行间所感受到的是他所秉承那种锐意进取的人生态度,积极求索的学术精神以及独立思考的个性品格。学者这种可贵的风范,是我们在写作这篇序言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受到的。我相信,看到这部著作的读者也必定会产生这样的同感。其实,笔者与作者并没有什么私交、旧情,也不是什么师生、校友,只是在学术的道路上共同前行的伙伴,共同的学术理想,相似的志趣爱好,使我们在精神的道路上越走越近。现在承蒙朋友不弃,请我为其论文集作序,内心诚感惶惶然矣。以上的文字姑且作为这部论文集的读后感言,同时也算是我们在学术思想上的一次坦诚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