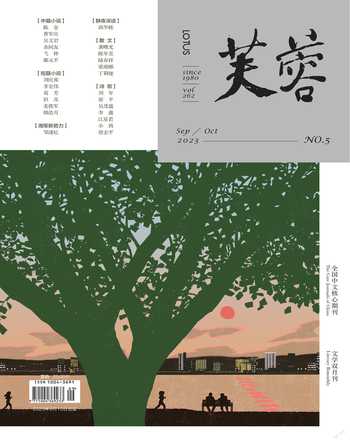无形之门
韩浩月,作家,文化评论人、影评人。在多家媒体发表大量评论、散文随笔。出版有“故乡三部曲”《我要从所有天空夺回你》《世间的陀螺》《错认他乡》等作品20余种。上海电影节传媒大奖、白玉兰奖、华鼎奖等影视奖项选片人、媒体评委。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获得者。
一
住进这栋公寓的第二年,第一次听到对门有了动静。在过去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第33层只住了我和妻子潘翠、女儿涵涵一家三口人。
在决定买下这栋公寓一处房间之前,犹豫了良久,犹豫的代价是比几个月前多花了十多万。买房的钱,是卖了几十公里外城里的老房子换来的。签购房合同的时候,手有些抖,100多万刚被打进卡里没几天,就当了首付,还欠了银行100多万。
此前,为了把现金留在银行卡里,我提出租房的建议,潘翠立刻驳掉了这个建議:“你愿意涵涵在别人的房子里长大吗?”我不愿意。潘翠在这点上特别厉害,她总是能一语中的说服我。
人一旦有了决定,就会推土机一般勇往直前,无可阻挡,就算看到网上有评论说,这栋公寓不远处有一座陵园,也没影响到我们义无反顾地付账。反正那座陵园我没看到。没看到,就等于没有。就算有,也算是“坟景房”,古人选墓地,讲究风水,差不了。
每层楼房有个长方形的环形走廊,大约可以住二十户人家,设计师的脑壳有包,没有把对门的房门错开,有些对门邻居,打开门后可以看到对方的半扇门,这在风水上,很不吉利,但售楼小姐嘴巴能说会道,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样的对门,更容易搞好邻里关系。
我家的门牌号是3303,对门是3304,我们两家就是斜对门,如果双方都打开门的话,能一眼看到对方家里。
对门住进来的第一天动静不小,主要是拉桌子腿发出的声音,我被这声音搞崩溃之前,要努力克制想冲进他家里去的冲动,我想看看他家的桌子,是不是自己会走路。公寓是“精装修”后统一交付的,数来数去,就客厅一个餐桌可以拖动,不晓得那家人要拖多少次,才能把餐桌的位置摆到满意。潘翠心倒挺大,说有点儿动静好,起码表明咱们这层人气上来了,不那么孤零零的。
我是第二天上午,见到对门邻居家男主人的。大约10点钟,他“哐哐”地砸我家门,我正躺在书房沙发上假寐,听到砸门声之后,穿上拖鞋没好气地打开了门。他穿着一件淡黄色的厚布料外套,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楼道里的灯本来就不算亮,帽子更是挡住了他三分之一的脸,所以我根本看不清他长什么样子。
“你好,大哥,我是对门新来的邻居。”他没有使用“您”字,像是我们已经很熟悉一样,“我可以进你家参观一下吗?”
“不太方便。”
“你是做什么的,大哥?”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不只是对他,所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一律选择不答。
“接下来该问我老家是哪里的了吧?”我故作幽默,但声音里其实都是冷淡。
“哈哈,是的。大哥,你老家是哪里的?”
我照例不回答,只是问了句:“有事吗,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他说:“没事没事,就是过来认个门,打个招呼,我姓张,叫张清西,你喊我小张就行了。”
我打量了一下他的整体样貌,35岁上下的样子,这个年龄,不应该自称小张了吧。
他叫张清西,还是张清晰?叫张糊涂蛮合适。我边想,边试图寻找他的眼睛,想通过他的眼神判断一下,这个家伙究竟是头脑清醒还是糊涂的人。但帽檐忠于职守,牢牢地挡住了他的眼睛。
“那个什么,大哥,”张清西似乎感受到了我的不友好,磕磕巴巴地问,“其实是想找你借个东西的,你家有电钻吗?我想在墙上钻几个眼,把画挂上。”
我把门向外关了一下,只留下一条可以看到他半张脸的缝,回到书房,踩着椅子从书架上把电钻取了下来,用消毒纸巾擦了擦上面的灰尘,走到门前,把门缝拉得大一些,将电钻交给了他。
“谢谢谢谢谢谢……”小张用吞舌音说了一串感谢的话。
“用完记得及时还回来。”我跟他说。
在一阵刺耳的钻墙声过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他把电钻送了回来,我接过电钻想要关门,他把手挡在了门框上,赔着笑说:“大哥大哥,你家有钳子和螺丝刀吗?”
“干吗用?”
“我试了一下几个水龙头,出水量都很小,可能是很久没用,出水口被铁锈堵住了,我想拧开清理一下。”
“家里没有?”
“没有。按理说这种小工具,每家都该必备的,可是我这不是刚搬来嘛。”他用讲道理的口吻说。
“用完记得送来。”我交代说,然后去洗手间旁边的工具柜,给他找来了钳子和螺丝刀。
又过了大约20分钟,“哐哐”的砸门声又响了,我气冲冲地拉开门,开口便提醒他:“敲门,敲门,记得敲门,别砸。”说罢探出半个身子,用中指骨关节敲了敲门,示意给他看,“或者按这个门铃。”我再次提示,用手指了指着被安装在猫眼上的白色电子门铃。
“好的好的,大哥,下次我像你这样用手指敲门。不好意思大哥,还有件事,你家拖把能借我用一下吗,家里地还没拖……”
“这个借不了。”
“就用一次,用完冲干净了给你送过来。”
“不行。”我语气强硬地说,“什么都可以借,拖把不行。坐电梯,下到一楼,右转出小区门,有个便利超市,那里卖拖把、扫把,说不定也卖钳子、螺丝刀。”
“我怎么没注意。”他摸摸头,然后又提出了一个要求,“大哥,能不能请你帮个忙,如果有快递送来,我恰好不在家的话,先放你们家?等我回家后再过来取。”
“不行。”
“为什么?”
“我心脏不好,不喜欢听快递员敲门、砸门、按门铃,我自己家都很少买需要快递送上门的东西。”
“那怎么办?”他没有一点发愁的样子,反倒有点嬉皮笑脸。
“给你出个主意,看到那边的水表箱了没?让快递员放那里面。”
“被人偷了怎么办?”
“这层楼目前就我们两户,我不拿,就不会丢。”
“好的好的,大哥。”
关上房门,我有点气喘吁吁,气的。
傍晚,潘翠接涵涵放学回家,餐桌上说起了邻居借工具的事,我对她说:“奇怪,我很讨厌这个人,其实人家也没做错什么,无非是多敲了几次门,多借了几样东西。”
潘翠说:“你再想想,肯定有原因的,你不是心眼那么小的人。”
“我不喜欢他敲门,听到敲门,心脏就要跳出来了。”
“胆子这么小?”
“你掉个汤勺在地上,我都会心惊肉跳一下。”
“还有呢?”
“我想到了,这个人和我长得有点像,他穿的衣服,戴的帽子,稍微的驼背,都让我觉得有点眼熟,但当时想不起是谁,现在才刚刚意识到。”
“居然像你?”
“是像我,像我30多岁时候的样子。”
“你知道你30多岁时有多讨厌了吧。”
“但是我不会去敲人家门,乱借东西,尤其是借人家的拖把。”
二
在家里闷了20多天没出门,这天是周日,初夏的阳光正好,潘翠说:“你带我和涵涵出去玩一下吧,涵涵需要晒晒太阳,运动运动。”
我问涵涵:“想出去玩吗?”
涵涵手里握着遥控器在看电视里的短视频集锦,她眼睛盯着屏幕说:“我不想出去。”
我说:“那我和你妈妈出去了,你自己在家待着?”
潘翠说:“不行,必须出去,再在家待着,要么待成呆子,要么待成傻子了。”
涵涵不高兴地关闭了电视机。
远的地方,懒得去;热闹的地方,不想去。想起离家不远处,有一个花卉市场,去花卉市场买花的提议,得到了潘翠和涵涵的一致同意。
到地下车库,忘记车放哪里了,按着钥匙找了半天,在角落里找到了整个车身都蒙了灰尘的汽车。钥匙插进点火锁眼,扭了一圈,车子启动机发出一声刺耳的“刺啦”声,没能打着火。
潘翠说:“太久没开了,你没事时应该下楼,开着遛两圈充充电。”
我没说话,屏住气,在心里默默数了五秒,再次扭动钥匙,能感觉到汽车尾部排气管重重地吐出几口脏气,发动机转动了起来。
花卉市场有两排巨大的房子,南边一排,北边一排,大好的天气,没几个顾客,营业的摊位,也不多。
许久没有买鲜花了。刚搬新家的时候,每周会来买几枝百合,买百合的同时,也会买一两盆绿萝、多肉,买棵发财树、龟背竹之类,但无一例外,百合花凋谢的时候,那些绿植也死了,约好了“集体自杀”一般。次数多了,就失去了买花、买绿植的信心,觉得家里没有这些,也不影响什么。
在南边市场里,潘翠挑了几枝百合,卖花的人给她修剪打包的时候,我选了一棵生长得很茂盛的绿萝。在打算离开的时候,涵涵提议到北边市场逛逛。
“你们才逛了不到15分钟就走,也太快了吧。”涵涵说。
两边市场所卖的花卉差不多,总共花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逛完了。出门的时候,涵涵在门口一家摊位停了下来,她没有看花,而是往上抬头,她看见了十几个笼子里装着的鹦鹉。
“爸爸,我想买一只鹦鹉。”涵涵征求我的意见,然后眼神迅速移向妈妈那边。
我也瞄了一眼潘翠,她在犹豫。
“确定要买吗?养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买回家你要负责照顾好它。”我对涵涵说。
涵涵有些退缩,但语气里还带着一点坚持:“我要买!”
潘翠说:“那就买一只吧,我同意了。”
涵涵很开心,在车里,就迫不及待地教鹦鹉说话。那只鹦鹉带着警惕的眼神,躲在笼子一角,一声不吭,刚才它话还那么多的。
回到家,潘翠清洗花瓶,安放她的百合花,我把花盆里枯萎的绿萝拔干净,将旧土倒掉,把新的绿萝从一次性塑料盆里移了出来,栽到花盆里,浇上水。
一路沉默的鹦鹉,到了家之后,变得话多起来,叽叽喳喳,一刻不停。鹦鹉有100多个品种,不知道这一只是虎皮鹦鹉、凤头鹦鹉、玄凤鹦鹉、金刚鹦鹉、玫瑰鹦鹉……中的哪一种。
涵涵想方设法让它安静下来,又是加粮,又是添水,但鹦鹉看都不看一眼,只是转着圈地叫,眼神从不聚焦在某一个地方。
“它这么闹腾,我们叫它闹闹吧。”我对涵涵说。
涵涵响应这个叫法:“就叫它闹闹。”
闹闹在家待到了第七天,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那天早晨我起床上洗手間,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屋顶消防喷头上的笼子,那里没有它的身影,但笼门打开着,这个小东西,自己打开了笼子。走到阳台那儿一看,卷帘纱窗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卷了上去,闹闹从这里逃走,太轻松了。
涵涵从床上爬起来知道这个消息后,说话时已经有了哭声:“闹闹不喜欢我们家。”
我安慰涵涵:“没事,咱们再去买一只,花卉市场里鸟多着呢。”
涵涵说:“我不要,我只想要闹闹留在咱们家。”
我说:“想飞走的鸟是留不住的。”
涵涵说:“爸爸,鸟是不是你放走的?”
我说:“怎么可能!”
涵涵说:“那就是妈妈放走的,它不可能自己走。”
潘翠说:“那个纱窗早就坏了,有风没风都会自己突然弹上去,让你爸修了几次,他也不修。”
这一天过得不愉快。晚饭的时候,涵涵突然拿过遥控器,把电视机的声音调到最低,然后告诉我说:“爸,你听听,是不是闹闹回来了?”
“不可能,没听说飞跑的鸟还会自己找回家的。”
“怎么不可能,鸟和小猫小狗一样,是能找到路的。”
“可我没听见它叫,一点也没听到。”
“你去阳台那儿看看。”
我放下筷子,走到阳台那儿,象征性地向外看了一眼,窗户外面黑洞洞的。从阳台回来之后,我跟涵涵说:“我就说吧,没有。”
涵涵说:“我明明听见它叫了,你们都别出声,仔细听听。”
是闹闹的声音。它的声音和别的鹦鹉不一样,会带着不同的情绪。只是,它高兴的时候不多,多数时候,叫声里都带着一丝焦虑、不安、害怕。本来以为,在家里待了几天之后,它会恢复我们想象中悠闲快乐的家养鸟的样子的,但可惜没有等到这一天。
虽然基本确定是闹闹的声音,但不确定声音从哪里传来的。我们在每个房间里寻找,并且仔细地检查了每一扇窗户,想看看它是不是站在窗台外面,这样的话,给窗户打开一条缝,它就能飞进来了。
可是,飞走的鸟,怎么可能自己自觉飞回来呢?
潘翠提醒我说:“我怎么感觉,闹闹是在走廊里叫呢?”
我打开家门,头顶的白炽灯把门外的走廊照得一片雪白,连一根羽毛也没看到。
但就在我打算关门的时候,又连续听到有鹦鹉叫了几声,这次我听出来了,声音是从邻居家传出来的。
关上门,我对潘翠和涵涵说了这个发现:“邻居家里有鹦鹉的叫声,像是闹闹叫的。”
潘翠不相信:“这不可能呀,纱窗开了,它飞到大自然里,这符合逻辑,但它怎么可能穿过两重门飞到别人家?”
涵涵说:“说不定是那家人从外面把闹闹捡回去的,爸爸你去敲门,把它要回来。”
“我不去,就像你妈妈说的那样,闹闹不可能飞到他家,鹦鹉也不是那种想捡就能捡到的鸟。”
潘翠说:“你爸说得对,不可能。”
我接着说:“说不定他家也有小孩子,人家也去买了一只鹦鹉。”
涵涵急了:“可那明明是闹闹的声音,我天天喂它,能听得出来。”
我说:“鹦鹉的叫声都差不多。”
涵涵反复要求我去敲门看看,我保持沉默,左思右想,没找到合适的理由与借口,这个门,最终就没有敲。
三
有一天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涵涵在看电视机上的短视频,我把各个房间垃圾桶里的垃圾归拢到一个黑色的袋子里,拎着准备下楼去扔掉,推开门的时候,险些撞到一个人的屁股,那是一名穿着工装的安锁师傅,正在拿尺子比对着门框,上上下下地测量着。
那个名字叫张清西的邻居站在门内,观察着工人师傅施工,这次张清西没有戴帽子,容貌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是一张普普通通、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面孔,他神情有些黯然,似乎是沒有洗漱的缘故,缺少一点精神,脸上有一层粗硬的胡茬。听见我家门响,他抬头向我看过来。
我冲他点点头,他迅速把头转向了房间内,没有和我的眼神对视。有十几秒的时间,他没有转回来。我跟安锁师傅打招呼,安锁师傅很客气,说:“打扰了,换电子锁,很快,顶多半个小时收工。”
在电梯叮的一声停在33楼的时候,张清西一个箭步从楼道里蹿了出来,见我还在,立刻同步收了一下脚与肩,这个家伙,有很好的刹车系统。他若无其事的放松样子,有点儿欲盖弥彰。我冲他笑笑,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打招呼。
他手里拎着一袋垃圾。垃圾袋同样是黑色的。我等待他开口说话,但他把背转向电梯壁,专心致志地看上面的广告。我想说一句“下去扔垃圾啊”,但感觉这是一句废话,于是便咽了下去,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划亮屏幕,随便看看。
到了地下负二层,往垃圾桶那里走的时候,张清西跟在我身后,但脚步明显放慢了,或许他是想避免尴尬吧。不对,几天前敲门借东西时,他挺热情的啊。
扔完垃圾,向电梯返回,再聚到楼道里,我们各自侧了一下身体,避免肩膀撞在一起。
将要进家的时候,看见安锁师傅,正在组装电子锁,从面板看,和我家的锁很像,我有点儿好奇,问了一句:“这锁是不是黑石牌的?”
安锁师傅边站起身给我让道,边说:“确实是,刚才我就发现了,和你家的锁,不但是一个牌子的,还是一个型号的。”
“巧了。”我说。
“真巧。”安锁师傅说。
这天晚上晚饭后,关掉了电视,我拉潘翠和涵涵下楼去逛逛,傍晚的温度舒适,不出去走走太浪费了。潘翠一眼就看到邻居家新换了锁,她说:“上午他们家叮叮当当了一阵子,我就猜是在换锁。”
我说:“你再仔细看看。”
潘翠问:“看什么?”
我说:“看看他家的锁,再看看咱们家的。”
潘翠发现了两把锁的共同特征,不以为意地说:“这个牌子卖得好。”
我说:“网上的电子锁,几十个牌子,几百个型号呢。”
潘翠说:“有一种人啊,就是喜欢这样,别人家怎样,他们就怎样,一点儿创意也没有。”
出了楼,看见灯火通明的商场,里面亮亮堂堂,但却没几个人。商场外,建筑轮廓留下的阴影里,有一个临时形成的小夜市,有几盏小小的直播灯在亮着,有人在卖小蛋糕、袜子、头绳、绢制假花、塑料玩具等等。
有一个摊位比较独特,一只笼子里,装着几只猫,猫很幼小,顶多两三个月大的样子,毛茸茸的,有的很活泼,好奇地向笼子外张望,有的精神有些萎靡,趴在笼子里无精打采。
涵涵看到装着猫的笼子,就蹲了下来,摊主递给她一根逗猫棒,她和小猫玩了起来,没几分钟,涵涵站起来对我说:“爸爸,我想买一只猫回家。”
我说:“咱们可是刚刚养丢了一只鸟。买猫的事,你问你妈妈。”
潘翠说:“不行,养猫可比养鸟麻烦多了。”
涵涵又用祈求的眼神看着我,我说:“如果你自己可以照顾好,爸爸可以考虑帮你买。”
潘翠说:“买的话,猫吃喝拉撒就是你俩的事情了。”
在支付了200元之后,涵涵开心地抱着猫回家了,回家的路上,路过将要打烊的宠物店,买了猫粮、猫砂盆、逗猫棒等。
家里有了猫,气氛活跃了不少。刚到家的时候,猫有些害怕,总躲在沙发底下,没多久,就开始欢腾起来了,从卧室到客厅,从厨房到阳台,一趟趟不知疲累地跑,涵涵追逐着它,在家里的活动量也多了不少。涵涵给猫起了个名,跑跑。
跑跑哪儿都好,就是晚上的时候,总是会发出一阵阵哀鸣,让人烦不胜烦,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潘翠说它是想妈妈了,涵涵说它想出去玩,我说不用管它,等到再熟悉一些,它就不会叫了。
猫可以磨炼人的性格,跑跑还是会叫,但人已经适应了。慢慢地,当它叫的时候,不去关注它,它也就收了声,默默地独自踱步,假寐,时常望着窗外发呆。
四
这真是一个寂静的夏天,在寂静中开始,就要在寂静中结束了,俯视下去,小区院子里的绿树疯长了一个夏天,变得比以前高大了不少,连过去有些枯黄的冬青,也吸收足了土壤里的养分和水分,叶子绿得发黑,一副营养过剩的样子。
这天上午8点多的时候,我正在昏昏沉沉地睡回笼觉,门外传来一阵砸门声,很大,带着点不砸开誓不罢休的意思,我用手安抚着心脏,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经过洗手间的时候,打开水龙头,吞了一口水漱了漱口,强压着火气去开门。
打开门,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用狐疑的眼神看了看我,又想探头朝屋里看。我挪动了一下,挡住了他的视线问他:“你是干吗的?”
中年男人说:“哦,我是居委会的,来登记一下,这间房子你是租客还是房东?”
我说:“租客还是房东,你们难道不是很清楚吗?”
他说:“那了解了,你是自住的,这是一份登记表,麻烦你填一下,家里几口人?”
我说:“三口。这些信息办理收房的时候都填过啊,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他说:“不好意思,麻烦你,确实需要填一下。”
我说:“那麻烦你,下次别砸门,看见没有,这儿有门铃,按一下,听得见。”
他说:“好的,好的。”
我倚在门框上,在他递过来的文件夹上的表格中填写着字,来自电梯口的风拐了个弯吹了过来,小腿能明显感觉到带着凉意的风在门口拐了个弯,冲到了家中客厅里。
花费了三四分钟时间,潦草地填完了表格,交还给他,没说任何话,我把门撞上并反锁了。
那个人走了,我听到电梯停在33楼的声音。
被吵醒的潘翠和涵涵,也起床了。潘翠在厨房准备早餐,涵涵从洗手间出来,寻找着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呢?”涵涵问我。
我说:“你各个房间去找找,丢不了。”
涵涵把所有房間找了个遍,没有找到,再说话的时候,声音里已经带了点哭腔:“是不是你开门的时候,跑跑从门缝里跑了?”
我说:“绝对不可能,它要是跑出去,我能看到。就是看不到,它出门也会碰到我的腿,我能感觉到。”
涵涵说:“就是跑了,你去找找。”
我没有出门去找,而是去各个房间转了一圈,跑跑一声不吭,我敢保证它就躲在某个角落里。可能,它是被刚才砸门的声音吓到了。
一个小时过后,我和潘翠、涵涵共同确认了一个事情:猫丢了,并且很有可能是我打开门做信息登记的时候跑的。
我带着沮丧的心情,出门去找猫。先是去了顶楼,顶楼那里四周有近两米高的阻隔墙,猫如果朝楼上跑的话,会比较容易找到。
午间的风,卷着被晒黄了的报纸碎片,在楼顶无聊地卷动着,没有任何动物行走的踪迹。我喊了几声“跑跑”,没有得到应答。
找猫是没法坐电梯的,只能一层层地向下寻找,33层,走到地下车库负二层的时候,我已经气喘吁吁,无力地晃动着手里剪开的猫条,试图以跑跑熟悉的食品气味吸引它出来。
车库里很安静,每辆车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原地,没有一辆车开出去,也听不到给车打火的声音。
“跑跑……”因为车库里没有人,我没有顾忌,大声喊了几声,车库的回声刺激着耳膜,耳膜有些疼痛。
我朝车库深处走去,那里有一排废弃的地下大排档商场,门不知道被谁踹开了,猫要躲起来不被找到的话,那里算是一个天堂。
我打开手机手电筒,朝大排档商场里照的时候,同样的一个手机手电筒发出的光,打在了我的脸上。我闭上眼睛,在失去视力十几秒后,睁开眼睛,看见张清西走到了我的面前。
“咳,你干吗呢,差点晃瞎了我。”我半开玩笑,但声音里有压制不住的恼怒。
张清西说:“是您啊,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说:“找猫,我家猫丢了,你看见里面有猫吗?一只三四个月大的小猫。”
张清西说:“里面一只猫也没有。”
我说:“不可能呀,我记得这里面起码有七八只流浪猫。”
张清西说:“真的没有,我骗您干吗?!”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问他:“你打着手电筒在里面干吗呢?”
张清西说:“找猫。”
我说:“你找猫?你的猫也丢了?你家也养猫?”
张清西只回答了个“嗯”字,就从我的肩膀处错开身,走掉了。
五
这天晚上,我情绪有点不对劲,躺在床上,借着床头灯看手机的时候,忽然心脏一阵紧抽。我保持手端着手机的姿势不动,慢慢地呼吸,逐渐地加大吸氧量,以前用这种方式,可以在几分钟里平缓下来。
但是这次效果似乎不大好,我大口吞咽了一下空气,胸腔一阵剧烈的疼痛。潘翠躺在我的旁边也在刷手机,但我没有力气呼唤她,只是静静地等待紧张的心脏舒缓下来,好让我有足够的力气,去把床头柜里放着的那一小瓶硝酸甘油取出来。
终于,我的手可以拉开抽屉,手伸进抽屉里胡乱摸着,发出一阵稀里哗啦的噪声。
潘翠问:“你找什么呢?深更半夜的。”
我没有说话,终于摸到了那个小瓶,拧开瓶盖,往手心倒了几粒药丸,也没数到底有几粒,一并放在了舌底下,然后闭上眼睛,等待不适感自己消除。
自从猫丢了之后,涵涵很不高兴,在家的时候,常常心不在焉。她想再买一只猫来,但被我和潘翠拒绝了。可能在内心深处,我和潘翠都希望那只猫丢掉,或者自己走掉。也可能那只猫预感到了我们的态度,自己跑了。
在我们就要忘记丢猫这件事后的一天早晨,一家三口人正在客厅吃早餐,涵涵突然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闭嘴手势。我不解地看着她,她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指了指我的耳朵,然后小声说:“听听,跑跑回来了。”
屏息静气地听,我果然听到了猫的叫声,只是不确定这是不是跑跑的叫声。
我说:“这不可能是跑跑吧,跑跑的声音没这么哑。”
潘翠说:“你们两个魔怔了,哪儿有猫的叫声?”
涵涵说:“爸,你打开门看看,说不定跑跑就在门口,我听说许多跑丢的猫能自己找回家来。”
我放下筷子,穿过走廊,小心翼翼地打开门。
门外并没有猫的身影,但就要关上门的时候,我听到了一声软弱无力的猫叫声,确实有点像是跑跑的叫声。
涵涵也跑了过来,她惊喜地说:“我没说错吧,就是跑跑,就是它。”
我和涵涵听了半天,最后基本确认,猫叫是从邻居家发出来的。
重新坐在餐桌前的时候,我说起那天去地下车库找猫,遇到张清西的事情,他说他家猫也丢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意味着,在我们养跑跑的时候,他家也养了一只猫。这不奇怪,小区里住的人家,不是有一只猫,就是有一条狗,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丢猫这个事,也要凑热闹一起丢?
涵涵提出了一个要求,她希望我能够敲开邻居家的门去看看,究竟是不是跑跑跑到了他们家,或者他们家收留了离家出走的跑跑。
我不想去。那只叫闹闹的鹦鹉丢了,涵涵一直觉得鹦鹉飞到了邻居家里,让我敲门去看看,但我一直坚持没去。
但这次扛不住了,看着涵涵眼睛里越来越多的失望,我决心去试试。
“你家猫找到了?”在张清西打开门的一瞬间,不容他说话,我劈头就问。
“你说什么?”张清西显得有点猝不及防。
“我说,我听见了你家有猫的叫声,前段时间,你在地下车库找猫,你家猫不是丢了吗?”我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
张清西淡淡地回答我:“找到了,那天它自己跑回家了。”
“自己跑回来的?”我说,“我不相信有这事。你家的猫,是什么时候买的?”
张清西笑了一下说:“朋友送的。”
我说:“好朋友。”
张清西说:“是。真是好朋友。”
我说:“能让我看看你家猫吗?”
张清西说:“老婆孩子都在家呢,不方便,改天吧。”
我追问:“你家猫是什么品种?”
张清西反问:“你家的呢?”
我说:“英短。”
张清西说:“我家是暹罗猫。”
我说:“你家的这个更名贵。”
张清西淡淡地说:“孩子喜欢就好。”
既然话说到这儿了,我不禁提高了点音量继续发问:“你们家是不是还有一只鹦鹉?”
张清西说:“你怎么知道?”
我笑了一下说:“这门的隔音没那么好。”
张清西说:“我家真的有一只鹦鹉。”
我问:“什么品种?”
张清西说:“谁知道呢,鹦鹉有100多个品种。”
谈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因为张清西在说话的同时,逐渐在把门缝縮小,这带有逐客的意图,就像我曾经对待他那样。
涵涵认准了邻居家的猫就是跑跑。我说我们家的是英短,人家的是暹罗,不可能是跑跑。涵涵说那怎么叫声这么像?我说猫的叫声不都这样吗?涵涵说不是的,我能听懂跑跑在喊我名字。我说喊你什么?涵涵说它在喊我姐姐。我说别开玩笑了。涵涵说你想办法进到他家里看看,要真的不是跑跑我就再也不问了。
我固执地没有去敲邻居家的门。我不喜欢别人敲我家的门,自然更不愿意去敲别人家的门,不受邀请而进到别人家里,这个更做不到。
在那几粒硝酸甘油发挥作用之后,紧张的心脏舒缓了下来。我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你怎么了?”潘翠问我,手机屏幕的光芒照射在她脸上,我转脸看了她一眼,头脑一阵眩晕。
“什么我怎么了?”我烦躁地回答她。
“我就是想问问你怎么了,没事叹什么气啊,还叹那么长的气?”
“你老老实实看你的手机挺好的,别管那么多。”
“我看手机怎么得罪你了?”潘翠把手机反过来,啪的一声扣在床头柜上。
“你能不能小点声?”我怒火中烧。
手机扣在桌板上的声音其实没多大,但不知道为何,听起来却无比刺耳。
潘翠没有再回应,而是把手机拿起来,又往桌板上扣了一下。我和潘翠爆发了一阵激烈的争吵。
涵涵的门紧关着。
这场争吵持续了一个小时,估计楼下几层的邻居都听见了。那个时候已经是深夜,但没有邻居表示抗议,因为没人在群里发消息抗议。所有人都在默默地睡着,或者说,所有人都在默默地听着这栋孤独的大楼中的一个房间发出的争吵声。
累了,我和潘翠喝了几口瓶装水,各自躺在床的一边,准备睡去。
失眠。睡不着。半个小时左右,我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争吵的声音,开始的时候听不太清楚,后来吵架的声音越来越激烈,已经远远超过了刚才我和潘翠吵架的声音。
这争吵声是对门邻居家传过来的。再接下来,就有了锅碗瓢盆摔在地上的声音,然后,就是其他重物摔落到地上的沉闷声音。
一阵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传来。
潘翠说:“打110吧。”
我没吭气。
潘翠说:“帮打一个110吧,别出了人命。”
我说:“要打你打吧。”
潘翠也没打那个电话。
六
张清西是什么时候爬上楼顶那堵两米多高的围墙的,没人知道。
我早晨7点多点准时醒来,习惯性地打开小区群,看到群里在谈:有人跳楼了。
6点多的时候,我耳边隐约听到消防车、救护车、警车紧促的鸣笛声,不过因为睡得太过昏沉,没有醒来,也没去想发生了什么。
跳楼的是张清西,有一早出门遛弯的邻居,在小区门口保安岗亭的位置,拍摄了他落地时的视频。他从让人望着眼晕的楼顶,一跃而下,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
有人问,是3号楼的吗?有人回答说,是,3号楼,靠近马路的那栋楼。
3号楼就是我住的这栋楼。确切地说,事发现场之一,就在我头顶上,与我只有一层楼板之隔。
张清西在早晨天蒙蒙亮的时候 ,打开自己家的门,走了十多个台阶,推开通往顶楼的安全门,爬上了两米多高的防护墙,双腿架在墙外,抽了一支烟。
他抽烟的时候,有眼尖的邻居看到高楼顶端的边缘处有个人坐在那里,于是报了警。
在消防人员忙着布置大型气垫,警察坐着电梯往楼顶冲的时候,张清西把烟头丢在了楼顶,跳了下去。气垫沒能精准地接住他。
我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见到张清西的邻居,见到他的时间是昨天下午,我拿着电卡去物业买电,正在窗口办理的时候,隐约感觉到有人在观察我,转脸便看到了张清西在最靠边的一个窗口,估计也是在买电。
我在收费单上签字的时候,张清西所在的窗口发生一次简短的冲突,是物业服务人员与他的对话。
“你家的物业费没有缴,按理说是不能卖电给你的。”物业服务人员说。
“法律明文规定,不得把买水买电和缴物业费挂钩,信不信我投诉你?”张清西声音很平静,但也很坚定。
“什么情况?就买20块钱的电?真是开了眼了。”
“谁规定不能买20块钱的?我想要买200万度电,你有权限卖这么多吗?”
出物业的时候,我和张清西在门边相遇了,我默默地帮他拉开了门,他瞥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一步跨了出去。
我刻意放慢脚步,走在他身后。
在3号楼等电梯的时候,我在电动车棚那里静立了一会,等到他乘的电梯上去了,我才走进楼栋。
张清西的话题,在小区群里只存在了半天,半天之后,就再也没人讨论他的事情了,仿佛他从未在这栋楼里居住过一样。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和潘翠、涵涵下楼散步。关门的时候,电子锁发出闭锁的马达转动声。这马达声,促使我下意识地往3304室的门锁那里看了一眼。
我用手轻轻触碰了3304门锁的电子面板,通常这个时候面板会亮起来,显示出白色的数字,我知道这样做有些冒昧甚至是冒犯,但还是没有忍住,做出了这个动作。
门锁面板没有亮。
张清西的妻子——那个半夜尖叫、痛哭的女人,还有那个孩子——总是在楼道里拍打篮球却一声不吭的男孩,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很想敲敲门,甚至弯起了手指,但没有敲。
那扇门虽然隔音不好,但看上去显得很厚重、结实,和我家的门一模一样。之所以停住手没有敲,是因为我忽然觉得,这是一种不必要的打扰。我仿佛看见张清西一家,依然如往常一样,正坐在餐桌前默默地吃晚餐。
几天后的一天上午,一阵让人崩溃的、急促的砸门声从外面传来。
是身上穿着一身物业工装的人在敲门,一个小姑娘,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夹着一摞表格,她说她是来让居民填居住基本信息的。
我说:“前段时间不是有人来过吗,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你们非得做两次?”
小姑娘说:“是吗?可能他们是居委会的人吧,和我们不是一伙的。”
我说:“莫非你们都是借着统计的由头,来骗私人信息的吧?”
小姑娘扑哧笑了:“不至于,不信你打一下物业电话,问问我是不是真的。”
然后她指了指挂在胸前的工作牌,上面印着她的照片。
填完了表格,将那张纸交还给她,她道谢准备离开的时候,我忍不住问:“这就走了?3304的人呢?怎么不去敲门也统计一下?3304还住着人吗?”
物业的人一愣:“这里住过人吗?”
我说:“怎么没住过?你们物业也太不专业了吧?”
她说:“不对啊,我印象里这家一直没住过人,您不是记错了吧?”
我说:“你敲敲门,万一有人在呢?”
“我不敲,还有别的事,我先走啦,您忙着吧。”说罢,她一溜烟地朝电梯那儿跑去了。
我目送她消失在楼道走廊,在关上自家门之前,又看了看对门的门牌号——3304。门牌是整栋楼所有入户门上都粘贴着的那种欧式牌子,字体与大小也是统一的,没什么特别之处。
后来,我偶尔也听到鹦鹉和猫的叫声,打开过两三次门,那叫声仿佛又没存在过一样。再后来,就再没听到过鹦鹉和猫的声音了。
整个33层,仍然只居住着我们一家三口人,我、潘翠和涵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