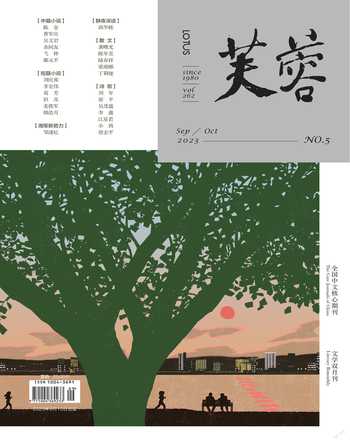画像
梁平
神经疼
每次有人给树木修枝,
我手指的关节,疼。
然后不停地抓捏、小运动,
训练自己习以为常。
被修剪了的树,不说疼,
习惯了刀剪。这样的比对好傻,
我明白疼痛自知,
与联想无关。
不是所有的痛都是伤害,
也有对麻木的干预和警示,
矫正太多的熟视无睹。
我确定我应该是神经性发作,
那疼,不会动骨伤筋。
这是冬天的规定动作,
与春天还有多远没有关系。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一根红头绳飞起来,凌空舞蹈,
我看见一个打死的结。
风声紧
风声很紧,行走小心翼翼,
一片树叶砸死一只麻雀,被野猫叼走。
斑鸠比麻雀魁梧,经常绝处逢生,
在院子里贵为凤凰。
蝴蝶回来了,没有去年的肥硕,
站在花蕊上摇晃,有醉态。
如果季节原谅,花儿不依不饶,
花瓣是打开的翅膀,也想飞,
没有蝴蝶,梦就碎了。蝴蝶有过承诺,
带花儿一起飞,想想也浪漫。
我见过的生死、海誓山盟多了,
那只鲜艳的蝴蝶,好瘦,好单薄,
不该随便留下豪言壮语。
而且,这院子堆积满满的前朝落木,
所有的轻佻,经不起风吹。
经历过
风吹走手里一张便条,
与一片树叶接头,纸上的信息有隐喻。
一只鸟飞过,假装什么也没看见,
天色越来越晦涩。
无花果已经挂满枝丫,
突然的花开,被江湖走卒裹挟而去。
甜言蜜语一句比一句煽情,
轻信季节死无葬身之地。
冬天的笑都不怀好意,
比笑里藏刀更不容易辨别,
雪花接近的目标还没有觉察,
我发出的暗号被风腰斩,零落成泥。
画 像
整整一晚都在画,
画一幅被拿走一幅。
要画的人多,看不清颜面,
手臂从四面八方伸来。
好在画的小品,极端虚无,
比鬼画的桃符还烧脑。
无论蒙别人还是蒙自己,
反正轻车熟路,信手拈来。
幻觉真好,月亮坝看影子,
盖世无双。其实画都是稀里糊涂,
胡乱堆码一些色彩,
要的就是花哨。
赞美一句比一句好听,
天边亮了,才知道复制了南柯。
镜子里看见有白色颜料打翻,
溅在鼻梁上,好有喜感。
梁 祝
梁山伯与祝英台,
十八里相送之后,化了蝶。
他们那点事儿,从坊间的流言蜚语
到落笔成白纸黑字,
不是也是了。
梁兄青春期没有暧昧,
乔装的英台举止得体,
也算清清白白。兄弟与兄弟,
比男人与女人之间,
更有一种情怀,牢不可破。
我的本家最早与英台,
就是兄弟,我想叫英台嫂子,
或者弟妹,尽管真的不是。
宁波鄞州滴落很多软语,
淅淅沥沥。
古墓遗址里的梁兄保持沉默,
飘飞的衣袂没有成双成对。
风被小提琴协奏成孤零的雨,
过眼一只蝶,老态龙钟,
已经扇不动翅膀。
读书梁
北郊一个普通山梁,
名字很好,梁上飘飞的书香,
在百年前那间茅屋的油灯下,
弥漫多年,从那根羊肠子的道上,
走出一个秀才。
秀才不知去向,
读书梁在城市隔山隔水的地方,
有后来人很美好地记上一笔。
尽管听不到读书声了,野草疯长,
那条小路,瘦得看不清模样。
对面半岛城市一天天发胖,
有很多脂肪漂过江来。
最先堆积起坡月山庄、爱丁堡,
后来有了景馨苑,再后来,
一夜之间垒起黄金堡。
有好多好车来来往往,
保安举手致敬。好多大腹便便的人,
走得大摇大摆,互不搭理。
那间茅屋在这里肯定没有产权,
那些人和秀才毫不沾边。
我也是半岛挤出来的脂肪,
这和当时的肥胖有关,
以后开始减肥,减得格格不入。
也许我丢人现眼了,
无奈《重庆书》把我关在里面。
在水之上
孤寂中旅行,
水上时间失去控制,软床想哭,
想找人说话,折磨自己。
风吹来,唇寒,齿彻,
感觉玻璃破碎,桅杆挑落了星星,
水在船尾激动不已。
鄂语柔和如水,有刀刺。
船舷上探出人头,疑是奉节城门上,
曾經悬挂过的风景。
不是每个人的伤感都在日记,
有极好的水性又如何,
或生于水,或壮烈于水。
在水之上,天机不可以泄露,
我,以及一尾鱼。
那 人
让那棵树成为遗址,
淡化植树情节,那人以为如何?
云团自天顶渐渐松润,
做压城之状逼向小巷深处。
落日直截了当,
宣布一滴泪的归宿,死一般寂静。
更夫失眠,一夜之间换了朝代,
弹拨不再流行。
从树的根部攀缘而上,
一只蜗牛,身后之路如此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