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驻留的生态与“在地性”名片
张意 崔兆萱
在当今快速变革的社会中,艺术驻留愈发成为艺术机构和艺术家与“他者”互动、构建“相遇”的重要方法。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逐渐发展,西方与东方、全球与地方、生态与方法等诸多冲突和问题不断催生,中国的艺术机构纷纷自发构建艺术驻留项目。其中,杭州天目里BY ART MATTERS RESIDENCY驻留项目、成都A4美术馆和重庆“器·Haus空间”“501序空间”的国际艺术驻留项目,因其国际交流的出发点与本地文化的深入融合而备受瞩目。同时,诸如成都的蓝顶美术馆、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重庆的十方艺术中心以及上海的“燃冉”艺术驻留项目,则更强调本土文化的主动性。在这些不断催生的艺术驻留项目中,它们形构出从国际交流到本土文化的艺术生态。
艺术驻留作为艺术“在地”的公共方法
艺术驻留作为一种艺术“在地”的公共方法,在当代艺术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积极探讨。这一方法的兴起和发展,既受到社会变革和全球化的影响,也与艺术家、机构和观众的需求紧密相连。艺术驻留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实践方式,正在重新定义艺术与地域、艺术与社会的关系。
艺术驻留通常的设想是为外来艺术家提供一个深入了解城市、社区和个体的机会,通过与在地人群的互动,融合不同文化、历史和经验,从而创造出全新的艺术体验和创作。艺术驻留项目的初衷是搭建一个跨越地域和文化的桥梁,让“他者”与“在地”相遇,共同创造出独特的艺术语境。A4国际艺术家驻留项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最初以较短的驻留周期为外来艺术家提供了一个“融入”的机会,让他们与城市、社区、历史和人群发生对话,从而激发出新的艺术灵感。同样,强调“国际”间的交流对话的天目里BY ART MATTERS RESIDENCY驻留项目,在招募国外艺术家的同时,也招募杭州地区之外的中国艺术家,他们2002年的驻留主题“本地魅力”,昭示出强化在地性创作,突出本地自然与城市环境相结合的文化作用力。
与此同时,国内的其他艺术机构也纷纷加入艺术驻留的行列。以蓝顶美术馆为中心,其周边有着成熟的艺术社区,通过艺术家驻留计划,让非当地青年艺术家与该社群发生联结,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灵感。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则通过艺术与社会创新实验室,将艺术家、社区和社会组织联系在一起,为艺术家提供了与社会互动的平台,使艺术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再比如,上海的“燃冉”艺术家驻留项目聚焦城市更新和创新实践,通过艺术家的创作,探讨历史记忆、人文现状以及社会变革。
综上所述,艺术驻留作为一种艺术“在地”的公共方法,正逐渐改变着艺术的生态和社会的面貌。它促进了跨文化、跨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不曾停滞的交流与“赛博驻地”
2020年,全球疫情席卷而来,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变革。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艺术界也在思考如何继续创作和沟通合作。与此同时,艺术驻留项目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不曾停滞的交流,并逐渐催生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赛博驻地。
香格纳画廊在2020年推出的“艺术家云驻留”系列,通过线上的方式,艺术家们得以跨越时空的限制,与观众分享他们的创作过程。比如,赵洋的“云驻留”项目分两天呈现:第一天,以随笔的形式分享他的思考,《酒与黄豆》一文引发了读者深入的思索与共鸣;第二天,赵洋通过照片将观众带入他的工作室和日常生活,为观众打开了一扇窥探艺术家生活的窗户。
A4美术馆也在疫情冲击下积极创新,推出了“艺术家隔离日志”线上项目。在数字化的公共空间中,艺术家们与观众展开了对话,分享了他们在隔离期间的所思所想。例如,“You Open a Box”团队通过“影响之圈”项目传递了社交距离的重要性,他们用圆圈的方式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安全距离,以一种巧妙而有力的方式传达了疫情背景下的社会关怀。
然而,与传统驻留项目相比,“赛博驻地”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虽然数字化交流让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更加便捷,但也可能削弱了现实空间中交流的深度和质量。短暂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可能无法完整地传达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和情感,观众也可能只停留在表面的了解而难以深入思考。艺术驻留在疫情的挑战之下,作为一种特殊的创作和交流方式,在数字化时代催生出了“赛博驻地”的新概念。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但数字化交流仍为艺术家和观众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当艺术驻留成为集体“临时的乌托邦”
从古至今,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从未停歇。托马斯·莫尔在其《乌托邦》一书中,描绘了一个人人平等、财富共有的美好世界。然而,现实中的种种限制使得乌托邦难以实现,成了一种远不可及的理想。在当代艺术领域,我们或许能够通过“艺术驻留”找到一种近似乌托邦的存在。
正如1933年创办的黑山学院(Black Mountian College)所体现的,乌托邦并非只存在于文字之间,它能在现实中以一种集体的、临时的形式呈现。这个学院不仅是教学的场所,更是充满了交流、合作等多种功能的社群。它与如今的“艺术驻留”有着某种共通之处。同样,重庆的“器·Haus空间”“501序空间”和十方艺术中心,都集中在四川美术学院附近,他们的发起人均为美院的老师。这些艺术空间的集中呈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乌托邦”群落现象。
同样具有“乌托邦”式体验的驻留项目“方志小说联合驻地计划”,它将“方志”与“小说”相结合,借用了古代方志的概念,将风俗、物产、舆地等详尽的地方知识与地方传说相结合,同时邀请艺术家以“小说”的方式进行记录创作,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创作模式。这种创新的尝试传递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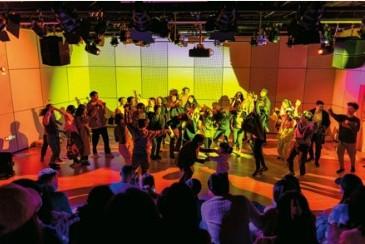
藝术驻留本身作为一种集体的“临时乌托邦”的存在,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艺术驻留的魅力,为艺术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仿佛在现实中重新书写着那个最美好的幻想社会。
当“在地性”成为一种标签
当下,艺术驻留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而在这股浪潮中,“在地性”成了一个备受强调的关键词。在追求“在地性”的过程中,一些关键问题浮现出来,引发了对于艺术驻留项目本质的深刻反思。当“在地性”成为驻地项目的标签时,是否可能存在一种背离,使得项目的初衷和“在地性”本身产生错位?
艺术驻留项目的兴起源自对创作环境的渴望以及交流的需求。随着文旅产业的复苏,催生出一些以度假型酒店为依托的驻留项目,但在其中伴随着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项目为艺术家提供了在异地创作的机会,但在时间和深度上未必能够满足创作的深层需求。因此,尽管它们标榜“在地性”,却未能真正推动艺术驻留项目的深入发展,亦难以促成有意义的学术对话和创作成果。
艺术驻留作为一种实验性创作方式,其核心应当在于对在地环境的洞察和融合。当一个驻留项目将“在地性”视为标签,但仅仅依赖于地点的吸引力,而未深度融入当地的文化与社群,这是否意味着它正在偏离“在地性”的内涵?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从更广阔的视角予以审视与思考。总而言之,当“在地性”成为驻留项目的标签时,我们必须审视其背后的真实内涵。“在地性”不应仅仅是一个概念,更应是一种实践。艺术驻留项目应更加重视对当地文化的理解与融合,通过与社区的密切互动,以及尽可能注入学术交流和调研工作,将艺术真正介入当地生活之中。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在地性”不会被空洞的标签所掩盖,艺术驻留项目方能展现其应有的价值与意义。
注:张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崔兆萱,四川大学哲学系本科生。
责任编辑:孟 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