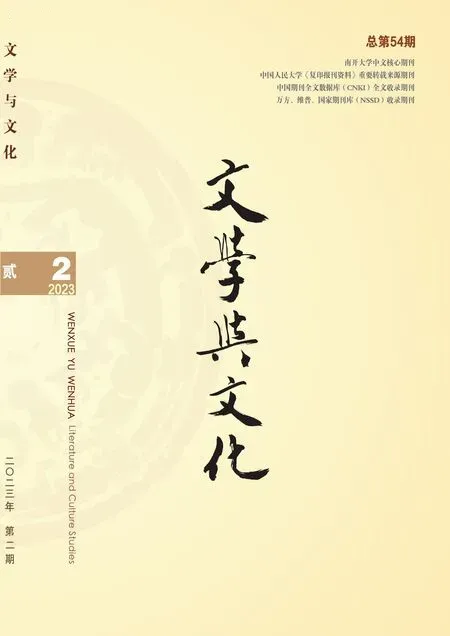民间文艺中的“苏二姐”意象及其多元审视*
李祥林
内容提要:“苏二姐”这一人物在民歌中常见,也不仅仅见于民歌,其是中国民间文艺所创造的符号化审美意象或意象化审美符号。借助这个约定俗成的符号,不同区域和不同族群的作者编码出多姿多彩的作品。时而,“苏二姐”化身为羌族村寨的“美呐巴啧”,是一个性情爽利、端庄美丽的羌家女子;时而,《苏二姐》在地化为四川乡村苏姓作者创作的歌曲,苏二姐以其女儿身份出场,她还做得一手好菜,至今当地有以“苏二姐”命名的菜肴闻名;时而,这“苏”姓女子又成了云南“嵩明人越看越亲热”的苏家村人。凡此种种,体现出“苏二姐”作为审美能指在鲜活的民间文艺创作中不乏弹性的运用潜力。
“苏二姐”是中国民歌里的常见人物,也不仅仅出现在民歌中。着眼民间,结合方言、相关叙事以及多民族文艺,会发现其涉及好些富有趣味性也不乏学术性的话题。下面,就此进行梳理和论述,以供学界参考。
一 市井故事中的“苏二姐”
“苏二姐”之称,蜀地竹枝词中有见,且留下相关龙门阵。过去,看相摸骨、测字算命是老风俗,流行于民间。民国时期,省城成都有王姓瞎子替人摸骨算命,以此为生,市井中相传其功夫了得,神奇、精准得很,四面八方来找他测算者多多,这位生意甚佳的算命先生也自称“摩骨神相”(摩、摸相通)。某日,来了一伙当兵的找王瞎子摸骨,其中有称“苏二姐”者,王瞎子摸来测去,始终不得要领,最后这位“神相”被难倒,窘迫尴尬下不了台,把自己也搞哭了。市井中这有盐有味的龙门阵,被记者捕捉到,登上了报纸,传声遐迩。当时蜀地文人刘师亮得知此事,也以调笑口吻在他的《成都竹枝词》中留下记录:“相谈摩骨具先知,共道王家瞎子奇。底事反遭‘苏二姐’(士兵的译音),一摩摩得哭嘻嘻。”诗末自注:“报载成都王瞎子自称摩骨神相,有丘八数人往求摩相,竟把王瞎子摩哭了。”
竹枝词中提及“苏二姐”,括号内注明是“士兵的译音”,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这译音,我认为应该是英文的译音。士兵之英文作“soldier”,其读音正跟带儿化音的“苏二姐”相近。丘八们戏耍王瞎子,故意谐其音报名字“苏二姐”给算命先生,后者眼睛看不见,以为是来了个女的,可是将来者五大三粗的骨相摸来摸去,要么是怎么判定也不像女的而下不了断语,要么是给出了测算结果却大大错位。这么一来,号称神奇的王瞎子便栽倒在恶作剧的丘八手中,“摩骨神相”再也“神”不起来。读此诗,不难想见当时的场景: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围观者哄堂大笑,出了洋相、脸面尽失的算命先生从此生路断了,只有哭地无门。在那动荡的年代,王瞎子也是挣扎在底层社会的庶民。从“底事”(为何)这设问句看,竹枝词作者尽管是以调侃的口吻描写市井事象,归根结底还是有某种哀其不幸的同情在诗中的。
或以为,对上述竹枝词中作为士兵之英文译音讹读的“苏二姐”,也可换个角度理解为诗作者不过是借用了当时社会上据英文将士兵讹称为“苏二姐”的流行说法。但如此理解,丘八们究竟是怎样退了“摩骨神相”的神光而恶作剧地将其搞“哭”了,诗中未写出,读者也猜测不了,诗作便索然无味。所以,笔者宁愿按照前一种理解来读刘师亮的这首竹枝词,为的是更有趣味也更有内涵些。不管最终能成立的是哪种理解,有一点倒是明确,“苏二姐”的确是那个时代的流行字眼(因为“苏二姐”不仅仅出现在竹枝词中或文人笔下,其在民间文艺中有更频繁的亮相,且看下文),诗人借此字眼入竹枝词,至少当时的读者是明白意思读得懂的。那么,谁是“苏二姐”?为何“苏二姐”会成为众所周知的流行词语?从“苏二姐”之称生发出去,还能读出些什么信息呢?
二 作为时髦字眼儿的“苏”
刘师亮(1876——1939),字云川,四川内江人,做过私塾,自号谐庐主人,为人正直,有文才,好打趣,目光敏锐,见解独特。1930年,他在成都创办《师亮随刊》,著有《师亮诗草》《师亮谐稿》《师亮杂著》《时谚声律启蒙》等,留下上千首诗词,有剧作《胭脂配》《错吃醋》,还写了好些脍炙人口的对联,其作品及故事至今在民间流传。当年,他借用竹枝词这种形式,川话连篇地写了不少记述时事、针砭时弊的作品,自称:“敢将旧调说新诗,聊作沿街唱竹枝。点缀太平新气象,不风不雅乱填词。”(《成都青羊宫花市竹枝词》)又说:“借开玩笑莫张巴,游戏文章共一家。君既抬花人不管,何妨我又再抬花。”(《姑姑筵竹枝词》)就以《成都青羊宫花市竹枝词》为例,这位风趣的文人先一口气写了30首(1923年),觉得不过瘾,几年后又续写了70首(1928年),凑足百首。此外,他还洋洋洒洒地写了近80首《成都竹枝词》,以及《新生活竹枝词》《新式美人竹枝词》《姑姑筵竹枝词》,将地方风情写得活灵活现。前述故事中的“苏二姐”这一人物称呼常见于川人的口语中,仔细考究,苏二姐姓苏,这“苏”字在川话中大有来历。刘师亮笔下屡屡述及与“苏”有关的世风时俗,出语诙谐,甚至令人捧腹,如前述连篇成套的《成都竹枝词》又云:“吊梳纂纂学苏州,浪说披毛近下流。花样随常都在变,而今又尚倒揪揪。”据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诗中“吊”之原文有提手旁①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9页。在林孔翼、沙铭璞辑《四川竹枝词》中,刘师亮的《元日游重庆真武山竹枝词二十首》中有一类似作品,云:“吊梳纂纂说扬州,剪发而今学美欧。有个女郎存古粹,高堆旧式牡丹头。”(四川人民出版社,第14页)此处写作“吊梳”,看来是口语记音,字无定型。至于说“苏”说“杨”,实无二致,都指的是来自苏地的时髦发型。另,本文所引竹枝词,若无特需注明者,均见此二书。,但电脑打不出字来,应是当时使用的俗字。川话“纂纂”和“揪揪”(鬏鬏)指女子发型,前者似饼状,后者为条状,至今二语仍见于民间口头。“披毛”指女子额前刘海。揣摩其意,“吊梳纂纂”无非是说刻意将发型梳成“纂纂”样,此乃女子追求时髦打扮,学的是“苏州”样式(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四川人服饰打扮学“海派”“港式”就与此类似)。这首竹枝词向我们透露的信息是,当年时风使然,大家追捧的正是代表新潮、时髦、洋盘的来自下江或曰江南的苏州产品、苏州样式、苏州派头。
历史上,四川是移民大省。清末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载:“成都之地,古曰梁州,历代皆蛮夷杂处,故外省人呼四川人为川蛮子,也不知现代之成都人,皆非原有之成都人,明末张献忠入川,已屠戮殆尽。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占土地,故现今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四川方言深受移民文化影响(尤其是明清以来),比如“苏气”。1924年的《乐山县志·方言》:“称人美好曰苏气。”1931年的《重修南川县志·土语》释曰:“从前外来服饰之物,苏州为美,故土语通称人物文雅脱俗曰苏气,曰苏派,且直曰姑苏。”口语记音,亦有写作“书气”“舒气”的(川人说话,卷舌音往往混同于平舌音)。方言研究表明,该词“不仅反映了苏州风物对巴蜀文化的影响,而且表明了东吴与西蜀之间的商贸往来”①崔荣昌:《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页。除了四川话,类似词语亦见于湘、赣方言。。清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百首刊于嘉庆年间,其中有云:“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述及当时省城多有来自苏、赣、陕等地的移民,他们甚至成了市民主体。《跻春台》由清末中江人氏刘省三编著,是用四川方言写就的一部拟话本小说集,书中保留方言俗语不少,就屡见“苏气”“姑苏”等,如“于是寻些衣服首饰,收拾得苏苏气气”(卷一《过人疯》)、“因收账常到陈家去,他妻子打扮甚姑苏”(卷三《巧报应》)②刘省三编著:《跻春台》,蔡敦勇校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7、430页。后引不再加注。,指的是收拾打扮得漂亮、体面。“姑苏”也用来赞美建筑物,如遂宁民间石工号子有“龙凤场白塔硬姑苏,遂宁县灵泉、广德出活佛”③《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遂宁市市中区资料集》,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领导小组印,1988年,第303页。。四川方言中有“玩格”及“玩格闹派”,至今常见于蜀人嘴边,方言工具书亦收录,意思无非是“闹享受,摆排场”或“摆阔气,闹派头”④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编:《四川方言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2页。。昔日川人的口头,有语义相近的“玩苏”及“玩苏玩款”等,且看《跻春台》用例:“老子生来家富豪,爱的玩格与玩苏。就是丫鬟与奴仆,时常打扮美而都”(卷三《南山井》),“有三串多钱,㧯进合州,每日吃酒吃肉,玩苏玩款,耍得心中快活”(卷三《巧报应》),“银钱壮人胆,玩苏又玩款。日里进秦楼,夜晚宿楚馆”(卷三《双冤报》),“他妻冯氏,亦大家人女,幼少教训,好款玩苏,不惟不知劝止,反说野味好吃”(卷一《失新郎》)。这“玩格玩苏”或“玩款玩苏”,释曰“享乐,讲排场”⑤李申、于立昌:《〈跻春台〉词语例释》,《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在诸如此类例子中,“苏”作为当时社会的流行语是跟洋气、派头、面子、排场相关的,关联着时尚。
竹枝词尤其是中华俗文学研究的对象,借前贤的话来说,研究竹枝词“必谈竹枝之民间性、历史性、艺术性,方能明确与彻底”(任半塘),因为“竹枝一体,根柢在民间,格调自然,辞义质朴,于以观一时一地之风俗得失,最为切近”(何韫若)⑥见林孔翼辑录《成都竹枝词》中的任半塘序、何韫若跋。。旧时蜀地,女性梳妆打扮之苏气、苏样、苏式、苏派成为时髦,被世人追捧,亦见于清代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不乘小轿爱街行,苏样梳装花翠明。一任旁观闲指点,金莲瘦小不胜情。”女子打扮苏气,招来满街注目。岁月推移,时风流变,新样更迭,人们也会以“姑苏”作为时髦的比较参照,刘师亮《成都青羊宫花市竹枝词》云:“宝髻由来羡蜀都,牡丹刘海赛姑苏。而今又变新花样,鬓鬓多梳太极图。”⑦“鬓鬓”是我使用的代替字,原诗此字下方不是“宾”而是“丙”(或是诗人所造字,或是当时流行这样写),但此字在电脑字库软件中没有。在四川话中,原字所指不是鬓角,而是指头上挽成饼状的发髻,今天民间指此常用“饼饼”,便于书写而已。诗末自注:“上年成都盛行牡丹刘海式,今则重太极图头饰矣。”翻开《四川方言词典》,“苏气”有四义:漂亮、好看;大方、脱俗;痛快;有气派⑧王文虎、张一舟、周家筠编:《四川方言词典》,第359~360页。据《成都通览》,旧时成都江湖上的袍哥话也有“不苏气”,意思是“对不住朋友”;又如说“某哥子顶苏气”,指的是“某大爷讲究对于朋友也”。可见,这的的确确是川人口头上常用语。。川人日常生活中常见此语使用,比如二人街头相遇,一人见对方穿着讲究不同寻常,便打招呼说:“你今天穿得这么苏气,去走人户么?”(川话“走人户”,指走亲戚去做客)富顺方言中有“苏儿客气”,意思也是“舒服安逸,干净漂亮”①胡云昌、徐玉才编著:《富顺方言》,富顺县文体广电和新闻出版局,2013年,第122页。,如说某人:“大家不要看他苏儿客气的,其实家里面恼火得很。”关于“苏气”何以成为四川话中的流行语,或曰:“近代成都人对以江浙等沿海地区为代表的时尚风气的称呼,喻指‘苏广气派’,即漂亮好看,大方脱俗”②马骥:《成都方言》,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95页。当然,“广式”与“苏气”又各有来头。;或曰:“‘苏气’:苏州气派。多指穿著打扮的高贵,时髦。也说成‘苏苏气气’”,而“‘苏’,指旧时商业繁华的苏州进入四川的家具服饰。苏气,本为‘苏器’,谓色色精致,器如苏省制也。后引申为漂亮、高雅脱俗,庄重大方”③《苏二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4921870102wy0d.html,发布时间:2015年10月10日,采撷时间2018年7月27日上午。;或曰:“四川地处较为偏僻的西南,自古交通不便,因此,四川人对外面的世界特别向往。明清时期,苏州、杭州经济发达,风气时尚很得四川人青睐。因此‘苏州气派’、‘追捧杭州样式’成了四川的时尚标准,由于‘苏州气派’、‘杭州式样’使用频率高,加上四川人特有的幽默诙谐,‘苏州气派’演变为‘苏气’,‘杭州式样’演变为‘杭式’”④周庆平:《简谈方志中方言的用字规范——从“苏气”、“杭式”和“巴式”说起》,《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2期。。说来说去,无非是对人之相貌仪态好看、梳妆打扮时髦的美誉,多用于女性,如民间圣谕《十美图》中谓美女“一个个天姿国色”、“穿戴苏派又齐整”、“好似仙姑下凡尘”⑤王洪林:《四川方言汇通》,巴蜀书社,2008年,第64页。。由此延伸,民间在口头习称的“二姐”这个大众化称呼上再冠以“苏”姓,用来赞美“苏气”的年青女子,其意思不言而明。
“苏杭二州出美人”,此见于《蜀籁》卷四,乃是彼时蜀地流行语。该书为民国十九年(1930)石印本,是遂宁人唐枢辑录四川方言的集子。民间文艺中,屡屡有见的“苏二姐”实系泛化的角色称呼(犹如“两小戏”中与“幺妹”相对的丑角“唐二”)。在川南地区,古蔺地处川、滇、黔三省交汇处,是多民族杂居地,古蔺花灯歌舞《干妹出嫁》便唱道:“一把锄头二面快哟,做些哟,做些庄稼逗人爱;苏二姐有心跟倒我哟,黄瓜茄子吃不完。”⑥《古蔺花灯,童年记忆中最好看的戏》,http://www.360doc.com/content/20/0525/20/7108612_914518818.shtml,发布时间:2020年5月25日,采撷时间2021年3月7日上午。地方志书引此作:“一把锄头二面快哟,做些庄稼逗人爱;苏二姐有心跟倒我哟,黄瓜茄子吃不完。”⑦《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中国ISBN中心,1993年,第105页。古蔺是多民族杂居地,汉族民间花灯在居住于此地的彝、苗等民族中也有传习。古蔺有彝族乡镇,据调查,“古蔺彝族花灯只在春节期间开展活动,是彝汉文化交融的产物。古蔺彝族花灯节目内容有‘贺年贺福’、‘赞勤斥懒’以及传播公理公德等,但主要表现的内容则是山区彝家男女之间纯朴的爱情。传统剧目有《干妹出嫁》、《摘仙桃》等”(唐继红:《恒部扯勒彝族音乐的整理研究》,《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查查网上,有“苏二姐”条,并称《苏二姐》是宣汉民歌(宣汉在川东达州地区),云:“《苏二姐》是四川民歌最具代表性作品之一,在全国有极大影响,成为川东北地区一笔重要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苏二姐’一语还作为该民歌中的衬词而反复出现,使之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苏二姐’完全有可能打造成川东北民间的一个文化象征,所传达的内涵便是美丽、纯洁、质朴、亲善。陕西‘兰花花’、广西‘刘三姐’、湖北土家‘黄四姐’都已是著名文化品牌,深入人心,分别打上了特定地域标记。那么,‘苏二姐’也完全可以打上川东北大巴山标记,成为一个著名品牌,走向全川全国。”①《苏二姐》,https://baike.so.com/doc/4264625-4467371.html,采撷时间:2021年3月7日上午。宣汉民歌《苏二姐》以马渡乡为代表,1950年9月宣汉县文联曾编民歌集,收入32首民歌,第一首便是《苏二姐》。主持此事的是马渡人李依若(1911——1959),民歌《苏二姐》亦经过他手整理。当时,“李依若整理和创作了一批民歌资料,拟编印成书,得到宣汉县文化馆馆长符风、宣汉师范学校音乐教师冉永继的支持。1951年初,李依若找到新华书店经理龚汝强,协商出版《宣汉民歌集》。2013年10月,时年82岁的龚汝强对笔者回忆:‘《宣汉民歌集》收录民歌32首,署名作者李依若的有《跑马歌》《苏二姐》。该书用的是白色土纸,三十二开本,淡红色封面,书名是扇形排列,由桂卓煦手写石印,共印500本,遗憾的是东找西寻,现在一本也找不到了。’”(冉奎:《世间女子任我爱世间男子任你求——〈康定情歌〉作者李依若考证》,https://www.so⁃hu.com/a/409807338_120158407,发布时间:2020年7月26日)相关研究不多,论者主要是从音乐切入对之进行探讨并从非遗抢救保护角度提供一些建议,如赵琴《马渡民歌的艺术特色及演唱分析——以〈苏二姐〉为例》(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赵栅凌:《“非遗”视阈下原生态民歌的艺术架构与生存路径——以马渡乡民歌为例》(《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等。另有若干媒体报道。民歌《苏二姐》在当地流传是事实,但“苏二姐”作为艺术形象是否仅仅属于川东地区,这个问题可以再讨论。本文拟追问的是为何这一艺术化的女性角色姓“苏”?或者说,赋予该女性角色“苏”姓有没有特别的含义?对此,若结合上述语言民俗来解读,不无趣味。民间口语称人“苏气”,是褒义词。蜀地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中,便如此描写“不像一个村姑,而像一个城里人”的邓幺姑(蔡大嫂):“新婚之后,新娘子只要一到柜台边,镇上的一班少年必一拥而来,纷纷喊着蔡大嫂,要同她攀谈。她虽是怯生,却居然能够对答几句,或应酬一杯便茶,一筒水烟;与一般乡下娘子,只要见了生人,一万个不开口,比并起来,自然她就苏气多了。”②李劼人:《死水微澜》,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22页。前述《乐山县志》亦载“称人美好曰苏气”。由此观之,民间文艺中常见的“苏二姐”,定位正属于长相漂亮、行事得体、为人大方的女子,其形象约定俗成。
四川话中,与“苏气”相对的是“苕气”,这“苕”是红苕(红薯)的苕,指说话、举止或打扮土里土气(如说某人穿着“苕眉苕眼”或长得“苕头苕脑”)。邓幺姑之所以如“苏气”的城里人而不像“苕气”的乡下女子,盖在嫁入蔡家之前,她老早就从邻近的韩家二奶奶处听说了许许多多关于省城的故事。韩二奶奶是成都大户人家女儿,如小说所写,邓幺姑从其口中“零零碎碎将整个成都接受过来”,俨然已是“成都通”。她知道成都有东南西北四道城门,城墙有好高好厚。她知道由北门至南门有九里三分长,西门这面有个满城,里面住的是与汉人有别的满人。她知道成都北门有个大寺庙叫文殊院,平时吃饭的和尚都有三四百人。她知道城里有很多大会馆,每个会馆里单是戏台就有六七处,都是金碧辉煌的;江南馆尤其阔绰,一年要唱五六百本整本大戏,一天总是两三个戏台在唱。她知道许多热闹大街,东大街、总府街、湖广馆;这湖广馆是顶好买菜的地方,新出的菜蔬野味这里全有。她还知道大户人家多么讲究,房子如何高大,家具如何齐整,差不多家家都有一个花园。她更知道当太太的、奶奶的、少奶奶的、小姐的、姑娘的、姨太太的是多么舒服安适,日常睡得晚晚的起来,梳头打扮,空闲哩,做做针线,打打牌,到各会馆女看台去看看戏,吃得好,穿得好,又有老婆子丫头等服伺……透过小说描写,我们看到了昔日蓉城“五方荟萃”的多元文化,看到了来自江南的会馆、物品、戏剧及风习的影响。上海与苏州同属吴方言区,来自上海的物品也对蜀地影响不小,如织绣行业的“顾绣”③自古以来,江南织绣业发达。《成都通览·成都之美术出品及价值》记载:“成都之绣工铺,其招牌则曰‘顾绣’二字。”顾绣又称“露香园顾绣”,汉族传统刺绣工艺,源于明代松江地区的顾名世家,因此得名。相传顾绣之绣法出自皇宫大内,顾家先后出现了缪氏、韩希孟和顾兰玉等顾绣名手。顾绣劈丝精细,绣品精工夺巧,闻名遐迩。顾绣弟子有男有女,分布四方,尤其集中在江苏、四川、湖南、广东等地,对四大名绣的发展都深有影响。除了刺绣,江南风物影响蜀地也反映在饮食方面,如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三山馆本苏州式,不及新开四大园。请客何须自设馔,包来筵席省操繁。”筱廷《成都年景竹枝词》:“白粉红糖共和匀,作来最好数南人。一气蒸成砖块似,压倒方圆式样新。”(蒸年糕),昔有竹枝词云:“舒家绫子碎花工,顶好宫绸洪义隆。见样虽高能学到,一般顾绣与倭绒。”(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
三 “苏二姐”在民间文艺中
在笔者看来,民间文艺中的“苏二姐”指漂亮大方人好的女子,为之冠以“苏”姓实际上正体现出民间艺人在塑造人物时的某种模式化角色审美意识。归根结底,这个意象化的“苏二姐”,是民间审美意识的体现,是民间艺术创造的产物。因此,顺从民间心理需求,民间戏曲中不管是哪个地方、哪家戏班搬演苏二姐故事,“苏”(漂亮大方脱俗)都是这个女子的基本角色定位,在此基础上再将其进而化身为各有地域、族群特色的艺术形象。
先看四川地区,川北灯戏是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的项目,其传统剧目有《三看亲》,内容是“苏二姐不爱屠夫、裁缝,偏爱种田的牛二娃”①吕子房、辛身、肖善生等编著:《川北灯戏》,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9页。。灯戏是中国民间小戏的类别之一,“苏二姐”题材搬演在不少地方的灯戏中,入乡随俗,形成因地而异的多种版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川灯戏集续编》(2010年)就此题材收录了若干灯戏本子,比如《三访亲》,剧演王媒婆贪图钱财,分别为员外之子丁七癞、当铺老板龚逢才、庄稼汉刘大海说亲,但对象都是苏家村那个“人人夸奖的苏秀英,苏二姐”。来到苏家村,见了苏妈妈,三人争相求亲,都觉得“苏二姐应该嫁给我”。苏妈妈让女儿自己挑选,苏二姐便出考题让三人回答,最后她选中的是“种出庄稼人喜欢”的刘大海。王媒婆只好把提亲的钱退给了龚、丁二人。该灯戏本子依据的是艺人陈华兴口述。又如南充新闻网报道,南部县柳树乡杨家观村有“天灯戏”,自清末流传到现在,春节期间演出,村民喜闻乐见。据年逾古稀的艺人杨子群(第五代传承人)介绍,“天灯戏只有一幕,表演总时长仅一小时左右,是一种民间土生土长、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小戏,塑造了媒婆李二嫂、李二嫂干女儿苏二姐以及张裁缝、李屠夫和庄稼汉兵郎子等人物形象”,其内容是“媒婆李二嫂想将干女儿苏二姐嫁给有钱的李屠夫或者张裁缝。苏二姐却看中了‘上无片瓦,下无鼠粮’但积极上进的庄稼汉兵郎子。经过一番激烈抗争,苏二姐最终如愿以偿嫁给兵郎子”。这位民间艺人说:“作为一种祭祀活动,天灯是从傩戏中的‘跳加官’‘端公跳坛’演化而来,和地灯、花灯一脉相承。”②李果、王林均、白刚:《寓教于乐:柳树天灯百年流传》,http://www.cnncw.cn/2019/0508/277159.shtml,发布时间:2019年5月8日,采撷时间:2021年3月20日中午。
在中国西部,“苏二姐”的艺术形象亦见于四川周边省份。甘肃文县玉垒乡有民间花灯戏班,所演剧目有《三看亲》,据老艺人口述本,该剧演述苏家湾苏大娘的女儿苏二姐人品出众,龚裁缝、苟屠夫、青年农民丁兰子都看上了她,苏大娘让女儿自己择婿。三人同去相亲,裁缝、屠夫嘲笑丁兰子“穷”,后者唱:“我一把锄头锋锋快,收的五谷惹人爱,只要苏二姐看上我,红苕芋子当小菜。”最终苏二姐选择了勤劳的庄稼汉。③该小戏由袁俊德、袁怀成、袁贵德等民间艺人口述,华杰搜集整理,辑入《玉垒花灯戏研究·历史资料卷》。川、甘相邻,出四川广元境,入陇南文县,经碧口镇沿江上行不久便到了玉垒关(位于今玉垒乡),白水江与白龙江在此汇合为嘉陵江。2019年2月中旬,我应邀赴甘肃文县参加“两省三市(州)三县创建中国白马文化生态保护区推进会”,途经此地,与兰州城市学院教授王萍聊起玉垒花灯戏。我说花灯戏源头在长江流域,随着历史上移民的脚步也有往北传播并地方化的种类,尽管不多,但值得关注,如玉垒花灯戏这样的个案。她告诉我,玉垒花灯戏班至今犹存,演小戏也能演大戏,由袁姓家族(以及与之有姻亲关系的张家)承头,袁家祖上是湖广填四川又从四川酉阳来甘肃文县的移民(起初是来嘉陵江上游淘金,后来定居在玉垒坪一带),花灯戏由他们带入此地,是其维系家族历史记忆的重要民艺。滇、黔、川接壤,彼此文化交流多。《三访亲》见于云南花灯戏,又名《三探亲》,说的是地主少爷刘兴富、当铺老板龚逢财和青年农民丁耐勤经王媒婆介绍同时向聪明美丽的苏秀英提亲,面对三个求婚者,苏二姐用巧妙的方式表明了爱憎,选择了质朴勤劳的丁耐勤。在云南,甚至有花灯戏《三访亲》源于嵩明县的传说,称“每逢新春佳节,嵩明县大闹花灯,各灯班演出的剧目中,都有《三访亲》,人们百看不厌……据传说,《三访亲》剧中的人和事,都是嵩明的真人真事。剧中的苏家村、丁官屯、小街、刘家坝、王家村这些村庄,都在嵩明坝子方圆八公里之内”而“剧中人都是这几个村中的人,其姓氏至今这些村子都有,占的比例很大”①《中国戏曲志·云南卷》,中国ISBN中心,1991年,第527页。。剧中人唱的是当地花灯曲调,老百姓看戏也感到格外亲切。贵州花灯剧亦有《三访亲》,又名《三会亲》,主要人物有农家女苏幺妹、农家后生宾啷啷、封裁缝、毛屠户以及说媒的王婆。该剧演农家女苏幺妹(从二姐到幺妹,“苏”姓未变)美貌出众,贪财的王婆引来三人与幺妹相见,苏幺妹不为裁缝、屠户的钱财所动,爱上质朴厚道、勤劳诚恳的农家后生。1978年遵义曾据此戏整理改编《苏幺妹挑郎》,搬上舞台。此外,傩戏是黔地民间戏剧中的大类和强项,“贵州傩堂戏、阳戏也有此剧目,内容大致相同”②《中国戏曲志·贵州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第82页。,这是“苏二姐戏”跨剧种交流的结果。再看中部地区,湖北楚剧有《丁癞子讨亲》,题材相同,“开端为孤女苏二姐主动招亲,干娘王氏作媒。重场在裁缝、屠户向媒人行贿”③《中国戏曲志·湖北卷》,中国ISBN中心,1993年,第118页。;湖南零陵花鼓戏中亦有《三看亲》。
着眼族群互动和文化交融,苏二姐在川西北羌族聚居区花灯戏中也有亮相,其形象较之汉族地区是同中有异,一方面是按通行标准塑造漂亮大方人品好的女子,一方面又在地化为生于羌山长在羌寨的“羌族姑娘”,以之为轴心展开的剧情也洋溢着羌风羌味。羌地灯戏中演述苏二姐故事的有《龚男子讨亲》④又作《丁郎子讨亲》,过去曾误为《龚男子招亲》。关于这出羌族花灯戏,我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赘。,剧中三男欲娶的女主角叫“苏二姐”。20世纪50年代,汶川县派去刷经寺参加全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艺汇演的即是此剧。2020年6月“自然与文化遗产日”,该剧又由汶川县羊角花艺术团在挖掘传统的基础上推出,目前在申请艺术基金资助,剧名之羌语叫“角若勒”(汉语译音,羌族有语言无文字),共有“祭山邂逅”、“智夺花魁”和“姻缘利双”三幕。整个演出,糅合使用汉语和羌语,男女主角除了汉语名字龚男子和苏二姐,还有羌语名字,前者叫“哈乐瓦支”,后者叫“美纳巴啧”,由帅哥、靓女扮演,很受观众欢迎。根据当地提供的节目单,剧情如此:“率真善良的羌族姑娘苏二姐(美纳巴啧)与勤劳朴实的羌族小伙子龚郎子(哈乐瓦支)在祭山会上邂逅互生爱慕,在招亲大会上,嫌贫爱富的王阿妈却百般阻扰……一波三折,最终王阿妈被哈乐瓦支诚实真挚的美好品质打动,成全了这桩婚姻。”剧中,对苏二姐的形象定位是“天生丽质、聪慧善良”。当时,县上演出该戏是在岷江大桥头的锅庄广场,后来又进中小学演出。此外,据我所知,除了由专业团体搬上舞台的版本,在汶川县雁门乡索桥、月里等羌族村寨,老百姓至今能演《龚男子讨亲》这出花灯戏,有汉语版也有羌语版⑤李祥林:《从民间文学看民间小戏》,《文艺报》2019年1月25日。,而据年逾古稀的羌族老人告知,当年这出戏去刷经寺(曾为阿坝州州府)参加全州文艺汇演时,原本是用羌语演唱的,但为了在汇演中让更多人听得懂,才改为汉语演唱也就是有了汉语版。
说罢竹枝词,又谈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族群的民间戏剧,再回到本文开头的民歌话题。“苏二姐”是流行于民间的意象化审美符号,在民间文艺中有较广泛运用,甚至作为衬词。谈到宣汉民歌《苏二姐》的衬词特征,有人指出:“马渡山歌一般以虚词作衬词,也有用实词作为衬词的。如:‘清早起来去(吔)放牛(噢),去(吔)放牛(噢),一根(那个)田坎(苏二姐),(你呀我呀妹儿娃子),放出头(噢)(二嫂哟)。’”①《马渡关:山歌响处是故乡》,https://www.sohu.com/a/402775081_100137573,发布时间:2020年6月18日。一般说来,民歌衬词多是虚词,有论者以上饶民歌为例将衬词分为八类,指出有二类并非虚词,一是称谓性的如“哥呀”、“妹呀”、“亲郎哥”等,一是“有一定实义的,寄托美好愿望的,如‘麦子嗦’、‘金马唆’”等②苏前忠:《上饶民歌的衬词初探》,《黄河之声》2017年第8期。。“前山落雨后(哦)山晴(罗),后(哦)山晴(罗),盼来(那个)红军共产党,(你呀我呀妹娃子),好喜欢罗(二嫂哟)。”“一杆大旗红(欧)又红(欧),红(欧)又红(欧),打到(那个)土豪和劣绅,(你呀我呀妹娃子),分田地哟(二嫂哟)。”这是四川民歌《我随红军闹革命》,该歌共四段,每段歌词有别但衬词均如此。以此歌为例,有论者指出:“在这首作品里,作者使用了语气词‘罗’、‘哦’、‘那个’,还加上了人称代词‘你呀我呀妹娃子’、‘二嫂呀’等等,既表达了红军的到来,让劳苦大众欢乐开怀,奔走相告的喜悦气氛,又天衣无缝地将整首作品融为一体。”③闫兵:《中国民歌中衬词成因初探》,《青岛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行内人知道,这首四川民歌正是根据传统民歌《苏二姐》曲调填上新词而来的。“地方文献记载,土地革命时期,《苏二姐》曾被川陕苏区群众改编为《我随红军闹革命》,在红军中广为传唱。”④孙和平:《四川方言文化——民间符号与地方性知识》,巴蜀书社,2007年,第227页。据该书介绍,现有宣汉民歌《苏二姐》是“宣汉籍音乐家李依若改编”。老版四川民歌《苏二姐》是如此唱的:“清早起来去放牛哦/去放牛哦/对着那个田坎苏二姐/你呀我呀妹娃子/快梳头嘛二嫂哟/快梳那个头嘛二嫂哟。”⑤《清早起来去放牛哦是什么歌里的歌词》,https://wenda.so.com/q/1476879175722313,发布时间:2018 年4 月28 日,采撷时间:2021年3月7日上午。由此看来,“苏二姐”之称在民歌中的使用情况当有二:一是整个作品以苏二姐为主角并唱述苏二姐故事,一是沿用此民歌曲调但“苏二姐”仅仅是借作衬词使用。
综上所述,“苏二姐”是中国民间文艺所创造的符号化审美意象或意象化审美符号,借助这个约定俗成的符号,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作者编码出多姿多彩又脍炙人口的作品。在汶川,“苏二姐”化身为尔玛村寨的“美呐巴啧”,是一个性情爽利、端庄美丽的羌家女子;在宣汉,《苏二姐》在地化为“李依若为同村好友苏清玉创作的歌曲”,苏二姐以后者女儿身份出场,她还做得一手好菜,至今当地还有“苏二姐热米豆腐”和“苏二姐滑肉”两个土菜远近闻名⑥徐洋、徐丽莎:《一曲〈苏二姐〉唱响山乡迎宾客》,《四川日报》2019年5月23日。;在云南省嵩明县,这“苏”姓女子又成了“嵩明人越看越亲热”的苏家村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体现出“苏二姐”作为审美能指在鲜活的民间文艺创作中不乏弹性的运用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