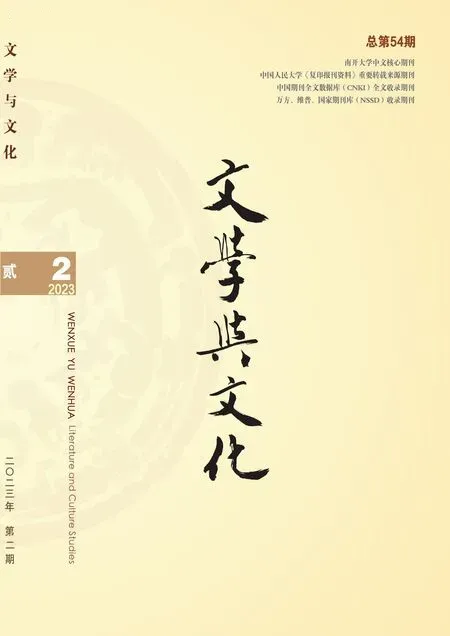《卡鲁基之夜》中的伦理困境与身份认同
饶 雪
内容提要:2010年布克奖得主、英国犹太裔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在其代表作《卡鲁基之夜》中,展现了犹太人在不同境遇中面对德国人时,于个人爱情与民族仇恨间产生的伦理困境以及他们对自身身份做出的不同抉择。小说主人公马克斯在对大屠杀的迷恋中将自己化身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的一名囚犯,幻想自己因控制不住对营地指挥官妻子的爱欲,而陷入个人欲望与民族仇恨的伦理困境,最终以受害者的身份坚决表明了对纳粹罪行的谴责。而生活在后大屠杀时代的亚舍,深陷于对忏悔的德国女子多萝西的爱与听从绝不宽恕的犹太父母这一伦理两难之中,无法做出伦理选择,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弟弟曼尼谋杀父母的犯罪行为。从整个叙事进程,尤其是曼尼出狱后的生存状态中,可以窥见雅各布森对犹太人如何在战后创伤性的记忆下做一个犹太人的思考。犹太人只有在坚守犹太民族之根的同时,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战后忏悔的德国人,才能走出大屠杀造成的创伤,成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当代犹太人。
对犹太身份问题的探讨一直贯穿于雅各布森的创作当中。在2006年其创作的长篇小说《卡鲁基之夜》①《卡鲁基之夜》中的卡鲁基(kalooki)指犹太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拉米纸牌游戏,因为这种纸牌天生具有很强的辩论性。中,他从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出发,探讨了这一问题。该部小说在2007年获得了英国《犹太季刊》温盖特文学奖(Jewish Quarterly Wingate Prize),被他称为“有史以来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没有写过的最犹太的小说”②转引自David Brauner.“Fetishizing the Holocaust:Comedy and Transatlantic Connections in Howard Jacobson’s Kaloo⁃ki Nights”.European Judaism,2014(02):p.22。。《卡鲁基之夜》以纳粹大屠杀为背景,展现了犹太人在不同境遇中面对德国人时于个人爱情与民族仇恨间产生的伦理困境以及他们对自身身份做出的不同抉择。到目前为止,国外对《卡鲁基之夜》的研究主要包括犹太幽默、创作手法、大屠杀呈现、文化身份等方面。如大卫·布劳纳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认为《卡鲁基之夜》充满了对美国犹太文化的暗示③David Brauner.“Fetishizing the Holocaust: Comedy and Transatlantic Connections in Howard Jacobson’s Kalooki Nights”.European Judaism,2014(02):p.21.;艾达·迪亚兹·贝德从创作观念出发,分析了《卡鲁基之夜》中犹太人幽默的本质④Aída Díaz Bild.“Jacobson’s Celebration of Comedy in Kalooki Nights”. Miscelánea: A Journal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2019:p.28.;安德烈·加西奥雷克则将《卡鲁基之夜》与美国犹太作家迈克尔·夏邦(Michael Chabon)的《卡瓦利和克莱的神奇冒险》进行比较,着重探讨大屠杀的当代政治含义①Andrzej Gasiorek.“Michael Chabon,Howard Jacobson,and Post-Holocaust Fiction”.Contemporary Literature,2012(04):p.899.;索菲亚·里科蒂利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小说中的犹太身份问题进行了分析②Sofia Ricottilli. Howard Jacobson’s Kalooki Nights: A Jewish Journey in Pursuit of Loss.Università Ca’Foscari,2012: p.21.。国内尚未有对《卡鲁基之夜》的研究。国外不乏学者对该作中的身份认同问题进行关照,但尚未有学者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来探讨该部小说中的伦理困境与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卡鲁基之夜》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犹太人在个人爱情与民族仇恨之间的伦理困境,体现了雅各布森对纳粹罪恶的批判以及对战后犹太人如何在创伤的历史下构建犹太身份的思考。
一 “灰色地带”:集中营里的伦理困境与现实中的身份迷失
意大利犹太裔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中,以“灰色地带”为题,在一个章节中专门讨论了集中营里介于纳粹迫害者与普通囚犯之间这一“灰色地带”特权囚犯在极端境况下的复杂人性。这一“灰色地带”是政治压迫下产生的一个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区域③[意]普里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杨晨光译,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65页。,是在权力和权势压迫下受害者与权力的妥协。在莱维看来,这体现了每一个人的道德模糊性,是每一个人的“第二天性”④[意]普里莫·莱维:《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第67页。。在《卡鲁基之夜》中,雅各布森呈现了大屠杀集中营里另一种形式的灰色人性,受害者孟德尔并不是为了权力而与迫害者达成同谋关系,而是为了在剥夺人性的集中营环境中证明自己尚存人性而企图与迫害者建立难以为其他犹太受害者所接受的情爱关系。孟德尔的形象体现了纳粹主义对人性的另一种形式的扭曲。
小说主人公马克斯,出生于20 世纪50 年代曼彻斯特的一个世俗犹太家庭,在犹太隔都中长大。虽然作为19世纪末移民曼彻斯特的东欧犹太人的后裔,曼尼的父母及其他曼彻斯特犹太人未受到大屠杀的直接伤害,但大屠杀已经成为战后犹太人的一种集体记忆,成为他们不可磨灭的文化创伤。正如学者彼得·劳森对雅各布森作品中关于大屠杀书写所作出的评价,在雅各布森的作品中,大屠杀被想象为是无国界的,尽管它起源于欧洲大陆,但同时也为盎格鲁——犹太人的集体焦虑提供了反乌托邦的边界⑤Peter Lawson.“The Promised Land:Utopia and Dystopia in Contemporary Anglo-Jewish Literature”.Yearbook for Euro⁃pean Jewish Literature Studies,2016(03):p.191.。这种对大屠杀的焦虑与恐惧在《卡鲁基之夜》中体现为马克斯的父亲对大屠杀的沉默,对犹太人历史的遗忘,而父亲的态度深刻影响着马克斯对大屠杀以及自身犹太身份的认识。
在小说一开始,中年马克斯就回忆起童年时家里隐藏的沉默的大屠杀事件。马克斯的叔叔笨艾克经常在家说纳粹要消灭他,而他的父亲就会斥责笨艾克说:“我要是知道纳粹在找你,几年前我就会告诉他们去哪儿找你了。”⑥Howard Jacobson.Kalooki Nights.New York:Simon&Schuster,2007:p.4.对于父亲尖刻的言语,童年的马克斯无法判断这是不是父亲开的玩笑。通过查阅字典,马克斯知道“消灭(exterminate)意味着完全摧毁,结束(人或动物),驱逐,赶跑,摆脱(物种、种族、群体、观点)”⑦Howard Jacobson.Kalooki Nights.New York:Simon&Schuster,2007:pp.4-5.,因此判断父亲不可能在开玩笑。马克斯的父亲以极端的方式试图阻止犹太人谈论大屠杀,希望犹太人能够从大屠杀的阴霾中走出来,面向未来而生活。在父亲的教导下,马克斯承载着父亲做全新的犹太人的期望。但在曼彻斯特犹太人的隔都里,关于大屠杀的历史仍在秘密流传,马克斯无法坚持父亲的期望,又被拽回到历史的漩涡中。
在家庭之外,通过童年伙伴曼尼与埃罗尔,马克斯了解到大屠杀的血腥细节。从曼尼的手中,马克斯获得了1955年英国鲁塞尔勋爵创作的《卐字旗下的灾祸:纳粹战争罪行简史》①《卐字旗下的灾祸:纳粹战争罪行简史》的具体内容,可参考原著Lord Edward Russell. Scourge of the Swastika a Short History of Nazi War Crimes.London:Cassell&Company Ltd.,1954。一书。从书中,马克斯知道纳粹迫害了超过五百万的欧洲犹太人,在这一庞大的数字面前,马克斯突然感到作为犹太人的庄严感,马克斯感到自己与受害的犹太人之间有着不可摆脱的联系。马克斯沉迷在纳粹所犯下的罪恶中,感受到自己有记住纳粹罪行的责任。
曼尼来自街区的一个正统犹太人家庭,埃罗尔则来自世俗的犹太家庭。在像埃罗尔一样的世俗犹太人眼中,曼尼是一个犹太疯子,与世界格格不入,是使犹太人遭受杀害的原因。埃罗尔对曼尼的孤立,影响着马克斯对曼尼的判断,使他不敢公开承认自己与曼尼的友谊。但在脱离埃罗尔的影响后,马克斯对曼尼又有一种崇敬之感。马克斯对曼尼矛盾的态度,是一种既想走出犹太传统又被其神秘所吸引的矛盾情感的具体体现。面对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马克斯也处于忘却与不能忘却的矛盾中。马克斯所面对的矛盾,归根到底是自己模棱两可的犹太身份意识的体现。而他的身份迷失,通过马克斯的第二人格——集中营里的囚犯孟德尔的伦理困境,得到了更加深入的体现。
在对大屠杀的痴迷中,马克斯将自己幻想成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的一名囚犯孟德尔,因为控制不住情欲而忘记了自己的囚犯身份,妄图成为营地指挥官的妻子伊尔斯·科赫②伊尔斯·科赫(Ilse Koch,1906——1967),穷凶极恶的纳粹女战犯,布痕瓦尔德营地指挥官卡尔·科赫的妻子,她在为希特勒政府效力期间,担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看守的职务,因用人皮制作人皮灯罩的残酷行为而成为集中营囚犯的噩梦。因喜欢在集中营里骑马,看到哪个囚犯不顺眼,挥鞭就打,被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称为“布痕瓦尔德母狗”,后来被研究者称为“史上最邪恶的15个纳粹分子”之一。的情人。他希望通过科赫维持生存的意义,他说:“如果我失去了她,我就只会变成一个囚犯,我会像其他人一样行事……为了活下去,我必须清空我头脑中的一切,除了伊尔斯。要想成为自己的人,我必须成为她的男人。”③Howard Jacobson.Kalooki Nights.New York:Simon&Schuster,2007:p.101.对科赫扭曲的爱欲是孟德尔在集中营这一使人丧失人性的极端状况下证明自己还尚存人性的途径。但他这一扭曲的思想违背了他作为犹太受害者的伦理。正如与他在集中营里分享同一个铺位的犹太同胞平查斯告诫他所说:“除非你停止想她,否则你该死。”④Howard Jacobson.Kalooki Nights.New York:Simon&Schuster,2007:p.103.孟德尔并不是集中营里唯一一个对科赫抱有性幻想的犹太人。告诫他的平查斯同样有这种幻想,但区别是他努力克制不去想她。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无论是社会中的人还是文学作品中的人,都是作为一个斯芬克斯因子存在的。没有纯粹的兽性的人,也没有纯粹的理性的人。”⑤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8页。犹太囚犯对科赫的爱欲,是人身上的兽性因子的体现,是一种性本能,但平查斯坚持自己犹太受害者的身份,使自己摆脱个人爱情与集体仇恨这一伦理困境。而孟德尔出于维系个人存在意义的目的有意利用这一性本能,陷入伦理困境,以反抗纳粹体制对人性的抹除,但其代价则是迷失了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孟德尔保持人性与丧失身份的矛盾是极端处境下人性扭曲的体现,表明了雅各布森对纳粹体制的批判。
不管是现实中的马克斯还是他的第二人格——集中营里的囚犯孟德尔,两者都因大屠杀而造成身份的迷失,大屠杀是犹太人身份认同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 后大屠杀语境中的伦理困境与身份混乱
自1970 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的“千年一跪”开启70年代德国全社会对二战的公开讨论与反思以来,“德国人把国家的荣誉、德国人的尊严与纳粹帝国分开,与希特勒分开。……德国从国家元首到普通百姓,都怀有历史负罪感,对发动战争都进行反思”①李文红、王建斌:《德国人是如何反思二战的》,《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5期。。《卡鲁基之夜》中,多萝西的德国父亲面对亚舍时的忏悔以及马克斯与妻子佐伊参观柏林时遇到的忏悔的德国青年,都是二战后德国人反思纳粹罪恶的体现,而亚舍与德国女子多萝西的爱情正发生于德国人寻求宽恕的转折时期。
亚舍与曼尼出生于同一个正统派犹太家庭,父母沃辛斯基夫妇希望他们成为犹太拉比。根据《圣经》中的戒律,犹太人需守安息日,在安息日应停止工作,礼拜上帝。于是,在这一天,犹太人就会请非犹太人为他们生火。多萝西就是在安息日为沃辛斯基一家生火的非犹太人的女儿,而亚舍爱上了这个替母亲来烧火的烧火女(fire-yekelte)。对于严格遵守犹太传统的亚舍来说,这一行为无疑是大胆的。他清楚地知道正统派的父母将会坚决反对这一行为,所以他不打算将他和多萝西的爱情告诉父母。而多萝西提出要见亚舍的父母,因此,亚舍陷入了两难的处境,遭到多萝西的斥责,陷入愧疚与耻辱之中,为自己没有勇气告诉父母而耻辱?为爱上了德国女子而耻辱?处于父母与多萝西的两难选择之间,亚舍也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而耻辱,陷入混乱之中。
在社区流言中,亚舍与多萝西的事还是被沃辛斯基夫妇知道了。当塞力克·沃辛斯基得知消息后,他因中风而被送进医院。而在亚舍看来,这只是父亲为了阻止他和多萝西的诡计。面对亚舍对自己过于极端的控告,塞力克在极端的狂怒中要杀了亚舍,而被卷入争吵的曼尼击打了他的父亲和哥哥,他癫痫发作,阻止了父亲和哥哥的争吵。面对家庭的不幸,亚舍陷入伦理两难,是对家庭的不幸感到愧疚还是逃离这一切?是放弃多萝西还是与她在一起?在爱情与家庭之间,亚舍不知如何抉择。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言:“伦理两难由两个道德命题构成,如果选择者对它们各自单独地做出道德判断,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并且每一种选择都符合普遍道德原则。但是,一旦选择在二者之间做出一项选择,就会导致另一项违背伦理,即违背普遍道德原则。”②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第262页。不管亚舍如何选择,都会违背另一种伦理,于是,他选择了逃避。然而爱情的欲望仍然折磨着他,尽管坚守着犹太教的传统戒律,但亚舍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人性需求。另一边,当亚舍为自己给家庭带来的伤害而深深自责,与多萝西分开,但又因思恋而备受煎熬、痛苦忧伤时,他的父母却只顾坚守犹太原则,而不顾儿子的悲欢,表现出偏执的特征。
亚舍与父母之间的不同立场造成了严重的伦理混乱,导致父母与子女间的正常关系被破坏。而这一切都在曼尼的眼前上演,他无法平静地面对父母与哥哥的争吵,无法无视哥哥的痛苦。曼尼自愿地承担起了亚舍的伦理困境,扮演起了拯救者的角色。雅各布森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借着罪来到神面前。犹太教有其卡拉马佐夫的形象。”③Howard Jacobson.Roots Schmoots:Journeys among Jews.New York:The Overlook Press,1994:p.29.曼尼就是一个卡拉马佐夫式的人物形象,希望通过罪来拯救。
面对哥哥的痛苦以及父母从痛苦中迅速恢复对哥哥痛苦的冷漠,曼尼开始了对父母的质疑。而在另一边,通过亚舍对多萝西的爱,曼尼看到了多萝西作为单独个体的人性的一面,而不仅仅将其看作标签化的德国人。正如研究者索菲亚·里科蒂利所言:“事实上,亚舍和多萝西成功地摆脱了‘犹太人’和‘德国人’标签上的刻板印象,这两种标签对两个群体的共鸣都有问题,他们只是作为真正的个人相互了解,克服了文化和宗教差异,接受他们存在的矛盾性和他们个性的弱点。”①Sofia Ricottilli. Howard Jacobson’s Kalooki Nights: A Jewish Journey in Pursuit of Loss.Università Ca’Foscari,2012: p.20.可以说,正因为了解到人性的美好与脆弱,正是因为将多萝西看作一个摆脱了国籍与宗教的人性化的个体,亚舍才会如此痛苦,而不能割舍对多萝西的爱。而通过对比,曼尼则意识到他的父母是多么缺乏人性、多么刻板。
亚舍克制不住对多萝西的想念,又与她重新相见。沃辛斯基夫妇为了阻止他与多萝西在一起,完全丧失了理性。亚舍被父母当作精神病人送进医院治疗,沃辛斯基夫妇的一系列极端的行为破坏了他们与亚舍和曼尼之间正常的伦理秩序,导致了他们的伦理混乱。而这一切又与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观念密切相关,沃辛斯基夫妇始终坚持不宽恕的犹太人身份,对德国人采取永不宽恕的态度。
亚舍既想遵循父母的教导,坚守犹太人的身份,又想成为多萝西的爱人,在他的伦理判断中,选择任何一种身份都会违背与另一方之间的伦理,所以在伦理身份的混乱中,他陷入了伦理两难。而处于父母与哥哥斗争中的曼尼,则更是不知如何选择。他既是父亲的儿子,又是哥哥的弟弟,哥哥与父母之间的伦理混乱,也造成了他的伦理困境。如何抉择,最终也变成了他对自身身份的拷问。
三 记忆与遗忘:犹太性反思与身份认同
如何面对德国人的忏悔,如何在民族传统与21世纪多元文化语境之下做一个犹太人?现实中马克斯的身份迷失、孟德尔在集中营里的伦理困境与亚舍在战后所面对的伦理困境,都是犹太人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面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映。记忆与遗忘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表现了犹太人的不同身份选择。绝不遗忘与彻底遗忘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吗?
在小说中,马克斯回忆起小时候父亲总是以讽刺的口吻称沃辛斯基夫妇为虔诚而过时的犹太教徒(Frummers),认为像沃辛斯基一家那样相信犹太教是疯狂的行为。沃辛斯基一家是街区令人憎恶的疯子。当沃辛斯基一家的争吵惊醒了街区的犹太人,父亲感到宽慰,看到了犹太人走出原始落后愚昧的桎梏的曙光。而多萝西的存在,对沃辛斯基一家具有解放的意义。当多萝西第一次遇见亚舍时,她就感到亚舍是一个需要解放的人。多萝西从未要亚舍改变他的信仰,而是虔诚地学习希伯来语,了解犹太文化,尊重犹太信仰,是沃辛斯基夫妇未曾给她一个机会,是他们关上了和解的大门。曼尼也同样看待多萝西,“她是他们的解脱。与宽恕无关。与德国人和解无关。甚至不是关于她,而是关于他们”②Howard Jacobson.Kalooki Nights.New York:Simon&Schuster,2007:p.418.。古老的犹太性在吞噬着他们的人性,他们不是伤害了多萝西,而是伤害了自己。亚舍的痛苦,沃辛斯基夫妇的无情,促使曼尼用煤气毒死了父母,而这一切归因于他们对犹太教疯狂的信仰,体现了雅各布森在后大屠杀的语境下对犹太性的反思。
在小说中,雅各布森戏剧性地设计了沃辛斯基一家的悲剧与马克斯父亲的死亡几乎同时发生的情节。正统派极端地维持传统的行为造成了自身的悲剧,但马克斯的父亲选择忘记犹太传统,对大屠杀保持沉默,规避自己的犹太身份就是在新时代生存的正确道路吗?
马克斯的父亲杰克是一个无神论者,有很多无神论及共产主义者朋友,经常参加维护人权的社会活动。他不允许妻子去犹太会堂,不允许马克斯谈论与犹太人相关的事,甚至没有给马克斯举行犹太成人礼。但马克斯的母亲诺拉以另一种形式补偿了马克斯缺失的犹太成人礼。得知诺拉的行为后,杰克陷入对自己剥夺马克斯做犹太人的权利的反思中,也陷入对自己规避犹太身份的行为的反思中。小说中叙述到,在此之后,杰克就病了,被自己所做的一切所吞噬,“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他厌倦了这一切。这就像是一种疾病,他以为他战胜了疾病却突然又咬在他的骨头上”①Howard Jacobson.Kalooki Nights.New York:Simon&Schuster,2007:p.128.,他失去了继续战斗的力气,他的做一个新犹太人的愿望失败了。而这一失败以他的葬礼得到最直接证明。小说中的杰克代表了战后英国犹太人想要融入新生活的努力,他们规避自己犹太身份的行为,不是麻木,而是努力生活的证明。但正如英国犹太史专家托尼·库什钠曾说:“英国社会……未能给积极的盎格鲁——犹太人身份提供健康的存在环境。”②转引自David Brauner. Post-War Jewish Fiction: Ambivalence, Self-Explanation and Transatlantic Connections.Basing⁃stoke:Palgrave,2001:p.20.小说中杰克以及像他一样想要融入英国社会的犹太人的失败,正是这一时代文化环境的反映。
杰克探寻新身份的失败延续到马克斯对自己身份认同的矛盾。他既否认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却也在一次次的否认中证明着自己的犹太身份。小说中马克斯在集中营里的第二人格孟德尔迷失在受害者的身份与科赫的情人这一伦理困境,他希望通过这种受虐的爱欲来证明自己在泯灭人性的集中营的存在意义。但科赫是一个传统的人,注定让他失望,“这是历史事实。另一个德国人使另一个犹太人失望了”③Howard Jacobson.Kalooki Nights.New York:Simon&Schuster,2007:p.166.。孟德尔的希望本身就违背了迫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伦理,注定会失败。而他最终也意识到在纳粹迫害这一语境下,忘记自己的犹太受害者的身份才是一种价值丧失。孟德尔最终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是现实中马克斯对大屠杀态度转变的一种投射。马克斯并没有像他的父亲那样逃避大屠杀,马克斯记住大屠杀的行为是对父亲规避犹太身份的一种否定,证明父亲的选择是错误的。然而,当在柏林遇到忏悔的德国青年时,他陷入宽恕与不宽恕的困境,他不想让德国人就这么轻易地从集体罪责的愧疚中走出来,但也不是永不宽恕。马克斯总是处于这种模棱两可的身份认同之中,想做一个非犹太人又处处证明自己是一个犹太人。
马克斯对身份模棱两可的态度,最终通过曼尼得到解决。当曼尼忍受不了亚舍的痛、父母的无情,最终用煤气毒死父母,而自己住进监狱后,小说叙述道,曼尼经过狱中监禁,已经出狱七年,在父母与哥哥都已不在人世的状态下,与造成父母和哥哥冲突的德国女子多萝西生活在了一起。小说意味深长地展现了曼尼像一个犹太拉比一样,教想要成为犹太人的爱尔兰人艾克意第绪语的场景。曼尼的父母对犹太教的坚守与他的哥哥对一个德国女子的爱在他的身上融为一体,并存不悖,他实现了坚守犹太信仰与宽恕德国人的统一,成了一个新犹太人。而马克斯从曼尼身上看到了该如何做一个新犹太人。正如有学者所言:“通过痛苦的自我解释过程,马克斯终于能够接受并原谅自己生活和身份的矛盾。”④Sofia Ricottilli. Howard Jacobson’s Kalooki Nights: A Jewish Journey in Pursuit of Loss.Università Ca’Foscari,2012: p.21.
通过沃辛斯基一家的悲剧,雅各布森实现了对战后犹太人与德国人关系的思考,大屠杀已经成为犹太人与德国人的一种文化记忆,对战后德国人的宽恕并不妨碍做一个正统的犹太人。雅各布森的观点与阿皮亚有根的世界主义不谋而合,阿皮亚认为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应该实现“区域性忠诚与普世性道德”的统一。⑤[美]阿皮亚:《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苗华建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9~11页。曼尼出狱后在坚守犹太传统的基础上对德国人的宽容,对想成为犹太人的爱尔兰人的接受,正是一种有根的世界主义者的体现。在后大屠杀的语境中,犹太人只有成为一个有根的世界主义者,才能走出历史的困境,面向新的未来。
结 语
大屠杀已经成为犹太人共有的文化记忆,深刻影响着战后犹太人对自我的身份认同。在小说呈现的两组伦理困境中,都体现了人性与兽性、个体爱欲与集体荣誉之间的伦理困境。所不同的是,在大屠杀的语境中,纳粹对犹太人所犯下的罪恶不允许犹太人对德国迫害者保有爱意,这是一种耻辱,一种背叛,所以即使内心有难以控制的爱欲,纳粹所犯下的罪恶仍需犹太人铭记,不能抹除。铭记是对遗忘态度的反驳。但铭记并不意味着不宽恕。在后大屠杀的时代,犹太人与德国人之间的伦理困境仍然存在,面对忏悔的德国后裔,极端的不宽恕态度只会导致犹太人自身的悲剧,只有在坚守犹太信仰的基础上以宽容的态度面对创伤的历史,才能使犹太人走出历史的困境,融入新的时代。对大屠杀的探讨,实质上是对犹太人如何在不同境遇建构自身身份的探讨,从集中营里的身份迷失到后大屠杀时代的身份混乱再到最终悲剧之后的有根的世界主义者,马克斯在矛盾的身份处境中最终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在21 世纪,当代犹太人应该以怎样的一种身份处理历史,面对未来,雅各布森为我们呈现了这种困境,也在积极地寻找解决之路。如何面对历史创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仍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