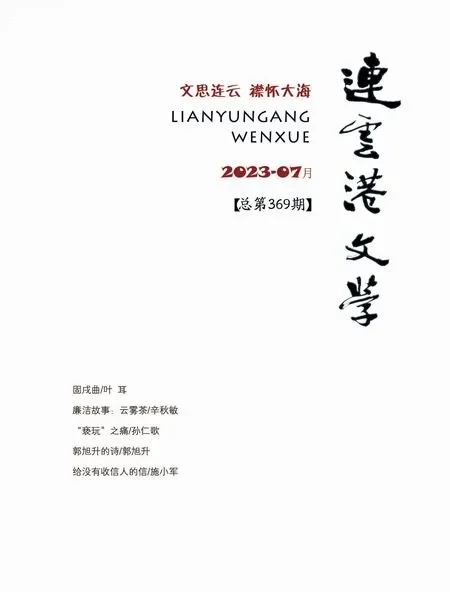旧日回忆(组诗)
解溪
旧日回忆
她在沉船的遗址旁犹豫
要不要建一座地下博物馆
婚姻下沉得太快,很多物件已经掩埋
压箱底的被褥,早不知去向
薄金的礼器,多了细小隐蔽的划痕
明亮的世界被年龄的水浪打湿
她用父亲的老花镜来磨,模糊中
找她想读的话
我是这艘沉船的纸锚
迟滞着抓住他们
却最终如风筝般飞走
仍有未织的言说游弋
她用箍形的顶针抵住旧日回忆
雾中人
冬雾骤降
树木浸在白色的孤独中
环卫工人在打扫城市的鼾声
一位环卫女工倚在饭店的橱窗
手掌抵住扫帚,在疲惫中小憩
窗内炭烤着肉香的铜锅
在玻璃罩里轻轻发射浓雾——
这冷暖的世界有短暂的重叠
再往外,垃圾中转站
在黑夜的掩护中轻轻分食
小心躲避月亮的探查
雾气里一切缓慢地进行
因为寒冷眼镜蒙上的水雾,看不清
这个世界,有多少摇摇晃晃的人
母 亲
母亲在卫生间偷偷掩上门
打开黑乎乎的药膏——染发
用这深海的石油覆上她
因久曝而渗出的白花盐田
她的半辈子都是盐一般的痛苦
青春的礁石早已被雄狮般的海浪击碎
坠落成家的沙塔,时间的铅锤
线裹着黑漆漆的瘀血,结痂着中年
我试手帮母亲染发,藏起衰老的痕迹
月亮剜心的冰凉,失眠成了母亲
不得不饮下去的姜汤
可触手一探,这碗底的白茬,我才恸悟
那升起明月的旗手
就是白日梦游着的我啊
药
父亲瘦了一圈
像鸟儿褪掉了羽毛
镜头外的他,像儿时摔下桌子
的座钟,只剩下沉默的表盘
想起离乡的最后一天
我拉开那藏着药剂的抽屉
——偷窃他和母亲衰老的告信
我看到饭后
父亲像抓药的老师傅
给自己包好五颜六色的钉子和螺栓
破败的船体让他饮下
我看到药剂的啄木鸟
无力地叩诊
那些失火的山林,倒下
才有一丁丁的痛楚从火星溢出
药剂仿佛成为他们的山水
他们成了寄居在上面的异乡人
他们小心翼翼,依然
在病中的地图被标明
而我这个回乡的孩子
却好像挥霍时间的游客,看不到
他们——正到处搬迁
磨 损
这日子磨损
从施工现场走向荒地
钻地的轰鸣逐渐失去引信
如同踩到时间的尾巴,钓鱼人沿车辙离去
月光照耀处,湖泊如墨盒开启
这是大地微萤而磨损的纽扣——
勉力合住——被城市撑破的肚膛
远处一片荒草地的中心
一棵树孤独地楔入虫鸣
像是旧市场的裁缝
缝纫后背炸线的衣裳
关掉闪光灯,光线涌入镜头
——枝干裸露着记忆,我看到自己
一枚投入商铺的硬币——流通已久
渴望邮寄回家
打锡锅
总是一对夫妻,推一架两轮农车
草绳捆着的石具如瓷碗倒扣
打锡锅喽,一声声吆喝让小区醒来
有需要的拿着锡罐,等着称量
架起炭火、风箱和坩埚
锡罐开始解体,它在主人的目光中坍塌
衰老的阴影沉沉,被填满的疲倦在火焰的
舔犊中卸成熔渣,轻轻刮开
露出它水银一样的明亮——牙齿洁净——看不出咬住的往痛
总是秋天,微凉的下午,打锡人看完锡的等候
用火钳小心夹住坩埚,解开草绳,倒入坟墓头般的模具里
让它在黑暗的土地里重新聚合,冥想,成形——
它前世是一块石头,在更多的矿中
金属的字典将它摘出,被火焰誊写
使用,它伴生的朋友——砒霜——散落在荒野
被雨水带进土地的窖藏
到时间了,打锡人用平勺探测它寤寐的
黑嗓门,揭开空气的面罩
磨砂,打光——
它的牙齿抛光得那般好,美得
矫正着人们的视力
再次进入生活,这一次
更接近火和油,这一次
更接近把自己的内心轻轻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