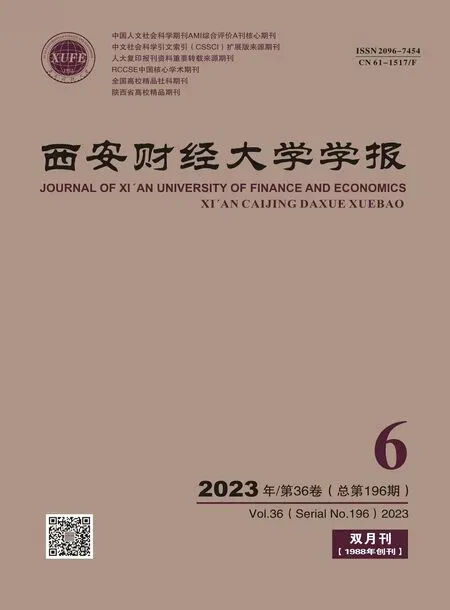嬴秦西迁历史探微
雍际春
(1.天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天水 741001;2.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甘肃敦煌 736200)
秦人称秦始于西周孝王封非子于秦,史有明载。但是,秦人此前来自何方,怎么发展,就必须追溯其前身久远的来历。秦人称“秦”是其“今生”,秦人出自嬴姓,则其“前世”为嬴姓部族。我们所讨论的秦人西迁问题,就是要从东夷嬴姓庞大的部族中寻找其中的一支——秦人先祖的来龙去脉,将其“前世”与“今生”贯通,我们就以“嬴秦”称之。由于先秦文献资料比较缺乏,对于嬴秦的追寻,不仅要涉及嬴姓诸族和东夷的资料,而且还要借助考古材料和商周历史线索探寻其蛛丝马迹。
一、关于嬴秦西迁问题的回顾
嬴秦西迁是一个既涉及秦人起源和族体构成,又与其生存状态、族际关系相交织,还与三代历史特别是周人历史密切相关的复杂过程。在现有嬴秦西迁问题的研究中,主张秦人东来说的学者,自然都认为秦人是从东方西迁至陕甘一带的,但在秦人西迁的时间、路线地域和西迁次数上,尚有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有以下代表性观点。
(一)西迁一次
陈秀云认为周公东征之后,秦人被迫从东方西迁至今陕西的“九毕”(咸阳以北)。然后又有三次迁移,初以非子由“九毕”至犬丘(今陕西兴平);再由非子被封至秦(今陕西眉县);最后秦庄公为西垂大夫居西犬丘(今甘肃礼县)[1]。李学勤在《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一文中,利用新发现的清华简《系年》资料,揭示在周公东征后,嬴秦由今山东曲阜一带的商奄直接迁至朱圉,也就是现在的天水市甘谷县西部一带[2]。
(二)西迁二次
黄文弼认为嬴秦西迁两次:第一次是商末飞廉一支至造父别居赵城;第二次是周孝王时非子自赵城居犬丘为王室养马,非子受封后“邑之于秦”[3]。即主张嬴秦自赵城西迁至今陕西兴平和甘肃天水。伍仕谦亦主此说[4]。汪勃、尹夏清认为夏末商夷联军攻夏,“畎夷入居邠岐之间”,为嬴秦的第一次西迁。商末,中潏时嬴秦迁至今天水一带的西垂,是为第二次西迁[5]。何汉文主张以商末周初为界,此前的秦人第一次西迁经历了“由山东的莱芜一带到西部的范县,越过河北平原,再由朝歌到霍太山、皋狼和赵城一带”。第二次是周初周公东征,灭国五十,大规模强迫包括嬴秦在内的嬴姓族民迁往洛阳以至关中的“九毕”等地[6]。
(三)西迁三次
高福洪主张嬴秦分三个时期西迁,也就是三次西迁。第一时期在伯益玄孙费昌之后,嬴秦为避水害由黄河下游溯河西上进入中原,即《史记》所载“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这一史实。第二时期就是“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第三时期是商末周初嬴秦遭周人镇压后,残留的一部西迁至晋南,即后来赵城造父一支;另一部分继续西迁到戎人所在的西犬丘一带,即后来为周孝王养马的非子一支[7]。尚志儒认为嬴秦第一次西迁在夏末商初,嬴秦随商夷联军反击夏军进而入居关中邠岐一带。第二次是商末居住于汾河流域的中潏一支弃商归周,迁至甘肃天水一带。第三次是周公东征时,原留在东方的秦氏等嬴姓部族多被消灭,秦氏被迫西迁,安置今西安附近的“九邑”一带,师酉簋所载的“秦夷”就是他们的后裔[8]。
何清谷所论秦人西迁,虽未明确提出三次说,但按其所述,从嬴姓至秦约有三次西迁[9]。第一次是晚商时,戎胥轩、中潏父子各率一支族人西迁,其中,中潏率部分族人在商之西方边陲为商“保西垂”,即天邑商(河南安阳)之西今太行山至黄河东岸一带;而中潏之父戎胥轩奉商王之命率嬴秦一支西迁至周人西边陕甘一带。第二次是周公东征后,也是两支同迁。逃回东方的蜚廉后裔和原居于“秦”地的秦人作为俘虏被迁至宗周京畿的“九毕”一带,这一支与秦人系同族异支;而恶来一支的后裔,即后来建立秦国的秦人,也在周公东征时被俘获并直接安置到今甘肃东部一带,与西戎杂居。第三次西迁是周孝王前后,先是从大骆开始迁至犬丘(今甘肃礼县),接着非子被周孝王封邑于秦(今甘肃秦安县)。
王玉哲所论秦人西迁,实际也是三次[10]。从商灭夏秦人开始西迁,第一步从山东迁山西,大约是在戎胥轩、中潏时代;第二步从山西再迁陕西犬丘,大约在大骆、非子时代;第三步是非子时代从陕西犬丘向西迁至甘肃西犬丘。
(四)西迁四次
杨东晨从嬴姓族开始西迁算起,认为秦人有四次西迁[11]。尧舜禹时,东夷嬴姓随皋陶、伯益佐禹治水,留居或分迁,伯益封于秦(今河南范县)为第一次西迁。夏末商初,嬴秦军民随商夷联军扫除夏的残余势力而至关中,此为第二次西迁。商末时,二次西迁至关中的嬴秦被周文王所灭,沦为游牧奴隶;与此同时,在晋南的蜚廉一支嬴秦亦亡国;周公东征时,俘迁大批嬴姓族人于关中东部,并奉周王之命去镇守“西垂”,是为秦人第三次西迁。嬴秦第四次西迁是周穆王时,迁晋南赵氏大骆、非子族和关中东部之“秦夷”至“西犬丘”。
郭向东也认为嬴秦西迁有四次[12]。第一次即夏末商初,是随商夷联军中的犬夷西迁至关中西部。第二次是商代末年戎胥轩一支奉商王之命迁至陕甘一带。第三次在周成王时,飞廉后裔及原居秦地的嬴秦在周公东征后被迫迁至关中。第四次即周穆王时,居于赵城的恶来后裔即大骆、非子一支从山西汾河流域迁至天水西犬丘。黄留珠观点与郭说相同[13]。
(五)重新认识嬴秦的西迁问题
对嬴秦西迁问题的争论,主要由于学界对史料的理解、认识和解读不同,致使在嬴秦西迁的起始时间、地点、路径、次数上出现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例如,非子受封前所居犬丘,就有槐里犬丘说,陇右犬丘说等差异。也有人认为秦人不存在西迁,也就是说“秦人”出现时就已经在西方。如史党社曾提出秦人的称谓有阶段性:“秦人在非子之前何曾叫做秦人?其并不以秦为氏。”又说:“我们既然认为是因中潏归周,秦人才到了西方,当然对有关秦人何时到了西方的其他论断、对于有人甚至说秦人分好几次到了西方的论断是持否定态度的。”[14]这些问题,既涉及如何看待秦人西迁,也与怎么理解秦人早期历史有关。
事实上,秦人一名的出现,是在中潏之后、非子受封之时。但是,水有源,树有根。由于秦人历史的特殊性,我们要对秦人早期历史进行探讨,就不能不对秦人受封之前漫长、复杂的嬴姓部族史事置若罔闻,故所有论及秦人起源历史的论著,无不从秦人远祖伯益甚至更早的时间说起,原因正在于此。要准确把握秦人的早期发展历史和文化特点,就必须将其“前世”和“今生”有机结合,才有可能揭示其起源发展的深层线索和真实面貌。
秦人早期发展的这一复杂性,也使秦人的西迁问题与秦人的起源发展紧密相关。所以,嬴秦西迁的过程既与三代历史相始终,也是其部族兴衰、聚散和开辟新天地的复杂过程,从而构成其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由此出发,依据文献和民俗资料,结合考古新发现和新材料,考察嬴秦的西迁,从帝尧时起至周公东征之间,先后大约有五次,分别为帝尧时期、夏初、夏末商初、商末周初和周公东征。下面分别进行讨论。
二、重黎之后与嬴秦西迁
嬴秦族的第一次西迁,大约发生于帝尧时期。由于伯益一支属于东夷部族擅长历法的成员,因而其始祖或首领女脩、伯益都曾在天文历象方面有所作为。而在五帝时代,东夷部族在天文历法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嬴秦族人在参与历次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的活动中,在帝尧时期,完成了部族的第一次西迁。
(一)东夷部族的天文学成就
东夷部族早在“五帝时代”就是一个文化发达、为中华早期文明多有贡献的部族。无论是“五帝”系统的产生,还是早期“酋邦”国家的出现,都与东夷部族密切相关。而特别突出的是东夷部族在天文历象方面成就卓著,为我国早期天文历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少昊和颛顼相继为东夷部族的主要首领,他们都曾在天文历法的革新与发展上多有建树。据《史记·历书》记载,黄帝是历法的发明者,而东夷族首领少昊、颛顼为历法的完善发挥了关键作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
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勾芒,该为薅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
以上五祀也就是夏商周时期所祭祀的“五行之官”或“社稷五祀”之神。其中,木正勾芒、金正薅收、水正玄冥三祀即出自少昊集团。而从其所司之职和名号分析,所祀三神可能在制造木工具、金属冶炼与铸造、平治水土等方面有所专长和成就。他们所司之职,必涉及天文或历法。
少昊氏四叔中有“重”又有“修”;颛顼氏有“犁”,这重与犁也许就和颛顼氏之南正重和火正黎有联系。而少昊四叔之“修”,陈平就认为是嬴秦始祖女脩[15]。《史记·历书》又载:
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祗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
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勿相侵渎。
上述记载表明,在继承黄帝历的基础上,少昊与颛顼进一步发展了历法,特别是颛顼所订历法被称为《颛顼历》,并一直沿用至西汉才被《太初历》所代替。
《史记·天官书》又载:“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可见,自颛顼以来,代代不乏专司天文的官员。《路史·小昊》则有进一步记述:
允格封鄀,有子鄀姓,玉帝投之幽州,是为阴戎之祖。已氏、格氏、戎氏、允戎氏、戎州氏,皆允类也。重、熙、修、该,帝之四叔也,佐高阳氏。高辛氏衰,五官失守,尧乃复育重氏之后,羲仲、羲叔俾世守之,有羲氏、重氏。
可见,羲仲、羲叔等是少昊、颛顼时代的重氏之后,帝喾时又“五官失守”,于是,帝尧“复育重氏之后”,让其继承先祖司天地之职,改革完善天文历法,授民以时。日本学者御手洗胜认为“允格”就是嬴姓的祖先神,亦即伯益[16]。伯益又称“噎鸣”,顾颉刚以为“噎鸣”就是伯益,“噎”与“嗌”乃一声之转[17]。《吕氏春秋》云:“羲和作占日,尚(常)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山海经》又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则伯益与羲和、常仪一道被列为太阳之神,伯益生岁当为四时之神。而帝尧时又将重氏之后以羲和称之,则是以黄帝时日神之名“羲和”来命名司天地之官。
(二)和仲西测日落与嬴秦西迁
以上事例说明,东夷部族自少昊以来,一直在天文历法上处于领先地位,而重、黎及其后代,包括嬴秦始祖女修、伯益成为东夷部族世代专司天文历法的家族。《尚书·尧典》比较完整地留下了帝尧分命重、黎之后羲、和诸位分赴各地观象测日、以正历日的记载: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
这段史料对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完成帝尧“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任务作了详细记述。羲、和诸位分赴东、南、西、北四个测日点——旸谷、明都、昧谷、幽都,不仅完成了“寅宾出日”“寅饯纳日”的祭日工作,而且通过观察测量也完成了测日的任务。其中,和叔前往“西”地“昧谷”,观测日落变化和太阳高度角。西方测日点“西”地即秦汉时西县,《索隐》云:“襄公始列为诸侯,自以居西。西,县名,故作西畤,祠白帝。”《括地志》云:“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则西县即今甘肃礼县一带。
在东夷部族中嬴姓首领伯益为四时之神,因而在重、黎及其后代羲、和测日观象、修订历法的队伍中,无疑会有嬴姓伯益部族的成员参与其中。所以,帝尧时在羲、和四人带领观测人员分赴四地进行测日的活动中,嬴秦的一部分成员就随和仲西去测日而来到了西犬丘一带。是为嬴秦的第一次西迁。
与和仲到西地测日大致同时,还有一支东夷族人的西迁活动。《史记·五帝本纪》说:帝尧时“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此事《左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如文公十八年“颛顼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谓之梼杌”。昭公九年又载:“先王居梼杌于四夷,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则东夷首领颛顼之子梼杌因迁入夷地而被称为“允姓之奸”,亦即三苗,而其新迁之地“瓜州”当在“三危”。《尚书·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郑玄注云:“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则在积石之西南。”《河图括地象》亦云:“三危山在鸟鼠山之西南,与汶(岷)山相接。”鸟鼠山在今甘肃省渭源县西。则三苗所迁之“三危”与“允姓之奸”所居“瓜州”实为一地。故三苗迁入后,渭源以西的洮水流域就成为土著羌戎与允姓之戎的杂居地。它们之间互相融合产生了后来的犬戎、猃狁和氐族[18]。陈平对此进一步揭示认为,在颛顼、帝喾时东夷重黎族或祝融氏的部分成员开始渐次西迁,一迁进入皖北、鄂东,与当地三苗族融合并成为其新成员。二迁约在尧舜时代,融合后的三苗从湖北涢水及汉水中下游西迁,进入洮河流域并创造了寺洼文化。三迁是从古“三危”南下,越岷山沿岷江进入川、滇交界的金沙江和大凉山地区,大凉山地区的彝族先民即由此而来[19]。这次重要的迁徙活动,在山东邹平县“丁公陶文”资料发现后,人们将之与古彝文互勘,不仅破解了古东夷文字,而且使东夷一支西迁至此发展为彝族的民族迁移秘密及其去向得以揭示。
寺洼文化属于青铜时代分布于黄河以东甘肃东部地区的文化遗存,其文化虽受到与之比邻分布的甘青地区辛店文化的影响,但就文化面貌的主体而言,则是“从外界侵入洮河流域的外来文化”[20]。寺洼文化普遍有陶鼎,陶器又以马鞍形口罐最为典型,墓葬则盛行竖穴式墓。这种文化特点,既不同于早于它的马家窑、齐家文化,也与同时期的辛店、卡约文化、刘家等羌戎、姜戎文化有别。在寺洼文化中,其陶鼎形制与陶器制作中常用陶末作羼和料等特点,与长江中游三苗地区古文化的陶鼎特征及用陶末等作羼和料则完全一致。“根据年代序列和分布区域判断,寺洼文化最早分布在洮河流域,后来自西向东、自南向北发展,因此寺洼山类型,可能是三苗的一支迁至‘三危’后的文化遗存,也就是‘允姓之奸’的文化遗存。”[18]在今甘肃礼县西汉水上游秦早期文化与寺洼文化遗址也呈比邻分布的格局。则东夷—三苗第二次西迁洮河流域的队伍中,可能就有嬴秦族人夹杂其中,他们与随和仲在西地测日留居的嬴秦族人共同成为最早到达天水一带的嬴秦居民。
三、夏朝建立与嬴秦西迁
嬴姓首领伯益佐禹度山导水,平治水土,功勋卓著,不仅受到帝舜的表彰,被赐以姚姓玉女,而且此后又主持畜牧生产,大获成功,被舜赐以嬴姓。舜禅位于禹后,皋陶与伯益是其最为重要的辅佐大臣,先后都成为摄政和继承人。禹死后,其子启与伯益发生王位之争,引发嬴秦的第二次西迁。
(一)伯益与夏启的王位之争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皋陶死后,禹以伯益为摄政。十年后,大禹东巡途中崩于会稽。“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在司马迁笔下,将禅让制下的尧传舜、舜传禹和禹传伯益的王位更替,描写成温情脉脉的让贤之举,其实则掩盖了由选贤任能的禅让制向王位世袭制过渡中血腥的权力之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容成氏》简33-34所记则是:
禹又(有)子五人,不以其子为逡(后),见叴(皋)咎(陶)之贤也,而欲以为逡。叴(皋)秀(陶)乃五壤(让)以天下之贤者,述(遂)爯(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乎壤(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21]。
可见,这一重大历史变革,其真实的历史事实却是伯益嬴姓部族在与夏启的王位之争中以伯益失败被杀而告终。关于伯益与启的王位之争,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又说:“益干启位,启杀之。”《战国策·燕策》记载:“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可见,史籍有意美化的禅让早在尧传舜时已经充满着刀光剑影和武力威胁。这种权力之争是夏立国前后部落联盟内部夏启与伯益之间权力争夺的真实写照。
(二)嬴秦的失势与西迁
嬴姓部族首领伯益,曾是尧舜的股肱之臣,帝舜时伯益为朕虞,佐禹平治水土,“而后举益,任之政”,成为大禹的继承人。可知在尧舜禹在位时,伯益为三朝辅佐大臣,且影响力不断扩大,地位日益上升,以至成为大禹的继承人。伯益地位的上升,除了伯益个人能力之外,更为主要的是其所在嬴姓部族势力不断壮大的反映。这种嬴姓族势力的壮大与伯益地位的上升互为表里,对本族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样,在伯益与启的权力之争中,伯益的被杀也就是嬴姓族势力在与夏启力量的较量中失败的结果。因此,嬴姓族不仅失去了原来的显赫地位,而且部族也遭到打击排挤,被迫离开故地。关于伯益之后嬴姓部族的迁移活动虽于文献无征,但我们从夏末商初嬴秦族人分布的变化亦可推知其概况。
作为东夷的一支,嬴姓族初居于费邑(今山东费县),后封于嬴邑(今山东莱芜)和秦(今范县,原属山东,现属河南),这些居地可以看作是嬴秦最初的根据地。相对于最初的根据地而发生的嬴秦全族或其中一支的向西迁移,即是嬴秦的西迁。就此而言,史籍所载伯益避居箕山以让位于启,及其后由伯益被杀引起的连锁震荡,促成了嬴秦继帝尧时测日西迁之后的第二次西迁。
伯益避居之地箕山,当在今河南林县。李江浙认为,箕字从竹从其,以竹为义,从其得声,则此山因其多竹而得名。据《山海经·北山经》记载,流经今河南安阳地区的淇水,发源于“沮洳之山”。沮与洳同属“豫部”,疾读如“具”,而箕山与淇水同为“其”声,故“沮洳之山”可作“箕山”[22]。《水经·淇水》载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该县初置于西汉,东汉时因避殇帝刘隆讳而改名林县。故箕山当在今林县境内。
除了伯益避居之地以外,伯益嬴秦部族在与夏启的王权之争失利后,为了避开夏启攻伐镇压的锋芒,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嬴秦部族的主体或部分被迫离开原居地,自是必然选择。按《秦本纪》记载:
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由此可以知道,本来居于东方的嬴秦,以费邑、嬴邑和秦为其封地的嬴姓子孙,其居地无疑均在东方,或者说就在东夷部族分布的范围之内。可是,夏桀前后,嬴姓子孙已是“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这就说明,夏初伯益之难,引发了夏人对嬴族的排挤打击,也引发了嬴族的迁移流散。所以,有人将这一变化看作是嬴秦的第一次西迁和第一次衰落,是很有道理的。而嬴姓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又说明夏商之时,嬴姓子孙既有居留原封地东夷地区的,也有迁往其他地区乃至夷狄之区的。这是一个不能否认的史实,也是探讨商代嬴秦线索与居地的重要参照。
四、畎夷西进与嬴秦西迁
畎夷作为东夷“九夷”中的一支,曾在商人灭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典型的就是参与了商夷联军进入关中消灭夏残余势力的斗争,战斗结束后,其主体也当居留关中。嬴秦族的一部分,在随商夷联军入关作战中,来到了关中,并与畎夷一道居留关中,这就是嬴秦族的第三次迁徙。
(一)嬴秦叛夏归商
嬴秦族经历夏初伯益与夏启的权力之争后,遭到夏启的排挤打击,迁移流散,艰辛备尝。而这段历史于史不彰。嬴秦为东夷的一支,我们只能从东夷与夏的关系演化中来了解大致概况。
夏建立后,东夷与夏的关系大致处于若即若离状态。太康时,“夏后氏太康失国,夷人始畔”[23]卷85《东夷传》。夏后相至少康时,甚至发生了东夷族首领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的政治事件[24]襄公四年,哀公元年。这说明夏人曾一度失国于东夷。少康复国后,“方夷来宾”[23]卷85《东夷传》。帝杼时,“征于东海”[25]。帝芬(槐)“即位三年,九夷来御”[23]卷85《东夷传》。帝荒(芒)“元年……命九(夷),东狩大海,获大鸟”[26]。帝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益、阳夷”[23]卷85《东夷传》。这说明少康复国以后,从少康到帝泄的五位夏主在位期间,东夷对夏时服时叛。此后夷夏间未见战事,直到夏末时,“桀为暴虐,诸夷内侵”[23]卷85《东夷传》,说明东夷利用夏末统治危机借机起事并成为助商灭夏的重要力量。
由此可知,在夏夷之间通过征服与被征服、反叛与臣服、纳贡等多重复杂关系,东夷与夏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二里头文化与岳石文化中所表现的相同或相近的因素、二者之间的互相渗透,“正是夏夷关系在考古学文化中的体现”[27]。嬴秦部族正是在这样一种相互交错的和战关系中,在经历夏初政权之争失败的打击之后,致力于自身的发展,但远非尧舜之时股肱之臣的显赫地位可比。故伯益之子大廉、若木之后,嬴秦世系不清,没有留下连续的记载。直到夏末,若木后裔“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鸣条”。费昌“去夏归商”与“桀为暴虐,诸夷内侵”,东夷反叛参与商人灭夏的记载相吻合。《论衡》云:“桀无道,两日并照,在东者将起,在西者将灭,费昌问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曰:‘西,夏也,东,夷也。’”于是费昌徙族归殷。《博物志》卷上亦谓:“夏桀之时,费昌之河上,见二日:在东者灿灿将起;在西者沉沉将灭,若疾雷之声。昌问与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曰:‘西夏东殷。’于是费昌徙族归殷。”这是说在夏代晚期,费昌在河上向河伯冯夷请教后,便去夏归殷。在夷人参与商人的灭夏战争中,嬴秦无疑积极加入了灭夏的队伍。
(二)畎夷入陕与犬丘
商夷联军进入关中扫灭夏残余势力,嬴秦作为畎夷的属族或一支随之西迁关中。傅斯年就曾说:“商代向西拓土,嬴姓东夷人,在商人的旗帜下入于西戎。”[28]《竹书纪年》:“桀三年,畎夷入于岐以叛。”《后汉书·西羌传》:“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邠岐在今陕西旬邑和岐山县,这里正当泾渭平原,为商夷联军入陕后畎夷迁至关中时的最初居地。胡厚宣搜集到商代甲骨文中还有以下资料[29]:
己酉卜,贞雀往正(征)犬,弗其禽。十月。(《铁》181.3)
令犬方。(《续》下6.11)
辛酉,贞犬受年。十月。(《虚》44)

乙卯卜,率,贞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五月。(《续》5.2.2)
以上六条材料均是武丁时期的卜辞。内容涉及商王曾派雀去征伐犬方;犬地成为重要的农业区,商王曾贞问那里是否丰稔;犬方接受商王派遣与多子族一起征伐周族等。可知畎夷入陕后一直活动于关中地区。周文王后期,畎夷可能归降了周人。
畎夷活动于陕西泾渭流域时,犬丘成为其中心居邑。犬丘一名见于文献者共有四处,分别为兴平犬丘、西县犬丘、宋国犬丘和卫国犬丘。前两个犬丘地在西方,后两个犬丘俱在东方。西方的两处犬丘是畎夷入居泾渭流域后,分别为商代的畎夷和西周的嬴秦所居。今兴平县东南的槐里村,周时称犬丘,后称废丘,系畎夷入居为都之地;甘肃天水西南礼县(西县)之犬丘,又称西犬丘或西垂,即中潏率嬴秦西迁立都之地。胡厚宣指出:“周之犬丘,当即殷之故犬地。”“犬丘”一名亦当是随畎夷由东方西迁而来[29]。可见犬丘一名是随畎夷的迁徙而迁徙的。东方的两处犬丘:一为宋国犬丘,在今河南省与安徽省交界的永城县;一为卫国犬丘,在今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的菏泽。《春秋》隐公“八年春,宋公、卫侯遇于垂”。左氏传则谓宋公与卫侯“遇于犬丘”。杜预注云:“犬丘,垂也,地有两名。”可见《春秋》经文所说之“垂”与传文之“犬丘”为一地。又《左传》襄公元年:“郑子然侵宋,取犬丘。”杜注:“谯国酂县东北有犬丘城。……今归德府永城县西北三十里有大丘集,与夏邑接界。”据此,犬丘之名由山东菏泽至河南永城县,再至陕西兴平和甘肃礼县,正是畎夷由我国东方迁移至西方的路线足迹[30],则秦嬴源自东方的东夷,并且就是畎夷的一支。
(三)毕族、毕原、京与嬴秦西迁

“京”的本义并非京城、国都,而是指地势绝高的山丘。《说文解字》:“京,人所为绝高丘也。从高省,象高形。”《尔雅·释丘》:“绝高为之京。”有人认为京最初为炎帝、黄帝时的明堂,实际就是一座祭神用的高架栅居干阑式建筑,并具有仓储、祭祖、祀神乃至分化出宗庙、社稷、居室、仓储、京(国都专称)等多重功能[39]。则京作为地名必在国都或国都附近。以此而论,所谓“京室”也就是周人至岐后在京地修建的一个宫室。据李仲操考证,今陕西岐山县京当镇即是周人“京”地所在。1976年在京当镇凤雏村发掘的西周建筑“甲组”基址,从其结构布局、铭文记载、陶器形制、碳14测年等综合分析,正是太王初迁至岐所建的京室遗址[40]。

五、周人灭商与嬴秦西迁
周人灭商是历史上一件既决定周人也决定秦人命运的重大事件,周人建立了前后存续长达800余年之久的周王朝,而夏商以来几经起伏又一直处于流徙动荡状态的秦人,则最终完成了从东方向西方天水一带的迁徙。这就是嬴秦的第四、第五次西迁,即商末中潏率族至西垂和周公东征迁商奄之民到朱圉,此后,嬴秦开始了自己兴起建国的历史新阶段。
(一)商末中潏归周与嬴秦西迁

在周人灭商之前的“剪商”活动,也是世居关中的畎夷及其嬴秦族人与周人发生力量转换之时。从商王武乙时起,首先畎夷反叛商朝,故武乙、帝乙都曾率军进入关中征伐畎夷,畎夷势力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周人作为商王的属国,也受到畎夷的攻击。《帝王世纪》载:“昆夷(即畎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文王闭门修德,而不与战。”《尚书大传》亦谓:“文王受命,四年伐畎夷。”《毛诗·出车序》又载:文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说明当时畎夷包括嬴秦与周人的争夺和较量非常激烈。史书未载双方战争的结果,但到文王晚年,“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四十余国”。在这归附的四十余国中当包含与周人相邻的畎夷及嬴秦在内。所以,周武王灭商之后,遂有“放逐戎、夷泾洛之北”[42]卷119《匈奴传》的举动。这当是武王灭商后回师关中对已经归附的畎夷、嬴秦势力的进一步处置,嬴秦归周,“在西戎,保西垂”,西迁天水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的。
史载嬴秦中衍“其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据此可知,中潏之子孙蜚廉、恶来与殷纣王、周武王约略为同时代人,则中潏当是与商王文丁、帝乙、周文王同时代人。中潏之时已经“在西戎,保西垂”,也就是说至迟在周文王时中潏已经迁到了西垂。中潏之父为戎胥轩,在西周孝王与申侯关于戎胥轩的一段对话中,也能证实西迁这一点。《秦本纪》载:“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骊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周人世与戎族通婚,自戎胥轩起,嬴秦首领也与戎族通婚,由于西戎与周秦两族都有了姻亲关系,周、秦两族由此而“亲”。也因为周秦有了间接的相亲关系,戎胥轩生子中潏之后,嬴秦便“以亲故归周,保西垂”。可知,嬴秦西迁西垂,就在中潏之时。这就是嬴秦的第四次西迁。
中潏西迁天水,“在西戎,保西垂”,既是其与周人较量中失利后归顺周室的无奈之举,也是中潏化危为机和寻找机会的明智选择。周武王灭商前后嬴秦族人的活动《秦本纪》有具体记载:
(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使)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猛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骥、温骊、华駵、騄駬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周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穆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自蜚廉生季胜已下五世至造父,别居赵,赵衰其后也。恶来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皋,旁皋生太几,太几生大骆,大骆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蒙赵城,姓赵氏。
这段记载是解开秦人西迁与秦赵起源的关键。但是这段记述过于简略,也有一些缺漏和错误,导致人们对秦人历史的认识存在分歧。综合《史记》记载和已有研究,在纠谬补正的基础上,庶几可复原中潏在商周易代之际对嬴秦族人的应对安排和后来分合变化的大致情况。这里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其一,中潏之子蜚廉生有三个儿子。其中,恶来显系长子,季胜为三子,恶来革自然当为次子。其二,中潏、女防一支西迁西垂。自戎胥轩、中潏父子时,周人已经强大崛起,他们处在商、周两大势力的夹缝中,为了保全家族力量而采取了分散部族的两全之策。即中潏将部族力量一分为三,即蜚廉与长子恶来留在殷都事殷纣;蜚廉三子季胜前往晋南“别居”赵;蜚廉次子恶来革之子女防随中潏和嬴秦主体西迁西垂。这一选择不仅避免了嬴秦偏向一方有可能被镇压的风险,又完成了西迁西垂、离开周人核心势力区关中的目标,由此奠定了嬴秦族人改变命运和崛起发展的基础。其三,《史记》记载蜚廉死葬霍太山可能有误。按《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时蜚廉正在守北方,殷纣王被杀,蜚廉在今山西霍县的霍太山筑坛报祭殷纣王。接着蜚廉死后也葬于霍太山。这一说法有误,蜚廉并非已死,而是逃往嬴姓故地商奄一带发动嬴姓诸国参与三监之乱。蜚廉的这一行动又与嬴秦的最后一次西迁密切相关。
近年来,秦文化五方联合考古队已经在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进行了深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确认和发现了西山、大堡子山和山坪三座周代城址,以及圆顶山、鸾亭山等多处秦文化遗址,礼县为中潏落脚之地和秦人早期都邑、祖陵的所在地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周初周公东征与嬴秦西迁“朱圉”
在秦人早期西迁历史的研究中,李学勤通过清华简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2]。据清华简《系年》第三章简文,在叙述了周成王伐商邑平叛之后说:

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孟子·滕文公下》与清华简《系年》第三章交相印证,周灭商时飞廉并非死葬霍太山,而是潜逃到嬴姓故地商奄,并迅速发动东方的嬴姓诸国策应参加了三监之乱。奄为东方大国,国都在今曲阜,曾为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奄之称为“商奄”即此之故。奄也就是《秦本纪》所载的嬴姓运奄氏,飞廉逃往东方,也是因商奄一带及周围地区俱为嬴姓同姓诸国之故。《逸周书·作雒》篇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可见嬴姓诸国在这次叛乱中充当了主力,在周公平叛所灭的五十国中,嬴姓诸国竟达十七国。



毛家坪A组遗存反映了从西周前期至战国时期的秦文化。杨东晨认为戎胥轩、中潏、蜚廉、恶来等,均为秦国贵族裔支。周公所迁俘虏之秦人,为其后裔,当无所疑[11]。可以肯定,作为“商奄之民”迁入甘谷的秦人,有一部分或者说主体就曾定居于今毛家坪所在的甘谷县磐安镇一带。甘谷县南与礼县东北部相邻,礼县东北部正是早期秦人主要活动的区域,故这里与甘谷朱圉山距离较近。这说明甘谷、清水与礼县都是秦人早期主要的活动区域。
(三)关中“淮水”与嬴秦西迁

顾颉刚的上述考证,不仅说明位于东方包括淮水下游的东夷嬴秦族人在周公东征后迁西方的嬴秦族人不独进入陇右,在关中西安及以西均有分布。关中西部渭水支流雍水、湋水之名俱源自“淮水”之名。而“淮水”一名系嬴秦西迁带来名称的发现:一是证实了秦人确为东方鸟夷部族;二是证实了秦人确为西迁之部族;三是揭示了雍州、雍山、雍水、雍县、雍城之名“雍”,包括雍县后改称“凤翔”,都是源自“淮水”一名随秦人西迁,秦人为祀奉少昊之鸟夷部族的文化奥秘。
据上可知,周公东征促成了嬴秦的最后一次西迁,为嬴秦最终完成漫长而多次的西迁画上句号。因此,商周之际,秦人既弃商归周又继续追随纣王,既西迁西垂又在东方参与三监之乱,周公东征平定东方与嬴秦族人再次西迁,这一系列事件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既是早期秦人悲惨命运的生动反映,也是了解早期秦人文化特点和民族性格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