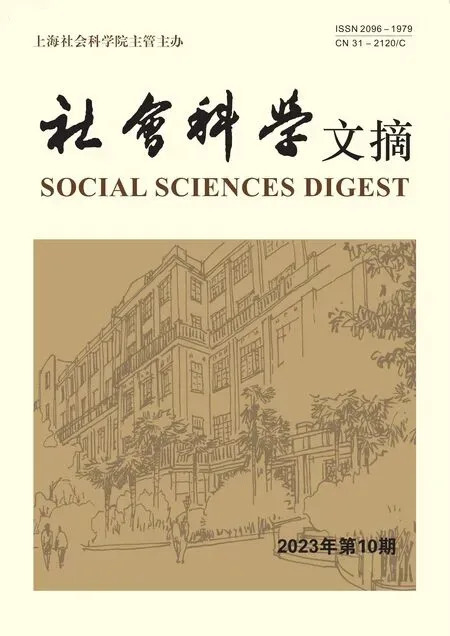四部区分与刘勰的大文论观
文/贾奋然
魏晋南朝四部区分,集部形成,文论话语大都将言说对象聚焦于集部文章。刘勰认同文章本体属性,又强调在整体文化传统中审视文章。他突破四部界域,将经传史子重新纳入文章视域中观照,融合其文艺精髓和文化内蕴建构理想文学范式,创建了“大文论”的学术视野和批评方法,促进了文学新变与文化精神的融合。本文诠释《文心雕龙》的大文论构架,探讨刘勰论文纳入经史子类之缘由,论述其创立的以文章为本位,融通四部的大文论思想的内在理路、价值旨归、民族特色和现代意义。
四部区分与刘勰论文立场
从汉代刘向、刘歆《七略》之“诗赋略”到魏晋南朝四部之分和总集编撰,中国古代集部形态逐步确立,文章本体特性也在四部区分和文笔之辨中得到较明确的阐发。此时文论大多摈除经史子类,独立审视文章,总集也大体在集部范围内收录文章。唯独刘勰《文心雕龙》论文四部并包,重建了经史子集贯通的话语形态,《文心雕龙》的性质也因此显得有些模糊。从历代目录归类看,《文心雕龙》曾被纳入集部总集类、别集类、文史类、诗文评类,子部子类或子杂类等。今人对其定位众说纷纭,有文学理论说,有文章学理论说,有文化学理论说,还有子书著作说,莫衷一是。但刘勰并非不明四部区分,他也没有打算研究经学、史学、子学,《序志》列举了魏晋文论经典并评说其优劣得失,鲜明地标明了自己的“论文”立场。刘勰的论文宗旨和目的是:其一,针砭时弊和建立文学理想。他从经学中寻找建构新文学的思想依据,从子史中吸取文艺创作的有益营养,创建文学的理想范式和人文精神。其二,不满于前代文论狭隘视域和窄小格局。魏晋文论开启了文章本体批评,但拘囿于作家作品或理论枝节问题,未能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刘勰极力从整体文化视域中探索文学之根脉本原,重建文论话语的整体形态和文化精神。刘勰论文四部并包,但始终立足文章本位,一方面吸纳经史子的文艺精髓建构理想文章范式,另一方面则竭力在文章中贯注经史子的文化精神。他对文章本体内核有清晰认知,《文心雕龙》“上篇以上”,囊括四部泛大之文,剖析了经史子之含文的特性,透视了文章由实用向审美,由公文向私文转化和聚合的轨迹;“下篇以下”则建构了完善的文章创造、文章形式和文章批评理论。其所论之“文”外延无限扩张,延伸至四部,内涵日渐缩小,追求文章本体内核,看似悖论,但实际并不矛盾。南朝骈文大盛,对语言形式美的追求几欲渗透至所有文章体式中,立足于审美观照文章是时代的普遍风气。刘勰也充分认识到文学与经子史之间区域有别,但并非壁垒森严、不可逾越,四部同源共生,互涵互摄,构成了统一的知识景观和人文精神。本于文化通观的宏大视域,刘勰突破四部界限,广泛地吸收经传子史的文章精髓,针砭时弊,创立新说,建构了“体大而虑周”的文艺思想体系,这使其文论带有子学性质,又具有了文化学特征。效果大于意图,《文心雕龙》呈现出多文本的奇特效果,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使其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永久魅力。
兼容四部的大文论构架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建构了以道、经为本原,以《离骚》为经文贯通的文学风标,以集部之文为主体,以史、子冠笔类之首的大文论构架。“文之枢纽”的《原道》《宗经》《征圣》三篇论经、文关系,提出文原于道,宗法经书,师范圣人的基本文学观点。本于“交错为文”的文章本训,刘勰推原文于道,建构了天、地、人、文的宇宙发生模式和文章生成模式;又通过“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理论逻辑推演“文以明道”的道德模式,为文章确立了一个宏大的逻辑起点和文化基点。刘勰历史、逻辑地建构以经书为本原的中国文章学谱系,五经是圣人体法道心神理制作的大文章,与后世之文构成了根茎与枝叶的关系。刘勰在“本然”和“当然”意义上统一文道,并将文章上升至本体论高度,较之汉人依经立义、魏晋以降文学批评囿于集部,视野更开阔,识见更深远,极大地提升了文章的终极意义和地位作用。这在当时文坛是独特的,其见识的确超出汉魏六朝文士之上。
刘勰论文广收博取,弥纶群言,但绝非“杂家”,他议论对象,无论经纬之学还是史子之论皆立足文章本位。刘勰将《辨骚》置于“文之枢纽”而非“论文叙笔”确有深意,体现了他“大文论”构架的独特“用心”,目的是在为其论文确立以审美为内核又融通文化精神的标杆。刘勰依经辨骚,论《楚辞》与经书的四同四异,但已然突破汉人宗经藩篱,从审美视角对《楚辞》的文学成就和艺术创新作了高度评价,称颂其“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在文学精神和艺术形式上皆堪作典范。刘勰“论文叙笔”文体论中有《史传》《诸子》两篇,冠笔类之首。在四部区分的南朝,刘勰论文纳入史、子,遭人诟病。纪昀高度肯定刘勰宗经思想,但对其论文辟专篇论史、子颇有微词。刘勰将《史传》《诸子》置于文体论中乃本于文章作法,更多地关注了史书和子书作为文体类型的文章学价值。中国文学根植于文史哲合一的整体文化传统中,圣贤书辞原本就是根本于道、衔华佩实的大文章,是文学的源头和典范。后世文章类型多发端于五经;而史、子亦文章大手笔,为文章写作提供了诸多范型,从早期史著和先秦诸子中亦分化出众多文章类型。
史传为载史之笔,体制宏大,《尚书》《春秋》分列“六艺”两部,实为史籍,亦史学之源。笔类文章肇始于史笔,《宗经》云“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刘勰所论公牍、书牍等文体,最早多载于史籍,后逐渐从史传中分化,成为独立文章形式,因讲究文采,且为“篇翰”,被纳入集部。《诸子》在文体论中有特殊地位。刘勰分析了子书与经书的复杂关系。从发生学而言,子先于经。先秦儒家原本诸子支派,战国至汉代逐渐杂糅阴阳家、道家、法家、名家等诸家思想发展壮大,升为经典,此即“经子异流”。先秦诸子较早奠定了论、说、小说等文体的基本形态,刘勰将论追溯到《论语》《庄子》之子论,又区分子与论的不同,先秦诸子是“博明万事”之宏论,后世之论则演化为政论、史论、经论、文论等不同类型,为“适辨一理”之专论,这是论由子出的轨迹。《宗经》云“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刘勰所云“论出于经”与“论出于子”亦不矛盾。《易》作为儒家六艺之一,经历了从子学上升为经学的过程,《易传》杂糅儒道诸子之说解经,实与子论无异。说是游说辩理之文,出于战国纵横家说辞。纵横之士陈辩政术,骋其巧辞,又由“唇舌”移于“刀笔”,形成独立成体的“说”。《诸子》云“青史曲缀以街谈”,《青史子》被《汉志》列为诸子十家九流之末的“小说家”,刘勰以小说体俗,未单独论列,而先秦诸子是后世小说发生的重要来源已为学界共识。刘勰论文兼及四部,充分关注了经史子集的血脉贯通的关系。史、子实则亦有文源意义,后世笔类文体多从其发端,故刘勰置史、子于笔类之首,这体现了其大文论构架的独特视域。
四部融通的文学发展路径
四部之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先秦文史哲合而未分,子学腾跃,经学尚未昌明;汉代独尊儒术,经学蔚为大观,《汉志》经、子、集初步分流,史部依附经部,集部尚未完备形成;魏晋南朝,文学、历史充分发展,荀勖、李充的目录编撰中经、史分流,集部形态在别集、总集编撰中逐步完善,四部体例形成;至《隋志》正式确立四部之目。四部之分延伸至清代《四库全书》,达到登峰造极,近代后才逐渐被西方精密的学科分类体系取代。
在南朝四部区分的学术视野中,《文选》标示“文”的界域,明确表示不选经史子类,张扬文章“沈思”“翰藻”之特性,促进了对文章本体特征的认知,这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这种文学观念在唐宋古文运动中受到抑制,至清代阮元“文言”说则进一步彰显,近代以来因与西方“纯文学”观念接轨而愈加畅行。但近代的“纯文学”进一步缩减了萧统确立的集部范围,视域愈加狭窄,弊端显露。
刘勰关于“文”概念有诸多层次:首先是最宏大的文,即天地之文,万物之文;其次是“繇辞炳曜”“文字始炳”的卦爻、文字之文,“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之人文;再次是“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的经文;复次是子、史文章;最后是“论文叙笔”中各类文章。所有这些“文”皆属于具有内在贯通性的“道之文”。刘勰观照“文”的视角本于“交错为文”的文章本训,这内在性地构成了对文章形式美的肯定。在刘勰看来“经史子皆文”与“经史子之含文”具有内在统一性。四部之分固然意味着经、子、史、集各有封域,但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四部以经学为根脉,史、子、集为流裔,彼此交融,血脉贯通,蕴含着天地人文的基本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内生力的完整知识结构和思想谱系。在历史发展中观照四部之分合,经书实则包含着今人所说的文学、历史、哲学等文本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性特征和人文精神;先秦诸子“入道见志”,洋洋渊博,亦艺文之大观;史书则开叙事文学先河:这些皆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若笼统地将经、史、子摒除在文学之外,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和审美精髓亦将随之不存。古人十分重视经、文的贯通性,即使是在四部区分的魏晋南朝,人们不再将经学视为文学研究对象,但在文原观念上还是肯定经书的源头和典范意义。
刘勰认同文章本体属性,也充分关注四部合而未分时期经史子各自蕴含的文学性特征,以及经史子在后世发展中与文学融合的那部分特性,构筑了以文章为本位的四部融通的大文论批评视域,其大文论思想指涉两方面。其一是重建文学的完整谱系、人文内涵和文化精神,以“文道合一”为基本价值取向。刘勰将各类文体追根溯源至经传子史的整体文化形态中,建构了以道、经为本原,旁通子、史的文章学谱系和文学批评视域,在四部融通中重建文学的民族文化精神。刘勰还提出风骨、通变等范畴践行文化与文学融通的理念。风骨是“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与“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的四部融通而创生的批评范畴。“风”源出《诗经》“六义”之首的风教,强调文学要蕴含情志意气;“骨”出于《尚书》“辞尚体要”,以“结言端直”为要旨。“风清骨峻”,则“篇体光华”。通变是“参古定法”与“望今制奇”的返本开新,创造“颖脱之文”的路径是“博览以精阅”与“规略文统”的融合,即在广泛吸收四部文章精髓的基础上运用文思,才能创作出文采如曲虹高拱、光芒似朱鸟振翅的杰出作品。其二是从四部中吸收文章写作的有益养分和丰富资源,促进文学创新发展。首先,作家要从经史子集中获得滋养,通过博览群书以颐养情性、陶冶志趣,在触景生情和兴致勃发中,写出情感饱满而具有深度内蕴的文章。其次,要从四部中吸收文章精髓,刘勰提出“六义说”,这是从经书中提炼出来的关于文章写作的基本纲领。再次,要从浩瀚渊博的四部中吸取丰富事典,加强文章的思想内蕴和艺术表现力。最后,从四部中吸收彬彬“丽藻”和技法文术。
刘勰以融通古今的宏大气魄,重建文学与文化的关联域,其开阔视域和深刻洞见不仅表现出针砭时弊的现实价值,也显示出超时空的未来指向性,为唐、宋以降的古文运动提供了启示和借鉴。古文运动直指齐、梁以来骈文写作的浮靡文风,在四部“旁推交通”中重建文学传统,其先驱者则是刘勰。宋代总集编撰开始突破《文选》不选六艺、史传、诸子的做法,大量在经传子史中拓展文章经典,也见出刘勰四部融通的大文论思想的影响。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纯文学”观念和精细学科分类的影响,“小文论”批评模式逐渐盛行。这首先表现在用西方“纯文学”观念剪裁中国文学话语的完整形态,将公牍文、书牍文、铭诔文、哀祭文等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文章文体皆排除在文学范围外,解构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其次,文学批评视域狭小,将文学、文论从整体文化传统中剥离提纯,建构“纯文学”批评范式,文学研究成为专门化研究。如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精细,文论与文学区分,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区分,许多学者据守自身领域深耕细作,缺少融通古今和打破学科壁垒的视野和格局。刘勰以文章为本位的四部融通思想和“大文论”的批评视域为我们重建具有中华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
结语
经史子集是互涵互摄、彼此交融和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完整文化形态,蕴涵着天地人文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刘勰在南朝四部区分和集部形成的语境中,立足文章本位,建构了经纬兼济、史子旁通、诗骚结合的兼容四部的大文论框架。他提出经史子之含文,一方面吸纳经史子的文艺精髓建构理想文学范式,另一方面则竭力在文学中贯注经史子的文化精神。他还提出风骨、通变等范畴践行文化与文学融通的理念。刘勰的大文论思想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批判精神,也具有指向未来的超前性,为唐宋以降的古文运动提供了变革路径,其融合古今、贯通四部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