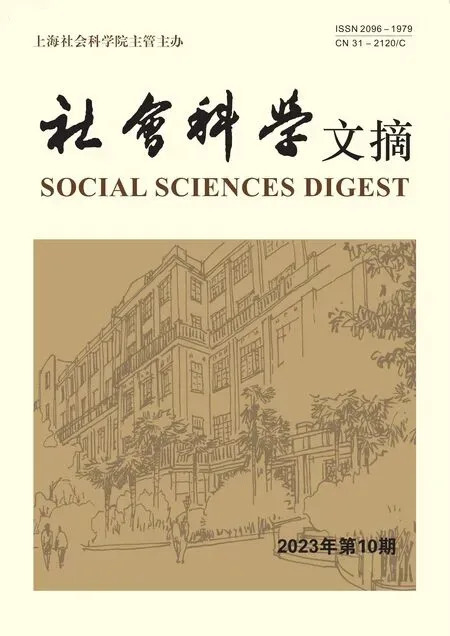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法治驱动的三个进路
文/王军杰
问题的提出:从政治驱动向法治驱动跨越的必要性
缘于政治动议、成于条约治理是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治理的成功经验。为了避免二战前贸易保护主义引发的国际经贸的混乱、失序与萧条,美英借助战时积累的国际政治影响力,动议并主导了战后国际经贸秩序的重建及法治化进程。国际社会广泛的政治共识推动了战后条约法律机制的速成。世界经济的“三驾马车”(IMF、WB和GATT/WTO)如期如愿达成落地,国际经贸秩序由战时的“政治驱动”转向战后的“法治驱动”,进而实现了由政治动议向条约治理的跨越与蜕变。在统一、稳定的国际条约法律机制的助推下,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治理迎来了长久的爆发期和繁荣期。
法治驱动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内在要求。当前,“一带一路”倡议面临多重挑战:一是在中美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倡议推进时常被西方某些人误认为我国在利用经济实力实现地缘扩张;二是沿线风险居高不下,传统商业风险和非商业性风险叠加,导致“走出去是看点,安全回来是难点”。完善的国际条约法律体系将有助于消除沿线法律的差异性及碎片化,增强制度的确定性、稳定性,提升合作的可预期性及透明度,消除西方的疑虑或诋毁。
法治驱动是掌控“一带一路”规则制定权的重要依托。近代大国兴衰的国际秩序演进揭示出,在复杂的国际秩序系统中,谁能引领并制定规则,谁就将获得系统持久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推动“一带一路”法治化的理由有三:一是用行动向共建国家表明中国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经贸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二是在规则制定过程中切实贯彻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精神,带领各国迈向真正的多边主义;三是沿线多数国家国际治理经验匮乏,法治化进程多半需要我国的引领和支持,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提升“一带一路”规制的制定权和领导权。
构建完善、协同的条约网络体系
完善的条约网络体系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基础性条件,是“制度性基础设施”。首先,须对现有条约内容进行全面完善,包括但不限于废止、修改、重签等。其次,填补条约的空白,尽可能实现共建国家条约的全覆盖。最后,在建构条约网络时,应特别注重不同条约之间内容上的协同性和逻辑性,避免不一致,甚或矛盾之处。本文以双边投资条约(BIT)为例予以分析。
其一,构建完善、新鲜的投资条约网络体系。首先,我国同“一带一路”国家所签订的BITs条约内容陈旧,已无法适应我国在沿线双向投资关系中地位的新变化和新形势,应及时对现有条约的陈旧条款进行更新、迭代。其次,截止到2023年9月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仍有10个国家尚未与我国签订BITs,须尽快实现共建国家BIT的全覆盖。最后,当前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呈现两种趋势,一是纯粹、单一的BIT条约持续繁荣,二是把投资法纳入综合性的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独立成章,替代传统的BIT条约。我国与共建国家间BITs条约的更新迭代,两种路径并行不悖,但须保持协定内容上的协调一致和逻辑上的衔接互补。
其二,及时迭代条约中的滞后规范。我国已成为典型的资本输出大国,BIT文本规则须及时回应这一变化,进一步强调对投资者利益的公平保护。另,BIT内容亦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保持协同。要点如下:第一,我国与共建国家已经签订的BITs中仍有少数未规定代位求偿权条款,应尽快修约或签署补充协议予以弥补。第二,我国与共建国家不同时期的BIT规定的补偿计算“时间点”不尽相同,须尽可能地明确统一征收补偿标准。第三,不同BIT中对“投资”标的界定不一致,在条约后续的修改完善中应尽可能地明确统一,避免歧义。第四,我国同“一带一路”国家所签订的BITs中只有少数规定了“岔路口条款”,且多数附加了限制条件。我国同东盟10国之间BITs中的管辖权条款可以直接嫁接《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第14条之规定,最大限度保持条约的协同性。尚未提供国际投资仲裁救济选择的其他BITs,应在后续修改中完善。
推动形成多元、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根据不同的争议主体,“一带一路”沿线的经贸争议包括:国家间的争议,国家与私人之间的争议,私人之间的争议三类。对于前两类争议可以考量设立独立的“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构。第三类争议可继续由传统的属地诉讼、商事仲裁调解等途径予以消解。如是,有望形成属地诉讼、商事仲裁与调解、“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构“三位一体”的多元化、综合性纠纷解决框架。
建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构有五个方面的必要性。第一,WTO争议解决机构难以胜任共建国家间争议之解决:一是WTO争端解决机构无法覆盖所有的争议类型;二是非成员国之间的争议亦无法诉诸WTO管辖;三是WTO上诉机构已经停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能否发挥原上诉机构的机制功能尚待观察;四是WTO专家组报告只有责令修改国内法和授权报复两种裁决,关键的裁决形式“损害赔偿”缺失。第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亦无法完全解决共建国家与私人之间的争议:一是ICSID只管辖投资争议,其他类型争议无法诉诸ICSID管辖;二是原则上ICSID对非成员国当事方没有管辖权;三是ICSID上诉机构缺失、透明度问题等一度引发国际社会对ICSID的信任危机。第三,东道国属地管辖难以克服属地保护,私人合法利益难获公平救济。第四,“一带一路”独立争议解决机制系推动倡议法治化的“牙齿”和保障。第五,“一带一路”独立争议解决机制是有效维护我国相关利益的最后手段。
设立“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构(BRDSB)须重点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BRDSB的管辖权范围。首先,BRDSB管辖权可从当事人适格、争议范围和双方同意三个方面进行限定。就国家间的纠纷而言,须是缔约国之间针对现行有效的“条约”的权利义务之纠纷,并由双方书面同意提交BRDSB管辖的,BRDSB方可取得个案管辖权。此处的“条约”包括缔约国之间所有现行有效的条约、公约和协定。就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纠纷而言,须是缔约国和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的争议,并由双方书面同意后,BRDSB方能取得管辖权。此处的“条约”主要包括旨在保护对方缔约国国民权益的投资条约、税收条约、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等。其次,关于成员国接受BRDSB管辖权的方式。可将加入BRDSB公约与接受BRDSB的管辖别而制之,即加入BRDSB公约并不必然代表接受BRDSB的管辖。
第二,BRDSB的主要程序。BRDSB可以设定三个基本程序。一是磋商,争议发生后,双方当事人应首先启动磋商程序,如限定期限内磋商未果,方可提起调解或仲裁请求。二是调解,调解和仲裁作为两个有限的平行程序可供当事人选择。调解成功后,可出具调解书,调解书与仲裁裁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和执行力。三是仲裁,磋商未果当事人可以直接启动仲裁程序,也可在调解未果后再提起仲裁。
第三,BRDSB上诉仲裁程序。首先,上诉机构须是一个常设机构,仲裁员应该是专职的且须是国际投资、法律、条约等方面的权威人士。吸取WTO上诉机构之经验教训,上诉机构常任仲裁员不应少于10人,且应是单数,两批次任期最好交错配合。此外,条约文本应把上诉机构仲裁员人数的确定权赋予理事会,避免必须修改条约才能调整人数,防止WTO上诉机构改革困境重演。其次,上诉审查不应局限于“法律适用错误”。上诉审查的范围可以限定在法律适用错误以及明显、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再次,上诉期限应适当。BRDSB上诉期限可确定为3—6个月。此外,BRDSB可以根据上诉理由决定采用更简洁的仲裁程序,并规定不同的上诉时限。最后,拟定“上诉机构规则”和“上诉机构附加便利规则”。一方面,基础性条约应该把立改废程序规则的权限直接赋予理事会行使,最大限度减少触发条约修改,保证条约的稳定性及运行效率。另一方面,“附加便利规则”是非缔约国同意BRDSB仲裁的规则依据。此外,如认为上诉仲裁过于激进,亦可采用裁决前评议制度作为缓冲。
第四,裁决的类型与效力。首先,国家间纠纷的裁决类型可以设定为违反条约义务、责令修改国内法等;国家与私人之间的纠纷,其裁决则以履行义务、损害赔偿为主。其次,BRDSB裁决效力须是终局的,未上诉的初裁裁决和上诉机构终局裁决在各缔约国境内具有既判力,任何其他司法、仲裁机构无权重新审查。国内法院在承认执行该裁决时亦不得进行二次审查,并应严格限定公共秩序保留的范围。最后,应明确上诉裁决之类型。借鉴国际常设投资法庭机制(ICS)之经验,对初审尚未生效的裁判,上诉庭可作出维持原判、全部或部分改判、驳回上诉、发回重审等裁决。
第五,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一是BRDSB条约的内部执行机制,即由条约明确约定各成员国应把BRDSB裁决视为本国终审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各缔约国在本国境内负有无条件执行仲裁裁决的义务。二是BRDSB裁决的外部执行机制,即把BRDSB裁决认定为《纽约公约》或《ICSID公约》多边条约项下的仲裁裁决,旨在借助此类多边条约赋予BRDSB裁决的执行力。需要注意的是,一则对于双方当事人均是国家的裁决,无法借助《纽约公约》或《ICSID公约》予以执行,只能依靠BRDSB的内部执行机制进行承认和执行;二则在拟定BRDSB条约、程序规范等方面应尽可能增强BRDSB的仲裁属性,着力避免其司法属性,确保裁决外部执行机制的顺利实施;三则根据调解程序而生成的调解书,可以允许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由BRDSB出具调解书或仲裁裁决书。此外,BRDSB裁决执行机制还应避免类似于《ICSID公约》第55条的执行豁免,促使其成为一个较为彻底的自足性法律体系。
第六,形成自给自足的闭环式机制体系。“自给自足的闭环式法律体系”的特征有四:一是争议解决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具有排他的专属审查权;二是对裁决拥有独立的自我审查机制,排除国别司法机构对BRDSB裁决进行审查;三是BRDSB裁决在缔约国境内具有确定的执行力,缔约国司法机构应无条件地履行裁决执行义务,确保裁决的既判力和终局性;四是条约赋予BRDSB采取临时措施的自我裁定权,进而排除传统商事仲裁机构依靠国别法院发布保全、查封的做法。
创建“一带一路”常设协调机构
设立常设性协调机构的必要性在于,第一,常设协调机构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条件。常设协调机构对条约及其组织发展具有强大的助推功用,国际贸易组织(ITO)到WTO的演进实践是最好的例证。当ITO确定无法成立后,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ICITO)成了事实上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秘书处,也正是该委员会全力推动了后续GATT的多轮贸易谈判,包括成功签署WTO协定的乌拉圭回合,最终促成WTO诞生。第二,常设协调机构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法治化转向的重要依托。“一带一路”倡议的上半场更多是基于双边互信的政治驱动,但下半场已步入高质量共建阶段,其路径是基于多边合作的条约驱动,这无疑需要专门机构的组织与协调。
构建“一带一路”常设协调机构有如下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名称及其法理基础。“一带一路”的法治化、一体化进程的未来发展可能存在两个递进的阶段:第一个是倡议阶段,其法理基础是各国支持倡议的备忘录等合作文件(软规则);第二个是组织阶段,其法理基础是各国签署生效的双/多边国际条约(硬法律)。在初级的倡议阶段,可以设立“一带一路办公室”。过渡到更高级的组织阶段后,应建立“一带一路”国际组织(BRIO)及其秘书处。
第二,法律性质及宗旨功能。根据国际法理,“一带一路办公室”不具有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只是一个联络协调机构。但BRIO应基于共建国家签署的“一带一路”国际组织协定而设立,该组织具有完全的国际法律人格和权利能力。同时,该组织及分支机构享有国际法上的豁免权。常设协调机构的职能包括组织、管理、协调,以及推动BRDSB高效、有序运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法治化提供硬约束。
第三,常设协调机构的组织架构。借鉴WTO及ICSID的治理经验,BRIO宜采用扁平化的双层次治理机构,即理事会和秘书处。理事会是权力机构,秘书处是日常工作机构。理事会和秘书处成员构成、任期、会议召开及投票规则均可参鉴WTO及ICSID治理经验。为了方便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展开合作,建议由AIIB行长兼任BRIO理事会主席。
第四,“三位一体”的组织框架。首先,BRIO、BRDSB和AIIB的价值目标趋同,均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法治化。BRIO的价值定位是综合性协调机构,BRDSB可设在BRIO组织之内并独立运行,AIIB则通过在各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了强化我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法治化的引领,实现三大支柱的有效协同,AIIB行长可以同时兼任BRIO理事会主席和BRDSB的秘书长。同时,BRIO和BRDSB的总部亦可设在AIIB所在的办公地点,在物理空间可以共享与同构。其次,三者宗旨趋同。BRIO和BRDSB为倡议法治化转向提供了“软资源”,AIIB则为倡议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硬设施”。再次,三者在功能上又存在互补。通过多边协调,BRIO可以提升条约法律的稳定性与统一性,BRDSB 将为解决AIIB投融资纠纷提供多元化选择,而AIIB可以为二者提供资金支持。最后,三者涵盖的区域范围基本一致。“一带一路”倡议主要覆盖范围依然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中亚、西亚及中东。三者功能各异,但地理范围基本统一。“三大支柱”相辅相成,有机衔接,有望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法治化升维的“三驾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