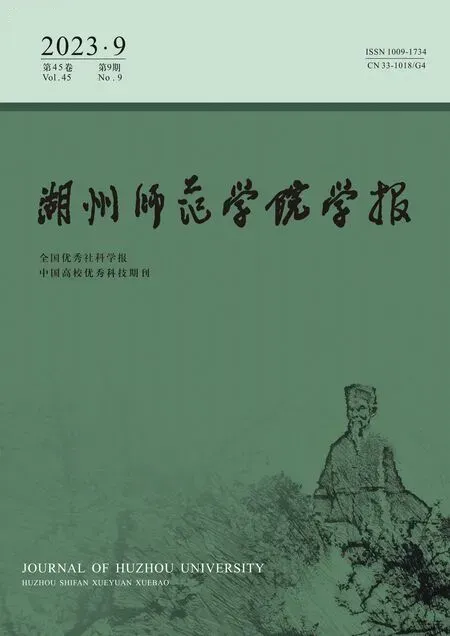现实语境、生成逻辑与实践样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三维探析*
杨磊鑫,叶荣国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1]16。可见,精神之于人、之于国、之于民族、之于未来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精神”的重要性做了新的考量,突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2]22-23。在新的征程上,多维度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定位其语境、厘清其源流、探寻其实践样态,对切实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增强全民族精神风貌与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语境
新时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深入,中国梦稳步推进。既然如此,为何还要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聚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语境。
(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向度
作为共同富裕的一体两面,物质共富和精神共富同频共振、缺一不可。单方面的物质富足不是真正的美好生活,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内在规定,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强大动力。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内蕴精神生活极大丰富的现实期许。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从物质需要的满足中获得快感是人的动物性体现,或者说是人的自然属性,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对精神交往的需要和精神世界的丰富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重要体现,即“对科学的向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的道德力量和他们对自己发展的不倦的要求”[3]107,可见,真正的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是实现人全面而自由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人民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满足,“物质幸福”得以普遍实现,人民对高质量美好生活的新需要转而成为矛盾的一方。如果说过去人们追求的是衣、食、住、行等生存性需要,是“体之要”,那么现阶段人们注重追求的是文化学识的丰富、道德修养的提升、视野胸怀的宽广、审美品位的高雅等发展性需要,是“心之要”,这些都与精神生活相关。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物质层面的绝对贫困,具备“个人硬实力”之后,人们更加注重“个人软实力”的提升,即满足感官欲望的同时,更加注重审美境界的跃迁[4]64-75,这表明发展性需要不再处于从属位置,追求“精神幸福”成为人们生活常态,精神生活的富裕程度自然成为衡量人民生活美好程度的标尺之一。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对人民美好生活现实诉求的主动应答。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转化为物质,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能仅停留在精神层面的畅想,更要以“改造世界”的决心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质性”呈现。何以呈现,“精神主动”至关重要,精神主动是主体在认识世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在遵循规律、改造世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展现的积极作为、能动奋进、勇毅自信的精神品质与精神状态[5]32-45。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能够增长人们的才智、凝聚人们的价值共识,以精神主动赋能美好生活的实现。美好生活具有全民指向性,如果个体精神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处于涣散无序的状态,缺乏价值认同,就不能集中高效地发挥人民之智,就不能汇聚起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奔向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与不息动力。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诉求不断增强的时空境遇下,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塑造主动的精神状态、统和美好的生活向往、构建良好的道德秩序、凝聚强大的奋斗合力,能够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支柱与动力支撑,使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中能够有力可用、有势可借,主动作为,共谋美好之策、同建美好家园、共享美好生活。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所以附加“伟大”这一限定性前缀,是因为单纯的物质崛起并不是真正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方位的复兴,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复兴之内涵,也是复兴之伟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蕴含中华精神文化强盛繁荣的复兴深义。“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6]5。民族精神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魂”“源”,根深才能枝繁叶茂,魂固才能基业永存,源清才能长流不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的复兴,不仅是物质的强盛,更是文化的繁荣与精神的富足。中华精神与文化的复兴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根据时代与人民需要实现持续的、科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化服务力、创造力、引领力不断提升;意味着中国民族共同体空前坚固,中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不断增强;意味着中华民族能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持续增进。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历次磨难中成长,从历次磨难中奋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世代中华儿女以独特智慧培育和发展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脱贫脱困脱险、向善向上向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鉴往知来,中华精神与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然之义与必然之要。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劲推力。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6]5。首先,精神共富能够凝聚全民族强烈的精神认同,为民族复兴塑造强大的精神定力。一个民族,只有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保持对本民族精神文化的坚守认同和对其他民族精神文化的理性审视,才能坚挺精神脊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在“两个大局”深度演进、思想文化交锋加剧、精神领域斗争频仍的历史境况下,中国人民能够站稳意识形态立场,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体认传统文化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居所。其次,精神共富能够调动全民族的精神自觉,为民族复兴注入不懈的精神动力。精神自觉是人的精神主动的现实体现,具有计划性、目的性、创造性等表现特征[5]32-45。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人们能够普遍预见民族复兴的样态,并发挥自身聪明才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新方案、新策略与新方法。最后,精神共富能够增强全民族的精神自信,为民族复兴提供坚韧的精神耐力。“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能力,也考验耐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意味着人们对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二者力量的确信,确保以团结奋斗的良久姿态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持续推向更深处。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优势表征
精神生活的贫富是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正如法国学者基佐所言:“文明主要包括两点:社会状态的进展与精神状态的进展;人的外部条件和一般条件的进展,以及人的内部性质和个人性质的进展;总而言之,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7]8-9
精神缺失是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文明旧形态之桎梏,反映人的单向性和社会的极权性。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新型极权主义社会,所谓新型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暴力型极权”,其通过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满足人们各种虚假需求,使人们身处一种看似舒适,实则不自由的生活模式,表现为政治领域的封闭、文化领域的同化与俗化,以及话语领域的封闭等,人们的生活被“极权主义”框定在特定范围之内,导致人的思想和行为逐渐趋于单一化和同质化,只有对现存秩序的“惯性认同”,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即丧失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遭到了剥夺”[8]3。除此之外,文化消费主义也侵蚀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在资本逻辑下,精神生产漠视对人的精神需求的满足,单以精神产品的快速流通获利为目的,结果就是缺乏“灵魂”的精神产品充斥精神市场,“占有主义”主导精神消费,精神经济看似一片繁荣,实则是人的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虚假统一”[9]5-11。马克思把人类文明历程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个性,造成“精神缺失”这一可悲现状的现实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无法挣脱对物的依赖。
精神共富是人本逻辑主导下的文明新形态之表征,指向人的全面性和社会的有序性。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五大文明的相育相生、同频共振、协调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秩序与显性特征。中国所创造的文明形态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畸形文明形态,而是兼顾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促进社会和人类更加完善的新型文明形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何以新”之问的特定回答,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超越性指向和独特优势体现。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终极追求。比较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之一就是,在“人本逻辑”主导下,人的精神生活实现了异化的扬弃,不仅以“人”为目的,而且以“精神增值”“精神共富”为导向,旨在于精神产品的优质多样供给与良性消化吸收的互动中跳脱“物”的束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脉脉相通、协调有序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支撑,贯通于其他文明领域之中[10]10-1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级样态,能够统一人们对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的价值共识,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23-24构建精神秩序、注入精神动力,推动整个社会在有序运转中前进。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源起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生活的科学理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富裕思想,生成于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的百年实践,以深刻的理论底蕴、文化底蕴和历史底蕴展现出强有力的逻辑必然性。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精神生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表达
中国当前的蓬勃发展和取得的现实成就以及未来的持续强盛无不展现和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真理性同样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中窥见。
首先,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探讨中确证精神生活的派生性与重要性。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经典的哲学命题,讨论精神不能脱离物质,黑格尔曾犯了“唯精神论”的错误,以“绝对精神”赋予精神以独立的外观,遮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相反,马克思以物质为源头和基点,探寻精神与物质二者关系,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11]161。“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2]2这为精神生活寻到源头,强调了精神生活的派生性。在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与动物的角度做了对比,认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1]56,而动物只能本能地、被动式地生产,这体现出精神生活之于人所以为人的不可或缺性。同时,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所谓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9。
其次,在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中展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美好场景。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思想在积聚财富的同时造成“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3]665,使人成为物的奴隶,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寻求“人的解放”,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无情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进行了颠覆式构想。第一,物的极大丰富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提供可能。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按需分配引发阶级、国家、战争和“三大差别”的消亡,为人们追求精神满足创造了先决条件。第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呈现样态。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摆脱了对人和物的依赖性,“利益式分工”也随之消亡,自由时间的充裕为人们更加积极地谋求精神生活的富足提供了条件。第三,必然王国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现实产物。精神的富足是为了现实的美好,人从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转而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都需要社会成员精神的普遍独立与富足。
最后,在精神生产和交往理论的阐发中呈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作用范式。精神生活的贫富程度是衡量人发展程度与潜力的重要因素,而精神生产是精神生活的关键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1]151-152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它的产品具有物的外壳,所以同物质生产一样,精神生产的流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这四个环节的有序衔接与循环。其二,交往是精神生产、发展、富裕的重要方式,人们总是通过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方式使自己处于交往的境地,物质交往能够携带精神的交流,精神的交往能够实现个体灵魂碰撞与修养的提升。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11]169。
(二)文化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精神富裕思想的传承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创造性、包容性、本土性和连续性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伟大智慧和美好追求理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源流。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描绘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生产力和文明水平都得到极大发展的今天才出现的“新愿景”,中华民族的先人们以其理性智慧对大同世界的畅想早已包含了对精神境界的规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大同社会描绘了一个全体成员安居乐业、讲信重善、人人为公、各尽其力的理想世界,这样美好的社会既是精神世界富足的体现,也是精神生活极大丰富的结果。其中蕴含的道德理念、文明状态和共建共治共享思想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社会层面的应然呈现。不仅如此,先哲们在个人层面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也作了设想和要求。不论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陶渊明《桃花源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还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 ,都体现了个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道德情操的高雅。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优秀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立”、得以“兴”、得以“久”的根基与灵魂,其孕育的优秀基因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描绘了底色,注入了智慧。第一,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不论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乾》),“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的规诫,还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劝勉,都诠释了自强不息之于人的重要,之于人的精神的重要。第二,先人后己的集体观念。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每一次大事都有“集体主义”的色彩,比如大禹的治水为民、岳飞的抗金卫国、司马迁的著书立学等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典范,肩负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与使命。这些优秀基因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构想和实现样态绘制了亮丽底色。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实践的民族”[14]105-111,不仅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做了愿景描绘,而且进行了实践探索。第一,以物质生活的富足为首要实现。面对弟子“既富矣,又何加焉”(《论语·子路》)之问,孔子以“教之”回应,之后董仲舒指出“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春秋繁露》)的道理,还有管子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等,都明确了物质富足之于精神追求的基础性。第二,以见贤思齐、和而不同的态度追求精神富裕。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裕关键是要端正态度,对于个人要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的态度向精神修养崇高的人看齐;对于国家,则要“和而不同”,既要传承弘扬本民族文化,又要学习、借鉴、融和各民族优秀文化,为追求精神富裕提供充足养料。第三,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和标准考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求在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时要循序渐进,遵循阶段性原则。
(三)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百年实践的守正创新
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中之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深入、完善、凸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生成脉络需要在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的百年历程中厘清。
从“被动”到“主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以精神上“醒过来”为主要内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悲惨遭遇导致中国人民精神上一度陷入“被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英勇斗争,“但终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15]180。究其失败之因,核心之一就是没有从精神上唤醒人民群众,没有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支持。为了唤醒人民的救亡意识,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主心骨,精神上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同年创立“人民出版社”,为人民出好书,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把文艺作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来建设,大范围开展“冬学运动”,中国人民争独立、求解放的意识空前强烈。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主动革命”下取得胜利的。
从“站立”到“站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以精神上“站起来”为主要内容。天安门城楼上的庄严宣告标志着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站立”了,但并不意味着“站稳”。为了使人民群众在精神上不仅立住而且稳住,党在全社会开展了精神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党领导人民禁绝黄赌毒,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提出“五爱”公德建设新标准,破除旧社会痼疾,移风易俗。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党领导各族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之中,这期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典型人物,形成一系列伟大精神,通过对“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16]5,饱满的精神状态成为全民所向,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幸福生活已成为普遍共识,中国人民在精神上逐渐“站稳”了。
从“匮乏”到“充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以精神上“富起来”为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人民基本温饱得不到保障,对物质富裕的追求成为必然,相较之下,则对精神追求的重视不足。再者,“文化大革命”时期,“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受到全面打压”[17]169,文化事业停滞不前,人民精神发展受到阻碍,种种现实因素致使人民精神十分匮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后“两手论”把精神文明建设置于新的高度,确定“四有新人”建设目标。进入新世纪,党确立“以德治国”新的治国方略,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的战略任务,这一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
从“先富”到“共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以精神上“强起来”为主要内容。进入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明确了新的历史方位。一方面,主要矛盾的转变明示我们,精神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关系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另一方面,“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更加强大的精神动力。由此可知,允许一部分人精神上先富起来,即局部性、散状式的精神富裕已经不适合人民的新需求与社会的新发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即精神上“强起来”才是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正确选择与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工作,开展“四史教育”,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力求精神共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内容、新方向、新理念。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态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强精神建设,增强精神力量,提高精神水平,需要从价值主体、内容要素和推进层次入手,探索把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态,为推进精神共富提供抓手。
(一)全成员参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8]142,提纲挈领地表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富裕。
首先,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为了人民的富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2]46新时代以来,凡是“共同富裕”所论之处,必能看见“人民”这一主体标识与价值指向,这是人民主体地位的体现,是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生动诠释。众所周知,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不变初心,现如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已然成为人民“幸福”之基本要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确立“人民至上”的工作导向是现实之必然。换言之,人民立场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何以可能的根本立场,是党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首要基点与价值向导,提出、推进并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党的初心相契合、相呼应、相贯通。
其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依靠人民的富裕,必须坚持共建共享。“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2]70,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纸上谈兵,其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依靠党谋大局、把方向,更需要全体人民的切身实践;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空中楼阁,并非不可抵达的美好幻境,而是全体人民集智聚力,共建共创,进而应然也必然实现的美好愿景。正所谓“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全体人民的能动参与是精神生活得以共富的动力之源,“勤劳致富,智慧致富”的理念与方法同样是精神建设的锦囊。没有人民智慧与力量的加持,精神共富将寸步难行,只有全体社会成员躬身入局、衔石填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才能如期如质实现。
最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造福人民的富裕,必须坚持普惠共享。“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2]46,在结果导向的视角下,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就是人民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极大提升[19]11-16。安全感是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呈现样态的基本表现,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基点,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充盈消除了精神追求的后顾之忧,使人们自发自觉地追求精神富足成为可能;获得感是人们在获取精神产品与享受精神服务之后的充实感,需要精神文化供给真正用之于民;幸福感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高级呈现,意指人民在创造、享受精神文化资源,进行精神领悟、交往之后拥有的满足愉悦之感,即优质的情绪体验。
(二)全方位联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18]117,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推进这一伟大工程需要实现“精神需求—精神生产—精神消费”三个环节的有序衔接与互动。
第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精神需求多样的富裕。“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6]14,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人民精神需求的多样性益发突显。具言之,包括知识性需求、思想性需求、审美性需求在内的多样性的人民精神需求,代表着人们对真理与技艺的需要、对善良与正义的追求、对文明与和谐的向往。其中,知识性需求是个人提升自身素养的基本需要,思想性需求与审美性需求则是个体成长需要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有机统一,是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满足全体人民对多种类、高品质精神生活的旺盛需求,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首要环节,能够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原生动力。
第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精神生产丰富的富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20]34,精神生产丰富是对精神需求多样的现实回应。精神生产丰富首先体现在精神生产力的极大增加,物质资料的丰富、精神生产时间的增多、高新科技的涌现使精神产品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而精神文化产品的充盈是精神生产丰富的直观体现,展现中国精神、彰显文化魅力、符合人民审美的各类优质创作不断产出更新,供人民选择;同时,多元主体的参与是精神生产持续丰富的有力保证,国家和社会、文艺工作者、广大人民群众分别担任领导者、先锋队、主力军的角色,合力保障精神产品的有序、高效供给,真正做到“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21]200。
第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精神消费升级的富裕。“精神消费是人们吸收各种精神产品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精神性活动”[4]64-75,随着人们对情绪体验、审美期待、感官愉悦要求的不断提高,精神消费的升级成为必然。初级的精神消费,顾名思义,就是人们获得低层次精神享受的消费,具有一次性、消遣性等特点,是“非绿色”的精神消费。而高级的精神消费以眼界、品味和修养的提升为目标,具有长远性、可发展性等特点,是可以洞明世事、启迪智慧的精神消费。另外,精神消费升级还意味着人们不再局限于对精神产品“量”的占有,而是更加注重对精神产品“质”的获取,是从“虚假消费”到“真实消费”的跳脱与跃升。
(三)全时空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18]147,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能一蹴而就,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既要打破时空界限,全面推进,也要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认识。
其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富裕。“坚持理论创新”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不仅要求我们用新的理论回应新的问题,更要求我们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进而解决问题。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党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作的理论回应,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就意味着精神生活不能止步于口中的共同富裕,而是要专注于脚下的共同富裕。同时,在推进实现精神共富的过程中,又会出现新样态、深层次的问题,阻碍“共”的范围与“富”的程度,彼时,又需要新的理论来解决困难,指导实践。概言之,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要部署“过河”的任务,又要解决“桥与船”的问题,更要奋力“抵岸”,知行统一,常进常新。
其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长期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富裕。“欲速则不达,骤进祗取亡。”“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18]146,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不能一蹴而就,人的精神发展也需要循序渐进。现阶段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处于目标提出向实践自觉的转换时期,精神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精神生产关系的调整与优化、精神生产方式的转型与升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配、监管等制度的创立完善都需要长期求索。但是,不能因为过程之漫长、道路之艰难就秉持“精神共富虚无论”。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推进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场“持久战”,只有解决好“等不得”与“急不得”的关系,保持历史耐心,逐步实现党制定的各阶段目标,才能循序渐进,稳中取胜。
其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整体性与差异性相统一的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18]142,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要注重整体,也应尊重差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之“共同”内蕴着破除时空限制的“整体性”智慧,包括人民全体参与、区域整体推进、评价指标统一等多重实践指向。但是,“整体”不是“整齐”,由于个人内在精神水平与追求不同,外在政策支持、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差异,同时同等同质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具有现实性,而应对之策是要在整体维度达到一定富裕水准后,在合理范围内允许客观差距的存在,从而实现差异可控、层次丰富、整体向好的精神生活富裕的理想状态。